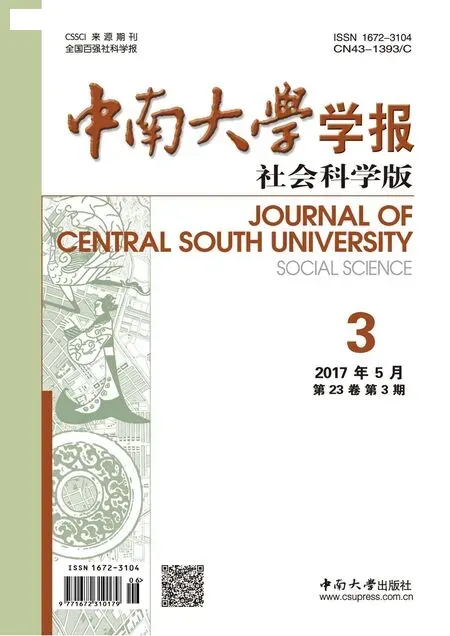恩格斯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是否一致?
方瑞
恩格斯与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是否一致?
方瑞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吉林长春,130012)
破除西方学界制造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个主义”的对立,关键在澄清“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是否一致”这一问题。基于对黑格尔哲学评价中的一致看法,马克思与恩格斯以破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为目标,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和真正规律分别运用到对社会历史领域和自然领域的研究中去,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他们始终把“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活动方式作为清除黑格尔辩证法中思辨玄想的武器,以工业和科学实验去证明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形式的正确性,从而为人类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图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把“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活动方式作为彻底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有力武器,最终得出的“马恩对立”的结论,也只能是“意识的空想”和“哲学上的怪论”。
恩格斯;马克思;黑格尔;彻底颠倒;辩证法;实践
如何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一直是学界长期争论的焦点问题。特别是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这两大流派的兴起,使得对这一问题的争论日趋尖锐,甚至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判断。无论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吕贝尔和诺曼·莱文为代表的“马克思学”者,都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给予了积极的肯定,而对恩格斯以“自然辩证法”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予以指责,认为这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辩证法扩展到自然界”。这就造成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颠倒黑格尔辩证法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形态,从而使这两种理论形态发展成两个对立的思想流派。如何破除西方学界制造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个主义”[1]的对立,关键在澄清“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是否一致”这一问题。要想真正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追问以下三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是否一致;二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路径是否矛盾;三是马克思与恩格斯何种意义上实现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澄清,以此来说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颠倒黑格尔辩证法工作的一致性,从而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提供一种合理的辩护。
一、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是否一致
由于当时黑格尔哲学有一定程度的复活,各种形式的唯心主义哲学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部分社会民主党知识分子中日益流行,恩格斯意识到有必要对他和马克思的哲学信仰予以清算。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工作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它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 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2](269)。但是,由于黑格尔试图建立一个能够完成“某种绝对真理”的唯心主义体系,使得这一革命的辩证法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样,恩格斯就深刻地向我们揭示了黑格尔哲学中出现的一对矛盾,即:革命的方法与保守体系之间的矛盾。
但是,对于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中的这一矛盾,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其中,西方学者科莱蒂就对恩格斯的这一评价给予了批评,他认为恩格斯所揭示的这一矛盾是建立在对黑格尔哲学误解的基础上的,未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所继承的革命的方法。而我国学者俞吾金教授也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神秘外壳’和‘合理内核’都是就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言的”,而“恩格斯却改换了马克思的话题,即把马克思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讨论改换为黑格尔的保守体系和革命方法的讨论”[3]。这样,无论是科莱蒂还是俞吾金教授,在他们看来,由于恩格斯与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有所不同,这就造成了二人在改造黑格尔辩证法时的路径也存在着巨大差异,从而指责恩格斯的改造工作严重背离了马克思。因此,要想澄清学界这一分歧,我们就有必要追问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评价是否一致。而这一点,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路径是否矛盾”这一问题。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诸多文本中,常常使用“神秘形式”或“神秘外壳”与“合理内核”或“合理形态”来评价黑格尔哲学。对于马克思来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无疑是其哲学的“合理内核”,因为马克思一直都有撰写一部辩证法著作的愿望,在1868年5月9日致信狄慈根写道:“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4](288)不过,由于马克思此时忙于写《资本论》,未能完成这一愿望。虽然马克思未能留下一部辩证法的著作,但是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运用了辩证法,并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对自己的辩证法进行了高度概括,以此来区分黑格尔的辩证法。这些都表明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辨证方法给予了高度重视。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哲学是处在哲学体系的“神秘形式”与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矛盾关系之中的。而这与恩格斯以“唯心主义的体系与革命的方法”之间的矛盾来指认黑格尔哲学的表述是不同的。因此,我们必须追问两个问题,一是在马克思的语境中,黑格尔哲学何以是神秘化的,是否与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体系”有必然的关联呢?二是马克思在这里所强调的辩证法是否与恩格斯的“辩证的革命方法”相一致。
对于“黑格尔哲学何以是神秘化的”这一问题,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曾经对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作出了判断,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外壳”是三段式的[5]。这就为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评价时所使用的“神秘外壳”这一说法找到了依据。即“神秘的外壳”就是指黑格尔哲学的三段式体系。而黑格尔三段式的体系何以是神秘的,马克思在谈到与黑格尔辩证法不同时,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回答:“我的阐述方法不是黑格尔的阐述方法,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而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4](280)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与黑格尔辩证法不同的关键在于他是唯物主义者,而由于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所以“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6](22)。这样就完全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使得黑格尔哲学的形式神秘化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在评价黑格尔哲学中所存在的问题时与恩格斯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并不存在“恩格斯改换马克思的话题”一说。虽然马克思没有直接指出“神秘形式”就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但是他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作为区分他与黑格尔辩证法不同的重要标志。而这一区分,就为马克思与恩格斯日后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埋下了伏笔。
虽然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指出了黑格尔哲学中的“神秘形式”,但是他们意识到,一旦剥去了这一“神秘的外壳”,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就将呈现出来。那么,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及其来源的认识,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否一致呢?我们通过对比马、恩文本,可以看出马恩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马克思与恩格斯都强调了辩证法的革命本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都是从暂时性方面去理解现存的事物和每一种既成的形式,并把辩证法的本质概括为批判的和革命的[6](22)。这与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的辨证方法的革命性质是一致的。恩格斯指认了这一方法“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 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2](269)。对于一切有关最终性质看法的否定,也就是马克思所强调的从暂时性去理解。其二,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指明了黑格尔已向我们叙述了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只是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向我们呈现的。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6](22),“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4](288)。恩格斯也认为,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做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7](463)。其三,马克思与恩格斯都认识到辩证的方法都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在他们看来,黑格尔辩证的方法之所以是神秘的,只是由于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造成的。要想去除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只需认识到这一辩证的方法只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马克思在批评黑格尔时,指出黑格尔“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其实,他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8](602),“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6](22)。恩格斯也认为辩证法“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的反映”[2](270)。这样,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评价中形成了三点共识,而这三点共识将成为他们改造黑格尔辩证法工作的基本原则。
通过以上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相关文本的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与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评价是完全一致的。虽然他们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方式来评价黑格尔哲学,但是都指明了要想拯救辩证法的合理形态,就必须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进行改造。因此,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颠倒”时,必然将破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作为其目标,把对黑格尔辩证法评价中所形成的三点共识作为其工作的基本原则。不过,为了把自觉辩证法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中拯救出来,马克思与恩格斯出于分工的考虑,从不同领域展开了“颠倒”工作。这就造成了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路径是否矛盾 ”这一问题的纷争。
二、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路径是否矛盾
基于对黑格尔哲学评价中的一致看法,马克思与恩格斯展开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工作。在这一颠倒过程中,他们清楚地意识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之所以被神秘化了,其根源就在于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体系。因此,要想拯救辩证法的合理形态,首要工作就是要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进行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通过这一唯物主义的改造,使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辩证法的三点共识得以真正呈现。
但是,由于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将辩证法运用到了社会历史领域和自然领域,这就迫使马克思与恩格斯必须从这两大领域中拯救辩证法。于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出于分工的考虑,分别从社会历史领域和自然领域展开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工作。正如恩格斯在1885年《反杜林论》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唯一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运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7](13)。这样,就为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马学者所强调的“马恩对立论”找到了理论依据。因为,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是通过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过程,以“历史辩证法”来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只是因为“他错误地跟着黑格尔把这种方法也扩大到对自然界的认识上”[9](52)。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两条颠倒路径是否矛盾”这一问题予以澄清。
要想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就必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总体评价下,对这二人的两条颠倒路径进行考察。我们知道,马克思与恩格斯在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工作中,是以破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为目标的。同时,他们也试图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三点共识运用到各自的研究领域。这样,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各自领域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方式必然是一致的,一方面,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破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干扰;另一方面,以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来反对各种形而上学的观念。
马克思从社会历史领域展开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在这一改造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无论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还是费尔巴哈的“感性的人”,都不过是现代“市民社会”的产物。要想真正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就必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感性的”“对象性”的活动方式,即: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样,马克思就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试图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和真正规律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考察中,以此来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性。马克思通过对工业生产过程的考察,向我们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指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暂时性,并且在《资本论》中,证明了黑格尔辩证法所揭示的“真正规律”的科学性。马克思指出:“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6](874)显然,在这一表述中,马克思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本身的自我否定,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暂时性;另一方面也向我们证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同样,马克思在讨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必要条件时,也向我们证明了黑格尔的质量互变规律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正确性。“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变为质的区别。”[6](357−358)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了质量互变规律可以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得以证明。而对于自然科学这一领域的研究,正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所要完成的。这样,马克思就从社会历史领域出发,破除了黑格尔的思辨玄想。并将辩证法革命性质和真正规律运用到对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中去,以此来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的特殊运动规律”。
不过,当马克思从社会历史领域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时,我们就有必要追问这一领域的完成是否意味着对黑格尔辩证法实现了真正地颠倒。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与恩格斯都指认了辩证的方法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所以,辩证的方法的来源就不只是社会历史领域,还将涉及到自然界的辩证法问题。而恩格斯正是沿着这一思路展开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进一步颠倒。
恩格斯意识到要想从自然哲学的泥潭中拯救辩证法,实现对黑格尔遗产的唯物主义的改造,就必须终止一切思辨的玄想。因为,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是一个由绝对理念产生的、辩证发展的体系,“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显然,这种把自然作为精神的产物,并通过精神逐步扬弃自然的自然哲学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自然观,其中包含了许多常识错误、虚构和幻想,必然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遭到自然科学家的厌恶。要想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改造,就必须以“实验和工业”作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2](279)。于是,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特别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等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我们证明了“自然界不是存在着,而是生成着和消逝 着”[7](415),并且直接确证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三大规律是自然界固有的规律。同时也彻底终结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即“自然界绝对不变的看法”[7](412)。这样,恩格斯就通过自然科学这一实践活动,彻底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得以确立,从而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
至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基于对黑格尔辩证法评价的一致性看法,以破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为目标,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和真正规律分别运用到对社会历史领域和自然领域的研究中去,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中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彻底终结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和自然观。这样,马克思与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路径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还是互补的。正是恩格斯这一颠倒工作的继续推进,才彻底终止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切思辨玄想,从而为人类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图景。
所以,对于恩格斯研究自然辨证法这一工作的承认,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性质的判断。恩格斯所要做的,并不是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适用范围的扩展,而是要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工作予以进一步推进。如果像西马学者那样,只承认马克思的改造工作,而否认恩格斯的改造工作,必然无法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唯物主义改造。但是,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要想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依靠“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才能彻底终止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切思辨玄想。
三、马克思与恩格斯何以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
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对黑格尔辩证法评价的一致性看法出发,以破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为目标,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和真正规律分别运用到对社会历史领域和自然领域的研究中去,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中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但是,如果马克思与恩格斯只是把辩证法的合理形式运用到不同领域,又怎么能够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呢?对这一问题的追问,也直接关系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合法性问题。
黑格尔在构造自己的世界图景时,总是“以为他是在通过思想的运动建设世界”,但是,这种建设世界的方式“只是根据绝对方法把所有人们头脑中的思想加以系统的改组和排列而已”[8](602)。这样,黑格尔所建造的世界由于缺乏对当时自然科学的细致考察,未能认识到当时自然科学研究已经转向经验和实验,从而造成其哲学体系中包含了许多常识错误、虚构和幻想。而恩格斯正是意识到了黑格尔这一缺陷,直接指出了“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2](279)。在恩格斯看来,“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8](526)。因此,恩格斯在自然领域中展开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拯救工作时,力图通过“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证明自然界是否有辩证法存在这一问题。他在《自然辩证法》中,总结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以及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通过自然科学这一实践活动,彻底改变了以往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得以确立。他指出,要想验证辩证法规律,就必须以自然界本身作为试金石。而自然科学这一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正在向我们逐步揭示自然界是一个辩证运动的过程。至此,恩格斯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彻底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出路,就是依靠“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人类实践活动方式,去证明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形式的正确性,彻底终止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一切思辨玄想。
但是,以卢卡奇为代表的西马学者,由于未能把恩格斯所强调的“工业和科学实验”理解为人类重要的实践活动方式,从而造成了对恩格斯的误解。在卢卡奇看来,虽然恩格斯以科学实验这一具体的实践活动作为中介来考察自然界是否有辩证运动规律的,但是,所谓的“工业和实验”并不是一种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实践活动,“实验恰恰是最纯粹的直观。……排除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的一切起妨碍作用的不合理因素”,而工业也“仅仅是社会的自然规律的客体,而不是其主体”。[9](213)这与马克思以社会实践中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作为其历史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去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工作是相背离的。这样,卢卡奇就把恩格斯所指出一条彻底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出路与马克思的实践观对立起来,也为日后“马恩对立论”找到了依据。
基于此,我们就有必要追问,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强调的真正的活动方式是什么?恩格斯把实验和工业的发展作为人类最重要的实践形式,以此来驳斥黑格尔辩证法中的一切思辨玄想。而马克思是否与恩格斯有着相同的认识?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真正理解“马克思与恩格斯何以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这问题,纠正“马恩对立论”的错误。
对于回答马克思关于“实验与工业”的认识问题,我们需要考察相关文本来印证他是否与恩格斯有着相同的认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工业这一实践活动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并且指明了工业与科学实验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虽然人在工业实践中是以异化形式呈现出来的,但是这种工业实践依然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不过,马克思意识到要想使人从异化形式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把科学实验与工业实践相结合,以此来为人的解放提供必要的准备。“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8](192−193)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和自然科学是人的本质力量展现的最为重要的实践活动。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针对一些人把“工业和自然科学”排除在历史之外进行了批评,指出如果将历史与工业和自然科学分开,就会导致“历史的诞生地不是地上的粗糙的物质生产,而是天上的迷蒙的云兴雾聚之处”[8](350−351)。而对“工业和实验”的重视,并不仅仅局限于早期文本,在马克思的成熟文本《资本论》中也有所体现。马克思还专门拿他的研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进行了比较[6](8)。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工业和科学实验才是人类认识现实历史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形式。
如果以马克思本人的相关文本来论证与恩格斯关于“工业与实验”认识的一致性,依然不能说明这一问题,那么,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工业和实验”的一致性看法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对于哲学上所谓的“‘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神秘莫测的崇高功业’的问题”,可以“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8](528−529)显然,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这里明确表明了工业的发展可以终止哲学的玄想。而这一认识与恩格斯所强调的通过实验和工业驳斥“哲学上的怪论”是一致的。
所以,以上文本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工业和实验”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都将工业和实验看作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实践形式,以工业和科学实验去证明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形式的正确性,以工业和实验这一具体实践活动去彻底终止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哲学怪论”。这样,马克思与恩格斯就以“工业和实验”这一重要的活动方式,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
因此,要想对“马恩对立论”者们进行反驳,就必须对马克思与恩格斯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予以澄清。从马克思与恩格斯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工作可以看出,他们以破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为目标,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和真正规律分别运用到对社会历史领域和自然领域的研究中去,在两条不同的路径中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为了实现这一彻底颠倒,他们始终把“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活动方式作为清除黑格尔辩证法中思辨玄想的武器,以工业和科学实验去证明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合理形式的正确性,从而为人类确立了科学的世界图景。如果我们不能以真正的实践活动方式作为基础,就无法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颠倒,最终也只能陷入到唯心主义的直观之中,导致“意识的空想”和“哲学上的怪论”。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缺乏对马克思与恩格斯这一颠倒工作的细致考察,更没有把“工业和科学实验”这一重要的活动方式作为彻底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有力武器,最终得出的“马恩对立”的结论,也只能是“意识的空想”和“哲学上的怪论”。
[1] 诺曼·莱文. 不同的路径: 马克思主义与恩格斯主义中的黑格尔[M]. 臧峰宇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3.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3] 俞吾金. 恩格斯如何看待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J]. 云南大学学报, 2005(3): 3−21.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 列宁全集·第58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0: 60.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9] 格奥尔格·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杜章智, 任立, 燕宏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Is Engels’ reversal of Hegel’s dialectics the same as Marx’s reversal ?
FANG Rui
(Center for Fundamentals of Philosophy &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ety,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To eliminate “the opposition of Marxism and Engelsism” which is brought about by western academic world, the key is to clarify whether Engels’ reversal of Hegel’s dialectics is the same as Marx’s. Based on their agreement on the evaluation of Hegel’s philosophy, Marx and Engels aim at breaking down Hegel’s idealism system, applying the revolutionary nature and true rules of Hegel’s dialectics to the research of social-historical area and nature domai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complete reversal of Hegel’s dialectics. They always treat the important mode of activities,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 as the weapon to eliminate the speculative illusion in Hegel’s dialectics. Marx and Engels prove the correctness of reasonable form in Hegel’s dialectics with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world vision for humanity. Western Marxists fail to use the important mode of activities,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experiment, as the powerful weapon to reverse Hegel’s dialectics, therefore the conclusion of opposition of Marx and Engels is just “mental fantasy” or “philosophical absurd”.
Engels; Marx; Hegel; complete reversal; dialectics; practice
[编辑: 颜关明]
B02
A
1672-3104(2017)03−0007−06
2016−09−10;
2017−01−03
201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本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16CKS001)
方瑞(1987−),男,内蒙古包头人,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哲学基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