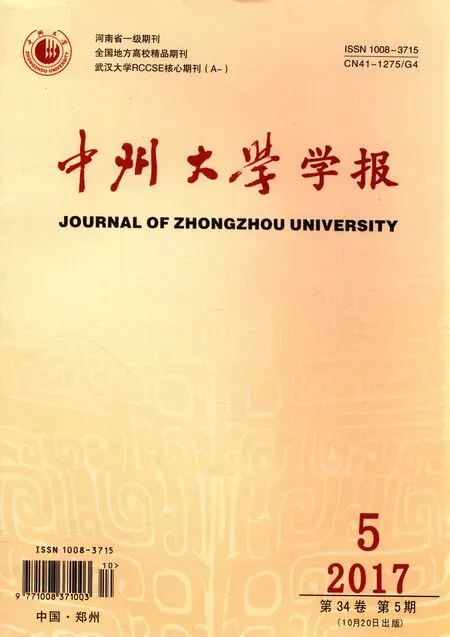看吧,“我们”的这个世界
——伯恩哈德《声音模仿者》与墨白《癫狂艺术家》比较研究
杨文臣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看吧,“我们”的这个世界
——伯恩哈德《声音模仿者》与墨白《癫狂艺术家》比较研究
杨文臣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墨白的《癫狂艺术家》和伯恩哈德的《声音模仿者》都以“我们”为叙述者,用“止于表面”的讲述,把世人司空见惯的世界撕开一个缺口,极致地呈现出这个世界的荒诞和残酷。不同于伯恩哈德大量使用夸张、变形等现代主义手法,墨白在《癫狂艺术家》中采用了写实风格,因为那些罪恶、苦难和荒诞,就真实地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上演过。隐而不察之物,需要艺术的照鉴;而对于本就血腥残酷的历史和现实,艺术的介入反而有可能导致弱化。
墨白;伯恩哈德;《癫狂艺术家》;《声音模仿者》
在奥地利作家伯恩哈德的系列短篇小说集《声音模仿者》[1]和中国作家墨白的系列短篇小说集《癫狂艺术家》[2]中,出现了一个很罕见的叙述者——“我们”。当然,严格地说,“我们”不能同时开口,叙述者只能是一个人,但由于说话的这一个始终不显露任何个体特征,他可以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因而笔者把“我们”作为小说的叙述者。众所周知,相对于第三人称叙事,第一人称“我”更容易引发读者的移情,更容易营造出强烈的现场感。不过,第一人称也有一个劣势,那就是无论在阅读中读者怎样认同于叙述者,无论叙述者的口吻多么真诚,在阅读之后,读者都可能离开叙述者,并以“主观性”为由对其加以拒绝。相比之下,第三人称叙事却较少招来“主观性”的指责,尽管本质上并无不同——无论哪种人称的叙事,都是作家的构建,都无法摆脱主观性的缠绕。从这个角度来说,伯恩哈德和墨白以“我们”的名义讲述故事①,既赢得了第一人称的那种现场感,又避开了“主观性”的指责,无疑是一种相当高明的策略。
当然,二人选择“我们”作为叙述者,意图不仅于此。因为集体身份的限制,叙述者的讲述只能“止于表面”②[3]141,既不能在个体好奇心的推动下对事件深入追索,也不能对事件和人物展开长篇大论。不过,伯恩哈德和墨白却巧妙地利用止于表面的讲述,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世界撕开一个缺口,面对这个缺口我们如临深渊,一股森冷之气瞬间袭遍全身……我们恍若从一个做了很久的迷梦中惊醒!再环顾四周,看到的是影子一般到处游走的人们,醉生梦死、麻木不仁又自以为是、执迷不悟。这就是我们的世界!
一、《声音模仿者》:醒世寓言集
“声音模仿者”成功地模仿了许多著名人物的讲话,“我们”要求他模仿下自己的声音,他却回答说办不到。两位哥廷根大学教授登上高山之巅,先后用观景望远镜眺望美景,一位被美景征服,另一位却在发出一声刺耳的大叫后倒地而亡。这是伯恩哈德在《声音模仿者》和《美丽景色》中分别讲述的故事。
模仿自己的声音是最简单不过的事情,无需任何技法,把声音发出来就行了,但“声音模仿者”说办不到,因为他根本没有自己的声音。这个世界上,触目皆是“声音模仿者”,人云亦云,毫无思想。代表著名人物的两位大学教授是“声音模仿者们”模仿的对象,面对同一个世界,他们看到了截然不同的景观。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性话语几成陈词滥调的今天,这个故事的象征意味不难揣明。不过,睹世伤情的那位死去了,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人们只能接受年纪更大、学问更高因而也更具权威的那位教授的说法:美轮美奂,歌舞升平!
不过既便明察世事者不死,也会被送进疯人院。《断言》中的那个奥格斯堡人,就因为坚持歌德去世前最后的话是颇为消沉的“就这么多了”而不是鼓舞人心的“更多的光”,惹恼了公众,被送进疯人院。将其送进疯人院的那位医生还受到了当局表彰,荣获法兰克福市歌德纪念章。说真话或持异见者被迫害放逐,而维护谎言或权威观念者却被视为英雄。《放弃》中的音乐家、画家和自然科学家倒是没有被送进疯人院,他们三个选择了自杀,“因为这个世界不再拥有与他们以及他们的艺术和科学相适应的接受器官和接受能力了”。《不谙世情》中的天才艺术家同样因为没有人能读懂他的东西而投湖自尽,“在死者的尸体被打捞出来之后,当地报纸关于这位未受到赏识的人发表了一则简短的消息,着重指出他不谙世情。”
人们的接受和理解能力何以会退化?“世情”何以会变成这样?人们何以如此抵触“离经叛道”?无论他们自己认同的“道”是否合理。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专制权力的规训。
《比萨和威尼斯》中,两位市长预谋调换下地标建筑,将比萨斜塔迁到威尼斯,将威尼斯钟楼迁到比萨。他们没有成功,预谋泄露后被双双送进疯人院。“意大利当局这件事办得干净利落,秘而不宣。” 变革现有秩序是绝不允许的,不仅变革行动会遭到无情的镇压(“干净利落”),变革思想也不允许流传(“秘而不宣”)。《归来》中的那位叛逆的艺术家也被送进了疯人院,他热爱的故乡用仇恨和诽谤迎接他的归来。相比之下,《难以设想》中的剧作家要幸运得多,不仅得到了认可,作品还在当时最好的一家剧院上演。作者特别强调,被认为最好并不等于确实是最好。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剧作家在看过演出后,竟然控告剧院经理,要求交还他的剧,同时还要求观众把看到的一切退还给他。法院没有审理他这种“难以设想”的控告,反而把他送进了疯人院。而我们知道,剧作家之所以提出这种控告,是因为他的作品已被“最好的剧院”涂改得面目全非。
又是疯人院!这不禁让我们想起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阐发的命题:疯狂是权力话语和医学话语合谋对异己话语进行压制的产物。《没有心灵》中,医生只对身体感兴趣,某学者因所谓古怪异常被送进了医院,做完身体检查后,他问医生:“那么心灵呢?”医生马上回答:闭嘴!小说就此结束,可以想象,这位重视心灵的学者也终将被送进疯人院。权力对人的规训不只发生在医院中,它无处不在。《九百九十八次》中,讲述了一个高中生在弗洛里茨多尔夫桥上走了九百九十八次后昏倒在地,原因是上学路上被“对学校的恐惧”所控制。我们不知道他在学校里经历了怎样的心灵压制,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在学校之外他也不能获得解脱。昏倒后他没有被送往医院,而是被送到弗洛里茨多尔夫尖形广场的警察值勤处——“尖形”是权力监控一切的空间象征。
放逐了思想者,清除了思想杂音,扼杀了心灵和自由,世界就变成了一个秩序井然的世界,也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人不重要,重要的是秩序。如《邮局》,讲述了生活中一个很普通的事件,“我们”的母亲去世后数年里,邮局仍继续将写着她姓名和地址的信件投递给她,而没有注意到她的去世。似乎没有理由去指责邮局,他们的职责是投递信件,客户的生死与他们无关。我们都有自己的职业,都像邮局一样行使职责,把他人当作管理或服务的对象,这个世界也因而像机器一样有条不紊地运转。可是,谁来关注人本身,生命关怀和人文关怀该如何安放?《决定》中,官员在城市遭受地震后,下令用机器把那座完全坍塌的饭店推平,而不是清除瓦砾,搜救幸存者。由于被埋的几百人的叫喊声实在不能让人心安,他进一步指示,封锁饭店所在地段直至喊叫声消失。这位官员的做法是为了给国家节约高额的搜救费用以及将来赡养伤者的巨大开支,从大局角度来看,也不失为忠于职责,自然也得到了国家的肯定,仕途升迁指日可待!《议会里的发问》中,面对中小学生自杀率比上年增加一倍的问题,萨尔茨堡州议会的一位议员关注的是:两年间自杀地点的变化——去年孩子们多跳河或跳下山岗,而今年一个工人家庭的孩子从华丽的洪堡平台上跳下——是否表明工人阶级已经上升到有产阶级?他的答案是肯定的。在他看来,一个城市被评价得越是美丽,自杀率就越高。所以,一切都很好!
死亡都能成为进步的证据,还有什么能阻止对这个世界做出至高的评价?在权力话语营造的尽善尽美的幻象下,苦难不是消失了,而是越来越多,只不过人们失去了感受和言说苦难的能力。《两张纸条》的图书馆员和猎手自杀了,他们留下纸条宣称不能再忍受人们遭受的不幸。可以想见,在“声音模仿者们”的眼中,他们不是怪人,就是发疯了。
二、《癫狂艺术家》:走进历史深处
墨白非常欣赏现代主义文学,对卡夫卡有着极高的评价,作为先锋小说家,他的很多作品中也不乏现代主义技法。但在《癫狂艺术家》中,他回归了写实风格。因为,伯恩哈德借助于夸张、变形等手法讲述的罪恶、苦难和荒诞,就真实地在我们这片土地上上演过,单单讲述出来就足以震骇人心了。隐而不察之物,需要艺术的照鉴;而对于本就血腥残酷的历史和现实,艺术的介入反而有可能导致弱化。
在《首长》中,墨白讲述了一次邂逅。在锡铁山以南40公里处的万丈盐桥上,“我们”见到了寻找出走妻子的首长一行。健谈的警卫员告诉 “我们”,首长的妻子是个貌美如花的高中生,以女兵的名义被征,召到了边疆,然后被强行“分配”给了大自己几十岁的首长做妻子,结婚那天她就疯了,之后多次出走。十万大军屯垦戍边,数万女兵报国赴疆,历史留给后人的是这样荡气回肠的篇章,没人知道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在我们的卡车沿着光滑如镜的万丈盐桥离开时,我们又朝正在消失的海市蜃楼看了一眼。我们知道,在那美丽虚幻的景象下面,就是广阔的受风沙侵蚀的盐湖。(墨白:《首长》)
行走在大漠深处的“我们”不期闯入了历史的深处,否则我们可能永远无从得知“海市蜃楼”伪饰下的历史是什么样子。
“我们”是谁?在不同的故事中,“我们”的身份各有不同,《按摩师》中“我们”是盲人按摩师;《追捕者》中,“我们”是刑侦队员;《流放地》中,“我们”是勘测队员;还有一些篇章中,“我们”似乎是带有采风意向的游客……不过,“我们”的声音却是一致的:“我们”总是结识到某些奇怪的人和事,然后引出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让“我们”悚栗不已,并沉陷在深深的怀疑和思索中。就对历史的认知而言,“我们”和芸芸众生一样,被历史的假象所蒙蔽,即便曾听说过一些事情,也如同听到一个遥远的神话,无关于己并抛之脑后。但“我们”又不同于芸芸众生,因为“我们”总是能邂逅到真实的历史。
伯恩哈德在《国王陵墓》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二战以来的某个时间,因为一个克拉考人在瓦维尔山国王陵墓听到从波兰末代国王的石棺里传出了国王颂歌,越来越多的人前来参观陵墓并像他一样倾听国王颂歌。当局逮捕了这个男子,并封闭了瓦维尔山,对每个上过山的人严格审查。现在瓦维尔山上的国王陵墓早就重新开放了,没有人还记得上述这段往事。国王颂歌的影射意味,我们在此姑且不论。当局曾经试图抹除真相、封锁历史,不惜诉诸暴力,现在解禁了,没有了暴力的震慑,可人们却失去了追索真相的兴趣,历史已被遗忘。或许正是由于人们如此善于遗忘,当局才重新开放了国王陵墓。和被迫缄口相比,主动遗忘更可怕!
事实上,历史并未走远,也是无法抹除的。在墨白的小说中,“我们”总能与历史不期而遇。甚至可以说,历史一直在发出声音——就像《护士》中那位女士的讲述每天都在进行,只是,以保洁员和年轻情侣为代表的庸众群氓们对此听而不闻,他们已变成伯恩哈德笔下的佩拉斯特人。在《佩拉斯特》中,“我们”想知道佩拉斯特那些破败的宫殿属于谁,历史对此没有记载,但被问到的人总是笑笑便转身离去。原来,佩拉斯特已经没有了正常人,他们都是由国家定期供给“食品”的精神癫狂者。
《首长》《护士》《枪手》《弹孔》《陪法场的人》等,墨白椎心泣血地讲述着猖狂的权力曾经如何肆无忌惮地剥夺人的生命,践踏人的自由和尊严,曾经如何以崇高的名义犯下最卑劣最暴虐的罪行。这些作品中的故事之悲惨和令人发指,让人不忍转述。我们会认定伯恩哈德的《两张纸条》使用了夸张的手法,图书馆员和猎手只是作者虚构出来的符号式人物,但在墨白的《记者》中,他们进入了我们的历史。那个姓鲁的新闻记者,不忍面对60年代初饿殍遍地的惨象,自绝于鸡公山一座荒凉的别墅中,死前给后人留下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影像和文字资料,还有血泪斑斑的控诉——用血在当时的一段信口雌黄歌功颂德的社论文字上写下了“谎言”两个字。《记者》带给我们的震撼,远远超出了《两张纸条》。
有人会不耐烦,何必纠缠于过去?为了不变成佩拉斯特人,我们必须铭记历史。一方面,长期匍匐于权力之下造成的奴性,依然根深蒂固地盘踞在我们的人格中。《纪念碑》的故事背景是1994年发生在克拉玛依的那场大火。“孩子们,不要动,让领导们先走!”这句耻辱的话出自一位女领导之口,她喊出这句话时是否清楚地意识到她是领导中的一员,或者说,她是为了作为领导的自己活命还是为了她的领导活命,我们不得而知,没有相关报导。但我们可以想象,这句话也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会场工作人员或普通教师口中喊出来。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场合,发言、拍照、宴会、坐车等等,我们都是“让领导先……”这几乎成了我们的下意识,即便有时领导不是我们的领导,我们也会“让领导先……”如果没有无处不在的深入骨髓的对权力的膜拜,可能会有夺路而逃者,但不会有女领导那般极致丑陋的表演。我们并没有真正从那个丧失精神自我的年代里走出来,所以墨白把“心灵的自省与自救”[4]17作为文学的首要使命。另一方面,权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敛起了过去那种明火执仗的嚣张气焰,但依然高高在上惟我独尊,依然在压制着民主和自由。“我们”的老师奔走多年最终没有达成心愿,旨在警世的纪念碑最终没有树立起来,甚至“我们”用原盐浇筑的那座暂时的纪念碑也因当局不予批准而无处安放,没有与世人照面便很快融化了。
到了第二年的十二月八日,那座雪白的纪念碑已经变得千疮百孔,我们老师雕刻在底层上的那些浮雕已经面目全非。
或许,比纪念碑融化得更快的,是人们对这件事遗忘的速度——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墨白:《纪念碑》)
三、结语
责之愈切,爱之愈深。无论伯恩哈德还是墨白,都没有放弃对世界、对人性的信念。伯恩哈德的《在女人沟》是《声音模仿者》中少有的“温暖”的篇章。“我们”在奥拉赫河谷碰到了一个沉默的男子,后者在聊天时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他在寻觅一个妻子,“我们”于是恶作剧地怂恿他半夜三更去一个叫女人沟的不见阳光的地方,那里住着一个完全残疾、酷爱动物的老女人。让我们意外的是,那男子一去不回,十年后从沟里出来和那位女人在教堂里成了亲,然后又回到沟里住了十年没有露面,据说他们生活得很幸福。
墨白《癫狂艺术家》中也有“温暖”的故事,并与伯恩哈德相仿,他把故事空间安放在了遥远的西域。在那里,麦吉侬一生都在唱着十二木卡姆,寻找情人阿依古丽,后者十五岁时跟随父亲去遥远的麦加朝觐一去不回,麦吉侬因而成为人们心中忠于爱情的偶像(《寻找歌手》);在那里,有位老人几十年来执着地用坎土镘在叶尔羌河畔的胡杨林中挖掘,他在寻找因河水漫溢而失去了标记的妻子的坟茔,他答应过那位薄命的上海女子,要把她带回老家去,他要兑现自己的诺言(《胡杨林》);在那里,沙吾尔·芒力克老人活得笃正坚忍,死得从容安详(《葬礼》);在那里,银匠父子一生都在流浪,跋山涉水寻找亲人,备受当地人尊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间谍罪”显得那样地鄙琐无聊……
笔者之所以给温暖加上引号,是因为可以感受到伯恩哈德和墨白讲述上述故事时的忧伤,即便前者摆出不动声色的姿态。墨白在《胡杨林》的结尾写道:
我们站在叶尔羌河畔,注视着倒映在河水里的胡杨树,那被河水摇曳着的金黄色,使我们突然萌生了一种遥远的孤独。
之所以孤独,是因为胡杨林之外,大漠之外,美好的人性已不复存在。正如席勒所说:“在一个污浊纷乱的时代,诗要追慕自然、表现理想,不能不是感伤的。”[5]165-166这也是墨白和伯恩哈德的故事空间设置的深意所在。相比伯恩哈德,墨白要温和一些。伯恩哈德的“我们”多扮演《在女人沟》中的角色,以反面形象参与到故事中;而墨白的“我们”,则多作为有良知的见证者出现,吁请读者和“我们”一起思考、前行。
在戈壁的深处,在这黄昏来临的夜晚,我们感受到了生命与灵魂的歌唱,麦吉侬,在你那混合了热血和泪水时而悲壮高昂时而低迷婉转的歌声里,终于让我们找回了前往的方向。”(墨白:《寻找歌手》)
是的,只要我们勇于反思历史、省察自身,只要我们找回前行的方向,这个世界就还有希望。
注释:
①虽然两部集子都各有一些作品叙述者没有亮出“我们”的身份,但这些作品与其他作品叙述者的声音是一致的,一篇篇连续读下来,在读者的阅读感受中,“我们”就不断地从一篇迁转到下一篇,成为了整部集子共同的叙述者。
②戴维·洛奇把“止于表面”视为小说艺术手法之一,认为“文本拒绝评议故事人物或情节,拒绝给读者提供明确的指引以供衡量角色时思考——许多读者会颇受这类文本的困扰;可是,这毫无疑问也是故事的力量所在,是它吸引人的特点。”
[1]〔奥〕伯恩哈德.声音模仿者[M].马文韬,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
[2]墨白.癫狂艺术家[M].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
[3]〔英〕戴维·洛奇.小说的艺术[M].卢丽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4]墨白.我为什么而动容[C]//杨文臣.墨白研究.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5]〔德〕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张玉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刘海燕)
Look,theWorldinWhichWeareLiving——A Comparative Study of Bernhard’sVoiceImitatorand Mo Bai’sMadArtist
YANG Wen-ch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 Litera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Both Bernhard’sVoiceImitatorand Mo Bai’sMadArtistuse “we” as the narrator, and they use the “surface” narrative statement to give fully expression of the absurd and cruel world. Different from Bernhard’s extensive use of modernist technique, such as exaggeration and deformation, Mo Bai adopts realistic method inMadArtist, because the evils,sufferings and absurdities are truly happened on our land.For those hidden cannot be seen, they need to be identified by the art. As for the bloody cruel history and reality, the art of intervention may lead to weakening.
Mo Bai; Bernhard;MadArtist;VoiceImitator
2017-08-05
杨文臣(1980—),男,山东兖州人,文学博士,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批评。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06
I206
A
1008-3715(2017)05-0022-05
—— 《印象:我所认识的墨白》编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