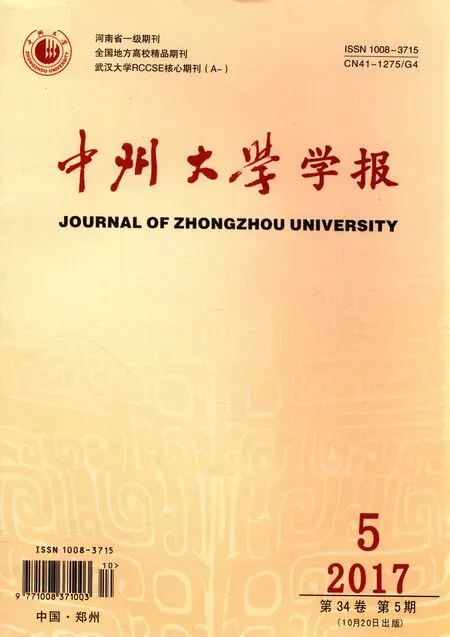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
——对虚拟现实技术的传播价值及其走向的一种理论思考
祁 涛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
——对虚拟现实技术的传播价值及其走向的一种理论思考
祁 涛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从人类传播发展史的总体状况来看,为了克服时空等诸多局限,传播形态经历了由面对面的社会现实交往向非现实交往的演变,并自照相术出现后努力向模拟社会现实交往的方向转变。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与发展,为实现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提供了可能,这将是一种以视像传播为基础、以身体在线为特征、以全感官参与为样态、以身临其境为体验的传播形态。正是对模拟现实交往的追求决定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也规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虚拟现实;现实交往;传播形态
传播形态的演变是由理论设想指导的,而理论设想体现了人类对理想传播状态的欲求。目前传播理论设想的即时、互动、全媒体化等要素已在网络传播中全部实现,传播要素之间的重新组合可能会产生巨大的能量,但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形态在理论空间中并没有找到位置。仅仅从传播要素层面来理解传播的理论设想,在互联网络快速发展并且全面渗透经济社会生活的今天,传播形态不会出现革命性的变化。从总体视角来看,以往人类传播形态的演变过程是扬弃社会现实交往模式,发展非社会现实交往模式,以释放传播能量,克服时空等诸多局限。现代传播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在把地球村落化的同时,其即时、互动和全媒体化的特点使得非社会现实交往转变为模拟现实交往的传播形态成为了可能。因此,未来传播形态的变革方向当是实现对社会现实交往形态的全方位模拟。
虚拟现实(VR/AR/MR)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当是传播向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形态转变的重要一步,也预示着人类传播形态演变的趋势和走向。但是,目前对虚拟现实技术的讨论,多是集中于其在军事、新闻、教育等部分领域的具体应用。虽然杭云、苏宝华[1]讨论了虚拟现实技术产生的沉浸式传播体验,史安斌、张耀忠[2]讨论了其引发的“拟像”与“超真实危机”,喻国明、谌椿、王佳宁[3]提出VR可以视为全新的未来媒介的主流形态,但是截至目前,还没有人从传播史的角度审视虚拟现实技术对人类传播形态演变的价值,从而也限制了认识虚拟现实技术的价值与发展走向的眼界。正如卢卡奇所说:“只有在把这种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现实的认识。”[4]笔者在此不揣冒昧,想从人类传播发展史的总体性中为虚拟现实技术对人类传播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的影响做出比较清晰的描绘。
一、社会现实交往与非社会现实交往传播形态的演变
按照杨保军教授的说法,“人类传播活动与人类是共生的,不存在哪个在先哪个在后的问题,是一种互生互动性的历史关系”[5]。在与人类相伴而生的传播活动中,媒介决定着传播形态,“因为对人的组合与行动的尺度和形态,媒介正发挥着塑造和控制的作用”[6]34。据此,麦克鲁汉将人类传播分为口头传播阶段、书面和印刷传播阶段、电子传播阶段;威尔伯·施拉姆将之划分为前语言传播、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五个阶段;黄旦将之分为口头媒介、书写媒介、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阶段。时期划分大同小异,描述异曲同工,主要的理论概念也已为人所熟知。笔者重提这一话题,意在从新的视角梳理这一过程,主要感兴趣的问题是,在传播形态演进的过程中,人类引入这些媒介,体现了何种传播欲求? 这对传播形态的变化意味着什么?
在人类传播史上,基础的传播形态是口语传播,它主要体现为面对面的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直接交往。它的特征是以口语交流为基础,以身体在场为要求,以全部感官的参与为样态,以即时互动为优势。一般认为,口语传播时代大约从36000年前语言产生到公元前3000年文字出现。当然,在当代社会,口语传播也是基本的交流模式。人类学家记载了原始村落人在集市、汲水处、饭市等场所进行信息交流的情况;历史文献记录了苏格拉底辩论和古希腊、古罗马的政治集会,还发现了游吟诗人、新闻叫喊者等职业。这种基于现实交往形态的传播,产生的是具体而丰富的生活经验,被许多学者视为理想的传播状态。伊尼斯认为,口头传统“涵义鲜活而富有弹性”[7]。萨丕尔发现,“许多原始的语言,形式丰富,有充沛的表达潜力,足以使现代文明人的语言黯然失色”[8]。
虽然许多人怀念或赞美社会现实交往的优势,但口语传播和现实交流向文字传播造就的非现实交往形态转变不可避免。伊尼斯指出,在人口稠密的地区,“时间的世界超越了记忆中的物体的范围,空间的世界超越了熟悉的地方的范围”[9],因而需要文字记载。将实物符号化的口语,虽然通过将传播对象化为语音而节约了传播成本,但是其对于身体的依赖,既不能将声音携带的信息延后,也不能传给不见面的人。因此,屈原疑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孔子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①。文字实现了语言符号的体外化,做到了使信息在空间上传之广远和在时间上传之久远。它既可使信息从中央直达边疆,也可使苏格拉底的辩论流传至21世纪。但是文字功能发挥的基础,是使传播摆脱对身体的依赖,使视觉与其他感觉分离,人们需要将意旨写成文字通过纸张传送,接受者则需要在与传播者隔离的情况下阅读文字、解码释义。
文字的应用标志着人类传播从部分社会现实交往中退却,向非社会现实交往迈进,并沿着该路径加快信息的生产和传送。文字传播面临着复制困难,人类遂发明了印刷术。首先,印刷加快了复制速度。中世纪抄书人在羊皮纸上抄《圣经》,10—15个月才能抄完,而谷登堡版《圣经》从出版到15世纪末,印制超过了2亿册,人们遂从在教堂里听牧师讲道变成了可以独自阅读领会。二是降低了印刷成本。“在13世纪初,为一本薄薄的手抄书支付的工资就相当于现在的3000美元,这是送给一位法国公主的生日礼物”[10]13,而印刷术出现初期,书籍成本就可以下降1/4。阅读成为普通人的生活内容。三是提高了准确性。在手抄时代,重要如英国大宪章,每年需要在英格兰各郡通读两次,但是人们很快便对哪个版本为真陷入了争论。印刷术的优势则是可重复性。印刷术和纸张的工业化,导致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由此推动了思想的普及。人们进一步改进了印刷机,发明了电报机,使欧洲从中世纪无文化的社会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型,阅读成为评判社会智力水准的根本标准。
人类依靠文字和印刷技术摆脱了社会现实交往的时空局限,同时更想摆脱文字传播设置的去社会现实交往的藩篱。英国人塔尔伯特想把瑞士风景经久不退地印在纸上,发明了照相术,标志着图像时代的来临;美国人贝尔为了实现不用出门也能交谈的目标,为了破除发电报必须先拟定文字的不足,发明了电话,塑造了一种亲近的交往形式;爱迪生制造“留像机”的冲动,推动了“可以把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生动活跃的语言和各种人物形象,以及自然界和生活中的真实情况,直接让观众看到影像和听到声音”的电影的出现。[11]人们期望声音的传播能够跨越无限的空间障碍,从而发明了广播;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电视,则是想通过声像一体化而创造出联觉的媒介,让人们看到真实的、动态的图像。作为可用所有传播要素互相连接的互联网,则满足了人们对于传播的即时、互动和全媒体化的想象。这些传播形态,在压缩了时间、消灭了空间的同时,更希望直观地再现现实,获得更多与身体相关的信息。
按照麦克鲁汉的描述,西方媒介的演变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他们“一直在一种徐缓的技术爆炸中被持续不断地塑造着,这一技术爆炸过程已经延续了2500年以上。然而,从电报问世之日起,西方人却开始经历了一种内爆的过程。他们突然以尼采似的漫不经心的态度,开始倒着放映过去2500年这部电影”[6]333。也可以说,从传播形态演变史的角度来看,从照相术出现引入图像开始,人类的传播形态同样发生了一个大的转折。在照相术出现之前,传播技术引导传播形态向非社会现实交往状态演变,以求克服交流障碍;照相术出现之后,传播技术则致力于模拟现实交往形态,目标是不断接近和重现社会现实交往状态,“借助电力媒介,我们到处恢复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仿佛以最小的村落尺度恢复了这种关系”。[6]315当然,这种“恢复”只是一种不完全的恢复,只是在文字传播的基础上加上了图像,在声光技术支持下引入了声音和视频,即使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互联网络综合了所有的传播介质,它们距离社会现实交往的传播形态依然有着明显的距离——它们往往没有社会现实交往的真实感,缺少对传播信息的直观的体验感,不能实现所有感官的同时参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虽然其传播价值仅仅展现出冰山一角,但是“从身体姿势到触控、手势,到语音,到全息投影、脑电波,虚拟现实将变得真正像现实那样可以感受和触摸”[12]。根据虚拟现实技术演进的状态来判断,它将为人类解决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的欲求提供技术支持,引导人类交流进入模拟现实交往时代。这种模拟现实交往与口语传播不同,它在突破时空局限的基础上,以视像传播为技术条件,以身体在线为特征,以全部感官的参与为样态,以身临其境为体验。这将是一种全仿真式的传播(见图1)。

图1 全仿真式传播形态
二、虚拟现实技术与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
审视人类传播形态演进的历史,我们发现,虚拟现实(VR/AR/MR)作为传媒场域应用前景广泛的技术,在满足信息可到达人类欲求的基础上,提供了实现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的可能性。正是对这种传播形态的追求决定了虚拟现实技术的出现,也规定了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实上,“虚拟现实”概念的提出者杰伦·拉尼尔就指出,虚拟现实技术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分享想象,生活在一个可以互相表达图像和听觉的世界”[13]。为此,我们不能仅仅将其视为利用计算机生成的一种模拟环境,并通过多种传感设备使用户沉浸到该环境中去的人机交互系统,而是将其与互联网技术结合在一起,看作是传播信息、建立关系的载体。它将“以更加丰富的手段、更为精准细腻的技术复制着世界,从而在新的界面层次上满足着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与感受,并打开了通向虚拟世界的大门”[3]。那么,虚拟现实技术能够为模拟现实交往提供什么样的技术支撑,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将会是何种状态? 如上文所述,虚拟现实通过综合3D建模、立体传感、图形制作和网络传输等技术,可以构建以视像传播为基础、以身体在线为特征、以全部的感官参与为样态、以身临其境为体验的模拟现实交往形态。这是一种与面对面交流极为接近的传播状态,虽然与之也有明显的不同。
1.虚拟现实技术以视像传播为基础
虚拟现实技术可以为交流者提供实时传送的3D/多维图像,这些图像具有超高清晰度,拥有立体视感。在人的层面,虚拟现实技术生产的影像既能够展示人的形体和声音,也能够展示人的表情,甚至“清晰得连呼吸都能感受得到”[14]。在物的层面,高清立体的影像能够提供360°的现场图像,如2016年“两会”期间新浪网推出的《人民大会堂全景巡游》,网友可以通过手机角度的变换,从不同角色、不同位置体验会场内部的视角感受。以视像传播为基础,虚拟现实摆脱了场域的限制,同时会产生高清效果和可制作效应。在现实交往中,距离会降低清晰度,而影像则可以通过无死角的特写镜头,看清现场的每一个表现,实现鲍德里亚所说的比真实还真实,即超真实。它也可以脱离现场的不可复制性,使受众既可以看到同步的交流过程,也可以看到已经发生过的交流状况,还可以体验人们未曾去过的旅游景点,甚至可以制作想象的场景。这种特性造成了模拟现实交往在某种条件下的不可检验性,如人们很难判断旅游景区的虚拟制作属于现场拍摄还是造了假。由此可见,全息网真图像建构的传播活动,可以无限接近社会现实交往形态,却与面对面的交流明显不同。
2.虚拟现实技术以身体在线为特征
与以视像传播为基础相对应,虚拟现实技术构建的模拟现实交往以身体在线为特征。在现实生活的交往中,人自身必须在现场,物本身必须作为摆设而存在,而在虚拟现实技术条件下,人和物固然可能在真实的时空中被记录,但都需要化为影像符号以在场的形式通过网络传输进行传播。更重要的是,与以往的影像不同,这种影像符号极其精致,“毫发毕现”,让人感到与现实生活毫无二致。当然,这种精致化的视像符号会造成两个具有悖论性质的影响。一是它与身体紧密相关,即它是对身体的精细复写,复写的目标是与身体的真实在场达成同样的效果。模拟现实交往就这样对身体产生了明显的依赖性,但它同时又是对身体的僭越,它是将身体制作成视像符号,这种视像符号不是对参与传播的主体的身体进行简单朴素的复写,它可以突出局部特写,可以将身体变形取得戏剧性效果,可以记录身体的某个瞬间做成记录。它可以穿越网络空间得到传播,也可以穿越时间为他人所见。身体的在线克服了口语传播因依赖身体的在场而受到的时空局限,同时也因为获得了对身体的制作权而使身体不再具有占据社会现实交往中心位置的神圣性,观众也“只是一个在场者的数字化身,他们没有能力对虚拟现实中的事件进行改变”[15]。
3.虚拟现实技术以全部感官参与为样态
虚拟现实技术与以往传播技术的最大不同,在于以往的传播技术只能有视觉和听觉介入,而虚拟现实技术则可以调动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等多种感官。它的视像可以对视觉和听觉形成沉浸感,而传感设备则使人如触其物、如闻其香、如尝其味。但是与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感官参与不同,这是一种拟感官参与,而这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学意义。一方面,这种拟感官参与往往会高于现实生活中的信息对于感官的刺激,属于高强度刺激。高清的血腥镜头、灾害的悲惨场景、放大的足球比赛声音,以及场景实物对于身体摩擦的模拟等,直接考验神经的承受力,从而产生显著的震憾感和同情感,这是虚拟现实技术模拟现实交往时临场感的来源。另一方面,由于是拟感官参与,视像交流还不能完全替代现实交往中的亲近感觉,即使能够清晰地看到对方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人却是不可拥抱的、物是不能抚摸的。男女之间的虚拟现实交往可能会使双方产生深深的情意,甚至有可能会产生强烈的触摸需求,却不会获得夫妻间的实际亲昵。在这种意义上,模拟现实交往可能会如美国歌曲所唱的“打电话更寂寞,无精打彩真寂寞”那样,使人们对现实交流产生更加迫切的渴望。
4.虚拟现实技术以身临其境为体验
钱学森先生建议将虚拟现实技术译为“灵境技术”,意指其制作的环境具有高度仿真特征,却非真实的情境。与社会现实交往不同,虚拟现实提供的模拟现实交往产生的是计算机情境,是通过计算机作用于用户的感官形成的交互式视景仿真,这种仿真技术可以产生代入感和沉浸感。用户可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亲临”事件现场,以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的身份,观摩和感受正在获取的信息,如美国《得梅因纪事报》所做的VR新闻《丰收的变化》,观众可以在360°全景视角“走动”,感受到身边是忙碌的农场主、散步的牲畜、嬉戏的孩子和草垛边飞舞的蝇虫,倾听农场主的交谈。用户也可能完全沉迷于虚拟世界之中,产生类似于身处现实世界之中的存在意识甚至是幻觉,浑然不觉甚至习以为常,进而忘记现实的社会生活,如马克·扎克伯格2016年2月参加三星发布会时,观众即沉浸虚拟现实世界中而浑然不知。
三、结语
莱文森指出,“一种媒介的存活系数,与前技术的人类交流环境的接近程度有直接关系。一切媒介的进化趋势都是复制真实世界的程度越来越高,其中一些媒介和真实的传播环境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和谐一致”[16]。虚拟现实技术之所以被视为传媒业的“下一个风口”,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在于其有助于人们“回归传播的原始形态”[17],能够为随时随地的沟通和交流提供高效的应用平台,并超越时空传递真实环境和表达真实情感,满足人们对沟通所需要的全方位和全身心的现实感受,重新定义人与人之间面对面和在一起的含义,展现人类真实的社会实践及其实践成果。
但是如前文所述,虚拟现实技术通过提高视像的精微度和传感设备的灵敏度,足以达到“以拟乱真”的效果,究竟是使人类更接近理想的传播状态,还是使人类更迷惑于或是更远离了社会现实交往,可能还是一个未知的问题。施拉姆曾经说过,“人们终将要适应自己加工和分享信息的非凡能力。他们必须要学会为自己的利益去使用这一能力,而不是为自己的毁灭去使用这一能力;必须学会为了进一步的人性化和社会化去使用这一能力,而不是为异化或退化去使用这一能力”[10]17。为了使虚拟现实技术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实现对社会现实交往的全模拟传播,需要我们学习适应现实技术提出的挑战,制订严格的传播规范,如对不同的传播文体设置不同的真实性要求,对全息网真技术的部署场所做出限制等等,规范的内容则由虚拟现实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而定。
注释:
①按照王振铎先生在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多次讲座上的解释,“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当指说话而不形成文字,就无法流传久远。本文取此释义。
[1]杭云,苏宝华.虚拟现实与沉浸式传播的形成[J].现代传播,2007(6):21-24.
[2]史安斌,张耀忠.虚拟现实新闻:理念透析与现实批判[J].学海,2016(6):154-160.
[3]喻国明,谌椿,王佳宁.虚拟现实(VR)作为新媒介的新闻样态考察[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5-21.
[4]〔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56.
[5]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6.
[6]〔加〕马歇尔·麦克鲁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 何道宽,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
[8]〔美〕萨丕尔.语言论[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4.
[9]〔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7.
[10]〔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1]崔金泰,崔玉屏,海虹.电影史[M].沈阳: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2:2.
[12]周逵.虚拟现实的媒介建构:一种媒介技术史的视角[J].现代传播,2013(8):29-33.
[13]Michael H.Virtual Realis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14]曹健.体验“网真”[J].IT时代周刊,2006(21):2.
[15]杜江,杜伟庭.“VR+新闻”:虚拟现实报道的尝试[J].青年记者,2016(6):23-24.
[16]〔美〕保罗·莱文森.莱文森精粹[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35.
[17]俞哲旻,姜日鑫,彭兰.《丰收的变化》:新闻报道中虚拟现实的新运用[J].新闻界,2015(9):61-65.
(责任编辑姚虹)
TheFullSimulationPropagationofSocialRealityContact——A Theoretical Thinking for the Value and the Spread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QI Tao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
From the general situation of human communicating development history,in order to overcome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s,transmission form has experienced the evolution from social reality face to face to the non-physical contact.Since photography appeared,the transmission form has translated to the simulate reality contacts.The emerge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have provided the possibility of achieving the full simulation propagation in social reality.This transmission form will base on video propaganda, characterized by the body online, with the whole sensory participation as a sample, and experience as immersive. The pursuit of simulate reality communication determines the emergence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and it also determines the rules of its development direction in the future.
simulate reality;reality communication;transmission form
2017-09-06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消亡论争语境下的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2014BXW012)
祁涛(1977—),男,河南滑县人,新闻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 新闻报道规范与新闻媒体运作。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5.013
G212
A
1008-3715(2017)05-005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