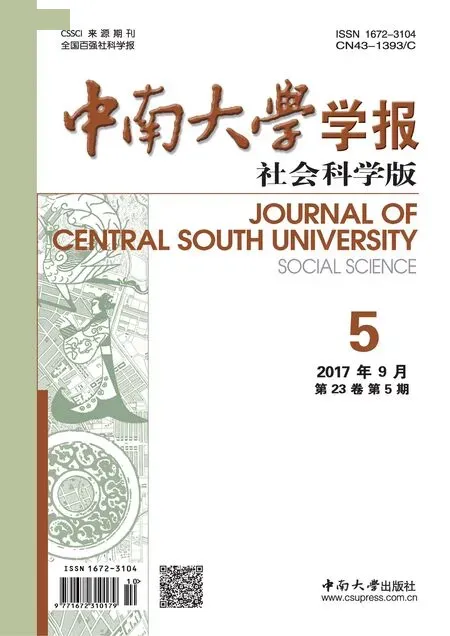阿伦特思想中的保守向度研究
林伟毅
阿伦特思想中的保守向度研究
林伟毅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阿伦特的思想中包含着一种保守的向度,这一向度是作为一种思想的成分展现的。在阿伦特那里,对传统的保守是与对宗教、权威的保守同时的。在实质的意义上讲,保守是对自由的保守。在阿伦特那里,保守不是恢复,在政治领域,对恢复的追求是危险的。在政治领域,阿伦特更重视启新的能力,但在教育领域,阿伦特认为,树立权威性与保守权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其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责任。
保守;自由;教育;传统;权威;宗教
汉娜·阿伦特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在政治学理论上,阿伦特十分重视公民的政治自由,但她的思想区别于自由主义理论;她强调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意义,但她的政治学理论却明显区别于激进主义,所以,在政治思想史中,阿伦特的思想很难被准确地归纳到某一个具体的理论谱系当中。这与阿伦特的思考特点紧密相关,阿伦特对政治的思考以政治世界的现象为基础,并对现象做出理解和解释,现象的复杂性就决定了她思想的复杂性,因此,阿伦特亦不把她自己的思考归纳进某个思想谱系中。但因为阿伦特非常重视公民对政治的参与,因此,一般而言,人们认为她是古典共和主义的复兴者,并通常把阿伦特的政治学思想归纳进共和主义的谱系之中。西方近代政治学理论以强调公民自由权利为主流,公民的政治参与在主流理论上处于一种遮蔽状态。到阿伦特这里,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性被重新发现,从这个意义来讲,我们有理由认为,阿伦特确实复兴了西方古典的共和主义传统,在政治学理论上,亦可以把阿伦特归入共和主义的谱系当中。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大致归类而遮蔽阿伦特思想的丰富性,事实上,阿伦特的政治学思想不仅具有复杂性和多维性,而且,即使从共和主义的谱系中看,阿伦特的政治学思想在整个共和主义的理论脉络中也具有自身的特点。通过分析阿伦特的著作,笔者发现,在阿伦特的政治学理论中,蕴藏着一种保守的思想成分,而且阿伦特的保守思想与一般意义上的保守主义理论存在区别。一般来讲,保守主义重视对自由或权威的恢复(这点阿伦特也曾指出),但在阿伦特这里,保守并不是恢复的意思,而是指向了开拓、建造与保存、爱护公共世界的能力,这使得阿伦特的政治学思想更具特色,亦使得阿伦特思想的多维度特征进一步得到展现。因此,论述阿伦特政治学理论中保守的思想成分,对阿伦特思想研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试图对此论题做出论述,笔者对本论题的探索主要基于对阿伦特著作的分析。
一、保守的思想维度
笔者认为,因为阿伦特重视公民的政治参与、重视推陈出新,她的政治学思想可以被大致归纳进共和主义谱系中。在阿伦特的政治学理论中,保守思想作为一种思想维度或思想成分呈现出来,而不是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而且阿伦特也曾对政治保守主义做出批评,因此不能因为保守的思想成分而把阿伦特的思想简单地归纳到保守主义的谱系中。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她的保守思想面向①。这种保守思想的维度使得她与著名思想家奥克肖特所指出与所批评的政治理性主义思想有一种本质的区别,并区别于激进的共和主义 思想。
在阿伦特看来,“极权统治表明,传统已经无可救药地断裂了,这一断裂使得西方的自我理解问题陷入一片混乱。”[1](346)作为思想家,阿伦特清楚地认识到,在现代性处境下,西方政治传统已发生突变,而这种认知是一种后意识,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事件。作为一个有着现象学的哲学知识背景的政治学家,阿伦特始终坚持的是以现象、事件为思考的核心,她必须以一种和古代不同的方式来回答这个事件,而不是在现代面前简单地怀古。一方面,阿伦特对西方传统做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另一方面,她并不因此持一种激进主义的态度。在她的文集《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前言中,阿伦特的保守思想清楚地展现出来。阿伦特通过分析夏尔的预见和观点指出:“没有传统,在时间长河中就没有什么人为的连续性,对人来说既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只有世界的永恒流转和生命的生物循环。”[2](3)我们可以看到,在阿伦特的观念里,在传统的保守中才能维持历史的人为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是通过人类依靠理性在短时期内能建构起来的。
阿伦特认为,在历史长河中,人的祖辈会遗留财富给他们的后代,一代代地传承,而“恰恰是传统选择了、命名了、传递了、保存了、指示了珍宝是什么和有什么价值”[2](3)。阿伦特指出,在古今之变的断裂当中,因为传统远离了我们,作为财富继承者的后代,我们或许手里仍握着祖辈遗留的财富,却忘却并且不再明了手里的事物是什么或者它有什么价值。因为在阿伦特看来,“记忆(虽然只是思想的一种方式,却是一种最重要的方式)只在一个预先设定的参照系中起作用,而人类心灵只有在极罕见的情况下能保存那些完全没有联系的东西。”[2](3)因此,当我们在古今之变的历史缝隙中拥抱遗忘以后,人的心灵开始陷进混乱,我们的思想走向模糊,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是新的事物,但我们持有的思想无法回答它。
阿伦特的思考并没有就此停止,而是从历史传统遗留的财富中进一步扩展,对传统的概念和现实之间的混乱关系做出思考。与我们所继承的历史之物却不知其为何物、其拥有什么价值这一种情境相对应的 是:在古今断裂的现代社会,我们还在使用一些古代的概念,但是,我们却并不知道那些概念是什么意思,它原初的意思和指向的事实是什么。我们的思想在现代社会中无力提出新的概念来回答此刻面对的事件和现象,却仍在调用以前的概念来解释现象,使得现象屈服于概念,并且,此刻旧概念对一切新的力量保持恐惧和警惕的心理。因此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前言中,阿伦特指出,在古今之变的断裂当中,思想和现实分离,但是我们无力的思想描绘不出新事物,因此,“现实在思想之光面前已经变得晦暗,思想脱离了现实也不再焕发活力,要么变成无意义的废话,要么只是在丧失了任何具体含义的陈腐事实上不断打 转。”[2](4)
我们已经指出,在阿伦特那里,传统与现代的断裂意味着连续性的缺位,我们看不到过去,在这种状态下,生命保存的只是必然性,就只是生存下去,我们不知道自身从哪里来,因此更不知道到哪里去。我们忘却了开端奠基的神圣和伟大,意味着我们忘却了政治领域的行动原初的意义和精神。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出阿伦特对权威概念的论述。阿伦特认为,权威“以过去的一次奠基作为它不可动摇的磐石,为世界带来了永恒性和持久性”[2](89)。在阿伦特的文章《何为权威?》及由杰罗姆.科恩所编、阿伦特所著的《政治的应许》中,我们都可看到,阿伦特非常重视古罗马的政治经验。在她看来,罗马政治是权威、传统、宗教结合的典范。阿伦特是这样写古罗马政治经验的:政治体的建立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它是由人的政治的行动开启的,由此政治体拥有了一个神圣的奠基,“创始者的模范等于是实际行为中的权威模式,本身携带着道德政治标准”[2](118),“祖先第一个见证和开创了神圣的奠基,又在数世纪以来通过他们的权威增益着它。只要传统不中断,权威就不可侵犯”[2](118)。在《论革命》中,通过美国革命和美国的建国故事,阿伦特指出,是立国的奠基行动本身树立了政治体的权威之源,开端的行动需要后来的人们不断地记忆,在记忆中保持在奠基行动中确立的权威的连续性,从而维护政治体的开端的精神。在阿伦特看来,权威由此可有在后来的政治体中保存下来②。权威需要人们在后来的历史当中不断想起,因此阿伦特认为,传统“守护并延续了权威”[3](58)。但在古今之变的断裂情境下,传统失落,就意味着权威失落了,我们不能想起奠基行动的伟大,不能理解行动的意义。行动,在阿伦特的理解当中,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开启,一个行动,它开启的将会是无穷的可能性。然而,现代与传统的断裂使得我们忘却了权威与自由的联系,不再知道行动原初的意义和精神。当政治领域把“行动变成了统治与被统治——也就是说,变成了发号施令和执行命 令”[3](59)的时候,意味着政治的精神失落了,政治的原初精神被遗忘了,而政治的自由和自由精神,是我们应该保守的内容。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阿伦特那里,保守传统的权威性对于保守政治的自由精神和保护人的自由,具有重要意义。
二、自由与传统的权威
作为一位思想深刻的政治学家,对于传统,阿伦特的观念绝非只是简单的立场之分。阿伦特的分析不只是告诉我们何为传统的意义,事实上,阿伦特对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有着非常深刻的剖析,她对传统的分析难以用一种简单的立场来概括。在《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政治的应许》等作品中,阿伦特分析并批判了自柏拉图到马克思以来的政治思想史传统。通过阿伦特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在阿伦特的观念中,人们对传统的继承不应该是原教旨的,保守应该是对传统的权威的保守,而传统里的反政治部分——统治与被统治因素,是应该被否定与被拒斥的。下面,笔者将论述什么是保守传统的权威以及它与自由有着何种关系,从而进一步探索阿伦特思想中的保守的思想向度。笔者将进一步探索阿伦特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批判,从而分析在阿伦特的视域中,对于传统,我们应批判什么。
阿伦特认为,“权威是以见证过神圣奠基的祖先们的证言为基础的。”[3](58)在她的文章《何为权威》和著作《论革命》当中,阿伦特的权威观念和奠基有着密切联系。通过一个神圣的奠基,公民的政治体(在阿伦特笔下,有罗马和美国)建立。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奠基那一个时刻的神圣性需要后来者怀念甚至抒写、补充。在阿伦特看来,“基于奠基的罗马宗教负有一项神圣的职责:保存从祖先或者更伟大的人那里传承下来的一切。传统因此变得神圣。”[3](58)因此,阿伦特指出,在古罗马,权威、宗教、传统“三位一体”,所以,我们看到,对传统的保守是保护权威和宗教。不过,还应该看到,这个意义上的宗教并非我们当代宗教的形态。在阿伦特看来,对“传奇性的奠基的神圣化,以及对创建新家园的神圣化,变成了罗马宗教的基石。而在罗马宗教中,政治活动和宗教活动被看作一回 事”[3](58),因此,核心是对“传奇性的奠基”的保守,也就是说,对权威的保守。
在阿伦特的视域中,对权威的保守事实上就是对自由的保守。在她看来,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已经忘却了什么是权威及何为权威的意义,在《何为权威》中,阿伦特致力于澄清权威的概念。在阿伦特看来,今天,我们常常分不清权力、权威、暴力的区别,以致误用它们,而这种误用对政治的伤害是巨大的。在《论暴力》中,阿伦特更是要界定这些概念。阿伦特指出,事实上,权威是拒斥暴力、强力的,亦不是以说服为前提,“在使用强力(force)的地方,权威本身就失败了。另一方面,权威也与说服不相容,说服以平等为预设并通过论辩的程序来进行。”[2](87)因为,在阿伦特看来,权威是等级制的,它不同于论辩,论辩需要以平等为前提,在《论暴力》中,阿伦特确切地指出,“它(笔者注:指权威)的标志是那些被要求服从的人的毫无疑问的承认;它既不需要强迫,也不需要说服。”[4](108)因此,和权力、暴力的保持和损毁方式不同,“要保持权威,这需要对人或职务的尊重。所以,权威最大的敌人是轻蔑,而最可靠的破坏方式就是嘲笑。”[4](108)所以,可以看到,权威和压制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权威绝不是专制或暴政,相反,权威和自由共处。阿伦特指出,“权威意味着人们在服从的同时保持他们的自由”[2](99),因此,阿伦特告诉我们,权威区别于暴政、极权、威权,后面三种意义上的“政治制度”是反自由、反政治的,而权威是反暴力的,是与自由联系在一起的。阿伦特对此做出论证:“在权威政府中,权威总是来源于一个外在的、优于它自身权力的力量;正是缘于这个超越政治领域的外在力量,权威政府获得了它的‘权威’及合法性,并且它的权力也始终受这个外在力量的制衡。”[2](91−92)因此,在阿伦特那里,我们可以概括出古罗马经验中,权威和政治的联系:通过政治体“传奇性的奠基”以及一代代人的记忆、诉说,它成为一种超越性的想象的存在,这种超越性在历史当中塑造了一种令人自觉地在内心敬畏的宗教(它不同于近现代宗教形态),而宗教形式就维持了权威的存在,宗教和权威共同约束政治权力的运用,超越性的敬畏力量使得权力必须有所畏惧,受到形而上力量的制约。
阿伦特指出,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忘却了权威的含义和意义,传统中的权威逐渐远离了我们,因此,“现代的普遍怀疑也侵入到政治领域”[2](88),政治权力逐渐远离了权威那种超越性存在对它的约束。我们在上面提到,在阿伦特看来,权威“为世界带来了永恒性和持久性”[2](89),因此,“权威的失落等于这个世界地基的塌陷,的确从那以后,世界就开始摇晃、变 动。”[2](89)阿伦特认为,传统的失落使得我们逐渐走向忘却过去的危险当中,我们的存在越来越失去深度,因为人类存在的深度依赖于记忆,而我们现在却处于遗忘状态,因此人的存在的根基是浅的,“因为记忆和纵深是同一的,或者说,除非经由记忆之路,人不能达到纵深。”[2](89)另一方面,宗教也失落了,阿伦特指出,“自十七、十八世纪宗教信仰受到激烈批判以来,对宗教真理的怀疑就成了现代的典型特征。”[2](89)阿伦特进一步指出,由于一场体制化宗教的危机,宗教信仰也发生了危机。这进一步证明阿伦特的观点:权威、传统、宗教三者的联系是三位一体的,一者的失落会难以避免地引起另外二者面临困境。这里,通过阿伦特的视角,我们有理由认为,对传统的保守事实上是对古老的权威的保守,对守护文明的宗教的保守,或者是保守某种宗教性,而保守宗教亦相当于保守权威,因为宗教的核心要素就是对超越性存在的敬仰,那是精神的权威,因此,保守传统的关键在于对权威的保守,这种权威包括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政治权威在一个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当中是会转化为精神权威的,因此,对权威的保守(包括政治权威和精神权威)的本质意义在于保守一种让人们在内心对它保持敬畏的超越性精神的存在。所以,阿伦特指出,这种对权威的保守是对具有宗教基础的权威性的保守。③在这种超越性存在面前,政治权力亦保持对它的敬畏的情感,权力的使用受到它的监管,权力的使用须对超越性存在(亦就是权威)负责,因为权威是在共同体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起来的。破坏权威,事实上就相当于毁坏共同体,是对共同体的历史的背叛,这明显地损坏政治权力的荣誉,而且,在现实上很可能会因为激起反抗力量而使得政治权力走向消亡。因此,权力受到权威的约束,权威为政治权力的使用划定界限,成为政治权力的有效的制约力量,这是权威对权力的规训。正是这种对带有宗教基础的权威性、超越性的保守和敬畏,促进了人们对自由的维持,因此,归根结底,我们所要保守的传统是对政治原初的自由精神的保守,是对自由的保守。
三、批判传统中的统治与暴力因素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在阿伦特那里,对传统的保守,其关键之处在于对权威的保守,对一种超越性的精神的保守,其实质就是对自由的保守。在阿伦特看来,传统并不是都由自由的因素构成,还有一部分是反自由的因素,它们需要我们加以辨别和消除。在政治传统里面,统治与暴力的要素是我们应该加以批判和拒斥的,因为对于政治来讲,统治与暴力意味着反自由,它们在实质上是反政治的。
阿伦特在她的多篇文章中分析了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马克思的西方政治思想传统,并深入地批判了政治思想史中关于统治的因素和观念,在她看来,统治恰恰是反政治的。在《人的境况》《政治的应许》中,阿伦特指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性,这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之一,是政治的重要前提,但差异性绝不意味着不平等,恰恰相反,在差异性的基础上,人与人又都是平等的,基于平等的人的复数性是政治得以存在的本质的基础。[5](138−141)因此,阿伦特认为,在差异性与平等的基础上,“政治从人与人之间产生,并且是作为关系被建立起来的”[3](93)。那么,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差异性怎样才展现出来呢?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告诉我们,那必须通过言说和行动。通过言说,人们显示出了差异性,而通过行动我们则拥有了开启、发动的能力,“通过言说和行动,人使自己与他人区别开来,而不仅仅显得与众不同”[5](138)。阿伦特指出,通过言和行来展现自我,必须以平等为基础,摆脱必然性,自由地言说、行动。此时的自由,“不是通过政治性的手段可以获得的东西;这种自由是一切政治之物的实质和意义所在。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和自由是一回事”[3](118)。因此,在阿伦特的视角中,政治以差异性和平等为基础,以自由为本质;政治不但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相反,政治的概念本身就内在地要求对统治的拒斥,因为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是建立在不平等、反自由和暴力的基础上,而那恰恰是政治本身所反对的。其原因在于,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根本上就预设了个体间的不平等。在阿伦特那里,主体间的不平等意味着在那里产生出的不可能是政治,因为在政治领域的活动必须以身份的平等为前提;在大部分情况下,统治依赖于暴力,统治须以暴力作为自身的基础和后盾,而暴力在根本上是对权力的弱化。阿伦特在她的《论暴力》一文中明确地区分了权力和暴力,权力的来源是人的聚集,而暴力“依赖的是工具”[4](105)。在阿伦特看来,“权力和暴力是对立物;一方占据绝对统治地位,另一方就会缺席。”[4](115)因此,统治与暴力在本质上是反政治的。阿伦特对政治思想史中的统治与暴力的观念因素提出了批评。
阿伦特对西方政治思想史传统做出了批判,在阿伦特看来,自柏拉图到马克思,西方政治学的主流思想充满了对“政治”的误解和贬低。一方面,阿伦特认为,政治哲学的传统自柏拉图发端以来到传统的终结处,政治生活一直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它没有属于自身的尊严和价值,只是人们追求其他更好生活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讲,传统哲学家也关心政治,但这并不说明在哲学家的观念里政治有着自身的意义与尊严。阿伦特指出,“这种关心与他身为一名哲学家的存在之间只是一种消极的关系:正如柏拉图所充分阐明的,哲学家所担心的是政治事务管理不善会令他无法追求哲学。”[3](83)另一方面,在阿伦特看来,西方政治哲学传统误解、扭曲了政治的概念。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区分了人类的劳动、工作、行动三种活动,劳动的目的旨在维持生存,工作的目的是提供人通过自身制造才会拥有的事物世界,行动关乎的则是建构、维持政治体[5](1−2)。阿伦特认为,行动具有开启新起点的特点,一方面它是希望,另一方面它有三重困难:结果的不可预见性、过程的不可逆转性和作者的匿名性[5](171)。阿伦特指出,为了摆脱行动带给人的那些困难和脆弱性,使得人类生活变得可预见,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自柏拉图开始就试图探索能控制行动的不可预见性的方法,对那种方法的探索导致了西方思想传统对政治概念、意义的误解和扭曲。从对柏拉图哲学的分析中,阿伦特看到,柏拉图的理念论清楚地展现出他构建的以工作这一种活动的方式代替行动的观念,用理念预先制定某些准则。在政治领域,哲学王通过运用这些固定的准则,和工匠或者雕刻家一样构建公共领域、城邦,试图通过“理念”这样的模型,使得行动所可能带来的不可预见的危险被克服。阿伦特指出,在这种方式下,“政治技艺的经验和其他技艺的经验一样,其中主导性因素不在于艺术家或工匠个人,而在于他的艺术或手艺的非人格对象。”[5](176)阿伦特认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恰恰是建立在对政治的概念与意义的误解之上的,这种政治哲学是无政治的,因为它在人类的三种活动中压制了行动的维度,这意味着人们不能再拥有开启新起点的能力,复数性逐渐被控制,而政治的前提就是复数性,因此它是无政治的。更致命的是,人本来有开启新起点的能力,它如何被控制呢?那么就需要通过暴力,以压制行动,从而摆脱行动带来的那三种困难。由此,在《人的境况》中,阿伦特指出,“在以制作来解释行动的政治规划和思考中,暴力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暴力,制造就无法进行)。”[5](177)通过阿伦特的分析可以看到,在阿伦特的观念里,自柏拉图以来,政治的意义和尊严、政治的概念在西方政治哲学传统当中就没有得到准确的认知。而在阿伦特看来,政治拥有自身的尊严,政治和自由是同一的,它拒斥暴力与统治。
到了马克思那里,阿伦特指出,马克思颠覆了政治在西方思想传统中的次要地位,以前沉思高于行动,而马克思强调改造世界的意义根本不会比认识世界弱。在这个角度上,传统对政治的贬低终结了;但阿伦特认为,马克思在另一方面还是接续了传统对政治的错误认知,也就是,在马克思的思想观念里,暴力对于社会进步来讲依然有意义。通过对马克思哲学特别是《资本论》的分析,阿伦特指出,马克思的“暴力是每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是“对整个现代所持信念的概括,并且引出了这个时代最核心信念的推论,那就是历史是人‘创造’的,正如自然是上帝‘创造’的一样”[5](177−178)。在对阿伦特政治学思想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阿伦特对柏拉图、马克思等哲学家政治哲学的解读是存在错误的。不过,不管阿伦特的解读是否正确,可以确定的是,阿伦特批判的核心指向了政治中的暴力因素,无论是现实政治中的暴力因素还是政治学思想观念中的暴力因素。在阿伦特的观念里,政治拒斥暴力与统治,政治是自由,而不是统治。
阿伦特对政治思想史的批判不能等同于对政治的批判,但从对思想史中统治、暴力观念的批判推论得出对政治中的统治、暴力因素的批判,却是一个正当的、合理的推理。事实上,对于政治领域的暴力要素,阿伦特一直在批判,透过《论暴力》《政治的应 许》及其他多部作品,我们可以看到阿伦特批判暴力的立场。因此,作为传统的继承者或者说作为后来者,对于传统的保守,不是无原则的。传统会对我们展现出不同的维度、不同的结构和因素,面对那些不同因素,我们应该做出清醒的识别和选择。我们要保守的是传统传承中留给我们的超越性的精神存在,其实质是保守传统中的自由因素,是对自由的保守,同时,后来者要否定传统中的暴力因素和其他的反自由因素,并抛弃这些暴力因素。
四、现代语境下的传统保守
阿伦特认为,传统、权威、宗教三者是互相构建的,对传统的保守是和对权威、宗教的保守共时的,对传统的保守不能离开权威性的约束,这种权威性是具有宗教基础的,因此对传统的保守必须以权威、宗教为根基。阿伦特指出,“如果对传统的接受,没有伴之以具有宗教基础的权威性,那么这种接受就往往是不具约束力的。”[3](76)权威是有着宗教基础的权威。阿伦特认为,“如果权威没有以柏拉图的精神来宣称‘上帝(而不是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权威就是独断的专制而非权威。”[3](76)对此,我们可以看到,在阿伦特的思想中,对传统的保守事实上是对有着宗教基础的权威的保守,这就是对自由和尊严的保守。如果对传统的保守离开了这种基础,那么保守传统带来的可能是灾难。阿伦特知道,对传统的保守会使得视角有固定的倾向,“传统的主要功能就是通过把一切问题导向预先确定的范畴而予以回答。”[3](61)但笔者认为,在阿伦特看来,这种确定性对于人的权利的保护来讲是必要的。阿伦特指出,尼采的“视角化思考”概括了传统瓦解带给我们的后果,那就是,“能够在传统的语境中任意(即仅仅由个人意志所支配)游移的思考”[3](75)。在阿伦特看来,继承传统,如果不同时接受传统的权威性,带来的往往是灾难,尼采的“视角化思考”虽然继承了传统的框架,却因为没有得到传统权威性的约束而变得危险。阿伦特认为,经由马克思、尼采,“现代思想继承了传统的框架,与此同时却拒绝了传统的权威性”[3](76)。由此,“马克思使辩证法摆脱了实质性的内容”[3](77),辩证法因此得不到约束而超越自己的界限。阿伦特认为,马克思由于拒绝传统的权威性,使他的思想逻辑在现实世界的运用中变得危 险[3](75−77)。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阿伦特看来,在政治领域中,如果离开传统权威的约束,传统权威性的瓦解带来的很可能是对共同世界和人的权利的摧毁。我们可以看到,在阿伦特那里,这种确定性来源于一种超越性精神存在即宗教和权威,这种超越性精神的存在是在历史中慢慢形成的,不是通过哲学推理、理性逻辑设计而在短时期内建构起来的。试图通过哲学、理性来建构一种确定性从而保证政治世界的秩序,是阿伦特一直在批判的。因为在公共领域,这种对确定性的追求将很可能导致对新生事物的伤害,甚至扼杀新生事物,而这将可能导致极权主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厘清阿伦特视角下的两种意义的确定性,在政治世界,阿伦特所要保守的是一种来源于超越性精神存在的确定性,而不是来源于哲学、逻辑的建构。
对传统的保守是以对具有宗教基础的权威性的保守,然而,传统的权威性现在已经失落了,阿伦特现在并不是要寻回原来那个有权威、宗教的政治体。事实上,她清楚地知道,那个原来的世界不可能回来。在她的《何为权威?》中,阿伦特明确地指出,起源于罗马的那个失落的权威,“在任何地方都无法通过革命或其他更无前途的修补手段来重建,也不可能通过时不时在公共舆论中泛起的保守情绪或潮流来恢复”[2](135)。而且在阿伦特看来,试图通过激进的方式恢复传统是不合适的,那很可能又给人们带来灾难。阿伦特指出,革命事实上是“行动者受到来自传统源头的伟大力量的激发,并始终从传统源头汲取力量的事件”[2](135)。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的目的是恢复传统,恰恰相反,阿伦特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建立自由的政治制度,在于建立而不是恢复。阿伦特指出,“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所有革命都走错了路,要么以旧体制的复活为终结,要么以专制为终结,这一事实似乎表明,传统所提供的这个解救之道也不再是合适的道路了。”[2](135)在阿伦特看来,我们不应该幻想重返古代,但我们也不应该只想维持现状。在《教育的危机》中,阿伦特指出,“这种保守主义的态度,即把世界照原样接受下来,极力维持现状,在政治中只会导致毁灭。”[2](179)“现代世界中无论危机发生于何处,人们都无法依旧例行事或简单返回老路了。”[2](181)“简单无反思的保存,不论是受危机的驱迫,还是因循守旧并盲目地相信危机不会吞没生活的某个特定领域,都只能因屈从于时代洪流而导致毁灭。”[2](181)
那么,在现代社会,我们如何保守传统的权威性呢?通过分析我们已经知道,在阿伦特看来,传统权威已经失落,我们不可能亦不应该幻想让拥有权威性的古代世界回来。在现代社会,传统权威性失落,对于政治领域,阿伦特并不幻想重新找回那个原来的传统权威,而是强调在政治领域与平等者的交往行 动[2](178−179);但在教育领域,阿伦特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树立起权威性。阿伦特指出,因为新生命不断地来到这个世界,使得世界能不断地被建设,从而,世界得以不断地更新而避免了毁灭,所以,每个孩子都给世界带来新的希望。阿伦特认为,我们不应该把孩子排斥在世界外,不应该夺走他们推陈出新的机会。阿伦特认为,父母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同时负有两种责任。那就是,“对孩子的生命、发展的责任以及对世界延续的责任。”[2](173)一方面,父母必须照料孩子,从而让孩子健康地成长,另一方面,新生命的诞生可能给世界带来伤害,所以父母有责任教育孩子,从而保护世界。在学校教育阶段,阿伦特认为,成年人有责任帮助孩子认识到和发展起自身的独特性,但不是让孩子提前进入公共领域,阿伦特指出,孩子“不受干扰地成长,本质上需要一个封闭环境”[2](175)。阿伦特认为,教育者有责任把孩子慢慢地 “引入一个持续变化的世界”[2](176)。阿伦特指出,“由于孩子还不熟悉这个世界,他必须缓慢地被引入;由于他是崭新的,必须留意让这个新人和原有的世界顺利接轨。”[2](176)这是教育者对世界的责任。阿伦特认为,在教育中,教育者以权威的形式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教育中的权威现在同样在失落。但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中的权威是我们应该再次树立起来并加以保守的,因为它关系到的是我们对世界的爱与我们对世界的责任④。Mordechai Gordon指出,“对阿伦特而言,权威在教育中与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紧密相关。”[6](161−180)Mordechai Gordon指出,对于教育,阿伦特的态度是保守的,但阿伦特在教育领域的保守态度不是为了怀念、颂扬传统,而是为了使孩子长大后能承担起对世界的责任与培养孩子的创造能力。在阿伦特看来,孩子的创造能力和批判能力“一般要以对过去的深刻认识为基 础”[6](161−180),所以Mordechai Gordon认为,在保守的思想这一向度上,阿伦特与大部分保守主义者存在区别。
在后极权主义时代,应该如何面对传统?在阿伦特看来,重建世界的共同性是非常重要的。有一点必须指出,对共同性的重建绝不是构建一致性,一致性的构建以摧毁多样性为基础,而建构世界的共同性却不破坏多样性,相反,共同性保护多样性。极权主义运动后,人们面对的世界是断裂的。对于此种情境,阿伦特指出,当我们从历史中继承了权力、暴力、权威、暴政等词汇,但那些词对我们来讲却不再拥有共同的意义,由于它们对我们失去了共同的意义,世界对我们来讲就失去了共同性。阿伦特指出,“不正是因为我们被罚生活在一个语词彻底丧失了意义的世界,我们才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退回到自己的意义世界,并且只要求每个人在用词上只和他自己的私人用法保持一致吗?”[2](90)结合笔者前面对阿伦特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到,世界共同性的消失意味着确定性的消失,在那私人各自确证的情境下,公共世界消失了,权利就随时可能受到摧毁。因此,在阿伦特看来,构建世界的共同性是必要的。怎样重建世界的共同性?阿伦特认为,思想必须去理解事件,思想必须面对事件,而不是面对某个先验的范畴或某类哲学体系。卡罗勒·维德马耶尔指出,在阿伦特看来,“为了思考现时代,必须要创造出新的概念,并与现代特殊的共同经验相对应”[7](159),而阿伦特“对过去共同的有力的经验的定位与理解是有另外的目的的:通过对概念的厘清,去理解人真正的存在”[7](159)。通过对阿伦特关于传统的观念的分析,卡罗勒·维德马耶尔还指出,在阿伦特看来,概念对应的是经验,概念的意义不是来源于哲学的想象或逻辑的演绎,而是来自于人们在世界上活生生的经验,经验是概念的意义来源,因此概念的产生还对应着人对事件、对世界的理解能力[7](158, 176)。因此,在现代社会——古今之变断裂中的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在思想的废墟上重建世界的共同性。对于共同性构建,思想拥有责任,思想有责任面向现象、面向世界的事实,对现象与事实做出理解、分析和解释。在对事件或现象做出解释时,一方面,思想应该对从传统当中继承的概念做出认识和界定,界定这些概念所指向的事实或现象是什么,并面对新的事件本身重构传统概念的涵义;另一方面,当传统概念在新的事件或现象面前失效,或者,当现象、事实超出传统概念的解释范围,思想有责任提出和构建新的、有阐释力的概念,以解释新的事件。
注释:
① 笔者并非将阿伦特界定为保守主义者,阿伦特的思想是复杂的,保守思想是她政治学思想的一个维度,或者说,是阿伦特政治学理论中的一个思想面向。一方面,阿伦特本人不把自己的思想归纳进某个确切的思想谱系,另一方面,阿伦特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强调使她的思想区别于一般的保守主义理论。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阐述阿伦特政治学理论中的保守思想维度。对于阿伦特思想的保守气质,著名学者张汝伦教授亦曾指出过。
② 在《论革命》中,阿伦特详细地阐释了美国作为政治体如何确立了权威,笔者在这里对阿伦特观点的展现参阅了阿伦特的著作《论革命》。
③ 笔者对阿伦特的观点总结参见了杰罗姆·科恩所编、阿伦特所著的《政治的应许》一书。阿伦特指出,“如果对传统的接受,没有伴之以具有宗教基础的权威性,那么这种接受就往往是不具约束力的。”关于这点,笔者在下文的分析中会进一步阐释。见汉娜·阿伦特.政治的应许. 杰罗姆·科恩编. 张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76.
④ 对阿伦特教育中的权威思想的归纳参见了阿伦特的《教育的危机》。本处值得补充说明的是,在阿伦特看来,教育必须与政治领域分开,阿伦特指出,“我们必须坚决地把教育领域和其他领域分开,尤其是和公共领域、政治生活领域分开,以便单独在教育领域中运用一种与教育相符的,但已不具有普遍有效性,也不应在成人世界中要求普遍有效性的权威概念和对待过去的态度。”见汉娜·阿伦特.过去与未来之间. 王寅丽, 张立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81.
[1] 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与思的故事[M]. 陈春文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346.
[2] 汉娜·阿伦特. 过去与未来之间[M]. 王寅丽, 张立立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3] 汉娜·阿伦特. 政治的应许[M]. 杰罗姆·科恩编, 张琳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4] 汉娜·阿伦特. 共和的危机[M]. 郑辟瑞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5] 汉娜·阿伦特. 人的境况[M]. 王寅丽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6] Mordechai Gordon. Hannah Arendt on authority: Conservatism in education reconsidered[J]. Educational Theory, June 1999, Volume49, (2): 161−180.
[7] 卡罗勒·维德马耶尔. 政治哲学终结了吗? 汉娜·阿伦特VS列奥·施特劳斯[M]. 杨嘉彦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编辑: 胡兴华]
On the conservative dimension in Arendt’s thought
LIN Weiyi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There is a conservative dimension in Arendt’s thought. This dimension was shown as a constituent of thought. According to Arendt’s thought, keeping conservative to tradition, religion and authority was at the same time. In a essential sense, what we keeping conservative to was liberty. In Arendt’s opinion, conservation was not restoration, in the political field, pursuing restoration was dangerous. In the political field, Arendt attached more importance to creation. But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Arendt thought that it was of important significance in building authority and conserving authority which meant our responsibility for the world.
conservative; liberty; education; tradition; authority; religion
B151
A
1672-3104(2017)05−0014−08
2017−04−13;
2017−07−07
林伟毅(1990−),男,福建漳浦人,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现象学,政治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