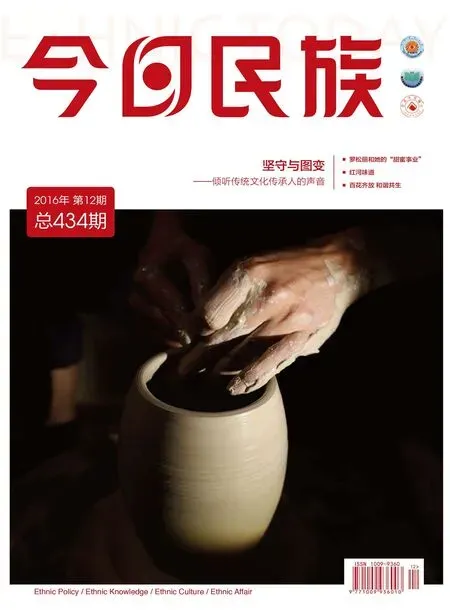成为历史意味着铭记而非遗忘
——读徐冶先生《横断山的眼睛》
◇ 文·图 / 龙成鹏
成为历史意味着铭记而非遗忘
——读徐冶先生《横断山的眼睛》
◇ 文·图 / 龙成鹏
2015年11月20日,
曾就职于今日民族杂志社,
从云南走出去后到光明日报社工作的摄影家徐冶先生去世。逝世一周年纪念日刚过,
写这篇文章,也算是一种纪念。
秘境家园
这期要介绍的书,正是徐冶所著的《横断山的眼睛——镜头下的西南边地人家》,出版于2006年,至今10年。《横断山的眼睛》是一套主题为“秘境家园”丛书中的一本,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一辑的四位作者都是云南的学者,分别是徐冶,云南社科院的杨福泉、郭净和王清华。
这套书的意图,从扉页上的几行字可以看出:“来自秘境的报告,著名学者、摄影家、旅行家、作家带您亲历秘境家园。”这里的“秘境”概念,显然是对旅行者说的。所以,丛书的设计,也尽量体现大众读物的特点。
镜头下的西南边地
《横断山的眼睛》接近200页,以图文结合的方式,介绍了作者从1982年至2002年(这一年徐冶离开云南到北京工作)20年间在云南以及西藏、广西等西南地区的旅行与考察。
全书分三章,第一章“咔嚓西部表象”,除了第一节“生活在秘境家园”具有总说的性质外,其余三节分别描述云南各地彝族的节庆与习俗。比如第二节分别记录了禄劝彝族的祭祖大典、石屏水瓜冲村12年一度的祭龙、弥勒县彝族的祭火神。或许是为了呼应前面的彝族祭祀活动,第二节最后一部分,作者还引用了祭祖、祭龙和祭火的经文。第三节写的是巍山,第四节写的是普者黑。
从考察时间看,1999年徐冶所在的单位与水利部联合做了一次“长江上游生态行”的考察,考察足迹主要在青海、西藏和滇西北。在迪庆,徐冶注意到从1998年10月开始,随着金沙江流域全面禁止砍伐,迪庆州财政“一根顶梁柱”被抽调,面临“放下斧头搞旅游”的转变。
第二章“串连旅途脚印”,从文章结构看,主要是云南之外的采访考察。其中第二节“历险滇藏文化带”,继续以藏文化为主题,但其考察时间可追溯到1986年,那一年班禅大师到迪庆考察,徐冶是随团摄影师。这一节还囊括了拉萨、阿里的旅行考察,显然是不同时段的经历。第二章第三节,内容沿着南昆线展开,采访时间应该是1999年,作为记者的徐冶参与了开通庆典并一路探访。
第三章(篇幅最大的一章)“速写边地人家”,则集中讲作者从1982年开始,深入云南乡村的旅行考察。其中涉及到众多的地区和民族:西双版纳中老边境的哈尼族、傣族、壮族、瑶族,绿春哈尼族,怒江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西盟的佤族,大理白族银器工匠寸发标的作坊、李建基的木雕、周城村的扎染,最后是泸沽湖的摩梭人。
历史的遗憾
从一本书的整体性和完整度来说,这些写于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媒体形式出现过的文字,组合在一起会让《横断山的眼睛》看上去缺少一些统一性。这种结果可能跟徐冶的身份和阅历有关。他借以完成上述诸多考察的身份,并不是一个科研单位的学者,而是一个记者、摄影家。这本书是他的职业生涯和工作履历的记录,而从中可以推断出徐冶先生是同辈中涉猎最广泛的一位(至少之一)。而这些地方尽管可以归入“西南边地”的范畴,但实际上它们之间还缺乏内在的统一性。而唯一能统一它们的,可能就是作者本人的经历和感受。
《横断山的眼睛》像笔记一样的文字,其实保留了尽可能多的信息,透过这些文字我能想象作者的经历还有很多未能说出来。读这本书,我有一种遗憾,这种遗憾因为徐冶先生去世而无法弥补。
之后,我听说在徐冶先生去世前不久,还探访过滇池和巍山。在滇池,徐冶先生努力寻找他熟悉的角度。而在巍山,他寻访曾经拍过的那位卖黄豆粉的回族女孩。滇池是徐冶先生长期生活的地方,而巍山则是1982年他大学实习教书的地方。这些地方在最近几十年,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
社会的巨变被摄影家持续20年的摄影记录弥足珍贵。然后,正如历史需要隔着一段距离才能看清楚一样,徐冶先生20多年的经历,也需要时间去显影它的价值。
云南的人文地理摄影
《横断山的眼睛》应该放在一个更大的时空背景才能看清楚它的完整价值,而这种背景今天正在被遗忘。
两年前,为做一期云南摄影家的内容,我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和知情者。其中郭净先生提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云南的摄影,最突出的成就就是诞生了一种人文地理的摄影方式。这种方式有两个特征:一是文字和摄影的集合,二是摄影体现一个故事而不仅仅是单幅照片。郭净先生认为,在云南的知识分子圈,搞摄影的、拍纪录片的和研究社会科学的都成为一个群体,他们相互影响,突破了摄影和社科的界限。
采访中郭净先生多次提到徐冶。说他1985年到社科院工作后,与民族学者王清华合写了西南丝绸之路的书,引起了摄影家的关注,最后促成了西南丝绸之路的考察摄影。
郭净先生总结的“人文地理摄影”,我从云南之外的摄影评论家那里也得到印证。著名的摄影评论家李媚说,上世纪80年代纪实摄影有了新发展,发展的方向上,云南与其他省份有所不同。其他省份的纪实摄影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尖锐批评,但云南则侧重于记录民族、文化与历史。

李媚和郭净先生一样都注意到,云南人文地理摄影还受到了来自台湾的影响。上世纪80年代,随着大陆的开放,台湾兴起了大陆文化热。到80年代末,这种文化热扩展到了云南这样的边疆省份。于是台湾著名的人文地理杂志《大地》在90年代初就开始做云南的内容,把云南作为重要的组稿地,这调动了一大批的青年学者积极投身于人文地理的写作。
云南人文地理摄影、写作的作者群阵容很强大。有邓启耀、徐晋燕、李跃波、于坚、谭乐水、郝跃进、李旭、木霁弘等等。这些人几乎都是上世纪80年代初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他们有表达欲望、有探索精神,从学校毕业后,又因为各种原因得以跟云南各地的少数民族接触。于是,他们开始了新的知识探险。
今天云南的文化状况,很大程度跟这代人的探索有关。著名的“西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这些概念,今天已经从知识界的讨论变成政府、商业各领域的命题。而最初提出这些概念的,就是云南注重实地考察,能写文字、能摄影的学者群体。
其中,《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徐冶和王清华合著)出版于1987年,《茶马古道》则出版于1990年,提出这个概念的是木霁弘、李旭等6人,他们在经历艰苦的川滇藏三角地带考察之后,用这个概念在三省之间找到了历史文化的一种关联性。
除了这些影响较大的文化事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知识阵营的足迹遍布云南,他们的观察与记录几乎覆盖了云南每个民族,他们保留的影像和文字,其文化价值无法估量。而徐冶先生就是其中成就卓著的一位。在《横断山的眼睛》后记里他提到,云南129个县市他去了120个,而西南各省他也几乎走遍。
值得一提的是,为整理、传播云南文化,从1995年开始,以邓启耀为首的学者,还改版了云南文学刊物《山茶》,使之变成人文地理的阵地。这个杂志后来改名为《华夏人文地理》,再后来就变成今天被“时尚”集团经营的《华夏地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探索已经落幕。《山茶》人文地理的大换血是时代转换的表征。郭净先生说,今天中国的人文地理摄影已经跟知识界脱离,跟民族学已经没有多少关系了。
成为历史,应该被铭记而非遗忘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对云南的探索,其意义还应该放在历史中去考察。
关于云南的知识,有很强的代际问题。随着一代人的老去、随着时代变迁,老一辈知识界所做的探索和努力都会被遗忘、埋没。
以最近的情况为例,那些想要了解云南的人,除了知道百度或是读一些娱乐化的游记之外,恐怕不知道从何入门。不止是大众如此,类似问题在知识界也一定程度上存在,最近二三十年学者们所做的探索已经被逐渐遗忘。如果再往历史深处讲,那被遗忘的还包括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调查和社会历史调查,以及更远的民国时代各种学术调查和游记随笔。
今天的人讨论云南,很少会追溯那么远。当然,也很少会意识到这些历史留存下来的文献具有何种价值。在我们的观念里,有一种粗俗的知识进化论,总以为今天人写的书,会比几十年前的更好、更“有用”。实际上未必如此。
今天的人的确有可以看到过去的优势,这意味着必须把过去纳入到当下的视野,我们才具有某种知识上的优越性。而知识上的这种代际因素,让我们盲目地把过去遗忘,以致我们的眼光只能局限于自己所处的时代。
对于云南来说,只有把至少80多年来积累的知识都纳入到阅读视野,才能够勾勒历史变迁中足够丰富的细节。
十多年前我读《云南民族工作回忆录》(三卷本),被书里那些民族工作者的诚意深深打动。在民族关系重新调整,民族知识范式重新确立的转换时刻,这些上世纪50年代的经历,不仅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打开了一扇门,也为我们认知今天提供了一扇窗。
重读徐冶先生的《横断山的眼睛》,其实并不是因为这本书必不可少。必不可少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一代代的知识人。历史的演进让太多过去鲜活的声音失声、消亡,我们应该铭记,应该重温。
(责任编辑 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