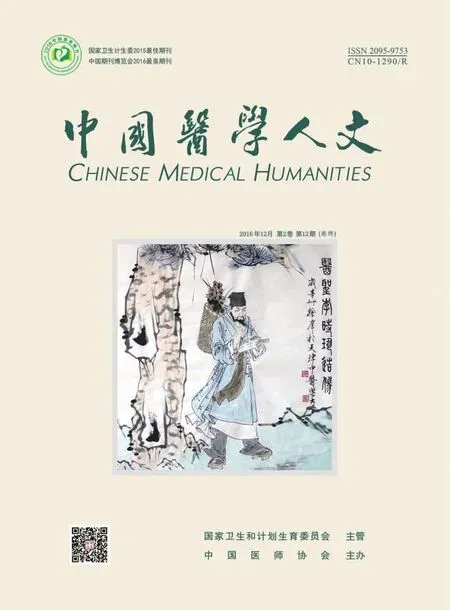晶莹的露珠
文/吕伟佳
晶莹的露珠
文/吕伟佳
就像问一个人何时坠入爱河一样,理想的确立之路也是难以说清道明的。
但或许,多多少少,又并非完全没有痕迹。就比如说,一些碎片式的生活经历串联在一起,也许潜移默化之中就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
我家所在的地方是一个退休军人集中居住的小区。放眼望去,目之所及多半是与爷爷奶奶年龄相仿的老人们。
还记得大约是十几年前了。那时候,不经意间看到小区门口的小黑板上用白颜色写了大大的粉笔字,不谙世事的我就如同平时“显示”认字本领一般,高声读来卖弄,却不想立刻被爷爷厉声制止。
“不要念——那是讣文啊,孩子。”
“爷爷,讣文是什么文呀?”
我抬起头,用不解的眼光看着爷爷。他却恍若未闻,只喃喃道:“老战友啊,未来的那一天,谁将目送我离开呢?”他的眸子失去了往日的神采,唯余一抹如血残阳所投射的余晖。
多年以后,当我终于明白了“讣文”之意时,每每再想起那时爷爷的眼神,竟分不清那究竟是他年轻时的锋芒余光,还是一层盈盈的泪光。
所谓戎马一生,经年乱离,都奈何不了最终同样的归宿。黑板白字,道尽了曲折而又醇厚的一生。数十年的彩色人生,最终都化作黑白两色,湮没于芸芸众生别无二致的生死别离。
他的眼神,也许正是为此吧。
只是,我再没有机会得到他的回答了。
他的喉咙,插着管子;他的手臂,一条一条管线连着机器;他的眼睛,似乎看倦了这个世界,总是懒懒眯起;他的神智,早已不清醒了。但是,我却总隐隐觉得,他一定还是想的:想爱,想懂,想去倾诉,想被陪伴……于是不禁紧握了他的手——尽管那手,有些浮肿,让人心疼。
他这样躺进医院,总有半年余了。
看着他,这样孤寂地躺在病床上,忽而想起杨绛先生的《我们仨》:“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是的,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然而,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说不清。但我知道,我打心眼儿里是渴望这份目送的,更渴望能亲自医治他,陪伴他,甚至只是简简单单地,仅仅是,能注视他就好。
龙应台面对她衰老的父亲,曾悔恨道:“他老了,所以背佝偻了,理所当然。牙不能咬了,理所当然。脚不能走了,理所当然。突然之间不能再说话了,理所当然。我们从他身边走过,陪他吃一顿饭,扶着他坐下,跟他说再见的每一次当下,曾经认真地注视过他吗?”
“老”的意思,就是失去了人的注视,任何人的注视?
那么我不要,哪怕他的嘴,不能言语;他的手,不能动弹;他的眼睛,失去光华;他的心跳,越来越弱……他已经失去了所有能够和我们感应的密码,但是我敢肯定:他是深深爱着我们的,他一定一定想要我们的陪伴……

农田的守望者 摄影/邢 露 大连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任何人,垂垂老矣,疾病缠身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是一样呢?
但是也许,除了血浓于水的亲人,还有一些人也在默默陪伴着他们:是日夜不离的护工阿姨,是温和耐心的护士姐姐,也是敬业认真的医生……
那么,那些最后“陪伴”着每一个“他”或者“她”的人,又是否给予了患者治疗以外的那些渴求么?
我不禁想:若我真的成为一名医生,是否也会有一天,将痛苦看惯?是否也会有一天,为亲人的离去努力控制着自己作为一个医生的情感?在每天“处理”痛苦、甚至是每天“处理”死亡的人眼里,是“亲人病重”因此变轻,还是“寻常痛苦”因此变重?
毫无来由地,我不假思索地认为是后者。我执拗地相信每一个医生都不仅拥有“仁术”,更拥有“仁心”;不仅拥有对己的“仁心”,更拥有对他人、甚至是陌生人的“仁爱”,尽管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说出这是为什么。但是人生在世,真的事事都能说清为什么吗?更多的时候,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一份不明来由的执著,就能带你走向一条崭新的人生路。
所以我想,做一个我理想中的医生,不管我与那些得我所医的人们是亲如鱼水,永远保持着亲厚的关系;还是像风中转蓬一样,各自飞向渺茫,相忘于人生的荒漠。
这些我都不在乎,因为从决定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然明了:与其说我们像医学芳草地上的新绿,不如说我们是日出时熹微晨光中的晶莹露珠——也许有的会在生活这个骄阳的炙烤下,不堪痛苦而化为一缕青烟;但是一定也会有那么一颗颗,愈加饱满,深入大地,滋养生灵万物。
这就是我立志从医的心路历程,愿未来的我也将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北京大学医学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