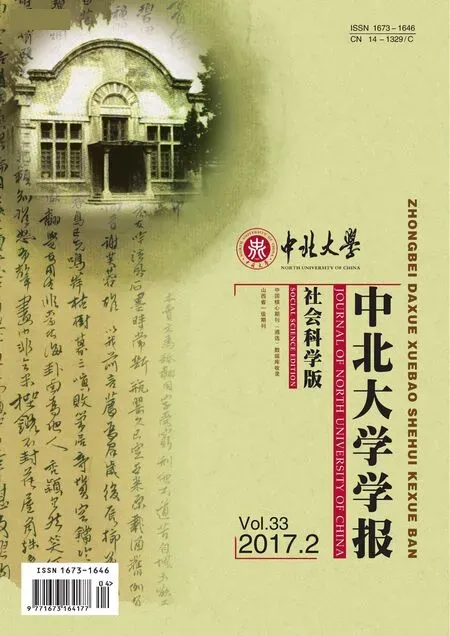上帝视角下的战时人生
——奥登对穆旦诗歌创作主题的影响
龙晓滢
(云南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上帝视角下的战时人生
——奥登对穆旦诗歌创作主题的影响
龙晓滢
(云南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穆旦在借鉴奥登的诗歌创作经验的同时也汲取了暗藏其后的基督教思想。 为此, 奥登与穆旦的诗歌作品具有诸多共同的主题: 作为难以逃离之宿命的原罪主题、 作为表现人类苦难的现实语境之战争主题、 人类作为进化过程中不完善的生物之“错误”与“失败”、 充满了危机与诱惑的人生之“阴谋”与“威胁”。 穆旦向奥登的借鉴是在特定文学环境下冲破传统和自身的一种努力。
奥登; 穆旦; 基督教思想
0 引 言
如果说近年来诗歌研究存在着热点, 那么, 这一热点为穆旦无疑; 如果说穆旦诗歌研究存在着关键词, 那么, “奥登”(Wystan Hugh Auden, 1907~1973年)则令人无法规避。 或许, 奥登对穆旦的影响已经成了现代诗歌研究领域人所共知的事实。 当谈及穆旦所接受的外来影响时, 每一篇文章都无一例外地指向奥登。 然而, 已有的这些研究对于穆旦具体在哪些方面怎样接受了奥登的影响却少有具体分析, 不少论著满足于简单地套用杜运燮、 袁可嘉、 王佐良等人对穆旦借用外来资源的简略陈述, 却没有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走下去。 带着这样的问题意识, 本文从细读奥登和穆旦的诗歌原典文本出发, 旨在分析奥登在诗歌主题方面对穆旦的影响。
奥登从小就生活在具有浓厚宗教氛围的家庭里。 奥登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牧师。 他的母亲是位英国国教徒(Anglo-Catholic), “她培养了奥登对文学的感觉和他对神学……的爱好”[1]16。 青年时期的奥登就读于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 那时的他自然受到了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 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 但相比较而言, 基督教对奥登的影响却是更为彻底而全面的。 正如奥登自己所说: “来自布莱克、 劳伦斯、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各种各样的宣讲、 布道‘都是基督教的同类’。 ……心理分析、 弗洛伊德主义、 马克思主义都是部分的、 一元的解释, 而基督教则是完整的。”[1]1891940年, 奥登正式加入基督教, 成为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直到生命的最后, 他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宗教热情。 他生命最后的诗篇是“描述祷告或以祷告形式出现的俳句”[1]15。 奥登认为:“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虽然本身有价值, 却是不完备的。 相比较而言, 基督教提供了一个可以解释世界邪恶的来源的超验视角, 也提供了一种广博得囊括了现今所有失败的历史哲学。”[2]519奥登的诗歌渗透着浓郁的基督教思想, 诗中每一个具体的现象都不过是上帝视角下一个更深邃问题的显现。
与奥登不同, 穆旦并非基督教徒, 生活中也并没有长期受到基督教思想的熏陶, 然而, 这并不妨碍诗人穆旦对自己的诗歌偶像奥登作品中所固有的基督教元素的借鉴与吸收。
穆旦进行创作的时候, 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借鉴奥登的诗歌创作经验的同时也汲取了支撑其后的宗教元素。 许多学者曾论及穆旦作品里的宗教意识, 却忽略了穆旦最喜爱的诗人奥登在他接受基督教影响时所起到的媒介作用。 可以说, 了解了奥登诗歌的基督教背景, 穆旦诗作中大量来源于基督教的主题、 词语乃至诗歌背景都有了最初的来源。 而本非基督教徒的穆旦何以频繁借用圣经故事为诗歌创作背景, 为何诗歌中反复出现“上帝” “主”等宗教语词, 以及随之而来的从高空俯视全人类的创作视角与其诗歌作品中体现出的悲悯风格和旁观心态等特征, 都成为了奥登的宗教思想对穆旦产生的影响这一问题所呈现出的不同方面。
1 原罪主题: 难以逃离的宿命
作为长期受到基督教思想熏陶的诗人, 奥登的原罪意识非常强烈。 他在发表于1935年的文章《好的生活》里写道: “我们的(邪欲的)存在归因于人类的堕落——我们本性中遗传的缺陷。 ……正如卡本特所指出, 这一基督教认为堕落是‘人类心理事实的表征’的信条成为了奥登宗教思想的特征: 他将堕落视为‘人类有了自我知觉并意识到自由和自治的可能性那一历史时刻的象征’。”[1]190
奥登的组诗《在战争时期》开篇即再现了《圣经·创世纪》中的原罪故事。 组诗从上帝创世写起, 写到人类的时候, 诗人用“稚气的家伙”[3]加以形容。 在诗中, 人是如此善变以至于“一丝轻风都能使他动摇和更改”。 人类“追寻真理, 可是不断地弄错”。 紧接着, 诗人写到了伊甸园中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的一幕: “他们不明白那为什么是禁果”, 可犯下错误的人类的祖先“在受责备时并不肯听取什么”。 于是, 他们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他们离去了”。 人类堕落了。 堕落的结果是, 从堕落的那一瞬间起, 他们“过去所学的一切/都从记忆里隐退”。 人类远离了上帝的同时也告别了往昔快乐无忧的生活, 剩下的只是无尽的困苦与烦忧: “他们哭泣, 争吵”, 当“稚气”的人类像“儿童”一样“向上攀登”试图重回上帝的怀抱时, “成熟”“却像地平线从他们眼前退避”。 等待人类的是严酷的现实和无法终结的放逐: “危险增加了, 惩罚也日渐严刻; /而回头路已由天使把守住, /不准诗人和立法者通过。”
随着诗篇的进展, 诗人描绘了战争中众多的场景, 这些细节无不暗示着灾难与困苦的原罪起因。 诗的结尾, 奥登回到了对人类生存困境的广阔思考上, 并最终将笔触停留在对伊甸园里那无忧岁月的追忆:
游荡和失迷在我们选择的山峦中,
我们一再叹息, 思念着古代的南方,
思念着那温暖赤裸的时代, 本能的平衡,
和天真无邪的嘴对幸福的品尝。
犯下罪责的人类终将远离最初的欢畅时光, 因为“我们已订约要给‘错误’做学徒”, 既不能“象大门那样安详而赤裸, 也永不能像泉水那样完美无缺”, 而是永远“为需要所迫”, 正如《旧约·创世纪》中上帝所说: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 直到你归了土, 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
1940年, 奥登来华两年后, 穆旦创作了《蛇的诱惑》。 诗中以《圣经·创世纪》中亚当与夏娃受蛇引诱偷食禁果的故事作为诗的背景。 诗前小序重述了这一故事, 也给全诗铺设了原罪堕落的背景。 《蛇的诱惑》里有许多诗句明显来源于《创世纪》, 如: “那时候我就会离开了亚当后代的宿命地/贫穷, 卑贱, 粗野, 无穷的苦役和痛苦……” “自从撒旦歌唱的日子起, /我只想园中那个智慧的果子”。 诗句“你不要活吗?你不要活得/好些吗?”道出了人类与生俱来却又无法克制的欲望, 对人类生而带有的弱点与欲望的假设正是原罪说的来源。
奥登的《在战争时期》正是从人类因偷食禁果而被逐出伊甸园写起的。 巧的是, 穆旦的《蛇的诱惑》与《在战争时期》相仿的不仅仅是诗歌的背景, 还有将人类定格为从降生之日起就带着罪恶的原罪视角。 在这样的诗歌语境里, 人类显得更加卑微、 萎缩, 每个人都是一个永远无法被救赎的缺憾, 人只能在错误之后重复着错误。 人类所有的努力终将指向惘然与虚无。
又如穆旦的《潮汐》: “而对于那些有罪的, /从经典里引出来无穷的憎恨; /回忆起卖身后得到的恩惠, /他叹息, 要为自杀的尸首招魂: /宇宙间是充满了太多的血泪, /你们该忏悔, 存在一颗宽恕的心。”基督教肯定人生而有罪。 由于“原罪”, 人自降生之日起就成为万劫不复的负罪之身, 不可避免地要承担人神关系破裂的恶果。 人类的先祖亚当和夏娃犯下了罪责, 人类就应“忏悔”。
穆旦有首名为《我》的诗:“从子宫割裂, 失去了温暖, /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 /永远是自己, 锁在荒野里。” 这是现代诗歌史上第一个残缺、 孤独却又痛苦挣扎着渴望救赎的自我。 “永远是自己, 锁在荒野里, /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 “我”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来到世间, 随之而来的是生的不安与迷乱。 自我在存在中日渐迷失、 远离完整, 于是, “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幻化的形象, 是更深的绝望”。 与20世纪之初郭沫若笔下那个要把日月吞了的急于破坏一切又要创造一切的“我”相区别, 20世纪40年代在战争阴影笼罩下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的“我”在穆旦这里呈现为慌乱、 迷失、 残缺而又不甘的自我, “想冲击樊篱”, 却陷入了“更深的绝望”。 当我们将穆旦诗中的“我”视为一个群体的时候, 这个“我”就像是人类整体的象征。 从温暖的子宫割裂正如人类诞生之初从伊甸园中被驱逐。 人违背了上帝的旨意, 从伊甸园被放逐到世间, 这意味着人类与上帝的疏离, 人类从此注定要世世代代承受生活的奔波与痛楚。 离开伊甸园的那一刻, 苦难便产生了。
2 战争主题: 作为表现人类苦难的现实语境
20世纪30年代, 是一个笼罩着战争阴影的时代。 奥登之前, 诗歌在艾略特的引领下钻进了象牙塔, 脱离了与社会现实的关联。 有感于混乱的政治状况与社会现实, 奥登重新建立了诗歌与现实的联系。 综观奥登20世纪30年代的诗作, 无一不呈现出鲜明的政治色彩与浓烈的现实关怀。 罗森瑟尔曾经说过: “(奥登和叶芝的)不同在于奥登的现实感中显著的政治色彩以及对‘生存着的民族’和民族之间因仇恨而引发之障碍的敏锐感觉。”[2]182正是奥登诗歌中强烈的现实感使其区别于以往的浪漫主义诗人和玄学诗人, 从而确保了他在20世纪英美诗歌中的重要位置。
对战争的思考和表现是奥登关怀现实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战争时期》里, 奥登以人类被驱逐出伊甸园开篇, 将战争置于宏大的时空中来写。 从纵向看, 由人类诞生之日的安详无忧写到了当下战时的硝烟烽火; 从横向看, 从南京写到了达豪集中营, 又从奥地利写到了中国、 法国和美国。 同样宏大的场景也见于奥登的《西班牙》。 《西班牙》由奥登1937年在西班牙战场写成。 这首诗从历史上西班牙的度量衡、 算盘和平顶石墓的传播写到今日的战争, 又从中国、 希腊写到阿尔卑斯山以及非洲和欧洲。 用这样的方式书写战争并非偶然。 作为一位笃信基督教的诗人, 战争在奥登眼中只是被放逐的人类滥用自由意志所造成的恶果, 是错误之后的又一次错误, 也是人类无法规避的种种苦难中的一种。 正如克劳德丁·萨莫斯所说: “(《在战争时期》里)邪恶(Evil)一词具有严肃的神学意义上而非心理学意义上的重要性。 ……不仅他的历史俯视包括了诸如堕落(The fall)与驱逐(The expulsion)此类的基督教事件,而且神学视角对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和战争的爆发作为原罪持续存在的证明给予了回响。 战争本身, 被客观地毫不动感情地描述 ……被视为一个有缺陷的‘已订约要给‘错误’做学徒’的在道德伦理选择上的错误与堕落。”[2]514奥登最后把这组十四行诗取名为《在战争时期》(InTimeofWar), 这无疑意味着这组诗是诗人结合战争时期的特定生命体验而写就的。 他对战争的思考也成为了他对人类生存境遇的思考的一部分, 对中国的关注则是他对世界苦难的思考的一部分, 对战时中国现状的思考也被其整合到了对全人类的忧思中。
奥登诗歌的社会方面吸引着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诗人”们。 奥登的诗在他们的诗歌里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作为奥登的热切推崇者, 穆旦自然不能例外。
任何一场战斗都由出发拉开序幕, 正如紧随出发之后的是血肉的洗礼, 穆旦的《出发》写出了战争的残忍与血腥。 诗的一节到三节充满了“杀戮” “蹂躏” “死” “摧毁” “毒害”这类散发着暴力气息的词语, 呈现了“智力体力蠕动着像一群野兽”和“死的制造必需摧毁”的残酷景象。 当读者有足够理由认为《出发》全诗都要写战争的破坏力与反人性时, 诗的最后一节写道: “就把我们囚进现在, 呵上帝!/在犬牙的甬道中让我们反复/行进, 让我们相信你句句的紊乱/是一个真理。 而我们是皈依的, /你给我们丰富, 和丰富的痛苦。”这样一来, 诗人就把前三节对战争的书写纳入了基督教的语境里。 战争于是成为了人类众多苦难中的一种, 从而具有了象征的意义。
1938年4月14日, 奥登与依修伍德在中国从抗战前线返回汉口后, 奥登就为一个死去的中国兵写了一首商籁诗(Sonnet), “他在4月21日的茶话会上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朗诵过这首诗”[5]。 其中一节是这样的:
他被使用在远离文化中心的地方,
又被他的将军和他的虱子所遗弃,
于是在一件棉袄里他闭上眼睛
而离开人世。 人家不会把他提起。
奥登借战争来思考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人类的生存境遇。 在他眼里, 战争只是人类承受不尽的苦难之一种。 穆旦的诗作《退伍》也在对战争的书写中表达了人类现实生活中的苦难。 奥登诗中透出一股矛盾的情感: 既认为战争漠视个体生命(“为将军和虱子抛弃”), 又认为战争是为了明日的和平。 这样的情绪同样也体现在穆旦的诗里。 在《退伍》中, 士兵只是战场上一个冲锋陷阵的工具、 历史时间里一个微不足道的符号、 一个“没有个性的兵”, 他只能在战后才能“重新恢复一个人”。 战争, 这个人类制造的游戏总是戏弄着人: 战时, 人类是“城市的夷平者”; 战后, 人又重新“回到城市来”。 游戏结束后意识形态构造的“巨大的意义忽然结束”, 个体的人不得不重新面对战后的生存现实, “要恢复自然, 在行动后的空虚里”。 经历过战争的士兵已经被异化、 工具化, “要换下制服”回到正常的生活反而不习惯, “也许反不如穿上那样容易”。 诗的最后道出了更深层意义上的荒诞: “想着年轻的日子在那些有名的地方, 因为是在一次人类的错误里, 包括你自己, /从战争回来的, 你得到难忘的光荣。”人寻找到了光荣, 却是在“人类的错误”里。 如果说“光荣”是令人难忘的成就感和他自认为的“生存意义”的话, 那么, 因犯下大错被驱逐出伊甸园的人类是否应该为了所谓的“难忘的光荣”而继续人类“错误”的游戏、 在战争中重蹈滥用自由意志的覆辙?
3 错误”与“失败”: 人类作为进化过程中不完善的生物
由于早年对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浓厚兴趣, 奥登吸收了进化论的观点, 认为人类与地球上其它生物一样处于发展进化的过程中。 同时, 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 奥登的原罪观念使他认为人类因为脆弱而犯下了错误, 人类离开了上帝后, 更容易放纵私欲、 贪行污秽, 犯下更大的罪行, 从而更深地堕落。 可见, 人类是不完善的、 有缺憾的。 这样的思想在奥登的诗歌里体现为人类往往被视为进化过程中不完善的生物。
正如理查德·哈葛德所说: “(《在战争时期》的)主题……是一个, 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 在奥登的作品里反复出现的主题。 人类总是一种处于进化中的生物, 从未处在已完成的状态中。”[6]119奥登曾在《诗解释》里直截道出了他的这一观点: “如果我们留心听, 我们总能听到他们说: /‘人不会象野兽般天真, 永远也不会, /人能改善, 但他永远不会十全十美’。” 人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与不足。 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不过是自然界进化过程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永不完善的物种。 《在战争时期》里, 奥登一以贯之的仍是一种“岁月推移”的发展进化的眼光。 人类被置于与“蜜蜂” “鱼” “桃”等物种相并列的位置。 然而, 人类却因犯下罪责而远离完美。 人类自己制造的恶果终将由自己去舔尝。 历经了现时战争岁月的种种生存困境之后, 诗的结尾终于展现了一丝希望:“思念着古代的南方, /思念着那温暖赤裸的时代, 本能的平衡, /和天真无邪的嘴对幸福的品尝。”人类怀念着偷食禁果之前的那个纯洁无忧的家园, 同时也希望自己的未来正如“睡在茅屋中”梦想的那样:“参加未来的光荣舞会; 每个曲折的迷途/都有个规划, 而心的熟练的动作/能永远永远跟踪它无害的道路。” 当“它们繁殖得像蝗虫”, 并“终于被他创造的一切所支配”时, 人类无疑成为了笨拙的生物, 为自己的选择所羁绊, 任凭怎样挣扎都难逃“犯错”的厄运: “但我们已订约要给‘错误’做学徒, /从没有象大门那样安详赤裸, ∥也永不能象泉水那样完美无缺; /我们为需要所迫, 生活在自由中, /是一族山民卜居在重叠的山峰。”虽然仍有美好的希翼和向真、 向善的愿望, 只因“已订约要给‘错误’做学徒”, 人类只能作为一个不完善的物种在他们充满了困苦与无奈的生命中继续着自己注定要犯的错误。
提及人类禁受不住诱惑而犯错时, 通常指的是成年人。 即使人自降生之日就已经是有罪之身, 但与成年人相比, 孩子毕竟单纯、 洁净。 令人惊讶的是, 奥登对人类的堕落与缺憾的断言是坚决而又彻底的——孩子终将长大, 走向欲望的深渊。 他写道: “我们计划改善自己; 唯有医院/使我们想到人的平等。 ∥这里确实爱孩子, 甚至警察也如此; /孩子体现着大人变为孤独/以前的年代, 而且也将迷途。”(《在战争时期·二五》)支撑在奥登对人类的否定背后的是他对堕落之前的人类的肯定。 因此, 他对人类的批判与对现实的审视永远都以上帝造人之初的完美无暇作为参照。 其诗篇常常因为对快乐往昔的追忆而呈现出伤怀之美。 在奥登的笔下, 创世之初的人类越纯洁完美, 现实中的人类也就越发丑陋不堪。
穆旦诗中反复出现“错误” “失败” “过失”这样的词语, 隐藏其后的将人类视为进化中不完善的物种这一观点显然来自奥登。 《潮汐》中曾有这样的诗句: “而那些有罪的/以无数错误铸成历史的男女, /那些匍匐着献出了神力的∥他们终于哭泣了, 自动离去了/放逐在正统的, 传世的诅咒中, /有的以为是致命的, 死在殿里, /有的则跋涉着漫长的路程。”人类由错误铸成, 不论是“死在殿里”, 还是“跋涉漫长的路程”, 最终的结局不过是证明了人生的无望与挣扎的徒劳。 正如《诗》中所说: “我们没有援助, 每人在想着/他自己的危险, 每人在渴求/荣誉, 快乐, 爱情的永固, /而失败永远在我们的身边埋伏。” 不论人们渴求什么, 失败始终如影随形。 人类的过失如此之多, 愚蠢也仿佛成了人类唯一的特征, 证实着人的缺憾。
穆旦在表现人性弱点时将笔触延伸到了爱情。 在他看来, 人类本身有着无法祛除的弱点。 在最体现人性的爱情中, 弱点显露无遗, 爱情也随之远离完美, 如战争般充满了危机与恐怖。 于是, 《诗八首》里, 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
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
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
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
他存在, 听从我底指使,
他保护, 而把我留在孤独里,
他底痛苦是不断的寻求,
你底秩序, 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这些诗作也闪现着奥登的影子。 穆旦的“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 /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 直接来自于奥登的“每种弱点原封不动, /相同对着相同”(《太亲热, 太含糊了》)。 奥登的《太亲热, 太含糊了》将爱情视为一场战争, 写出了两颗心灵的缠绕与纠葛。 例如: “声音在解释/爱的欢欣, 爱的痛苦, /还轻拍着膝, /无法不同意, 等待心灵的吐诉/象屏息等待的攻击。” 穆旦的《诗八首》明显受到奥登这首诗的影响。 穆旦曾经翻译过这首诗, 他在“诗译注”里写道: “爱情的关系, 生于两个性格的交锋, 死于‘太亲热, 太含糊’的俯顺。 这是一种辩证关系, 太近则疏远了。 在两个性格的相同和不同之间找到不断的平衡, 这才能维持有活力的爱情。”[7]188实际上这正是《诗八首》的主题。
恋爱的双方在不断地改变, 因而“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且危险”(《诗八首》)。 不太可靠的是, 个体之间的交流却倚仗语言作为媒介:“我们拥抱在/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窒息着我们的/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诗八首》)。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从来没有人这样写过爱情。 现代诗歌中歌咏爱情的名篇如《雪花的快乐》 《教我如何不想她》 《雨巷》等, 都不吝惜笔墨来赞美爱情的轻灵、 美好, 抒发因爱情而萌生的欢畅和愉悦, 既便是烦恼, 也有一层对爱之希翼的欢快底色。 然而, 这类对美好纯真的爱情的歌咏仍然沿袭着《诗经·关雎》“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的抒情传统, 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换用了不同的语词罢了。 如果说鲁迅的《伤逝》第一次道出了冲破封建伦理束缚的“新青年”们的爱情困境, 曹禺的《雷雨》第一次在戏剧领域捅破了爱情纯洁无瑕、 炫美无比的窗户纸, 将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感情纠葛呈现于世人眼前的话, 那么, 首次在诗歌领域里展现了与现代人类的认知相同步的爱情世界的人则为穆旦无疑。 诗人穆旦从不断发展变化的辩证过程中的个体出发来写爱情, 写出了恋人之间艰难的磨合以及爱情潜在的危机。 诗中总有两个不同的个体力量相纠结、 缠绕。 爱情就是一场战争。
由于奥登眼中的人类是不完整的世界里存活着的不完善的物种, 于是, 他对疾病和治疗的重视也就不可避免。 这与奥登的父亲是一位外科医生不无关系。 “从父亲那里, (奥登)形成了对心理学、 疾病和北欧英雄史诗的兴趣。”[1]16对疾病和治疗的关注在他的诗里体现为大量的医学词语入诗。 比如: “天空象高烧的前额在悸动 ”(《在战争时期·十四》); “暴力流行好似一场新的瘟疫”(《在战争时期·二三》); “给我们神效之方/治疗那难以忍受的神经发痒, /断瘾后的疲惫, 说谎者的扁桃体炎, /还有内在童真的变态表现。”(《请求》)医学词语入诗同样是穆旦诗歌的明显特征。 例如《哀悼》中把整个世界视为一个“广大的医院”, 认为每个人都是病人, “他有他自己的病证”, “一如我们每日的传染”。 在《玫瑰之歌》里, 世界俨然毫无生机可言——“什么都显然褪色了, 一切是病恹而虚空”。 有学者把医学词语入诗归因于穆旦从自身现实境遇中得到的生存体验[8], 然而, 当我们发现诗人最喜爱的奥登经常在诗中采用医学词语时, 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断言穆旦诗中的医学词语完全来自于他自己的生存境遇。 这其中不可避免地有着奥登的影响。
4 “阴谋”与“威胁”: 充满了危机与诱惑的人生
创世之初, 亚当和夏娃本来是自由无忧的。 他们可以选择听从上帝的话不吃禁果, 然而他们却听了蛇的话。 蛇不能强迫人吃禁果, 只能引诱人吃禁果。 在这里, “蛇”象征着人的一种易受引诱而堕落的生活处境。 诚然, 伊甸园里有难以抗拒的诱惑。 人类被逐出伊甸园之后, 诱惑与阴谋有增无减, 现实生活危机四伏。
与奥登浓烈的基督教思想相关, 在他的诗歌世界里, 难以见到恒定不变的事物, 生活仿佛充满着诱惑与阴谋、 隐患和不安。 或许是因为心中怀有一个理想的彼岸, 现世在奥登看来自然乏善可陈, 处处潜伏着坠落的可能。 在奥登的诗里, 频繁出现“阴谋” “威胁” “诱惑” “迫害”这样的词语。 正如保拉·马彻狄所说: “(奥登的诗歌)图景上聚集着间谍、 密探和持有残缺的国家地图的神秘英雄, 也聚集着对手、 敌人、 审查员、 满怀敌意的复仇的人物, 他们也许正追踪着诗中的主角, 甚至试图杀死他们。”[1]201例如: “但假使由于夸张或者沉醉/而比这走钢丝更狂放一些, /前前后后都充满了威胁。”(《要当心》) 又如: “他们结实而成为他们的奇迹: /每种怪异的诱惑所呈现的形象/都成了画家动人的画意。 ”(《探索·冒险者》)
奥登有一首名为《诱惑之三》的诗, 从中可以看到诗人对诱惑与欲望的理解。 “他使用一切关怀的器官注意到/王子们如何走路, 妇孺们说些什么。”人一旦太在乎外在的本不属于自己的事物, 那么, 他就很容易迷失自我, 在众多惶惑虚幻中找不到自己的方向, 甚至把本来拥有的值得珍视的东西也抛弃在黑暗的角落里。 奥登紧接着写道:“于是不太情愿地达到如下结论: /‘所有书斋的哲人都胡说八道; /爱别人就是使混乱更加混乱; /同情之歌只是魔鬼的舞蹈。 ’”求真、 知爱和怜悯这些人类最过珍贵的品质都被否定, 在诱惑中, 人彻底走向堕落与沉沦。 诱惑本身就是令人走向深渊的阴谋, 因而, 奥登接着写道: “他对命运鞠躬, 而且很亨通, /不久就成了一切之主; /可是, 颤栗在秋叶的梦魇中。 ∥他看见: 从倾颓的长廊慢慢走来/一个影子, 貌似他, 而又被扭曲, /它哭泣, 变得高大, 而且厉声诅咒。”想要的东西原本求之不得, 一旦对命运鞠了躬, 一切就变得唾手可得。 与此相伴的, 是人性的扭曲和丑恶的显露。 宁静与纯洁, 再也无法找回。 人类在阴谋与威胁中艰难地行进, 稍不留神就会坠入深渊。 无处不在的危险向人们步步紧逼, 令人失去理智。 生活, 混乱无序。 人, 近乎非人。 “他成了寒酸和神经错乱的人, /他开始饮酒, 以鼓起勇气去谋杀; ∥或者坐在办公室里偷窃, /变成了法律和秩序的赞颂者, /并且以整个的心憎恨生活。”(《在战争时期·五》)
也许是因为欲望的永在, 穆旦的诗里也遍布着威胁与阴谋。 对诱惑与危机的书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然而, 穆旦对威胁与诱惑的表达常常带有对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存在的悲悯, 这就使穆旦再次与自己的诗歌偶像奥登产生了关联。 与奥登相仿, 穆旦带着对彼岸的怀想, 讲述着今生罪恶的渊薮。 在穆旦的诗作里, “阴谋”与“谋害”这样的词语也经常出现。 比如: “虽然, 塑在宝座里, 他的容貌∥仍旧闪着伟业的, 降伏的光芒, /已在谋害里贪生。”(《潮汐》)又如: “无尽的阴谋; 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 /是你们教了我鲁迅的杂文。 ……愚蠢的人们就扑进泥沼里, /而谋害者, 凯歌着五月的自由, /紧握一切无形电力的总枢纽。”(《五月》)诗人仿佛是多次吃过轻信的亏, 陷入了阴谋难以逃离, 于是, 友谊也难以信赖。 “只有你是我的弟兄, 我的朋友, /多久了, 我们曾经沿着无形的墙/一块儿走路。 暗暗地, 温柔地, /(为了生活也为了幸福, )再让我们交换冷笑, 阴谋和残酷。”(《从空虚到充实》)
各种各样的诱惑就是形形色色的阴谋与潜在的威胁, 就像许多看不见的力量拉扯着脆弱的人, 分流着他们苦苦前行的努力。 在众多的选择面前, 到底该何去何从? 人类似乎注定要迷失, 迷失在自我的脆弱和惶惑。 人类也许终将堕落, 堕落于潜在的欲望和不安。 就像穆旦《控诉》里写到的那样:“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生命永远诱惑着我们/在苦难里, 渴求安乐的陷阱。” 太多的诱惑如影随形, 最终造成了人类挥之不去的困惑。 困惑在恒定的短暂甚至匮乏, 困惑在太多期待的不可得兼。 在生之永恒的苦难里, 可怜的我们祈盼安乐。 可谁知安乐竟是陷阱, 它不过是人类在看不到尽头的挣扎中虚构出的一根稻草。 当我们猛力伸出手想要抓住它的时候, 却发现手中空空如也。 梦醒时, 未来一片虚无, 只剩下永远也无法追回的过去, 似乎记忆才是茫然一片中残存的真实。 于是, “阴霾的日子, 在知识的期待中, /我们想着那样有力的童年。”我们唯一可做的只有追忆往昔, 不经事的“童年”也因而变得“有力”。 与童年相对照, “成长”似乎徒有虚名。 年龄的增长让所谓的“智慧”丰富, 而智慧越丰富, 欲望和可能也就越多, 前行的阻力也就越大。 因此, 在穆旦看来, “智慧使我们懦弱无能”。 穆旦确实是太过清醒, 他看到了现象背后潜在的危机, 也道出了更深层次的普遍的真实。 诗的结尾, 诗人发人深思地写道: “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呵, 谁该负责这样的罪行; /一个平凡的人, 里面蕴藏着/无数的暗杀, 无数的诞生。” (《控诉》)
5 结 语
“奥登对穆旦诗歌创作的影响”是一个几近常识却又少有人具体分析的话题。 究其原因, 可能不仅仅在于穆旦生前好友袁可嘉、 杜运燮等人的简要论断已经为这一话题“一锤定音”, 令后人难以“再创新辞”, 还在于中国读者对奥登的相对陌生。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所做的分析并非要把穆旦视为奥登拙劣的模仿者, 笔者也并不认为穆旦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意义仅仅在于向西方寻求了资源。 穆旦是丰富复杂的, 其诗歌特色绝非奥登之影响所能概括。 近来出现了一些否定穆旦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的价值的论断, 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看到穆旦向奥登的借鉴是在特定文学环境下冲破传统和自身的一种努力。 当文学止步不前时, 自觉的革新者们自然要为文学变革寻找资源和依托, 这样的资源寻求无非有两个方向——要么向内, 要么向外。 鲁迅向内依托着六朝文章之“清俊” “通脱”, 向外看到了厨川百村和安特莱夫; 周作人则找到了明清散文和日本俳句以及印度小诗。 正如鲁迅、 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并不会因为他们向外寻求资源而受到丝毫降低和削减, 穆旦为新诗的发展与革新所做的向英诗学习的努力也不可简单地归结于“在中国复制出一个奥登”[9]。
[1]Stan Smith. W H. Aude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4.
[2]Jay Parini, Brett C. Millier.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american poetry[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5.
[3]穆旦. 英国现代诗选[M]. 查良铮, 译.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4]穆旦. 穆旦诗文集[M]. 李方, 编.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5]黄瑛. W. H. 奥登在中国[J]. 中国文学研究, 2006(1): 103-107.
[6]Richard Hoggart. AUDEN: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M].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N. J., 1964.
[7]穆旦. 穆旦诗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8]段从学. 《出发》与穆旦的宗教意识[J]. 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6, 21(4): 15-21.
[9]江弱水. 伪奥登风与非中国性——重估穆旦[J]. 外国文学评论, 2002(3): 124-132.
Human Life in Wartime from the Viewpoint of God——W. H. Auden’s Influence on Mu Dan’s Poetic Themes
LONG Xiaoyi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Mu Dan draws Christian thoughts while he borrows poetic creative experience from W. H. Auden. Therefore, Mu Dan and Auden share common poetic themes in their works: the theme of inescapable destiny from original evil, the theme of war as human suffering in reality, the theme of mistake and failure of human beings as an imperfect species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 the theme of conspiracy and threat in human beings’ real life of temptation and crisis. The imitation of Mu Dan from Auden is an effort to transcend tradition and oneself in certain literary circumstances.
W. H. Auden; Mu Dan; Christian thoughts
1673-1646(2017)02-0090-07
2016-11-02
龙晓滢(1982-), 女, 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从事专业: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
I207.25
A
10.3969/j.issn.1673-1646.2017.0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