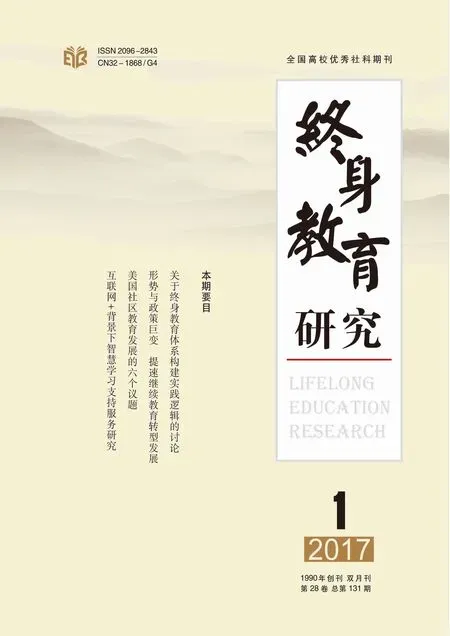推动终身教育发展的重要人物及学术著作
保罗·朗格朗
推动终身教育发展的重要人物及学术著作
保罗·朗格朗
在实践中,保罗·朗格朗不断将自身的教育经验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结合,系统地诠释了终身教育思想。他的基本观点是:终身教育并非传统教育的简单延伸,而是“一系列很具体的思想、实验和成就,换言之,是完全意义上的教育,它包括了教育的所有方面、各项内容,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时为止的不间断的发展,包括了教育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有机联系。”在他看来,终身教育的目标在于“努力建设一个将保证自己的公民更多和更公平地分享消费品和文化资源的社会,也就是为了丰富和改善精神生活”,促进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要尊重人的个性,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过一种更和谐、更充实、符合生命真谛的生活”,又要为社会培养新人,实现教育民主化的理想。针对传统学校教育存在的诸多弊端,朗格朗指出,必须以终身教育思想为依据,对学校教育的教育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将学习的重点从“必然局限、刻板的内容”转到增进“理解的能力、吸收和分析的能力、把学得的知识加以条理化的能力、应付裕如地处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和一般与特殊之间关系的能力、把知和行联系起来的能力以及协调专业训练和学识广博的能力”中。而跨越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之间的鸿沟,使学生学会学习、实现自我,增强生活的意义,创造更美好的世界,则是终身教育应该追求的理想与目标。
主要代表作和论文有《终身教育引论》《终身教育为何重要》(1966)《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1969)《终身教育的问题》(1970)《未来的人》(1975)《终身教育的前景》(1979)《以终身教育为基础的学习领域》(1986)《终身教育:概念的发展》(1989)等。
(执笔:李艳)
埃托雷·捷尔比
埃托雷·捷尔比(Ettore Gelpi)(1933—2002)[8,10-11]。意大利教育学家、思想家,民主与实践终身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与推动者,反体制终身教育学派的代表。
1933年出生于意大利米兰,最初在米兰大学专攻历史、哲学与宪法,并获博士学位; 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在米兰郊区移民劳动者集居的区域从事文化与社区发展活动(Community Development);从1957年至1961年,转至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Società Umanitaria协会的米兰综合制中学工作;1962年,转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获得教育硕士学位;1970年至1972年,在意大利总同盟(Confederazione Generale Italian del Lavoro)为担任专门职务的教员进行再培训而设置的特别委员会任委员长;1971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服务于非洲的象牙海岸;1972年至1993年,接替保罗·郎格朗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教育部门的负责人;1994年至1995年,在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任成人教育协调员;1995年,在苏黎世ECAP-CGIL科学委员会任主席;1995年至1997年,在欧盟教育与俄罗斯联邦一项教育政策合作中任专家;1997年,任CEMEA(Training Centers Active Methods of Education,积极教育法培训中心)国际联盟主席,与巴黎、东京、佛罗伦萨、巴塞罗那、墨西哥等地著名高校开展教学合作。
捷尔比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教育事业,他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感受到那些移民劳动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穷者、无家可归的流浪少年以及在殖民地身受欺侮的有色人种所遭受到的痛苦和不满。为了“解放”这些受到环境重压的人们,他的终身教育思想散发出浓郁的“斗争”哲理。他明言:“终身教育绝不具有政治上的中立性。”1983年,捷尔比出版了《终身教育——被压制与解放的辩证法》,进一步阐发了终身教育的思想,而以此思想为代表的反体制终身教育理论亦开始形成。
(执笔:赵华)
R.H.戴维
R.H.戴维(Ravindrakumar H.Dave)[12-18]1929年出生于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他先后在印度孟买大学、古吉拉特邦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教育学。离开印度前,他曾担任印度国家教育研究与培训理事会 (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的教授和主任,以及课程与评估、教材和教师教育等多个部门的负责人。1972年至1976年间,他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技术所长,极大地推动了研究所多个研究项目的开展。1976年至1979年间,他又任职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UNESCO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法国巴黎)。1979年,他再次回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并担任所长,直至1989年退休。退休以后,他继续服务于教育界,如担任印度学校教育理事会 (Indian Council of Board of School Education)的首席顾问,圣雄甘地古吉拉特大学 (Mahatma Gandhi's Gujarat University) 访问教授,同时在其他教育机构担任类似职务。
R.H.戴维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在推动终身教育的研究与发展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他倡导以整体性和连续性的视角看待教育,强调教育是贯穿人生各个阶段的连续历程,强调终身教育实现形式的多样性及丰富性。他注重教育概念和教育理论在实际工作中的应用,并重视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教育概念进行解读和研究。他提倡对教育实践的关注,鼓励审视和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教育实践的异同,认为教育理论的构建、教育理念的推广、深化和创新、教育教学方法的开发等都应该以教育实践为基础。
大学课堂教学,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学是对大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主渠道。高校教师要坚持言教与身教相结合,坚持继承传统与创新手段相结合,着力提升课堂教学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着力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性和实效性。尤其是思想政治课教师,要在真知、真懂、真信、真讲上下功夫,在培养真情、付出真爱上下功夫,紧密结合青年学生的思想实际,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通俗化、具体化,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从而引导大学生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个人需求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培养他们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
他还编著了许多具有影响力的研究论文和教育专著,如《教育评价和评估》《扫盲后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学习策略:跨国视角的研究》《终身教育和教师的培训:以终身教育为准则的师资培训课程》《为扫盲和扫盲后教育项目设计一个评价和监控体系》《终身教育基础》《关于终身教育与学校的反思》《终身教育与学校课程》等。其中《终身教育基础》是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终身教育论著之一。在本书中,R.H.戴维认为,由于终身教育概念内涵的综合性和呈现形式的多样性,很难被准确定义,因而往往会被片面解读。因此,在进行大量文献分析和访谈的基础上,R.H.戴维归纳出终身教育概念的20个基本特征,并从意义、功能、目标等角度进行了综合分析,他还从跨学科的视角解读终身教育的指导原则以及多侧面的呈现形式,以确保它获得完整的解读。由于R.H.戴维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准确把握了终身教育概念的内涵,以及形成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由此为终身教育理念的传播、实践的运用发挥了关键而奠基的作用。
(执笔:王默、杨进)
克罗普利
克罗普利(Arthur· John· Cropley)[19-22]1935年出生于澳大利亚的南澳大利亚州,19岁即毕业于阿德雷德大学的艺术与教育专业。此后曾在澳大利亚、英格兰以及加拿大的中学教书。1965年又获得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教育心理学的博士学位。在新英格兰大学教了两年(1965—1967)心理学以后,于1976年开始任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其后又被聘为汉堡大学心理学教授。
他的贡献在于将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于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探索,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他与当时的终身学习研究所所长戴维(R.H.Dave)合著了《终身教育基础》,开拓性地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实验研究成果,拓展了终身学习研究的新视野。其著作《终身教育:心理学的分析》(Lifelong education:A psychological analysis,1977)《对终身教育的盘点》(Lifelong education,a stocktaking,1979),与纳普尔(C.K.Knapper)教授合著的《高等教育与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1985)等都引起了国际终身教育学界的关注。与此同时,他还参与了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终身教育规划与实施工作,对终身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执笔:邓璐)
《终身教育引论》
《终身教育引论》[1,8,23-25]法国成人教育家、终身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的代表作。196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届成人教育国际促进会议(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ult Education)召开,朗格朗在会上提出《关于终身教育》的提案,在此基础上,1970年写成并出版了《终身教育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Lifelong Education)。该书一经出版即引起广泛关注。至1983年,已被译成17种文字广为流传,并被公认为终身教育理论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在初版序中指出,“本书旨在阐述终身教育思想的不断发展变化的重要意义,说明促使它产生和发展的各种力量,探讨它的含义和内容,指出它对人类整个教育活动的影响和将会产生的后果。”
本书由前言、终身教育探索、全面综述以及论证和实例等4部分构成。前言部分主要交代了本书的内容结构与读者对象,探索部分简要回顾了作者的终身教育思想探索及其形成过程。综述部分包含7章,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现代人面临的各种挑战,终身教育具有的重要意义,包含的内容、范围和目标,以及关于终身教育战略的建议。
该书的重要贡献是对终身教育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全面的界定,指出:“教育的真正对象是全面的人,是处在各种环境中的人,是担负着各种责任的人,简言之,是具体的人。”由此,教育应坚持4个目的:(1)积极接受变动的目的;(2)愉快的目的;(3)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4)和平与国际谅解的目的。
(执笔:李艳)
《学习社会》
《学习社会》[8,26-27]是美国永恒主义教育思潮代表人物罗伯特·赫钦斯于1968年出版的专著,明确提出了走向“学习社会”(The Learning Society)的教育理想,是系统论述“学习社会”理念的第一部专著。赫钦斯在书中对教育的功利化、职业化倾向提出批判,认为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瓦解和社会的富足,未来将出现一个人们不必为了生计而终日劳作的闲暇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类将以“睿智、愉快、美好的生活”为价值追求,教育将不再是政治和经济的附庸,而是回归其本来面目,人人都将有机会终身享受以“学习、自我实现和成为真正的人”为目的的自由教育。
赫钦斯对“教育”与“教育制度”2个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教育”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地帮助人们发展其心智(mind)的活动。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于理解,除此之外没有更加实用的目的。制造基督徒、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工人、公民、法国人或商人等都不是它的目的。教育之旨趣在于使人的头脑(mind)得到发展,并由此实现人的发展。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力(manpower),而是培养人(manhood)。”“教育制度”则是承载教育的具体形式,必须反映政治社会的意志。人们总是根据“社会需要什么”而不是“真正的教育是什么”来确定教育制度,从而导致过去所有的教育制度都未能提供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只是一些包含了教育的某些要素。赫钦斯以“教育”为一把标尺,衡量所有的“教育制度”,指出一种教育制度是不是在提供真正的教育,取决于它是不是真正地以培养“人”为目的。
运用这一“标尺”,赫钦斯对当时流行的教育观念进行了批判。在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普遍认为个人受的教育越多,或上学的时间越长,他就越能够拥有美好的前景;而一个国家受过教育的公民比例越高,这个国家也就越富强,因而教育被认为是一种“最好的投资”。国家亦把投资教育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个人也期冀通过追求更高的学历来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收入。但是,赫钦斯指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不可预期性,未来对人才的需求也是随时变化的,以当下的预期来培养未来的人才,往往会产生偏差,并培养出过时的人才;而且,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教育制度把人视为生产工具,并且训导人们自己也这样看待自己。这种教育制度的重点将放在就业上,把教学和就业联系起来。各级教育被认为应当给接受了不同等级教育的学生以从事某种特定工作的资格。如果大量学生的教育层次都达到了从事某种工作所需要的资格但却得不到这类工作时,就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从而影响经济增长。如果一个人把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和就业联系起来,当他具备了相应的资格却没有得到相应工作的时候,他也会感到自己受了欺骗并产生怨恨。即使教育有可能带来国家的繁荣和提升个人的地位,但这也不是教育的终极目的所在。“教育投资论”造成了教育目的的偏离,教育“最经常被强调的目的不是提高理解力或提升心智水平或帮助人们通过使用头脑成为人,而是经济增长”。赫钦斯进而提出,最好的教育不是那些为了培养某一类人才而设计的专门教育,而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理解能力和心智水平而开展的自由教育。
赫钦斯指出,在21世纪,人人都将享有自由教育。在现代社会提倡自由教育并不是要以希腊语、拉丁语,或古典巨著作为课程内容,这些只是培养学生理解能力和批判能力的手段,而手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和结果。自由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尽可能地变得心智聪明,提高理解力,使其思想自由。它传授从事理智活动所需的技能,使学生熟悉生活于其中的知识传统,向学生打开新的世界。人们必须认识到,在现代社会,第一,人人都有享受自由教育的权利和能力;第二,自由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实践者,而是发展人们的心智,让年轻人养成思考的习惯和思考最重要事情的能力,让他们具备鉴别事物重要与否的判断能力,使他们能够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使他们为终身的学习做好准备;第三,自由教育所能做的就是使他能够理解和反思经验,从而成为一个更加充满智慧的人,人要实现其潜能,就必须终身地学习和再学习。人在其一生的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做出残忍或愚蠢之举,保存人性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学习。
在此基础上,赫钦斯进一步提出了“学习社会”的构想。学习社会的出现有两个前提条件。其一,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在未来社会,大量的人类劳动将被机器所替代,经济也日益富足而使得人们无须再为生计而终日劳作,于是将由劳碌社会转变为经济学家凯恩斯所预言的闲暇社会。劳碌的人们将普遍获得大量闲暇,这将为人们通向无限的教育奠定基础。其二,社会快速变化,“大一新生所修的某个科目等到他四年级的时候就会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最好的教育不是根据现在的技术水平去培养未来的工作者,而是要培养人的理性,发展人的心智,使人成为人,使人们认识到他们普遍的人性,这样人们才能应对所有可能发生的变化,而这一过程必须是终身性的。
但是上述2个条件并不必然导致学习社会自动到来。在传统的社会,专注于工作是实现个人价值的根本方式,人们将工作视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视为其自身存在的价值所在。当人们突然获得大量闲暇时间的时候,最初将感到无所适从。因此,学习社会必须实现价值的转换,使人们学会安排闲暇时光,并以“睿智、愉快、美好的生活”为价值追求。
简言之,赫钦斯所描述的学习社会应该是——“(它)不仅为处于人生任何阶段的每一个成年男女提供闲时的成人教育,而且社会的价值成功地实现了转变。学习社会的目的是学习,是自我实现,是成其为人,而学习社会的所有机构或制度都以这一目的为指向”。具体而言,在学习社会中,人们不再以工作和经济发展为唯一目标,而是转而追求睿智、愉快、美好的生活;由此教育的价值也回归其本身,即致力于培养普遍的人性,而不是作为一种和某类工作或某个职位挂钩的训练和信息灌输。在学习社会中,人人都将接受基本的自由教育,以使其心智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为其终身追求自由的教育和人格的完善奠定基础,并终其一生自由学习。所谓自由教育,又是以培养理解的能力、思考判断的能力为目标,人们通过自由教育来追求至善的人性。自由教育也不是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和固定的人生阶段进行的一种割裂的活动,而是人们追求自我实现和人格完善的手段,是整个社会的目的,并且整个社会的文化都在提供这样一种教育。
(执笔:周晟)
《终身教育——被压制与解放的辩证法》
《终身教育——被压制与解放的辩证法》是埃托雷·捷尔比1983年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捷尔比在书中对终身教育思想进行了4个方面的论述:(1)提倡运用辩证法的方法论,为实现终身教育的终极目标——帮助那些受到压制,受到榨取及遭受差别的人们脱离困境,提出自觉追求“自我决定学习”的斗争策略;(2)对所有遭受社会不公平待遇的人们,终身教育应该站在社会公正的立场对他们的要求予以声援;(3)应改变以往的“为了适应社会的变化而倡导终身教育”的被动构想,积极引入为了人类解放所必须采取的“自我决定学习”的能动理论;(4)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之际,应从劳动者的日常生活需要及以生产劳动为原点进行考察。即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知识、技能及训练,应该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出发点。
相对20世纪60年代,保罗·郎格朗从西方先进国家的立场出发,倡导克服危机型的终身教育理论以来,在20世纪70年代,捷尔比站在第三世界“社会弱者”的立场,构筑了为贫者争取解放的斗争型终身教育理念,从民族自主的发展立场来考虑终身教育的课题。学术界普遍认为,捷尔比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了现代终身教育的思想。
(执笔:赵华)
《终身教育基础》
《终身教育基础》(Foundations of lifelong education)[16]是20世纪70年代,由设在德国汉堡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研究所所长R.H.Dave领衔主持的研究课题及最终成果。该著作记录了R.H.Dave领导的研究团队在进行这一研究项目时的缘起、目标、范围、方法及研究流程和研究成果等,是目前国际上有关终身教育的经典论著之一。
《终身教育基础》对终身教育概念总结了20个基本特征:(1)终身教育的含义构建在三个基本术语之上,即生活、终身和教育。因此,对上述术语的界定和阐述,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终身教育概念的范围和含义。(2)教育不应该终止于正规学校教育的终结,而应该是一个终身的过程。终身教育覆盖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3)终身教育不仅局限于成人教育,它还包含和统领教育的各个阶段——学前、小学、中学等。因此,它试图概括的是教育的整体性。(4)终身教育包括正规、非正规和无一定形式的教育模式。(5)家庭在启动终身学习的过程中起到首要的、微妙的和关键的作用。家庭学习过程会一直持续和覆盖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历程。(6)社区在终身教育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人们在孩童时期开始与它有交互活动起,社区的教育功能就开始显现和发挥。它的教育功能会持续覆盖人们的职业生涯和生活的方方面面。(7)教育机构,如学校、大学和培训中心的作用当然重要,但它们只是终身教育载体的一种形式。它们不能再“垄断”人们的教育,也不能和社会中其他具有教育功能的载体割裂开来。(8)终身教育将教育视为一个连续的、可以不断衔接的过程。(9)终身教育也旨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实现横向的整合和深化。(10)与精英教育相反,终身教育强调教育的普遍性,代表了教育的民主化。(11)终身教育的特点体现在它所囊括的教育内容、学习的工具和技术,以及学习时间的灵活性和多样性。(12)终身教育强调教育方式的动态化,这样才能根据新的发展状况不断调整学习材料和媒介。(13)终身教育允许以可替代的模式和形式来获得教育。(14)终身教育由2大部分组成: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这些组成部分之间不是截然不同的,而是在本质上关联和互动。(15)个人和社会的适应和创新能力可以通过终身教育来实现。(16)终身教育具备矫正功能,它能对现有教育系统的不足进行修正。(17)终身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维持和改善生活质量。(18)终身教育主要有3个先决条件:机会、激励和可教育性。(19)终身教育是所有教育的组织原则。(20)在操作层面,终身教育为所有教育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系统。
(执笔:王默、杨进)
《终身教育:心理学的分析》
《终身教育:心理学的分析》(Lifelong education:A psychological analysis)[20-21]是克罗普利教授撰写的一部从心理学的视角分析终身教育的专著,出版于1977年。自20世纪60年代终身教育理念被提出以来,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倡导把终身教育作为每个社会中组织各类教育的主导思想。为了宣传并实施这一指导理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在1972年5月决定把以终身教育为主旨的学校教育改革作为国际合作研究项目的重点。本书即是该所与克罗普利教授合作产生的研究成果。
本书主要解决2个问题:一是检验终身教育的心理学假设;二是阐明以终身教育为导向的教育体系的心理学含义。为此从5个方面进行了论述:(1)描述终身教育主要的心理学特征;(2)用心理学术语陈述终身教育的主要观点;(3)以事实说明这些观点的有效性;(4)分析学校课程按终身教育框架重新设置,心理学知识对学校课程设置具有的意义;(5)研究近年来对终身教育提出的批评,并论述进一步研究对终身教育的意义。
本书由8章构成,第一章介绍现代教育面临变化的挑战。第二章对支持终身教育思想的论点作了分析。第三章指出为了证实终身教育原则的合理性,应用基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意义。第四、五、六章综述心理机能对人作用的研究结果,以验证终身教育原则合乎于各个年龄阶段的心理机能;第七章阐明心理学背景下,终身教育对学校所具有的意义;第八章对终身教育进行批判性评价,侧重于心理学问题及其他评论。
本书在终身教育研究领域实现了两大突破:一是拓展了终身教育研究的心理学视角,进一步完善了终身教育的实证基础。二是将终身教育研究视域从成人教育领域拓展到了正规学校教育范畴,强化了国际组织将终身教育覆盖于学校教育的主张。
(执笔:邓璐)
[1] 叶澜.终身教育视界: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聚通与提升[J].中国教育科学,2016(3):41-67.
[2] 宫坂广作.生涯学习的理论[M].明石书店,1990:39.
[3] 保罗·朗格朗.终身教育引论[M].周南照,陈树清,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
[4] 平塚益德.世界教育辞典[M].黄德诚,夏凤鸾,等,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307.
[5] 吴式颖.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十卷——20世纪的教育思想(下)[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412,418.
[6] 朱镜人.外国教育思想简史[M].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266.
[7] 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4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340-343.
[8] 吴遵民.新版现代国际终身教育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7,45.
[9] 何光全.培罗· 朗格朗(1910年—2003年1月30日)[J].成人教育,2012:封二.
[10] 捷尔比.维基百科[EB/OL].[2013-04-12].http:∥it.wikipedia.org/wiki/Ettore_Gelpi.
[11] 焦春林.捷尔比终身教育思想研究[J].成人教育,2009(3):17-18.
[12] Ravindrakumar H.Dave,P.M. Patel.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Assessment[M].New Dehli:National Counci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Training,1972.
[13] Ravindrakumar H. Dave,Adama Ouane,D.A. Perera,etc.Learning Strategies for Post-literacy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A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M]. Hamburg:UIE,1985.
[14] Arthur J.Cropley,Ravindrakumar H.Dave. Lifelong Education and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Developing A Curriculum for Teacher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Principles of Lifelong Education[M]. Hamburg:UIE; Oxford:Pergamon Press,1978.
[15] Ravindrakumar H.Dave.Designing a system of evaluation and monitoring for literacy and post-literacy programmes[M]. Paris: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Paris: the text-processing facilit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ducational Planning,1985.
[16] Ravindrakumar H.Dave.Foundations of Lifelong Education[M].Hamburg:UNESC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Oxford:Pergamon Press,1976.
[17] Ravindrakumar H.Dave,Malcolm S. Knowles,Karl-Heinz Flechsig,etc.Reflections on Lifelong Education and the School[M]. Hamburg:UNESC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1975.
[18] Ravindrakumar H.Dave.Lifelong Education and School Curriculum[M].Hamburg:UNESCO Institute for Education,1973.
[1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网站[EB/OL].[2016-09-10].http:∥www.uil.unesco.org/.
[20] Cropley,A.J.Lifelong Education:A Psychological Analysis [M].Oxford and New York:Pergamon Press,1977.
[21] 克罗普利.终身教育:心理学的分析[M].沈金荣,等,译.北京: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
[22] 克里斯托弗·K·纳普尔,阿瑟·J·克罗普利.高等教育与终身学习[M].3版.徐辉,陈晓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3] 李明德,金锵.教育名著评介·外国卷[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526-527,529.
[24] 单中惠,朱镜人.外国教育经典解读[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345,348.
[25] 单中惠.外国教育思想史[M].2版.上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09.
[26] R.M.Hutchins.The Learning Society[M].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1968.
[27] 罗伯特·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 虞晓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