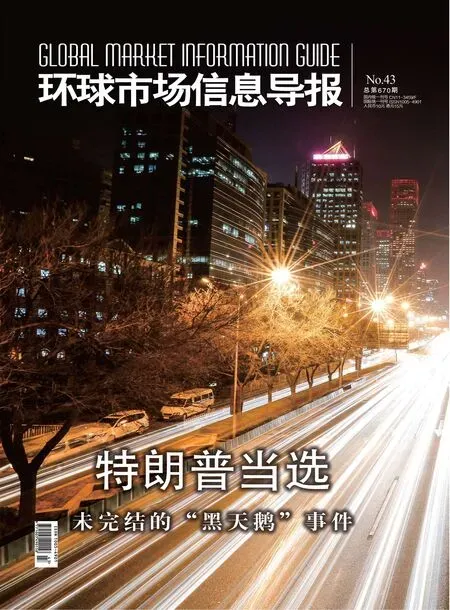《纽约时报》,或许就是媒体转型的最佳样本
《纽约时报》,或许就是媒体转型的最佳样本
Point
尽管我们尚无法评判,传承到第五代的这份“家族报纸”能否转型成功,但起码它曾经或仍然在定义着一个成功的媒体所应具备和承担的职能。

今年稍早时候,《纽约时报》迎来了它的第五代“领导人”——亚瑟·格雷格·苏兹贝格。这意味着这份传承了120年的媒体巨头迎来了它的新时代。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全球媒体掀起数字化转型的浪潮,《纽约时报》早在前两年就开始了“转型之路”。2014年上半年,《纽约时报》那份96页的内部研究报告在呈送到其高层后,就传遍了海内外媒体圈。在我的记忆中,当时正值国内媒体圈对有关媒体转型的话题讨论得甚嚣尘上之时,几乎所有国内媒体人都想方设法地搞到了这份报告:管理者以期从中寻找到转型的灵感,记者、编辑希望看到自己在未来可能担任的角色,其他八卦好事之徒则好奇多年后媒体会变成什么模样。
遗憾的是,不知道是否由于这份报告过于冗长,它并没给国内媒体在转型的道路上带来太多共识,至今,我们的媒体转型仍然只是在各说各话——每个人在自己认定的道路上艰难前行,留下一地鸡毛。
在数字化时代,作为一份有着120年历史的传统媒体,它依旧是全球的行业标杆。尽管我们尚无法评判,传承到第五代的这份“家族报纸”能否转型成功,但起码它曾经或仍然在定义着一个成功的媒体所应具备和承担的职能。
有意思的是,从上世纪初起,在《纽约时报》就职的记者、编辑和管理人员就十分清楚这个名字所意味着的巨大荣耀,并且他们并不会刻意去对其表示出谦虚和保留,即使他们偶尔也会对其发出批评,但从未怀疑过这四个字所拥有的巨大能量。曾经在《纽约时报》任职了十余年的盖伊·特立斯就是一个例子。

这位被后世称为“新新闻主义之父”的作者,最初不过是《纽约时报》的一个送稿生:也就是给编辑跑腿儿送报纸文章,给记者买三明治、咖啡,为临时出席活动的部门主任买皮鞋、皮带、领带……他们也有可能写一些无关紧要的小稿子,运气好甚至可能登到《纽约时报》,但不会有署名。
不过,他在上班第二个星期里,就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写的是时报大厦外的滚动广告牌(用灯泡组成,只显示新闻标题,类似于今天液晶显示的跑马灯),以及操作这个广告牌的“灯泡男”。在升为记者后,特立斯长期跑的是体育条线。正是有了这个职业生涯的“伏笔”,在离开时报多年之后,特立斯依旧出于职业敏感而关注到了中国女子足球队。
在离开《纽约时报》不久,特立斯便开始回顾自己在《纽约时报》的经历。他在写了一篇有关当时《纽约时报》的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1964-1969年担任主编)的文章后,又继续挖掘克利夫顿与管理层其他人员的关系,在这其中他采访了在或曾在时报供职的上百位人士,最终碰触到了这份伟大报纸的历史,并将其还原在纸张之间,这就是《王国与权力:撼动世界的〈纽约时报〉》。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特立斯的这本书里,克利夫顿会经常穿插出现,用作者自己的话说,这本传记作品是在克利夫顿的采访基础上衍生而成的衍生品。所以,我们也能看到,《王国与权力》的叙述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展开,而是按照人物角色来展开。很显然,特立斯认为,这些“重要角色”是带领时报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也同样是这些“重要角色”给时报带来了曾经经历的那些挑战、矛盾、困惑和迷惘。
如果把克利夫顿看成是特立斯这个“宏大故事”的引子的话,我们想要了解时报的精神品质,就不得不去追溯它的“奠基者”阿道夫·奥克斯。之所以我们在这里将奥克斯称为“奠基者”,而非创办者,是因为《纽约时报》是由亨利·贾维斯·雷蒙德和乔治·琼斯在1851年9月18日创办的,最初的名字是《纽约每日时报》,到6年后才正式改为今天的名字——《纽约时报》。
不过,半个世纪不到,《纽约时报》就陷于濒临破产的境地。这时候作为南方报纸《查塔努加时报》的老板,奥克斯以75000美元收购了《纽约时报》,正式开启了《纽约时报》的王国。奥克斯上任后,就开始对《纽约时报》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三年内就将时报的发行量从9000份提升到了75000份,其广告量也出现大幅增长。特立斯如此评价奥克斯:他的“天才不仅在于他创造的报纸的类型,而且在于他使这个报纸赚了钱”。
对此,我们可能会意识到,这个“对报纸有着特殊热情的小个子”在媒体经营上所具有的平衡观念:他希望报纸能够盈利,同样又希望能够杜绝利润的诱惑;他希望“不仅仅是为了利润而经营《纽约时报》,而且多少要遵循伟大教会的经营路线,靠美德来给财富镀金”。
除去经营,奥克斯的“平衡观念”还体现在新闻报道上。1897年,奥克斯就为《纽约时报》确定了报道原则:报道“所有值得印刷的新闻”。这一原则直到今天仍然是时报的圭臬。同时,奥克斯还认为,新闻报道应该“力求真实,无畏无惧,不偏不倚,并不分党派、地域或任何特殊利益”。
正是有了这些原则的存在,《纽约时报》诞生之初似乎更像是个“怪物”,尤其是与当时那些偏好报道小道消息和乱发评论的媒体相比,《纽约时报》却不断地扩张版面来为读者提供新闻信息;同时,时报还十分注重抑制发表自己的观点,而只把评论的版面圈囿在有限的栏目里,尽管它在历史上并不缺少犀利的评论。这样的办报理念,可以说直到今天对大部分媒体来说都极为另类。
当然,随着时报的成功和扩张,它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起码在外观上来看,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新闻工厂”。
“它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的大屋子,从第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据着《纽约时报》14层大楼的第三层,内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打字机和电话连接起来,几百个人手里握着笔坐着,或者敲击打字机,写作、编辑或阅读着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看起来,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仰光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政变或者地震。但所有这一切似乎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这些消息像是一种无害的病毒,漂流进这座大楼,通过这个系统流传,在打字机上进出,经过笔下加工,进入旋转的金属机器,被印在报纸上,装进卡车,分发到报摊,销售给容易烦恼的读者,在世界上引起反应和反行动。”
特立斯的这段速写,为我们鲜活地呈现出了时报编辑部的表面模样。或许,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景象的“观众”都会感叹这个庞大的“新闻流水线”——这是现代新闻工业的巅峰。
正是基于这种“新闻生产”的理念,奥克斯虽然并不否认个人才能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但他更希望自己的雇员能有鲜明的团队精神,能够尊重时报的价值观。所以,“应该雇佣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有才能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纽约时报》没有哪个人是不可或缺的”。这样的用人标准,使得时报在一个世纪以来的运作过程中,得以将奥克斯确立的报道标准和经营原则一以贯之。有趣的是,这种限制性的用人原则并没挡住《纽约时报》不断涌现出“新闻明星”。
更有意思的是,《纽约时报》这么多年来都严苛地保持着家族经营的模式。奥克斯曾要求“自己去世后,《纽约时报》应只由他的家庭中的直系亲属来掌管,进而再由他们的家庭成员来控制,他们全都有责任以他所具有的那种奉献精神在一生中进行管理。”这个看似传统保守的经营原则,竟然不可置信地被保留至今。我们很难判定,这个传统的人事原则在《纽约时报》的成功过程中起到了何种作用,但它确实保证了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时报领导层的相对稳定。
当然,同一切大机构一样,《纽约时报》也不可避免地遭遇过内部纠纷和权力斗争。尤其是纽约总部和华盛顿分社的矛盾,特立斯将其穿插于整部作品的始终。在特立斯的笔下,这两个机构之间的斗争之激烈,并不亚于其他大企业里的高层权斗。可以想象,特立斯通过这样的描写也是在提醒我们,《纽约时报》的历史同样面临着挑战和分裂,“《纽约时报》是人的组织,庞大而脆弱”。
诚然,曾经作为记者的特立斯,在写作过程中无法抛开新闻报道的风格影响,也因此我们可能无法直接从这部作品中获得《纽约时报》的成功经验。更何况,在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让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应对技术手段的冲击上。这也使得特立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所写的有关《纽约时报》的故事,似乎多少就有些不合时宜了。
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忽略了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作为一个19世纪末成长起来的媒体,《纽约时报》经历了广播技术、电视技术、数字技术这三个媒体史上的大转折,但它在今天依旧傲然卓立于世。从这一点来看,《纽约时报》就可以被看作是媒体转型成功的最佳样本和案例。
所以,读它的历史和故事,我们就一定能从中有所体悟:对于今天的媒体来说,哪些法则和习惯应该被抛弃,哪些观念和原则又值得珍视和保留。就像特立斯在结尾处写道,“就要像一棵根深蒂固然而又灵活的大树,每天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摇摆,在摇掉了它的衰老的旧叶子后进行调整,保持四季茂盛。”
(文/严杰夫 来源/经济观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