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摄影之路
林叶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领舰队敲开了日本的大门。自此,日本开始大量接受来自西方的文化。1860年代之后,照相馆开始迅速在日本各地出现并很快得到普及。在那个时代,去照相馆拍照这种行为,就是证明自己拥有迎接新时代的勇气。随着摄影在日本接受度的提高与发展,摄影很快就与日本传统工艺相结合,出现了以外国人为主要销售对象的“横滨写真”。于是,传统工艺便渐渐被纳入到摄影创作之中。出现了“写真画”、“写真屏风”之类的工艺品。这种以照片为材料的工艺品的出现,导致摄影被排除出“美术”,纳入“工艺”或“工业”部门之中。
明治中期,绘画获得了“艺术”的地位,而摄影则是以再现技术的身份存在停留在实用性的技术上。从这个时期开始,摄影便努力尝试在类似绘画的特性中去寻求成为艺术的可能,希望能够通过对绘画的模仿上升到艺术的高度。而画意主义摄影在日本出现,更是让摄影成为了一种“追赶绘画”的行为。直到新兴摄影出现为止,摄影的本质在日本始终没有得到严肃而正式的讨论,一直作为一种主观表现的手段,笼罩在“艺术”的阴影之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艺术摄影在欧洲逐渐式微,以拉兹洛·莫霍里-纳吉(Laszlo Moholy Nagy)为代表的德国新摄影运动开始兴起。1925年,莫霍里-纳吉出版了《绘画·摄影·电影》一书,对摄影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新兴摄影的势头逐渐高涨,这一摄影运动被引入日本之后,也相应地对日本摄影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29年,摄影编辑、摄影家木村专一(1900-1938)开始积极地在《摄影时代》杂志上对新兴摄影进行介绍。
1929年,德国工作联盟在斯图加特举办了“电影与摄影·国际展”。1931年4月,经过电影演员、电影制片人冈田桑三(1903-1983)的斡旋,朝日新闻社在东京举办了“独逸国际移动摄影展”,其中展出了2000多幅曼·雷、莫霍里-纳吉、李思兹基、亚历山大·罗钦可、爱德华·史泰钦等欧美和苏联代表摄影家的摄影作品。不久之后,这个展览在大阪巡回展出。之后,许多日本摄影家纷纷开始效仿,从而导致了“新兴摄影”在日本的出现。
“新兴摄影”所追求的方向,就是在摄影的机械性上追求摄影特有的表现,这就意味着要与以往的艺术摄影诀别,可以说,在这个时期,日本摄影界才明确意识到摄影的现代主义。在这种情况下,从本质上对摄影的机械性特质进行思考的要求便呼之欲出,伊奈信男(1898-1978)那篇著名的摄影论《回归摄影》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1932年,在日本战前艺术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野岛康三(1889-1964)的努力下,《光画》杂志创刊,这是一本代表当时日本新兴摄影发展趋势的摄影杂志。《光画》创刊号上刊登了由伊奈信男撰写的《回归摄影》,这篇文章之后被视为是日本新兴摄影的宣言书。在这篇文章中,伊奈信男呼吁:“与‘艺术摄影绝缘吧!放弃现有‘艺术的所有概念吧!毁掉那些偶像!深刻理解摄影特有的‘机械性!新艺术的摄影美学—摄影艺术学,必须要建立在这两个前提之上。”这成为了日本摄影全面转向的风向标。
在这里,伊奈信男否定了以往的摄影艺术概念,针对摄影的独特性,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即“所谓摄影,究竟是什么?作为艺术的摄影,其本质与目的又是什么?”
事实上,在伊奈信男之前,日本摄影史上的开拓性人物福原信三(1883-1948)也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思考摄影的独特性,力求让摄影摆脱绘画的从属地位。他强调光是摄影的真理,认为摄影要超越其作为机械的限制,要与其他艺术类型等价齐观,就必须坚持“光及其层次”的原则。然而,在《回归摄影》中,伊奈信男对福原信三的理论同样抱以怀疑的态度。
他根据莫霍里·纳吉在《绘画·摄影·电影》的分类,并基于自己对摄影机械性的认识,将摄影美学分成三类:第一,表现物象(对象)特异之美的摄影;第二,作为时代的记录、生活的报告并表现摄影艺术的摄影;第三,将“摄影是依靠光来造形”作为宗旨的摄影。然而,对于这三种类型的摄影,他也都提出了质疑。
伊奈信男认为:“对现象性的正确把握与描写”—这对其本身而言是正确的,但因为这是同一形式的重复,因此也存在很快陷入千篇一律之境地的危险;“生活的记录,人生的报告”—这也是正确的,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苦于内容的琐碎细小,沦为无法予人以任何感动之物;“用光造形”—这确实是一个能够毫无遗憾地覆盖摄影艺术所有领域的定义,或者说,在意义上是最为正确的,但是内容太过单一,而且是一个形式主义式的规定。
显然,在他看来,如果用“机械性”来涵盖摄影所有的特性,这样的定义似乎太过简单,而应该从存在论、本体性层面上对摄影进行深入地思考与探索。在强调摄影的机械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拍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他指出,“照相机的‘机械性是‘特殊的·摄影式的事物的‘起源。但并不是摄影艺术的‘起源。摄影艺术的整体是存在于相机背后的人。而且,是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社会性之人。在新的视点上捕捉现象、记录下世界的截面、发表公布自己的作品、利用光线进行造形等等,这样的创作行为全都是由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实施完成的。”通过强调拍摄主体—社会性之人,让建立在机械性基础上的“相机眼”与拍摄者相结合,以达到主客体关系上的平衡,从而避免落入片面迷信机械的物神化陷阱之中。
可见,对于“所谓摄影,究竟是什么?作为艺术的摄影,其本质与目的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伊奈信男是从机械-主体这种辩证关系中来探求的,一方面他否定以往那种纯粹模仿绘画的艺术摄影,强调摄影的机械性对在创作行为中的功能性作用;另一方面,他也清楚地认识到,照相机的“机械性”并不是摄影的全部,而只是摄影行为的一个出发点,而摄影的真正载体依然是相机背后作为社会性存在的人。在“深刻理解摄影特有的‘机械性”前提下,他认为,摄影要立足于现实性,在现实世界中去寻找摄影的对象,避免陷入“唯美主义”与“形式游戏”的危险境地。也正因为这样的观念,他之后才会与名取洋之助一拍即合,大力倡导“报道摄影”。

在《回归摄影》一文中,伊奈信男辩证式地为摄影主体性建立了一个坐标系,一直到1970年代为止,他的这个坐标系都一直决定着日本摄影的发展方向。可以说,之后由土门拳倡导的写实主义摄影也是伊奈信男这个坐标轴的延伸。
如果说,伊奈信男的《回归摄影》是在摄影的主体性上为日本摄影找到了一个发展方向的话,那么摄影家、编辑名取洋之助(1910-1962)的《阅读照片的方法》则是在方法论上为日本摄影开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1933年,以特派员身份被派回到日本取材的名取洋之助在《光画》杂志的聚会上,认识了伊奈信男与木村伊兵卫。回国之后的名取洋之助雄心勃勃地打算“发动一些行之有效的运动”。他认为,当时新即物主义(又称:新客观主义)以德国的包豪斯为中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他希望将报道摄影的知识与现代艺术的思想从德国带回到日本,并在日本发起一场新的摄影运动。为此,他先是与伊奈信男、木村伊兵卫、原弘等人创立了“日本工房(第一次)”,后来又组织了“日本工房(第二次)”与“国际报道工艺”。到了战后,又策划编辑《周刊太阳新闻》与《岩波写真文库》,成为了一名出版策划人与摄影指导者。对于“报道摄影”,名取洋之助注重用多张照片组成有情节的组照,并围绕这一点形成了自己的摄影理论体系,而他的这些经验最终结集成《照片的阅读方法》这本书。
当时,以莱卡相机为代表的小型相机已经成为摄影的重要手段,而大量复制、大量传播的时代的到来,也为摄影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转机。名取洋之助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展开自己的摄影方法论。
在这本书中,名取洋之助从摄影的记录性出发,来确立摄影作为沟通交流手段的基础。他说道:“照片的正确性给予了摄影重要的特性,即照片的记录性。正因为有着正确性,无论什么样的照片,以何种目的进行拍摄的,作为记录的价值已经诞生,这便是照片与绘画、电影等形式不同的一点。在拍摄时,非常的个人化、充满个性,然而一旦时间流逝,就会变成纯粹的记录照片。将我们这个世界的某个时间的某种状态,停留在感光材料上,变成某种记录。”然而,摄影的记录性本身并不具有完整的叙述能力与准确的表达能力,因此,这样的特性是可以利用的。他认为,“拍摄照片本身并不是目的,只不过是手段而已”,应该将这样的手段纳入到印刷媒介之中,摆脱以个人目的为基础的摄影,让照片成为被大众观看的物品。而基于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将摄影中的各种要素错综复杂地进行组合,让照片成为可以自由变化的符号,使之成为某种交流的系统。
名取洋之助进一步阐述道:“照片与文字一样,可以说是一种符号。符号这个词语所指的并非‘物的实体,而是‘物的代替品。未开化的人在看到肖像照片时,误以为看到了‘实物而大吃一惊,即便这也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照片确实符合符号的这一定义。然而,照片是‘物忠实的记录,是无法进行抽象化的符号,所以从一张照片可以解读出很多内容。根据观者的经验、感情、兴趣的不同,同样一张照片,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接受方式也会有所偏差。”
因此,在《照片的阅读方法》一书中,贯穿始终的就是照片所产生的各种意义,即“摄影师、使用摄影师所拍照片的编辑者与始终存在于编辑者心中的读者,此三者所要求的谎言相结合的结果”。在这个前提下,名取洋之助得出这样的结论:照片这种符号,最初拍摄的目的,与拍摄照片的人并没有关系,而且也并不是简单的记录,全都是作为一种素材,在个人立场上,娴熟地加以运用的艺术,通过多张照片的运用来克服单张照片的弱点,可以用照片组织故事,能够打破现实的流动,能够摆脱现实的束缚,这就是新摄影所获得的方法,是一种场域。
而他的这一理念也实实在在地被贯彻于他的工作之中,不论是“日本工房”时期,还是《周刊太阳新闻》与《岩波写真文库》时期,他都非常强调通过照片的组合编排来服务于所要表现的主题,力求让照片摆脱作者-照片-读者这样一种封闭的系统,而变成作者-读者这种直接而又开放的交流系统。然而,这样一来,照片也就失去了照片本身的意义,正如在他手下工作多年的日本摄影家长野重一(1925年-)所言:“归根到底,照片只是插图而已,是引导读者理解内容的说明照片。”
战后的日本摄影界很快就迎来了一个摄影杂志复兴的时期。一方面因战争而停刊的摄影杂志纷纷复刊;另一方面,新的摄影杂志也不断创刊。可以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日本摄影杂志的一个黄金时期。这也为名取洋之助的摄影观念的推广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1955年至1957年,日本迎来了战后的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日本人把这个神话般的繁荣称为神武景气(Jinmu boom)。神武景气的出现,宣告日本拉开了高度经济发展时代的帷幕。在这个时代,摄影这种媒介与当时的其他媒介相比,无疑是非常新鲜的,充满了各种各样未知的可能性,成为了一种全新的大众媒介。这样的摄影氛围为后来的日本摄影表现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然而,随着战后成长起来的一批年轻摄影家的登场,以及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影像文化的出现,旧的摄影理论也很快便遭到了质疑与反抗。这批年轻摄影家迫切地希望能够与过去划清界限。1960年代,瓦尔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被翻译成日语引入日本,为日本摄影界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视觉文化理论。以“十人之眼”展与“VIVO”摄影团体为象征的日本新摄影表现的抬头,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摄影的本质,重新探索摄影的记录性、真实性以及复制性。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重森弘淹(1926-1992)的《摄影艺术论》。
在这本书中,重森弘淹以摄影作为复制艺术的特性为切入点,通过对摄影所具有的现实性的重新理解,来把握当时那个时代的影像特性与摄影表现的可能性。在他提出了那个时代最深刻的一个课题,即“如果在主题与方法、主题与形式的辩证关系中寻求新的现实主义契机就是前卫的话,那么在对当今摄影中的现实主义进行思考的前提下,前卫依然还具有重要意义吗?”他从这个视角出发,来重新转换并确定摄影的现实性。

对于现实主义摄影,重森弘淹这样说道:“如今,摄影的现实主义就是某种题材主义,即把目光全都集中在所有的社会性主题上,通过对社会性主题的把握来确立现实主义摄影的。所以,如果是把游行或者政治现象作为主题的话,那么这就说明,‘将现实置于发展的方面来进行把握这种单纯的信念依然存在。而在把映像作为表现素材的前提下,要想把握摄影的现实主义,‘映像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他还认为,摄影现实主义的问题,首先是存在于创作主体与对象现实的关系中,理所当然应该通过这种关系的摄影方法在独特的表现方法中进行探索。就这样,他将摄影作品与拍摄对象在表层意义上的相似性从摄影的现实性中剥离,将现实性放置在创作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中进行考察,使之超越表层意义上的相似性,成为“我们观念中或者意识中所看到的某种事物”,“所谓真实,也许只不过是某种观念而已”。
基于这样的观点,重森弘淹进一步说:“因为一般情况下,现象既是外部状况,同时也是内部状况,换言之,必须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总体来理解的现实主义。迄今为止,摄影始终是以直接现实为对象的,所以就成为了主要把现象当作外部状况来理解的现实主义。但是外部状况总是必须作为内部状况被意识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理解这个关系的总体就必然成为新现实主义的课题。把现象当作某种未知的可能性来看的时候,我们把握事物的视角也必须始终放在能够理解未知的可能性的位置上。这并不是依靠固定视角的现象判断,而必定是多种视角的确立,即必须要灵活多样地理解那些纷繁复杂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这本书中,重森弘淹将摄影从“写真”一词的字面意义中提取出来,让摄影的现实主义不再停留在眼前所见的实在现象上,而是在“映像(或称影像)”一词—照片仅仅是实在现象透过镜头映射在底片上的影像,在所隐含的意义中进行考察,即“我们观念中或者意识中所看到的某种事物”。这样,“写真”所营造出来的“真”之假象就被打破,摄影的现实主义便成为了实在现象与观念的辩证关系的产物,成为了通过事物与现象来加以认知的存在。
重森弘淹这一观点的提出无疑是为当时的日本摄影注入一股新鲜的血液,为日本六七十年代的摄影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1967年出版到1981年为止,14年间《摄影艺术论》被再版了13次,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
随着所谓“战后派”的一批年轻摄影家的出现,日本摄影内部也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与反思。这批年轻摄影家虽然是从土门拳的写实主义摄影与名取洋之助的报道摄影出发,但是很快地,他们就对写实主义摄影和报道摄影提出反对的声音。因为他们的出现,“映像(或者说影像)”一词开始在摄影领域中广泛提及,他们也被称为“映像派”。这个说法的提出,是为了区别于那种重视摄影特性、追求只有摄影才能实现的摄影表现行为。这个术语从提出伊始便被赋予了有某种微妙意味,即映像是高于单纯截取现实的照片(写真)。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伊奈信男建立起来的“摄影本质”的位置开始被撼动。
重新提出新的摄影本质论的人就是中平卓马。作为VIVO摄影团体的重要人物东松照明的弟子,中平卓马受东松照明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中平卓马的摄影思想正是建立在对东松照明摄影思想的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以东松照明为代表的VIVO摄影家在纪实摄影的前提下,以摄影家的主观意志为出发点开展摄影创作。这一点与名取洋之助的报道摄影和土门拳的写实主义摄影是有很大不同,VIVO这批摄影家在机械性与主体性这个辩证关系中找到的新的创作节点。可以说,如果没有VIVO这批摄影家的反思,就没有中平卓马后来所倡导的“个人生活的即时记录”。不过,中平卓马很快就对VIVO这批摄影家的那种“对自我内心的挖掘、象征性地表现普遍性与本质性”提出批评。中平卓马相信的只是“对当下-此处-我来说是真实事物”的事物,而不追求普遍性与本质性这种不具有实体的东西。
“现代历史确实是将世界与个人假定为某种二元对立的绝对之物,按照这种模式,现代历史就是通过个人的、人类的欲望把世界道具化、对世界加以改变的历史。……时至今日,所谓现代艺术,当然主要就是那些被称为创作者的个人所投射出来的世界影像,不对,应该反过来说,是对创作者预设的影像世界的反投影。这就是影像的本来面目。……作为创作者的个人所抱持的关于世界的影像完全是优先的,完全就是让观看作品、接触作品的多数人所拥有同样的影像达成一致,这样,他们不会违背已经熟悉的、习以为常的既定样式,不会违背对现实所具有的既定观念,只要按照既定样式、既定观念进行解说,表现行为就结束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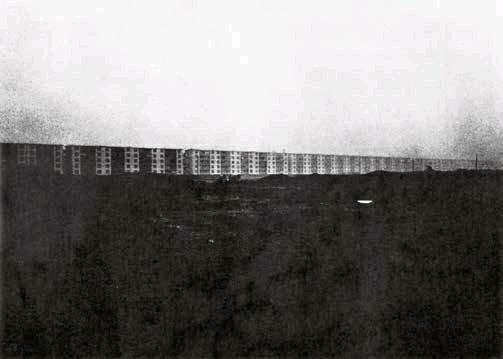
在《为什么,是植物图鉴吗?》一文中,中平卓马对现有的艺术家创作模式进行了拷问。在这里,他把矛头指向了创作之前便已经存在的创作者对世界的预先设定。因此,影像并不是对世界的真实记录,而是对创作者预设的影像的反向投影,是用现实世界去应对预设的影像世界,因此,这样的创作行为是不客观的。同时,他也对自己之前的创作风格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自己之前所拍摄的那种晃动-模糊的照片能够“诞生‘诗意,能够诞生情绪”。因此,他认为晃动-模糊的照片是“旧态依然的‘艺术‘表现”,认为这是自己的“骄傲自大”,是“眼之懒惰”。在这里,中平卓马对摄影中的“诗意”、“艺术”、“表现”做了批判,或者可以理解为中平卓马按照自己的意思对这三个词重新做了定义,他认为摄影之中不能有“诗意”、“艺术”、“表现”的存在,而只能是“记录”。
于是,针对这样的反思与批判,他提出了“植物图鉴”式的摄影,即要原原本本地把握事物自身的状态。之所以称为“植物图鉴”,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图鉴断然不是一个对某些事物进行特权化,并把它设置在中心的系统;另一方面是事物因为事物本身的明确化而成立。而关于“植物”这个提法,他说:“动物的话,腥气太重了,而矿物质则与生俱来地拥有‘彼岸的坚固性的优势,在这二者之间的,就是植物了。”由此可见,他所追求的就是,创作者应该是世界与图像之间的一种中立的存在。正如他所说:“‘图像已经成为了应该超越的对象。图像被假定成是一种从个人出发、单方面地去代表世界的产物,并通过这种行为来歪曲世界,用自己的意愿去渲染世界。现在,在我的心里,图像是被否定的。世界与个人,并不是通过个人片面的视线来联系的。而通过事物,通过物的视线,个人也是存在着的。……拍摄照片这种行为,就是一种将事物的思考、事物的视线组织化的行为。”
中平卓马希望通过这个概念,将“摄影即表现”这种行为转变成“摄影即记录”,即拒绝个人视线的摄影,达到事物视线的摄影。可以说,这种摄影观念打破了伊奈信男与重森弘淹的摄影思想中的那种辩证关系,极力弱化创作者主体性,甚至压制任何形式的预设与表现,以求无限接近现实。然而,这种思想观念终究还是太过于理想化,从而让他的摄影行为掉入了主体意识与客观现实之间无法填补的沟壑中,“为什么,是植物图鉴吗?”这个追问,最终还是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有效实施。
事实上,中平卓马提出的所谓视线的问题—个人视线与事物视线,已经将摄影从相机的机械性与创作者的主体性的辩证关系中抽离出来,放置在视觉现象学范畴中进行思考。而深入思考并阐述“视觉现象学”这个问题是中平卓马的“战友”—日本思想家、批评家多木浩二(1928-2011)。
所谓观看,就是对“物”的知觉。对视线的意识这种行为,不仅对“物”本身产生作用,也会对我们的认识构成影响。在《眼之隐喻》一书中,多木浩二对视觉表现与事物、乃至人类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提出人类是借助某种无法语言化的无意识视线来认识世界的,而那种无意识的世界也在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文化地层。
在这本书中,多木浩二不只停留在摄影上,还围绕版画、绘画、建筑等领域展开讨论。在“视觉的政治学”一章中,他以19世纪拿破仑三世与奥斯曼男爵对巴黎的大改造为例,提出了观看都市的两种视线:一种是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前在巴黎不断蔓延的反叛的视线,即革命者搭建了大量的路障街垒,将巴黎的街道一截一截地分割开来,这是一种非远近法式的视线;另一方面,奥斯曼男爵则希望将巴黎建设成一座理想都市,因此他投向巴黎的则是一种远近法式的视线。多木浩二认为,这是继来自英国哲学家杰里米·边沁(1748-1832)和法国的哲学家福柯(1926-1984)的“圆形监狱”之后,成为“眼之隐喻”的一个代表事例。
多木浩二在书中始终将视线作为某种问题提出,他说:“这两种性格正反相对的视线以都市作为舞台展开斗争。叛乱以远近法与非远近法,理性秩序与迷路、地上与地下这种象征异文化空间对立的形式,在不断蔓延。换言之,政治就嵌在这两种视线相互对立的‘隐喻的宇宙之中。在这里,观看就是生存,被观看就意味着被杀害。”多木浩二之所以这样看,是因为这样的前提条件,既不可能是先验的,也不可能是恒常的,而是某种极其不安定的东西。他所说的“视线”是大多数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投向事物的视线。而他所做的就是,反过来追溯这种视线,从各种各样事物事象的图像中,探索人类面对世界在编织什么。
“由于人类在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是具有某种心理上的距离感的,我称之为视线的这种东西,产生了这些包含多种因素的认识,这已经超越了视觉,而指向心理上的活动。与此同时,我们自己则只不过是借助某些表象让这个世界得以显像的一种方法,或者说,是某种生存的样式而已。”多木浩二如是说。显然,在他看来,当人将摄影作为这种视线活动的一个整体来把握的时候,某种超越自我与意识的历史无意识就会显现出来。而多木浩二在书中反复强调的,并不是创作者的意图与作品的主题,而是这种历史无意识在摄影中所构成的视线。
在这里,多木浩二利用“摄影”,将以远近法为主轴来观察事物的观看主体设定为外在于人的某种存在。相机眼是人眼之外的某种眼睛,因此,画家在裁切自然并将其裁切下来的风景当作风景画的这种“文化”视线,在摄影中是不存在的,远近法也是不存在的,摄影纯粹只是用来裁切拍摄对象的“眼睛”,是一种由历史无意识构成的、是一种作为视线的摄影。
他对摄影的这种理解对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摄影产生很大的影响。当时私摄影在荒木经惟、深濑昌久等人的带动下,越发呈现个人化的趋势。而这种个人化的摄影表现所导致的就是影像解读上困难,很多摄影作品陷入脱离现实的、自说自话式的个人情绪的表达。多木浩二在《眼之隐喻》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则为这样的摄影表现提供了某种结构性的肯定与支持。
“摄影自发明以来,便一直在持续拍摄都市。即便是拍摄自然,其视线也无法抛弃那种社会化了的都市概念,为暗箱化了的意识所覆盖,蕴含着都市感受性的映像就这样显现出来。从19世纪到20世纪,异常发达的都市创造出来的照片蜂拥而至,照片就是这种都市的庞大而透明的日记。”在《写真都市》一书中,摄影批评家伊藤俊治(1953-)是这样确定摄影与都市之间的关系的。他还认为,“在摄影这种具有高度自律性的复制产业文化构造的堆积之中,都市与人类以同样的方式建构自己的精神,按照那种规则,忠实地组织都市空间。在人类的内心、也同样在都市的内部,摄影让‘个人与‘世界具备了某种复杂地纠缠在一起的新感觉中枢。都市结构与人类的精神结构之间,潜藏着某种本质上的相似性。”
伊藤俊治所强调的是,将都市、摄影、人类这三者联系在一起的并非具体的制度与规范,而是某种相似性。因此,由都市创作出来的大量的照片也就成为了解读都市的文本,即都市映像本身以及摄影本身都具有某种解读文本式的功能。这为当时的日本摄影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创作及理解影像的线索。
在1984年提出这样一种观点,与那个时代的发展脱不了干系。进入198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发展开始停滞,而日本经济却正好达到一个巅峰,大量杂志的创刊成为了摄影家发表作品的重要平台,也成为消费者观看摄影的一个平台,更是接纳来自社会的视线的一个平台。城市化在日本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消费社会的到来,让摄影成为某种可以消费的商品,而都市则越发成为摄影表现中的一个重要的主题。另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的摄影的普及,也让摄影所承载的某种视觉习惯发生倒转。原有的那种观看到被观看、拍摄到被拍摄的主被动关系,到了80年代开始发生崩塌。辛迪·雪曼、桑迪·斯各格兰德、贝尔纳·弗孔等以摆拍方式进行创作的新一代摄影家日益活跃,他们的表现活动也对当时的观看行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的摄影表现也对日本摄影构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催生了摄影批评的变革。
在《写真都市》一书中,伊藤俊治的摄影论并不是建立在“摄影是什么”这种本质性问题上,而是从摄影的结果中寻找摄影的可能性。他从历史上摄影与都市之间的关系入手,在摄影的感受性与无意识的基础上来尝试思考这样的问题,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摄影就是都市的媒介,摄影挑衅都市,让它扩散、生成,在这个过程中,都市被转换成摄影的意义与功能。这并不是都市与自然的二分法、也不是都市与人类之间的区分,而是背负了都市感受性的“某物(影像)”,是被都市的无意识渗透的“我们(媒介)”。通过对细节的深入挖掘,对摄影历史的回溯,伊藤俊治在共时性层面上对摄影进行解构,让摄影表现得以超越时代与脉络,为1980年代的日本摄影打开出一条新的道路。
1990年代之后,以饭泽耕太郎为代表的新一代摄影理论家开始成为推动日本摄影发展的主要动力。以1986年出版的《“艺术摄影”与它的时代》为出发点,饭泽耕太郎出版了大量的摄影理论著作,从入门读物到专业摄影理论的探讨,从摄影史的编撰到摄影家的个案分析,对日本摄影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梳理与总结。在他的推动下,日本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之间,兴起了一股强大的女子摄影潮流,将摄影从专业领域带入到日常生活领域,甚至让摄影成为时尚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日本摄影批评家仓石信乃以往的摄影论提出质疑,在1998年出版的《反摄影论》一书中,他认为对照片进行阐述是一种信息重复,因为照片本身就是一种简洁明了的媒介,摄影批评应该像照片一样地进行书写。在这样的前提下,他对摄影行为本身进行考察,探寻隐藏在摄影背后的社会意义与心理背景。2000年之后,从德国留学回来的摄影批评家清水禳将全新的西方视觉文化理论纳入摄影批评之中,通过具体的图像文本分析方法对影像进行解读。除了文中所提到的这几位摄影理论家及作品,日本还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摄影理论家与作品,对日本摄影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过,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再具体展开说明。当然,要在这篇短短的文章中展现日本摄影理论的全貌更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挂一漏万、以点概面地对日本摄影理论做一个极其简单且粗略的介绍,希望能够引起大家对日本摄影理论的重视与引进。
综上所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日本摄影表现的发展与日本摄影论的发展之间有着相互影响、互为表里的关系。每个时期的摄影表现总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提出各种问题,呼唤着新的摄影思考的产生,也催生出适应那个时代的摄影表现的摄影论。同时,每个时代的摄影论都不只是停留在既定观念与现有的摄影表现上,而是更加深刻地对摄影的本质、摄影与现实的关系、摄影与主体的关系、人与现实的关系以及影像与人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索,为新的摄影表现开疆拓土,提供最有力也是最具可能性的思想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将日本摄影史与日本摄影理论史结合在一起进行探讨,才有可能相对全面系统地了解日本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