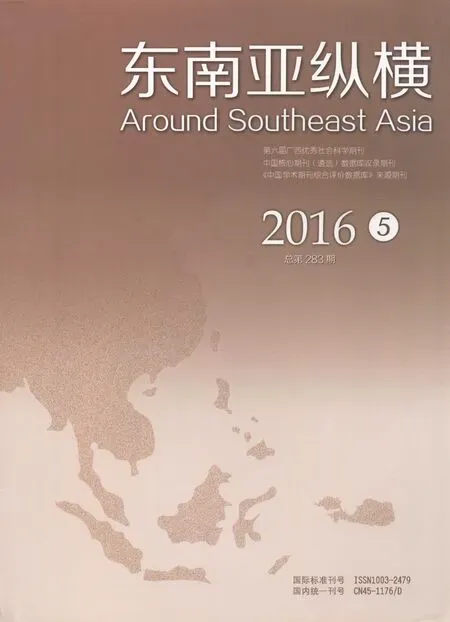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化”的形成及影响
王庆忠
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化”的形成及影响
王庆忠※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紧张和中国的持续发展,下游国家在利用湄公河水资源的过程中,通过社会化和政治化两个步骤逐渐把水资源“安全化”了,水资源进而由公共问题转变为安全问题。水资源的“安全化”让大湄公河的水资源合作更加举步维艰;使域外大国不断介入到次区域的合作中,为遏制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借口;严重影响了中国的周边形象。要想共同维护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和谐发展,下游国家必须在水资源开发中去“安全化”,使水资源真正回归到社会性问题的范畴中来,才能解决沿岸各国在水资源开发中出现的分歧。
水资源;安全化;机制;大湄公河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政治中,国际河流①中国国内对国际河流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是黄雅屏:《中国国际河流争端解决的困境初探》一文。在此文中,作者认为国际河流是指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河流,既包括穿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跨国河流,也包括分割两个国家而形成其边界的边界河流。详细参见黄雅屏:《中国国际河流争端解决的困境初探》,《大连海事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55页。的水资源治理一直是沿岸各国比较关注的议题,但各国在国际河流水资源治理过程中,有的成效十分明显,有的则收效甚微,其中原因值得我们认真探讨。中国也是一个国际河流分布的大国,与沿岸各国合作开发水资源的过程中,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水资源的“安全化”成为阻碍合作的主要原因之一。大湄公河是流经中国的一条重要国际河流,在水资源合作开发方面,中国与下游国家存在一些分歧。既有的文献大多从合作治理、环境政治、建立机制等方面来探讨如何进行大湄公河的水资源合作,他们侧重的是对如何达成合作结果的探讨①相关的研究文献可参见:郭延军:《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多层治理及中国的政策选择》,《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郭延军、任娜:《湄公河下游水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各国政策取向与流域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7期。刘稚:《环境政治视角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合作开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朴键一、李志斐:《水合作管理:澜沧江—湄公河区域关系构建新议题》,《东南亚研究》2013年第5期;汪霞:《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合作机制研究》,《东南亚纵横》2012年第10期等。。而要想达成合作,首先要分析是什么因素在阻碍合作,这是探讨达成合作的前提。本文将以“安全化”理论为视角,系统地阐述为什么大湄公河水资源合作成效甚微?水资源“安全化”的形成机理是什么?这种被“安全化”的水资源政治的消极影响有哪些?只有采取去“安全化”,才能让水资源恢复到正常的社会性问题轨道上,从而让合作得以正常进行,共同维护河流开发的稳定秩序。
二、“安全化”的形成逻辑
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个基本的价值。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行为体来说,免于伤害或危险的现状或感觉,在任何时候都是参与国际互动的首要目标与条件②李少军著:《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页。。根据《现代汉语词典》,“安全”的定义是“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根据《美国传统书案词典》,“安全”的基本定义是“免除危险、疑虑和恐惧”。根据这两个词典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对“安全”的最基本概念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没有危险才是安全。中西词典的语义解释都是把“安全”与“危险”看作是一对相反的概念,同时也是一对相互依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危险的客观存在,人们就无法知道什么是安全③阎学通著:《国际政治与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8页。。阿诺德·沃尔弗斯对安全有一个比较好的界定,他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的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④Roger Carey and Trevor C.Salmon,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Modern World,New York City:St.Martin’s Press,1992,pp.13.。因此,所谓安全就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
冷战结束后,随着大国军事集团对抗的消逝以及诸如环境、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安全概念不断延展,安全研究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⑤有关“安全”概念的发展演化,参见任晓:《安全——一项概念史的研究》,《外交评论》2006年第5期,第36~45页。。在对安全的研究中,哥本哈根学派独树一帜⑥“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这一术语最早是由比尔·马克斯维尼提出的,他认为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出版了“多部与安全有关的著作,完全可以被授予学派称号”。参见Bill Mcsweeney,“Identity and Security:Buzan and the Copenhagen School”,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Vol.22,No.2,1996,pp.81.,展开了对安全研究的新领域,把安全由一个静止的概念发展成一个能够得到操作的动态概念,为我们观察世界提供了另一个视角,而“安全化”概念就是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领域的最主要贡献之一⑦哥本哈根学派是近些年安全研究中最为显赫的一支,主要代表有巴里·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默顿·凯尔斯特拉普、皮埃尔·利梅特等。关于哥本哈根学派有关安全研究的最新成果可参见,(英国)巴里·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安全化”最早由奥利·维夫(Ole Waver)提出,随后巴里·布赞对其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在《新安全论》一书中,“安全化”理论得到了重点阐述。布赞等认为“安全化”是这样一个过程:某个公共问题只要还尚未被成为公共争论与公共决策问题以及国家并未涉及它,这一问题就还被置于“非政治化”的范围,所以还不是安全问题。当这个问题成为国家政策对象的一部分,需要政府的决心和考虑资源的重新配置,或者还需要一种不同以往的公共治理体制的介入,则它就被置于“政治化”的范围,成为“准安全”问题。而当这个问题被政府部门作为“存在性威胁”而提出,并需要多方面采取紧急措施,甚至这些措施超出了政治程序的正常限度而仍然被证明不失为正当,则这个问题就成为安全问题了⑧(英国)巴里·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2~33页。。所以从广义的角度看,安全化就是使得一种公共问题经过特定的过程(如权威机构“宣布为危险”)而成为国家机构涉及的安全问题。为此,“安全化”不仅使“宣布或认定为危险”成为一个合理的施动过程,而且还能很好地解释为何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安全重点,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安全重心。而且,真正的安全问题被“政治化”之后表明,“安全”自然“是超越一切政治规则和政治结构的一种途径,实际上就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所以在现实中,当任何问题被认可为“安全化”的对象时,就会形成新的安全领域①(新加坡)梅利卡·拉贝若-安东尼、拉尔夫埃·莫斯、(加拿大)阿米塔夫·阿查亚编著,段青译《安全化困境:亚洲的视角》,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

图1 安全化的逻辑示意图②王江丽:《安全化:生态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安全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37页。
在这个过程中,哥本哈根学派强调了3种因素的重要性:首先,安全化的客体,即“存在性威胁”是什么。它可以是个人和群体(难民、人权滥用的牺牲品),也可以是问题领域(国家主权、环境、经济)。其次,安全化的施动者,即由谁来宣布人们面临着“存在性威胁”。它可以是政府、政治精英、军队和市民社会。最后,安全化的过程,即运用安全的“言语—行为”使大众确信存在安全威胁。一旦大众接受了安全威胁是既成事实后,威胁对象就成为安全客体,安全化也就完成了。
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对于安全化主体而言,保证一个本身并非安全的问题被安全化为对指涉对象的“存在性威胁”并被听众接受是一个重要课题。换句话说,安全化如何取得成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成功的安全化包括3个步骤:(1)识别存在性威胁;(2)采取紧急行动;(3)通过破坏和摆脱自由规则来影响单元间关系。这样,识别出存在性威胁并不保证安全化就能成功,成功的安全化不但由安全化施动者决定,而且由安全话语行为的听众决定,即这些听众是否接受一种共有价值遭受存在性威胁的说法。安全化得以成功取决于安全化主体、指涉对象和听众的关系,即需要两方面条件:一是安全化主体从因果、时间、道德3个层面上合乎逻辑地将威胁代理描述为对指涉对象的“存在性威胁”;二是安全化听众需要在聚焦事件和媒体宣传的帮助下接受安全化说辞③潘亚玲:《安全化、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第52~53页。。安全化概念的提出使人们对安全的认识增加了一个维度,即加入了“言语—行为”的社会认同要素,安全问题也就呈现为“安全性”“安全感”和“安全化”三者互动的新状态④王江丽:《安全化:生态问题如何成为一个安全问题》,《浙江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第37页。。
在安全话语中,经过渲染,一个问题作为具有最高优先权被提出来,这样一来,通过将它贴上安全标签,一个施动者就可以要求一种权利,以便通过非常措施应对威胁⑤(英国)巴里·布赞、奥利·维夫、迪·怀尔德著,朱宁译:《新安全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安全化在有些情况下不可避免,但并不是“安全越多越好”,基本上,安全应当被视为是消极的,是作为常规政治处理问题的一种失败而不得已的措施。理想地说,政治应该能够根据日常事务的程序,并不特别地将具体“威胁”拔高到一种刻不容缓的超政治状况来阐述。因此,一个问题的“安全化”是一种不得已的政治选择,而“去安全化”是长时间范围的最优选项,因为它意味着没有问题需要用像“威胁我们”这样的话语来表达。
三、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化”的形成机制
澜沧江—湄公河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北麓,其在中国境内的河流称为澜沧江,流经青海、西藏、云南三省区,其流出中国国境的河流称为湄公河。澜沧江—湄公河全长4880公里,是东南亚第一、亚洲第三、世界第八大河,素有“东方多瑙河”的美称。该流域总面积达81万平方千米,人口约为2.5亿,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地区的桥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该流域国家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是一块尚未开发的处女地。1992年在亚洲开发银行(ADB)的倡导下成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机制(GMS),其目的就是为了促进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地区和谐。虽然大湄公河次区域有GMS合作机制,但是GMS合作机制在大湄公河水资源开发利用及治理方面发挥的作用并不大。
水资源本来是一个很普通的社会话题,如果在常态化的背景下,人们也许并不会意识到水资源也是一个安全问题,并有意图地推动水资源的安全化。但是由于对水资源利用的增加,下游各国开始逐渐重视水资源问题,把中国在上游开发利用水资源的行为上升为政治问题,最后上升为关系到国家安全的安全问题,湄公河的水资源被下游各方逐步地“安全化”了。政治议程和科学议程是水资源问题安全化两股最主要的推动力。政治议程和科学议程都是一种社会建构,两者相互交叉并互相塑造,共同完成了水资源问题的安全化过程。政治议程属于政府和政府层面(如国家和联合国系统),由公共决策过程和公共政策组成,并最终决定如何对待生态问题。科学议程在政治中心之外,由科学研究机构(社会精英)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目的在于提出环境难题及其对文明进程的影响,并寻求解决的可能,从而做出是否采取安全化步骤的权威评估。一旦对安全边界的新划定形成普遍认同,就会直接影响国家之间安全设防的必要与程度,也会影响国家安全及其相应制度运作的合法性基础,还会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实现的可能性限度①赵远良、主父笑飞主编:《非传统安全与中国外交新战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通过以上分析,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化”的步骤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把水资源由普通的社会问题逐渐纳入国家政策对象的一部分,需要政府决心考虑和重新进行评估,用不同以往的公共治理体制介入,这是水资源由社会化转变为政治化的过程,水资源成为“准安全”问题。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各国对水资源的需要越来越多,水资源在各国发展中的地位逐渐凸显,以前不被重视的水资源问题开始逐渐被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政策的范围,政府对水资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给予了重新的评估和认识。由于湄公河拥有丰富的水资源,所以沿岸各国都想积极加以利用,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个跨境河流的水资源,各国决定制定更加完善的公共政策,以更好的管理体制来有效地掌控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经过政府行为的政策“包装”,水资源由普通的社会问题开始了其政治化的过程,成为一个“准安全”问题。湄公河下游各国的行为充分证明了水资源由社会问题经过政治化手段转变为“准安全”问题的过程。例如,越南一贯重视水资源管理,除了采取比较先进的技术手段之外,还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措施。1998年越南通过了《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水资源法》,该法是对水资源管理、保护、开发、利用和防治水害的法律规定②吴明海、张代青、杨娜:《越南水资源利用与水权制度建立》,《中国农村水利水电》2010年第10期,第119~120页。。在政府和民众都感受到水资源压力的同时,他们势必去寻找新的水资源以减轻用水的压力,湄公河这条国际河流就成为各国利用水源的目标。在利用湄公河水资源的过程中,政府设立了一套新的管理体制掌控这里的水资源,水资源问题的政治敏感性更强了,也就从一个普通的社会问题逐渐政治化,成为公众十分关注的政治问题,这就是水资源的“准安全化”过程,为其进一步的“安全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政府部门认为水资源问题作为一种“存在性威胁”,它可以要求采取紧急行动或非常措施③晋继勇:《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安全化:以世界卫生组织规范变迁为例》,《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21页。,甚至这些措施超出了政治程序的正常限度而仍然被证明不失为正当,则这个问题就成为安全问题了。在水资源由“准安全”问题过渡到“安全”问题的过程中,政治议程和科学议程是两股最主要的推动力。对于湄公河下游各国来说,水资源问题越来越显示出其政治敏感性,特别是上游国家的建坝行为,更让下游国家确认了水资源不仅仅是单纯的社会问题。如果不被重视,就有可能成为别国威胁本国的工具,所以水资源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成为安全的主题。一旦下游国家有了关于水资源的这种信念以后,那么他们就会认为可以为了本国的水资源利益采取任何措施,而这些措施虽然超出了平时处理水资源问题的正常限度,但是政府仍然认为这种措施是合理的、必须的。水资源问题就在这种超出正常限度政治程序的作用下成为安全问题。
所谓政治议程就是指各国政府认为把水资源安全化是符合国家利益的,需要通过政治程序,把水资源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看待。纵观湄公河下游各国的政治议程,无不是在把湄公河水资源问题向高度政治化的方向推进。例如,越南认为,湄公河的水资源关系到该国渔民的农业生产、水产养殖、水上运输和生态环境等,如果忽视对水资源问题的管理,对民众的生产和生活造成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泰国政府也认为,湄公河水资源生态的任何变化都会对当地居民的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因此不仅要重视湄公河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同时也要加大对水资源环境的保护。2010年整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又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旱,下游国家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对中国澜沧江水电开发的指责更是甚嚣尘上①潘一宁:《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34页,第35页。。在政治议程的倡导下,民众对水资源问题有了更新的认识,但是这个认识如果想得到科学的论证,还必须引入科学议程,而科学议程的实施涉及到对水资源问题有科研经历的科学家、学术界、政府精英等的行为。通过科学议程,一方面用科学数字来说明水资源问题的严峻性,加速水资源问题的政治化,在全民心中形成共识,另一方面向政府提出加强水资源利用和保护的具体建议,使政府加速制定有关水资源问题的政策文件,促进水资源问题的政治化和超政治化进程。湄公河沿岸国家在科学议程上对水资源问题的“安全化”呈现加速的趋势,越南的水资源问题专家认为,湄公河不仅是越南渔民生活的重要纽带,而且其水质及周围的生态环境也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果不对湄公河的水资源进行有效地治理,那么湄公河将成为越南的灾难之河。缅甸政府也认为湄公河的水源是该国人民生活的重要依靠,如果忽视对湄公河水源的管理,不仅人民的生活水平将受到影响,国家安全也将得不到保障。通过政治议程推动和科学议程的论证,水资源问题最终被“安全化”了,但是在水资源“安全化”的过程中,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言语—行为”互动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第三,国内民众相信政府关于水资源“安全化”的话语是正确的,政府、精英和民众之间的倡导与说服的互动更确认了民众对政府话语的信任,这时有关水资源的“安全化”信念通过“言语—行为”的互动最终建构而成。成功的安全化不但由安全化实施者决定,而且由安全“言语—行为”的听众决定,即取决于听众是否接受对一种共有价值造成“存在性威胁”的说法②王凌:《安全化的路径分析:以中海油竞购优尼科案为例》,《当代亚太》2011年第5期,第80页。。政府和学术机构通过政治议程和科学议程把水资源问题提升到安全的高度,但是如果民众不认同他们的宣传,那么水资源问题的安全化也不能完成。只有政府的宣传得到民众的认可,那么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水资源问题才能真正从普通的社会问题政治化为安全问题。在政治议程和科学议程实施中,媒体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媒体将大众的头脑连接起来,使人们的认识标准化,个人意识融入地方舆论,再融入全国舆论和世界舆论,直到公众意识完全统一,而这也使通过媒体塑造大众的头脑成为可能③张巨岩:《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13页。。湄公河下游国家的人们在政府的宣传和学术机构的论证下,不仅认识到水资源的重大政治意义,而且还亲身体会了水资源在生活中的紧张程度,因此他们对政府和精英的看法持比较赞同的态度。认为水资源问题不仅是普通的社会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它就可能成为危害人民生活和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问题。所以,必须响应政府和精英的号召,重新确立对水资源的看法,这样政府和民众在“言语—行为”的互动中就形成了一致,水资源也就在这种一致中逐渐由社会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水资源的“安全化”在各方的共识中得到完成。次区域内外国家间的利益博弈甚至权力斗争使澜沧江—湄公河的水资源开发问题更加政治化,加重了安全的话语④潘一宁:《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34页,第35页。。
四、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化的影响
水资源问题的安全化使有关各方更加确证了自己以前对水资源的认识,这种认识在政治议程和科学议程的引导下也激起民众对水资源安全化的认同,如此便形成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言语—行动”互动,水资源安全化彻底完成。对于本地区来说,虽然水资源对各国的发展都十分重要,但是完全没有必要把水资源问题由一个社会问题上升到安全问题,因为一旦水资源由社会问题上升到安全问题,那么将不可避免地对本地区的合作产生消极影响。
第一,水资源问题的安全化使各国在水资源问题上的合作更加举步维艰,进而导致各国在水资源开发中各自为政。大湄公河是一条水资源非常丰富的河流,但迄今为止仍然没有形成一个合理开发湄公河水资源的协议,这对于国际河流的管理和利用是非常不便的。在水资源问题上,沿岸国家认为,对于本地区来说,水资源不是普通的社会问题,而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安全问题,如果本国的水资源被别国利用,那么将对本国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很大的威胁。在政府的宣传下,各国民众也提高了对水资源的认识,水资源在本地区就具有了特殊的政治意义。一旦水资源问题安全化,各方必然把水资源提高到与政治、军事等同等重要的程度,水资源也就进入了“高政治”领域。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在“高政治”领域,国家之间很难达成合作,因为“高政治”领域的议题对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这个领域的博弈基本是零和的,国家很难在“高政治”议题上做出让步,所以达成合作的意愿也就非常薄弱,进而导致合作很难形成①倪世雄等著:《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8页。。湄公河水资源问题被安全化之后,各方在水资源合作中更加看重相对获益,这就很容易导致各方放弃达成合作协议的机会,在水资源开发中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湄公河水资源开发协议很难达成以及下游国家对中国在水资源利用问题上的指责,很大原因就是下游国家把水资源问题“安全化”了,各方不愿意在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开发协议。
第二,水资源问题的安全化为大国介入本地区的合作提供了机会和口实,对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的实施非常不利。相对于中国来说,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是小国,随着中国的持续发展,这些国家不免对中国产生一种恐惧感,他们害怕中国会恢复以前的朝贡体制,进而成为地区的强权国家。在历史上,这片区域经常受到强权大国的侵略,历史的记忆促使他们担心中国一旦强大了也会践行强权容易扩张的这个国际政治“规律”。对于下游国家的担心,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中国是维护地区稳定的和谐力量,中国的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不会以牺牲别国的利益来换取自身的发展。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各国对中国的疑虑加重了,就是因为中国在水资源开发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他们把中国开发水资源的一般社会行为解读成会对他们的发展造成很大威胁的政治甚至是安全行为。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下游国家对中国的防范必然加强,同时还容易导致域外大国插手本地区的事务,借此遏制中国的发展。2000年湄公河地区发生严重洪涝,致使下游国家的人员和财产遭受很大损失,于是,对中国在上游建坝的质疑和抱怨开始此起彼伏。2010年整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又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旱,下游国家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对中国澜沧江水电开发的指责更是甚嚣尘上,认为上游大坝建设不但不能有效地控制水流量,反而加重了下游国家的旱涝灾害,这一问题成为2010年4月初在泰国华欣召开的首届湄公河委员会峰会的一个关注焦点以及中国与湄公河下游4国对话的重要议题②潘一宁:《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34页,第35页。。美国一些媒体和智库也不断论证中国的“水坝威胁论”,认为中国的水坝会使湄公河的河水流量发生变化、水质恶化、生物多样性降低,会影响地区生态和粮食安全。所以,美国应重视中国在湄公河流域的举动并做出反应。在2009年的第16届东盟地区论坛上,美国极力插手湄公河次区域的水资源开发合作,号召湄公河下游国家与美国密西西比河紧密合作,同时美国也愿意帮助湄公河下游国家开发水资源、提供技术援助和防震救灾等工作。日本也借口中国在上游修建水利设施不利于下游国家的开发,以此来向下游国家提供积极的援助,并且帮助下游国家修建了很多大坝,试图与中国在下游国家中争夺影响力。在经济合作过程中,这些国家颇为强调生态安全与人的安全理念,同时还非常警惕中国在该区域的战略安全主导地位和作用③潘一宁:《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34页,第35页。。可见,湄公河水资源的“安全化”对中国的影响是最不利的,下游国家和域外大国往往以水资源的安全化来遏制中国,这点中国必须密切关注,并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否则中国在下游国家心目中的形象会受到很大的消极影响。
第三,水资源问题的“安全化”不利于中国在下游国家心目中的形象。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单纯的物质实力的增强同时也是国家形象的优化,中国的形象优化就是要改变近代以来国外对中国各种消极、诋毁的看法,重新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是一种社会建构的过程,是需要别国对中国实际行为的认同,并在这种认同基础上对中国形象的重构。为此,中国的形象在周边国家的建构就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国家在周边中的形象很差,那么它在世界中的形象也会受到消极影响。中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合作很大程度上彰显了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但是,在水资源开发利用问题上,下游国家对中国的意见很大,他们认为中国在上游的水资源开发阻碍了他们对水资源的利用,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有消极作用。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下游国家通过“安全化”把水资源的重要性提升到“存在性威胁”的层面上,水资源成了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政治议题。下游国家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各方合作达成水资源联合开发的协议,而且对中国的形象存在消极影响,极有可能在“安全化他者”的情况下,把中国看成是下游国家的威胁(“安全化他者”可以被界定为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一个“他者”被当作自身主导认同的威胁,“安全化他者”的最高目标是获得特别的、额外的权势以保卫这一认同①潘亚玲:《安全化、国际合作与国际规范的动态发展》,《外交评论》2008年第3期,第56页。)。下游国家在水资源安全化议题中的行为就极有可能包含将中国塑造为此议题上“他者”的努力,认为中国是导致他们水资源安全化的存在性威胁主体。一旦他们形成了这种观念,那么中国的国家形象将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
五、结语
次区域内外国家间的利益博弈甚至权力斗争使澜沧江—湄公河的水资源开发问题更加政治化,加重了安全的话语。由于各国政府都把水资源开发看作是效益大于成本的综合安全工程②潘一宁:《非传统安全与中国—东南亚国家的安全关系: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水资源开发问题为例》,《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4期,第34~35页。,因此,水资源安全化有其必然性。中国不希望各国通过水资源“安全化”这个私利行为最终导致本地区的合作陷入停顿,中国愿意为化解各种分歧和纠纷进行对话与协调,使水资源开发利用最终在相关国际准则的基础上进行。同时中国也在为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去“安全化”不懈努力,我们提出与东盟国家建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就是有力的写照③关于建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论述,可参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10月3日在印度尼西亚国会的演讲: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04/c1024-23102653.html.。中国在上游的水资源开发是有节制的,并不像某些国家宣传的那样,会对下游国家造成严重的安全危害。相关的数据表明,下游国家的水资源干涸与中国在上游的开发也没有必然的联系④钟华平、王建生:《湄公河干流径流变化及其对下游的影响》,《水利水运工程学报》2011年第3期,第50~51页。。以“安全”为借口来指责中国在上游的开发只能让次区域的合作陷入困境。但是中国在此过程中也应该积极倾听下游国家的呼声,理解它们的相关利益诉求,努力做到水资源开发的透明化。本着建立互联互通利益共同体的原则,认真探讨水资源合作的相关模式,真正做到水文监测资料共享,让下游国家对中国的湄公河政策有更好的预期。以多边主义为合作的平台,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并积极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进行多层合作治理⑤关于多层合作治理的更多论述可参见郭延军:《大湄公河水资源安全:多层治理及中国的政策选择》,《外交评论》2011年第2期,第91~95页。,使大湄公河真正成为连接地区合作的纽带。
注:本文是2014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中国东南周边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研究”(项目编号:14ZDA087)的阶段性成果,同时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编号:14CX04018B)、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青年教师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代号:Y120911W)。
(责任编辑:雷小华)
The Securitization of Water Resources of Great Mekong River and Consequence
Wang Qingzhong
With arising tension concerning water resources and China’s development,countries downstream The Mekong River‘securitize’this issue by two procedures,socialization and politicalization respectively,therefore transferring the problem of water resources from public-oriented to safety-oriented.This act causes rather bad effects upon ongoing cooperation in this region,allowing of other big countries’involvement and thus providing them excuses of interfering as well as preventing China’s development which has bad effects on China’s image thereby.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bring these downstream countries back to the original issue,that is,ridding‘securitization’,to resolve differences in promot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 this region.
Water Resource;Securitization;Mechanism;Great Mekong River
TV213.4
A
1003-2479(2016)05-0011-07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系讲师、法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