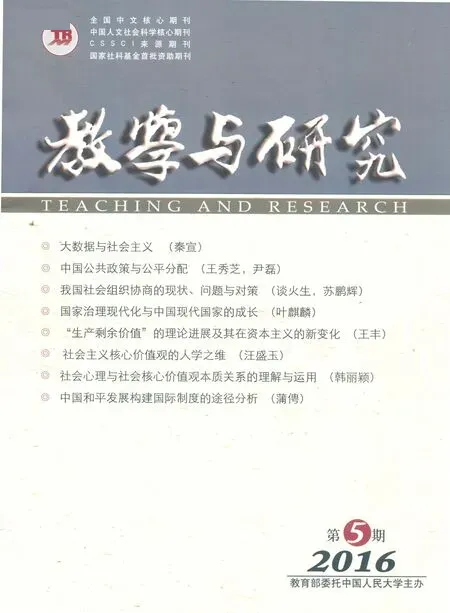国际环境政治研究的变迁及其根源
董 亮
国际环境政治研究的变迁及其根源
董 亮
国际环境政治;节点;国际关系理论;议程;研究方法
国际环境政治研究通常以1972、1992、2002及2012四个重要年份的国际会议作为公认的重要节点。鉴于知识生产与节点大会的密切关联,加之极强的跨学科性及应用性,国际环境政治研究不断演化。目前,可分为四大类研究议程:与环境相关的传统国际制度研究;环境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结合的问题;环境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国际环境治理中的相关规范性问题。研究方法也日益细化,定量、定性方法得到均衡发展。具体而言,过程追踪、大型事件的团队研究、统计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分析,嵌入式问卷试验及排放情景等受到推崇。
一、研究的背景与问题
20世纪60年代,环境问题开始逐渐出现在全球议程之中,并于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后,最终确立了它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国际环境政治(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IEP)研究的影响力逐渐扩散。[1](P500-501)20世纪90年代起,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性日益明显。近三十年来,众多世界顶尖社会科学学者,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等学者,陆续加入国际环境政治研究之中*总体而言,国际环境政治(IEP)是在国际关系学科下衍生出来的,而全球环境政治(GEP)是一个更广并且更为跨学科的术语,从而允许使用更为丰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视角。但是通常两者在国际环境政治学者中是互用的。本文采用国际环境政治的说法。,使得这一领域在理论创建等方面取得了更大成就。然而,这一领域的基本文献年代较短,核心问题的讨论仍然具有很强的活力,领域内知识更新速度飞快。笔者仅比对权威的《全球环境政治手册》2005年版与2014年版,便可发现2014年版的40篇文献中只保留2005年版中的6篇。[2]
纵观近几年的文献,可以发现,西方学界已经开始关注此领域快速的知识流变,梳理国际环境政治与治理研究现状的文献也日益增多*西方国际环境政治文献,可参见:Frank Biermann,et al., “The Fragment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rchitecture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Vol. 9,No.4,2009,pp.14-40;Michael Zürn,“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 Review of Current Research”,World Politics,Vol.50,No.4,1998,pp.617-649.。迈克尔·祖恩(Michael Zürn)系统阐述了IEP的研究议程。他认为,国际环境政治可分为两代研究,第一代是在20世纪80年代为把国际环境政策带入研究国际政治之中,将安全、经济、外交政策和国际制度联系在一起。处于20世纪90年代的第二代研究者使用了更精确的问题和方法,尤其是对全球机构和制度进行研究。凯特·奥尼尔 (Kate O’Neill)认为国际关系理论是国际环境政治必须依靠的母学科,可以借助国际关系理论理解国际环境政治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弗兰克·比尔曼(Frank Biermann)评述了国际环境治理与研究中的碎片化。面对纷繁的研究议程的变迁,罗纳德·米歇尔(Ronald Mitchell)归纳为:第一,国际环境政治和全球治理所进行的重新调整。第二,行为体(包括超国家行为体、区域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跨国公司)正在参与全球环境政治。第三,国际环境政治的现实是多个层面发挥作用的结果。第四,目前公认的全球环境问题和治理,与其他名义上非环境问题之间的关联日益密切。第五,学术文献更多地认识到全球环境政治和治理影响扩大。[3](P274)
由于目前气候变化问题无疑处于IEP的中心,与之相关的国际气候变化谈判、制度设计、资金、科学等问题,都引起了高度关注。托马斯·博诺尔(Thomas Bernauer)对气候变化研究的类型进行了分类,他认为气候变化政治研究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全球合作的制度设计、国家及地区层面的驱动因素及民族国家外的参与(市民社会、政治与科学互动及民众参与)。[4](P421-448)
然而,以上研究均忽略了国际环境政治中重要节点对研究议程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对这一领域的过程追踪与梳理,试图回答国际环境政治研究的议程、方法及变迁的原因。
二、国际环境研究的议程与方法
20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形势出现巨大变化,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开始成为一种基本的政治考量。环境恶化也逐渐引起各国的重视。因此,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全球主义范式的转变。国际环境政治研究也体现了这一变化。
(一)国际环境研究的演化历程
进入20世纪,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国际环境问题具有深远的复杂性。这也涉及国际关系的方方面面。[5](P437-462)通过回顾20世纪的国际环境政治,可以将这一时期的研究大体分成三个阶段:
1.国际环境理念传播阶段(20世纪60年代起)。
由于20世纪一系列震惊全球的公害事件和一批重要环境相关著作的反思性作用,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些关于全球环境觉醒的重要作品,如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1968年发表的开创性文章《公有地的悲剧》、[6](P1243-1248)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1962年的《寂静的春天》。[7]到了20世纪70年代,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8]及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亚理论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些作品的重要意义在于形成了全球环境意识,使世界感受到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迫切性。在传播重要环境理念的同时,它们也成为国际环境政治一直相伴的隐喻。国际环境理念的传播有力地促使了国际环境政治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出现。
具体而言,“公有地悲剧”的比喻表明了资源注定因不受限制的自由使用而被过度剥削。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每个个体都企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然而资源耗损的代价却转嫁所有可使用资源的其他人。“公有地悲剧”不仅影射
了国际环境问题,也成为全球公域和国际环境研究的基础。因为,究其根本,国际环境政治是集体行动问题。《寂静的春天》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强烈震撼了全球各国民众,为全球的环境运动提供了动力。1972年,德内拉·米德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对经济增长做出了比较悲观的分析,发现诸多因素与经济增长相关,并反思了当时的经济发展模式,贡献在于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提供了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詹姆斯·洛夫洛克提出了盖亚理论。随着全球变暖的发展,这位盖亚女神不断苍老,报复心增强,随时会惩罚人类。这一隐喻警告,气候变化的危机会让人类不得不为工业化对地球所造成的影响付出代价。它所传达的道德理念对气候变化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国际环境政治研究的萌芽阶段 (20世纪70年代)。
国际环境政治在20世纪70年代真正萌芽,与此同时,早期的国际环境政治文献也在这一时期产生。1970年,遏制之父乔治·凯南( George F.Kennan)在《外交季刊》上发表名为《防止地球成为荒原》的文章,[9](P401-413)讨论全球环境危机与治理的愿景。[10](P5)凯南指出环境恶化是累积产生的,已经成为美国的全国性问题,并已超越国界。他认为不仅是国际科学界,而且世界上最广大的市民都需要对全球环境问题引起注意,呼吁世界各国一道追求全球环境利益。
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后,理查德·福尔克(Richard Falk)等一些学者从国际法角度,论述了国际环境治理的迫切性,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于1972年发表了国际制度与环境危机的特刊,同年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的环境研究分会设立了奖励国际环境研究的哈罗德和玛格丽特·斯普鲁特奖。1987年4月,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正式出版《我们共同的未来》,呼吁全球将可持续发展原则融入经济发展之中。
3.国际环境政治的崛起与成熟阶段(20世纪90年代)。
国际环境政治崛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成熟于90年代末。在短短不到十年时间里,研究日益细化与成熟,使得这一领域不断发展。随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UNCED)的推动,各国领导人将全球环境变化议程提升到最高等级。从全球140余个多边环境公约的订立来看,半数以上是在1973年后产生的,而1992年之后,全球的环境制度设计成为国际政治的重要议题。这些公约中,包括保护臭氧、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濒危物种等环境问题的公约。
由于这些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关系学者开始加大对全球环境问题的研究。他们普遍认为,研究环境政治的历史是与全球性环境变化交织在一起的,而环境变化具有新的政治经济含义。1998年,迈克尔·祖恩在《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上发表的《国际环境政治的崛起》评述了当时主流的国际环境政治著作,系统阐述了IEP研究,标志着这一研究开始走向成熟。[11](P617-649)同样,全球范围内的众多博士生完成了其全球环境政治类的博士论文,很多政治学系开始开设国际环境政治课程。2000年,《全球环境政治》(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杂志创立,明确要求学者提交“当代国际与比较环境政治”类论文,发表如国家、多边环境制度和协议、贸易及环境运动的文章。目前,该刊在政治科学期刊中,影响因子一直居于前列。
在这一进程中,国际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一直保持了同步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崛起,其更加关注国家间的合作、国际政策协调等集体行动问题。20世纪90年代,建构主义学者将理念、规范因素等引入国际关系分析,力求通过国际规范的传播理解国际环境机制和国际环境问题。虽然,现实主义一直怀疑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对国际合作持悲观态度,并且认为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关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但是,双方的争论却推动了相关研究。[12](P5-49)目前,在三大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在国际环境政治中的影响最大。而建构主义在国际环境理论与案例的实证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突破。[13](P5-11)
(二)研究议程分类与变迁
目前,这一领域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研究日益细化,并且开始关注更多方法上的创新,以期更好地评估国际环境政策与治理的有效性。国际环境政治本身体现了国际关系中一系列规范性、理论性和经验性的问题背后的根本症结。其根本逻辑是集体行动问题。从国际关系角度看,它包括了绝对与相对收益的辩论、国际制度的角色、权力的作用、与合作相关的各种集团行为体的角色(非国家行为体、科学与政治互动等)。从具体研究领域看,国际环境政治可以分为气候变化治理、自然资源管理(水、空气、捕鲸、生物多样性、森林与荒漠化等)、环境污染治理等具体问题。[14](P1-2)从学科研究角度上看,国际环境政治研究又可分成四个重要类别:
第一类主要是依托于传统国际关系研究。这类研究主要包括环境制度与环境安全两个方面。这一类问题与国际关系研究紧密联系而又相互补充。[15](P13)在2005年到2014年的10年间,制度研究占《全球环境政治》研究性论文总数的53%。国际环境机制与制度研究为国际环境政治研究中的重点。目前,全球性环境组织、国际环境法律法规的体系、全球性的资金机制,以及与其他国际制度中环境相关的规则等内容构成了具体的研究议程。[16](P2-11)在国际环境机制的研究者当中,奥兰·扬(Oran R.Young)的研究为国际关系理论家所关注并借鉴到其他领域之中。他认为制度引发社会惯例,并将不同的角色分配给这些惯例中的参与者,进而治理不同角色占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17](P1-3)从最初的机制形成到机制进化、机制的复杂性、有效性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来看,环境制度学术讨论不断变迁。而在环境安全研究上,其最新的研究议程是分析环境恶化(气候变化)与战争、冲突和国家间暴力的关系。[18](P76-116)[19](P132-172)
第二类研究主要是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研究的内容包括资本主义、民主、WTO、贸易和跨国公司等对全球环境的影响。大量研究试图解释环境变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关于工业化与环境变化的研究则是该类别中的重点,还有些学者研究资本主义与南北结构的不平等问题。其中,贝奇·曼斯菲尔德(Becky Mansfield)从政治生态学视角,特别是环境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分析了南北关系的动态变化。[20](P236)此外,关于环境变化中的资本主义、贸易与跨国公司和WTO的研究等问题也备受关注。[21](P15-17)对于贸易与环境间的争论,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冷战后,贸易自由化在经济增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在进行国际贸易过程中却付出了环境代价,国际环境制度的规则与WTO相冲突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22](P160)国际环境政治的这一研究分支与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联系十分紧密。经笔者统计,近十年,这一类研究在《全球环境政治》的发文比重大约为19%。
第三类研究体现了环境方面的非传统安全因素。这一类通常研究市民社会、环境非政府组织、科学知识与政治的互动及环境话语。20世纪90年代,很多全球环境政治研究脱离政治科学、经济学和国际法等传统领域,开始关注环境运动、知识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其中,环境非政府组织研究在这一类别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外交的研究,表明了外交属性的变化,已经不能以国家间的视角理解全球环境问题的多边谈判过程。而外交属性的变迁反映了国际政治的复杂性,其中,米歇尔·贝西尔(Michele Betsill)等人关于环境NGO在国际谈判和决策中的作用的研究成为代表。[23]国际环境政治中的科学团体也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为,在应对环境问题时,决策者必须向科学家求助,所以外交家或政治家与科学家共同探讨治理全球环境问题或是参与环境谈判已成常态。彼得·哈斯(Peter Haas)等学者关注科学团体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24](P501)最近,科学与政治互动的研究,通过对科学评估中的政治过程和其对谈判的影响展开,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方向。[25](P1-2)
第四类主要研究一些与环境相关的哲学及规范性问题,如环境与人权、环境伦理及正义等在国际环境政治中的作用与影响。这类规范性研究在国际环境政治研究性论文中比例低,但是也不应该忽视其重要性。仅在环境与人权的关系上,规范的联系日益紧密,尤其体现在环境政策的制定对人权状况的影响方面。2012年的“里约+20”体现了建立平衡与整合经济社会发展(包括人权)和环境保护的全球计划达成政治共识。这些国际议程的推动,使得环境与人权间的关联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随着环境问题与人权等问题的联系加强,一些学者已出现将国际法、基督教思想、资本主义等研究运用到环境正义与伦理的讨论当中。[26](P359)因此,这类研究无疑也将会获得其他学科学者研究者的更多关注。
当前国际环境政治研究形成了以下一些特点:(1)研究议程日益丰富;(2)学科间交叉日益深入;(3)问题研究大于理论建构;(4)制度研究为核心;(5)以研究方法区分,而非理论学派。

表1 《全球环境政治》10年间(2005—2014)发表论文统计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全球环境政治》2005—2014年刊发情况整理,统计内容仅选取研究性论文,不包括书评、纪念性文章和论坛短文。

图1 10年间《全球环境政治》刊发论文的类型分布及趋势数据来源:作者统计与整理。
众所周知,国际环境问题的性质赋予了研究上的跨学科特征,它从自然科学延伸到哲学和宗教领域。[27](P500)与此同时,全球环境政治自身也是一个广阔的范畴,国际政治和环境之间的联系使其拥有庞大的跨学科文献,重点议程包括主权国家、国际机制、主权、国际制度、资本主义、全球贸易、跨国公司、国际金融、安全、伦理、市民社会等全球治理的方方面面。近年来,研究趋势表明,全球环境治理与制度有效性的研究日益加深。但是,政府间谈判、国际机制理论和理论假设等传统研究却一直没有改变。[28](P205)
(三)研究方法的演化及创新
通过政治科学的工具,国际环境政治学者已经就一系列环境变化与治理中的复杂问题进行了有效分析。由于传统政治和国际关系方法在解决全球环境治理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一些学科以外的方法和工具在环境问题中的作用很容易显现出来。[29](P1-3)环境、气候问题的跨学科特点决定了多元研究方法的应用。[30](P447)鉴于这一研究领域的复杂多变,传统的国际环境政治学者如奥兰·扬、彼得·哈斯、茜拉·加萨诺芙等人通常使用演绎的社会科学方法进行研究,为国际环境政治开辟研究领域。而新一代研究者突破了传统方法,不断借鉴其他方法进行研究。自2000年以来,国际环境政治朝着更加细化的方向不断发展。
按照凯特·奥尼尔(Kate O’Neill)等人的分类,当前国际环境政治的研究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定量、定性与模型(场景)(MSB)。决定研究方法的本质是“问题为先”环境研究特性所决定的。
从定性研究上看,从传统的案例研究到多场地研究,再到大规模数据采集与分析,国际环境政治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汲取了多元的定性研究方法。[31](P448)近年,除了传统的历史的比较的方法、案例研究及分类理论方法之外,过程追踪和大型事件团队研究受到广泛重视。
由于过程追踪(process tracing)方法的推动,[32](P114-129)案例研究近年来重新成为国际环境政治研究的重要手段。过程追踪是指侧重时间维度的研究,核心是理解因果机制。过程追踪的主要目的是理解原因与结果之间的中间过程,是利用对过程的历史阐述来验证理论或者假设的中间变量与互动,有助于理解案例内的因果影响机制。国际环境政治的机制与议题具有很强的过程追踪特征,通过议程内案例的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国际环境制度与机制的运作模式。[33](P646)
大型事件的团队研究(Collaborative Event Ethnography)。最近,一些学者将这种方法应用在201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第十次缔约方大会(COP10)的研究上。CEE的研究方法融合和借鉴了人物志(ethnography)的研究方法,这些研究团队观察大型事件,如对重要国际会议进行记录和分析。在大型会议上,团队的工作主要是:(1)分析场景中的个人、群体的思想倾向及其能动作用;(2)记录社会,政治、制度与机制过程中的合法性与竞争性观念;(3)会议记录对比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环境治理中的焦点问题。[34](P2)这种方法相较其他定性方法无疑具有很多优势,也符合国际环境政治大型会议多的特点,同时,由于也有动用人力和物力较多,对参与研究的人员要求也较高、分析过程步骤不清等缺点。
在量化研究方面,由于统计方法一直在不断发展,这种研究已经成为西方学界的国际关系研究的主流。采用统计、数学或计算技术等方法来对国际环境政治中的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经验考察,也在IEP研究中得到体现。这类研究的最重要过程是数据选择与测量过程。大样本数据采集与分析的方法,在欧美一些研究机构受到重视,因此建立起一些较为有名的数据库,如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库、密歇根大学的森林资源数据库等。[35](P446)
此外,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也开始使用在国际环境政治之中,[36]主要用于捕捉复杂的变量关系和弥补统计分析的不足。网络中的各种关联构成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中的结构。通过研究网络关系,能更好地把个体间关系、“微观”网络与大规模社会系统的“宏观”结构联系起来。在国际环境政治中,这种方法能够弥补简单的行为体分析,更加关注它们之间的关系,理解复杂的行为体与体系间的关系结构,如使用这种方法对美国国会中气候变化议题的研究,描绘出了不同意识形态对气候变化的不同发言,进而分析出气候政策的制定模式。[37](P457)
嵌入问卷的试验方法(survey embedded experiment)是调查者运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向被选取的调查对象了解情况及做出的反馈,进而分析调查政策偏好的研究方法。[38](P4)这种方法通常以了解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为目的,它是在问卷中嵌入试验,通过随机给与受访者一些环境相关信息,测试在不同条件下的反馈,进而为决策者制定环境政策提供依据。一般而言,问卷试验都有编码过程及清晰的变量关系。编码是把问卷中询问的问题和被调查者的回答,全部转变成为代号和数字的数据,以便运用电子计算机对调查问卷进行回归分析。使用这种方法可以有效测量全球环境治理的合法性及国际气候变化政策的偏好。
除了以上提到对过去或是当前的研究,还有一些方法主要处理对未来的预测与分析。这一研究方法的具体体现就借用模型和情景分析。由于其具有直观性的特点,而成为了一种趋势。特别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特别报告中所使用的排放情景(SRES)方法。[39](P57)
当然,研究议程与多元化方法的结合,也形成了诸多不同专长的团队。通过分析《全球环境政治》近10年研究型论文的方法,发现该刊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之间达成了良好的平衡。这说明,一方面是两个阵营的研究方法都在不断创新,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国际环境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这一现象的产生。
三、国际环境政治演化的原因
国际环境政治研究在方法和议程上的演变是由于深刻的内在属性和外在推动所形成的。跨学科特性使得学科在方法论上日益多元化,众多议程的调整则源自几次重要节点大会的推动。在国际环境研究中,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时间节点诱发研究议程的变革,如在20世纪80年代,气候变化问题并没有被推上研究议程,而是1992年里约会议后,这一研究开始大量涌现。
(一)跨学科性与应用性
国际环境政治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与应用性。通过政治科学的工具,国际环境政治学者已经就一系列环境变化与治理中的复杂问题进行了分析。然而,与此同时,IEP也证明了传统政治和国际关系方法在解决全球环境治理中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一些学科以外的方法和工具在环境问题的研究中效果显著。国际环境政治研究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它在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公共政策、科学技术研究、法学、经济学等领域都有交叉。国际环境政治研究中的跨学科性和应用性要求问题为先的内在变化需求。简而言之,环境、气候问题的跨学科特点决定了多元研究方法的应用。
迈克尔·吉本斯(Michael Gibbons)认为新的知识生产的出现是全球化时代的突出特征。一些新出现的研究系统具有高度的互动性和社会性分配的特点,以前的研究议程一直主要是在大学或是某些特定的学科之内。然而,现在一些研究已经开始在研究方法、研究议程、学科上及实践中出现了异质化。这样一种研究更加注重应用性,并且倡导跨学科的合作。[40]
(二)节点大会的影响
节点(benchmark)是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标志。巴里·布赞(Barry Buzan)认为国际关系的基准日期应该以重要性进行排列,主要的基准线要具有深层次变革、广泛的全球反映与后果等特点。并且根据这一标准,依次排列次等重要基准日期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准日期可能上下移动,重要性也将有先后的变化。理解基准日期和节点的变化,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的变革。
节点具有三个重要作用:第一,它服务于学科本身的自我理解,第二,使学科间相互区分,第三,由于具有具体时间特性,容易区分主要的变革动力。基准节点有助于理论建构,理解研究的主流化与边缘化等现象。在国际环境政治中1972、1992、2002、2012年四个节点具有不可否认的重要性,因此,这四次国际大会在国际环境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性与方向性意义。纵观西方国际环境政治研究,可以发现重要时间节点在不断塑造研究议程与方法的变革。因为具有重要历史变革性的基准节点释放了重要的研究机遇与动力。客体的变化无疑决定研究主体在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与适应。
跨学科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是国际环境研究的本质特征。在国际环境治理或政治研究中国际与国内各个研究流派方面具有突出的异质化特点,众多的环境政治研究都是基于现实需求展开的,在反思与社会责任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三)国际环境政治中的四个重要节点
第一个节点是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会议在规范、制度、纲领和融资层面形成了动议。第一项动议是通过宣言,鼓励和指引世界各国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第二项动议是建立了环境规划署;第三项动议是通过了环境政策发展的行动纲领;第四项是基于自愿设立了环境基金项目。这次大会之后,国际环境问题正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重要问题,其后一系列国际环境公约订立。由此,引起了更多学者的重视,国际环境制度研究正式开启。此外,也是在这次大会之后,才出现了第一本国际环境法的教科书。
第二个节点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在1992年地球高峰会上,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及《生物多样性公约》。此后,永续发展和可持续性等议题逐渐浮上台面,部分取代了旧有以生态为导向的思想。这些议题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兴起的反全球化可视为生态运动的后续行动。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科学团体等行为体成为国际环境治理必不可少的参与者,研究开始撰写国际环境领域的谈判进展。国际环境政治研究从谈判走向履约研究。这次节点大会使得南北问题成为热点,国际环境政治中的公平问题受到关注。[41](P51-55)
第三个节点是2002年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它是继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和1997年在纽约举行的第19届特别联大之后,全面审查和评价《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重振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动力。这次大会在意义上虽然无法与其他三个节点相比,但是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治理处在十字路口,多变的国际形势使环境治理变得日益复杂,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张力加剧,因此,这一情况使得研究不断呈现多元化的发展。
第四个节点是2012年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通常称为“里约+20”峰会。这次会议释放了绿色经济与制度变革的信号。具体而言:第一,达成新的可持续发展政治承诺;第二,对现有的承诺评估进展情况和实施方面的差距;第三,应对新的挑战。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集中地讨论两个主题:(1)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作用;(2)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里约大会的规范性意义十分重大,所形成的文件《我们希望的未来》,体现国际治理体系中各个领域关联性日益加深。[42]这次节点会议对国际环境治理的碎片化给予了关注,表明国际环境制度整合仍是重点。
四个重要节点性国际环境大会与国际环境问题共同对国际环境政治研究施加影响。特别是1992—2012年每隔10年不断地向问题领域发送新的信号,使得国际环境治理研究出现极快的调整和日益细化的倾向,使其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议程与多元化的研究方法。
与此同时,国际环境政治的实践随着历届节点大会的召开不断发生变革,这也是国际环境问题的跨学科性及应用性共同作用的结果。针对上述问题的重新调整反映了全球环境问题的相互联系以及人类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问题所面临的认识论的转变。未来国际环境政治研究需要更加关注问题领域间的关联: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环境与贸易的关系;环境与安全的关系;环境与卫生的关系;环境与人权的关系。就国际环境政治的研究议程与方法而言,议程的变迁仍然围绕着制度设计与不同行为体的影响而展开,但是研究的问题日益具体、分工更加细致,研究方法不断创新,借用不同定量、定性及模型场景的工具从事研究的趋势还在加强。因此,国际环境研究,将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大规模定量和定性研究之上,并且系统地检验理论和假设。总之,回顾国际环境政治的发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环境政治研究,把握学科正在进行的深刻调整,应对未来国际环境政治所带来的挑战。
[1] Ronald B.Mitchell.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Thomas Risse,Beth Simmons,Walter Carlsnae,(ed),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2.
[2] Peter Dauvergne.Handbook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M].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2014.
[3] Liliana B.Andonova and Ronald B.Mitchell.The Rescaling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J].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10,(35).
[4] Thomas Bernauer.Climate Change Politics [J].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13,(16).
[5] Barry Buzan.Rethinking Benchmark Dat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14,(20).
[6] Garrett Hardin.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J].Science,1968,(162).
[7] 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 [M].Orlando: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2002.
[8] Donella Meadows,Jorgen Randers,Dennis Meadows.Limits to Growth [M].St White River Junction: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2004.
[9] George F.Kennan.To Prevent a World Wasteland[J].Foreign Affairs,1970,(48).
[10] Kate O’Neill.The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1] Michael Zürn.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 Review of Current Research[J].World Politics,1998,50(4).
[12] John J.Mearsheimer.The False Promise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J].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4/95,19(3).
[13] Kate O’Neill.The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4] Matthew Paterson.Understand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Domination,Accumulation,Resistance [M].New York: Macmillan Press,2000.
[15] Peter Dauvergne(ed.).Handbook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M].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05.
[16] Frank Biermann,Bernd Siebenhüner,Anna Schre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New York: Routledge,2009.
[17] [美]奥伦·扬,[加]莱斯利·金,[英]海克·施罗德主编.制度与环境变化:主要变化、应用及研究前沿[M].廖玫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18] Thomas F.Homer-Dixon.On the Threshold: Environmental Changes as Causes of Acute Conflict[J].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1,16(2).
[19] Joshua W.Busby,et al.Climate Change and Insecurity: Mapping Vulnerability in Africa [J].International Security,2013,37(4).
[20] Becky Mansfield.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M].London: The SA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Geography,2007.
[21] Peter Dauvergne(ed.).Handbook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M].Cheltenham: Edward Elgar,2005.
[22] Kate O’Neill,The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23] Michele Merrill Betsill,Elisabeth Corell(eds.).NGO Diplomacy: the Influence of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Negotiations[M].Cambridge: MIT Press,2008.
[24] Ronald B.Mitchell.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Thomas Risse,Beth Simmons,Walter Carlsnaes(ed.).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2.
[25] Miller,Clark A.,Paul N.Edwards(eds.).Changing the Atmosphere: Expert Knowledg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M].Cambridge: MIT Press,2001.
[26] Hill,Barry E.,Steve Wolfson, Nicholas Targ.Human Rights and the Environment: A Synopsis and Some Predictions[J].Geo.Int’l Envtl.L.Rev,2003, (16).
[27] Ronald B.Mitchell.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Thomas Risse,Beth Simmons and Walter Carlsnaes (ed.).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2.
[28] Susanne Jakobsen.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Review of the Burgeoning Literature on the Environment[J].Cooperation and Conflict,1999,34(2).
[29] Kate O’Neill,The Environmen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30] Kate O’Neill,Erika Weinthal,et al.Method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13,(38).
[31] Kate O’Neill,Erika Weinthal,et al.Method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13,(38).
[32] Jeffrey T.Checkel.Qualitative Method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Pluralist Guide[M].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8.
[33] Michael Zürn.The Rise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 Review of Current Research[J].World Politics,1998,50(4).
[34] Lisa M.Campbell,et al.Studying Global Environmental Meetings to Underst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Collaborative Event Ethnography at the Ten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o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J].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2014,14(3).
[35] O’Neill,Kate,Erika Weinthal,et al.Method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13,(38).
[36] Stanley Wasserman.Social Network Analysi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37] Kate O’Neill,Erika Weinthal,et al.Method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13,(38).
[38] Mitchell,Ronald and Thomas Bernauer.Empirical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cy: Designing Qualitative Case Studies[J].The Journal of Environment & Development.1998,7(1).
[39] Kate O’Neill,Erika Weinthal,et al.Methods and Glob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2013,(38).
[40] M Gibbons,M.Trow,P.Scott,et al.The New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The Dynamics of Science and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Societies[M].London:SAGE,1994.
[41] P.W.Birnie,A.E.Boyle and C.Redgwell.International Law & the Environment[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42] UNCSD.我们希望的未来[R].2012,https://rio20.un.org/sites/rio 20.un.org/files/a-conf.216-1-1_chinese.pdf.pdf.
[责任编辑 刘蔚然]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Research and Its Reasons
Dong Li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benchmark;IRT;agenda;methods
Four important years (1972,1992,2002 and 2012) are recognized as important benchmarks by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Research.Given the close associ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together with interdisciplinary application,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is highly evolving.Research methods and agenda are driven by the intrinsic properties of both factors.Now,IEP research agendas focus on four main areas: traditional IR related agenda;IPE related agenda;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actors;ethical factors in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IEP presents plural research methods.This is because this area is always problem-oriented and with its interdisciplinary characteristics.Therefore,research teams,by means of qualitative,quantitative methods and models,work on the above agendas in depth to reach further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董亮,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