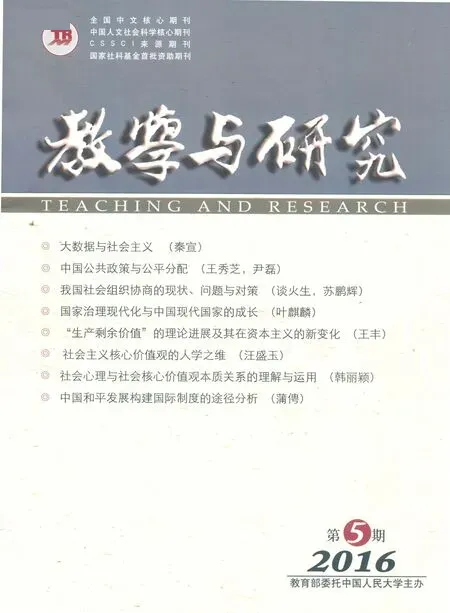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
叶麒麟
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
叶麒麟
国家治理;现代化;现代国家成长
以社会资源正义分配、国内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证为核心要义、任务的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而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在逻辑,它是考察现代国家成长较为科学、合理的维度。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维度下,中国的现代国家经历了独特的成长轨迹,即由传统国家治理危机所促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阶段,到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运动式治理所带来的国家一体化阶段,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化治理所带来的执政兴国阶段。
以民族国家作为组织形态的现代国家的出现,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其成长或曰建构(State-building)体现着一个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政治方面,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在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掀起的回归国家研究热潮下,现代国家成长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当然,西方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的现代国家成长上。例如,美国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指出,西欧的现代国家是通过战争的方式从而产生国家权力对社会的集中控制,进而逐渐成长起来的。[1]又如,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认为,国家行政力量的强大所带来的内部绥靖、军事进步所带来的国家对暴力更加强有力的垄断,致使国家对社会形成反思性的监控,这是促成民族国家形成的根本因素。[2]再如,美国学者西里尔·布莱克(Cyril E.Black)指出,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政治权力的集中化(表现为决策的强化)、法律规范的普及(同时导致官僚机制的发展)和公民在公共事务中作用的扩大。[3]不难看出,现有西方学者关于现代国家成长的研究大多只停留在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与控制的层面上。
相对于西方学术界而言,国内关于现代国家成长的研究热潮则是进入21世纪才兴起的。也正是进入21世纪,才兴起了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专门研究热潮。但是,综观现有文献,与西方学术界一样,国内学术界现有关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研究也大多停留在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与控制的层面上。例如,学者徐勇从以权力集中为特征的民族—国家和以权力合理配置为特征的民主—国家这两个角度考察了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4]又如,学者樊红敏尝试从权力的集中、渗透与重新分配等角度来探讨中国现代国家的理想型。[5]再如,学者储健国从国家机构的设置与调整角度来剖析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6]
不可否认,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扩张与控制,是现代国家成长的重要内容、任务和特征,但它不是现代国家成长的全部内容、任务和特征。因为在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与控制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合法性问题,换言之,我们为何要追求现代国家?本文认为,认可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扩张与控制,以及追求现代国家,关键的原因在于现代国家能够解决传统国家的治理危机,能够带来更好的治理绩效,包括社会资源的正义分配(即尽可能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和诉求)、内部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证。就此而言,相对于国家权力对社会的现代性扩张,以社会资源正义分配、内部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证为核心要义、任务的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更能准确反映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在逻辑,更是剖析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科学、合理维度。但是,现有关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与控制的层面,深陷在“统治”的理念桎梏之中。鉴于此,本文试图从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维度来剖析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
一、传统国家治理危机与革命建国
新中国成立以前,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经济等条件造就了“君主——官僚——民间精英”的独特的帝国治理体系和治理逻辑。在这一传统国家治理体系中,权力的核心在于君主,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但它则是通过体系化的官僚队伍进行国家治理的。由于官僚队伍主要居住在地域性城市中,因而传统国家权力并未直接深入到广阔的乡土社会中,即“皇权不下乡”。而广阔的乡土社会则是由族长、乡绅、商绅和地方名流等民间精英进行治理,从而使得乡土社会超然于国家。同时,“学而优则仕”理念的科举制对社会进行教化,选拔和吸收民间精英进入官僚体系,从而又实现了官僚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最终造就了君主专制集权的帝国治理逻辑。但是,该帝国治理逻辑的根本要害就在于君主的专制集权上。在相当大程度上,王朝的兴衰命运系于君主个人上,取决于其品质。而这一根本要害又带来了帝国治理体系如下三个具体弊病:(1)王朝重“内控”轻“御外”。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重心在于如何统治社会成员,以及在此基础上征收税赋。相对内部秩序而言,外部安全则较为忽视。(2)君主与官僚体系的沟通衔接往往存在问题。除了各种形式的朝会等正式渠道外,君主与官僚体系更多地通过君主的侍从、亲信和家人(尤其是外戚)等非正式渠道进行接触和沟通。而这些非正式沟通渠道往往会导致君主和官僚体系的冲突和矛盾,从而造就了宦官、外戚和女主专权这三大王朝祸患。(3)社会缺乏活力。在君主专制集权的帝国治理逻辑下,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官僚体系垄断了所有公共权力,对社会采取“重农抑商”经济政策,并借此对社会进行“分而治之”的统治,社会大众依附和受制于家族以及官僚体系,社会活力十分欠缺。
正因为上述弊病,中国传统国家无法提供长久的社会资源正义分配、内部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证,常常出现外族入侵、君权争斗以及农民起义等治理危机,从而出现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境遇。尤其在明朝宰相制度被取消之后,君主专制集权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帝国治理逻辑的弊病更加暴露出来,致使鸦片战争后的清朝政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治理危机。这具体体现在:(1)社会资源分配相当不正义。奢靡贪污、卖官鬻爵之风盛行,官僚、贵族、地主、富商大量兼并土地,失地无地的农民越来越多,大量农民因无法忍受横征暴敛而弃田逃亡,失去生计,四处流浪,整个社会贫富相当悬殊。(2)内部秩序紊乱。阶级矛盾激化,各地起义不断。其中,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沉重打击了清朝的统治。(3)外部安全荡然无存。在中华文明无法同化的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和开放通商,国家主权和领土逐渐丧失,致使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正是传统国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治理危机,以国家和民族为认同对象的民族主义才开始形成,中国的国家转型和现代国家成长之路才被迫开启。
在如何推动国家转型、解决传统国家治理危机的问题上,出现了改良和革命两种思路和做法。但实践证明,“戊戌变法”和“预备立宪”等改良式的现代国家建构在中国行不通,尤其是清政府在实行“预备立宪”时将科举制废除,更是中断了国家与乡土社会的流动与沟通,瓦解了国家对乡土社会的整合,造就了“一盘散沙”的社会状态,加重了国家的治理危机。而这更加决定了中国要走“革命建国”的道路。为此,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结束了帝国形态,并建立起了中华民国。然而,中华民国徒有现代国家的形式,地方军阀割据,社会资源正义分配、内部秩序以及外部安全都无法实现,国家仍然处于治理危机之中。正因为如此,孙中山意识到了组织对于革命建国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列宁式的政党”来解决国家治理危机,推动现代国家的成长。随后,孙中山的“以党建国”主张被国民党和共产党所继承。其中,国民党在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指示下,试图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专制政权来解决国家治理危机。然而,这一努力给社会带来的是无穷战争和沉重赋役,不仅未能解决国家外部安全问题,更加剧了社会资源分配的不正义以及内部秩序的动荡,从而遭受全社会的强烈反弹,由此也直接掀起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相对国民党而言,共产党的纪律更严格,组织更严密,革命方法更为彻底。共产党坚持以阶级斗争为指导思想,并由此引出群众观念,走群众路线,将组织深入至地方基层社会,动员广大群众参与到革命中来。正是在共产党的广泛动员和坚强领导之下,中国革命终于取得胜利,并于1949年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使得中国获得了国家主权独立,在全社会范围内确立了有效的中央权威,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换言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实践在解决传统国家的社会资源分配不正义、秩序紊乱以及外部安全荡然无存等治理危机,推动传统国家转型的任务上,已经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
二、运动式治理与国家一体化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真正结束了帝国这一传统国家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国家已经完全成长起来了。这是因为新生的政权还不稳固,国家治理还面临着因长年战火导致的社会经济资源匮乏,国民党特务、土匪和恶霸地主等国内反动残余势力扰乱国内秩序,美国等国外敌对势力威胁外部安全等严重危机。面对这些严重的国家治理危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继续采取了革命时期的群众运动方式,先后发动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具体而言,为了消除反动势力的扰乱,巩固国家政权,开展了“剿匪”、镇压反革命以及内部肃反等运动;为了改造社会,开展了“土改”、农业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等运动;为了发展生产力,开展了“大跃进”、“增产节约”以及“农业学大寨”等运动;为了改造思想,开展了“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以及“破四旧”等运动。据国内学者胡鞍钢的初步统计,从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开展各类政治运动多达67次,年均2.5次。[7](P620)据此,美国学者詹姆斯·R ·汤森(James R.Townsend)和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指出,“反复出现的群众运动是中共政治自1933年以来的一个特征,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政府运作的一种主要方式。”[8](P153)换言之,运动式治理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主要国家治理方式。
从本质上说,运动式治理是一种人治治理。具体而言,运动式治理是一种自上而下动员型的群众运动,是一种贯彻魅力型领袖意志的强力治理。这种治理方式极力反对官僚主义,极为崇尚领袖的智慧权威和群众的运动力量,因而具有如下显著的弊端:群众运动高度依赖于社会成员饱满的革命意志和激情,国家治理的绩效高度取决于领袖个人的运动治国理念和目标指示;一味要求社会成员个体的自我克制和自我牺牲,忽视个体必需的自由和权利;反对官僚主义,容易摧毁掉必需的国家科层制;崇尚群众运动式“大民主”,容易阻滞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直至损害到民主自身;群众运动过度,容易扰乱稳定秩序,削弱共产党的威信,等等。运动式治理的上述弊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之后,充分暴露出来。尤其是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更是运动式治理上述弊端的最充分体现。它造成了政治上的长期动乱,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迫害,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升,简言之,国家治理秩序遭受严重破坏,现代国家成长遭受严重阻滞。
既然运动式治理暴露出上述严重的弊端,那么是否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运动式治理对于国家治理和现代国家成长毫无积极意义呢?对此,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Gilbert Rozman)所言,“无论共产党在其前30年的统治中有过什么样的政策失误,由于认识到要适当地保持各级地方之间的平衡,它始终十分重视如何控制社会、积累资源、发展经济和国家一体化等问题。中国共产党同样面临着1949年以前阻碍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各种问题,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在许多领域受挫,但它还是基本解决了这些问题。”[9]应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运动式治理的客观结果就是,实现了国家权力对整个社会的高度动员和深度控制,对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执政党地位和纯洁革命队伍起到了积极有效的作用,从而造就了国家一体化的现代国家成长态势。
三、制度化治理与执政兴国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运动式治理,虽然实现了国家权力对整个社会的高度动员和深度控制,造就了国家一体化的现代国家成长态势,但其所带来的十年“文化大革命”这场严重的国家治理危机,引起了全社会对运动式国家治理的反思和批判。也正是在这种反思和批判的潮流下,自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伊始,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开始推动的国家治理方式由运动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的转变,自觉承担起执政兴国的使命,现代国家成长也才由此逐步恢复到常规化的理性轨道上来。
当然,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在制度化的国家治理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总结了运动式治理的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和反复强调要加强法制建设,努力完善各项具体制度。他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10](P333)“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0](P333)正是在邓小平的倡导下,自20世纪80年代初伊始,中国逐步恢复和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以及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和基层群众自治等基本政治制度。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不断深化的基础上,也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对各项制度的权威确认的宪法也得到修改,刑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也得以制定,中共十五大更是将以“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为基本要求的“依法治国”确定为基本治国方略。在某种意义上,该治国方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身份认知转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自觉以全面的制度化国家治理来完成执政兴国使命。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化治理,充实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相关领域的制度,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促进了人民民主的成长,保障了公民社会的成长,奠定了法理制度权威的基础,促成了重大的经济发展成就,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维护了国家的基本安全秩序。简言之,较之于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运动式治理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化治理在社会资源正义分配、国内秩序以及外部安全等国家治理层面具有不俗的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完成执政兴国使命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由于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等层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致使制度化治理还不完美。具体而言,在制度设计层面,由于认识和客观环境等原因,一些制度机制的设计还不到位。例如,中国各层级政府的权力清单制度还未到位,法制建设滞后,党纪约束、反腐以及协商民主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也尚未到位。在制度运作层面,一些制度运作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和冲突现象,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例如,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架构,在现实实践中还不完善,作为人民当家作主重要途径的人民代表大会未发挥应有作用等问题。总之,正是制度设计和制度运作存在某些问题,致使社会分配不公、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秩序不够稳定等国家治理问题。
制度化国家治理所存在的上述问题,恰恰给运动式治理提供了存在的理由和空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常常看到“扫黄打黑专项斗争”、“消防安全专项治理”等“集中整治”、“专项治理”、“零点行动”这类的行政性运动治理,还看到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三讲教育”、“先进性教育”、“群众路线教育实践”以及“三严三实”教育等政治学习性运动治理。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上述行政性运动治理和政治学习性运动治理的实践过程中,相应治理领域的制度也得以处于不断改革和完善的进程之中。换言之,改革开放以来的运动式治理不仅仅是为了弥补当前制度化国家治理的漏洞,而且还促成了相应治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关于这一点,最显著的体现就在于,为了应对治理的制度化不足,规避运动式治理的弊端,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和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国共产党更是首次专题讨论依法治国,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做出了总体部署。总之,尽管改革开放进程中存在着如美国学者汤森和沃马克所指出的由运动式治理来推进制度化治理进程这一“制度化运动的悖论”,[8]但制度化治理已是目前中国国家治理的主要方式,执政兴国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自觉认识和行动,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国家成长态势。
四、结 语
综上所述,以社会资源正义分配、国内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证为核心要义、任务的国家治理,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而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在逻辑,它是考察现代国家成长较为科学、合理的维度。正基于此,如前文所述,中国现代国家经历了独特的成长轨迹,即由传统国家治理危机所促成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阶段,到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运动式治理所带来的国家一体化阶段,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化治理所带来的执政兴国阶段。应该说,制度化治理是中国目前现代国家成长的主要任务,也是现代国家的理想治理模式所在。
另外,必须提及的是,本文所选择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维度,对于目前现代国家成长研究至少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不能简单停留在国家权力对社会的扩张与控制层面上,还应深入剖析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与控制的合法性问题。国家权力对社会扩张与控制的合法性在于,国家权力对社会基本诉求的实现和满足,而这涉及的是国家治理范畴,包括社会资源的正义分配、国内秩序的保障以及外部安全的保证等。现代国家成长的研究,应重点关注国家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这样才能更深刻地认识现代国家的基本属性以及现代国家成长的内在逻辑。正因为国家治理之于现代国家成长的重要性,作为为数不多的探讨国家治理能力与国家构建关系的学者,日裔美籍政治学者弗兰西斯·福山的相关研究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11]
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可以淡化现代国家成长研究的西欧色调。正如有国内学者指出,国内学术界在论及现代国家成长时,主要引用和分析的是西欧经验。[12]国内学术界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西欧民族国家的成长经验为依据,探讨现代国家成长的动力问题,探讨国家权力与社会之间的组织结构架设等问题,从而忽视了非西欧国家的特殊情境。而从以社会资源正义分配、国内秩序保障以及外部安全保证为核心要义、任务的国家治理维度,来探讨现代国家成长问题,就可以淡化现代国家成长研究的西欧色调,可以增加现代国家的多元成长模式。
第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现代国家成长的比较研究提供更为科学、合理的分析维度。目前关于现代国家成长的比较研究,往往简单地从国家组织结构、制度形式等维度进行比较。这样的比较研究容易陷入制度结构形式的简单论争之中,得不出有价值和规律性的认识。而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维度,对各国制度结构形式运作效果进行比较研究,将为各国现代国家成长的比较和评价提供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维度,而这将有助于深化和充实现代国家成长的比较研究。
[1] Charles Tilly.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2] [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
[3] [美]西里尔·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4] 徐勇.“回归国家”与现代国家的建构[J].东南学术,2006,(4).
[5] 樊红敏.论现代国家的理想型——以权力运作为视角[J].东南学术,2006,(4).
[6] 储建国.大部制改革与现代国家构建[J].学习与探索,2008,(7).
[7] 胡鞍钢.中国政治经济史论(1949—1976)[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8] [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9] 转引自郭为桂.群众路线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J].东南学术,2011,(4).
[10] 邓小平文选[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1] [美]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政治秩序的起源[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2] 刘义强,管宇浩.国家建构:为什么建构、建构什么与如何建构——简论国内研究之不足[J].学习与探索,2015,(6).
[责任编辑 刘蔚然]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the Building of China’s Modern State
Ye Qili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state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the building of modern state
The state governance, which takes the justice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the guarantee of domestic order and the external security as the core, is the basic attribute of the modern st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s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building of modern state. In the dimens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the modern state in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unique building path, which is from the traditional state governance crisis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successful revolu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o the 30 years of state integration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then to the new stage of building the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 本文系华侨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华侨大学高层次人才科研启动费项目“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研究”(项目号:14SKBS204)的阶段性成果。
叶麒麟,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福建 泉州36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