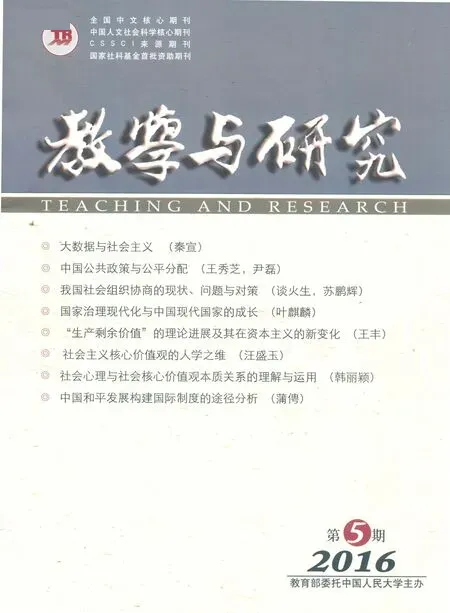“生产剩余价值”的理论进展及其在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王 丰
“生产剩余价值”的理论进展及其在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王 丰
生产剩余价值;理论进展;现实变化;新特点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在《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指出了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随着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微观组织形态、行为的变化,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也出现了较大变化。在新形势下,国内外学者深入探讨了“生产剩余价值理论”,实现了理论进展与现实变化的契合。现实变化主要有五个方面,即金融资本的掠夺式剩余价值生产、资本空间扩张的剥削式剩余价值生产、技术进步式的生产剩余价值、劳动者技能升级式的生产剩余价值和新产品投资式的生产剩余价值。五大变化形成了当前“生产剩余价值”的三个新特点:长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短期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并举、提高全要素增长率与资本投资并重、劳动力价值提高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并存。
所有资本家的利润都来自剩余价值,它们是雇佣劳动者生产的总价值中超过支付他们工资所需要的产品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利润必须由雇佣劳动者以剩余价值的形式生产出来。然而,新古典学派从劳动与资本的物质边际产品开始,就好像经济是可以撇开社会关系而可理解的纯技术过程,社会关系是固定不变的。马克思的重要贡献不是关于相对价格的理论,而是对资本主义关系如何导致剥削所提供的解释。市场经济推动的经济形态演进和变化,更使得国内外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利用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来否定被歪曲了原意的马克思理论,或者时常纠缠于无关紧要的技术性细节,试图转移人们关注马克思主要贡献的视线。海尔布罗纳强调指出下述逻辑上的区别,即,置于“生产上的剩余价值”概念与劳动价值论是有差异的,劳动价值理论旨在用劳动力解释相对价格。[1](P45)工资劳动者能够生产的剩余,不管价值来源如何,只要劳动力价格加上使用的原料价格少于劳动产品的价格就可行,这里的“剩余”,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就是剩余价值。因此,探讨“生产剩余价值”的现实变化和特点,首先应该厘清“生产剩余价值”的理论演化。
一、生产剩余价值的理论进展
对有关剩余价值生产的新探讨,是随着全球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微观组织形态、行为的变化而展开和推进的。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典型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部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衰落趋势,其制造业优势逐渐转移到东亚、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并利用金融力量和金融权利,向全世界扩散本国的剩余资本来攫取经济资源,不断促成国际垄断资本的成型。但是,资本的生产关系一旦形成,无论是以实体形式存在的资本,还是以虚拟经济形式存在的资本,垄断资本的属性都不可能摆脱资本的本质。所以,即使在国际垄断阶段,利润最大化仍然是当代垄断资本的内在趋势。垄断利润总额限于剩余价值总额。“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2](P975)据此,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者认为,在总利润量既定时,垄断利润要么是在同非垄断的市场主体竞争中,从非垄断企业转移来的利润;要么是通过低价购进的原材料高价出售制成品,从其他中小企业中转移来的利润。甚者,通过降低劳动力工资,把一部分必要劳动转化为剩余劳动,来增加利润。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生产的加强受阻于生产成本的上升。戈尔茨坦认为,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扩张,都带有资本积累和大规模投资的特征,这使得失业率降低;失业减少提高了劳动力讨价还价的能力,因而出现平均工资上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放缓;资本家只有通过迫使雇佣劳动者创造出高于成本的剩余价值,才能保障再生产的继续。[3](P211-234)马克思承认,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资本家的投资增加,导致劳动力供给短缺,引起工资增加、剩余价值减少,进而引起危机。马克思把这一过程的诱致因素称为“工资的特殊提高”。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资本主义扩张,剥削率会提高,即利润的提高快于工资的增加。“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从而和劳动剥削程度趋向提高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工资率的提高来说明利润率的降低了,虽然这种情况在例外的场合也是存在的。”[2](P267)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正常的情况是,在扩张时期,工资的增长赶不上利润的提高,不能把周期高涨时期利润率的下降归咎于工资的增加。
对于马克思这一观点的回应,巴兰(Paul Baran)和斯威齐(Paul Sweezy)把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剩余价值”修正为“经济剩余”。他们认为垄断企业同中小企业、劳动力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都是受他们影响的市场建立起来的。这些大企业、跨国集团(资本)的价格和成本政策,使它们获得的“经济剩余”不仅在绝对量上,而且在相对量上都在不断地增长。据此,两位学者判定,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不再是利润趋向下降的规律,而是“剩余增长的规律”,并认为这是与竞争资本主义最本质的区别。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垄断资本在不断创造出经济剩余的同时,并没有为这些增加的经济剩余提供出路。“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制度,它总是形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可是它不能提供日益增长的剩余所需要的、因而是为使这个制度和谐运行所需要的消费和投资的出路”。[4](P74)与此观点对应的是,哈维(David Harvey)提出了“剥夺性积累”的概念。他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领域受到威胁,转而通过金融领域来维持剩余价值量的增长。由于运输成本的降低、各国基础设施的改善,降低了很多发展中国家重新安置所需的固定资本投入,提升了制造业资本的地理流动性,从而导致金融资本日渐出现过度流动的局面。当前,金融资本越来越具有易变性和掠夺性,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对工人阶级运动的规范和国家行为的调节施加决定性影响。[5](P55)2009年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给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接管受影响严重国家的金融体系、产品市场以及逐渐壮大的公司的机会。这种利用金融权力,接管国外或区域外的贬值资产,以攫取高额剩余价值的方式,为核心地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剩余”找到了出路,实现了哈维所谓的“剥夺性积累”。达斯古普塔(Byasdeb Dasgupta)据此认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有利于剩余价值转移,并将其通过国民储蓄、公司投资等方式积累于金融部门。金融创新带来的各式衍生品帮助剩余价值从最初的金融部门的投资G膨胀成G’,产生出金融剩余价值ΔG。[6]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金融部门的运行生产,来榨取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即资本主义的金融化。
资本主义金融化背景下,国家资本主义崛起、新自由主义影响的双重叠加,使劳动力的性质有了新的变化,即劳动力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在全球(金融)资本主导下,大规模的资本积累成为资本主义追求的目标,并具备了实现该目标的条件,即金融资本的掠夺性和劳动力的弹性化。对于后者,劳动者要从过去仅仅在工厂中从事剩余劳动的生产(固定的劳动力)转变为金融化时代自由流动地从事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1)劳动力在不同工种之间的不断转化,或在就业与失业间转换;(2)劳动力在空间的不断流动。流动的生存(生产)方式,最终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常态,是将劳动力“偶然的”、“暂时的”、“无规律的”、“流动的”劳动变为他们“规律性”常态,这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剩余劳动、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提供必要条件。资本金融化时代的劳动力碎片化程度更为严重,生产过程呈现非正式化和离土化趋势。流动性是劳动力的当前形式。相比固定劳动力,流动劳动力为维持生计更有可能在同一时间、相同或不同地点占有多种的、不同的阶级地位。因为,如今的劳动者在金融资本的强大攻势下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风险。
这样阶级关系、阶级分析被引入剩余价值的纯技术分析之中。当代多数的国外左翼经济学家都继承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方法,认为剩余价值生产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经济技术决定,而是应该更多地看作是由劳动力和资本家两大阶级关系决定。其中,一部分学者从两大阶级之间的冲突入手分析剩余价值生产,另一部分学者则强调阶级合作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对于前者,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迪斯(Herbert Ginitis)的研究表明,即使有明确劳动时间和工资合同,劳动者的劳动强度(我们知道,劳动强度和剥削、剩余价值生产息息相关)也与阶级冲突密切相关。例如,在劳资关系缓和阶段,劳动强度通常是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一般标准。不过,在劳资矛盾激化时期,劳动强度通常无规则可循。[7]可能出现的现象是,劳动者在工作日内看似认真劳动,实际行为上非常消极。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用大量事实证明,在一定技术水平下,资本家总是竭力提高劳动力的劳动强度,精确测算劳动时间和构建标准的工作规范。除非工会力量强且有充分就业条件,否则劳动力无法抵制劳动强度的增加,更无法分享“经济剩余”。[8](P127)卡弗(Tho ̄mas Carver)以美国为例,进一步补充说明,工会化企业普遍比非工会化企业生产率高,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比较低。[9](P120)对于后者,普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只要劳动力与资本家作出妥协,就可以在互利的基础上保持自由企业自由雇工的制度。[10](P183)因此,在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范式中,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使得欧美工人阶级运动遭遇了历史性失败。[11](P575)科技变革促成了以不变资本形态存在的生产要素成本价格的下降;与过去传统的工厂工人相比,当前的劳动力素质大幅提升,使得作为人力资本储备的可变资本数量大大增加。两者的合力,必然降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水平和剩余价值率。如果没有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长,很难想象资本主义会生存至今。
当然,在维持剩余价值生产增长方面,据阿姆斯特朗(Philip Armstrong)、哈里逊(John Harrison)、格林(Andrew Glny)的统计检验表明,积累及其新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积累的动力和新领域的投资,前者保障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后者保证较多的剩余产品能够找到市场。[12](P157-158)剩余价值生产和新部门的开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以日本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期间为例,据都留重人的统计,在这一时期以前的工业品,从当初占全部产品的100%,下降到这一时期期末的61.9%;20年间,新产品占总产品的比重不断上升。例如,1951—1955年间问世的产品占总产品比重由1955年的6.8%发展到期末的13.4%;同上,1955—1959年间问世的产品占比由1960年的5.5%发展到期末的14.2%;1960—1964年间问世的产品占比由1965年的4.2%发展到10.5%。[13](P106)可见,保证剩余价值生产持续增长的宏观实现条件是剩余资本能够顺畅地流向符合消费和竞争需要的新部门。如前文所述,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整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制造业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削弱。产业空心化和经济虚拟化引发的多次金融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深刻认识到虚拟资本的空资产性质和难以收回的特征。国内有学者指出,后危机时代,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正在进一步加快“再工业化”的回归实业进程,并将重点放在新能源和环保产业上,把低碳技术及其产业化作为突破口,实现产业结构再调整,推动新一轮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张*参见周宏:《后金融危机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求是》,2011年第9期;王秋石:《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的五大特征》,《当代财经》,2009年第12期。。
以上关于“生产剩余价值”的探讨是多角度的,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长提出了各自的答案。无论这些方法多么的不同,都要回到马克思那里,他认为,与剩余价值的生产不一样,剩余价值的来源,且唯一源泉就是活劳动。自马克思以来的一百多年资本主义历程,诸如科学技术水平、设备现代化水平等劳动的客观条件发生了巨大变革,也引起了劳动的主观条件,即劳动力的发展。马艳认为,马克思的时代,劳动客观条件的变化在程度和速度两个方面,远远强于主观条件的变化;这使得马克思在构建价值理论,进而分析剩余价值生产时,假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是一定的,“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只存在自然形态的变化,不存在密度形态的变化”,[14]也就是只考虑劳动客观条件的变化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众所周知,剩余价值的生产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方式。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自然劳动时间不变,如果密度形态的劳动增加了,绝对剩余价值相比上期仍会增加;同样的,单位时间内密度形态的劳动增加,可以在劳动力价值不减少的条件下,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14]学术界普遍承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当代社会进行财富积累和价值增值的主要方式。“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15](P583)沈开艳强调,劳动技术过程的革命就是科学、技术的变革;社会组织的革命,是组织管理的科学化;因此,包括脑力劳动中的经营劳动、管理劳动和服务劳动,尤其是以知识要素为内涵的密度劳动具有超前性、垄断性、稀缺性和创利性等特点,在商品价值或者社会总价值中,能够起到降低价值构成的作用,推动利润率提高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16]
当前生产剩余价值理论的新讨论、新争鸣、新应用,一是基于理论本身的发展,这是文本研究的结果;二是基于现实问题的回应,这是宏观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解决实践困境的结果。有效地运用这些新的理论成果,作用于现实社会实践,必将带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新变化,推动剩余价值生产。
二、生产剩余价值的新变化
正是剩余价值来源与生产的分析,实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理性批判,唤醒了工人阶级的主人意识。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者群体通过自觉的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及其所统治的社会为了生存而不断调整生产关系。“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7](P34)如今,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发生了新变化,不断认识和总结这些新变化,是新形势下剖析资本主义有机体,丰富“两个决不会”和“两个必然”内涵的重要途径。
1.生产剩余价值新变化的现实背景。
第一,技术革命的新变化。每一次的经济繁荣和飞跃背后必然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马克思也提醒,资本主义抽身经济危机漩涡的方法之一就是“创新”。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科技进程中最大的创新就是“信息技术创新”。直到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设备和软件投资的几何年平均增长率为13.5%;20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十年间,它的几何年平均增长率为8.6%;大大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但2000年至今,该数据回落至2%,[18]与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持平。由于信息技术创新和相关投资的总体疲软,使得信息技术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推动力日益降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正好发生在这个时期,反映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群推动了世界经济上升周期趋向的结束。新技术的发展和变化,又导致生产剩余价值的环境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
第二,资本流向的新变化。戈登指出,经济增长的上升期,常常伴随信用扩张;特别是经济周期繁荣阶段的后期,常常产生不计后果的信用扩张和没有节制的(逃避政府监管的)信用欺骗。由于技术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使市场产生非常乐观的预期,在稳定的经济系统中,包括企业家、农场主、消费者、政治家和经济学家都会认为这样的情况会长期持续,社会开始更多地信贷,信用扩张由此形成,且速度越来越快。[19]作为信息技术创新领导者的欧美国家,由于其自由的经济体系、高涨的科技创新和大量的先进专有技术,在实物和金融投资上拥有比其他国家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当技术创新获取的边际利润下降,资本在实体经济中难以获取超额利润时,已经创造出来的各种金融工具将会被用于金融市场进行金融投机。在信息技术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释放殆尽,又缺乏新的技术发明时,大量的积累资本、剩余资本投向没有出路,便开始流入房地产部门或者流向金融等虚拟经济部门。
第三,劳动力条件的新变化。随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产业结构的高端化和资本金融化,雇佣劳动者普遍受到教育或职业培训,以往“体力劳动型”的雇佣劳动者被高素质的劳动者所取代。国家以及企业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对劳动者进行教育投资的比重也不断增大,推动形成复杂劳动,培养他们支付了高得多的教育、训练费用,其劳动力价值也远超一般劳动力。剩余价值生产和流通方面的复杂劳动,与一般劳动相比,在单位时间内表现为密度形态的劳动,有助于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者不仅实行8小时工作制,还普遍实行每周5日工作制;某些国家,如法国,一些产业部门甚至实行每天7小时、每周4个工作日的劳动制度。
第四,资产阶级国家社会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新变化。上述一系列新情况的出现,使得作为总体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逐步调整了劳资关系的应对方式。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劳动时间和劳动价格的制定成为劳资双方博弈的结果,资本家很难单方面决定;资本家从维持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利益出发,也可能用提高工资的方法提高效率。这样,资本主义国家在表面上,从对资产者的偏袒、对劳工运动的镇压,转换为一种貌似公正的中性立场,并推出一系列社会福利方面的措施。人们以此作为生产力发展红利在两大阶级之间的共享制度化凭证,就不足为奇了。这一表象背后隐藏的是,资产阶级国家通过对劳动者征收重税的形式,来实现所有人(包括资产阶级和其他不劳动者)福利水平的普遍提高,剥削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形式有所变化,即单个资本家剥削局部劳动者变为他们的总代表,即国家来剥削总体劳动者。国际上,全球经济秩序处于国际垄断资本控制之下,推动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交换格局的形成,资产阶级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利用劳动力创造和扩张剩余价值,进一步缓解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
2.生产剩余价值新变化的主要内容。
如果将劳动者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两个部分,则剩余价值生产有两种方式: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即将工作日延长到必要劳动时间以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即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就绝对剩余价值而言,只要是剩余价值生产,工作日总是要超过必要劳动时间,即使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也不例外;从这层意思上说,所有剩余价值生产都是“绝对的”,只是方式各异。当然,这不是绝对剩余价值同相对剩余价值相区别的论述方式。但为了叙述上的方便,我们暂时站在这一观点上来阐述在工作日界限限制、劳动力身体界限和道德约束条件下,这种类似绝对剩余价值*这里把工作日不变,在劳动力身体界限和道德约束下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称为“类似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以区别于完全依靠延长工作日和无休止提高劳动强度的传统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本文不再研讨传统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生产出现的两个新变化。
假设一定时期,科学技术水平保持稳定,没有出现重大创新和发明;社会组织总体上没发生变革和大规模的转型;实行经济开放,贸易壁垒较少。如果上述假设条件成立,在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受到自然的、道德的、生理的限制情况下,从宏观看,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只能靠资本形态转化或者资本空间扩张。因此,“类似”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两个新变化为“金融资本的掠夺式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空间扩张的剥削式剩余价值生产”。首先,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产业空心化,以及实体经济领域的职能资本从产业发展方面来生产剩余价值日益困难,转而将职能资本更多地配置在金融资产上。以美国为例,非金融企业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其总资产的平均比例由1980年的26.9%上升到了2007年的48.9%,同期,美国金融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80年的7.5%提高到2007年的12.9%。[20]金融资本的扩张,是对现阶段职能资本不易获取剩余价值或超额剩余价值的现实回应。同时,它通过自身的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衍生品的多样化,不仅可以获得最原始的存贷款利息差,还能攫取高额的金融剩余价值。这里的金融剩余价值有两层含义:其一,金融资本盈利的最终来源是当前时期,职能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属于“现时”的剩余价值。其二,金融资本的产品和工具,可以夷平购买力的时空界限,在时间上,使市场上交易的对象不仅包括当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剩余价值),也包括还没有生产出来的商品(未来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因此,当前实现了的利润或剩余价值总额大于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剩余价值被名义化了。在社会现有生产力条件下,金融资本通过大规模的信用和货币创造,实现了生产剩余价值总量呈几何倍数的增长。在空间上,金融资本更显示了它的掠夺性。它直接通过“入侵”他国,通过迫使他国一次次的资本贬值和资本损失,来重新获取他国的相关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商品设备和基础设施等,用来应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在扩大再生产过程无法保持资本积累和剩余价值生产平稳进行的情况。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最近20年来,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活动中的应用,促进了金融资本的扩张、异化(实体经济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与金融资本脱离实际生产所创造的、各种资本需要瓜分的剩余价值总量之间缺口越来越大),进而为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提供了物质技术支撑,为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埋下了伏笔。
其次,资本空间扩张的剥削式剩余价值生产,也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剩余资本不仅通过金融领域寻找剩余价值生产的出路,还通过国际垄断资本的形式,向全球进行资本渗透和产业布局,大规模地剥夺全球自然资源及其商品化成果;大规模地剥夺全球文化形态、历史和智力创新领域的商品化成果;大规模地剥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开发的控制权,使国内过度积累的资本能够以极低的价格,有时甚至完全免费的形式,抓住这些资产,并迅速利用这些资产进行赢利、生产剩余价值的活动。其二,根据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和国际剥削”理论,劳动在国际间的不可流动性导致了工资的国民差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资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两者之间的产品和价格也有所差异,发展中国家用一定数量的劳动时间所生产的产品只能交换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较少的劳动时间所生产的产品。这个过程中,在国际垄断资本主导的经济秩序下,改变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及其生产的具体形式,原有的平均利润越来越变为国际垄断利润。剩余价值也超出了单个企业、单个国家的范围, 成为国际资产阶级对国际无产阶级进行剥削的集中表现。
上述绝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新变化,是在假设技术不变的前提下,资本形态变化和活动范围变化所引起的。而非单纯依靠延长工作日和增加劳动强度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要突破工作日和身体的界限,关键还是应当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它是指,在假定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从而增加剩余价值。撇开上文所假设的三个条件,只考虑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生产剩余价值有三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技术进步式的生产剩余价值。当今社会,工作日的缩短成为趋势,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必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前提。劳动生产率是以单位时间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或者单位产品生产所需时间来进行计量的,它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展、科学技术在工艺中的应用、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组织管理等因素。其中,技术进步是关键。学术界很多人都提出,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应该把技术单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加以重视。那些实现了以“效率”来驱动经济增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全要素增长率(由技术进步所产生的GDP增长率)都在60%以上。[21]可见,技术进步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最先采用新技术的个别资本将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当新技术被普遍采用,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一般剩余价值率提高,超额剩余价值消失,相对剩余价值就产生了。在信息技术的创新出现停滞、技术红利出现衰竭时期,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开始重视低碳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具有广阔创新空间的新技术领域。
其次,劳动者技能升级式的生产剩余价值。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倾向承认,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劳动者素质提高,工人技能升级的长期趋势。“总体而言,‘认知的’素质(即要求推理能力和特定工作岗位上的专门知识)以及‘互动的’能力尤其是协调和管理他人的能力,在过往的至少三十年间都稳定地表现出增长”。[22](P183)这一趋势,使原来体力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向脑力劳动者生产剩余价值转变。后者的劳动是一种高级复杂的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能在同样时间内比一般劳动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这种趋势的延续,对价值构成产生了影响,虽然劳动总量或者价值总量不变,但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阻碍了平均利润率的降低;保障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最后,分工和新产品投资式的生产剩余价值。前文提到,剩余价值生产和新部门的开辟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常常利用国际分工的优势,占据着产业链的高端,引领新产品的开发和销售,获取超额剩余价值。此次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过后,这些国家开启了以“数字制造化”和“个性化”为主导,以“低碳产业”、“洁净能源”为方向,以“高端制造产业”为依托的再工业化进程。企业家、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注点也已经转移到低碳产业和洁净能源产业的新产品问世和应用上。这些新产品的创造,必将引起新一轮的消费需求,带动生产剩余价值的增加。
三、生产剩余价值的新特点
传统的观点认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有着难以逾越的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限制,要突破这些制约,剩余价值扩张的关键是由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但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必须以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前提条件。因为,单个生产部门提高劳动生产力,只会使它自己生产的那种商品变得便宜,只能降低劳动力价值中相应的一部分。基于此,从社会经济发展长期来看,这一观点是正确且合理的,一是长期内技术进步是可以实现的;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特别强调科技进步的作用。短期来看,现实实践与理论逻辑出现了偏差。在短期内,技术创新和发明可能发生在个别企业,而难以在全社会范围内出现。即使个别企业在短期内出现了技术创新,在获得超额剩余价值过程中,会引起其他企业的竞相效仿,但要实现由此产生的技术大范围扩散和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也是很难的。
这样,当今生产剩余价值就出现了第一个新特点:长期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短期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并举。上文已经论述,这里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并不是传统的绝对延长工作日和劳动强度,而是在工作日“绝对地”超过必要劳动时间的现存条件下,所呈现出的一种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形态特征,如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职能资本具体化等资本形态变化来实现剩余价值生产。资本金融化,就是职能资本的转化和具体细化过程;是职能资本流向金融部门,转换为金融资产,金融资本不断壮大的过程。金融资本对社会财富和价值的掠夺性、扩张性,使其能在短期内和较大范围内,实现价值增值,弥补技术创新短期变化不明显所形成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停滞的缺陷。
生产剩余价值的第二个新特点: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并举”相对应的是,以“提高全要素增长率与资本投资并重”实现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快速崛起、新帝国主义的目标引领和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主导等多重背景下,使得依靠提高全要素增长率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重要性不断降低,资本投资和空间扩张显得更为重要。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大量资本剩余,这些积累的资本必须找到吸收自身的载体。因此,在新帝国主义意识的影响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国际经济组织的干预,并利用逐渐萌芽的新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和国际垄断资本实力,在全世界范围内剥夺他国的贬值资产,尤其是能源与金融贬值资产。另一种方式,就是投资他国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产业渗透布局和新产品开发,为信息技术创新停滞情况下的长期剩余价值生产和增值奠定基础。
劳动力价值的确定,包括维持劳动者本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维持劳动者家属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和劳动者的教育培训费用。因此,长期内,即使实现了普遍的技术进步,提高了全社会的劳动生产力,降低生活资料价值,但未必就能降低劳动力价值以及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原因在于,劳动力具有“技能升级”的长期趋势,伴随的是,劳动力教育培训费用等人力资本投资出现大幅度增加,甚至能够抵消生活资料价值的下降幅度,最终提高了劳动力价值。不能实现劳动力价值的下降,就无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当然就不可能实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由此,推论生产剩余价值的第三个新特点:既然无法降低劳动力价值,就在保持总投资不变的情况下,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利润率,实现生产剩余价值增值。我们看到,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抢夺人力资源,甚至包括工业革命时代被抛弃的熟练工人。高素质劳动力的复杂劳动,能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这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劳动力是生产力体系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
生产剩余价值的理论进展和实现变化表明,虽然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产关系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变换了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缓和了阶级关系,推动了经济发展。但这根本没有改变资本的本质,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剩余价值的生产,在把全世界卷入资本主义运动之中的同时,必将反作用于资本主义运动,改变其面貌,最终成为共产主义实现运动的历史缩影。
[1] 海尔布罗纳.资本主义的本质与逻辑[M].马林梅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Joshua Goldstein.Long Cycles:Prosperity and War in the Modern Age[M].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
[4] 巴兰,斯维齐.垄断资本[M].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5]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沈晓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6] 拜斯德伯·达斯古普塔.金融化、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全球危机和新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视角[J].车艳秋译.国外理论动态,2014,(11).
[7] Bowles, S and Ginitis, H. Structure and Practice in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J].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2006,(12).
[8] 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M].方生,朱基俊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9] Carver , T. and Thomas , P. eds. Rational Choice Marxism[M].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5.
[10] 普沃斯基.国家与市场——政治经济学入门[M].郦菁,张燕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
[11] E. Mandel.Late Capitalism[M].London:London New Left Books,1975.
[12] 菲益浦·阿姆斯特朗,安德鲁·格林,约翰·哈里逊.战后资本主义大繁荣的形成和破产[M]. 史敏,张迪恳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13] 都留重人.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经济发展[M].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14] 马艳.马克思主义剩余价值理论的数理表达与创新[J].财经研究,2007,(7).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6] 沈开艳.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若干新思考[J].上海经济研究,2010,(12).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18] 陈漓高,齐俊妍,韦军亮.第五轮世界经济长波进入衰退期的趋势、原因和特点分析[J].世界经济研究,2009,(5).
[19] Gorden. Ian Economic Forecaster & Interpreter of the Kondratieff Cycles[EB/OL].http://www. the long wave analyst. ca / news html, 2007- 11- 05.
[20] 赵峰,马慎萧.金融资本、职能资本与资本主义的金融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美国的现实[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2).
[21] 刘霞辉.四种经济增长路径比较[N].经济日报,2015- 05- 14.
[22] Gorden.Fat and mean[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6.
[责任编辑 陈翔云]
Progress of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Surplus Value” and Its New Changes in Capitalism
Wang Feng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production surplus value; theoretical progress; realistic change; new characteristics
The theory of surplus value is one of the two major findings of Marx.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global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the way of production of surplus value has also changed greatly.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studied the theory of production surplus value in depth. There are real changes mainly in five aspects, namely the predatory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in financial capital, the exploitation of the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in capital spatial expansion, the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ype, the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of labor skills upgrading and the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of new product investment. These five major changes have formed three new features of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including the increase i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upgrading of the labor value.
* 本文系重庆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统筹城乡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项目号:2013PYDS04)和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国家资本主义的商品拜物教解说与调控机制研究”(项目号:SWU1509165)的阶段性成果。
王丰,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后(重庆 400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