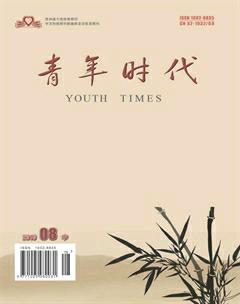论徐特立思想从“教育救国”到“红色教育”的转变
刘索素
摘
要:徐特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教育家,是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他的教育思想产生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深深地刻上时代的烙印。早期抱着教育救国的宗旨,虽然教育救国的目的没有达到,但他所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是很有价值的。后期受革命的打击和农民运动的影响,否定“教育救国”,走上了“红色教育”的道路。本文就徐特立“教育救国”和“红色教育”两个时期所进行地教育活动、思想动摇的过程以及二者的区别进行探讨。
关键词:徐特立;教育救国;红色教育
所谓教育家并不是特殊的个人,只是一定时代的社会代表。他的学说,只是时代思潮表现在教育的一个侧面。所以,教育学说不是一种抽象的一般的学说,而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学说。徐特立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1877-1927)与后期(1927-1968),这个划分恰好也是从“教育救国”论投身到“红色教育”论转变的界限。
一、“教育救国”论
“教育救国”论盛行于20世纪20~30年代,非常重视教育、提高民族文化和素质,并为此而奋斗拯救国家。但这种思想的弊端是没有认清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没有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企图通过发展教育来解决中国的落后。
徐特立家境贫困,8~14岁在蒙馆学习,15岁辍学,亲身感受到读书的困难,所以他十分关心当地农民群众的学习问题。他边教边学,把几亩遗产田逐年变卖用以买书,抓住一切闲余时间读书。通过阅读,徐特立的知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为以后的教育工作奠定基础。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徐特立所期待的民主共和国化为泡影。这时,他更矢志笃行“教育救国”,在这一阶段兴办的教育事业和参与教育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更为可观。1919年,有20年教龄的徐特立已43岁,在湖南政界、教育界名闻遐迩,在别人眼里是扶拐棍的“洋学生”,他赴法国参加勤工俭学,法国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26年11月,长沙掀起了声势颇大的学潮,长郡中学校长在省都督的倚仗下开除学生骨干分子,接着又勾结军警拘留学生,旧势力对民主进行了践踏,徐特立不畏强暴,公开为学生辩护,但以失败告终,此时在徐特立“教育救国”的信念上添加了一个大问号。
二、“教育救国”思想的动摇
1925年徐特立从欧洲留学归来,原本想把学得新知识活学活用到实践上,但命运却把他卷入农民战争的漩涡中。大革命时期,他在湖南省教育界已经获得了崇高威望,但仍不免受到旧势力的排挤,在长沙县教育会的选举中没有被选资格,他感受到政治背景下的教育不公平,此刻他对教育的影响力量就产生微微动摇。
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如火如荼,他回到五美乡,发现自己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亲眼看见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新的世界。使他觉得“自己真正渺小,无知的农民一旦解放了,成了全知全能”。于是,逢人便说农民协会的“伟大”。经过农民运动的洗礼,多年来的思想苦闷一扫而光,他曾信奉的“教育救国”论,而现在要对它否定了。
徐特立曾认为帝国主义非常强大,迫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要赶走外侵,只能指望后一辈。他为这个理想奋斗了二十多年,创办学校和帮助清贫学生。而他亲眼看见自己费尽心血培养出来的贫苦青年,有的一经有了能力就会回过头压迫穷人。同时也感到自己所能教的学生是有限的,靠有限的少数学生去挽救国家是微不足道的。于是,他彻底否定了“教育救国”,清理自己的办学思想。
三、“红色教育”论
1.“身教主义”的新篇章
1927年5月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徐老已经五十一岁,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了“新鲜”的血液,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光荣成为共产党一员是发展“红色教育”思想的前提。
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区从历史上就承受一个沉重负担,即文化教育落后,文盲众多,这不利于动员群众支援革命战争与苏维埃政权的建设。他提出了《识字运动的办法》,以及一套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
“老公教老婆,儿子教老子,秘书教主席,识字的教不识字的,识字多的教识字少的。”因为识字的方法简便,群众乐于接受,扫盲运动不仅迅速展开并取得显著成效。
1932年,徐特立为培训苏区急需的小学师资,创建了中央列宁师范学校,兼任校长。这所红色师范学校办学条件的建设难度是远甚于当年的,不仅当校长,还做教员,还管摇铃扫地等一些学校事务,在短时间内为革命根据地培养了六百多名教师,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区乡的列宁小学,成为发展教育的骨干力量。徐特立以革命的精神想办法克服摆在面前的困难,为党对人才的需要作出了重要贡献。
2.“红色教育”的严峻考验
关于革命根据地教育的性质与方针,即土地革命时期,根据地应实行反封建的工农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还是“共产主义教育”方针。以徐特立为首的教育人民委员部以启发工农群众的民主意识为宗旨,以反封建、迷信为教育的基本内容,是真正符合土地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特点。
关于革命根据地教育的重点问题,毛泽东主张以成人教育为重点,而中共临时负责人博古则主张以儿童教育为重点,徐特立支持毛泽东的观点。成人教育包括识字班或识字组、图书馆以及业余文艺体育活动。不限于单一的教学形式和场所,以能者为师、分散的随机学习的形式学习,统一规模化的学习时间是不能得到保障的。
关于中央革命根据地建设“正规化”与“游击性”教育的分歧。1931~1932年间,根据地教育在徐特立的主持下,采取灵活多样的非正规的办学形式,推动了根据地工农教育的发展。因为处于被“围剿”的特殊时期,教育亦应灵活机动,跟着战争跑,他提出了“上课军事化,下课儿童化”的口号。
3.“红色教育”的重新点燃
历经长征,中国革命的中心从南方转移到北方。陕甘宁边区不仅是全国人民战争的指导中心,还是国内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徐特立作为教育行政负责人,领导根据地干部和群众为陕甘宁边区人民教育事业奠定基础。他首先关注的是当地环境和原有教育工作基础,从调查出发,逐渐开展教育工作。其教育工作又以扫盲为重点,并通过推广拉丁语新文化扫除文盲,从培养师资人手推广新文字。
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日阶段,教育工作也面临着迫切转变,一面适应客观情势的迅速变化,更大规模地开展干部教育与群众教育:一面着手制定教育制度、规章和发展计划。徐特立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基本上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根据地需要与实际出发,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发展教育的道路。
四、启示
徐特立的“教育救国”论和“红色教育”论,人们常以改革和革命的范畴来对号入座,认为“教育救国”从不革命,甚至存在反革命的意义。我认为,改革与革命属于不同的层面,用后者作为衡量前者的标准是不科学的。今天,我们看待“非革命”的历史,要分清时代背景、发展趋势,不能断然就说教育救国是“反革命”的。其实,“教育救国”及“红色教育”构成历史合力,共同促进时代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