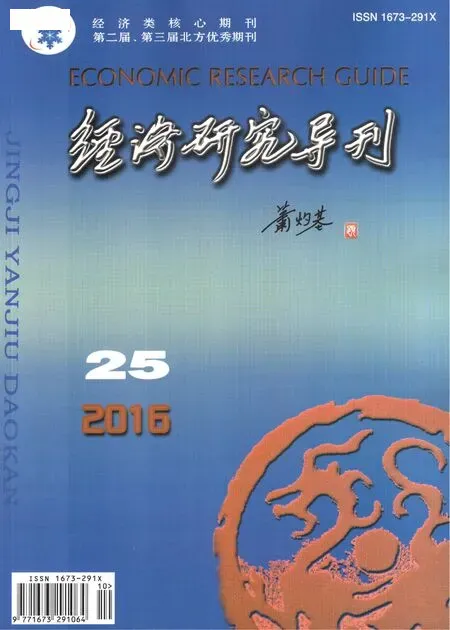深化改革才能根本解决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问题
崔志宏
(北京物资学院,北京 101149)
深化改革才能根本解决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问题
崔志宏
(北京物资学院,北京 101149)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需要再进行一次思想解放。中国房地产市场近二十年的高速发展,尤其近十年来的超常规发展模式暴露出来的问题、带来的隐患、积累的矛盾不能允许按照原有模式走下去,必须通过思想解放,深化包括政府财政体系、政府管控体系甚至是政治架构模式等各方面的改革,来解决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中遇到的以房地产市场为典型的发展问题。
房地产;市场;改革
中国进入21世纪,经济实力为重点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升。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得益于中国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经历了严重压抑的中国经济,通过改革开放焕发出蓬勃生机,综合人口红利、丰富的能源以及整体稳定的国内社会环境等等因素,中国获得了超常规的发展。但是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以及国际市场的变化,传统的外向型的经济模式难以为继。很难想象在世界市场生产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中国能够仅仅依赖世界市场保持自己的高速发展。
21世纪初,扩大内需的思想得到更多人的认同。要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人口是决定潜在消费的最主要因素。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的消费市场不应该得不到重视。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根据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教育、住房、医疗不可避免地成为扩大内需的突破口。本文仅论证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问题,房地产等成为刺破中国高储蓄率文化的尖刀。
一、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
“高”房价是目前房地产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表象。在一个成熟的拥有充分理性并且信息对等透明、交易双方平等自愿不受干扰的市场,其形成的价格无所谓高低。目前的高房价直接引发或埋下诸多极具威力的隐患。
目前的高房价已经突破了合理水平。以通行的租售比指标来衡量。房屋租售比是什么?一般而言,“房屋租售比”=“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月租金”/“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的房价”。一般而言,按照国际经验,在一个房产运行情况良好的区域,应该可以在200—300个月内完全回收投资。有学者研究,在2015年北京上海两地,需要至少500多个月才可以收回投资,而2016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房价又遭遇了疯狂的涨幅。以另一指标,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191元。北京市城区房价很难找到4万以下的,即使紧邻北京的燕郊等地的房价也已经突破2万每平方米。
二、“高”房价带来的经济社会问题
第一,高房价极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成本,降低人们的生活品质。高房价首先体现在高地租上。以北京为例,城区一居室租金五六千是很平常的,而一个北京在编事业单位的科员的税后月工资也仅仅5千元左右。造成北京市交通拥堵的原因之一就是超高的房价,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燕郊等地成为睡城,店铺租金占据了店铺经营成本中的很大比例。以通州为例,店铺租金每日每平米十元是很低的标准,通州万达广场要达到15~20元每日每平方米。
第二,高房价也造成了对社会伦理文化的冲击。代表例子就是高房价衍生出来的离婚潮。“假”离婚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规避政策限制,节约购房成本。高房价对于人们的价值观也构成冲击。以笔者为例,十多年的教育工作,个人收入不过几十万。本单位同事,入职恰逢单位分房,30余万购入,几年后,以近300万卖出,然后辞职。辛苦一生买不到一套房或辛苦工作数十年不如炒一套房子。这对于人们的价值观和事业观不能不说是巨大的冲击。
第三,高房价扭曲了经济结构,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据媒体数据显示,2015年以412家上市公司为准,两市(上海和深圳)共有46家公司的全年净利润不足1 500万元。2014年的年报数据也显示,494家上市公司净利润不足1 500万元,占全部2 818家上市公司的17.53%。农业是国之基本,实业是国之柱石。高房价引致的生产成本的上升很难在终端消费者那里获得足额补偿。价格上升,消费数量下降。成本上升幅度大于产品价格上升幅度必然压缩利润。当实业利润降低和炒房收益巨大两者冲突的时候,很多企业家选择关掉企业去炒房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第四,高房价,尤其是持续高涨的房价给了政府和银行乃至社会公众一种“房价”幻觉。“土地财政”成了地方政府的政绩鸦片。银行也以房贷为优质贷款,利润重要来源而推波助澜,社会公众面对持续高涨的房价失去理性。
三、高房价的成因
只有找到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高涨的原因才能够对症下药解决这个顽疾。
首先要明确的就是房地产具有的双重属性中的消费属性完全被投资属性所掩盖,否则无法解释超高的租售比,无法解释只要有可能人们就要购买超过其居住需求的住房。房地产彻底沦为投机标的是高房价的直接原因,以下是推高房价的其他因素。
第一,政府土地财政的强烈驱动力。中国大政府格局必然要求庞大的财政支持。姑且不论政府官员的寻租问题,单纯从政绩考核驱动来讲,花钱尤其是耗费巨资打造形象工程也是官员的优先选择。土地是政府掌控的最佳资源。目前的一个“隐雷”地方债务问题和土地财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财政资金无法满足地方官员迅速提升政绩的要求时,举债就是一个必然。而担保品往往就落在了政府能掌控的优质资源——土地上。为了维持这个格局,推高地价,高涨的房价是地方政府官员乐于见到的事情。通过比价效应,制造出来的“地王”会刺激房价进一步高涨。
第二,银行提供撬高房价的杠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16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增加2.3万亿元,同比多增1.2万亿元,6月末增速达32.2%,月度增量屡创新高。京沪两个城市今年上半年个人住房贷款总计增加了超过3 000亿元。如果没有银行的参与,房价如此高涨是不可想象的。即使有了股市等融资渠道,但是银行依然是房地产市场各方最值得信赖的杠杆提供者。杠杆的产生伴随了泡沫的风险,这个是常识。尤其是银行为了利益,次级贷问题引爆了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当前,无论是房地产开放商还是最终购房者都充分利用银行提供的资金来推动房价的上涨。而房价下跌,首先受伤的就是银行,极端例子就是断供。银行以金融市场崩溃要挟政府,所以持续上涨的房价是银行乐于见到也是极力促成的。银行风控受到各种外部干扰,银行敢于提供推高房价的杠杆,背后其实还是对于大政府的一种信任和诈欺。
第三,经济增长方式单一。中国经济结构需要调整是共识。但是,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打断了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进程。4万亿投资不仅没有优化经济结构,反而强化了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一旦遇到经济出现问题,推高房价拉动经济就成了一个熟悉的套路。上文也谈到,炒房收益高企打击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创新能力缺乏合适的土壤,企业家更多是把资金投向了房地产市场,加剧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
第四,供需双方博弈力量失衡。任何泡沫的产生都离不开失去理性的赌徒抑或是被贪欲蒙蔽了理智而幻想自己总会有好运气不会成为最后接盘者的买家。土地有其特殊属性,在特定区域,土地是固定的。中国人投资渠道少,股市波动太大,理财中各种陷阱更多,人们目前更多是尝到房产升值的甜头,又没有受到贬值的伤害,所以投资房产成为一个最优先选择。同时,开发商为代表的卖房通过各种手段制造恐慌氛围,消磨买方理性。
第五,政府管控手段和能力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政府的管控手段和能力不强是不能回避的问题,首先,缺乏预期从而政策制定缺乏提前量往往被市场牵着鼻子走。政策的滞后性极大削弱了管控效果。例如北京市政府东迁通州,只是到了通州房价已经爆炒之后才出现限购政策。其次,政策执行缺乏持续性。限购等政策在大中城市本应是需要持续执行的,但是往往地方政府受经济环境影响时而放松时而收紧,导致政策失灵。再次,调控手段单一。目前调控手段更多依然是依靠行政命令,例如地方政府要求不出地王等。经济行为最有效的管控,还是从经济角度改变经济成本收益。
四、对目前房地产市场的政策建议
第一,必须切断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依赖。地方政府的财政过度依赖房地产市场必然导致地方政府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房地产市场存在的问题。所以,需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有取有舍。中央政府应重新审视分税制带来的现实问题,而要从根子上切断土地财政,首先要深入反腐斗争,房地产领域是腐败高发区域,就是因为这个领域寻租空间巨大。所以,通过有力的反腐斗争可以抑制地方政府官员的个人谋利冲动。其次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对于大政府的取向要进行检讨,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只有简政才能精兵,只有精兵——压缩冗员才能够降低社会税负。
第二,坚定持续有效地贯彻调控政策。调控政策要有持续性,例如限购政策在大中城市必须要持续坚定的执行。否则断断续续的执行只会导致需求在短期限购空窗期爆发,反而会促使房价非理性上涨,限购的预期便不会达到。限购等政策是把房地产回归商品而非投机标的有效手段,所以利用现有技术通过大数据全国一盘棋,可以有效地打击房地产投机行为。
第三,切断银行的输血链条。可以讲,房价的暴涨背后的资金就来自于银行的信贷。所以严查银行信贷,提高银行的风控水平,同时保证银行的信贷业务不受地方政府的胁迫,并在适当时机通过上调首付比例来降低资金杠杆。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严禁以房抵押二次贷,这相当在杠杆上面继续加杠杆。
第四,要有勇气破产一批房地产企业。要有勇气让一部分地区的房价降下来,这么做的目的是破除人们对于政府给予房地产市场背书的预期。一旦人们对于政府是最终保险人的角色认识不变,那么疯狂炒作就不会休止。一旦人们对于政府需要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预期不变,那么人们炒房的热情就不会减退。
第五,要加大对于房地产租金税收的征收力度和幅度。通过降低租金收入预期,从经济角度抑制商业地产租金暴涨对于整个经济的伤害。
第六,最终依然是要地区均衡发展才能根本解决大中城市房价暴涨的困局。分散式经济布局比辐射线经济布局要更健康更安全,所以要多中心发展模式而不是辐射线发展模式。缺乏接盘的炒作很快就会停止,所以经济发展方式的顺利转型是解决房地产市场的最终法宝。
[责任编辑吴明宇]
F293.3
A
1673-291X(2016)25-0095-02
2016-08-16
崔志宏(1977-),男(满族),北京人,讲师,从事体制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