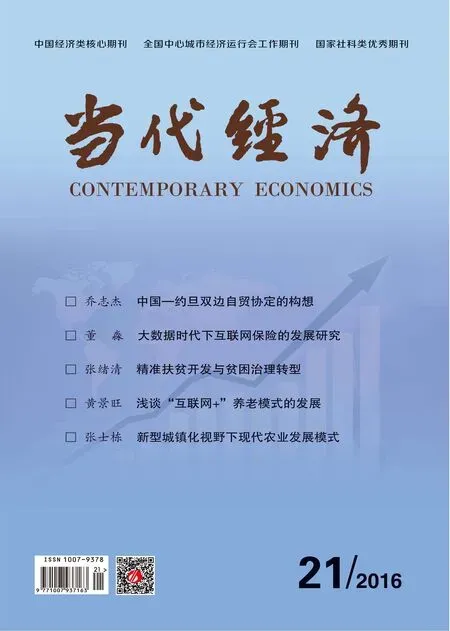农民利益表达研究综述
万红斌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3)
农民利益表达研究综述
万红斌
(武汉理工大学,湖北 武汉 430063)
本文对国内外农民利益表达这一研究领域进行简要的回顾后,把农民利益表达在研究路径上归结为注重表达策略与手段的资源/关系视角和倾向情绪表达的情感/意识视角;从农民利益表达如何上升到政府议程设置高度以及如何由个人表达转向集体表达这两方面来讨论农民利益表达效果。
利益表达;资源/关系;情感/意识;政府议程
我国目前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再加上农民本身作为弱势群体,表达利益的方式有限,导致我国目前因农民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发。为此,对农民利益表达问题进行文献研究很有必要。本文在回顾已有研究基础上,将从农民利益表达研究路径以及农民利益表达效果两方面对文献进行归纳分析。
一、农民利益表达研究路径
1、资源/关系视角
资源/关系视角在研究当代中国农民利益表达中具有重要地位,带有明显的经济学研究取向,深受斯科特思想的影响。斯科特重点描述了东南亚农民采用诸如嘲笑、偷懒等小动作对抗无法抗拒的不平等。资源/关系视角侧重分析农民在抗争中所运用的手段和策略。
裴宜理认为中国民众通过抗争表达利益的方式都是在遵守规则。李连江、欧博文两位学者通过研究提出“依法抗争说”。他们认为,农民是运用国家政策和法律维护自身经济政治权益不受地方政府侵害,是一种政治行为。为了超越李连江、欧博文的“依法抗争说”,于建嵘进一步提出“以法抗争”。 “以法抗争”是直接运用法律武器作为自己抗争的手段,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色彩。但是,应星以“合法性困境”为逻辑起点,通过四个案例总结出“草根动员”的弱组织性特征和非政治化取向,直接批判于建嵘的观点,即农民抗争具有强组织性与政治性。应星也提出了“以气抗争”,认为利益冲突是农民维权的原发性基础,“气”是行动再生的推动力量。吴毅认为“合法性困境”的逻辑起点本身并不牢靠,它忽视了转型中国政治特征的复杂性和过渡性,简单化了行政权力和人际关系网络在乡村社会的影响。基于此,吴毅认为,农民利益表达之难以健康和体制化成长的原因,更直接归因于乡村社会各种既存“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的阻隔。董海军在“以法抗争”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以势抗争”,认为弱者身份可以成为农民抗争的一种资源。折晓叶研究了中国农民在本土非农化压力、城市化暴力情况下所采取的利益表达策略,认为农民的表达手段是通过运用“韧武器”,即采取非对抗的方式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因为我国利益表达渠道的局限性以及农民本身资源的稀缺性,从“依法抗争”到“以势抗争”往往并不能取得理想效果。因此,一个更适合农民自身情况的新的解释框架——“以身抗争”逐渐建立起来。王洪伟通过对艾滋病人抗争行为的研究,发展出了“以身抗争”,认为身体作为一种资源本身就可利用来表达利益。黄振辉的表演式抗争,韩志明对“闹大”现象的研究以及徐昕提出的“以死抗争”都是“以身抗争”典型。田先红认为以往农民抗争的研究没有跳出农民弱者地位开展维权的范围,他通过个案调查发现,农民牟利型利益表达开始凸显。
农民除了通过“以身抗争”动用内在资源外,还可以动员自身的关系网络表达利益。吴毅认为,失地农民与基层政府官员本身就包含于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之中,在网络中的人各自掌握一定的资源并且与其它成员之间以互惠的方式履行各自的义务,身处网络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既躲不开又自觉运用这一资源。正是这一义务使得失地农民在表达利益时,可以动用各种资源和社会关系对其利益表达的客体——基层政府施压。冯仕政认为一个人的经济地位高,他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表达利益的方式越有效,反之则选择沉默。石发勇研究发现,不仅民众善于调动自身关系网络表达利益,地方政府也用关系网络来动员民众的支持,化解社会矛盾。
2、情感/意识视角
持情感/意识视角的研究认为,抗争者之所以采取行动,不是出于怨恨、愤怒、就是出于责任感或自觉的伦理意识。斯科特在《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中特别强调“生存伦理”对东南亚农民反抗的独特重要性。李培林指出:利益格局变动确引发社会冲突数量的增多,但“利益变动本身尚不足以导致冲突行为的发生,由利益变动导致的不公平感和对现状的不满才是冲突行为产生的直接根源”。(李培林,2005)刘能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的研究传统中,综合出了一个解释框架,认为怨恨是都市集体行动的关键变量。何艳玲通过对城市经济抗争的研究发现,公平感、心理因素也是导致环境冲突的原因之一。如果把农民抗争的情感因素归于怨恨、不公平感,那么理性意识决定抗争者采取何种行动。有学者认为,农民抗争行为是理性的。当农民合法的权益受到损害时,其在选择抗争的方式时会考虑“成本-收益”,表现为抗争过程中理性计算意识。在具体的抗争方式上,相较于正规而繁琐的法律抗争,农民往往采用法律之外的抗争方式,抗争的结果取决于利益的政治化博弈。即使是极端的“以死抗争”,仍然是基于理性考虑的,因为“局外人认为行动者的行为不够合理或非理性,并不反映行动者的本意,用行动者的眼光衡量,他们的行动是合理的。”(詹姆斯•S•科尔曼,1999)吴长青认为农民抗争行动本身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策略范式的解读范围,其忽视了抗争行动的道德逻辑与伦理因素。因此他将伦理带入到农民抗争的研究之中,认为: “伦理在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中国社会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更是中国农民抗争行动的重要维度。”(吴长青,2010)
二、农民利益表达效果
1、议程设置
农民利益表达要想取得效果,必须使得其表达的问题被政府关注,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而对问题界定便是进入政府议事日程,解决农民利益表达问题的第一步。弗兰克与布莱恩认为人的偏好是固定但多维的,只要对问题做出不同的界定就能影响人们对事件的偏好,从而决定事件能否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 “问题的定义形成既可以是自上而下的过程,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过程。”(詹姆斯•E•安德森,2009)王绍光根据议程提出者的身份以及群众参与的程度不同区分出来六种类型的议程设置模式,总体可认为中国是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模式。但是,农民是社会抗争的直接参与者,他们本身就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在定义社会问题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然而,与官僚、利益集团以及企业家等社会上层而言,农民由于受到知识水平、自身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他们反而缺乏界定问题的能力。面对利益侵害,通过正常的利益表达渠道不能有效地解决他们的利益诉求,他们往往通过向公众和社会诉苦,展示其困境,表达内心的不满与诉求。但是,一般的诉苦行为并不能引起政府的注意。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程是充满竞争的过程,政府本身没有足够的时间、资源以及意愿去考虑其中的大部分诉求,只有竞争中获胜的问题才能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因此,社会问题必须要通过焦点事件、指标、符号、反馈等来促使政府部门关注这些问题。格斯顿也认为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需要“促发机制”,也就是一个重要事件,给政府产生压力。就此而言,农民利益诉求要想进入政府议程,最快捷的方式便是激烈的个体或集体行动,在视觉上给公众以冲击,造成广泛的社会影响,从而增加政府解决问题的压力。
尽管农民通过激烈的个人或群体性事件能够自下而上的把利益诉求进入政府议事日程,但是解决问题的路径依然是自上而下的。金登认为,社会问题进入政府议程并且能够得到解决需要问题流、政策流以及政治流的结合,他称这样的结合点为“政策之窗”。当“政策之窗”被打开的时候,政策制定者以及参与者必须迅速采取行动,抓住时机以便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基于此,农民利益诉求的有效解决还必须等待政策的成熟,满足政治需求的考量。
2、个体到集体的转化
农民利益表达群体的规模会影响表达效果,集体的利益表达效果明显会强于单个人的利益表达。但是作为个体的农民抗争并不会自然转化成集体抗争。奥尔森认为,作为理性的个人,在采取行动前会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并且集体行动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在很多情境中,集体不行动才是自然结果。为了摆脱集体行动的困境,奥尔森提出了两种方式解决此困境,一是个体如不参与集体行动,便受强制;二是“选择性激励”。(奥尔森,1995)但是于建嵘认为奥尔森的“选择性激励”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农民维权抗争解释力不够,为此他提出了“压迫性反应”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农民之所以维权抗争,是因为“集团”外部“压迫”超过他们忍受的阀值,而不是基于“集团”内部的“赏罚分明”做的选择。邓大才认同阿罗不可能定理,认为个人偏好只有在严格条件下才能加总形成集体偏好,而农民以家庭为行动单位,只有面临生存威胁时,才会参加集体行动。
早在奥尔森之前,勒庞从心理学角度去解释个人为何参与集体行动。他认为,只有形成了共同感情与思想的团体才能成为集体,集体心理支配着集体行动。因此,集体心理的形成过程决定集体行动发生的内在机制,而集体心理来源于人类共有的本能和情感。(勒庞,2005)基于此,国内文献中也有通过感情心理方面去研究个人为何参与集体行动。郭景萍认为唤起参与者的情感认同是集体行动的必要条件。黄岭峻通过对农民工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研究后发现,只有通过共同意识的构建才能使个体不满传导为集体不满,从而参与集体行动。
[1] 李培林等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当代中国社会矛盾问题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 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层[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3] 吴长青.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J].社会,2010(2).
(责任编辑:梁蒙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