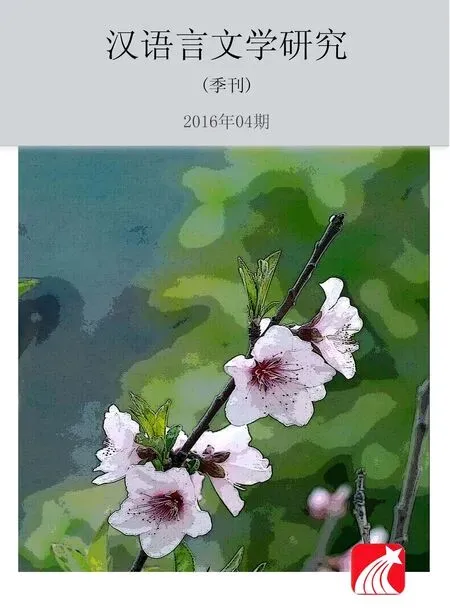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创作(1921-1996)中的《旧约》*
【斯】马立安·高利克/文 刘燕/译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与创作(1921-1996)中的《旧约》*
【斯】马立安·高利克/文 刘燕/译
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作家和批评家就致力于介绍《旧约》。周作人强调,作为西方文学重要源头的希伯来文学和希腊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尤显重要。朱维之的思考方式别出心裁,其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中国批评中独树一帜,有必要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旧约》对谢冰心、李健吾、茅盾、巴金、钱锺书等作家的创作都有影响。新时期以来,中国—《圣经》、中国—犹太文学研究已成为欧美汉学研究的一个崭新分支,该领域的研究在今后将会获得更为深入而广泛的拓展。
《旧约》;朱维之;中国现代文学;比较研究
近些年,各国学者有关《圣经》与中国现代文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兴趣越来越浓,他们主要聚焦于基督教而非犹太教的遗产。显然,这主要归因于基督教传教士以及后来的本土基督教牧师及其追随者、信仰者或文学批评家的推动。
由于资料的匮乏,台湾和香港的情况不在本文的探讨范围。1949年前,中国大陆对《圣经·旧约》的兴趣并不多见,但自1980年后,可以看出中国文学批评家和比较文学学者研究重点的转移,他们热衷于《旧约》研究,该领域的论文数量已超过对《新约》的研究。这主要归功于中国文学批评家对于“文革”前一直被忽视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就文学方面而言,《旧约》的价值显然要超过《新约》。
到本文写作为止,有两篇关于《圣经》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影响的论文在欧洲发表:第一篇是本人撰写的《中国大陆对〈圣经〉的接受(1980-1992):一个文学比较学者的观察》;①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Bratislava),4(1995),1,pp.24-46.第二篇是梁工撰写的《中国〈圣经〉文学研究 20年(1976-1996)》。②Irene Eber(伊爱莲)and others(eds.),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Sankt Augustin-Nettetal,1999).根据梁工的考察,中国发表了介绍与评论《圣经》文学的论文160篇、论著30多部,其涉及范围不只限于文学或思想特征方面。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成果数目的确令人可观。
有关《圣经》与中国文学的研究,有两本重要的论著:一本是美国汉学家L.S.罗宾逊的《双刃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另一本是南京大学马佳的《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③L.S.罗宾逊:《双刃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1986年版。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基督宗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此外还有杨剑龙:《旷野的呼声:中国现代作家与基督教文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前一本分析了《旧约》对20世纪中国小说的影响,后一本则较少论及这个主题。这两本专著都比较关注《圣经》对现当代中国小说的影响,却没有提及诗歌和戏剧,后两种体裁至今被学者忽视。
罗宾逊和马佳在其论著中皆以现代作家中德高望重的鲁迅(1881-1936)为开篇,我则想以鲁迅的弟弟、同样才华横溢的周作人(1885-1967)作为本文讨论的起点。
1920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圣书与中国文学》的讲座①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小说月报》12(1921),第1页。引自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1919-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6-385页。,面对听众,他声称对于宗教从来没有什么研究,只是对作为文学的圣书感兴趣。他认为,古希腊文学与希伯来文学达到了古代世界文学的最高峰。对于前者,他高度评价了它们在诗歌、史诗和戏剧方面的成就,并高度评价《旧约》。与当时周围的许多作家一样,周作人被托尔斯泰的文学批评《什么是艺术?》(What is Art?)所吸引。该书曾由耿济之(1899-1947)译为中文,于1921年出版,是有关该议题的开篇之作。②Leo Tolstoy,What is Art?Trans.from the original Russian ms.,with an Introduction by Aylmer Maude(London–New York–Melbourne 1899).(本文此处根据托尔斯泰的英文译本翻译为中文——译者)称道托尔斯泰文艺观的中国现代作家及相关文章,主要有:茅盾(1896-1981)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载《学生杂志》6(1919)4-6,第23-32、33-41、43-52页;郭沫若(1892-1978)的《艺术的评价》,载《创造日报》1923年11月25日,收入郭沫若《文艺论集》,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第四版,第253-259页;张闻天(1900-1979)的《托尔斯泰的艺术观》,载《小说月报》俄国文学特辑,1921年,第1-23页(部分是译文,部分是作者撰写)。参见M.Gálik,Mao Tun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 (Wiesbaden 1969),pp.31-32,and Bonnie S.McDougall,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ies into China,1919-1925(Tokyo 1971),pp.140-141.与周作人一样,一些人赞同托尔斯泰有关艺术的社会与道德的见解,部分地认同他对文学艺术的“宗教认知”(religious perception)。对此,托尔斯泰认为:
艺术让我们意识到无论是物质或精神,个人或集体,短暂或永恒,都依赖于全人类的兄弟情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彼此友爱和谐。③Leo Tolstoy,What is Art?,p.159.
虽然周作人并非像托尔斯泰一样的虔诚基督徒,但他依然认同托尔斯泰的观点:“只要作者所体验过的感情能感染观众或听众,这就是艺术。”④Leo Tolstoy,What is Art?,p.113.或者,按照托尔斯泰的话:
艺术开始于一个人想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使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⑤Leo Tolstoy,What is Art?,p.50.
由此,周作人不由自主地发现其观点与《毛诗序》的相似之处:“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⑥郑玄:《毛诗郑笺》卷1,见《四部备要》,台北:中华书局,第1A页。根据托尔斯泰的观点,周作人阐释道:“一切艺术都是表现各人或一团体的感情的东西。”⑦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第377页。除此之外,“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⑧同上。。
在阐释中西文学之间的关系时(主要指类型学上的类同而非渊源学或接触影响),周作人将《旧约》与儒家的“五经”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记》等纪事书类与《尚书》《春秋》,《利未记》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申命记》与《尚书》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之处。周作人主要参考了当时出版的美国神学博士谟尔(George F.Moore)的《旧约之文学》(The Literature of Old Testament,London,1919)一书。他认为《旧约》是希伯来的民族文学,应从文学的视角进行研究。《旧约》蕴藏着文学精华,如果读懂了它,会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快乐,身心愉悦,指导人生,受益匪浅。与谟尔一样,周作人将《创世记》等列为史传,“《预言书》”等列为抒情诗,《路德记》《以斯帖记》及《约拿书》列为故事。他此处提及“《预言书》”时,也许犯了一个小错误,实际上应是《诗篇》。周作人认为,《约伯记》是“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著作,世界文学的伟大的诗之一”①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第379页。,差不多是希腊爱斯吉洛斯 (公元前525-456年,现译为埃斯库罗斯——译者注)式的一篇悲剧。由于没有细说,我猜周作人可能指的是《被缚的普洛米修斯》。
当周作人讨论《圣经》与现代中国文学时,不如他分析《圣经》与西方文学的关系那么清晰。这是因为从1918年开始《圣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过才两三年,时间短暂,还不足以进行学术总结。周作人主要强调了希伯来文学的人道主义理想以及“神人合一”的观念②同上,第381页。:“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记》1:27)。③《圣经》英文均出自“詹姆斯王版本”。周作人以《约拿书》的结尾为例,说明了希伯来文学高大宽博的精神遗产。他引述了上帝对那个胆怯而优柔寡断的先知约拿说的话。当时,约拿在离他目的地不远的地方忍受着烈日曝晒,惦记着自己的性命,而不是执行上帝告诫的使命(《约拿书》4:9-11):
这蓖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
周作人引用了谟尔对《以西结书》18:23的转述:
神所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么。④周作人非常关注文学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关系。参见M.Gálik,The Genesi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1917—1930)(London–Bratislava 1980),pp.18-21.
周作人提醒在座的多数年轻听众和后来的读者有关神拥抱一切的“慈悲”(compassion)或“慈慧”(kindness)的观念。这也是以色列的“神”与佛教的“觉者”所共有的特征。⑤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第382页。此外,他还引用了重复该观念的一段引文(《以西结书》18:32):
主耶和华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
在写作并发表其讲稿时,周作人希望现代中国文学与《圣经》文学(以《旧约》为主)的相遇有助于中国新文学衍生出一种新的体裁“优美的牧歌”⑥同上,第383页。,虽然这一点至今未必成功,但在更新民族语言这一点上却已变为现实,《〈圣经〉官话合和译本》在1919年(“五四运动”)的翻译与出版,标志着新文学变革的开始。《圣经》的白话译本产生的深远影响出人意料。⑦同上,第385页。事实上,其影响力被证明是无与伦比的。
周作人还强调,中国新文学的发展需要世界各国文学和哲学思想的滋养。在他看来,作为西方文学重要源头的希伯来文学和希腊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尤显重要。
我认为,作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一个历史学家,周作人并不是出色的预言家。因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瞬息万变,无法预测,没有谁会成为一个预言者。周作人也不例外。就在发表有关《圣经》和希腊文学的这篇文章之前,他就指出:“中国的特别国情与西欧稍异,与俄国却多相同的地方。”⑧周作人:《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0年11月19日。参见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 1919-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12页。周作人试图说服其同胞追求西方社会重视个人、民主、自由等,但却毫无成效。胜利者反而是他的那些对手们:鲁迅、陈独秀、郭沫若和茅盾等。
早在周作人写作并发表其演讲之前,这种新趋势就已开始呈现。1920年2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沈定一(1892-1928)说:“在社会生活中,我们要拒绝一切宗教。”①沈玄庐(沈定一的名号,1883-1928):《对于“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怀疑》,载《星期评论》1920年2月8日第36期(此句引文根据英文译出——译者)。该文是对陈独秀(1879-1942)发表在《新青年》1920年2月1日第7期上的文章提出的批评,第15-22页。参见周纵策 (Chow Tse-tsung):《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Stanford 1967),pp.321-322.1922-1928年间中国发生了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给社会、政治以及文学生活等领域的宗教活动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②参见周纵策(Chow Tse-tsung):《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The May Fourth Movement.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Stanford 1967),pp.320-327;Yamamoto Tatsuro and Yamamoto Sumiko,“Religion and the Modernization in the Far East:A Symposium.Ⅱ.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1922-1927,”in: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Ⅻ (1953)2,pp.133-147;Yip Ka-che,Religion,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Bellingham 1980).
周作人之后的杰出继承者是朱维之 (1905-1999)。朱维之并非周作人的学生,而是他的同事朱自清(1898-1948)的学生。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分析了朱维之写于1980年后的著述,但他在1930年代就已开始撰写发表有关《圣经》的研究文章,如《〈旧约〉中的民歌》。③有关“朱维之”的条目,参见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编:《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二卷《现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页。朱维之在文学与宗教领域的其他论著,参见孟昭毅:《老当益壮的比较文学前辈——朱维之教授》,载《中国比较文学通讯》1989年第1期,第24-25页。朱维之最初任职于福建协和大学,后又转到沪江大学。他是燕京大学著名神学家刘廷芳(1891-1947)的朋友。刘廷芳是“基督教新思潮”——更准确地说是“中华基督教文社”(1925-1928)的领导人,其宗旨是“推动本土基督教文学的创作,鼓励中国人阅读这些作品”。④Wang Chen-main, “Missionary Attitude toward the Indigenous Movement in China,The Case of the Wenshe文社,1925-1928,”Republican China17(1992),2,p.113.但该运动并不成功。年轻的朱维之在1941年完成其著作《基督教与文学》⑤本书《基督教与文学》最早由青年协会书店在上海出版,后在香港多次重印。本文使用的是1992年上海书店再版本。时,刘廷芳亲自为此书作序,在序中把这部著作比作“远象”(vision),⑥刘廷芳《序》,见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页。或许他想起 《申命记》3:27中的一段话,上帝对摩西说:
你且上毕斯迦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或《申命记》34:1-4:
摩西从摩押平原登尼波山,上了那与耶利哥相对的毕斯迦山顶。耶和华把基列全地直到但……直到琐珥,都指给他看。耶和华对他说:“……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⑦也许刘廷芳想起了《旧约》中的另一些典故,如《箴言》29:18:“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摩西未能进入应许之地,刘廷芳也未能进入他期待的“远象”,直到几十年后其同时代人才蓦然发现,在《圣经》影响下催生了如此广阔深厚的文学全景——其中主要是外国文学,部分是本国文学。虽然对于学识渊博的西方读者而言,这并无太多新意,但中国作家对《旧约》与现代中国文学问题所做出的贡献,仍然引人注目。与许多前辈和后辈学者一样,朱维之把《旧约》视为基督教文学的早期部分。他认为:“在公元前一千多年中所结的果子就是 《旧约》这部灿烂的文学杰作集。”⑧朱维之:《导言》,见《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页。
与周作人一样,朱维之也被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所吸引。周作人主要参考了谟尔撰写的那本广博而简明扼要的论著《〈旧约〉之文学》。与此不同,朱维之参考了当时在上海、南京图书馆中可以查到的大量图书与文章。当他论述《圣经》,特别是《旧约》在文学方面的伟大贡献时,是把它与西方古典文学的三部代表作,即荷马的《伊利亚特》、但丁的《神曲》和《莎翁集》进行对比阐释。①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5页。这在中国不足为奇。在朱维之之前,张闻天向中国读者介绍歌德的《浮士德》时,就是这样论述的。②张闻天:《哥德的浮士德》,载《但底与哥德》,《东方文库》第一编,上海:进步书局,1924年版,第32-33页。这篇长文最初发表于《东方杂志》19卷1922年8月10日、9月10日和25日第15、17和18页。他们的看法稍有不同。在谈到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时,张闻天提到《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而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只提到《哈姆莱特》。参见M.Gálik, “Young Zhang Wentian and HisGoethe’s Faust,”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Bratislava),8(1999),1,pp.3-16.或许张闻天和朱维之两人都参考了丁司牧(Charles Allen Dinsmore)的批评论著《作为文学的英文圣经》(The English Bible as Literature,Boston&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931),这部书清楚地表达了此类见解。如果我的推测可行的话,他们二人的不同点是:张闻天想要以此突出《浮士德》的地位,而朱维之引用丁司牧的话,是为了彰显《圣经》的重要性。③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5-46页。在把《圣经》与《伊利亚特》进行比较时,他认为《伊利亚特》只讲述了发生在五十天中间的事,而《旧约》却囊括了近两千年的历史:
它那复杂的事态,广大范围的道德真理和极复杂的情感,比起《伊利亚特》来,真可说是汪洋大海之比江河呢。④同上,第45页。
从文学的角度看,这似乎有些夸张,但对于读到这个典故的中国读者来说,则会一目了然,印象深刻。此典故出自《庄子》第17章“秋水”,写河伯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望洋兴叹”。⑤《庄子引得》,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47年版,第42页。以及Burton Watson’s translation inThe Complete Works of Chuang Tze(New York–London 1968),pp.175-176.
但丁固然也能如《圣经》作者一样深入魔鬼的地狱,也能高升到天堂,在上帝面前认识人生的奥秘。他虽能深能高,但“只游入太虚幻境,而真正神圣的火焰,常为中世纪神学的狭隘所障蔽”⑥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5页。。所以《神曲》断不及《圣经》那样普遍地感动万人。在此,朱维之暗指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另一本名著,即曹雪芹的《红楼梦》。该小说中的“太虚幻境”是第5章中秦可卿以及金陵十二钗的梦幻居所,或是从第17章至97章中贾宝玉及其年轻丫鬟女孩所居住的大观园,直至他所爱恋的林黛玉死去。朱维之并未进一步说明,也未把《红楼梦》与《圣经》进行对比分析。⑦曹雪芹:《红楼梦》卷3,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1378页。英译本可以参见Yang Hsien-yi(杨宪益)and Gladys Yang(戴乃迭)translated,A Dream of Red Mansions,3 vols.Beijing:Waiwen Press,1978,vol.1,p.226 up to vol.3,p.256.
朱维之认同丁司牧的结论,即除了《圣经》之外,再也没有比这三部作品更伟大的了。他觉得要在中国文学方面也选出几部杰作来和 《圣经》比较,“可是太难了”。⑧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46页。在此结论之后,他提出以下几个选择:屈原(约公元前340-280年)的《离骚》,杜甫(712-770)的诗,以及14世纪施耐庵的《水浒传》。基于李贽(1527-1604)对《水浒传》冠以“忠义”二字代表勇敢、慷慨或豪爽等德性,朱维之指出了它与《伊利亚特》之间的相似,因为小说描写了一百单八条好汉替天行道、为弱小打抱不平、抵抗强暴的行为。屈原很像但丁,尽管但丁是一个由地狱走向炼狱、渐达天堂的基督徒,而屈原是一个在天上和人间都没能找到“美人”,失望之极,最终自沉于汨罗江的巫神崇拜者,这两位诗人在天才、风格、兴趣等方面却非常相似。这里指出了《圣经》中有关“远游”的幻象,包括现实与超自然的方面。杜甫被称为“诗圣”,是可以与莎士比亚相互媲美的诗人。不过在后面这个例子中,我们看不出它们与《圣经》的关联。⑨同上,第47页。
在当代比较文学学者看来,朱维之的这种思考方式别出心裁,因为他所在的那个时代比较研究中的类型学方法尚未发展起来。其观点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中国文学批评中简直是前所未闻,因此,这一点有必要得到学界的高度评价。
朱维之认为,在世界无论哪一个民族的伟大文学中,《圣经》都有极高的地位,纵然不说是唯一的、最伟大的书,也该说是包罗万象、综合众美的一部伟大文集。其最大的特殊点在于“博大精深”,①同上,第49页。因为《圣经》包含广泛的人生经验、真理和复杂多样的情绪,所以能够震动古今东西各民族的心弦,给人以崇高的美感,给人以无限的慰安,并且救赎了无数人民的灵魂,从地狱般的黑暗超度到光明的天国。它是世界上(包括中国)唯一销行最广的、译本种类最多的书。1939年,有22.4万册《圣经》被售出。②同上,第50页。
《圣经》之伟大,在于它是古往今来最深入广大群众的唯一作品。对人类的多数来说,它具有特别广泛的真理和复杂多样的情绪。③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51页。在此,朱维之再次从托尔斯泰那里获得证据。在他写作我们正在分析的这部论著时,托尔斯泰的书成为他忠实的助手:
《伊利亚特》、《奥德赛》、以撒、雅各和约瑟夫的故事、希伯来预言、《诗篇》、福音故事、释迦牟尼的故事,还有吠陀经的赞美诗;所有这些都传达了非常高尚的情感,对我们现在的人,不管是否受过教育,都是可以理解的,就象它们对很久以前那个时代的人(他们甚至比我们现在的体力劳动者所受的教育还要少)是可以理解一样。④Leo Tolstoy,What is Art?,pp.102-103.
在论述希伯来民族时,朱维之特别强调其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与屈辱,而这一点——我认为在1940年——对他而言,可与中国被日本侵占的形势相提并论。他指出,希伯来民族自古以来直觉地感知上帝的存在,在患难中满怀希望——尽管在不同时期它被埃及、亚述、巴比伦等强国所征服,夹在其中,经历了极其严重的磨难,陷入几近绝望的境地。⑤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52页。
面对迫在眉睫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及其独裁统治推行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企图,朱维之引用了《耶利米书》51:34-36,以此表明“自己的”中华民族绝不会被“万军之主”所抛弃,乌云之后将是无限的光明:
以色列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吞灭我,压碎我,/使我成为空虚的器皿!/他像恶龙,将我吞下,/将我珍馐,充他肚肠,/并且把我驱逐出去!
锡安——巴比伦以强暴待我,/损伤我的身体,/愿这罪归他身上!
耶路撒冷——/愿流我血的罪,/归到迦勒底的居民!
耶和华——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她的泉源干涸!
同时,朱维之还引用了《诗篇》126:4-5:
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方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流泪带种出去的,必要欢乐带禾捆回来。
在讨论到其它先知文学时,朱维之明确指出希伯来人经历的痛苦屈辱。例如,《以赛亚书》第40-66章描述了巴比伦之囚和重返故土后的情形。那时,虽然耶路撒冷的城墙尚未建造起来,但神殿已耸立。不过,他对灾难的想象不是引自《以赛亚书》,而是大量引用了《哈巴谷书》最后一章3:10-13。它被摩尔登教授(R.G.Moulton)⑥R.G.Moulton,The Literature Study of the Bible(Boston 1899).参见摩尔登著,贾立言编译:《圣经之文学研究》,上海:广学会,1936年版。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57、64页。誉为“先知狂欢歌”(prophetic rhapsody),一首描述希伯来人在迦勒底人(即新巴比伦人)铁蹄蹂躏下的狂欢歌:
山岭见你无不战惧;/大水泛滥过去;/深渊发声,/汹涌翻腾;/因你的箭射出发光,/你的枪闪出光耀,/日月都在本宫停住。/你发愤恨通行大地,/发怒气责打列国如同打粮。/你出来要拯救你的百姓,/拯救你的受膏者;/打破恶人家长的头/露出他的脚直到颈项……
在谈论这篇先知文学的结尾,朱维之高度评价这首《圣经》中的“破灭歌”(摩尔登)①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62-64页。,并大量引用《以西结书》27:3-11、27中的《推罗破灭歌》,这些段落描写了宏伟壮观的腓尼基城市推罗的衰落及其灭亡的悲惨结局:
你的资财、物件、水手、掌舵的、补缝的、经营交易的,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在你破坏的日子里必都沉在海中。
对于汉学家来说,朱维之的这本著作中有关《圣经》对中国影响的结论极具启发性。
“十几年前”许地山(1893-1941)重新翻译《雅歌》,载于《生命》杂志。②同上,第72页。更引人瞩目的是,中国现代翻译之父严复(1853-1921)曾将《马可福音》中的几个章节译为中文。③严复:《马可所传福音》(第一章至第四章),圣书公会印发,上海商务印书馆代印,1908年版。遗憾的是,他后来没有继续这项工作。与《旧约》中的其它部分相比,也许《雅歌》更吸引中国文人。除许地山外,抗日战争之前至少有另外两个作家将这首爱情诗中的珍品译为中文:吴曙天(1903-1946)的中译本出版于1930年,④唐弢:《“雅歌”中译》,《晦庵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47-448页。有关女作家吴曙天的生平及创作的简介,参见Raoul David Findeisen(冯铁),“Wu Shutian.‘Eine Schriftstellerin sechsten Ranges’?”in:minima sinica,1996/1,pp.74-82.陈梦家(1911-1966)的中译本出版于1932年。⑤陈梦家译:《歌中之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2年版。但朱维之却未提及这些以小册子形式出版的《雅歌》中译本,也许对他而言,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爱情主题显得微不足道,虽然它具有一定的价值。
我是通过唐弢(1913-1992)的一篇短文才得知上述第一个《雅歌》译本的。唐弢是一位著述颇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家,他欣赏吴曙天译本的原因非常简单,即该译文使用了散文体而非诗歌体。《雅歌》被划分为五章和五天。这在《雅歌》中译本中非常特别。也许唐弢喜欢该小书附录中薛冰的文章《“雅歌”之文学研究》,并引用了其中的一段,其中描写了一个名为书密拉(为什么不是书拉密呢?)的美丽少女、一个无名的牧羊人和所罗门王一起玩浪漫游戏。最后,所罗门假扮为牧人独自跟随她走进树林,而她却消失无踪。⑥唐弢:《“雅歌”中译》,《晦庵书话》,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448页。也许她接受了《雅歌》第8章最后一节的忠告:“我的良人哪,求你快来。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该书的附录收录了周作人的《圣书与中国文学》和他翻译的海夫洛克·埃利斯(Havelock Ellis,1859-1938)研究《雅歌》与《传道书》的文章,以及冯三味的《论“雅歌”》。⑦同上,第447页。其中还包括周作人的另一篇短文《〈旧约〉与恋爱诗》,该文可能紧随前面提及的那篇文章而写,或与之同时写作(标注为1921年1月)。虽然朱维之没有提到此文,但它对于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如何接受《圣经》的影响颇有借鉴作用。在文中,周作人主要依据谟尔的观点,⑧周作人:《谈龙集》,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版,第247-249页。反对一篇题名为《基督教与妇人》的文章中对《雅歌》的攻击,极力维护《雅歌》的道德与美学价值。《基督教与妇人》一文发表于《新佛教》的基督教批评专号上。⑨同上,第248页。根据该文提及的资料来看,《基督教与妇人》谴责《雅歌》“把妇人的人格看得太轻漂了”,又引了《雅歌》第8章第6节作为证据,说这“是极不好的状妇人之词”。在为此节“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作辩护的时候,周作人认为“它只是形容爱与妒的猛烈,我们不承认男女关系是不洁的事,所以也不承认爱与妒为不好”。①周作人:《谈龙集》,上海:开明书店,1927年版,第248页。
需要提及的是,由于当时人们,尤其是外国传教士往往对待本土宗教及其活动持有不宽容的态度,佛教徒对基督教的过激批评亦有情可谅。②Holmes Welch,The Buddhist Revival in China(Cambridge,Mass.1968),pp.183-186.
陈梦家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是浙江一位新教牧师的儿子。但直到21岁左右,他才系统深入地阅读了《圣经》:
近来常为不清净而使心如野马,我惟一的活疗,就是多看《圣经》,《圣经》在我寂寞中或失意中总是最有益的朋友。这一部精深渊博的《圣经》,不但启示我们灵魂的超迈,或是感情的热烈与真实,它还留给我们许多篇最可欣赏的文学作品。其中的诗,传说上认为所罗门王所写的 《歌中之歌》,是一首最可撼人的抒情诗。③陈梦家:《歌中之歌》“译序”,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2年版,第1页。
在讨论《圣经》的深刻内涵与广博内容时,我们不难发现陈梦家与朱维之的观点类似,而当谈到情感的影响力时,其见解与托尔斯泰颇为一致。但陈梦家最感兴趣的并非托尔斯泰的书,而是摩尔顿的《〈圣经〉的现代读者》(The Modern Reader’s Bible,New York 1906),这是一部有关《圣经》的阐释与改写本。④同上,第6页。摩尔登把《雅歌》分为七个牧歌,而陈梦家的《歌中之歌》则将全诗分为十七阕。陈梦家认为,这首希伯来杰作表达的是“上帝是他们灵魂上的爱,他们肉体的上帝是女人 ”。与佛教徒的禁欲相反,陈梦家认为,“希伯来民族的‘爱’,是有膂力的,强蛮的,而且是信仰。他们诚实与简单的叙述,却胜过一切繁文富丽的修饰,他们的爱是白色的火。”⑤同上,第2页。如:
你的头如像迦密山,/你的秀发仿佛紫云,/你的发髻是王的囚栏。/你是如何美好,如何可爱,/阿,爱,为了喜快!/你的身体好比一株棕树,/你的两乳葡萄一样挂住。/我说,我要上这棕树,/我要攀住枝桠。(陈梦家《歌中之歌》)
陈梦家在1932年3月底完成了《歌中之歌》的翻译,即日军攻占上海后的两个月,此后几天,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被宣布为伪满洲国的皇帝。不过,与朱维之的论著不同,我们在这个中译本中一点也感觉不到当时阴郁窒息的氛围,反而是青岛的李树正含苞待放。⑥同上,第11页。《雅歌》描写的季节恰是春天。⑦穆木天:《〈梦家诗集〉与〈铁马集〉》,《现代》4(1934)6,第1064-1070页。
朱维之也提到《雅歌》,甚至将它与据传屈原所写的《九歌》进行了比较,这在中国学者中独树一帜,因为其他学者一般都是把《雅歌》与《诗经》进行比较。⑧裴薄言:《〈诗经〉比较研究》,载《中外文学》11(1982)8、9,第4-55页;Zhang Longxi(张隆溪),“The Letter or the Spirit:The Song of Songs,Allegoresis,and The Book of Poetry,”in:Comparative Literature39(1987),3,pp.193-217;Christoph Harbsmeier, “Eroticism in Early Chinese Poetry.Sundry Comparative Notes,”in:Helwig Schmidt-Glintzer (ed.),Das andere China.Festschrift fǖr Wolfgang Bauer zum 65.Geburtstag(Wiesbaden 1995),pp.323-380;M.Gálik,“The Song of Songs(Sir Hassirim)and the Book of Songs(Shijing).An Attempt at Comparative Analysis,”in: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Bratislava),6(1997)1,pp.45-75.虽然在《基督教与文学》中,朱维之只是泛泛地比较了《雅歌》与《九歌》,不过在他后来的著作《文艺宗教论集》⑨朱维之:《文艺宗教论集》,上海:青年协会书局,1951年版。中,对此则有细致入微的论述。朱维之将两部作品中描述的爱理解为人对神或上帝的爱,以及人与人之间互相吸引和彼此依恋的亲密关系。
后来,《诗篇》成为朱维之的文学批评聚焦的一个对象。《文艺宗教论集》收入了他一篇研究分析《诗篇》的文章。1941年,朱维之高度评价天主教法官、外交官吴经熊 (John C.H.Wu 1899-1986)首次用文言文翻译《圣咏篇》(即《诗篇》)的工作。吴经熊最初使用五言体翻译《诗篇》,后来被新教徒的蒋介石“修正”为四言体,好似《诗经》中的诗。①参见 Francis K.H.So(苏其康),“Wu Ching-hsiung(吴经熊)’s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Images of the Most High in the Psalms,”in:Irene Eber and others(eds.),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Sankt Augustin-Nettetal 1999),pp.321-349.朱维之在其论著中全文引用了《诗篇》第19首。中国文人一致称道吴经熊的中译本端庄典雅,这些古体诗句唤起了天国的美妙胜景:“乾坤揭主荣;碧穹布化工。”在《诗篇》作者的语言述说中,耶和华的词章真实,全然公义,“价值迈金石,滋味胜蜜饴”。
时代的危机氛围迫使朱维之更多关注 《圣经》中与此相关的主题,如《耶利米哀歌》,据传它是耶利米所作,但他并非真正的作者。显然,在公元前586年巴比伦入侵占领耶路撒冷与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在巴比伦人对犹大人的暴行与日军对中国人的暴行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的相似性。
早在1934年,朱维之已开始用“骚体”试译《哀歌》,这是屈原及其继承者所使用的楚国哀歌体。②朱维之:《基督教与文学》,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76页。在他之前,“全国基督徒文学协会”成员之一李荣芳已采纳“骚体”将五首全部译出。李荣芳的想法与吴经熊大致相似,只是稍有一点不同:吴经熊是以一种忧愁、焦虑、疑惑、相信、爱、赞美、祷告和沉思的态度解决家仇国恨,而李荣芳则通过这首世界文学中的著名哀歌抒发了中华民族正在经受的苦难与屈辱。朱维之完整地引用了李荣芳以骚体翻译的《耶利米哀歌》第4章,它描述了一个亲历者目睹耶路撒冷的陷落。其1、5、6节中译文如下:
1.何黄金之暗澹兮,何精金之葚葚,
彼圣阙之叠磐兮,委空衢而愁惨。
……
5.享珍馐之王孙兮,伏路衡而消亡,
曾衣锦而食绯兮,兹偃卧于粪壤。
6.所多玛之疾亡兮,非人力之所为。今我民之罪愆兮,视所邑而尤亏。
无论是内在情绪还是外在描摹上,《耶利米哀歌》的中译文与《九辩》都有类似之处。据传宋玉是《九辩》的作者,他曾出入楚襄王(公元前298-265在位)的宫廷,其哀诗被誉为悲怆郁结,词章华丽,铿锵有力:③《楚辞》(Ch’u Tz’u.The Songs of South).Trans.by David Hawkes(Oxford 1959),p.96.
窃美申包胥之气晟兮,恐时世之不固。
何时俗之工巧兮?灭规矩而改凿!
独耿介而不随兮,愿慕先圣之遗教。
处浊世而显荣兮,非余心之所乐。
与其无义而有名兮,宁穷处而守高。④引文出自Hawkes的翻译,稍有改动。王逸注,沈雁冰(茅盾)编辑:《楚辞》,上海:会文堂书局,1928年版,第80页。
申包胥是另一个著名历史人物伍子胥的有力对手,但司马迁(公元前145-约86年)认为他俩其实也是好友。⑤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于秦。伍子胥率越国军队攻入楚国都城,将杀害了他父亲和兄长的楚平王鞭尸。一方面,他被视为孝道的典范,另一方面,其行为却有悖礼节与规矩。申包胥批评伍子胥说:
子之报仇,其以甚乎!…… 今子故平王之臣,亲北面而事之,今至于戮死人,此岂其无天道之极乎?⑥司马迁:《史记》卷66,见《四部备要》,台北:中华书局,第4B页。英译本参见:Yang Hsienyi and Gladys Yang transl.Records of the Historian(Beijing:Waiwen Press,1979),p.41.
乍看之下,在尼布甲尼撒王与伍子胥、《耶利米哀歌》第4章的佚名作者与宋玉要表达的同情心之间,表面上并无太多相似之处,但对其中的残暴与非人道的谴责却是一致的。楚平王(卒于公元前506年之前)生活于尼布甲尼撒之后不到一个世纪期间。使用“骚体”来翻译《耶利米哀歌》真是恰到好处,这有助于中国读者以“中国化”的调适方式接受理解它,使其成为本土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旧约》对现代文学创作的影响稍逊于文学批评。《诗篇》第19首和第23首对于著名女诗人、作家谢冰心(1900-1999)早期皈依基督教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她的许多诗作使人想起繁星密布的苍穹。①参见M.Gálik, “Studies i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Ⅵ.Young Bing Xin (1919-1923),”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Bratislava).2(1993),1,pp.41-60.20世纪20年代的另一位作家向培良(1901-1965)曾被鲁迅刮目相看。向培良借用了大卫王之子暗嫩与妹妹他玛的冲突情节,创作了中国版独幕剧《暗嫩》。②鲁迅:《〈小说二集〉导言》,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5年第二版,第139-140页。and M.Gálik’s, “Temptation of the Princess:Xiang Peiliang’s Version of Amnon’s and Tamar’s Last Rendezvous”,in:M.Gálik,Influence,Translation and Parallels.Selected Studies on the Biblein China(Sankt Augustin: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2004),pp.287-250.
20世纪40年代初的另外两篇现代中国短篇小说名扬一时,这两篇小说都写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内局势和前前后后的一些预言。第一篇小说《使命》发表于1940年,其作者李健吾(1906-1982)是一位作家、剧作家和学者。③参见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编:《中国文学家辞典》第二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6-399页。作为一个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的杰出研究专家④同上,第398页。,他曾翻译了长篇小说《圣安东的诱惑》和两篇短篇小说《慈悲·圣·朱莲的传说》(La Légende de Saint Julien d’Hospitalier)、《希罗底》(Herodias)。从这些译著来看,他肯定花费了一些时间研读 《圣经》。⑤“外国文学”条目参见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5页。
李健吾的《使命》开头描述了1937年7月1日日本侵华之时,有六个人(五个失业的教员和一个学生)应聘为宣传员,传播抵抗侵略者的“福音”。在一本杂志中,他们读到希伯来预言书中的一段,大概是对《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中的片段摘引或半模仿。罗宾逊曾将其译为英语:
有你们苦受的,百姓!犹太的叛逆,以法莲的酒鬼,住在肥沃的山谷,酒喝的蹒跚的人们!……摩押,你要和麻雀一样逃入柏林,和跳鼠一样逃入山穴。堡子大门比胡桃壳碎的还要快,墙要倒而城要烧;上天的惩罚仍不会中止。他要在你们自己的血里翻转你们的四肢,好象毛在染坊的缸里。他要像把新锄撕烂你们;他要把你们的肉一块一块散在山上!⑥L.S.罗宾逊:《双刃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1986年版,第147页。
这些预言性的句子主要来源于 (稍有改动)《以赛亚书》28:1和28:7:
祸哉以法莲的酒徒,住在肥美谷的山上,他们心里高傲,以所夸的为冠冕,有如将残之花。但就是这地的人(Judah)的儿子们,也因酒摇摇晃晃,因浓酒东倒西歪,祭司和先知因浓酒摇摇晃晃,被酒所困,因酒东倒西歪,他们错解默示,谬行审判。
接着是《以赛亚书》16:2、4:
摩押的居民在亚嫩渡口,必像游飞的鸟,如拆窝的雏;求你容我这被赶散的人和你同居。至于摩押,求你作他的隐密处,脱离灭命者的面。勒索人的归于无有,毁灭的事止息了,欺压人的从国中除灭了。
随后是《以赛亚书》17:9:
在那日他们的坚固城,必像树林中和山顶上所抛弃的地方,就是从前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人抛弃的。这样,地就荒凉了。
最后是《耶利米书》6:25:
你们不要往田野去,也不要行在路上。因四周有仇敌的刀剑和惊吓。
面对那些中国基督徒,他们想要说服他们去抵抗日本侵略者,不过误用了这些预言。因此,六位宣传者饱经挫折,收获甚微。在经历了十天失败的宣讲后,他们来到了一个教会,这里住着一位年长的外国天主教神父。在做晚祷时,这位神父与他们一起阅读了 《耶利米书》4:19-22:
我的肺腑呵,我的肺腑,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因为我已经听见角声,和打仗的喊声。毁坏的信息连络不绝。因为全地荒废。我的帐棚,忽然毁坏,我的幔子,顷刻破裂。我看见大旗,听见角声,要到几时呢。我的百姓愚顽,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智识行善。①同上,第149页。
此话被这六位新的预言者视为外国人对他们的亵渎,对同胞的侮辱。中国人不需要上帝来帮助他们。其中一位忍无可忍,在教堂中大声喊道:
不对!不对!不要信他!他在用一本古书哄骗你们!救我们的不是什么耶和华——是我们自己!自己!你们自己!②同上,第100页。
故事以这位天主教传教士的话结束,他不相信中国的宣传家会成功。他确信中国农民不会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并引用孔子的话来支持自己的论断: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③李健吾:《使命》,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0年版,第20页;《论语》英译本参见:Arthur Waley transl.,The Analects of Confucious(London 1964),p.119.
看来,这位西方传教士比中国知识分子更了解中国的农民。
第二本小说是茅盾在1942年发表的 《参孙的复仇》。④See M.Gálik, “Mythopoeic Warrior and Femme Fatale:Mao Dun’s Version of Samson and Delilah,”in:Irene Eber and others(eds.),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Sankt Augustin-Nettetal,1999),pp.301-320.它叙述的是神话时代的一位武士遇到了邻邦敌对国的女子,结局是主人公和腓利士人同归于尽的悲剧(小说并未描述有关大利拉的境况)。与《使命》的作者不同,虽然茅盾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但他非常熟稔《圣经》故事的遗产,包括上帝以杀死三千敌人的方式介入历史。同样,与李健吾小说中的虚构故事不同,茅盾的小说模拟了《士师记》第14-16章,只是在叙述方法、心理与环境描写等方面稍作改动。⑤See M.Gálik, “Mythopoeic Warrior andFemme Fatale:Mao Dun’s Version of Samson and Delilah,”in:Irene Eber and others(eds.),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Sankt Augustin-Nettetal,1999),pp.314-317.
抗日战争期间还有另一本小说值得一提,即巴金(1904-2005)的《火》三部曲之三《田惠世》⑥L.S.罗宾逊:《双刃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1986年版,第159-171页。。田惠世是该小说主人公的名字,与其他多数无神论革命者不同,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年老体衰,疾病缠身,在小说结束前不久死去,其理想是成为一个基督教菩萨:“不要进入上帝一个人的王国,而是去拯救自己的同胞于苦海。”⑦Olga Lang,Pa Chin and His Writings.Chinese Youth 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 (Cambridge,Mass.1967),p.209.茅盾认为上帝主要是普通人的上帝,他一直高度评价《圣经》中对于普通人的爱并为之谋幸福的段落。
这部小说的最早版是以摩西在何烈山上目睹燃烧的灌木丛的景象结束。田惠世的女儿为父亲扫墓。夕阳西下,她看到树后夕阳放射出鲜艳的光芒,树林似乎在燃烧。她取出《圣经·出埃及记》3:1-5,读道:
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忒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①L.S.罗宾逊:《双刃剑:基督教与二十世纪中国小说》,香港:道风山基督教中心,1986年版,第169页。
引文戛然而止。田惠世的女儿合上《圣经》,注视着似乎在燃烧的树林。巴金或许不想深究燃烧的灌木丛所具有的神话意义。上帝在《出埃及记》3:7-8中赋予了摩西以使命,在这部小说中并未引用: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
对于巴金来说,这个“远景”(vision)对于本民族和同时代人而言,似乎遥不可及。他以如此“虚幻的结局”来结束其三部曲,这可能是最真诚而有效的解决途径。
不难看出,在抗日战争之后与1949年解放之前,有关《旧约》题材的作品并不多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十余年间,“基督教成为禁忌”。②同上,第198页。可惜对于中华民国此类题材创作情况的研究,我至今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此,有必要提及钱锺书(1910-1998)文集《人·兽·鬼》③钱锺书:《人·兽·鬼》,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1947再版,第1-20页。中的一个短篇小说《上帝的梦》。从哲学和文学的角度看,它比上文提到的几部小说更有价值,我个人视之为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老实人》(又译《堪第德》)的文学传承,它是对这个充满忧愁与泪水的世界抱有某种毫无缘由的乐观主义的讽刺性描述。这个小说充满着“许多滑稽的插曲、对欧洲与中国文学文化的评论和影射,以及对当前欧洲文化中的某些观念与象征的一系列嘲讽评论”④Zbigniew Slupski’s review in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1900-1949.vol.2:The Short Story(Leiden 1988),p.145.。伏尔泰的嘲讽直接针对单纯而诚实的堪第德及其导师潘格罗斯,而钱锺书则以同样的方式面对上帝,以他自己的宇宙进化论与本体论为献祭。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认为,这个潘格罗斯形象是伏尔泰对莱布尼兹(Leibnitz,1646-1716)的一个漫画式讽刺。后者曾宣称我们的这个世界是“所有可能存在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对此,布拉德利(F.H.Bradley)嘲讽地评述“其中每件事皆具有某种必要的恶”。⑤Bertrand Russell,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London 1946),p.604.
钱锺书的小说主题来源于 《创世记》1-2章,主要情节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一种理论,即认为《创世记》所描述的人类还未存在的年代,上帝自己经历了进化的全部过程。但是“神看着是好的”这句话导致了一种错觉,上帝总是在一种新物种创造完成之后不断重复,甚至在创造人后,依然声称“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即便是在宇宙与大地消失后,这种错觉也未曾消失,这种乐观的错觉在上帝的梦中一再出现。但是在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之后,他感觉到的只有愤怒、厌倦和幻灭。全能的上帝不仅面对自己的创造物无能为力,对自己的梦也如此。钱锺书的这个短篇小说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在1951年的社会主义时期,朱维之顺利地出版了《文艺宗教论集》一书,直到1980年中国人重新开始《圣经》研究时,该书几乎成了一个绝唱。1980年后朱维之得以“复出”,成为将圣经文学重新引介到中国学界的重要学者之一。⑥关于朱维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前半期的情况,参见梁工:《近二十年中国〈圣经〉文学研究》,载 Irene Eber and others(eds.),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pp.383-407.
在我的一项研究中,我已分析了1980—1990年代初期中国关于 《旧约》批评研究与出版的情况。⑦M.Gálik, “The Reception of the Bible in Mainland China (1980-1992):Observation of a Literary Comparatist”,in: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Bratislava),4(1995)1,pp.24-46.因此在本文中,我主要聚焦于1992年7月后所发表的论著。在中国-希伯来、中国-犹太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中,1992年标志着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九江师专的“犹太文学研究中心”于1997年7月10-19日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中国首次犹太文学国际学术研论会”,来自15所大学的30位学者讨论了有关犹太文学、犹太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美国犹太文学等议题。两位重要的《旧约》研究者梁工和刘连祥阐述了他们对《旧约》的看法及其与犹太文学或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①吴晗:《1992年犹太文学庐山研讨会纪要》,《外国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第140页。遗憾的是,我至今未能读到刘连祥的文章。梁工的《古犹太文学如是说》②梁工:《古犹太文学如是说》,《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1期,第33-38页。简要地介绍了《圣经》文学发展的历史以及《次经》《伪经》和《死海古卷》,概要地描述了它们与近东、埃及和希腊文学的关系,及其对后来欧美文学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梁工挖掘了《圣经》文学研究中闻一多(1899-1946)的文章《文学的历史动向》。③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85-90页。在这篇一直被忽视的颇具启发性的论文中,闻一多指出包括中国、印度、希伯来和希腊在内的四种伟大文学几乎同时进入文学世界,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力。在大约公元前一千年时,一系列文学经典同时问世,如《周颂》、《诗经》中的“大雅”、吠陀经、《诗篇》中最古老的部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闻一多强调,中国人应该“受”(接受)外国文学,这有助于促进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而此前的主要趋势是前现代中国“予”(给予)影响邻邦(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如果说希腊与印度文学在中国获得了充分的研究,那么,相比之下,希伯来(在某些年代完全)被忽视了,故应得到更多的关注。
自庐山研讨会以来,在《圣经》研究领域(尤其是批评方面)所做出的努力的确卓有成效。无论如何,如今这方面的研究更具组织性。1994年10月10-12日在北京召开了另一次大型会议“犹太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美国和加拿大的一百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一起讨论了《圣经》研究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圣经》与文学。④梁工:《近二十年中国〈圣经〉文学研究》,Irene Eber and others(eds.),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pp.383-407.伊爱莲于1996年6月22-28日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斯考普思山主办了国际会议“《圣经》在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影响”,体现了中—希研究的新气象,大家一致希望这类会议以后可以继续下去。⑤2002年1月5-8日台北辅仁大学举办了第二届“《圣经》在现代中国”国际会议。
在庐山研讨会和北京研讨会之后,可以看出,中国研究者对先知文学和《约伯记》愈来愈抱有兴趣,至少发表了三篇这方面的论文。梁工在《古犹太先知文学散论》⑥梁工:《古犹太先知文学散论》,《南开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第26-30页。和阎根兴在《热情与幻想的结晶:希伯来先知文学简论》⑦阎根兴:《热情与幻想的结晶:希伯来先知文学简论》,《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第109-112页。中强调了后代先知的道德教诲对道德规范的需要及其在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尽管它们仍不时地流露出早期研究中外来威胁与本土抵抗的倾向,但已经不再那么明显了。在此期间,或多或少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阐释《圣经》的趋势并未得到突破。
在这些会议之后,又有一些关于《圣经》与神话方面的论文发表。刘连祥的《试论〈圣经〉的神话结构》⑧刘连祥:《试论〈圣经〉的神话结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第77-81页。一文涉及先知文学方面的神话议题。刘连祥最初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后来到特拉维夫大学继续从事研究工作。他试图为《圣经·旧约》之首六卷及其之后的书卷构架一个“U”型的神话发展结构。在这个“U”型模式中,起始代表较高的发展阶段,中间则是衰落阶段,甚至跌至最低点。后先知书代表了《旧约》的最后阶段,此部分的结构恰好与起始的六卷书相同。在达到“流奶与蜜之地”(《出埃及记》3:8)之后,《圣经》的这种结构模式始终没变。在《玛拉基书》4-6章的最后一节中,我们读到:
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
由此可见前、后先知书之间的密切关联和类似“远象”,这个神话循环结构首先是上帝的荣耀与显现,随后是衰落,最终是上帝的大日子。它从《创世记》2-3章至《出埃及记》的结尾,从《出埃及记》到《玛拉基书》,到《希伯来圣经》最后的内容反复出现,体现出一致性。
另有两篇论文涉及了希腊神话与希伯来神话之间的类型学比较。这两篇文章是马小朝写的《古希腊神话与〈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异同论》①马小朝:《古希腊神话与〈圣经〉对西方文学影响异同论》,《文艺研究》1994年第6期,第93-100页。和《希腊神话、〈圣经〉的表象世界及其对西方文学的模式意义》②马小朝:《希腊神话、〈圣经〉的表象世界及其对西方文学的模式意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第71-76页。。特别是第二篇论文深入对比了不同神话中的人、神性人物的不同模式,尤其是(两个传统中的英雄人物)在审美、伦理道德、叙事方式和丰功伟业等领域的经验与超验个性。马小朝认为,《圣经》中的《旧约》已经成为基督教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必要进行专门独立的研究。但我未能搜集到比较《约伯记》与《天问》(据传屈原所作)的大部分研究资料,这或许将成为一个学术讨论的话题。
本文是一篇关于《旧约》在现代中国(1921-1996)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中的接受与复兴的简略综述。其中第一篇重要的批评论文始于周作人发表在《小说月刊》上的《圣书与中国文学》,此刊是192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刊物。本文结尾处提到梁工发表于《南开大学学报》的关于先知文学的论文,此刊是中国-犹太文学研究开拓者朱维之教授后半生生活和工作的南开大学的学报。本文论述了大约四十位中国作家学者,他们见证了《圣经》文学的伟大,尤其是《旧约》对现代中国文学的批评实践与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遗憾的是,我本应提到更多的学者或作品,但由于其中一些已在其他文章中做过介绍,此不赘述。另外一些则是本作者限于中国大陆或港台方面的资料而无暇顾及的方面。
概言之,中国-《圣经》、中国-犹太文学研究已成为欧美汉学研究的一个崭新分支,我们期待该领域的研究在今后将会获得更为深入而广泛的拓展。
【责任编辑 孙彩霞】
译者简介:刘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教授。
马立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斯洛伐克科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西思想文化史、中西比较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基督教文学研究。
* 本文作者特向陈剑光(Chan Kim-kwong,Hong Kong)、Tony Hyder(Oxford)、冯铁(Bochum)和李侠(Newcastle,Australia)等表示谢意,他们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此外,还要感谢华裔学志(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的马雷凯 (Roman Malek)。本文首次发表于Roman Malek ed.,From Kaifeng to Shanghai.Jews in China(Sankt Augustin–Nettetal,2000),pp.589-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