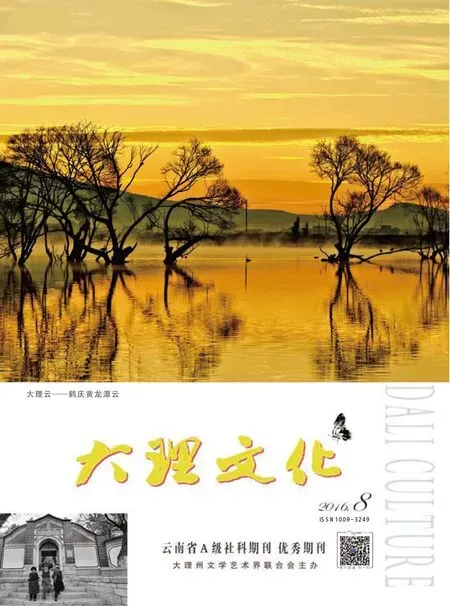第一百零一个问题
●余文飞
第一百零一个问题
●余文飞
我自然醒来,四周一片漆黑。看了看窗口的方向,没有亮光穿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
难道时间还早?两幅窗帘的中间,我特意留了一个笔记本厚的缝隙,便于早上起床的时候判断一下天气情况。多年的经验,让我都不用大众化地哗啦一下拉开窗帘,世俗化地叫一声,哇,今天是个好天气!抑或,叹息一声,唉,又天阴了!缝隙里的透进来的一束光亮,让我已经能准确地判断出今天天气的好坏。光线亮而明,外头肯定是个大太阳。光线亮而昏,定是多云天气。光线昏暗,天是阴了。若要判断是否刮风下雨,只需竖着耳朵仔细听一听。窗台上檐装了雨棚,声音的急骤与稀疏,可以判断雨点的大与小,雨脚的密与疏,风刮得大不大。至于扯闪打雷之类的,就不用我饶舌了。有了这条缝隙透露着天机,我的揣测一般八九不离十了。每天该从衣柜里扯出什么衣服套装,该加减多少衣服,心里有着数,我的着装和外头的气候亦是相得益彰了。
定了神,想了几秒钟,我有些质疑。难道是我醒早了?这不可能呀。
我的生物钟早已经固定了,每天七点半雷打不动地醒过来。这么说吧,二十几年了,我就从没在床头放过什么闹钟、手表之类的醒时玩意儿。我计较过,不论头天熬了夜,醉了酒,第二天早上七点半,我都会准时睁开眼,若要精确到分秒,我想出入仅仅只会介于三五秒之间。就算是休养生息的双休日,我照样准时醒,醒几分钟后,继续和被窝纠缠,睡个回笼觉。
难道大清早发生了日食?我对自己的奇思妙想晒了一个微笑。伸了个懒腰,侧过身子,伸出手向床头柜摸去。手机在柜头左上角,那个固定的位置,是我的手机现在的夜晚栖息地。自从一年前离了婚,妻子带着女儿走了,我就有把手机放在那里的习惯,全天候开机。
伸出去的右手折了回来,挠了挠头,我离婚了吗?听了听身畔,没有均匀的呼吸声。那肯定是离了,妻子睡觉的呼吸声我最熟悉了,细微而均匀,和我女儿的一样,都是无邪稚嫩的。通俗点说,就是那种没心没肺地睡着了才会有的闲适而生动的呼吸。要不然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干嘛,我不需要报时,更讨厌打搅。一直以来,我的手机也和我的生活一样,是有规律的。早上我洗漱完毕,八点钟从电视柜右侧的第二个平台上拿起它,开机。晚上我洗漱完毕,十点钟关机,把它放在电视柜右侧的第二个平台上,端端正正。虽然只是目测过,没有用卡尺量过,但手机的东南西北和长方形平台的边线肯定是平行,和妻子的手机也是并排平行而卧的。我还不止一次地纠正了妻子没放规整的手机位置,看着小小的两个手机并驾齐驱,我的觉才睡得踏实。
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就是等着妻子的电话。
和妻子的离婚,让我沮丧。我们从认识、相知、相信、相爱、结婚,诞下可爱的女儿,我们一直相濡以沫,从未因为争执红过脸,从未因为琐事拌过一句嘴。我尊重妻子,像妻子尊重我一样。古代所谓的举案齐眉大抵也不过如我们尔尔。就在我憧憬着白头偕老的未来,一年前,她突然提出离婚。我仅仅愣了几分钟,就点点头。她说女儿归她,我也仅仅愣了几分钟,就同意了。这婚离得莫名其妙,也简简单单,就是两口子一言不发地前后脚踏进民政局办事大厅,签个字。民政局的同志还苦口婆心地劝我们俩冷静想想。我问妻子,决定了?妻子点点头。我便拿起笔,一板一眼地在右下角写上自己的名字,按上手印。妻子带着女儿回了娘家,完了。
我躺在床上,自省了三天。当然,这三天我也是晚上十点半准时闭上眼,早上七点半准时睁开眼。所不同的是这三天我没有洗过脸,没有刷过牙,没有脱下衣裤折叠得整整齐齐地放进衣柜最下层。没有早餐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片面包。没有把一张纸巾一边擦干净嘴,擦掉鼻涕,一边整整齐齐地折成豆腐块,放进垃圾箩。没有早餐,自然午餐、晚餐也没有了,反正这三天我不吃不喝,连拉屎撒尿的事儿都很没有做过。
三天的反省,我扪心自问,没做错什么。要是觉得唯一做错的一件事,就是这三天,手机在电视柜右侧的第二个平台上,一直端端正正地放着。要命的是,电视柜在客厅,与卧室隔着一堵隔音墙。更要命的是,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这样的失误让我自责不已。若是按照平均一分钟拨打一个电话计算,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那是十四个六十分钟可以拨打八百四十个电话的时间。三天?那是二千五百二十个电话,更是二千五百二十个解释,二千五百二十个道歉,二千五百二十个原谅,二千五百二十个和好。结婚是个纸头,离婚是个纸头,复婚不也是个纸头么?
我的手机便摆在了床头柜上,一摆就是一年零八天,二十四小时开机。半夜骚扰电话接到过不少,打错电话的不在少数,更多的不是午夜牛郎就是欲火少妇,连开假发票的都接到过几回,但就不是妻子的。
我的右手又伸了出去,我得看看手机,确定我的生物钟没有问题。昨夜没接到过骚扰电话。自从我一接到骚扰电话就日娘捣姨地破口大骂,半夜骚扰电话也越来越少,连打错电话的主儿也很少了。手机上有时间,我要确定外面若没发生日食,黑漆漆伸手不见五指是咋回事。莫不是我在做梦?
伸出去的右手又不由自主地折了回来,在左手背上拧了一把。火辣辣地痛。没做梦就好。
右手第三次是快速折回来,着实吓了我一大跳。
固定的位置没有固定的手机。纯粹连床头柜都没有。右手摸到的是一片虚无。我唬得一骨碌跳爬起来。这一跳,更让我吓得魂飞魄散。我居然丝毫没有着力点的感觉,也就是没有爬起来,也没有跳起来。定了定心神,我手足并用,四处摸了摸。越摸越心惊肉跳,没有床,没有铺单,没有被子,没有衣柜……我的周围什么都没有,我在虚无的处所,是卧是立都不知道,不能走,不能跳,不能跑,只有我自己能动。如果看得清自己,我一定是张牙舞爪地动,像一只翻倒在水泥地上的乌龟,做徒劳无功的挣扎。不,乌龟还有硬邦邦的水泥地做支撑,我却什么都没有,毫无意义的动,不知所措的动。周遭只有无尽的黑,黑得渗人,让人毛发倒竖,肝胆俱裂。
还好,我摸到我的身上穿着衣服,是睡衣。是我的睡衣没错,从上数第二粒纽扣掉了,前几天刚掉的,还没找到针头线脑来缝补。自从妻子和女儿走后,许多东西都变着戏法一样找不到了。左边的衣角有个小小的洞,这是淘气的女儿偷着擦火柴玩儿,烙的。我当时只是作势要呵她的胳肢窝,算作对她的惩戒。摸到这个小小的洞,我的鼻子酸酸的。我还穿着衣服,我自己的衣服。这让我微微有些心安,有衣蔽体总好过赤身裸体。想想又哑然而笑,这样黑漆漆的境遇,赤身裸体和穿着衣服有区别么?
肯定是做噩梦了,我扬起左手,啪地给了自己左脸一下。火辣辣地痛。四下一摸,还是一样,我还是穿着我的睡衣,比一只四脚朝天的乌龟还可怜。我又扬起右手。右脸肯定红肿了,这一次力量奇大,眼前都冒出些星星。星星闪过,还是黑漆漆的。
我被歹徒绑架了?关在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吊在半空中?我又惊又慌,本能地叫了几声救命。空落落的黑,没有回音。唬得我赶紧又把自己浑身摸了一遍,后背够不到的地方,我都使劲抻着手企及了一通,看看有没有电影拍摄中的吊威亚,抑或魔术表演中的细丝。没有绳子,没有钢丝,没有细丝,没有任何捆绑的迹象。不禁苦笑了一回,哪有歹徒绑架人质还用得着像拍电影一样的折腾。再说了,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有份勉强糊口工作,业余写点小文字,没权,没钱,没势,没地位,没名头。绑架我,连空头支票都开不出一张,有个屌用。
排除了绑架,折腾出的一身细汗干得很快。
完了,我莫不是无声无息地死了,被小鬼扔进阿鼻地狱了。我浑身汗毛立即又竖了起来。仔细一想,不对呀,看了许多神呀怪呀的东西,书上描写的地狱确实让人毛骨悚然。但地狱不是应该凄风苦雨,哀鸿遍野,孤魂野鬼游荡,夜叉发嗔,小鬼龇牙,牛头马面暴叱,黑白无常阴笑的吗?地狱不是应该充斥着刀山、火海、血池、棺材,什么断头台,什么绞肉机,什么拔舌桩,什么开膛破肚,什么锁链镣铐,什么鞭影杖痕的么?最起码,地狱再怎么样阴风惨惨,冷酷的光亮应该有些许吧,就是一双两双带着狞笑亮着恐怖的眼睛应该有吧。

不对,这不应该是地狱。这里只有无穷无尽的黑。徒劳无功的挣扎。
这是被外星人绑架了?
非常像。我有些自负地肯定。
看了许多好莱坞科幻大片,只有在外太空的失重状态下,才会让人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有力使不出。想到这,我又验证了一遍自己的想法。拼命地向前后左右手足并用地想移动一点,除了挣扎还是挣扎。我移动不了分毫。
我顿然产生了绝望的念头。被外星人绑架了,岂还有生还的念头。庆幸的是,我摸了一遍全身,没有刀疤,没有被开膛破肚的感觉。使劲地呼吸了几口,呼吸正常,口腔、咽喉、肺部没有不适。切了下脉搏,探了探心跳,一切正常,我相信,就是这黑黢黢的状态,我身体里流淌的仍然是鲜红的血。这让我放心。
死就死吧。反正妻子走了,女儿走了,岳父岳母家境还算殷实,妻子有工作,女儿听话,无非就是一些不在一起的牵挂,心头那一个纠结了一年零十一天的解不开的死结。父亲和母亲早几年就仙去了,他们的后事我和兄弟姐妹们一起料理得妥妥当当,风光体面。我的兄弟姐妹都有家室,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我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执教的那些孩子,无非就是我走后,遇上些个不三不四,混日子,误人子弟的主儿。这是当下教育的通病,也是当下社会的通病,有能力的,有责任心的,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总是四处碰壁。无赖的,无耻的,欺骗的,虚浮的,混世的,丢人现眼的,拍马溜须的,昧着良心的,行尸走肉的,相反还吃得开。这多少还是让我有些心酸,为着纯洁可怜的孩子们,他们白纸一样的心灵,从小就被这些乌烟瘴气侵蚀着,为着这溃烂的,人心不古的社会。忽然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那句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
唉,想那么多干嘛!谁又来救救我。
忽然很想最后看一眼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可爱的地球,她的蔚蓝,她的圆润。她的被无知和野蛮伤害的憔悴的面容。啊!地球,我的母亲。
什么都没有。我已经把眼睛瞪得生疼,期望着哪怕看到一抹太阳的红,一点地球的蓝,一星月亮的白。只有无边无垠,无际无涯,无穷无尽的黑。没有月亮,没有地球,没有太阳。更别提眨着眼睛闪呀闪的星星了。女儿扑闪的眼睛真像两颗星星呀,可惜我看不到了。
我向着绝望的深渊越陷越深。快来吧,外星人,把我解剖。切开我的头颅,割开我的胸腔,把我的心脏血淋淋地拿去。拿去研究吧。只是最后给我片光亮吧!哪怕是手术台惨白的无影灯,照耀一下足矣。我要看看我的鲜红的血,被黑暗污染了没有。血会被污染成黑色的么?我一阵惊悚,激灵灵地打了个冷颤。
狗日的外星人,你们来吧!我声嘶力竭地吼。没有回音,没有动静,我像个小丑一样,在寂静的黑夜里上演着自己的悲剧。直到累了,累得一塌糊涂。我想躺下,睡个好觉,一睡不醒也行。可我怎么躺下,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我是直着还是横着。我应该躺在哪里,哪里有我身体蜷缩躺倒的地方。
索性闭上了眼睛。感觉我的灵魂搂着我的躯壳渐渐死去,安眠在无尽的黑暗里,无声无息。
……
你想走出这黑暗吗?
我忽地惊醒。
你想走出这黑暗吗?
声音若隐若现,时远时近,生硬而威严。我赶紧挥舞着双手向四处乱抓,希望抓到一个东西,哪怕是一根羽毛……
你想走出这黑暗吗?
想!想!想!你是谁?救救我!救救我呀!求求你了——救救我,救救我……
我救不了你的,你只有自己救自己。
我怎样救自己?我努力了,我挣扎了。我被外星人绑架到太空了……
什么外星人?胡扯!你就是你!你的臆想也太稀奇古怪了吧!
啊!那我怎会如此。你快告诉我,我怎样出去,走出这可怕的黑暗。我要我的床,我的被子,我的手机。我要第一时间给我的妻子打个电话,无论谁对谁错,我都认错。我要抱抱我的女儿,我要亲亲她。我想她们,我想她们。我痛哭流涕起来。这么久的黑暗。我竟然第一次痛哭失声,落下了眼泪。从记事起,我记得我只是流过三次眼泪,一次是母亲去世,一次是父亲去世,我看着他(她)安详地躺在棺材里,想着今后我再也看不见他们的音容笑貌了,眼泪便掉了下来,冰凉冰凉的。第三次是女儿出世,看着她黑黝黝的眼睛,骨碌碌地看着我,心头一热,两眼满是滚烫的热泪。这次是第四次流泪,眼泪是热的,流到脸颊上也是热的,挂在下巴上还是热的。
这到底是哪儿呀?你是谁?细听着你的声音很耳熟,似曾相识。你快救救我呀!你怎么不说话了。
我一直都在听你说话呀!这个地方是你最熟悉的一个地方,只是你从没有来过,也不想来而已。至于我嘛,走出这里,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了。刚才就告诉过你,我救不了你的,你只有自己救自己。
这地方我熟悉——先生,我都从没有来过这里,这上不巴天下不拔地的黑暗地狱我咋会熟悉。好人,你别逗我了,你不告诉我你是谁不要紧。你说——我自己——能救自己,怎样救呀?你快告诉我。我一定感你的大恩,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呵呵,其实救自己很简单。
你快说,你快说。
你只需要自己想好一百个问题问一下自己,这些问题不能重复,而且你必须诚实回答,理直气壮地说:是!每回答对一个问题,你就会向上飞升一截。每回答错一个问题,你又会下坠十倍的距离。出口就在上面,怎样出去取决于你的诚实,你心中的疑惑。
就那么简单?
你大可以试试。反正你被困在这里,问自己几个问题,无伤大雅。但我提醒你,提问题一定要谨慎,回答问题一定要诚实。要不然一百个问题问完了,你离出口还差那么一截,任谁也救不了你。你就在这无尽的黑暗里折腾算了。
我将信将疑。但又不得不考虑这个似曾相识的陌生声音带给我的生机。反正死马当作活马医了。第一个问题不假思索就出来了。
我是不是个男人?是。
忽然,我感觉身子飘了起来,倏倏倏往上飞,耳边嗖嗖嗖的尽是风声。我止不住内心的狂喜。大叫起来,我要脱困了,谢谢你,好人。
飞升忽然停止了。
唉,那个声音似乎在我耳边叹了口气。我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抓,却什么也没有抓到。
你呀!平日里不是一个很按部就班,诚实严谨的人么。才稍有转机就得意忘形啦?
不是,不是,我只是一时兴奋,黑暗让我绝望,忽然有了你的点拨指引,情不自禁而已。
算了,你慢慢提问题,慢慢回答吧!我到出口处等你。记住我的话,诚实,谨慎,机智,心静,平和,果毅,是你逃出黑暗的关键。相信你自己的感觉,相信你自己内心的真实。
别走,别走。和我说说话,黑暗让我恐惧。我害怕,我害怕……
那声音再没有回应,他许是真的走了。
我不得不重新审视我的处境。周遭的黑暗仍然是无穷无尽的。唯一逃出升天的办法就是陌生人点拨的自问自答,第一个问题虽然问得草率了些,但是我的回答没有错,我离脱困更近了一步。以后的问题我得深思熟虑,陌生人说得对,诚实,谨慎,机智,心静,平和,果毅,是我逃出黑暗的关键。我得珍惜这样的机会,万一一个不慎,将万劫不复。
我是不是爱我的母亲,深深怀念着她?是。
我是不是爱我的父亲,深深怀念着他?是。
我是不是爱我的兄弟姐妹,默默关心支持着他们?是。
嗖嗖嗖,每一个问题,我都像坐着上升的火箭一样。飞速地上升。忽然我有些后悔第四个问题问得马虎大意,我有五个兄弟姐妹,干嘛不逐个喊着名字问一遍,那就是一个问题变成了五个问题了。问到这里,我也不敢贸贸然去重复问一遍五个兄弟姐妹了。陌生人说过,问题不能重复。到现在为止,陌生人所说的一字一句都得斟酌。兄弟姐妹一词涵盖了五人,冒那样的险不值得。虽然有些懊恼,但还是要感谢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你们是我摆脱困顿的第二、三、四步坚实的台阶。
我是不是深爱着我的妻子?是。
我是不是深爱着我的女儿?是。
我的妻子是不是善解人意?是。
我的女儿是不是乖巧听话?是。
我的妻子是不是喜欢黄颜色衣服?是。
我的女儿是不是喜欢粉红色衣服?是。
我的妻子是不是勤劳贤惠?是。
我的妻子是不是对我体贴入微?是。
我的女儿是不是聪明机灵?是。
我的女儿是不是我的开心果?是。
……
我的妻子是不是喜欢蜷在我的怀里睡觉?是。
我的女儿是不是喜欢我亲亲她,抱抱她?是。
……
我的妻子是不是喜欢嗑瓜子?是。
我的女儿是不是喜欢吃洋芋食物?是。
……
我一边想着我的妻子、女儿,一口气自问自答了五十五个问题。都是些生活中琐碎的点点滴滴,这么多年和妻子的相濡以沫历历在目,和女儿开心快乐宛若眼前。谢谢我贤良的妻子,谢谢我可爱的女儿,让我飞升得那么快,那么远。我真想赶紧打个电话,向我的妻子道歉,在电话里听听女儿银铃般的笑声。我仰头看看,出口还不知在哪里,四周依旧是黑黢黢的,我只能从感官上感觉到我腮上的泪痕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我是不是一个正直的人?是。
我是不是一个有良知的人?是。
我是不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是。
我是不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是。
我是不是一个不懂得蝇营狗苟,投机取巧的人?是。
……
我是不是一个虽然默默无闻,却时刻关心着我的祖国当下和未来的人?是。
我是不是一个一旦国家有难,甩开笔杆子拎起枪杆子就冲锋在前的人?是。
这一波提问,我扪心自问,问了自己三十八个问题。说实话,有几个问题提出来了,心虚虚的,就怕一不小心,自己没有掂量准确自己的内心,再一次掉下深渊。还好,我口读我心,我对自己的了解还是把握得恰如其分的,这一路飞升,坦坦荡荡,有惊无险。我算了算,还差三个问题就足一百个问题了。最后的三个问题,着实让我一番挣扎。该问的问题已经问得差不多了,有种江郎才尽的感觉。一些滑到嘴边的问题,不敢脱口而出,因为心里对它们惴惴不安,不敢理直气壮地作肯定的回答。忽然忆起陌生人的话,相信你自己的感觉,相信你自己内心的真实。是呀,我的妻子,我的女儿。我能相信你们吗?
我的女儿是不是一直都深爱着我?是。
飞升。我似乎已经听到出口的动静,有回声了。出口就在不远处了。
我的妻子是不是一直都深爱着我?是。
我虽然理直气壮地回答,但是我都不敢睁开眼睛。直到感觉到耳畔是嗖嗖的风声,我在飞升而不是下落。我激动得睁开眼睛一看,上方虽然还是一片漆黑,但回声隆隆。
我大声地问道:我们一家人的心是不是一直都彼此牵挂,相亲相爱?
我嘶哑的声音高声答道:是!
飞升。头顶上方有一个模糊的圆圆的亮点。亮点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刺眼,越来越大,是个巨大的洞口。已经可以看见洞口上空的蓝天白云,阳光明媚。我幸福地闭上了双眼,沉浸在莫大的喜悦中。
我的飞升突然停了。睁眼一看,离洞口十米左右,我使劲地蹬腿,双手做划水动作。无济于事,我又一次悬在空中。我急了,赶紧对着洞口大喊。好心人,好心人,你在哪儿呀。你不是说先在洞口等我么。我已经理直气壮地自问自答了一百个问题了,咋还脱不了困境呢。
呵呵,你真行,一百个问题居然没有出现一次差错。那个陌生的声音仍然忽隐忽现,冷峻的语气倒是没变。
那我怎么还是脱不了困呢?原本还想说一句,你不会耍我的吧。黑暗的经历让我懂得冷静,不确定的话不乱说,没有根据的猜测不乱讲。陌生人指点我从黑暗找到光明,已经是善莫大焉了。
陌生人嘿嘿一笑,不抱怨我就行。记得你的第一个问题吗?
记得,记得。我赶紧点头。我问的是,我是不是个男人?我肯定的回答说是,马上飞升了起来。
你飞着飞着戛然而止了,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时因为有了脱困的希望,欣喜若狂,得意忘形了一些。不会——和这有关系吧?
就差那么一点点,你就顿悟了。
好心人,我错了。现在能补救吗?我重新自问自答几个问题,行吗?
一百个就是一百个,现在你再说一千个也没用了。
那怎么办呢?你得好人做到底,再帮帮我。
唉,好吧。我再帮你一次,谁叫我和你休戚与共呢。你最后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三个问,你回答对了,兴许你就脱困了。
我迫不及待地催促,你快问,你快问。
这个问题很简单:我是谁?是谁绑架了我?我该怎么办?
陌生的声音叮嘱道,好好回答哟,用你诚实和机智。说完了,嘻嘻一笑,像朝着蓝天白云飞升飘去,又像朝着我脚下的无底深渊落去。
我连忙问道:好心人,你究竟是谁?谢谢你救了我。
声音飘远,依稀听见:我就是你自己呀!
啊!怪不得声音那么熟悉。
我该怎么回答呢……
老公老公,醒醒,醒醒。我猛然睁开眼睛,忽地坐直身子,浑身汗流浃背。妻子正坐在我旁边,焦急地把我推醒。
你怎么了,做噩梦啦!又是蹬又是叫又是哭的。妻子关切的神情让我久久回不过味来。
你——不是一年前——和我——离了——婚,带着——女儿回家——了么。
你说什么?妻子瞪大眼睛,一脸嗔怒,泪珠儿在眼眶里打转。你疯了,谁跟你离婚了。嗳!难不成你看不上我这个黄脸婆了,到外边乱去了!
没有,没有!我一把抱住妻子,眼眶里红热了起来。做梦,做梦!
真的没有?妻子破涕为笑。打了个长长的呵欠,倒头睡去。
我披上衣服,走进女儿的小卧室。她睡得正香,鼻息轻盈。右手大拇指不安分地塞在嘴里,不时吧唧几下,许是梦到什么馋嘴的好东西了。我轻轻地把她的手指拉出来,在她的两腮上各香了一下,退了出来。
我蹩到客厅里,没有开灯,窗外的月亮正明,依稀照得物景分明。电视柜右侧的第二个平台上,我的手机和妻子的手机并排卧着。拿起自己的手机,关着机呢。我忽然想看一下现在的时间。打开手机,已经是半夜三点。我忽然想起那个有三个问的问题。手机突然闹了起来。我怕吵醒妻子和女儿,赶紧掐响听筒。
喂,哪位?
电话那头嘻嘻一笑,声音是那样的熟悉。你脱困了么?记得回答第一百零一个问题哟。
编辑手记:
《小生活》:这篇小说有些新写实小说的意味,新写实小说注重回到生活事实,不再强调“人”的生存价值,凡人琐事就是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忠实地描写了一对开小吃店夫妻一天里最真实的生活,生活中琐碎,生活中的辛劳、生活中的冲突作者都以非介入的态度细致记录下来,其中作者只还原生活本相,表现一些“纯态事实”。在其中,小说不再承担政治,道德和哲理说教的职责,只描写凡夫俗子们的平凡生活,关注其生存处境,小说里没有巧合,没有解释,只是写出烦琐生活的原色,用“平常性”、“庸常性”、“平凡性”来呈现生活的原生状态,展示当代人的生活存在状态。
《第一百零一个问题》:这篇小说的场景就是一个梦,一个人在黑暗深渊里,一个人在巨大压力里、一个人在痛苦场景中的梦。只是在梦里,人忽然起了变化,为了寻求生机,人变得诚实和真实起来。小说看似荒诞和虚幻,实则深刻和真实,看似是在荒诞中追问真实,实际是人与自己在探讨人生的重大问题,之前的一百个问题让“我”更了解了自己,也让“我”真实地面对内心。而第一百零一个问题:“我是谁?是谁绑架了我?我怎么办?”这是最后一个问题,却也是“我”最难回答的问题,同时也是该认真思考的人生哲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