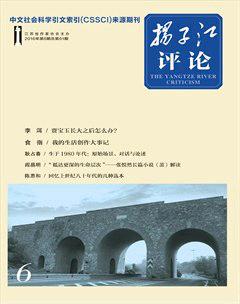一个完美主义者的悲凉心曲
孙晓燕
弋舟是西部小说家里的“新八骏”之一,除了《春秋误》是借用了历史题材的躯壳来书写,其他所有的小说都在言说书写着当下和现实的故事。像福斯特所说的那样,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总是在纠缠着,“进行着两败俱伤的战斗”a,弋舟小说世界的人物明显是和情节较着劲:刘晓东(《等深》、《而黑夜已至》、《所有路的尽头》),马领(《跛足之年》),郭氏父子(《蝌蚪》),阿莫(《凡心已炽》),金枝(《金枝夫人》),虞搏、姬武和逗号(《年轻人》),汤瑾(《被赞美》),这一系列人物占据着小说的主体视野,围绕着他们,故事和情节才会得以慢慢绽开。因为这些人物的性质不仅是“根据小说家对别人和对自己的推测而定”b的,而且是作者自己“依仗生命本身的蹉跎之感”,虚拟地给出自己的一个来路和一个归途c。
在弋舟的小说世界里,绝大部分故事的主角都是男性;在他的长篇小说和短篇故事里,男性人物形象的设置形成了相似固定的程式:一对主角男性形象,他们是父子关系,同窗朋友伙伴,与之配搭,有时还会有一两个男性配角人物,作为主角的映衬和补足。当我们掀开这一组组男性人物之间关系的披风,确是可以看见和领悟到作者对于这些男性人物形象所赋予的真诚用意: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成为作者探询“自我”的不同维度的依据,并由此来建构具有主体性的理想“自我”。在康德看来,我们期待的主体性不是相对于经验客体而存在的经验主体,而是具有永恒自在的价值独立性的精神主体。真正的主体性体现在主体的内在自我完善上,体现在人的精神自由是否得到了完整的实现上d。人物的塑造源自于对“自我”的探询和建构是弋舟小说世界显明的特质,作者希冀让“自我”获得真正的主体性笔直地挺立起来。《跛足之年》是弋舟一部准自传的长篇小说作品,男主角马领强烈地意识到现实里自我的混沌和存在的困境,但是最终皈依无门的灵魂被庸常里穿行的躯体裹挟着茫然前行。长篇小说《蝌蚪》里,男主人公郭卡被裹挟进红尘里的爱恨情仇之后的“自我”依然是躲避喘息的姿态。《我们的底牌》堪称弋舟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主人公“我”(曲兆寿)真的非常想站着“挺立”起来前行,但是在成就经验主体的途中还是弃甲卸盔,显出癫痫病患般的生命本相才能混世生存下去。以刘晓东为主人公的三部系列中篇小说在2014年出版发行,小说依然坚守着对于“自我”的书写和探寻,但理想的“自我”建构依然没有顺畅地完成。在环抱短刃上路的少年响亮郑重的“古风”面前自惭形秽(《等深》);在挣扎于黑夜和罪恶之中的年轻女子徐果面前(《而黑夜将至》)“用几乎令自己心碎的力气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在《所有路的尽头》里,作者将对于生命个体的“自我”观照转向了一类人和一代人的自我寻找,但结果是“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见《等深》)。在弋舟的小说世界里,我们感受到作者始终孜孜以求于为自我的灵魂找到一种自由之境,但是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主体完善自我之后挺立起来的男子汉形象呢?在马领们貌似特立独行的决绝举动背后,那并非凭依价值独立和精神自由的主体性而架构起来的生命姿态让人存疑,由此还可以窥见年轻的男性主人公心智的不健全和精神的脆弱;在刘晓东们幻灭的生命旅程里,那灰色平庸的人生和残酷的时代正面的相遇,终究无法凝聚和成就自我主体的生命能量,甚或沉淀为自我毁灭的炭火。年轻的马领和郭卡,到中年的刘晓东这一系列主人公形象,犹如友人眼中的弋舟一样,“迷惘又自知”e,他们的“自我”在此岸与彼岸之间逡巡,皈依无门的灵魂被穿行于庸常的躯体裹挟着,无奈地天荒地老下去。
为什么在弋舟的小说世界里几乎找寻不到一个笔直站立着的成熟男子汉的形象呢?人类庸常的命运和残酷的现实当下确实是这个结果不可超越和回避的事实所在,而有一个关键的因素确是更为直接、不可忽视:在生命个体建构自我的成长过程中,最早接触到的第一个男性样榜形象——“父亲”,严重阻碍和干扰了生命个体和这个世界之间本应建立起来的正常关系,甚或是“父亲”直接间接地摧折了本可以伟岸起来的“腰”和“臂膀”,使之无法真正挺立。弋舟的小说在发见和找寻自我主体性的言说叙写中,让我们把捉到了小说家或明或隐的“父亲情结”。作家自己说过:“小说家每一笔动人的书写,大约都该是源于自己的‘没有和‘失效。因为‘没有,所以虚构,因为‘没有,所以严肃认真地自欺欺人”。f弋舟意识到的“源于自我”的“没有”和“失效”,不仅仅是对于“自我”无法获得真正主体性的感慨,更潜隐着作者对于“父亲”的“没有”和“失效”的耿耿于怀。
长篇小说《蝌蚪》是作者一部较为完整叙述成长的小说故事。父亲这个形象被描画成身上充斥着人类种种局限性的俗物和不可理喻的怪物,虽然不乏为现实所迫,但父亲们确是将人的“本我”与其间的不堪赤裸裸地展现在儿子们的成长历程中。主人公郭卡“自我”的建构与“良心”的获得都是在父亲郭有持毫不避讳的“本我”笼罩下习得。小说还设置了一对配角的父子形象,儿子赵挥发的成长也没有逃脱出俗物父亲不堪的笼罩。即使最终儿子们胜过老子们,但成长中“父亲”的阴霾最终难以驱散剔净。到了《我们的底牌》里,父亲沦落为地道的庸人可怜虫,如同一道凝重的暗色,苟延残喘于子辈们的成长历程之中。正因为有这样一位父亲“在场”的成长历程,曲氏兄弟才会最终以癫痫病患般的“自我”与现实对战。这些成长故事把子辈们的“成长”或“进步”,退回到了私人的家庭居室里,在这里他们形成了对自己最初的真实的重要评价g,这些“另类”的成长事件不仅不能使主体的价值支撑建构起来,并且还会聚拢精神的脆弱和迷惘,如影相随。与《蝌蚪》里“父亲”的明晰和在场相比,《跛足之年》《年轻人》这些故事里,“父亲”形象被影影绰绰地叙说着,在场的笼罩感淡下去了。《跛足之年》里,父亲的“在场”被转移到信笺的空间里,不见父亲的肉身模样,只觉他正襟危坐,义正言辞地训诫子女,偶露的一点父亲的人性也布满了老耄昏聩的斑点,映现出“父”的狐假虎威式权力的衰颓,而“子”的成长就建制在对“父”的叛逆行为之中。《年轻人》里的父亲形象几乎是不在场的衣食父母的符号化存在。虞搏和姬武这些子辈们逾越父亲而成长,把父亲训育的良心留给父亲,而用自己的方式孵化自己的“良心”。这些令人发毛的父子关系的叙写,亦可以看出“父亲”也变相地完成了催生子辈们“良心”的任务,当然,作者弋舟想建构的那个自我主体并不仅仅满足于良心的获得。在2014年出版的《刘晓东》小说集中,作者和主人公刘晓东终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他们在年龄、人生历程、甚至职业和社会角色层面几近等同,郭卡和马领们终于长大成了“父亲”刘晓东们,他们固然和自己的父亲迥然有异,脱离了形而下、低级趣味的生命轨道,但也最终亦没有成为子辈们的守护神和榜样,脱胎换骨成为真正的父亲。《等深》里的自顾寻找这个时代答案的父亲周又坚,在怀抱短刃上路的少年儿子面前,黯然失色;《而黑夜将至》里的父辈刘晓东眼见着年轻的徐果们在黑暗、罪恶和生死的边缘堕落下去而无力相助;《所有路的尽头》更让我们察看到了一代理想主义者的改弦易辙和溃败颓丧。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孕育出的一代理想主义青年,刘晓东们在应该承担父亲的角色和职责时,却是放弃了对于理想的坚守,屈辱着妥协,甚至堕落着去适应,与马领、郭卡们充满着青年人无助无奈的逃避和颓废相比,更令人惊愕和悲凉,连弋舟自己都情不自禁地在《等深》的故事讲述中跳出来慨叹:“我们这一代人溃败了,才有这个孩子怀抱断刃上路的今天”,“眼前的这个男孩,却在光明磊落地谋求着敢作敢为的责任。在他的比照下,站在‘十四岁这根红线一侧的我,才是一个凭直觉就永远拒绝着责任,永远乖巧与轻浮的劣童;而站在另一侧的男童,却响亮、郑重。他几乎是一种‘古风,如此的气概,已经远离我们有多少个时代了?”理想主义者长啊长,长成了“劣童”。
短篇小说《天上的眼睛》难得塑造了一位正面的父亲形象。他在现实面前俨然一位“无能”的夫与父,在妻子离家出走之后,依然持守着善良正义乐观的生命姿态,最终感化了妻子回头,也让父女关系温情地回归了。故事的结尾是身处拘留所里的“我”,趴在铁栅栏窗边看着星空,想象着破镜重圆后的生活。一方面,作为父亲的形象似乎在一片布满星星的夜空下美好定格了,而另一方面,“我”的内心却觉得在星星的凝望中,自己不过这尘世“一条微不足道的狗”而已。狗样的父亲只能爬着生,如何能像人一样立着行呢。《天上的眼睛》亦不过是对于其他小说里所贬抑的父亲形象所做的正面呼应。这个故事不仅是弋舟小说世界里难得地对现世里一位正常父亲的叙写,也算得上是作者在所有故事讲述中最为温情的父女之情的描述。女儿青青为父雪耻,义无反顾,父亲为女儿受过,不畏牢狱之灾。故事的本身不乏现实人生的酸楚和无奈,而这段父女之情无疑超越了鸡零狗碎般的现实人世。与之相比,其他小说里对于父女关系的叙写从没有这样乐观温情的基调。《年轻人》里的逗号,为了虞搏迫不得已去向自己有权势的父母求情却遭到了拒绝,看上去她的父母是不愿意帮助虞搏这个陌生人,实质上却是逗号这个女儿在背离了父辈们的“希望”之后必然要承担的后果,这完全是父辈们的报复。《蝌蚪》里的庞安,她的成长在父亲招致的屈辱与恐惧之中度过,这使得她一生都辱没在无良父亲的阴影中不得安宁。有父亲又如何?于是逗号们唯有以自我放逐的生命姿态回返到“五四”式的“弑父”价值立场中,让“父亲”消失出场,完全“没有”和“失效”。《凡心已炽》里的阿莫,《金枝夫人》里的金枝,《被赞美》里的汤瑾,《隐疾》里的小转子,《跛足之年》里的罗小鸽,《我们的底牌》里的曲兆禧,她们干脆判决那个终将辱没自己的亲生父亲出局,在无父的生命旅程里与现实世界里的男人们遇见、纠缠,犹如“一朵花,在不知明的某处 阴坡或阳坡 开了落了”。然而世事注定,那些“间或的树,石头流水隔着,高高矮矮”h的她们遭逢的男人,还是替代了缺场的亲生父亲的位置,将她们钉在了“怪女”和“圣女”的十字架上。这究竟是女性不可逃脱的一种宿命,还是再一次显现出弋舟对于“父亲”形象的耿耿于怀?《凡心已炽》里长相不同于常人的阿莫,似乎一生的愿望就是为了寻求真正的理想爱情,所有的男人们都是攫取者,最终把她推向了毁灭的深渊。《金枝夫人》里的金枝为了舅舅和男友唐树科,最终被商人刘利欺辱却无处呻吟。《被赞美》里的汤瑾算得上是一个现实的女子,但她亦是出于无奈为了生存利益,委身于自己的上司周瑶石,还要强作欢颜接受周介绍的男友康至;《跛足之年》里的罗小鸽不仅要领受男友马领浪子般的爱意和脾性,还要为男友的生意贡献出自己的青春,最终不能承受而逃离到另一个男人的罗网之中。罗小鸽的逃离与其说是女性扭曲的报复,不如说被放逐到另一个男性统治下的生命枯井之中。《隐疾》里的小转子一出场就很惊艳,大大的嗓门,热情外露的举止,夸张的妆饰,显出和其他故事里女性形象的显明差异。故事一直展开着讲述“我”目睹和感受小转子和老康兄妹般的恋情进展和结局。而这样美好的小转子却是一个重度梦游症患者,也正是由于这个病症,被老康厌弃。其实这个故事的讲述有些模糊,老康和小转子最终劳燕分飞的结局,到底是因为小转子觉得自己所托非人,还是老康因为小转子奇怪的病症抛弃了她,不管怎样,小转子最终还是没有找到父兄般的男人与之相伴一生。最为悲壮的受难“圣母”的形象莫过于《蝌蚪》里的徐未,她平生遇到的所有的男人都不同程度迫不及待地将她献祭到受难“圣母”的神坛之上。作为夫的赵生群和郭有持,给予她的只是兽般的欲望和暴虐;她亦看不到赵挥发和郭卡这些子辈的希望,在承受了一切的折磨和屈辱,完成了人世应尽的职责之后,与卡车相撞断然了却红尘。
在弋舟的小说书写里,父女关系的书写确是再一次显出作者对于“父亲”这个角色的洞察与思虑。与阿莫们相遇的男人中,那些年岁辈分与父亲相当的男人们已然配不上“父亲”这个角色,而那些终将成为他人父亲的年轻男人们,亦无力担当起父亲的角色和责任的,他们是懦夫,遇事逃开,让女人们来面对并收拾残局;或以浪子面目自暴自弃,装扮和放任自我,遇事则对现实和女人衍生怨怼。一旦与这些男人们有染,女人们或是染上怪疾,成为在现实和梦之间飘忽游移的“怪女”,或是成为被献祭、受难的“圣女”。至于《被赞美》里的仝小乙这个男性形象,他对于女性的爱是人性有温度的。但成年的他确是没有真正长大,还是一个心智不全的大男孩;或许作者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和凡间现实全然对立的男性形象,而让他为爱而毅然赴死。不管怎样,仝小乙这个男性形象的面目是模糊的,看不清他的样子,这不过又一次呈现出弋舟塑造男性人物形象时复杂的心理情绪。我们几乎看不到一个配得上父亲这一称谓的父亲形象,更没有一个面目清晰的男子汉伟岸坚毅的身影驻立于弋舟的小说世界里,有的尽是面目可憎或者令人生疑的男性侏儒,这侏儒般的男人群像怎么能够担当起父亲的称谓和角色呢?在找寻自我主体性的忧伤旅程里,“父亲”形象的书写确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悲凉心曲的咏叹。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大众文化通过“精神和道德的领导”已经争取到了社会被统治阶级的赞同,并且开始强有力地塑造着他们i。与此同时,价值选择的多元化,使得生命个体容易被一些时代,文化和惯性的约束力裹挟进与他人关系的无形网罩中,使得个体会失去自我原有的姿态。2000年开始写小说的弋舟,当时对于这样的生存氛围一定有自身诸多的体验感受。在《蝌蚪》开篇题记中,弋舟引用了德国女诗人赫塔·米勒的诗歌《我怕故我在》:“在没有上帝和天使护卫的行程中,我就靠天边的云彩活着,我不能不把它画下来,挂在床头。”这片披着上帝与天使神性辉光的“天边的云彩”,必然是那个理想自我的倒影,弋舟仰望着这片云彩,始终孜孜以求于为灵魂找寻自由之境。傅雷以为“小说家最大的秘密,在能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唯有在众生身上去体验人生,才会使作家和人物同时进步”j。以此观照弋舟小说世界的人物形象,显出的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态势:从《跛足之年》、《蝌蚪》的将自己的主观感觉有意识移注到主人公身上,到《刘晓东》系列小说里“跟着创造的人物同时演化”的主人公形象而渐入佳境。与此同时,“父亲”形象的书写则潜隐于对于自我探询的小说主旨之后,父亲的“没有”和“失效”成为寻找自我的生命旅程里不可逾越的天堑和障碍,使得作者转而祈求天上神祇的守护,幻化出那片“天边的云彩”,“在自己的作品里再造另外的逻辑,以此给自己一个‘有效的立场,让自己不再显得那么勉强和荒唐”k。
【注释】
ab[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83、39页。
c弋舟:《我们这个时代的刘晓东》,《刘晓东》,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d[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5月版。
e张楚:《完美主义者的悲凉和先锋者的慨然从容》,《弋舟的小说》,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3页。
fk弋舟:《〈蝌蚪〉后记》,《蝌蚪》,作家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第234页。
g[美]C·W莫里斯:《开放的自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87页。
h弋舟:《〈凡心已炽〉》题记,《弋舟的小说》,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年4月第1版,第1页。
i[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j迅雨:《才华最会出卖人——论张爱玲的小说》,原载《万象》1944年5月第三卷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