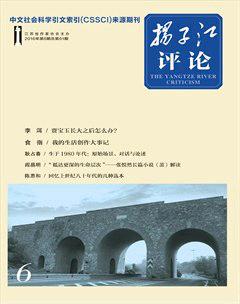直觉、塔布与文学写作
黄德海
如果我们把梦看成一个作品
不知是不是因为直觉和本能愈晚近愈被推重,梦越来越成为文学几近公开的隐秘来源,甚至有人奢望,梦可以直接就是一个作品——“如果能有一种梦,梦中的我写好一首诗、一篇文字或者一篇小说,那么有多好,我只要醒来时一字一字抄下来就行了”a。声称能够把梦平移到纸上的写作者,也几乎立即会被认定为某种特别的天才。不必知道莎士比亚说过,“我们是用与我们的梦相同的材料做成的”b,写作者在某些时刻可能都会暗暗期盼,不用经过艰难的思考、时常的中断和反复的修改,作品便已自动完成——使用的仍然是我们自身的材料,跟来于现实的没什么不同不是?
不管梦是对日常精神压抑的释放,还是对清醒时思想冗余的消化,我们大体上都容易相信,“梦是人对自己的松手,一种彻底的松手,大概正因为这样,我们往往相信,梦暴现出某个,或某些‘更真实的我,赋予它一个深向的意义,一个诸如认识我自己的睿智意义”c。随着弗洛伊德的流行,如下的判断几乎被确认为常识:生活在现实世界的“我”被可恶的理性强行管制,只好在梦里流露出自己更本质更率真的一面,从而接近了某种更原始、更具活力、更不受拘束甚至更有时间来历的东西。现时代文学中经常出现的变形的怪兽,残缺的人体,黑暗的人心,无序的生长,失控的欲望,放纵的狂欢……差不多都跟梦的释放有关,“这也许才是梦最富意义的地方,我指的是,一种几近不可能的自由,一种取消白天世界种种界线的自由”d。
不管取消了多少界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莎士比亚说的相同材料,到底包括哪些呢?是不是梦和现实都来于心灵的图景,如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说?人的心灵塑像,是多头怪兽、狮子和人三种形体长在一起,人们外在能看到的,只是这一联合体“人形的外壳,看不到里面的任何东西,似乎这纯粹是一个人的像”e。诸多写作者缺乏洞察,是因只看到人形的人心,看不到塑像里面的幽微,等于抽去了其中本有的怪兽和狮子,人难免平面刻板,缺了特殊的精气神儿。说到这里,有人或许要迫不及待地断言,只有把多头怪兽和狮子释放到纸上,艺术和文学才可能拥有旺盛的生命力——那些能把在梦中释放出狮子和怪兽、并落于纸上的人们,将被指认为时代英雄。
原始的、野性的、未经调理的人性姿态,有益于让文学作品保持活力,把过于柔腻的优美变换为某种庄重的崇高,涤除现代人身上趋于病态的孱弱。不过,这种未经约束的人性原始状态,仍然有其风险,一不小心,原始的兽性将露出可怕的獠牙。一味放纵和加强多头怪兽和狮子的力量,会“让人忍饥受渴,直到人变得十分虚弱,以致那两个可以对人为所欲为而无须顾忌”,或者“任其相互吞并残杀而同归于尽”f。是心灵塑像中的人与两个精怪,一起构成了生命的活力,而照现代过度思路经营的作品,释放出来的,往往是多头怪兽和狮子,那个看不太清晰的人形,只是现实里的行尸走肉,梦境里的浅淡阴影。我们从不少现代作品中感受到的气息奄奄,或者阳亢的反抗挣扎,差不多都可以看成对两个精怪的屈从或放纵。
未经驯服的多头怪兽和狮子,最终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是横冲直撞的鲁莽,不管不顾的欲望。只是因为现时代对原始活力的过度赞许,才将这不加节制的欲望认定为人的内在本质。在苏格拉底看来,一个人身上会有两个趋向不同的自我,“一个是天生的对诸快乐的欲望,另一个是习得的、趋向最好的东西的意见。这两种型相在我们身上有时一心一意,有时又反目内讧;有时这个掌权,有时那个掌权。当趋向最好的东西的意见凭靠理性引领和掌权时,这种权力的名称就叫节制。可是,若欲望毫无理性地拖曳我们追求种种快乐,并在我们身上施行统治,这种统治就被叫做肆心”g。肆心会让人忘记属人的艰辛和荣耀,不是诱导人变得沉溺,就是刺激人变得残暴。
在苏格拉底看来,正确对待精神中三种力量的方式,是“让我们内部的人性能够完全主宰整个的人,管好那个多头的怪兽,像一个农夫栽培浇灌驯化的禾苗而铲除野草一样。他还要把狮性变成自己的盟友,一视同仁地照顾好大家的利益,使各个成分之间和睦相处,从而促进它们生长”h。“所谓美好的和可敬的事物乃是那些能使我们天性中兽性部分受制于人性部分(或可更确切地说受制于神性部分的事物),而丑恶和卑下的事物乃是那些使我们天性中的温驯部分受役于野性部分的事物”i。
或许有个问题需要提示,所谓“内部的人性”,显然区分于心灵塑像中的那个人形,是“人性中之人”,英文翻为“the man in man”,或“the human being within this human being”j。那个人性中的人,是一个不断认识自己、不断反省中的人,从而赢得了对心灵塑像的培养权,自反而缩,几乎接通神性(感受到神性的限制,不正是对神性的接通?)。只有经由自省和教化而生的人性中之人,才有可能让心灵中的三种力量抟而归一,裁断狂简,归于彬彬,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庄子·人间世》说的那样,“雕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
这奇妙的隐喻另有个以显现的方式深藏的部分,即不管人、多头怪兽和狮子多么醒目多么耀眼,最终必然投射在人形的心灵塑像上。通过梦,人们释放了被文明抑制的活力,变化成各种动人或吓人的花样,如振奋时的攘臂或忧郁时的啸歌。那些活跃在人形塑像上的一切,跟梦一样,不会有“多出来的东西”,“最多,只是某些我们以为已遗忘的东西,乃至于某个更原初、更幼稚、更未经改善处理、更接近生物性的我”k。再怪诞的梦,也没有为那个本来完备的自己添减些什么,梦的意义,原不在内容的增加,“而是一个对白天森严界线的纠正和解放,通过相同材料的组合,以一种示范的模样、一种启示的模样,告诉我们,我们自己,以及整个世界,可以不必然只此一途”l。
只是,梦经常组合状况不佳,不保证完整也不承诺完美,它更像是小孩子玩的“what if”游戏——What if 老鼠会说话,What if 狗狗能驾驶飞机,What if 小鸭可以自由飞翔……“我们有绝对的理由相信,梦更多时候因此只能是‘失败的作品(那些只相信直觉、由笔拖着走的作品亦然),证之我们每个人的实际做梦经验应该也如此没错;还有,横向的随机组合,不会有真正触及稍深一层东西的机会,有时仿佛有但其实不会有,那只是混乱的伪装……所以,梦不仅总是失败的作品,还是个初级的作品”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