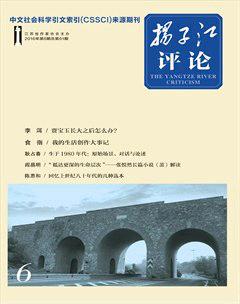诗人的隐居时代
王晓渔
从“春秋战国”到“海市蜃楼”
中国大陆的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尤其是1986年,从写作和阅读的广泛程度来说,只有1958年可以相提并论。但1958年全民写诗的盛况,是政治运动在诗歌领域的表现,是“大跃进”的一部分。诗歌千篇一律,不越雷池一步,在诗歌史上只是一个空前绝后的“负面案例”,几乎没有诗学的价值。1986年前后的诗歌运动,则与“文化热”有关,是公众在数十年精神饥荒之后的文化饕餮。各种写作实验前仆后继,呈现出开放的气象。
1986年,《深圳青年报》和安徽《诗歌报》联合主办“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共有100多位诗人、60余家“诗派”参展,成为诗歌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徐敬亚是这次活动的策划者,他曾列举这么一组数据:
1986——在这个被称为“无法拒绝的年代”,全国2000多家诗社和十倍百倍于此数字的自谓诗人,以成千上百的诗集、诗报、诗刊与传统实行着断裂,将八十年代中期的新诗推向了弥漫的新空间,也将艺术探索和公众准则的反差推向了一个新的潮头。至1986年7月,全国已出的非正式打印诗集达905种,不定期的打印诗刊70种,非正式发行的铅印诗刊和诗报22种。a
这组数据只会低估而不会高估当时的诗歌状况。当时,也有诗人对这一活动持保留意见。在安徽芜湖,三位诗人周墙、北魏、丁翔产生分歧,北魏认为应该参加这次活动,周墙和丁翔则认为没有必要,后来周墙将报名表格撕碎,以示抵制此次大展。他们后来在诗歌史上“失踪”,除了当年的朋友,几乎无人知晓这段经历。20年后,已经成为实业家的周墙出资赞助了“中国第三代诗歌20周年纪念会”,纪念“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这段往事才被公之于众。一家媒体报道纪念会时,这样写道:“当年的诗歌大展就像一艘临时拼凑的船,上了船的和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上船的诗人们,在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同的地位。上船者成为文学史上的‘第三代诗人,没上船的诗人则成为默默无闻的另类,在诗界的名气和影响看起来别如天壤。” b
在80年代,诗歌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本。默默在《我们就是海市蜃楼——一个人的诗歌史》里回忆,他居住的新村有一个有名的大流氓,听说默默会写诗,不仅表示佩服,还主动提出帮他打印一本诗集。c但是,诗歌的“奇里斯玛”(charisma)在面对公众时有效,在同行之间却需要借助诗歌以外的力量。诗人的声名不仅取决于诗歌的品质,还取决于诗人是否参加某次文化行动、是否拥有某种文化资本,这种评判标准一直贯穿于当代中国诗歌史,并且产生了相应的压抑和激励机制。
1987年,欧阳江河在《星星》诗刊召开的诗人座谈会上把身处的时代称作“诗坛的春秋战国”d。这种命名呈现了当时的诗歌景观,诗人们“自由组合”或者“拉帮结派”为各种诗歌流派,形成诸侯林立的格局,不同流派之间经常展开“合纵”或者“连横”,流派内部也会产生“政变”。诗歌流派的划分不仅取决于艺术趣味,还取决于诗人的地缘、学缘乃至惯习,有时则取决于一些偶然因素。“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要求以“群体”的方式展现诗歌,一些诗人化零为整,临时组合为诗歌群体,拟写宣言,参加大展。西川孤身参展,只能以“西川体”的名义撰写艺术自释,以符合“群体”的要求。
“春秋战国”的命名,既说明了诗歌热火朝天的景象,也说明诗人们对文化资本的争夺。翻看当时的诗派宣言,首先表述的往往不是自己的诗歌理念,而是如何与既有的诗歌理念划清界限。“打倒北岛”、“PASS北岛”是流行一时的诗歌口号,但是,这种句式又说明诗人们不但没有超越北岛,甚至又回到前北岛时代的革命话语。
这种“春秋战国”的繁盛景象,在20世纪90年代看来如同南柯一梦,直至1999年的“盘峰诗会”才再次回归,同时回归的依然是曾经熟悉的话语,诸如民间和知识分子的诗歌立场之争。无论如何回归,1958年和1986年的诗歌盛世都是非常年代的产物,不再可能重现。默默回顾自己的诗歌生涯时,使用了“海市蜃楼”一词,这准确地描述出时代精神的演变,诗歌是光荣与梦想,又是虚构与幻觉。
“遗老”和“遗少”
在20世纪80年代,北京、成都、南京、上海是当代诗歌的四座重镇。北京见证了朦胧诗以降的当代诗歌史,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位置,使得诗歌在那里仿佛拥有了一个扩音器,能够获得更大的影响。这座城市有点像20世纪上半叶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文学青年的发迹之地。进入90年代,当体制开始松动,各地诗人纷纷进行文化迁徙,成为“北漂”的重要组成部分。
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在北京成为可能,“锦城”成都和“六朝古都”南京的氛围适合古典文人式的生活。相对缓慢的生活节奏、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使得诗人们在成都和南京较为便捷地拥有基本的闲暇和生存条件。
上海一度是波西米亚式文人的聚集地,在20世纪上半叶,相对独立的租界和繁荣的出版业提供了宽松而且丰富的文化空间,但这些要素在90年代的上海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高效的行政体系和式微的媒体出版。相比之下,北京一方面是政治中心,另一方面又存在大量的行政缝隙,可以见缝插针,广州偏安于岭南,又临近香港,媒体得风气之先,这两座城市部分继承了上海昔日的传统。不仅波西米亚式的生活在上海不再可能,紧张的生活节奏、高昂的生活成本,使得古典文人式的生活只是一种梦想。作为一座诞生于近代的都市,上海只有不足200年的历史(历史绵长的松江府位于上海郊区),不适合发思古之幽情,也缺乏古典文人必需的山水。
80年代诗坛“春秋战国”的中坚力量是大学生,上海众多的大学成为诗人生长的空间。“城市人”的四位成员宋琳、孙晓刚、李彬勇、张小波,在参加“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时的艺术自释里表示“我们中的每个人都是所谓的‘大学才子”e。当时参加诗歌写作的大学生有华东师范大学的宋琳(中文系79级)、刘漫流、周泽雄(笔名天游)、张远山(笔名海客)、徐芳(均为中文系80级)、张小波(教育系80级),上海师范大学的陈东东、王寅、陆忆敏、成茂朝(均为中文系80级)、京不特(数学系82级),复旦大学的孙晓刚(中文系78级)、许德民(经济系79级)、李彬勇(国政系79级)、张真(新闻系80级),上海机械学院(即上海理工大学)的孟浪(精密仪器工程系f78级),复旦大学分校(即上海大学)的张烨(文献信息系78级)等。他们的诗歌理念不尽相同,一部分以高校文学社团和刊物为阵地,一部分则是自己印刷诗歌刊物,后者在当时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g。
即使不在大学的郁郁(上海粮食局技校78级)、默默(上海冶金工业学校81级)等,也与大学生诗人有着密切的交流,并把大学校园作为活动空间。冰释之的经历稍微特殊,他于1978年进入上海摩托车厂技校,1983年进入上海大学。在80年代前后,不仅大学是诗人生长的空间,很多诗人从中学开始写作,孟浪、郁郁、冰释之是中学同班同学,他们的文学认同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诗歌写作从高中开始h。80年代初期,王小龙在上海青年宫文艺科主管中学生诗歌培训工作,开了两期半年一期的诗歌讲座,学生由上海各个中学的校长推荐,第一期学员有沈宏菲(即沈宏非,暨南大学新闻系80级)、卓松盛(复旦大学中文系80级)、王依群(笔名胖山,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80级)、张真等,默默是第二期学员。
80年代的“遗老”通常于80年代前中期就读于大学,发起或参与当时的各种诗歌运动,并且分享诗歌带来的光荣与梦想。80年代的“遗少”属于被遗忘的一代,他们往往在80年代中后期就读于大学并开始诗歌写作,秉承了80年代的精神气质,尚未充分在当时的文化空间中展现,就仓促进入90年代,随后成为蛰伏的一代,如古冈(深圳大学经济系83级)、陈先发(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85级)、丁丽英(上海财经大学会计系85级)、韩国强(笔名天骄,复旦大学哲学系86级)、叶青(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87级)等。“遗老”与“遗少”年龄相差甚微,但是由于时代的斗转直下,个人际遇出现巨大的差异。
当“春秋战国”成为“海市蜃楼”,“天之骄子”也成为没有精神家园的“丧家犬”。90年代,上海的诗歌处于一个全面蛰伏的时期。除了“遗老”和“遗少”,诗人很难构成一个代际。在这个时期出现的数量有限的诗人中,韩博、马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91级)具有一定影响力。韩博大学毕业之后继续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之后辗转于上海的媒体。马骅大学毕业之后在上海短暂停留,然后赴厦门、北京等地,2003年赴云南省德钦县做乡村教师,2004年于一场车祸中坠江失踪。
没有场域的诗歌场域
“场域”(field)是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的概念,他将场域称作“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同时又表示不太喜欢专业定义i。
80年代的诗人,通常在校园或者单位之中。大学实行毕业分配制度,大学生的工作不取决于个人,而是取决于学校。由于大学生是“天之骄子”,毕业分配的工作单位大都差强人意。当时的单位制度缺乏流动性,自由职业尚未成型,计划经济依然具有主导作用,诗人们基本寄身于工作单位之中,很少“跳槽”和“下海”,却也拥有基本的经济保障。加之当时浓厚的文化氛围和较为宽松的政治管制,使得80年代的上海形成较为正式的诗歌场域,诸如“实验诗社”、“海上诗群”、“撒娇派”、“城市人”等。
但是在90年代,诗人的聚会和诗集的非正式出版都面临种种困境,同时诗人们纷纷脱离校园或者单位,为解决生存问题而不再拥有闲暇,很多诗人干脆放弃了诗歌写作。刘苇如此描述当时的情景:“至90年代初期,突然之间,许多诗人放弃了诗歌写作,转入各行各业。……诗歌的销声匿迹就显得顺理成章。因而在表面上,整个90年代,上海诗坛属于相对沉寂的年代。”j在冰释之的简历里,90年代是诗歌空白,没有写诗。默默曾经回忆,1991年创作完史诗《在中国长大》第五章节“争取未来”以后就封笔,1998年夏天应邀赴漳州参加一个诗歌笔会,由于岑寂多年,除神交已久的舒婷和吕德安外,与会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一个都不(原文没有“不”字,根据上下文,补上——引者按)认识,颇为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诗歌场域几乎难以形成。不过,没有场域也是“诗歌场域”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
刘漫流认为“从未存在过一个诗歌上海”,因为“诗歌从来没有真正占领过一座城市”。他指出:“多年来,本地值得注意的诗歌作者很少会超过两位数。即使在流星雨爆发的八十年代诗坛,他们也更像是一些行星或恒星,在各自的生活轨道上自转或公转。诸如此类的集合,甚至算不上是一次江湖啸聚或飞行集会。如果说诗坛已经越来越江湖化,上海诗人从来就不是一伙热衷于闯荡诗歌江湖的杂耍艺人或行为艺术家,或一些以诗作为敲门砖的政治市侩与投机分子。”k刘漫流指出了上海诗人的一个特质,即很少以发起诗歌运动的方式进入诗坛。刘苇也认为上海诗人“彼此分散,不交往,也不交流,独自沉浸于孤独中”。尤其在90年代,上海诗人普遍具有隐者气质,很少以诗歌流派或者诗歌行动的方式呈现自我,而是以独立个体的方式出现,他们坚持诗歌的内在尺度,却缺乏外在名声,这是上海诗歌场域的主要特征。
钱穆先生曾经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士大夫可以依托门第或寺庙,宋、明以后士大夫已经没有退守之基业。他总结明末遗民的生活状况,大致是七种境遇:出家、行医、务农、处馆、苦隐、游幕、经商l。80年代“遗老”和“遗少”们的选择不比明末遗民更多,只有更少,出家需要有信仰认同,行医需要专业知识,务农需要拥有土地,处馆需要有学校接收,苦隐需要解决衣食住行,游幕需要有开明官员,经商需要有“第一桶金”。钱穆讲到“苦隐”时提及亦有“避地海外”者,如朱舜水之至日本。
部分诗人选择了移民,张真早在1983年就因为跨国婚姻移居瑞典,后赴美国攻读学位并任教,宋琳1991年因为跨国婚姻移居法国,孟浪1995年应布朗大学之邀赴美国任驻校作家。京不特的经历最为传奇,1988年成为佛教沙弥,1989年到达泰国,1990至1992年在老挝身陷囹圄,随后赴丹麦。还有一些诗人短暂地离开上海,郁郁曾在福州逗留。
留在上海的诗人,一部分诗人开始从“单位人”到“无业游民”的转换,一部分诗人开始“下海”经商,还有一部分诗人“跳槽”,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刘漫流在介绍一本诗集里的上海诗人时,这样概括:“大都是一些忠实地履行纳税义务的温和市民而非由纳税人供养的组织机构成员,他们或者只是一些职员、大学教师、策展人、广告文案、电视台导演、公司经理、高尔夫俱乐部总监、自由职业者或家庭妇女。”m张远山曾交待部分诗人们的下落:“八十年代以后至今,‘海上诗人的基本情况是(仅就我知道的而言,来必完全也未必准确):我和周泽雄于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离开教职,成为体制外的职业作家。刘漫流始终供职于上海一所大学。杭苇目前供职于深圳—家报纸。王寅离开教职以后辗转于各种形式的媒体,现为《南方周末》驻上海站的记者,陆忆敏离开教职以后,目前是上海某区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主任。陈东东先供职于上海市工商联,现成为职业诗人。成茂朝从一名教员变成一位商人。孟浪漫游全国后于90年代中期远赴美国。默默成为广告从业人员,近来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郁郁长期闲居,但一如既往地热心于各种诗歌活动。京不特先出家为僧,还俗后赴丹麦攻读哲学,目前正从事克尔恺戈尔著作的汉译。这些人现在有的已经不再写作,继续写作的也未必局限于诗歌,不少人已经把写作领域扩展到小说、散文和学术。”n
从“单位人”到“无业游民”
大陆作家通常被纳入到单位制度里,中国作家协会系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单位。作家协会有作协会员和专业作家两个层面:前者是身份认证,主要看申请者在官方认可的出版物上的创作成果,名额没有严格限制;后者是工作岗位,有固定薪水、福利保障,甚至可以分配住房、调动户口,名额极为有限。只有极少数作协会员,能够成为专业作家。80年代,作协会员曾是一种文化资本,但是随着文学的式微,逐渐失去了魅力。进入21世纪,经常出现作家退出作协的行为,但是退出作协的往往是作协会员,而非专业作家。即使专业作家退出作协,也是有选择性的,比如小说家李锐,公开宣称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但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李锐虽然退出了中国作家协会,但是他并没有退出山西作家协会,他还是山西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继续享有作家协会分配的房子,拿着专业作家的工资o。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以表明反对体制;同时保留地方专业作家身份,享有体制保障,这种行为说明部分作家的两难困境。
80年代,体制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诗人和作协之间的关系并不紧张,许德民、宋琳、王小龙、张烨、李彬勇、徐芳、孙晓刚、陈东东等都是上海作家协会会员p。但是他们都不是专业作家,相比先锋小说家和先锋批评家,先锋诗人成为专业作家往往需要在文学观念上做更大让步。也有诗人拒绝加入作家协会,比如王小龙曾经劝说默默参加上海作协的青年创作讲习班,结业之后可以加入作协,从工厂调到事业单位,在工厂图书馆工作的默默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q。不过,这并不意味他们和作协是绝缘的,1986年作协诗歌组为他和郑耀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80级)、王依群举办了一场诗歌演唱会。
不是专业作家的诗人,通常有着自己的工作单位。郁郁是最早一批离开单位的诗人之一,1987年他因为发起各种诗歌活动被单位辞退,虽然他强烈要求单位把他直接开除,却被告知单位对此并无发言权,是奉命而为r。进入90年代,更多的诗人陆续从“单位人”转变为“无业游民”。
张远山和周泽雄1984年同时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分别于上海体育运动专科学校和上海财经大学执教,1995年张远山辞职,后来周泽雄也辞职,他们都居家写作。陈东东1984年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最初在上海市第十一中学执教,1986年调至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史料室,这是一种公务员式的生活,1998年他辞职,成为“无业游民”。关于这次辞职,陈东东多次表示时间冲突是一个主要原因,他习惯于上午写作,可是上午必须在单位坐班,所以他曾假设如果上班时间是下午1点到8点,自己很有可能不会辞职s。陈东东与上海的关系若即若离,近年来时常于上海附近的江南小镇居住并且写作。丁丽英1989年从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在上海城建机械厂财务科任会计,1998年辞职。
在这些“无业游民”之中,只有陈东东、郁郁坚持以诗歌写作为主,张远山和周泽雄转而写作小说、随笔,丁丽英转而写作小说、剧本,亦曾成为上海作协的短期签约作家,近年来转而从事绘画。“无业游民”必须考虑生存问题,但是诗歌写作几乎无法获得经济回报。即使陈东东这种在当代中国诗歌史上不可或缺的诗人,依然表示:“靠写诗是无法养活自己的,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我得打点零工。”t他在诗歌之外,写作一些随笔和专栏文章。
从“单位人”到“无业游民”,诗人们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但是由于稿费制度的低廉、社会福利保障的匮乏,以及驻校作家、文学基金会、诗歌朗诵会这些文化机制的缺失,诗人始终无法摆脱后顾之忧。诗人和艺术家在身份上没有高下之分,但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两者命运迥异,诗人依然无法凭借诗歌生活,艺术家却凭借艺术作品成为“暴发户”。很多诗人改行从事艺术,许德民则在这个潮流之前,具有前瞻性地一边写作抽象诗,一边创作抽象画。
“下海”:诗人与商人的分合
在当代大陆的经济领域,存在一个特殊现象,即很多商人在80年代都是诗人,有的当时广为人知,有的当时默默无闻。这一方面是因为80年代处于诗坛的“春秋战国”时代,大学生不分专业,都会参与诗歌运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诗人常常具有商人的冒险精神,这种精神在农业国家是稀缺的。80年代的诗人有云游四方的习惯,即使双方从不相识,只要有过写诗的经历,往往一见如故。这种诗歌交流在无意之中锻炼了他们的游走和交往能力。
90年代诞生了众多“诗人书商”,以四川诗人为主,他们去北京从事民营出版。这种转变有着内在逻辑,因为这些诗人最初几乎都曾参与过民间诗刊的出版,只是民间诗刊无需刊号,民营出版则需要跟出版社合作,获得书号。
80年代的上海诗人,在1992年之后纷纷“下海”,但是转型为书商者并不多见,似乎只有张小波。张小波离开单位的时间比郁郁更早,1984年从华东师范大学毕业,被分配至江苏镇江文联,但只工作半年就回到上海,参与筹备《现代人报》,随后成为“无业游民”,并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入狱数年。1992年,他通过朱大可获得温瑞安武侠小说版权,掘得“第一桶金”,随后在北京从事民营出版,1996年以出版《中国可以说不》而著称,2009年又以出版《中国不高兴》再次获得关注,两本书都主张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反体制的诗人,转型为商人之后,与体制形成高度默契,这种现象并不鲜见。
除了“诗人书商”,“诗人房产商”和“诗人广告商”也成为一种现象。默默1989年初辞职,1996年从事房地产咨询顾问工作,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的“人,诗意地栖居”作为房产广告,成为房地产业的成功案例。王依群、叶青均从事广告工作。
此外,李彬勇、成茂朝、冰释之也以不同方式“下海”。李彬勇1983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先后在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上海大学任教,随后辞职,1989年去澳大利亚,1991年回国,后来先后涉足房产和广告,然后创业。成茂朝1984年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先是在上海唐山中学任教,随后辞职,创办服装公司。冰释之1987年从上海大学毕业,先是在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编辑校刊,随后辞职,南下从事广告、印务、展览等工作,创办公司,后来返回上海。
钱穆讲到明末遗民经商,表示“纯粹经商,便与学术文化事业脱离”u。这道出了士人经商的一个困境,虽然明清之际士商渐为一体,但是两者并重并非易事,需要有所侧重。诗人经商同样如此,张小波、李彬勇、成茂朝基本中止了诗歌写作,默默和冰释之也在90年代暂时停止诗歌写作,在 21世纪前后逐渐恢复,王依群则从诗人转型为摄影家。更大的困境是,由于市场尚未充分独立,诗人经商不仅要遵循商业思维,还要遵循体制思维,这就是一个自我规训的过程,诗人如果缺乏反思,将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进入21世纪,很多“下海”的诗人度过艰难的创业期,拥有了丰厚的经济资本,开始投资诗歌活动,一圆昔日诗歌梦想。这一方面对诗歌生态具有建设性作用,另一方面也制造了诗歌泡沫,并且存在以经济资本换取文化资本的现象,同样走向了诗歌的反面。
“跳槽”:媒体或大学
诗人面临两难境遇:成为“无业游民”,有了时间却为生存所累;成为商人,有了经济条件却没有时间或状态从事写作。
一些诗人通过“跳槽”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在闲暇和经济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曾任工厂团委书记的王小龙后来进入上海电视台,曾在中学任教的王寅进入《南方周末》,曾在华东师范大学执教的徐芳进入《解放日报》,韩国强进入《青年报》,韩博在90年代系大学在校生,此后进入媒体。
可以提供经济保障和文化身份的媒体,成为诗人的主要去处。此外,媒体的工作与诗人的写作具有一定的契合之处。“跳槽”媒体的诗人基本没有中断诗歌写作,同时进行其他艺术创作,如纪录片之于王小龙、摄影之于王寅、话剧之于韩博,有些创作与工作互相重合。但是,上海的媒体大都拥有单位制度的惯性思维,缺乏足够的开放性,具有独立意识的诗人要在媒体安身并非易事。陈先发毕业后回家乡安徽,后在新华社安徽分社供职。
除了媒体,大学也是诗人的容身之地,刘漫流、张烨分别在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已并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执教。大学一般可以保证充足的时间,但是薪水较低。从90年代后期开始,大学对学术论文的强调,使得诗人在大学往往处于边缘位置,年轻的诗人更是限于学历和科研的要求,几乎不太可能进入高校。成名诗人“跳槽”大学,是21世纪的后话,而且数量有限。从制度上说,大学设立驻校作家,才有可能缓解诗人和学院之间的冲突。
一些诗人进入政府机构,成为公务员。卓松盛在读大学期间,就决心放弃诗歌写作,专心经济研究,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共青团中央研究室。后来,他先后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供职。陆忆敏则从街道工作做起,先后在上海市徐汇区多家党政机构供职。成为公务员的诗人,基本都停止了诗歌写作或者不再参与诗歌活动。还有一些诗人在公司工作,如古冈供职于某石油公司,后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供职。
90年代的上海诗歌,处在一个低潮期,诗人主要在探索和城市、市场和体制的关系,并且在这三者之间徘徊。限于当时的环境,民刊只能勉强惨淡经营,甚至难以为继。这段时间,可以称为诗人的“隐居时代”。但从事各种职业的诗人们,大都没有中断与诗歌的关系。等到1999年前后,网络的出现改变了诗歌的格局,诗人们将陆续浮出水面。
【注释】
a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60页。
b此次纪念会颁发了“第三代诗人杰出贡献奖”:野夫、杨克、远村、陈朝华、丁翔、周墙、潘维、北魏、王琪博、梁健、海波、何拜伦,十二位获奖者均为当年没有参加大展的诗人。还颁发了“第三代诗歌功德奖”:黄怒波、石虎、刘丽安、麦城、胡建雄、万夏、潇潇、柔刚、远村、聂圣哲、李岱松、默默、歆菊、卢苇,十四位获奖者曾以不同方式资助诗歌。黄长怡:《已过20年,他们来相会》,《南方都市报》2006年11月26日。
c默默:《我们就是海市蜃楼——一个人的诗歌史:1979-1989》,诗生活网站,诗观点文库:http://www.poemlife.com/Wenku/wenku.asp?vNewsId=2189。
d 《本刊编辑与作者交流》,《星星》1987年第10期。
e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页。
f此处信息,蒙黄粱先生告知,谨致谢意。亦可参见孟浪:《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唐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g关于这种分歧,详见郁郁:《废墟上的瓷——〈大陆〉或与诗有关的人和事》(上篇:1976-1989),《大陆》纪念号,05、06、07期合刊(民刊,2008年6月)。
h冰释之:《冰释之郁郁孟浪和〈MN〉》,《门敲李冰:冰释之诗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195页。
i[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验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2-134页。
j刘苇:《背对时代的诗意——〈爱洛思诗丛〉总序》,《妙意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k刘漫流:《上海诗歌地理:时间在水里的版本》,《星星》 (下半月刊),2008年6月,第94-95页。
l钱穆:《国史大纲》 (修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50-851页。1989年春夏之交与明清之际截然不同,但是两个时代的士人心态亦有可作参照之处,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者赵园,在90年代转而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m刘漫流:《上海诗歌地理:时间在水里的版本》,《星星》(下半月刊),2008年6月,第95页。
n张远山:《艰难的反叛和漫长的告别:八十年代上海民间诗歌运动一瞥》,《博览群书》2003年第8期。
o杨舒:《专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我不知道作协有什么权力》,《凤凰周刊》2006年第34期。
p《上海作协八个会员小组分组名单》,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zx/2003/2003-08-02/1139.html。
q默默:《王小龙其人其事》,《星星》(下半月刊)2008年第2期。此文节选自《我们就是海市蜃楼——一个人的诗歌史:1979-1989》,但是王小龙劝说默默加入作协的情节在这一版本中不见踪影。
r郁郁:《废墟上的瓷——〈大陆〉或与诗有关的人和事》(上篇:1976-1989),《大陆》纪念号,05、06、07期合刊(民刊,2008年6月),第217页。
s蔡逍:《陈东东访谈录:它们只是诗歌,现代汉语的诗歌……》,《新诗》第6辑(民刊,2004年12月)。
t唐骋华:《暗夜独行 一种存在以诗为名》,《生活周刊》2009年9月17日。
u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下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8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