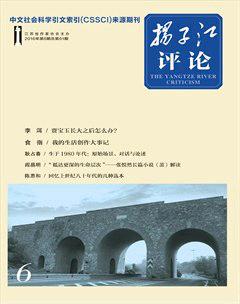启蒙焦虑与文化批判
台湾新旧文学论战以来,乡土文学以其启蒙主义的精神和现实主义的特质成为台湾知识分子用以揭橥时弊、批判现实的审美载体,无论这种文学思潮处于高峰抑或低谷,至今仍方兴未艾。1990年代以前,台湾乡土文学曾表现为以赖和、朱点人、杨逵、吕赫若等为代表的抗日反殖、民族解放主题,也曾表现为以陈映真、黄春明、杨青矗、王拓等为代表的阶级关怀、反抗资本压迫主题,甚至论及1980年代分裂后的乡土文学各阵营,其审美诉求都与社会现实和大众民生发生密切关系。一方面,这些时期的乡土文学大多凭借深刻的批判精神和真挚的现实关怀对台湾人民在20世纪所经历的种种苦难作了较为细致深入的反映;另一方面,它以自身裹挟的现代意识与民主思想,对于随后展开的台湾社会体制变革,有着更为深刻的启蒙意义与社会意义。因而,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过程呈现出自发→自为→自由的文学样貌。“自发”是源于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身份觉醒所激发的乡土作家民族主义的天然性格;“自为”是源于乡土作家认识到台湾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现代文明和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人性扭曲以及劳动异化;“自由”是源于“高雄事件”之后,国民党政权面对以市民阶层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不断壮大的事实,无力扭转“党外政治运动”的发展趋势,逐渐放松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钳制,乡土作家能够在较为轻松的社会氛围中表达各自不同的思想倾向,出现了“自由”意识形态的文学表现。
哈贝马斯在谈及“公共领域”时认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a。由此可见,公共领域是相对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公共空间,我们可以将它视为一种文化上的舆论形态,既可以有助于政治权力的运行,使其更为通畅与稳定,也可以制衡这种权力运行,使其迫于某种压力做出妥协。如果我们将1990年代以前的台湾乡土文学视为一种公共领域的话语资源,那么乡土作家对它的争取与塑造就是试图从启蒙的高度获得一条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的途径,以此表达自己对现存社会体制的思考与意见。但需要指出的是,公共领域的开放性使其极易受到统治政权或大众传媒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受迫转型”的情况。台湾解严前后,民族与民主诉求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见诸乡土文学,而作为“利益专门化”政治集团的本土势力也充分利用这一时机,以报纸、杂志、新闻媒介、学术团体等形式人为操纵乡土文学的转型,使其出现了鲜明的“本土化”趋势,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以工具理性为特征的系统对以交往理性为基础的生活世界的侵入,即‘生活世界的殖民化”b。如果说西方审美现代性被启蒙现代性制度化的过程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广泛渗透表现出对现行体制的认可与依赖,从而消解了自身的颠覆性与批判性,那么,台湾乡土文学被制度化的最大特征就是在“启蒙”幌子的迎风高挑中,“乡土”在基本实现了民族与民主的权力伸张后,却陷入了本质主义的“本土”话语怪圈,沦为民粹政治的附庸而丧失了根本的自主与活力。
1990年代以来,由于台湾社会语境的持续衍异(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最终完成、经济发展环境的相对宽松、两岸关系的正常化趋势等)以及西方“后学”思潮的不断涌入,台湾文坛开始审视并反思原有乡土文学的启蒙困境,继而思考如何以一种多元化与微观化的叙述模式超越以往的文学泛政治化倾向,并在这种文学范式的自觉转换中实现对“启蒙”之“再启蒙”、“批判”之“再批判”的文化格局。这其中既有“都市文学”的大胆尝试也有“现代主义”的再度出发,而台湾后乡土文学的出现无疑是这一新时代文学潮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世代乡土作家依循重观历史与建构现实的思想进路,将原本凝聚在“乡土”中的国族神话降格为对世俗生活的当下想象,书写“乡土”成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与找寻在地时空、寻求自我定位的“捡拾”过程。由是而观,后乡土文学叙事境界的提高是在降低自身社会话语地位的现实中得以实现,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仍接续了原有乡土文学的批判精神与人文情怀,但以往“乡土”过度热衷的启蒙意义已逐步由“后乡土”积极置前的传统文化再现、宗教信仰复归以及现代性批判的微观化重构等多元文化价值所取代。台湾后乡土文学对公共领域话语权的再争夺,至少造成众声喧哗的热闹景象,有效阻止了文学收编带来的文化领域权力结构的集中化与同一化,消解了人们对台湾社会发展的单一性盲点与短视行为,有助于形成更具积极意义的发散性思考,也标志着其对以往乡土文学的最终超越。
一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这个生命共同体最基本的精神底蕴,同时也形构出民族存在与民族延续的外在表象特征。传统文化的形成离不开民族发展历程中的环境地理因素、人文风貌背景以及断续有度的时代精神折射,其一旦成为一种精神向度沉淀在所有成员的集体无意识深处,就会演变为一种潜移默化的社会规范力量,通过主体行为缓缓溢出,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指导”或“纠正”的调控作用。以往台湾乡土文学由于肩负反封建、反殖民、反压迫、反剥削以及建立新文学传统的时代任务,无暇顾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梳理与发掘,从而将其笼统视为阻碍现代性发展的负面因素加以批判拒斥或置之不理。应当说,彼时的历史背景规定了台湾乡土文学的发展方向,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制约着它无法在追逐启蒙现代性的同时又去思考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
这种情景在1990年代以后的台湾后乡土文学中发生了根本改变。一方面,随着台湾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的步伐加快,新世代乡土作家发现原本作为最高价值目标去追逐与向往的现代文明,虽然带来了理想中的生活进步与物质丰富,但同时也造成了对人的精神世界的挤压与侵占,逐渐以“商品拜物教”或“消费拜物教”的形式吞噬了人们对除自身以外时空维度思考的兴趣与动力,并消解或异化了原已具有的种种人格仪范。一时间,人们似乎忘记了欲望满足之外更为重要的生命价值与存在意义,面临着被彻底物化的危险。正是由于看到了工具理性、技术理性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人为灾难,后乡土文学才转而向传统文化取法,以期借用“文化同置”的策略,促使人们以陌生化的传统文化视角重新审视现实社会中的自我行为表现。至此,传统文化在后乡土文学中以“文化他者”的形象为世俗社会中的实践主体提供了一面反思与启悟的铜镜,它以鲜明的内在性、自洽性、和谐性、普泛性为现实景观中对物质文明的狂热崇拜、操控欲望带来的自私自利、科层制造成的切割感与机械感等现象开启了一条观照与修补的途径。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后乡土文学在传统文化领域的再度出发,已然超越了以往乡土文学以启蒙现代性为是的绝对审美标准,从单一僵化的“启蒙”思维中脱身而出,为其自身的审美张力拓展了新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从现代性的“重层”性质来看,在启蒙现代性基本实现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在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的层面实现民族认同与身份定位,也已成为众多文化工作者思考的重点,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寻根与文化自觉的热潮。对此叶舒宪认为,“人作为世界上唯一的文化生物物种,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的珍视和保存、传承,其实也就是人对自己的种群的生存资源和生存方式的自觉延续。这种文化自觉正是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刺激之下日渐成熟起来”c。毋庸置疑,台湾后乡土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重新挖掘自然也有这方面的审美意图。需要指出的是,后乡土文学的这种文化自觉并不同于以往台湾乡土文学中狭隘的“本土化”认同,而是在更高层次上表露出区域人民尝试在世界发展大潮中进行自我文化标识,并对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发展以及现代性的丰富维度作出自己的积极探索与深度回应,从而具备了较为突出的文化生态学意义。
小说《缝》是台湾后乡土作家张耀升的代表作品之一,主要探讨了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在现代商业社会中的式微与崩塌,却又巧妙地通过第三代的叙事视角使之得以延续与传承,表现出作者试图以传统伦理道德对人性恶的一面进行救赎的期望。小说名为“缝”,无疑是一种“缝合”的期盼,既试图用人伦情感缝合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又希望缝合传统与现代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作为对儿女们不良对待的绝望反抗,奶奶的最终去世似乎意味着“缝合”努力的失败与无望,但良知尚存的父亲由此变成了一个无法自解的疯子,而作为第三代的“我”则永远感念和奶奶之间的真挚情感与点滴回忆,此处作者显然又在冥冥之中昭示了传统文化的规训意味与引导力量。除此之外,李仪婷作为台湾新世代女性作家中的佼佼者,在小说《邮路》中又为我们展现了另一种不同的文化关怀。小说讲述了一个名叫“布马”的布农族青年,因为考取了公职邮递员而成为部族的骄傲。在一次到部落的邮件投递中由于驾驶不慎跌落并不很高的山崖,却由于手机信号不畅受困于此。小说篇幅不长,却珠玑处处。百步蛇原是布农族的神兽,却在布马的口中成为对破烂山路的咒骂对象;布农族人原是野外生存、徒步狩猎的好手,但身处困境的布马却怎么也攀登不上并不陡峭的山崖;在送递的包裹中,布马发现了大量的手机,于是开始逐一拨打试图向外求助……小说的企图在于,作者以现实世界的生活景观(如部落年青人口的大量流失、手机通话代替了手写通信、城镇工作取代了狩猎生活等)覆盖原本传统神秘的部落景观,暗示了原民文化在没落与衰败的同时也彻底丧失了原有的凝聚与约束力量。原住民早已不是以前的原住民,族群文化的消泯与同化使他们变为徒有原住民外貌的汉人,“原住民”身份成了幻想中自我形构的图腾。在作者的精心安排下,深谙现代生活节奏的布马陷入尴尬处境,面对加持于身的传统布农服饰他欲哭无泪,猎人般的矫健身姿在他的身上难觅踪影,祖灵的血液虽然还在血管流淌,但身心已然被现代社会收编。此处,作者显然使用了“文化同置”的招数,一面是摆在布马面前大量无法使用的手机,一面是由于机能退化而摆脱不了的现实困境,孰是孰非,已昭然若揭。李仪婷在小说中为以原住民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设置出一种精神困境:做出改变,将被世俗同构,保持传统,则意味孤守青灯,如何面对,需要我们共同抉择。
台湾后乡土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发掘并不仅限于对启蒙现代性的审视与反省,其附加意义还在于反思过程中对以消费文化为代表的文化内涵的空洞化与概念化做出回应。现代社会中,由于资本的逐利性质、人们的消费心理以及传播媒体的符码化介入,人的生活意义被完全抽空。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现实世界中的能指与所指已产生前所未有的断裂,其参照物也在符号化的世界中消失不见。在此背景下,文化本质发生位移,已由以往的现实性价值指涉演变为流行于宣传口号中的虚幻概念。文化形态的“堕落”表现,致使身处消费时代的人们开始漠视文化自身的规范性意义,而去疯狂追逐一种名叫“文化产品”的无根替代物。后乡土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与再现,形成了“文化价值”在现实生活中的有效显现,让人们在冷漠荒芜的符号世界中重新感受到来自人类自身经验的温暖关怀,而这种创作意图在吴丰秋的《后山日先照》、吕则之的《寻找一座岛屿》、舞鹤的《思索阿邦·卡露斯》、甘耀明的《邦查女孩》、杨富闵的《花甲男孩》等文学作品中都不难发现。
二
宗教信仰的形成来自于人对自身以及世界的起源和存在做出的形而上阐释,是人类在进行物质生产的同时,由于精神和心理上的需要而展开的思维建构活动。这种价值体系的建立为人类社会塑造了玄秘澄明的彼岸世界,以“天启”或“缘起”的形式为人的精神或灵魂提供了一块安息之地,因此往往带有浓郁的人文关怀特质。然而由于权力机制的缺陷以及宗法教义的僵化,东西方宗教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步入困境。不堪重负的压迫终于引发革命的力量,西方现代性的出现本质上就是源于对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的反抗与背叛,它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运行机制与文化模式为目的,将科学与理性标榜为核心价值,并力图将宗教因素完全排斥在这种体系之外,马克斯·韦伯曾将之称为资本主义兴起过程中的“袪魅”。无独有偶,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台湾乡土文学在发轫之初,也将“赛先生”的大旗高高擎起,高呼“启发民智”与“破除迷信”的口号,这一点从当时知识分子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创办宗旨中不难发现。从此,台湾乡土文学的“任务首在‘反映人生。……传统的怪力乱神自然难有一席之地。鬼魅被视为封建迷信,颓废想象,与‘现代的知识论和意识形态扞格不入”d。
台湾乡土文学选择与宗教信仰划清界限源于在特殊时代环境中肩负的种种启蒙任务,试图通过对“袪魅”的提倡,以“人”的意义呼唤台湾大众主体价值的觉醒,继而摆脱精神束缚,在社会的不公现实中敢于展现抵抗的姿态。但在客观层面确也完全摒弃了宗教信仰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人性价值,如真诚、向善、友爱、不争、克己等。随着台湾社会发展的突飞猛进,启蒙现代性的各种核心价值目标已基本实现,迎来了丰衣足食的人们却发现一个不受任何信仰约束的人类社会竟然如此可怕,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享乐与虚无的放纵蔓延、道德伦理的彻底崩塌,这一切都源于“人”的价值更确切地说是“人”的欲望的无限膨胀,而失去了对“他者”的敬畏。正是由于洞察到这种精神维度缺失后的灾难性后果,台湾后乡土文学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宣告了宗教信仰的回归。翻阅众多后乡土文学作品,大量宗教因素渗入其中,其主观意图当然不是为了复辟封建迷信而说神道鬼,而是后乡土作家敏锐地发现在天、地、人的宇宙架构体系中,人只居于其中一维,无限度地扩展人类唯我认知,只会反衬出人类的渺小与无知,因此需要重估人与神的关系以及人在整体宇宙系统中的地位。宗教信仰在后乡土文学中复出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以建构一种带有反思与批判性质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以人文关怀与人文教育的角度促使人们从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泥潭中抽身而出,在功利的世俗社会中重新发现“神圣”的存在,以追加的方式在物质世界之上重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向度,以便重新树立健康丰满的人格形象。另一方面,“复魅”书写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审美手段,还有助于后乡土作家表达在“现实主义”规范中难以述说的“存在”之思。通过作者巧妙的叙事安排,小说文本中宗教现象的出现总有一些合理阐释,它承担起作者交付的某种精神上或心理上的指代任务,这些叙事企图可能是某些情结的象征,也可能是某种生活的隐喻,从而强化了后乡土文学作品中的多元价值和模糊语义。
《林秀子一家》是台湾作家阮庆岳的长篇小说,以独立成章的形式分别叙述了主人公林秀子及其女儿淑美、淑丽,儿子凯旋一家四口在情感交流、人际交往、宗教救赎等方面的种种际遇,这其中既有每个人不同的生活经历,也有最终的汇聚交集。林秀子自小由于父亲的虐待被外婆抱养,在生活的历练中形成了坚韧不屈的性格。成家后面对丈夫的弃家出走和日常生计,最终以开庙为生养活一家老小。由此,宗教背景的种种因与果、爱与恨、妄与真便在每个家庭成员身上以不同的形式得以诠释。无论是林秀子既以宗教立身也以布道为生,或是淑美以个人牺牲超度他人孽缘,还是淑丽以“海纳百川”的姿态用身体当做道义的布施给人以灵魂安慰,甚至凯旋“圣婴”般普渡众生的行为表现,作者都在反复强调一件事情:这世界缺少信仰与大爱。林秀子供奉的是金母娘娘,这是一种源于道教谱系的台湾民间宗教,其“上善若水”的宗教思想与“以理化情”的行为操守就是支撑这种“圣洁爱”的坚实思想基础。小说试图通过对善与恶辩证关系的讨论告诉读者,桃源般的理想世界并不遥远,不用长途跋涉到圣地朝拜或死后等待天国的召唤,它就在我们面前,只要每个人都能放弃贪婪的索取心和过度的占有欲,现实世界自然就会充满“神圣”与“爱”的光辉。这种对宗教信仰的求解,在袁哲生那里又产生了新的演绎。《天顶的父》是作者颇具代表性一篇小说,主要以“我”的视角讲述了发生在乡土之上有关省籍隔阂、宗教传播以及在地信仰的奇谭趣事。作者在小说中将西方基督教与本土的丐帮作了同质化处理,一方面对外来宗教进行了别有意味的亵渎与调侃,另一方面也特意对原本低人一等的乞丐世界作了大幅度的神格升等。乞丐头子空茂央仔获得了几乎与耶稣等同的神圣地位,他友爱邻里,关爱他人,乐于帮助弱小,他似乎也居于彼岸世界,拥有操鬼驾神的特殊能力,吸引无数少年心向往之,以加入丐帮为生平志向。应该说,作者此处皈依的是以民间文化为表征的在地宗教信仰,它代表着一种带有精神性趋向的价值旨归,无论是外来亦或本地的人、鬼、神,都能在这种具有巨大包容性与和谐性的文化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实现了对不同省籍、不同身份、不同种族、不同阶级的超越与融合。
纵观台湾后乡土文学中的“复魅”表现,还有如甘耀明的《伯公讨妾》、舞鹤的《拾骨》、宋泽莱的《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吴明益的《虎爷》、郑清文的《天灯·母亲》等较具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显然都寄予着作者的良苦用心,即试图引导读者去发现在现实生活之上更高层次的生命感悟,并希望以这种深刻的观世视角翻转当下的庸俗化世态。当然,这种文学与宗教的深层交融也暗含着谨慎的“资源意识”与“对话态度”,后乡土作家清醒地认识到,当人类社会的相互依存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不仅将文学与宗教的互动精力集中在人类如何理解世界和它的意义,还要关注在原初原则的基础上人对自己、对他人、对自然该如何行动,并以此超越由文化虚无化和文化符号化带来的妨碍和扭曲人们通向最初原则的单边思维习惯。e
三
社会学意义上的微观视域主要来自于福柯、德勒兹、加塔利、利奥塔等西方学者提出的后现代微观政治学理论,认为对现代性意义的分析应该从从中心化的宏观权力转向多维度的微观权力,明确反对完整历史观和宏大叙事论,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不连续性曾是历史学家负责从历史中删掉的零落时间的印迹。而今不连续性却成为了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f。这种崭新的思维范式也为台湾后乡土文学的创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与逻辑支点。我们知道,以往台湾乡土文学秉承传统现实主义风格,惯于采纳社会发展的宏大视野,围绕时代中心议题展开文学表述,不断将个体价值观与世界观依附于经典社会理论所关注的国族想象,其倡导的乡土现代性带有本源意义上的纠结与建构,既会在受挤压时产生抗力也会在得自由后陷入僵化。后乡土作家启灵于微观政治学理论,当他们以差异、边缘、世俗的视角重新审视惯以标榜科学与理性的启蒙现代性时,发现表面上因现代化、科学化、理性化而欣欣向荣的现代社会,却在文化霸权、党同伐异、物欲横流的扭曲撕扯中变得支离破碎、丑态丛生。原本各种美好的事物之间被一种欺骗与虚假的关系勾联着,这种异化的纽带又被长期积淀下来的民粹传统和将之作为操控工具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巩固与推崇,不明就里的人们就在这种“现代化”的潮流中随波逐流,成为物质化、阶层化、等级化的对象而无法分辨真与伪、恶与善、美与丑。微观视域的新视角使台湾后乡土作家获得一种醍醐灌顶式的启示,即要想恢复美好事物的本真面目,粉碎乡土之上的虚假图像,使真实的乡土现实得以呈现,就必须打破这种用以链接个体、板结整体的虚伪层级关系,将目光从宏观方向转向微观领域,关注个体的自由成长与发展,并将它们以忠于自然本性的方式结合起来,以期揭示出一个全新的历史真貌g。源于对微观视域的自觉养成,台湾后乡土文学得以将对现代性批判的触角延伸到乡土生活的方方面面,试图通过庖丁解牛式的探索找寻真正困扰“人”之发展的问题与危机。
舞鹤在小说《逃兵二哥》中以“我”的视角讲述了军队中的生活经历。“我”由于接受不了部队中的种种陋习与歧视而又无法逃脱,于是自愿去猪圈养猪,成为一名“养猪工兵”。在猪圈工作时,“我”产生意识流动,军队变为国家的大阳具,任何男性的小阳具都要阳痿在大阳具的柄垂之下。这种看似荒唐的思维,却深刻揭示出台湾地区兵役制度的弊端以及军队内部的黑暗。台湾施行以强制性义务兵制度为主的兵役制度,规定年龄达到一定标准的青年男子必须服役,这也是作者在文中所说的,“兵役制度是一个大王八,必要强奸每一个处男”。在这种法律制度面前,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沦为国家机器的工具,在以“大阳具”为象征的军队淫威下逆来顺受,而部队里的思想禁锢与黑白颠倒也就使其成为“养人如养猪”的“猪圈”。在舞鹤笔下,以边缘化视角来表现现实世界的扭曲和人的痛苦是揭示历史真实与启蒙本质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超越自我、追求本真存在的重要途径。也许在舞鹤看来,微观视域中的荒诞情节会“倾全力于基本处境,同社会现实主义剧作家一样与社会密切相关,由于它不反映时事的偏见,不受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所以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h。《蓝色项圈》和《友达》是张耀升创作的两篇小说,由于连贯的故事内容和相同的叙事人物,我们可以将其看做姊妹篇或一部小说的上下部分。在这两篇小说中,都有一个共同的主人公——林友达,故事也即从友达在学校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展开。通过友达与“我”、阿文、父亲等人的纠葛关系,我们发现他的性格特征无疑具有多面性和分裂性,这和其所处人生阶段应该具有的思维与表现格格不入,甚至背道而驰。原本应该单纯善良、勤奋好学、怀抱远大理想的在校青年学子,却变成了势利、阴暗、自虐、算计的无良少年。针对这惨痛的事实,作者径直指出造成“吃人”现象的根源就是泛政治格局下官僚等级体制在台湾教育界的种种表现。两篇小说中的林友达一直在学校中过得十分压抑与痛苦,为了获取他人的赞赏与注意,他就像是为别人而活的机器,完全没有自我,只能依靠本能生存。其实远远不止林友达一个人,在庸俗价值观的教育体制下,阿文、“我”以及其他孩子都摆脱不掉悲剧的命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学校校长的发言中还提及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自由。正是这种所谓的“自由”使得孩子们就像监狱中的囚徒,成为只会相互攀比、倾轧的傀儡,他们的天性被无情地扼杀,在这里,取得成功和自缢身亡被残酷地划上了等号,而叙事人物的悲惨结局也带给世人巨大的警醒与批判力量。
现代性批判的微观化重构为台湾后乡土文学带来了足够的动力与活力,它不再游离于乡土之外以悲天悯人的姿态去找寻推动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助力,而是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生命脉动中去揭示现代性流行过后留下的条条伤痕。这里既有不合理兵役制度与教育制度带给人性的戕害(除上述示例还有如许荣哲的《那年夏天》),也有性别歧视与省籍隔阂造成的伦理悲剧(如李昂的《看得见的鬼》),还有保守思维与族群矛盾带来的社会问题(如舞鹤的《余生》),而后乡土文学的目标或任务就是正告人们,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力这些象征美好乡土家园的“宏观政治理念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转化为内在的文化机理,才不会变成一种抽象的口号和普遍化的宏大叙事”i。
对启蒙的焦虑和由此展开的文化批判,证明台湾后乡土文学已完成自我蜕变并已具备较为成熟的多元文化品格,这种宝贵的审美品性使其能够在狂热的历史线性发展中保持冷静头脑,适时变身为时代进步论的怀疑者,以“不和谐”的姿态站在社会发展的对立面,转而成为渴望获取心灵慰藉、重返精神家园的现代人可资倚重的重要思想资源。
【注释】
a[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b 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07页。
c叶舒宪:《现代性危机与文化寻根》,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
d[美]王德威:《魂兮归来》,《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e[美]列奥纳多·斯威德勒,保罗·莫泽:《全球对话时代的宗教学》,朱晓红,沈亮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18-226页。
f[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页。
g吴鵾:《台湾后乡土文学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
h[英]阿诺德·P·欣契利夫:《荒诞派》,樊高月译,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
i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