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艮第之旅:光、美酒和革命
周轶君
“大家”阅读
互联网时代,读者并不缺乏信息,但一些真正具有传播价值的内容,却往往淹没于信息洪流之中。力求将最有价值的信息,最有锐度、温度、深度和多维度的思考与表达,最值得阅读的网络优质原创内容,快速呈现给读者,是《世界文化》与腾讯《大家》建立合作的初衷与共同努力的方向。【“大家”阅读】每期将臻选《大家》所汇聚的中文圈知名学者、专栏作家的最新文章,与读者分享“大家”眼中的“世界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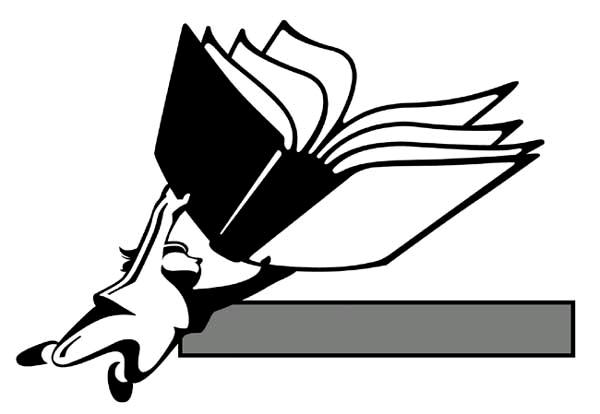
一
它就在那里。
车止于山脚。烈日下石阶发白,所有人必须徒步。路程很短,并不辛苦。但登顶而见,幡然喜悦。
我之前并不知道它,甚至连影像都没有看过。世间流传更广的,是追随者安藤忠雄(日本建筑师)的“光之教堂”。第一次在印刷品上看到安藤的版本,黑暗与光明极强的反差,过目难忘。然而,印刷品见了多次,再经网络传播,竟似洗去了灵光,感动变得迟钝。
勒·柯布西耶(法国20世纪著名建筑师)的原版,立于布勒芒山顶,包裹在白色砂石墙里,于我的无知,像一份静待拆开的礼物。它的外观,已经让人不安起来——难以名状,各个版块的形状无法套用既有的词汇——长、方,还是圆?不是扎哈·哈迪德的奇巧乖张,但每一条线在即将归入“正常”时,荡开去。
满目青山,脚下是开阔的平原与山谷。千年来,朗香礼拜堂接受四方信徒朝圣。1955 年,柯布西耶建成朗香教堂前,这个山头早就出现过崇拜圣母玛丽亚的天主教圣殿,但先后毁坏。“二战”中,布勒芒山居高临下的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几经易帜,死伤枕藉,教堂亦遭炮轰。战后自然要讨论重建。

门前停了几秒,终于屏息直入。光,彩色的光,满室倾泻。同行的人泽被光芒,幻化成图景的一部分。临窗祷告的人或坐或立,转动身形,好像画框里的流沙。原来石墙上不规则的彩色小窗,有如筛子上的小孔,入内无门的光寻到出口,用劲力气穿透。
朗香教堂重建委员会找到柯布西耶的时候,他63岁,名满天下,也饱受争议。刚刚完成的马赛公寓,获得“人性、纯粹、代表未来”的褒奖;而负面评价则是,“他要把法国人塞进兔子窝”。
来自边界另一边、瑞士法语区的柯布西耶成长于新教家庭,曾经批评天主教教会是“死掉的机构”。这样的人来设计天主教堂?
柯布西耶的初稿交上来,委员会中有人震怒:“这不是清真寺吗?我们的玛丽亚哪里去了?”伊斯兰教不崇拜偶像,清真寺四壁无物。柯布西耶的草图建构了这样的空旷感,不知是否跟他早年游历中东有关。委员会中亦有人力保这个方案,说柯布西耶的特点在于“洞察人性,直觉上帝”。新教信仰虽然不拜圣母玛丽亚,柯布西耶却是个孝子,90多岁的母亲非常虔诚。
眼睛适应了光线,慢慢举头,会看到墙壁上方、窗台上的圣母玛丽亚。那是一尊最传统、最具体的怀抱圣婴的小雕像。低角度的晨光进来时,她会在地面投下长长的影子,远远大于实体,在观者心头一击。
如有神迹。以轮廓、空灵来构建神明,让我想起一位英国友人从阿富汗巴米扬发来的邮件:“……远远望去,虽然大佛炸碎了,但塔利班没有想到,山体上凿出的拱型神龛还在,晨光雨雾,看不太真切,那个硕大的轮廓之下,你觉得大佛仍在那里,甚至在想象中变得更大,更震撼了。”
柯布西耶并没有排斥玛丽亚。相反,在修建过程中,他说自己理解了玛丽亚故事中人性的优雅、光辉与悲剧。在一扇蓝色的玻璃窗上,他手书:“我迎接你,玛丽亚。”
除了建筑设计,柯布西耶擅绘画、雕塑。朗香教堂内外装饰,就像他随手一撒,或平面或立体的艺术品恰到其位。
我在三个小祷告区前停留最久。圆弧线内凹,高处划开一线小窗,掷下光,在砂石面上漾开,轻轻触及燃烧的一支白蜡焰火尖。面壁,沉思,还是替代天主教堂里传统的忏悔室?
在柯布西耶的建筑之前,这里早流传着种种神迹。相传19世纪,一名被土耳其抓获的法国士兵在狱中等待死刑的前一晚,向守护家乡的朗香教堂祷告,竟一夜之间由天使们送回故地。
奇迹流传,巩固天主教会威望。所以,印度特丽莎修女封圣首先要鉴定奇迹是否属实,比如,她本人的触摸甚至她的画像,是否治愈了绝症病人。特丽莎修女曾经历信仰“黑暗期”,一度觉得自己离上帝越来越远,孤独而痛苦。那段时期持续了30年。16世纪就有人创造“属灵的黑夜”这个词,指历史上灵性大师成长过程中遭遇的信仰危机。但俗世无神论者揶揄特丽莎,“像乡村西部音乐中的妇人,拿着一个火把等丈夫回家,但她丈夫离家去买包香烟后,30年也没有再回来”。特丽莎早年宣称受到神的召唤,“来吧,来吧,带我到穷人的中心去”,由此放弃教师职业,到贫民窟服务。而度过信仰黑暗期的方式,别无选择的,是继续在地上行公义。
我在加尔各答遇见过一个40年前追随特丽莎的志愿者,如今他是个富翁。关于那些争论,他摆摆手:“特丽莎修女教会了我人的尊严。”
神之光辉,若没有人的义事支撑,如同印刷品上的光之教堂,灵光熄灭。
望不见神的时候,人坚持行公义,这不正是“奇迹”吗?
二
朗香之后,沿浮日与汝拉山脉之间继续走,就到了勃艮第。
正如有江河处文化荟萃,葡萄酒产地农业富饶,艺术丰盛。古罗马人传播酿酒技术,12世纪天主教修隐会建起葡萄园,再加上黄金等矿产,勃艮第曾经是欧洲最富有的地区,领土绵延到今日意大利西北和卢森堡。绵长鲜艳的历史,留下千层宫阙、名画珠宝。
木心假托托尔斯泰的话说:“我们到陌生城市,还不是凭几个建筑物的尖顶来识别么,后日离开了,记得起的也就只几个尖顶。”
好吧,Hotel-Dieu无疑是勃艮第最难忘记的那个尖顶。黄、绿、棕、黑四色琉璃盖顶,12世纪以来只有法国王室可以用这样的颜色。朗香礼拜堂以水泥承托拙朴厚重,Hotel-Dieu则是灵巧秀丽的木建筑。最令人惊叹的是,王室屋顶、建筑杰作下面,安抚的是衣不蔽体、奄奄一息的穷人病者。
Hotel,在今天的英文中指“酒店”,但在拉丁语和古法语中与“医院”(Hospital)同源。“热情好客”叫Hospitality,原意是医院向病人张开怀抱。Hotel-Dieu就是“上帝的医院”,上帝的怀抱。

1376年,Nicolas Rolin生于富庶人家,结了三次婚,每次都是贵族联姻,其中一次还让他跟“巴黎显贵”攀上了亲。不过,身为勃艮第执政官,他又跟法国签订协议,维护公国独立。究竟是出于什么目的,建造了王室屋顶下的“穷人大厅”?官方说法,1443年他与最后一任妻子、比他年轻27岁的Salins,为了“实践信仰”回报上帝。
这位慈善先生请来北方文艺复兴大师扬·范·艾克画像,他与圣母子出现在同一个画面,等高。这张收藏在卢浮宫的油画上,Rolin无法用“慈眉善目”描绘,倒是有些忧心忡忡,僵硬的面部线条,暗示他的强势,有时不惜动用霹雳手段。
Rolin做了40年勃艮第执政官。Hotel-Dieu医院院长的任命,规定世世代代都不许交给家族以外的人决定。我疑心Nicolas Rolin的善举,根本出自有钱有权者千百年来共有的焦虑:怎样才能不朽?然而,或许正是这样带点私心的行善,成就了Hotel-Dieu的可持续发展。Rolin除了自掏腰包,还寻找金主,又每年拍卖这里出产的葡萄酒,做成欧洲闻名的盛事,获利供给医院。Hotel-Dieu为穷人服务了500年。
“穷人大厅”容纳数十张床,都覆盖着红色帐幔,保护病人私密。医院中也有“自费医疗”部分,即富人病室。一室两三张床,日夜有人照料。室内布满油画、挂毯、铜器,更像是他们不愿离开的自家客厅。
神坛上方,有一幅罗希尔·范德魏登(早期尼德兰画家)受邀之作——《大天使打开天堂之门》。画悬高处,平时遮蔽,当有病人进入弥留之际,整个大厅点亮蜡烛,修女们俯身做最终祷告,神父这才命人打开画匣。于是,病人在人间见到的最后一幕,便是天堂之门大开。
法国大革命来了。天主教和封建贵族都是它的首要造反对象。18世纪的朗香教堂被砸,神职人员遣散,勃艮第大公的干尸从坟墓里刨出来,挫骨扬灰。Hotel-Dieu也有几幅画被打烂。
法国大革命,前半部似文艺复兴,人的自我价值惊醒;后半部分却尽显癫狂与人的毁灭。群众的热情不应该被赞美吗?攻占巴士底狱,那股决堤般的不满,抛头颅洒热血,暴力才能建构的自由,似乎都是“非如此不可”。可是,哪里才是底线?
从柯布西耶到特丽莎,再到Nicolas Rolin,都画下了一个 “人”字。不论动机为何,尊重、救护一个一个具体的人,皆为圣。相反,不论以何名义,来对一个人实施未经审判的加害,或者不公正的裁定,都是罪。如汉娜·阿伦特作为大屠杀受害者,在纽伦堡审判中发现,纳粹固然可恨,但以色列政府为了获得对犹太人建国的支持,把审判变成一场国际政治秀,不惜把德国纳粹所有的罪加在前纳粹军官阿道夫·艾曼希身上。阿伦特发声,被炮轰不合时宜。革命浪潮从来汹涌、粗放,正义的红线却纤细得若隐若现,很容易被淹没、冲垮。
Nicolas Rolin的不朽计划高瞻远瞩。虽然艺术品受损,医院因为收治穷人,建筑本身在大革命中并没有遭到更多冲击。
参观Hotel-Dieu的最后一部分是药馆。原来西医的开端,也是不断尝试各种天然成分的混合。药馆里陈列的瓶瓶罐罐,是数百年来欧洲人的摸索。
中西医并非截然对立,在古代还多有相似。中医号脉,中古传教士也擅此术。曾经在欧洲一个古老图书馆看到记录:一名神父、医生,也是诗人,受邀入王宫出诊。公爵有心寻开心,找来一名女子躲在帘子后头假扮自己。神父号脉相告:“公爵怀孕了。”几个月后,女子果然分娩,而当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有喜。
中国炼丹,欧洲炼金。从宋代起,通过炼丹让自己长生不老的希望减少了,炼丹术渐变为医疗化学。根据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说法,中古时期中国的药剂师已经成功将雌雄两性激素混合,制成比较纯净的晶体形态,治疗性功能衰退。
今日中西医民间之争,大多建立在对两种都理解不够、外加民族情感混杂的基础上。还是来看看Hotel-Dieu里,一名实用主义兼享乐主义医生,如何青史留名:
“在勃艮第,葡萄酒被用来消毒、疗伤。某手术医生每年都要求院方提供相当于今天250加仑的白葡萄酒。但被人发现,他喝掉的酒比用于伤口的多。于是,医院下令将酒与其他药品一起看管,钥匙和锁交予修女……”
三
“你握着的,是1亿年,少说也有300万年的海洋历史。”

Paul递过来一块石头。浅土色,微红,两面打磨光滑,诱人摩挲。平面上无数细小的软体挤在一起,如一张张尖叫的嘴,定格在直扑过来的海浪里,无可躲闪。翻过来看侧面:层层叠叠,石灰岩、陶土,再加上牡蛎壳等海洋生物化石,构成了勃艮第白葡萄酒产区Chablis独特的启莫里黏土地层。
勃艮第,与波尔多齐名的优质葡萄酒产地。谁更好?我宁可相信酒无第二。二者从葡萄到风味,只有差异,难论高低。
我对葡萄酒的喜爱,源于故事,口味有时还在其次。葡萄和人一样有天性,有身世,因地因时造化万千。什么样的土壤,什么样的时间,经了谁的手,遇到了什么样的调和……它实在适合安慰人生。
有一年在阿根廷,寻到高山上Malbec葡萄园。这种葡萄最早在法国种植,遍及波尔多至勃艮第北部。但后来长势不佳,收成惨淡。19世纪中期,经阿根廷官员移植南美,竟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淮南之橘,生于淮北”,一出怀才不遇、终遇伯乐的故事还没讲完。Malbec移居南美没多久,整个欧洲葡萄园都感染了源自北美的根瘤蚜虫病,毁坏殆尽,法国灾情尤为惨烈。最后在每一棵法国葡萄藤下,都嫁接了美国的葡萄苗,才抑制住疫情扩散。而Malbec栖息于南美高地,葡萄蚜虫无法企及,避开一场灾祸,也成了当今世界罕有的纯种葡萄。
Petit Chablis, Chablis, Premier Cru , Grand Cru……Paul斟上不同等级的本地葡萄酒。同属一地,又以坡度高低、阳光照射角度不同而风味迥然。
“这是个因祸得福的故事。那年葡萄质量不好,又歉收,不得不人手一颗颗捡出最好的葡萄来酿酒。精挑细选产量又小,反而成就了这一年特别而珍贵的味道。” Paul递过来2013年的Chablis。
酿造与土地——Paul说起葡萄园的开垦,于我心有戚戚:母亲的身体如同土地,孕育了葡萄的天分。新建葡萄园,头三年注定辛苦而无所获,恰如初生至3岁的孩子,付出无穷心力却看不见尽头。我的一个医生朋友打趣说,最好有商店出售3岁以上的小孩儿,还注明性格、喜好。孩子是我们酿造的葡萄酒。
Paul说中国市场口味偏甜, 更喜欢浓重的波尔多,微酸清冽的Chablis并不流行。“从前还有些中国旅行团光顾,最近游客都不见了。”“为什么呢?”我也注意到街上冷冷清清,没有夏季旅游旺盛的样子。“可能因为那些恐怖分子,现在谁还来法国。”真没想到除了巴黎,连东部小镇都殃及了。“他们可不喝葡萄酒。”“可能问题就在这里。”Paul苦笑,又斟上。
不同于波尔多的混合调配,勃艮第无论红白酒,惯用单一葡萄。用Paul的话来说,Chablis白葡萄酒“永远是百分百的霞多丽葡萄”,虽然霞多丽今天已经广泛种植于各地,但Chablis只能来自这里,因为土壤不同。一如临近勃艮第的香槟产区,世上再多气泡酒,只有产于香槟区的,才能冠以“香槟”的名字。
微曛中,我想,美国与法国,似乎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流行路线。美国的东西,几乎没有一样不能复制:迪斯尼、麦当劳、流行音乐。法国的东西,却是结结实实地离不开本土。其他地方出产的只能叫仿制。

——以印度昌迪加尔法院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