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给源文提供一种新的语言
——在二〇一六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汉学家翻译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瑞典]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
世界文学
文学翻译:给源文提供一种新的语言
——在二〇一六年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汉学家翻译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瑞典]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
如果要谈什么是可译的,什么是不可译的,或者谈一个译者对原文本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边界在哪里,那么我们首先必须考虑翻译是什么。不做翻译的人会有一种很常见的误解,以为翻译就是把某种语言的词句,替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同样词句。这样的想法,实际工作的译者必须迅速抛开。文学翻译做的是不同的事情:给原有的文本提供一个新的语言和一个不同文化语境的新形象,不仅抓住文本表面的情节和对话,而且还能把握其情感和风格,理解文字下面潜在的意义、暗示或者文字游戏。如果说在过去翻译经常被看作一种机器,像奴隶一样把原文本完整全面地转成新的语言,而不会用任何方式去影响或者改变原文(这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现在比较常见的看法是把翻译看作原文作者的创作伙伴,和原文作者一起写出这个作品的一个新版本。这个新版本也许在某些方面与原文有些不同,但是不一定就更差。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他的论文《译者的任务》(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里说的,“如果是在终极本质的意义上去努力追求和原文相同,那么没有任何翻译是可能的。因为,在其再生之后,原文经过了一种变化。如果没有一种转型,一种鲜活事物的更新,那么也就谈不上再生”。
翻译和作家的作用当然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作家是自由的,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而翻译无论如何必须尊重已经存在的文本,不能随便去改变、删掉或者添加。因为这个原因,这个理由,也许把翻译与活的音乐相比去更好:如果作家是个作曲家,写出了一部交响乐的总谱,那么翻译就是表演这部交响乐的乐队。不同的翻译就是不同的乐队,都可以对这部交响乐有自己的阐释,但出发点总是这个总谱。有些乐队会演奏得节奏快一点,而其他乐队可能慢一点;有些乐队会做出比较抒情的解释,而其他乐队会比较强有力,甚至咄咄逼人。此外,如果这个音乐家是生活在文艺复兴或者巴洛克时代,那么他的音乐是为那个时代的乐器写的,那些乐器和我们今天使用的乐器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一个现代乐队演奏这部作品的时候,今天的乐器会提供一种不一样的新的音调。不过,依然还是这个作曲家的作品构成了演奏的基础。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可以这么说,翻译不可能逐字逐句原原本本翻译一个文本,正是这个事实,让翻译的工作有了价值。因为要把一个故事、一首诗歌或者其他文学文本介绍给新的读者,翻译必须努力克服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这个过程的结果经常使得原文本要翻译成的那种语言也变得丰富起来,译文读者会得到新的洞见,得到新的知识。就是说,翻译不仅是一种尝试,把陌生的语言塞进一件新的语言的衣服里,而且也是一种测验,测试出目标语言可能做到什么。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一种测试可能使得目标语言的文学也丰富起来,有了新的故事和思想,目标语言本身也有了发展。我认为,现代汉语文学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无论从语言上还是文学上它都受到了外来文学的促进。
有一派翻译认为一个译本就是要“陌生化”,或者叫“外国化”,方法就是要尽量保持原文的结构。我个人不属于这个派别。“陌生化”常常导致一种夸张的异国情调,制造出读者和译文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往往让读者失去阅读兴趣,而不是引起阅读的兴趣。我认为,一个在原文语境里容易接受的、有日常生活特色的文本,不应该成为一个奇怪的、难以琢磨的译本。如果保持原文术语,而实际上在目标语言里有完全相同的或者非常接近的同义词,那我也看不到这么做有什么意义。比如说,把奶奶依然翻译为Nainai,而不翻译成瑞典文的Farmor,或者把伯伯依然翻译成Bobo,而不是瑞典语的Farbror,以为那样就能制造出一种比较“中国式”的感觉。同时,我也不认为,作为译者,总是要把原文本土化。在把中文翻译成某种欧洲语言的时候,这也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中文文化语境本身是很不一样的,是难以在欧洲做到本土化的。此外,还有些原文本的翻译,要求在目标文本中做些实验和发展。这里和原文语言的难度有一种联系:如果作家利用原文语言可能性的程度越高,那么译者在目标语言也必须做到的程度也越高。所以,译者对原文语言掌握得好是不够的,如果要能够再现出和作家在原文里达到的语言效果,那么译者必须对自己要翻译成的语言,对这种语言的可能性,也得有良好的感觉。
在瑞典,有译者谈到过翻译有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可以称为真实层次(和中国译者谈到的“信、达、雅”的“信”差不多),就是说,原文的词语、表达方式和象征等等,都必须完全真实地转到译文里去。这可以包括韵律节奏和语法结构,或者说在一首诗歌里某些词安排在句尾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作家的意愿是这首诗要这样来结尾。尤其是最后这个特点,当我们把中文翻译成欧洲语言的时候就不那么简单,因为原文和译文有完全不同的句子构造。
第二个层次可以叫作等量层次,在这个层次里原文的某些成语可以转换成译文语言里同等的成语,表达与原文对应的风格、意义或者感情,尽管它们在语义上不完全一样。比如,歇后语和骂人话,经常就有这样的等量的对应。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层次叫作发挥层次。这是因为译者既不能找到可以直接翻译的词句,也没有什么等量成语可用,而作家在充分发挥艺术手段,玩语言游戏、开玩笑或者炫耀技能的层次,到了译者也必须全力以赴,大胆想象,运用知识,允许自己实验和自由创造。
要在这三个不同层次中间判断和决定边界在哪里,不那么容易。
那么,是否还有完全不可译的文本呢。这个问题我肯定会回答“是”。很可能,有些文本可以翻译成有些语言,但几乎不可能翻译成另一些语言——如果要想在译文里保持文学质量就几乎不可能。我举个例子,台湾诗人陈黎的《战争交响曲》。请看下面的原文。
这首诗歌的翻译难点当然是陈黎在利用中文字的意义、发音和独特形象的组合,同时作为诗歌整体上还构成一幅图画。作为译者,你怎么可能在译文中再现这些特点?兵字排列出的矩阵给人强烈印象,让人想到整齐列队前进的罗马帝国军团。译者要是把这个中文字翻译成某种欧洲语言的对应词,就已经破坏了原来这种四四方方的矩阵图形。然后,带着两条腿的兵字图像,在行进中被打散,逐渐损失了身体这个部分,最后就变成了一排排坟丘的丘字。而丘这个字也很难在翻译中重现同样画面。从声音角度来说,原文是从短促和具有军事特点的“兵(bīng)”到连续不断模拟枪声的象声词“乒(pīng)”和“乓(pāng)”,而最后是悲哀而无力的“丘(qīu)”。我知道有人尝试把这首诗翻译成英文,但是效果不可能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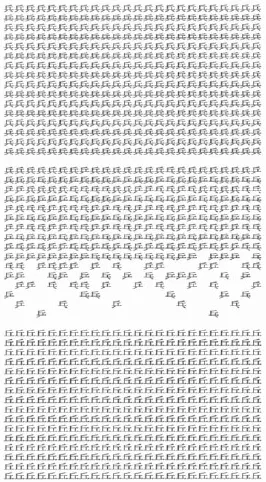
陈黎另外一首诗歌也可以作为例子,说明有的文本也许不一定完全不可能,但也难以翻译。这也是一个例子,说明现代中文受到不断增加的外来语言和文化的影响,而这种交流也会制造出新的翻译难度。这首诗《奥菲莉亚》包括在一套受莎士比亚启发而创作戏剧诗独白里。全诗如下:
奥菲莉亚
“要屄,不要屄,那是个问题。”
你踟蹰自语,我焦急不已
要我,就要行动
要果实,就要敢
你张口送我甜言蜜语
不敢动手为亡父复仇
要逼,不要逼,那是个问题
我被逼做好女儿,好妹妹
不敢逼自己成为一个诱你
摘我,释放我的坏女孩
伦理的推土机,把我们
连同我们所爱的花花草草
推到疯狂的池塘
那边有迷迭香,还有三色菫
那边有茴香,还有耧斗花
这边有芸香,还有延命菊
这边有枯了的紫罗兰……
这里的问题当然是在第一段第一行和第四段第一行,作者拿发音相同的中文字“屄”和“逼”与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的著名独白中英语be做了文字游戏,所以,英语原文“To be,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在这里就转为“要屄,不要屄,那是个问题”。那么,这种特点怎么可能翻译到没有这种发音同样性质的第三种语言呢?这就要求翻译作一种转化,自己尝试用自己语言里的词汇玩文字游戏。
但是我们可以问,是发音的相似性最重要,还是意义最重要?翻译在寻找一种有效的文字游戏的时候,他敢于离开陈黎的原文多远?在翻译用自己的语言作翻译实验的时候,他可以用原文利用的那种语言的哪个词:是因为的be,还是中文的“屄”和“逼”,或者是已经存在于自己的目标语言里的莎士比亚那段独白的译文呢?
陈安娜(Anna Gustafsson Chen,全名安娜•古斯塔夫森),瑞典国家图书馆馆员,汉学博士,翻译家,是二〇一二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作品的瑞典文译者。高中毕业后先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学院师从著名汉学家马锐然、二十多年译了二十多部中文小说,包括莫言的《红高粱》,阎连科的《受活》,余华的《活着》,苏童的《妻妾成群》,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