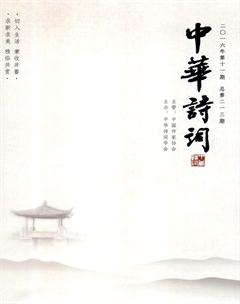茶轩诗话(十则)
李增山
灵才二气兼而诗
何谓有诗才?曰:“有写诗的灵气加才气也。”所谓有灵气,就是对事物比较敏感,容易产生他人难有的灵感。所谓有才气,就是有学问、有才华。有灵感才能为诗;有才华方能写出好诗;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灵气与才气的关系,也就是灵感与修养的关系,或曰顿悟与修炼的关系。灵感来自书外。有修养的人,必须到书外找灵感。整天抱着书本,满脑子古人的东西,食古不化,不深人生活,自己的智力开发不出来,灵感焉来?灵感者,兴会也。融景才能兴怀,情来才有神会。顿悟启于修炼。笔下诗乃心中诗之天然流露。心中诗就像火山里的岩浆,一旦有了条件就会爆发。单凭灵气,不懂得厚积薄发的道理,不懂得茅塞顿开那一刻来之不易,不懂得神来之笔来自何处,灵感是很难惠顾自己的。宋代吴可有一首论诗的诗,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诗曰:“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闲拈出便超然。”刘章先生有《晚秋山中》诗:“山色转苍凉,黄花开未了。秋风吹客心,落叶乱归鸟。”他说这是他“半生的观察,一瞬间得诗”,十个字道尽写诗之禅机。诗有深浅之分、好次之别。有灵气而无才气,可以写诗,也可能写出一两首好诗,但不可能写出太多的有深度的好诗来。
灵动自有神来笔
人们往往把古人的“神韵”说,看得玄而又玄,不可琢磨。秦中吟先生说:“它是诗人气韵、风采的流露,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是超然的艺术魅力。有的表现为活跃灵感、高远意象、奇巧构思,有的表现为遣词造句的灵秀,即神来之笔。”“活跃灵感”,是对的;而“超然的艺术魅力”,又把人们引入玄学的云雾之中。其实,神韵并不神秘,用“灵”、“动”二字便可概括。空灵而不太实,活动而不呆死,这就是神韵的内核,是神来之笔的秘笈。清·钱泳在《履园谭诗·摘句》中,举了许多例句,赵仁叔的“蝶来风有致,人去月无聊”,比较流传。今人刘征的“花笑若有声,蝶梦觅无迹”、刘章的“独行无向导,一路问黄花”、刘庆霖的“秋山才褪军衣色,白雪先沾战士眉”也都广为传诵。这种神来之笔,往往出自有灵气人之手,并不费太大力气,脱口而出,有如神助。还有一种看似神助的妙句,实为人的苦吟而得,是“炼”而得之,就像贾岛那样。然而这种炼,都是往“活”炼,而非往“死”炼,故显其有神韵。实际上,炼而得来的神韵,比“神助”得来的要多。“信手拈来”、“手到擒来”者,实为千锤百炼而得也。
性情本质是真情
清·袁枚曰:“诗者,人之性情也。”也就是说,作诗是性情中人的事。何谓性情?或曰:“性情者,热情、激情也。心不热、肠不热、血不热,焉能为诗?无灵感、无冲动、无进发,焉能为诗?”或曰:“性情者,忧国忧民、愤世嫉俗、悲天悯人也。饱食终日、无忧无虑、事不关己者,焉能为诗?”或曰:“性情者,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热爱社会、热爱自然也。厌生、厌世、厌人、厌物者,焉能为诗?”这些话都很对,但挖掘其本质、核心,乃真情也。真情者,有感而发而非无病呻吟也,真情实意而非虚情假意也,实话实说而非言不由衷也。强笑者、效颦者、醉语者,焉能为诗?性情中人,就是爱动感情、注重感情的人,悲亦能泪喜亦能泪,而且是真感情,是悲不自禁、喜不自禁的泪,而非硬挤出的泪。有真感情,诗中的联想、想象、幻想、虚构、假设、夸张、移情、错位……也就是允许的了,而且能产生无理而妙的诗美。被启功誉为“如此新声世所稀”的聂绀弩诗,胡乔木称其为独一无二的“聂体”。究其真正的特色、本质、灵魂,并非只是语言的率真、活泼、不拘一格,而是在“真情”二字上。他的诗,是以歌当哭,是心底的泪。何永沂有《哭聂翁绀弩》诗,曰:“夺去秦坑未死儒,始知天眼亦无珠。人间多少真歌哭,诗界凭谁再直抒。”真歌者,真诗也;真诗者,真情也。
诗味尽在情意间
何谓诗味(或谓韵味)?很难说清楚。但情趣与意境是少不了的。诗味不在文字的雅俗,而在情趣的浓淡、意境的深浅。顺口溜、格律溜、口号诗,一般都无多少情趣和意境,所以也就无多少诗味。真正的打油诗,其实是很有诗味的;它的那种机智、幽默、风趣,都内藏着深厚的或悲或喜的情,深藏着或美或刺的意。我们提倡的白话人诗、口语入诗,是口语化的文学语言,是精炼了的口语,而非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的所谓“白话诗”。所谓“入”,是诗人把自己脱口而出的话写到诗中,而不是类似把文言诗翻译成白话诗那样,故意而为之。这种脱口而出的诗,类同口语,诗论家称之为口语诗,其以自然取胜。这类诗多是民间日常话语,且是一些饱含情意哲理的经典之句。徐元猛《支农》:“唇齿相依鱼水情,扶犁翻土助春耕。任他老茧添新茧。俺是人民子弟兵。”刘征《擂鼓咚咚和泪吟》:“亿万同胞十万军,咱们都是汶川人。同心救死争分秒,伟力回天泣鬼神。大难不孤凭大爱,春风来抚感春温。老夫也佩黄丝带,擂鼓咚咚和泪吟。”这“俺是人民子弟兵”、“咱们都是汶川人”,包涵着多大的情感,留下了多长的意味!其不仅不是格律溜,而且成了统领全篇的纲,是诗的灵魂,是诗眼。鲁迅的“未敢翻身已碰头”、毛泽东的“前头捉了张辉瓒”、聂绀弩的“中国共产党同志”……这些孤立看似并无诗味的句子,一旦经他们之手巧妙地融入诗中后,便情味浓浓,意味长长,使整首诗成为经典之作。
写诗就是写意象
周啸天先生著文·《写诗就是写语言》,说:“没有好的兴会,难以写出好的诗词。有了兴会,还得有词儿。没有词儿,就会茶壶里装汤圆——肚子里有,却倒不出。”这话不错。但我想进一步说,什么词儿才是写诗最需要,或者说舍其即不能成诗的呢?那就是意象。所以,也可以说写诗就是写意象。小说写的是人物形象,诗写的是意象。意象是注入了诗人主观情感的物象,它赋予了物象以灵魂、思想,变成了一个生命体。我们说,要把诗写成活生生的生命,就是要写出活生生的意象。诗人有了兴会,要宣泄情感,就必须找到寄托情感的特殊载体。没有这个载体,就无法表达诗人的情感。这个载体就是意象。谭昌辉的《鼓浪屿观海》:“无边大海夜茫茫,屿小风高巨浪狂。眺望台湾半轮月,相思骨肉别离长。”“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诗人相思、别离的载体,就是那“半轮月”。这个意象就是把“茶壶里的汤圆”倒出的语言,若无它,这首诗就会失去灵魂,失去诗眼。诗人的天职,就是创造意象语言。美国的庞德说:“与其写万卷书,不如一生只写一个意象。”王维创造了“相思红豆”的意象;甄秀荣的“夕阳一点如红豆,已把相思写满天”,创造了“相思夕阳”的意象;何鹤的“相思豆种除夕夜,结串灯笼点点红”,创造了“相思灯笼”的意象。笔者有《偕妻游张家界》诗,曰:“张家界上李家游,万座青山两白头。我看夕阳红一点,宛如老伴少时羞。”是想创造一个“少妇夕阳”的意象,不知能否被大家认可?
妙在似与不似间
写咏物诗要神似重于形似。形似好理解,就是写得像不像所咏之物;神似,有人就觉得神乎其神了。其实也不难理解,就是写没写出所咏对象的灵魂、精神与本质。因为写此类诗的目的不是单纯地给物画像,而是有所寄意。而要达到寄意的目的,就必须用有灵魂的活物来作比。怎样才算神似呢?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作诗亦然。这“似与不似之间”就是把物的表象模糊了的“象外之象”,也就是神似。太似,成了死物;不似,成了它物。如何才能写出神似呢?妙法有二:一是创造意象。通过“形”去表现“神”的过程,也就是通过“象”去表现“意”的过程。把你拿来作比喻的物象,变成了能寄你意的意象了,也就达到神似了。二是以虚代实。眼见为实,心想为虚;已然为实,未然为虚。唐·杜牧是虚笔作比的高手,他的“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沈下贤》),不涉沈下贤人品一字,而尽显沈感人形象。今人刘征也是这样的高手,他的“论文梦到天人际,一棹桃花流水声”(《答沈鹏同志》),不涉沈鹏文风一字,而尽显沈之文清字洁。咏物诗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咏景诗亦同此法。只不过,咏物的似与不似,是在挖掘物本身生命的过程中形成的;而咏景的似与不似,则是在赋予景新的生命的过程中形成的。张俊华的“一日携风呼啸起,砸平天下虎狼窝”(《棒槌石》),诺大山峰能飞起吗?眼中不能而心中能,亦似,亦不似,妙!
得一趣者即称佳
有人著文称,诗的最高层面是哲学层面,并以古人做例证,说古人创作的优秀作品,都有一定的哲学层面的高度和深度。如果按照王国维的“境界说”,此种认识就是把诗的最高境界说成是“哲学的境界”,这未免太片面、太绝对了吧!其“都有”之判,也未免太臆断了吧!“诗无达诂”,早已成为常识。诗的最高境界是情景吻合,或曰情景交融,这种提法,也早被人们认可。即是这种提法,朱光潜还说:“诗的好坏决难拿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衡量。我们说,诗的最高理想在情景吻合,这也只能就大体说。”何况说好诗必须要有哲学的高度和深度呢?清人史震林说:“诗文之道有四:理、事、情、景而已,理有理趣,事有事趣,情有情趣,景有景趣。”作诗都会有所侧重,得一趣者即可称佳。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人作诗多重哲理,把苏轼的这首诗划归到“哲学层面的高度和深度”,是可以的。今人读陆游《游山西村》中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感到很有哲理,但硬说成是陆游追求哲学层面的有意为之,许并不符合事实,金性尧选注时就说“其实是状难写之景,却写得不费力气”。把它拿到景趣的层面上来评价,也不能说不是首好诗。
以死追求一“新”字
刘征先生说,杜甫所说“语不惊人死不休”,就是以死追求一个“新”字;新的思想感情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不新怎能惊人?我的理解,“新”,起码应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有时代感,不像古代的;二是有个性,不像别人的;三是有变化,不像(自己)过去的。模仿古人或他人只是初学阶段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写好诗的法宝。总踏着别人的脚印走,永远找不到属于自己的那片天地。据说,张大千早期办画展,问观者:“张大千画如何?”答:“张大干在哪里?”自此,张大千彻底摆脱了别人的影子,找到了“自己”。作画如此,作诗亦然。只是找到“自己”还不够,还必须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有新的创意;否则,读者会对你产生审美疲劳。正如吴之振所说:“文者日变之道也。……一息不进,则为已陈之刍狗。”何谓创作?就是必须要有创造,写出他人没有的和自己过去没有的东西;总是复制别人的或自己的旧的东西,岂止读者生厌,恐怕连自己也会生厌的。丁文江先生有咏竹诗,曰:“竹是伪君子,外坚中实空。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根细善钻穴,腰柔惯鞠躬。文人都爱此,臭味想相同。”读后不禁拍案叫绝!绝在何处?绝在一“新”字也。它不仅翻了诸如“未出土时先有节,至凌云处总虚心”等颂竹诗的案,更重要的是与得了软骨病的文人挂钩,别开咏物诗的新面。
不拘一格唱心声
优秀的诗人,一般都能形成自己一定的艺术风格。此话不谬。但必须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只能指其多数作品的风格,或其代表作的风格,统称主要风格;二是“一定”不是“固定”,一个诗人的风格是会随着时代的变迁、生活的影响、思想的变化而改变的。故真正的诗词大家,必不囿于一格。或一格为主他格为辅;或不同阶段有不同的风格;或兼容并蓄,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看似无格实为大格。多数诗人,是有主有辅。豪放派创始人苏轼,既写“大江东去”,又写“花褪残红青杏小”。婉约派代表李清照,既写“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又写“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诗人追求自己的风格基调,并不影响海纳百川的胸怀。杜甫说:“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戏为六绝句》之六)既要选择适合自己的风格,也要突破一家一派的拘限,尽可能广泛地学习和采纳一切好的东西。这样才能扩展自己创作内容的范围,不被风格所束缚。因作品内容而决定创作风格,是大家高手的本事。高尔基说:“诗是心底歌。”吟哦不做违心事,想低吟浅唱就低吟浅唱,想引颈高歌就引颈高歌,只要能打动人就是好风好格。略改龚自珍的两句诗,曰:我劝诗朋重抖擞,不拘一格唱心声。
燕瘦环肥美不同
人们总爱争论“隔”与“不隔”孰优孰劣?“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孰高孰低?其实,这两个问题都不是绝对的。“隔”就是偏重“隐”,“不隔”就是偏重“显”。写景宜显,写情宜隐。“无我之境”实际是不存在的,诗在任何境界中都是有我的,都是自我性格、情趣的返照。人们总以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作为“无我之境”的例子,难道这“悠然”之境不是从作者心中产生?只是“移情作用”不强而已。若将杜甫的“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作为“有我之境”,你能说它就不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移情作用强或弱,各有其妙处,实不宜论高下。笔者有一首《评诗》诗:“燕瘦环肥美不同,焉凭好恶说西东?”飞燕瘦,玉环肥,都好看。笔者有《边秋》同题诗两首,曰:“坝上秋来早,山林一夜黄。高风乱归鸟,落叶舞斜阳。”曰:“燕麦开镰日,高原遍地黄。南飞千里雁,带去一天香。”有人评:“前者不隔,进入无我之境,优于后者。”有人评:“‘带去一天香,流露出作者对丰收的喜悦心情,优于前者。”我认为,有所侧重是创作中的普遍现象,这两首诗各有侧重,前者重在景趣,后者重在情趣,不宜争个谁好谁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