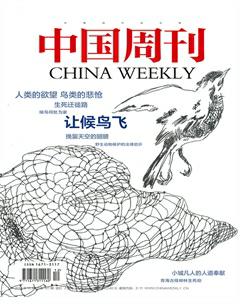逆进化从刘若望的艺术作品看人性的自然向度
宣宏宇
就雕塑艺术而言,人或动物向来都是十分常见的创作题材,它们有时仅仅作为自身出现,有时则蕴含着其他的寓意,刘若望的作品属于后者。近年来,刘若望的作品主要以动物为题,虽然塑造的是动物却富含表情,拟人化意图显而易见,这与他早期的那些徒有人形却神情空洞的兵马俑式作品形成鲜明对比。而尤其有意思的是,在两个时期之间的《原罪》作品,恰好以人与兽之间的过渡形态连贯出一部逆向的文明进化史。然而,这种形态上的逆进化还只是一种提示,更重要的是,在后来的那些动物们深邃的眼神里,充满了对文明的诘问。其中不仅关涉到许多已经让现代人感到岌岌可危的生态恶化问题,而且还直接指向所有导致这些问题的社会结构,甚至也深及对人性的沉思。

《苍生》系列 油画 350x300cm 2016.01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类拥有自己认为“其他动物所没有的智慧”,但这不等于说人因此摆脱了动物性;相反,随着掌控事物能力的增强,人的原始欲望也在膨胀。尽管文明意味着人对自身欲望的控制,然而,最近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显示出欲望的膨胀速度日渐飙升,大有失控之趋势。虽然自命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种危机,但所谓文明的社会组织形态从一开始就是为着生存需求而来的,其后千百年间不断完善的秩序不过是为着满足欲望能力的提升而调和物种内部关系的产物,它根本上就是一个牵涉到每个成员的利益链,即便时常会因分配不均衡而出现社会动荡的局面,但总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良或革命来修正。总之,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总体上仍然是一种基于物种自身立场的利益形式,而远没有达到两千多年前就萌生的和谐理想。
对于这样一种人与自然的对峙关系,刘若望的早期作品从自身经验的社会现实出发,借用古代大规模陪葬品的雕塑形式,呈现了人类在追求美好过程中经由集体无意识体现出来的盲目性,以及因此而来的适得其反的结果。尽管那些作品不乏时代与民族的特殊性痕迹,但其中千人一面的形象实际上也揭示了人类社会构成的普遍法则,一如福柯论证过的:有选择自由的人选择的绝不是“权利”,而是“权力”;选择的绝非正义,而是统治,所以任何以普遍立法名义开展出来的权利或正义只能是掩饰压迫和非正义。在刘若望的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引吭高歌的群众,还是庄严肃立的战士,都无意于传达任何通向未来的希望,倒像是从千年墓穴里爬出来的行尸走肉,代表着那种为各种各样的道德包裹了许久的原始欲望。

《苍生》系列 油画 350x300cm 2016.02
为了进一步呈现这种原始欲望与人类理想的更深层关系,刘若望把人的形象还原到最初的阶段。《原罪》里的蒙昧的猿人们与夹在书页间的殉难者,以及作品标题本身的宗教意味构成了一个极具象征性的场景。作为人类滥觞的节点,这个场景是悲壮的,也是积极的,它标识着人性的曙光,是人对神的第一次胜利。然而,从刘若望的整个“倒叙《进化论》”的视觉谱系来看,这一作品的语义是双关的,即人性的起点亦即人类背叛自然的起点。“文明”地说,是人从顺从自然走向改造自然的转折,其前途是通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终极美好。然而,站在今天现代文明所处的困境中回望先民们淳朴的希冀时,看到的却是一条从屈服到奴役的泥泞之路,而其中不断加大马力推动人类社会加速前进的能量,则是人之为人所要克服的兽性。这是一个颇具黑色幽默意味的悖论,置身其中的我们,在那些被刘若望放大了的人兽混合体面前,惊骇的发现——理想文明意义上的进化其实尚未企及,甚或是在倒退!
不止一位观众从刘若望的作品中感到了一种对现实的悲观,但同样有目共睹的是,其中并不至于绝望。作为艺术家,刘若望无法为社会的前途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但却可以通过艺术表达的层层推进提示我们自省。从《渡渡鸟》系列作品开始,作为理想的人性之光从动物的表情中闪现出来。兽形的人性和之前人形的兽性完成了“倒叙《进化论》”的首尾呼应,错位的能指与所指关系解构了观念上的成见,进而更加生动地呈现出人性的自然向度。
在刘若望的动物题材作品中,猛兽占了大多数,这大概不只是艺术家对于力量形式的偏爱所致。作为生态食物链中的上游环节,猛兽的形象影射着人类,同时又暗示着一种人类可望不可即的力量。人没有虎狼般锋利的爪牙,亦没有狮熊的肥厚皮毛和猎豹的速度……作为一种在肉体上十分弱小的生物,人竟能够成为这个星球的主宰,靠的是所谓的“智慧”。凭借“智慧”,人不断发明并升级工具,从满足生存到满足生活,再到掠夺,掌控事物能力的提高并没有优化人的生物属性;相反,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类正在加剧自身的异化。不再为着生理需要或精神需要的生产加速地自我增殖,似乎有一种非神、非人、非兽的力量将要接管这个世界,对此人已经深感恐惧,一如刘若望笔下的那些猛兽,早已没有了王者风范,或独孤地伫立在荒野,或惶惑地游荡于丛林,或无奈地与我们面面相觑……
在《渡渡鸟》系列作品中,渡渡鸟骨架雕塑以仿真的比例和形态以及巨大的尺寸引发观众对物种灭绝问题的关注,但这不仅仅是一个“前车之鉴”式的案例模型,而更是一种唤醒人性理想的视觉启示,正如艺术家本人在作品介绍里说的那样:“文明的最高境界是使人对生命敏感,渡渡鸟归来的意义在于,它的故事和命运,足以引起生命之间的共鸣。”这种共鸣不只是同病相怜,而且也是人对自身独特性的根本信念,即人性与兽性的差别所在。无论人性之生成怎样地建立于原始欲望之上,但人之为人就是要克服曾经的自然属性,毕竟向死而生才是存在的根本方式,当然也是人性的自然向度的根本所在。
显然,就目前的境遇看来,人类远没有完成自己所定义的那种物种的进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关于人性的所有美好愿望始终被持存着。如果说从猿到人是建立人性的开端;那么,克服当下的危机则就是人性的实现。幸运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知到,文明的敌人并不来自外界,而是驻留于人类身心之中的原始欲望,在刘若望作品中那些动物的眼神中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刘若望的“倒叙《进化论》”不是一个主题性的计划项目,而是艺术家通过创作思考人性的自然深入过程,其间没有图解式地讨论具体的生态问题,但却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将观者引入问题的情境之中,从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征的社会问题开始,一步步追问困顿的根源,以极富冲击力的感性形式激发充满逻辑性的理性思考,最终所提示的不是人所共知的和谐愿望,而是如何达成这一愿望的自省之途。
最后,我们似乎遗漏了刘若望最为重要的一组作品——《狼来了》。说这组作品重要,不仅是因为它的影响巨大且广泛,而且还因为它在“倒叙《进化论》”的视觉谱系中有着十分特殊的位置和意义。无论从创作时间还是作品形态上来说,《狼来了》与《原罪》有着异构同质的关系,它们都是人与兽的直接交锋,所不同的是前者是外在的,而后者是内在的。在总览了刘若望的其他全部作品之后返回来看这两件作品,可以发现艺术家自己也真切地经历了一次从“突围”到“内省”的蜕变。正如一些观者理解的那样,《狼来了》流露出一种英雄情结,那是一种承袭于传统民族文化并在近半个多世纪来被强化了的宏大情绪,刘若望置身其中,自然免不了像其他人一样受到影响,以至于在这组作品中以一种自我指涉的方式将之前被作为反讽对象的认知方式爆发出来。不过也正因为如此,《狼来了》的人兽对峙形式才充满了强烈的感染力,也才会有后来《原罪》的深刻内在转向;同时,以狼群代替了之前的人群实际上赋予了作品一种开放性的内涵,除了直观的视觉语义之外还可以有多重解读,尤其可以令我们重新审视动物与人的关系,这大概也是通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重要一步。

《苍生》系列 油画 350x300cm 2016.06
刘若望,艺术家,现居北京。
1977年生于陕西省榆林佳县山区。2005年毕业于中央美院助教研究生课程班
2016年,“若望苍生”刘若望作品展——北京798艺术工厂;
2016年,“若望苍生”刘若望作品展【世界巡展·德国站】——德国NordArt,并获NordArt2016最高人气一等奖;
2015年,《狼来了》对话《哀悼基督》威尼斯双年展——意大利威尼斯,并获那不勒斯文化奖;《狼来了》对话康德的名著《纯粹理性批判》展——意大利都灵大学;
2013年,韩中文化交流展刘若望作品个展——韩国国会;
2012年,《狼来了》刘若望作品个展——新西兰皇后镇;
2012年,第12届全军美术作品展——中国美术馆并获奖;
2008年,2008亚洲当代艺术展——新加坡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