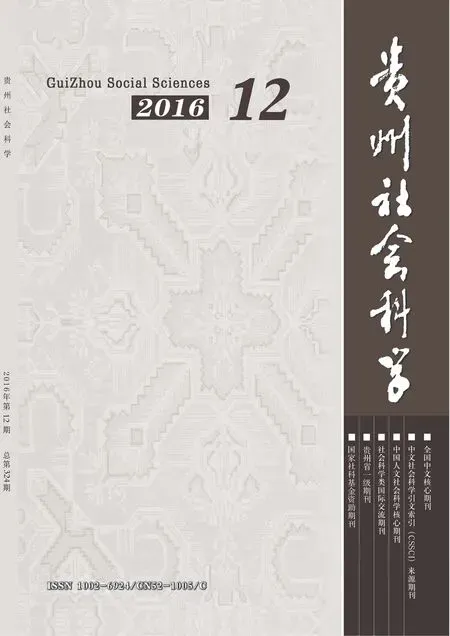科学事实与价值——以朱熹的科学研究为例
黄 昊 张丹丹
(1.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2.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科学事实与价值
——以朱熹的科学研究为例
黄 昊1张丹丹2*
(1.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2;2.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0)
休莫问题的重要观点之一是道德的根源不是理性,事实和道德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即是与应该是有区别的。数百年来人们对此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但还没有能很好的解决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科学研究却为解决科学事实与价值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其有益的探索方向,并取得积极的成就。
科学事实;价值;朱熹;科学研究
在《人性论》中休谟阐述他所遇到的命题的连词不再是通常的“是”与“不是”,而是“应该”与“不应该”,这种变化尽管静悄悄的、很难让人发觉但却有重大的意义。注意这个细节会推翻相关的道德体系。并指出区别恶与德不是简单地建立在对象关系上、也并非仅被理性所查知[1]。休谟提出了从“是什么或不是什么”的事实命题能否推导出来“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的价值命题的问题,“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与“应该怎样或不应该怎样”是不同的问题,详细点说就是对事实的描述“是”中无法推导出规范性陈述“应该”来。
一、事实与价值关系变迁
实际上在古代哲学家大多认为真善美是统一的、是公理、是不证自明的。到了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事实与价值问题的统一性受到质疑,人们较多的认同事实与价值是相互分离的,特别是牛顿经典力学确立后,伴随的是机械自然观的确立。事实多认为是科学应该研究的问题,是可以用科学方法鉴别真伪的,是理性的也是客观的。价值多认为应该是人本主义哲学家研究的问题,是意识的,是情感的对象,其研究方法和科学方法是不同的,是主观的也是形而上的。上世纪随着科学的发展,科学进入大科学时代,科技的运用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问题,人们开始思考科学的问题不仅是“是什么”的问题了,也需要“应当怎样”来全面的评估,也就是科学事实需要价值的引导,事实和价值这一对从未分离的范畴又开始了迈向结合的第一步。也就是事实和价值之间经历了以下的历程(图1):
虽然有众多的学者试图从不同的视角、运用不同的理论来说明“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也是事实与价值的问题,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能真正合乎逻辑的、令人信服的、从事实推导出价值来。也就是休谟三百多年前提出的“是”与“应该”的关系问题现在还没有令人信服的解答。但八百多年前朱熹在其重建理学的过程中却对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有益研究,特别是科学事实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可为今天对事实与价值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

图1 事实与价值关系变迁
二、朱熹哲学中有关的科学事实和价值
朱熹以前的儒家哲学对事实和价值是不分的。儒家伦理学不但将事实与价值混淆在一起,还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为一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事实与价值在同一论述中纠缠在一起的案例在中国古代儒家典籍中很容易见到。这种现象出现不仅有外部客观世界信念基础,还具有内在的精神基础[2]。但是朱熹重建儒学时,自觉不自觉的将事实和价值向区分的方向前进一步,不像从前那样混淆。这种前进只是一小步,但是意义是巨大的。特别是朱熹在科学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见解。
(一)朱熹进行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
1.理与氣
在朱熹的哲学中最高的范畴是理,“和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个理。”[3]114在朱熹的理学中的理是抽象的理,是逻辑上的质的规定性,是对事物本质的规定,且此理具有超时空性,永恒性,不会随着某些具体事物的生灭而变化。但是在朱熹的哲学中基于理的范畴又引入了气的概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3]114有了氣便化育萬物,萬物皆有氣流行而成。“有是理後生是氣。”[3]114“先有個天理了,却有氣。”[3]114“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3]115-116“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无形,氣有粗,有渣滓。’淳。”[3]115“或問:‘必有是理,然後有是氣,如何?’曰:‘此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説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掛搭處。氣則为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人傑。”[3]115“‘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氣以成形,而理亦赋焉。銖。”[3]114从以上的表述可以看出在理气关系是一种形上和形下的关系,理在气先,但理气又相依。这里理在氣先是指一种逻辑上的先後。陈来认为逻辑在先论是合适的、恰当的。朱熹说“推上去”“推其所从来”,从逻辑上可以说理在气先,理在气先的结论只是一种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是广义上、理论上的联系,不是狭义的某种形式逻辑关系。理在气先不具有时间延续上的先后性,也就是理在时间上不先于气。陈来指出朱熹认为“理气不分”说明理与气实际上、事实上是无所谓先与后[4]。“問理与氣。曰:‘伊川説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言,只是一個理;及在人,則又各有一個理。’夔孫。”[3]114在朱熹的理学中又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就是理一分殊,理一分殊的思想是朱熹理学重要的命题之一,该思想赋予朱熹哲学思想极大的丰富的内涵。理一分殊的关系可以用“月印万川”来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如同一个月亮在天上,但是散照在众多的江河湖泊的月亮有数千万个之多的月亮。
2.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出自儒家经典《大学》,但是在《大学》中没有对格物致知作解释,导致后世不同的人对于格物致知的理解不同,历代的儒学名家也对格物致知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但在众多的诠释中,以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影响最为深远。朱熹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其中的格物致知论是其中最重要的关键环节。朱熹汲取了程颐格致说的相关思想。在《补格物致知传》中,朱熹详尽的阐释了自己的格致思想与理论。“格,至也。物,犹事也。穷推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右传之五章,盖释格物致知之义,而今亡矣。闲尝窃取程子之意补之。日: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未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贯通,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5]以上一段话不仅精炼的表达了其认识论,也表达了其方法论。“‘上而無極、太極,下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阙了一書的道理;一事不窮,則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則阙了一物道理。須着逐一件與他理会過。’道夫。”[6]477根据朱熹的观点,一草一木皆有理,从宇观到微观都应该努力的追求明白每一事物的道理,这和后世的追求真知和知识虽然所用的语词不同,但是语义却是惊人的相似。“‘格物,是逐物格將去;致知,则是推得漸廣。’赐。剡伯問格物、致知。‘格物,是物物上窮其至理;致知,是吾心無所不知。格物,是零細説;致知,是全體説。’时舉。”[6]471从朱熹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格物是要达到致知的层面,但是要达到致知的层面必须要格物,也就是说格物是致知的充分必要条件。朱熹説的致知也没有给出其概念具体的内涵和外延,根据大多数人的理解,这里的致知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也包括伦理的知识等,主要以伦理的知识为主。很明显的是没有区分科学事实之知和价值之知,这不能说是一个重大的缺陷,但是在朱熹生活的年代能意识到致知包括科学事实之知和价值之知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尽管没有能具体的区分它们。
朱熹的格物所要关注的首先是在道德层面,但是他格物中的物没有排除自然事物和现象,因而他的格物中确实是有研究和探索自然现象和规律之意。
同时格物也是成为圣人的充分必要条件。“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7]其间的逻辑结构如下(图2):

图2 格物逻辑结构
朱熹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可以用下面的图形来表示(图3):
从朱熹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看,万物各具一理,为了明理必然要格物,格物本身就具有科学研究之意,事实上也是如此,同时格物本身就具有讲求实学、实理,格物当然要实地的观察,格物当然也要认识事物的客观规律。格物到一定的程度导致了致知,致知内容之一包括科学之知和科学事实。格物致知只不过是明天理的一种手段,朱熹进行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明天理,朱熹的科学研究不过是明天理的一个必要的步骤。也即是说朱熹的科学研究不是为科学本身,而是追求明天理过程中的不得不涉及的关键一步,科学研究中所得到的科学事实也是明天理过程中所得到的一些有意或无意成果而已,但这是明天理所必须的。

图3 朱熹科学研究的哲学基础
(二)朱熹的科学研究
朱熹生活的年代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最为繁荣的时期,该时期的科学研究属于自然哲学范畴,或者说该时期的科学研究和自然哲学就是一回事,当然该时期的科学研究也具有自然哲学的思辨特色。朱熹进行科学研究除了以上的哲学基础外,还有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因素,通过格物来探究自然世界的规律与秩序,进而揭开自然世界背后隐藏的道德上的秩序[8]2。为道德论提供基于自然观基础上的宇宙论,这种自然观基础上的宇宙图景也是人们安生立命之本。“由于程颐和朱熹的倡导,‘道’和‘理’逐渐脱离了当时文人一向视为源泉的文化传统,变成了独立的存在,而其得到确认是由于自然的进程而非文化的记录。确切地说,这一变动的主要结果,便是对道德自我修养的重视逐渐胜过了在文学和文化上的造诣,同时也使人们对天地自然地兴趣与日俱增。”[8]2
朱熹的科学研究涉及的领域较广,本文只能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科学研究作为研究的文本材料,来论证本文的观点。
在宇宙生成论方面研究:“某自五六岁便烦恼道:‘天地四边之外,是什么事物?’见人说四方无边,某思量也须有个尽处。如这壁相似,壁后也须有什么物事。其思量得几乎成病。到而今也未知那壁后池本作‘天外’。夔孙録作‘四边’。是何物。”[9]从以上一段话可以看出朱熹小时候就对宇宙的本体问题有很浓厚的兴趣,也说明朱熹从小就会提出问题和发现问题,和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论断 “科学始于问题”契合。爱因斯坦认为提出问题更重要,相对于解决问题,提出新问题、从新的视角看待事物、对事物发展提出新的可能性,需要创新性的灵感与想象力,这才是真正的科学进步之所在。解决问题可能仅仅是实验上的技能、数学上的技巧而已。朱熹说:“‘天地初间只是阴阳之气。这一个气运行,磨来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许多渣滓;里面无处出,便结成个地在中央。气之清者便为天,为日月,为星辰,只在外,常周环运转。地便只在中央不动,不是在下。’淳。‘清刚者为天,重浊者为地。’道夫。”[3]119在朱熹看来宇宙起源于阴阳之气,阴阳之气相互之间的摩擦运动,随着运动的速度加快,密度不同的就开始分化,密度大的渣滓没有办法出去在中央就形成了地,即重浊者为地;而密度小的则在地的周围形成了天,即清刚者为天。从朱熹对宇宙起源的认识看,朱熹的宇宙起源说有地心说的因素在里面,但是朱熹认为宇宙是有阴阳不同的气团摩擦而生成的,这比古代中国乃至于古代世界关于宇宙起源的说法更具有科学性,也更接近科学事实。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与科学哲学中的一种观点,即我们无法达到科学真理,但是我们可以无限接近科学真理是相符合的。同时仅仅有宇宙的形成还是不够的,根据常识重浊者为地,清刚者为天,那么重浊者会往下降的,就像一块石头在水中,由于密度大就会往水下沉,但是根据常识,地好像没有向下沉。朱熹也根据思辨和研究给出了解释。“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放,上声。属,音注。数,所句反。○九天,即所谓圜则九重者。际,边也。放,至也。属,附也。隅,角也。○右三章六问,今答之曰:或问乎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气。其形也有涯,其气也无涯。’详味此言,屈子所问,昭然若发矇矣。┈┈地则气之渣滓聚成形质者,但以其束於劲风旋转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坠耳。黄帝问于岐伯曰:‘地有凭乎?’歧伯曰:‘大气举之。’亦谓此也。”[10]从以上朱熹对楚辞的注释中可以看出来,朱熹对天与地相互依存的关系,以及天绕地运动原因都是有所解释的。使朱熹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更完整和全面。下面朱熹关于天绕地运动有更深入和更全面的解释:“天运不息,昼夜辊转,故地傕在中间。使天有一息之停,则地须陷下。为天运转之急,故凝结得许多渣滓在中间。地者,气之渣滓也,所以道‘清轻者为天,重浊者为地。’道夫。‘天以气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气。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尔。天以气而运乎外,故地傕在中间,隤然不动。使天之运有一息停,则地须陷下。’道夫。”[3]119
朱熹这种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是出现在十二世纪。西方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是十八世纪的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于1755年出版了他的《宇宙发展史概论》。康德认为太阳系起源于—片原始星云,且星云是不均匀地扩散在空间,由于粒子的质量不一,粒子间有引力也有斥力,质量大的粒子具有较大的引力,该引力大于小粒子的斥力,使得附近的小粒子向它们靠拢,慢慢的就形成一些中心天体。质量不同的粒子碰撞、吸引和排斥作用使天体开始转动和运动,就形成了以太阳为中心,附近的小粒子汇聚成为行星,在一个椭圆轨道绕太阳旋转起来。这解决牛顿的一个难题,牛顿的物理学解决了现在天体运动的原因,即物体间万有引力的作用,但是牛顿经典力学没有解释太阳系最开始的运动是什么样的?牛顿也一直为这个问题所困惑,最后牛顿认为这个运动的初始的原因为上帝,这也是牛顿在其研究的后期转向宗教神学的原因之一。1796年,法国人拉普拉斯发表《宇宙体系沦》,拉普拉斯提出和康德了类似的观点,使康德的观点直到时隔近半个世纪才受到重视。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不仅回答了太阳系的起源,也回答了太阳系的初始的远动的原因。尽管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说不完美,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却是一个有意义、有价值的起点。“在此后直到今天,共出现了20多种星云假说,仍遵循着康德、拉普拉斯的基本思想。”[11]我们把朱熹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和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对比一下,从理论上两种学说基本相近或相似;从时间上朱熹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是在十二世纪,但是康德—拉普拉斯星云说是在十八世纪,时间上相差约六个世纪;在此不得不为朱熹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感到钦佩,目前学界基本认同朱熹不是科学家,但是他做的工作一点也不比科学家差,朱熹具有科学家所具有的科学素养,他取得了无与伦比的科学成果。对于朱熹关于宇宙生成及其初始运动的科学思想,后世的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梅森指出朱熹认为在太初,宇宙是一团混沌物质,且这混沌物质进行涡旋式的运动,运动导致重浊的物质趋向涡旋的中心,形成大地;清刚的物质趋向上而成为天。大旋流的中心是不运动的,涡旋形成的大地也是不运动的,进而成为宇宙的中心。涡旋式的运动形成的天绕着地昼夜不停的旋转,若天的运动停留一息会导致地陷的结果。朱熹认为天体由于‘刚风’[朱熹说过,道家有‘高处有万里刚风’之说]而不断地运动,每一天体都有其自身的‘风’,这些‘风’分别形成宇宙漩涡中的一层或一重。认为朱熹在天文学领域的研究发展出来自己的自然哲学[12]。“清代来我国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1888年说,朱熹的理论传到欧洲,曾对笛卡尔(公元1596-1650年)提出天体演化的漩涡假说起了影响。”[13]杜石然也认为朱熹提出的宇宙起源说“提出了一个处于不停顿的旋转运动中的、由阴阳二气组成的庞大气团,由于摩擦和碰撞的作用、旋转而引起的‘渣滓’向中心聚拢的机制以及清浊的差异原因所造成以地球为中心,在其周围形成天和日月星辰的天地生成说,从而给张载的聚散说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说明,使之增添了力学的性质。这些推测虽然还只是猜想的、思辨性的,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有价值的见解。”[14]席泽宗指出朱熹认为初始混沌未分时只是一团气,这团气做快速旋转运动使重浊者在中部沉淀形成地、清轻者形成日月星辰并在周围运动。水与火是朱熹设想原初的物质,地组成中有水的渣滓,理由是朱熹联系并参考了地上山脉的形状。席泽宗认为朱熹的天体演化学说相较于前人考虑到离心力而具有力学性、不同于《淮南子·天文训》《灵宪》中认为天地未形成前是从虚无中产生的一团混沌状态的气而具有物质性和联系地质现象的特征,这是重大的进步。并推测康德的星云假说受到朱熹天体演化学说的影响[15]。
三、结论
通过对朱熹科学研究中的科学事实与价值的相关关系研究,不难发现朱熹认为科学事实与价值之间不是没有关系的,正相反,科学事实与价值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朱熹那里是有逻辑,即从小到一草一木,一禽一兽,大到宇宙皆有理;所以要格物,格物要一件一件的格,一物一物的格,要“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坚持不懈的格;由此可以得到见闻之知,也可以得到德行之知,但是本阶段主要是获得较低层面的“物理”,即较多的科学事实。用力持久,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会引起质变,达到临界点就会呈现一旦豁然贯通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会有两种境界,第一层境界是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第二层境界是吾心全体大用无不明。最终获得的是较高层面的“天理”,即价值。也就是在朱熹那里,科学事实是获得价值的前提,或者把价值奠定在科学事实的基础之上。
在朱熹集成理学的形而下层面科学研究及获得的科学事实较多,科学内容或自然哲学内涵明显,将精湛思辨与敏锐观察结合获得的科研成果代表了当时的最优秀、最高的科技成就;理学的形而上层面没有科学的位置与内容。但是朱熹集成理学形而上的层面的结果是立足于科学研究得到的大量科学事实基础之上,就使得理学的形而上的内容与结论的得出不可避免的受到科学思想、科学研究方法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样得到的理学形而上的内容更容易获得人们的理解、也更容易获得成功。南宋时吸收最新时代科学成果的理学,又影响同时期的科技发展,使宋元时取得的科技成就令同时期西方望尘莫及。
作为一种学术思想的理学,由于朱熹将价值的逻辑起点放在科学事实上,使理学不可避免的具有科学文化的因子,尽管这种科学文化的因子还刚刚处于一种极端弱小的端倪状态,但也正是这种处于弱小的端倪状态科学文化因子使理学达到一种新的高度,在南宋中后期与其他学术流派的思想交锋中立于不败之地,并一度作为官方哲学与主流意识形态影响整个东方儒家文化圈数百年,并将作为一种思想继续存在并影响人们。
[1] (英)休谟.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09-510.
[2] (美)孟旦.事实与价值的混淆:儒家伦理学的一个缺点[J].哲学研究,1999(3):77.
[3] (宋)朱熹.朱子全书第十四册·朱子语类·卷一·理气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 陈来.朱熹哲学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5-26.
[5]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3:6-7.
[6] (宋)朱熹.朱子全书第十四册·朱子语类·卷十五·大学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宋)朱熹.朱子全书第六册·四书章句集注·大学章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17.
[8] (韩)金永植.朱熹的自然哲学[M].潘文国,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9] (宋)朱熹.朱子全书第十七册·朱子语类·卷九十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129-3130.
[10] (宋)朱熹.朱子全书第十九册·楚辞集注·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6.
[11] 王鸿生.世界科学技术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127.
[12] (英)斯蒂芬·F·梅森.自然科学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75.
[13] 郑文光,席泽宗.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29-130.
[14] 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106.
[15] 席泽宗.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2.
[责任编辑:黄 昇]
贵州省2016年度社科规划一般项目“王阳明的朱子学研究”(16GZYB59);贵州省社会科学院2016招标课题(省领导圈示)“贵州瑞士山地文化之路径比较研究”(QSYB2016011)。
黄昊,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科学技术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科技史、科技发展战略、科学哲学、科学思想史和科学文化;张丹丹,河南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数据库及信息系统。
B244
A
1002-6924(2016)12-035-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