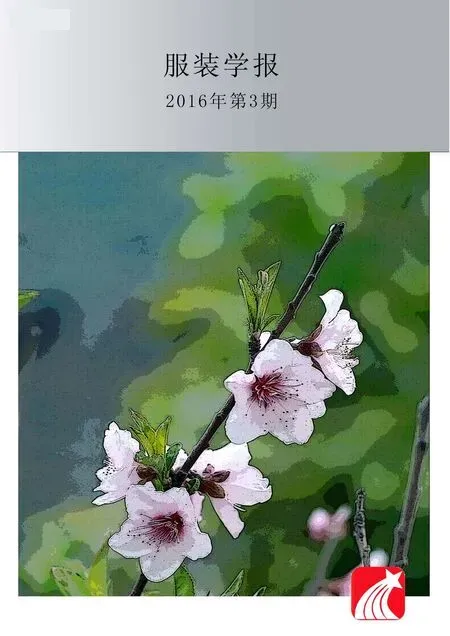大理地区白族服饰的生态审美观
赵玉, 孔凡栋, 秦德清
(青岛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大理地区白族服饰的生态审美观
赵玉,孔凡栋,秦德清*
(青岛大学 纺织服装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采用文献查阅方法,结合生态美学要义对大理地区白族服饰的图案元素、色彩、社会功能等方面进行分析,提出大理白族服饰蕴含着“平等”、“共生”、“和谐相处”的生态审美观,主要体现在人与客观自然环境的和谐、人与图腾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认为大理白族服饰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符合现代的生态美学和当前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对今天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也将起到一定的建设性和指导性作用。
白族服饰;女性头饰;生态审美观
白族主要聚居在以苍山、洱海为中心的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这里景色秀丽、气候宜人,并且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是中外游客极为向往的旅游胜地。在大理白族的文化系统中,服饰作为白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白族特有的象征符号。
目前,有关大理地区白族服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① 对于服饰类型及其文化蕴意的研究;② 从符号学角度,对服饰的深度解析;③ 对服饰的演变过程进行深入分析;④ 对服饰美学要素的详细阐释。其中对于服饰大理地区白族服饰的美学要素研究主要是从色彩、工艺等方面展开,而结合生态美学要义对其解释的较少。因此,文中从生态美学角度对大理地区白族服饰展开进一步的研究,提出白族服饰不但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在白族的世代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与自然界相处共存的思想体系,其中包括了以“平等”、“共生”、“和谐相处”为主导的生态审美观。这种以和谐为核心的生态审美观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步伐,也是白族服饰绵延不息的重要内在力量。
1 生态美学要义
对于生态审美观的解释,学术界有不同的阐述,徐恒醇在《生态美学》一书中提到:“生态审美观正是以生态为价值取向而形成的审美意识,它体现了人对自然的依存和人与自然的生命的关联。”[1]他又强调“在这里,审美不是主体情感的外化或投射,而是审美主体的心灵与审美对象生命价值的融合。”[1]曾繁仁在《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探索与对话》中对生态审美观的含义作了进一步的概括,他认为生态审美观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解释,“狭义的解释就仅仅局限在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人和自然要达到亲和和谐;广义的理解指建立人与自然生态的审美关系延伸到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审美关系。”[2]而这种站在“物我交融”的高度审视和反思当下的审美弊端、强调审美主体的参与性与主体对于所处的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关系的生态美学观念正是对以往的主客二分、主客对立的传统美学的反思和克服,并且在具有悠久历史的白族文化中早已显现,在服饰文化中尤为凸显。大理地区白族服饰中的生态审美观得益于人们赖以生存的居住环境,对具有宗教色彩的自然崇拜以及丰富的日常生活实践。在其相互作用和影响下,达到了一种“自然——神——人”相通的境界,缔造出了人与客观环境、人与图腾、人与人(包括人与自身)之间多维度的和谐关系。
2 大理地区白族服饰的生态审美观
2.1人与客观自然环境的和谐
人的生存离不开客观自然环境,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人的审美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它“既表现为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又表现为主体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1]换言之,人需要在受动性和能动性、主体内在和外在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使之维持一种稳定的有秩序的状态。
“人对于生态美的体验,是在主体的参与和主体对生态环境的依存中取得的,它体现了人的内在和谐和外在和谐的统一。”[1]特殊的地理环境又孕育着特殊的生态审美观。大理山川秀丽,四季如春,优美的自然环境赐予了白族人们丰富的创作灵感,客观存在的物质现象和自然物种都成为了白族人生存依赖的活动客体。服饰的图案元素大都截取生活中的常见事物,如蜜蜂、喜鹊、青蛙、山茶花,甚至将大理白族地区特有的自然景观蝴蝶泉、三塔、苍山等都一针一线地绣制于服饰中。再从头饰上看,“风花雪月”是大理白族女性头饰的标志性符号,它代表了大理独有的“上关花、下关风、苍山雪、洱海月”的优美景致,花代表着山顶的山茶、杜鹃,这些是大理白族人们最喜爱的花卉。头巾一侧垂吊着白色的缨穗,飘飘洒洒,象征着终年吹拂的下关风,在绣花头帕上梳理着的那些白色的绒毛是苍山顶上皑皑白雪的形象表现,而姑娘们那形如弯月的发辫置于花海之中,象征洱海上空升起的一轮明月。这件极具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的“风花雪月”在表达白族人对自己家园热爱的同时,也直观地反映出他们与自然生存环境相融合。同样,白族人也将自然界中的日、月、星、辰等通过一些相应符号“印烙”在服饰中。如利用色彩的明暗关系在背幼儿的裹背上表现“日月纹”,表达人们对于光明的追求,绣制“万字符”则是刻画白族人心中那周而复始、循环出现的太阳模样等。白族女子选择周围的自然环境元素以艺术性的表现手法装扮自己,将自己置身于美妙的服饰自然图案和色彩之中,在自然界与自我之间寻求到了一种和谐共存的平衡状态。人在此时既是一位客观自然的欣赏者,热爱、赞美着家园的美好景观;同时,人又成为客观自然环境的互动者,以一种“亲自然”的参与者身份,促使自己融入自然景观、适应自然景观,颜色、图案均与周围客观自然环境相协调。此刻的自然界对于白族人而言,不单纯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审美的客体,更多的是一个与“我”可以相融的“主体”,人在自身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融洽的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实践创造中人类的主体性,取消主、客体对立存在现象。
白族服饰通过图案、颜色,以尊重自然、适应自然代替与自然对立、疏远自然,体现了由服饰与自然的和谐达到人与所处自然环境之间“共生”的观念。而这种以“和”的思想指导着人们看待自我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也折射出白族人更多的生存智慧。
2.2人与图腾的和谐
白族人相信万物有灵。白族人认为,日、月、星、辰、云、水、火、山、石、昼、夜以及动植物都具有某种内在的神圣力量,它们都是有生命、有灵性的个体,而不是冷冰冰的毫无生气的审美客体。人类可通过一些方式与之沟通、融合,并为自身带来吉祥和安宁。因此,各种物种的形象在白族文化中跃升为崇拜的图腾,成为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蝴蝶是白族服饰中最具代表性的服饰图案。蝴蝶拥有美丽的姿容,除了具有连年丰收、子孙满堂以及美好爱情的符号语义外,白族还“把它视为母亲的化身。”[3]认为它拥有与人类一样的伟大母爱,这可能与白族文化中的“重母性”[4]特征有某些关联。在白族女子的飘带处常常绣制蝴蝶和山茶花,形似蝴蝶的尾翼,它寓意着蝴蝶母亲护佑着儿女,穿上了这样的衣服,自身便感觉有了母亲的保护和关爱。蝴蝶在白族文化中被赋予灵性,成为可以与人心灵交流的对象,彼此间形成一种奇妙的亲和关系。除了蝴蝶,大理白族人同样也将狗视为安全卫士,这种信赖在白族儿童的“诞生礼”服饰中更加明显。“在洱海地区白族人民心目中,诞生礼是守护生命的启端,是人生四大礼仪之首。”[5]历经战乱的白族人对于传宗接代、种族延续极为重视。在新生儿诞生后,长辈们会为婴儿穿上仪式性服饰——“狗皮衣”,白族语言称之为“kua bei”。它“通常为白色上衣,下身使用白布、蓝布或者包被包起来。”[5]“上衣领部造型多为交领,也有对襟鸡心领、斜襟等形式,一般用三根带子系结,同时在领口及衣襟等处装饰有红色布条。”[5]若从形制上看,“狗皮衣”并非制作成狗的外观,而把它与狗相联系的重要原因在于这种服饰一般是在狗的身上象征性套一下,再将其穿在孩子身上。在白族人看来,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它不但勇敢,而且还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新生儿穿上了这种“狗皮衣”,狗身上的灵气也会被吸纳到孩子身上,消灾镇邪,幼儿便会茁壮成长。在他们观念中,狗与人之间可以进行力量传递,狗为人们带来了勇敢和胆识、健康和安全,人们对狗予以信任和爱护,这种和谐关系也正是白族人所追求的。除此之外,白族人认为树是神灵的化身,它可以帮助人们消灾解难。若将树的形象和太阳纹结合在一起,生命便得以永生,“太阳纹和树纹”由此便被绣制于服饰之中。白族人也视白虎为崇拜对象,认为它们拥有镇宅驱邪、消灾降福的神力。若给小孩穿上一些与虎有关的服饰就可以达到驱除邪气的效果。于是,凶悍的虎形象便在孩子的鞋、帽等服饰中得以演绎。
白族人将对于万物神灵的崇拜和敬意通过图案的绣制得以体现,在内心则是以一种完全平等的态度看待这种神秘神灵。在白族人观念中,这些神灵不是与“我”相疏远之物,而是和“我”一样的物,它们有生命有灵魂。人们主动参与到这种与图腾所构建起的“我—你”关系中,在人神之间搭建了一座沟通和交流的桥梁,实现两者的互动,崇拜的图腾成为人的知己、朋友。借助神灵的实体形象,将美好的心愿绣制在服饰上可以为自己带来祝福,满足人们的心愿,给予人心灵上的慰藉。从宗教层面,白族人意识到自己与许多崇拜的图腾多多少少都存在着某些特殊的亲密关系,在生产实践中对于这些神灵化身——自然物产生伤害就等同于伤害自己,而尊重它们也就意味着尊重自己。可见,服饰中的图案寓意真实地表达了白族人与图腾和谐的生态审美观,体现了白族生态审美文化中所包含的浓重的自然崇拜和图腾崇拜情结。
2.3人与人的和谐
服饰作为美的实现载体是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外在表现,也是着装者之间交流的重要传感器。俗话说“观其服,知其人”,“服饰是自我表白的工具、载体。”[6]人们通过服饰中颜色、面料、款式无声地将自身的性格、气质传达给对方,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又因为“在人们的视觉感知、接收过程中,服饰上的色彩信息传递最快,情感表达最深,视觉感受的冲击力最大,而且最具美感诱惑力。”[6]因此,作为服饰组成的重要元素之一的颜色常常被视为服饰美的灵魂。
李泽厚曾对“自然美”问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人化的自然”观点,他认为“自然对象只有成为‘人化的自然’,只有在自然对象上‘客观地揭示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的时候,它才成为美。”[7]换言之,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界之物,它的美不在于自然属性,而在于社会属性。在白族人的观念中,为人厚道和清白是特别重要的品质,“‘清白传家’也作为他们传以后世子孙的准则。”[8]在大理白族服饰色彩体系中,白色成为了一种与道德相关联的词汇,“‘白’是心肝白,意即白族人胸怀宽广、清清白白、光明磊落。”[9]它被视为本民族的标志性色彩,具有符号性意义。而白族自古居住在湖泊周围,人们世代以捞鱼捕虾为生,对于世代相依的洱海便产生了崇拜、热爱之情。洱海的青色成为了白族服饰的青睐颜色,青包括毛蓝、青蓝,它代表着洱海那忠厚、朴实、宽广的胸襟,人们将白、青色作为底色,再用对比强烈的净色线,黑与白、青与白搭配绣制,代表着纯洁、善良、高尚等吉祥寓意。颜色的搭配是白族人对于自身“真善美”本性的强调和追求,蕴含着特殊的社会属性。白族人对于穿着这样颜色服饰的人格外亲切,人们携手共同热爱这片土地、这片海。白、青色彩自身的美好语义和内涵也为白族人和外界人之间的交流构建了平台,看到白色,像是看到对方的光明磊落;看到青色,像是看到对方的淳朴和踏实。这样既密切本族人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加深白族人与外族人的心灵沟通。在相互信任的心理基础上,间接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
如果将“服饰颜色传达真善美,进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作为“明显示”的话,那么“服饰的形制、服饰的来源等在社会关系系统维护中所体现的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便是一种“暗显示”。这种“暗显示”是一种隐性方式,但同样体现了白族服饰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在大理白族服饰中,“风花雪月”头饰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并且还是辨别婚否的一种重要标志。未婚姑娘头饰侧边垂下穗子,而已婚女性则没有穗子,这样,人们在恋爱时就可依头饰外观形制判断婚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不必要的混乱现象,从而间接地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此外,在洱海地区的新生儿诞生礼仪式上,婴儿均会穿着来自外祖父家的女性以及父辈家族族人送来的服装,这种穿着意味着“婴儿作为父系、母系两个家族联系的纽带,将要把两个家族的理想传承下来,从而为整个家族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生命力。”[5]力量的凝聚是整个家族的心愿,孩子成为这种心愿的延续,而传递这种心愿的载体——两个家族的服装则成为了亲密关系以及美好期望的物化形式。此时的服饰被赋予更多象征性的语言,成为融合家族关系的有效媒介。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族成员之间的和睦同样也促进了社会的整体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除了审美主体之间的关系外,也包括人与自身的和谐。这种自我之间的和谐是指“在与己相关的多重因素中寻找一种平衡关系,包括肉身与精神,劳作与休息,爱情、亲情和友情,以及生离死别等。”[10]白族服饰淳朴的色彩和图案是白族人的精神写照,通过颜色的选择、图案的搭配,展现出一种民族“真善美”的美好品质,这种美好品质也正是白族人所追求和向往的精神境界,人们穿着这种服饰,在精神的理想世界中体会着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愉悦他人的同时也充实了自己内心,实现人与自身的和谐。
3 结语
中国自古就推崇“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强调物我相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从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性美学理论。随着社会的发展,物质的丰盈,以人为主体的意识增强。最终,启蒙运动以主体性哲学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主宰地位,建立在主体性哲学上的审美观念便是将人与自然相对立,形成二元对立的局面,由此产生的矛盾逐渐加深,并且已经深刻影响到了人类的生存。但生态美学建立了与主体性美学相反的审美观念,“生态美学将和谐视为更高的审美形态,这种和谐核心是生命的存在与延续,是生命的网络系统。”[11]
服饰是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具有自然属性的同时更具社会属性。大理白族服饰作为白族文化的象征符号,通过颜色、图案、服饰寓意等将人与客观自然环境、人与图腾、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体现的淋漓尽致。这种以和谐为主导核心的审美观念不但符合现代的生态美学的要求,也适应了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因此,大理白族服饰文化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和生态美学将会对时下生态文明社会的构建起到一定的建设性和指导性作用。
[1]徐恒醇.生态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9-136.
[2] 曾繁仁.生态文明时代的美学探索与对话[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3:97.
[3] 陈萍.大理地区白族服饰图案释义[J].大理学院学报,2010,9(1):22.
CHEN Ping.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clothing patterns of the Bai Minority in Dali[J].Journal of Dali University,2010,9(1):22.(in Chinese)
[4] 何志魁.白族母性文化辨识[J].云南:大理学院学报,2011,10(3):14-17.
HE Zhikui.On the maternal culture of Bai Nationality[J].Journal of Dali University,2011,10(3):14-17.(in Chinese)
[5] 王柯,冯玲玲.大理白族人生礼仪服饰初探——以洱海地区白族为例[J].服饰导刊,2014(3):12-16.
WANG Ke,FENG Lingling.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life etiquette dress of the Bai people in Dali - a case study of the Bai Nationality in Erhai[J].Fashion Guide,2014(3):12-16.(in Chinese)
[6] 贾京生.服饰色彩[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12.
[7] 李泽厚.美学论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5.
[8] 李萨丽,郝云华.大理白族女性服饰中蕴含的美学要素解析[J].美术界,2013(5):88.
LI Sali,HAO Yunhua.An analysis of the aesthetic elements in costume of the Bai Nationality in Dali[J].Arts Circle,2013(5):88.(in Chinese)
[9] 李雯,郭爱梅.白族服饰的文化意蕴[J].云南:大理学院学报,2012,11(7):6.
LI Wen,GUO Aimei.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Bai costumes[J].Journal of Dali University,2012,11(7):6.(in Chinese)
[10] 丁筑兰.苗族生态审美观中的宗教意识——以黔东南苗族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2,33(2):157.
DING Zhulan.The research on ideology of primitive relig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of Miao people in southeast of Guizhou province [J].Guizhou Ethnic Studies,2012,33(2):157.(in Chinese)
[11] 陈望衡.当代美学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25.
(责任编辑:邢宝妹)
Ecological Aesthetics of Costume of Bai People in Dali
ZHAO Yu,KONG Fandong,QIN Deqing*
(College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Qingdao University,Qingdao 266071,China)
Combining with ecological aesthetic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attern element, color and social function of the Dali Bai people's costumes and proposed an ecological aesthetics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totem,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different human beings. Ecology wisdom which is contained in Dali Bai costume culture conforms modern ecological aesthetic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 Besides, it can play a constructive and instructional role in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e Bai nationality costumes,female headdress,ecological aesthetics
2016-02-25;
2016-03-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15CG161)。
赵玉(1991—),女,硕士研究生。
秦德清(1962—),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服装设计及服饰文化。Email:ginaqing@163.com
J 01
A
2096-1928(2016)03-03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