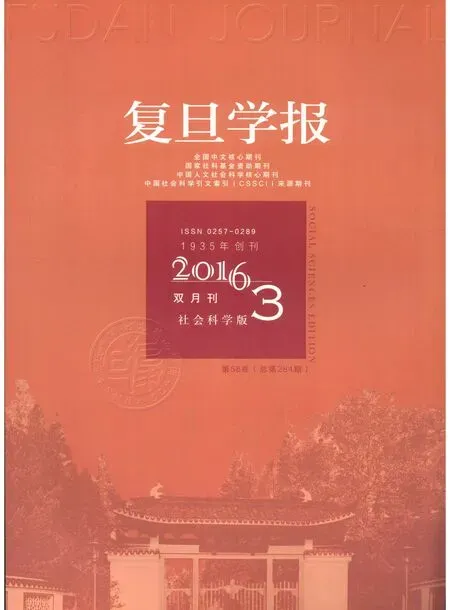中世纪西欧修女规章的发展
——以圣克莱尔修规为中心的讨论
汪丽红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 上海 200433)
世界史研究
中世纪西欧修女规章的发展
——以圣克莱尔修规为中心的讨论
汪丽红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上海200433)
【摘要】修女是中世纪修道体制的重要组成,然其所遵守的修道规章往往因以男性修规为导向而容易被学术研究所忽视。本文以西欧历史上第一个女性自己主笔并获得教廷认可的修女规章——圣克莱尔修规为中心,从历史纵向和社会横向剖析该文本中“贫穷”、“爱”、“圈禁”等核心理念所展示的时代意义,以及女性对于修规和修道的不同理解。继而在梳理西欧中世纪不同历史时期修女所遵守的诸种修道规则基础上,分析中世纪盛期修道运动的若干变化,阐释圣克莱尔修规诞生的背景及其开创性。尽管圣克莱尔修规的现实影响力有限,然而它的诞生标志着修道领域内性别意识的觉醒与实践,并打破了传统宗教写作中的两性合作模式,因此其所具有的历史意义超越了文本本身在中世纪的现实影响力。本文以圣克莱尔修规为中心考察中世纪西欧修女规章的发展,观察伴随社会和宗教本身的变迁,男人和女人对理想的女性修道模式认知的演变,以及两者之间微妙的分歧;解析在男性威权笼罩下的中世纪修道运动中,女性为获得身份认同,不得不与男性修道者之间维系既紧密追随又试图区隔的复杂关系。尽管历史处境复杂,以圣克莱尔为代表的女性以其独立的思考为修道运动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关键词】性别圣克莱尔修规修女
修规作为指导修士或修女日常生活及行为规范的文件,尽管与实际执行之间存在一定差距,但毫无疑问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对由男性主导而成的修规,例如在西欧影响深远的本笃修规,学界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然而中世纪近千年数量众多的修女们遵守何种修规?她们又是如何理解修规的?相关的英文和中文研究都不多见。本文拟围绕中世纪第一个由女性主笔为自身撰写的修规——圣克莱尔修规,试图梳理中世纪西欧修女规章发展的脉络,重新审视性别因素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历史发展中所呈现的复杂图谱。
一、 圣克莱尔修规
圣克莱尔(St.Clare of Assisi)是西欧中世纪历史上著名的女圣徒,也是圣方济各的早期追随者之一。据其传记,她在1194年出生于意大利显贵家庭,在一次听过圣方济各布道之后受到感召,决意逃避家族安排的婚姻而加入修道行列,1212年3月于波尔祖科拉(Porziuncola)发愿正式受戒成为修女,圣方济各随即将之送入附近的圣保罗(San Paolo)本笃修女院,之后又送往另一所本笃修女院(Sant’ Angelo in Panzo),随后定居圣方济各修建的圣达米阿诺(San Damiano)修女院,并担任院长近40年,直至1253年于此地去世。她不仅在方济各传统中开创了女会,还撰写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女性主笔的修女规章——圣克莱尔修规。
作为第一个女性为自己撰写的规章,圣克莱尔修规的诞生相当艰难。圣方济各本人并没有为居住在圣达米阿诺的修女们特别指定修规,克莱尔一开始加入的是本笃修女院,遵循的是圣方济各教导,包括其1209~1210年获得教皇口头许可的原始修规(现已遗失),但“没有证据表明该生活方式包含针对克莱尔及其姊妹所宣生活的任何详细规定”。*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trans. Regis J. Armstrong (Ignatius C. Brandy, New York, Mahwah: Paulist Press, 1982) 209.1215年第四次拉特兰大公会议规定,所有新成立的宗教社团,都必须遵守某个已经制定的修规。为此,1217年枢机主教胡戈里诺(Hugolino di Segni)以本笃修规为蓝本,为追随克莱尔的修女们制订了修规;1247年教皇英诺森四世修改胡戈里诺修规,是为第二修规。但是以上两个教会指定的修规都没能严格践行圣方济各的贫穷理念,克莱尔并不满意,于是着手撰写自己的修规。然而新修规提交教廷后迟迟未能得到许可,几经争取,直到1253年8月9日处于弥留之际的克莱尔才在病榻上收到教皇批准的消息,两天后克莱尔去世。
圣克莱尔修规一共12章,涉及准入、礼仪、管理等日常生活的方方方面,很多条款看上去与此前修女所遵循的传统修规似乎没有太大区别,但其所表达的三个核心理念使之真正成为中世纪里程碑式的修道文献。
第一,克莱尔与枢机主教和教皇分歧的焦点在于“贫穷”。经过克吕尼改革,12世纪西欧宗教界改革的重心从神职人员的道德状况逐渐转向宗教生活性质和信徒个体信仰,*Giles Constabl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所以在圣方济各和克莱尔生活的年代,效法基督(Imitation Christi)和使徒生活(Vita apostolica)成为核心议题。圣方济各以实际行动践行和丰富了格利高里改革时期就已提出的“使徒生活”概念,使之囊括三重含义:模仿原初教会:贫穷、简单、忏悔;炽热的爱;乞讨为生或劳动得食。*Ernest W. McDonnell, “The Vita apostalica: Diversity or Dissent,” Church History 24.1 (Mar., 1955): 15-31.三重含义的基础都是贫穷,因此贫穷在中世纪盛期不再只是一个形容词,而跃升进入形而上的领域。康普贝尔(Josie P. Campbell)分析中世纪盛行的拉撒路故事说:“表面上看,这个寓言显然是讲城市穷人的。……那些拥有权力享受世间愉悦的人注定受永恒的痛苦,除非他们将财富分享。从这个角度看,13世纪起托钵修士团可能赋予贫穷神圣的性质。”*Josie P. Campbell, ed., Popular Culture in the Middle Ages, Bowling Green (Ohio: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86) 11.事实也确实如此。13世纪后半叶一位无名作家在他的《贫穷论》(theSacrumcommerciumsancitFranciscicumdominaPaupertate)中将贫穷拟人化,并自陈来历说她原在伊甸园内陪伴亚当,揭示正是人类社会造成了贫穷的分化。圣方济各修会正是为了呼应伊甸园的无邪状态,通过自愿贫穷,试图在现世创造一个永恒不变的平等世界,将创世纪、基督时代、圣方济各时代和修会的自身历史保持在当下。*Thomas Frank, “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of Law in the Middle Ages: Franciscan Debates on Poverty, Property, and Inheritance,” Law and Literature 20.2 (Summer 2008): 255-256.从这一角度而言,贫穷绝非简单意义上的放弃财产行为,也不只是众多修道操练元素中的一种,而是真正来自上帝拥有神格的神贫,成为圣方济各修道理念和实践的核心要素。
作为圣方济各的忠实追随者,圣克莱尔在修规第6章“不要拥有财物”中全面表达了她对神贫的理解:“不得通过中间人接受或持有任何所有物、财产,或任何其它可称之为财产的东西,除了为保证修道院的适当隔离和完整所需而按需保留的土地;除非当作菜园满足姊妹所需,否则不能开垦这地。”*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p. 219.院制修道兴起之初,为了供养等问题,一些修道院拥有的公共财产和外围人员数量并不少,*帕克米乌斯建立的达本尼西(Tabennisi)修道院大约有1300人,入院者包括阿芙赛钮斯(Aphthonius)这样的贵族。而潘诺波利斯(Panopolis)城里的修道院中有15个裁缝、7个铁匠、4个木匠、12个赶骆驼的、15个漂洗工,从事种植、锻造、制作面包、木活、漂洗、制革、编篮、制鞋、制作乐器、抄写等,除供应院中日常所需外,富余的产品一部分送给女修院、监狱等作慈善用,一部分用于出售。中世纪早期西欧的修女院虽然财产状况时常陷入困境,但拥有俗家女仆也很常见,诸多修规明文规定必须放弃财产以及不得拥有私人物品等条款落到现实并不等于一无所有。克莱尔对私有财产和集体财产的双重限定从源头上遏制了修女院和修女生活滑向世俗的任何可能性。
在这一核心条款之前,克莱尔反复强调坚守神贫的重要性。本章第一句话开宗明义说自己和姊妹服从于圣方济各,接下来她说:“真福之父见我们不害怕贫穷、劳作艰辛、受苦、羞耻、世人轻视,我们反将这些视为大喜乐,被他为我们写下如下的生活方式而感动:‘既然圣灵令你让自己成为最高王、天父的女儿和仆人,以圣灵为配偶,选择按照圣福音的完美生活,我为自己和弟兄们决议并宣誓对你们和对弟兄们一样始终同样关爱并给予特别关怀。’”*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pp. 218-219.申明了圣方济各对本会修女的重视,要求修女们遵照指引者遗命,不要移志:“我们永不偏离自己怀拥的最神圣贫穷,在去世前不久,他再次为我们写下遗嘱,说:‘我,弟兄方济各,微小的,希望追随最高主耶稣基督及其最神圣母亲的一生和贫穷,坚持到永远;我要求并劝告你,我的女士,永远过最神圣的生活,身处贫穷。小心警戒不要因任何人的建议和教导背离之。’”*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pp. 218-219.圣克莱尔顺理成章地要求会中修女继承圣方济各遗志,将神贫永远坚持下去:“我和姊妹,从来心念要护卫我们曾向上主和真福方济各宣誓的神圣贫穷,继承我担任院长的人以及所有姊妹一定要奉行,不可亵渎之,永远。”*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pp. 218-219.本章“直接来自圣克莱尔”,没有引用圣经经文,而完全引用圣方济各的语言,因此在克莱尔看来自己所遵守和强调的正是圣方济各贫穷的原初本义。
克莱尔在一个规章制度中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强调贫穷,还存在更为现实的背景。方济各修会获得教皇许可后在西欧迅速扩张,不得不接受大量赠予的动产和不动产,圣方济各建立无会之会(the ordo sine ordine)的理想破灭,本人也辞去会长职务。但是神贫理想与现实组织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随着创始人去世而消失,修会因是否要坚守圣方济各原初的贫穷理想分裂成两派,并为此争论不休。为了协调双方矛盾,避免在宗教界引起思想混乱,1230年教皇格利高里九世颁布通谕(Quo elongati),区分所有权与使用权,对无可避免必须使用的土地、教堂、衣物等,圣方济各修会只拥有使用权,其所有权则归属以教皇为首的罗马教会。进而,圣方济各修会的会长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1221-1274)将财产、所有物和收益权等这些概念归属到法律范畴,论证方济各修士所涉及的“仅仅使用”(usus simplex)与法律无关,只与跟随基督和使徒的坚定意志相联。然而以上两种解释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坚决维护圣方济各原初理想的激进派代表人物法国南部修士奥利维(Petrus Johannis Olivi)批评波纳文图拉的“仅仅使用”不够纯粹,将圣方济各的神贫总结为“贫穷使用”(usus pauper)。直到1253年圣克莱尔去世后,14世纪20年代修会内部以及教会还爆发了一次大争论,*Thomas Frank, “Exploring the Boundaries of Law in the Middle Ages: Franciscan Debates on Poverty, Property, and Inheritance,” Law and Literature 20.2 (Summer 2008): 254.教皇不得不组织专门委员会进行调查和研究,最终坚持神贫理想的属灵派失败且遭到驱逐。在这场关于修会财产所有权的大讨论背景下,圣克莱尔修规对神贫的坚持并最终获得教皇许可不得不说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胜利,因此就这一层面而言,认为克莱尔不仅是圣方济各修道的女性伙伴,还是其遗产的真正继承人并不为过,而第6章也“因包含新宗教生活方式的基石”*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pp. 218-219.被认为是圣克莱尔修规的核心章节。
圣克莱尔修规传达的第二个核心理念是“爱”。“爱”在克莱尔时代的基督教世界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西多修会的主要领导人圣伯纳德(St. Bernard)的感性神秘主义*Bernard of Clairvaux, “On the Song of Songs,” “On Loving God,” and “the Steps of Humility,” Selected Works, trans. G. R. Evans (New York, Mahwah: Paulist Press, 1987).令他对爱的阐释不同于早期教父,他把爱分为四个等级:为自己的缘故爱自身、为自身而爱上帝、为爱上帝而爱上帝、为上帝的缘故而爱自己。四个等级不存在高下之分,只是自然归类。这为很多宗教女性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爱”扫清了道路,她们以女性独特的身体体验为基督教传统的“爱”增添了新内容。例如,比阿特丽斯的《圣爱七种》(SevenMannersofLove)、海夫塔修女院的大格特鲁德所著《圣爱报音》(TheHeraldofDivineLove)、海格堡的玛提尔德的《特恩之书》(TheBookofSpecialGrace)、马格德堡玛提尔德的《神性流光》(TheFlowingLightfromtheGodhead)等等,在书中她们将母子、夫妻、恋人之爱等世俗情感的元素植入宗教理解。海德维希形容她与上帝合一的体验说:“只是体验甜蜜的爱,拥抱和亲吻。”博若莱修女玛格丽特比喻基督“你不是我妈妈却胜似妈妈”。*Margaret of Oingt, The Writings of Margaret of Oingt, trans. Renate Blumenfeld-Kosinski (Newburyport, Mass.: Foucus Information Group, 1990) 31.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理解帮助中世纪盛期基督教徒从被动地畏惧上帝威权转向主动地贴近基督人性,她们认为“如此纯粹和高贵的渴望方式源自爱而不是出于恐惧。恐惧主的愤怒和正义审判,或害怕永罚,或意外的灾祸,因此恐惧令人痛苦。然而在她的事工中,爱只是导向构成自身的纯粹、卓越和至高至贵……”。*Beatrice of Nazareth, The Life of Beatrice of Nazareth (1200-1268), trans. Roger De Ganck (Michigan: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Kalamazoo, 1991) 295.大格特鲁德也认为自己更受上帝友善之爱触动,而不是对永罚的恐惧。*Gertrude of Helfta, The Herald of Divine Love, trans. and ed. Margaret Winkworth (Mahwah, N.J.: Paulist Press, 1993) 97.
以上女性写作者拓宽了对爱的理解,克莱尔也将其融入修规,表现姊妹之爱。基督教早期,圣奥古斯丁写给修女院的信恰恰就是为了解决姊妹纷争,他在这封信件中引用马太福音(7:3)“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约翰一书(3:15)“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等语句,*凯撒里乌斯修规同样引用这句话作为警戒。Emilie Amt, ed., Women’s Lives in Medieval Europe: A Sourcebook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3) 227.以仲裁者的身份劝诫姊妹之间不要争吵,要相互谅解。而克莱尔的角度不同:“如果从生理上一位母亲喜爱并养育她的孩子,那么在精神上一个姊妹应该有多么喜爱和培育其姊妹啊!”*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p. 220、222、231.“令她们热衷维护团结互爱,这是完美的纽带。”*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p. 220、222、231.因此她的修规虽然严格,某些方面甚至十分严厉,*第9章要求犯错的修女于大众广庭之下在地上取食。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p. 221.其依赖的不是对神权的恐惧,而是要在“爱”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的约束机制。
在遗嘱中克莱尔更全面地阐释了她对于爱的理解,“以基督的怜悯相互友爱,让你们信仰中的爱外显于你的行动,从而在这样一个榜样的驱使下,姊妹们在爱上帝和相互宽容中成长”,“姊妹们不仅仅因其职务,更出于爱服从她(院长等管理者)。令她也像一个好母亲对待女儿那样谨慎看顾姊妹”。*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p. 220、222、231.正是以爱为立足点,圣克莱尔修规与由男性主导的修女规章发生区别,后者出于男性对女性的预设多注重约束性,而圣克莱尔修规更关注灵性指导。克莱尔不但措辞与圣奥古斯丁不同,还着意培育修道院内朴素的民主作风:“在那里,她还必须就任何与修女院福祉和益处相关的事务征询所有姊妹的意见。”相比之下,胡戈里诺修规和英诺森四世修规没有相关条款,方济各会前后两个修士修规也未能在爱的基础上就兄弟情谊(brotherhood)予以充分体现。克莱尔重视姊妹情谊(sisterhood)并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既是时代焦点的体现,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女性对院制修道生活有着不同于男性的关注点。
第三,圣克莱尔修规继承了前代所有修女规范的基本原则——圈禁。“通过文献和考古资料复原清楚表明,许多实体修女院并不是都有防护性的物理围墙;围墙往往是概念性的:出于修规中寄予的希望、对其内居住者的部署,人们将修女院理解为圈定的,与世俗世界割裂的空间。”*Julie Ann Smith, Ordering Women’s Lives: Penitentials and Nunnery Rules in the Early Medieval West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1) 179.“死亡通过夏娃降临”,*Emilie Amt, ed., Women’s Lives in Medieval Europe: A Sourcebook, p. 23.妇女天生背负着引诱者的嫌疑,无论有无院墙,无论遵从何种修规,修女院的圈禁政策总是比男修道院更加严苛。因此不管愿望多么美好,修女院和修士院存在本质差别,后者被视为“人间天国”(paradise),前者却是“荣耀的监狱(glorious prison)”*10~11世纪作为重整本笃运动的克吕尼改革并没有为女性修道提供便利,直到西欧大地上已经为修士树立起上百座克吕尼修道院之后的1055年,第六任会长于格(Hugh of Cluny)才在Marcigny创立第一所克吕尼修女院,其初衷就是为那些克吕尼修士抛弃的妻子和姐妹设立“荣耀的监狱”。或坟墓。
圣克莱尔修规同样通过门、栅栏、布帘等隔断贫妇与外界的接触,然而比之胡戈里诺修规和英诺森修规,它在“缄默”方面要求更严,却在操作上更灵活。比如,胡戈里诺修规规定,修女正式受戒后除非建立新修女院,否则不得外出;英诺森四世修规补充“在修会总会长或修道院所在省会会长允许下”为建立、改革修道院,或管理、纠察或避免某些巨大损失可以出修道院;而克莱尔却允许修女在“某些有效、合理、有据可被批准的理由”*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p. 212、228.之下可以出院。作为一份修规,圣克莱尔修规固然有其规定性和约束性,但显然克莱尔更看重灵性培育,试图以贫妇纯洁灵性的生活为世人树立镜鉴(mirror),而这才是克莱尔“圈禁”的真正目的。
克莱尔在遗嘱中反复提到“镜鉴”一词。“就在他刚刚皈依之后,当时他还没有弟兄没有同伴,他充满圣意(divine consolation)建立圣达米阿诺教堂,他被引导着彻底放弃世界。这个圣人被圣灵照耀怀着巨大喜悦,做了一项有关我们的预言而后上帝实现了。他爬上教堂围墙冲着站在周围的可怜人用法语大声说:‘来吧,帮我建圣达米阿诺修道院,因为住在这里的女士将以她们著名而神圣的生活荣耀天父,享誉整个神圣教会。’”“主不仅把我们作为他人的榜样和镜鉴,还当作应上帝之命加入我们生活的姊妹的榜样和镜鉴,她们又再度成为活在此世人们的镜鉴和榜样。因此,主召命我们行此大事,世人的榜样和镜鉴将存于我们中间,我们真的一定要念福并赞颂主,时常在祂之中巩固。如果按照赐予我们的方式生活,我们稍作努力就会给别人留下一个高贵的榜样,获得永福的奖赏。”*Francis and Clare, The Complete Works, p. 212、228.在克莱尔看来,无论她自己还是圣方济各都希望圣达米阿诺的贫妇们通过院墙内贫穷、圣洁的生活为世人树立榜样,孕育德行,成为映照世人品性和虔诚的镜子,正如研究圣克莱尔修会的杰瑞迪恩·伍德(Jeryldene M. Wood)所说,“她将之与母子情感比较,令人觉得抚慰,包括修女纯洁的身体像圣母子宫那样蕴含基督,将修道院从监狱或坟墓变成包围、含蕴和拯救的场所”。*Jeryldene M.Wood, Women, Art and Spirituality: the Poor Clares of Early Modern Italy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9.
克莱尔对于“圈禁”的理解令其名下修女院有别于传统,因此教皇1255年封圣克莱尔时说:“她身在院墙内,却依然在外。克莱尔隐起来了,但是她生活的道路却开放了。克莱尔沉默了,但是她声名传扬。她隐居陋室,却在城镇中教导。”赞颂“克莱尔,是赐予整个世界的明镜”。*Alexander IV, Clara claris praeclara, Fontes Franciscani, ed. Enrico Menestò, et al. Assisi. (Italy: Edizioni Porziuncola, 1995)2331-2337. 英文参见http://www.franciscan-archive.org/bullarium/clara.html.
二、 圣克莱尔修规诞生的背景
从历史纵向上看,圣克莱尔修规的诞生具有开创性意义。基督教修道运动诞生于罗马帝国晚期的小亚、北非等地,本质是对基督教日益体制化的反动,追求更为灵性的生活,*安东尼等著,本尼迪克塔·沃德英译,陈廷忠译:《沙漠教父言行录》,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5页。而女性从运动一开始即介入其中。*Philo of Alexandria, “On the Contemplative Life or Suppliants,” The Works of Philo Judaeus: The Contemporary of Josephus, trans. Charles Duke Yonge (London: G. Bell, 1855), 见网页http://www.earlychristianwritings.com/yonge/随着修道运动蓬勃发展,良莠不齐,迫切需要一个制度加以规范。4世纪初修士帕克米乌斯在岩洞隐修时梦见天使晓谕,*Palladius, “The Lausiac History,” trans. Robert T. Meyer,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ed. Johannes Quasten, Walter J.Burghardt, Thomas Comerford Lawler, No. 34 (New York/Mahwah: Paulist press, 1964) 92-95.要他聚集僧侣,将独居隐修归拢为集体共修,并授予一块铜板,上面刻着修规,这就是帕克米乌斯修规。帕克米乌斯修规相当于集体隐修手册,较少高屋建瓴的理论建构,在苦行程度上趋向于较为温和的中间路线。*当帕克米乌斯抱怨祈祷次数太少时,天使告诉他说:这个修规是为大多数人制定的,他们没有很强的自控能力,那些具备这样能力的人可以在自己的单间里不受限制地沉思上帝之道。至于与之同时代的修女规范,我们则可以从帕克米乌斯的姊妹玛利亚(Maria)主持的达本尼西(Tabennesion)修女院窥见一二。达本尼西修女院与男院隔河(Nile)相望,建制完全相同,但发生在该院的一则故事显示:由于性别原因,女院更易受到伤害,昭示了未来的圈禁趋势。帕拉迪乌斯(palladius)记录说:某天一个裁缝在修女院墙外路遇一位修女,就问修女院是否需要缝衣,修女回答说她们已经有裁缝了,裁缝于是离开。这一幕恰巧被另外一个修女看见了,于是修女院内蜚短流长。路遇裁缝的修女终于不堪忍受流言中伤而投河自尽,散布流言的修女也经受不住良心谴责上吊自杀。神父听了众修女的忏悔后,裁定今后禁止她们献祭,分开禁闭7年。*Palladius, “The Lausiac History,” trans. Robert T. Meyer,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ed. Johannes Quasten, Walter J.Burghardt, Thomas Comerford Lawler, No. 34 (New York/Mahwah: Paulist press, 1964) 95-96.
帕克米乌斯修规之后,教父们对女性也多有劝导,但均未构成独立的修规体制。修女们在主教的帮助下往往借用教父为修士定制的修规,比如奥古斯丁在为解决院长选举之争写给修女们的信中所延展出的修女规则与其400年制定的修士修规内容基本一致,只在个别遣词上稍有差别。*Julie Ann Smith, Ordering Women’s Lives: Penitentials and Nunnery Rules in the Early Medieval West, p. 117.由此可见,虽然女性在修道运动诞生伊始便参与其中并占有一席之地,个别修女虔诚高洁的生活方式甚至感动、影响了巴西尔等教父,但掌握话语权力的长老或者教父们对此并未予以重视,更未曾考虑过女性修道的特殊性,而是简单地将修士修规强加其上,令其遵从。
罗马帝国覆灭后,蛮族纷纷入侵,西欧战乱不断。与此同时,基督教凭借传教士的不懈努力逐渐向高卢、英伦三岛、萨克森等地传播,这一过程中女性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裔昭印:《西方妇女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211页。因此,大约7世纪西欧地区出现了一波短暂的创建修女院和双修院的热潮。*617年伯甘多法拉(Burgundofara)与瓦德贝特(Waldebert)共同建立了布里(Brie)双修院,克罗维的王后克罗提尔德(Clothild)在莱桑德里(Les Andelys)建立修女院,里昂的Sadalberga修女院,王后布鲁希尔德(Brunhild)和主教西阿格利乌斯(Syagrius)于6世纪在图尔建立了一个供奉玛利雅和约翰的修女院,6世纪建立的雷米尔蒙(Remiremont)双修院,大约建于660年的爱尔兰基尔代(Kildare)双修院;英格兰第一所双修院是圣西尔达修道院(St. Hilda)在惠特白(Whitby)由圣艾丹(St. Aidan)监督创建的,700年左右奥斯维斯国王的姐妹艾巴(Aebba)建立的科丁翰(Coldingham)双修院,大约建于672或673年由诺森布里亚王后埃特尔特里特(Aethelthryth or Etheldreda)创立伊利(Ely)修道院,666年主教艾肯瓦尔德(Erkenwald)为他的姐妹埃泽布加(Ethelburga)建立了巴京(Barking)双修院。正是这一时期诞生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专为女性制定的修道规章。508(或509)年阿尔勒城外的阿利斯坎普(Aliscamps)修女院被毁,不得不迁往城内寻求庇护。为了抵御城内的诸多诱惑,阿尔勒主教凯撒里乌斯(St.Caesarius of Arles,470-542)以卡西安修规(Cassian)为蓝本,结合圣奥古斯丁编写的使徒书,专门为该修女院撰写修规。得益于作者本人的才华与声望,另一方面也由于凯撒里乌斯的信徒遍布高卢,担任诸多修道院院长,凯撒里乌斯修规在高卢地区女院中颇有影响力。但该修规在生活细节上规定得过于细致,比如详尽地规定了所有物件都不得刺绣或者有针脚或纺织精细,宣道所用物品不刺绣、不用银线,使用普通白布,只能用边角布料缀成的十字架,不得悬挂染的布帘,不得摆放用金属框或瓷框的人物像,*Emilie Amt, ed., Women’s Lives in Medieval Europe: A Sourcebook, p. 230、224-225.甚至规定了洗澡的时间、洗澡的方式等等,缺乏灵活性,处理具体情况主要还是依赖修女院长的个人能力和判断。更为甚者,凯撒里乌斯还规定,“不要在恶魔的驱使下在心中升起凝视男人的欲望;如果你有不贞洁的眼睛就不能声称有贞洁的灵魂:因为不贞洁的眼睛是不贞洁心灵的信号。……让她惧于令上帝不悦;令她避免罪恶地取悦男人。如果修道院的供养者或其他同他一道的男人,你们站在一起相互保守谦逊(modesty);因为你心中的上帝也同样守卫着你”。*Emilie Amt, ed., Women’s Lives in Medieval Europe: A Sourcebook, p. 230、224-225.可能正因如此,院长小凯萨莉雅(Caesaria the Younger)在写给拉德甘德(Radegund)*圣拉德甘德(Radegundis of Poitiers)于6世纪左右在波瓦第尔建立圣十字修道院,在争取当地主教支持未果的情况下,因此写信寻求阿勒尔的凯萨利雅帮助。的信中虽然盛赞凯撒里乌斯教规,但也强调修道生活最好、最基本的规章仍然是《圣经》。
几乎与凯撒里乌斯修规同时代诞生的本笃修规在整个拉丁基督教范围内取得压倒性优势,*Marilyn Dunn, “Mastering Benedict: Monastic Rules and Their Authors in the Early Medieval West,”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05. 416 (Jul.,1990): 567-594.促使当时大部分修女院接纳本笃修规,即便凯撒里乌斯影响下的修女院也往往采用混合修规,以本笃修规在内的各种规章弥补凯撒里乌斯修规之不足。6世纪晚期以后,随着爱尔兰传道士向欧陆回流,西欧许多修女院采用本笃和科伦巴(St.Columbanus)的混合修规。
综上所述,在基督教修道如此强调两性隔离的环境下,圣克莱尔修规诞生之前修女们所遵循的各类规章不是修士修规,就是打上了鲜明的男性印记,饱含男性因性别优越感生成的各种预设,或多或少都有不适合修女的地方。进入中世纪盛期,越来越多的妇女加入修道行列,迫切需要一部适合女性需求、表达女性主张的规章,而这个修规只能在妇女中间产生。
经过12世纪文艺复兴洗礼,妇女修道与此前相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第一,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增长。在500~1099年,今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地区,大约一共有3178所修道院,而修女院不到300所,只占9.4%。*Jane Tibbetts Schulenburg, Women’s Monastic Communities, 500-1100: Patterns of Expansion and Decline, Signs 14. 2,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Middle Ages: Perspectives on Women’s Communities (Winter, 1989): 261-292.即使在修道运动十分兴盛的11世纪,情形也大体相同,整个11世纪法国和比利时地区新建立的修道院中只有4%是为女性设立的,而英国于1000~1049年新建的修道院中专为女性设立的只占6.3%。*Jane Tibbetts Schulenburg, Women’s Monastic Communities, 500-1100: Patterns of Expansion and Decline, Signs 14. 2, Working Together in the Middle Ages: Perspectives on Women’s Communities (Winter, 1989): 261-292.然而英法“从11世纪晚期起,修女院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长,1080~1170年修女院从100所猛增到400所以上,到1220年这个数字大约增长到525所,到13世纪末达到650所”。*Bruce L.Venarde, Women’s Monasticism and Medieval Society: Nunneries in France and England, 890-1215 (Ithaca: Con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11.
第二,形制上呈现出多样化趋势。除了传统的本笃修女会外,罗伯特(Robert of Arbrissel,1055-1117)在1101年建立丰特夫罗双修院(Fontevrault),1131年在法国学习的英国人吉尔伯特(St. Gilbert)回乡(Sempringham)建立了吉尔伯廷双修院,西多修会名下修女院,以及加尔都西修会名下的修女院等,这些新兴的双修院或修女院都制定了相应的修女规章。保留下来的丰特夫罗双修院院规出自该院第二任院长之手,基本上以本笃修规为蓝本,补充部分也只是为了适应双修院体制。独特之处在于,其规定女院长必须拥有世俗生活经验,而不能是自幼生活在修女院的修女,遗憾的是1201年该条规定被教皇英诺森三世废除。吉尔伯廷双修院中修女们遵守西多会解释下的本笃修规,女院由三位院长(prioress)共同管理,每天的聚会由这三位轮流主持,然而在重大事件上却是男院院长拥有最终裁决权。加尔都西修女会的修规取自大规章,其制度更为严格,与同会修士相差无几,且女院院长在任何重大问题上都必须向修士咨询。以上修规在传统修规基础上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改动,这些改动虽然未能表现出某种一致的倾向性,但是反映了12世纪新型修会创立者各有侧重的革新理念。
第三,这一时期大部分改革派修会或多或少都重视发挥妇女的作用。《圣爱七种》的作者拿撒勒的比阿特丽斯(Beatrijs of Nazareth, 1202-1268)和尼维勒的埃达(Ida Nivelles)都曾经在西多修会接受教育;博若来的玛格丽特撰写《默思》*Margaret of Oingt, “A Page of Meditations,” The Writings of Margaret of Oingt, trans. Renate Blumenfeld-Kosinski, pp. 25-41.(Meditations),得到加尔都西修会的支持和鼓励;比萨的波娜(St. Bona of Pisa, 1156-1208)曾经担任奥古斯丁守规教士团女祭司(canoness)。罗伯特本人关注穷人和妇女,他成立的丰特夫罗修会特别吸引各阶层妇女,不论出身、贫富、寡妇或贞女,妓女和麻风病人都被网罗其中。1115年秋他去世前召集信徒于病榻前说:“我最亲爱的人,你们知道,我在此世为修女所建立的,我让她们控制我所有资源。为了拯救灵魂,我甚至让自己和信徒听命服务于她们。”*Bruce L.Venarde, “Making History at Fontevraud: Abbess Petronilla De Chemillé and Practical Literacy,” Nuns’ Literacies in Medieval Europe: The Hull Dialogue, eds., Virginia Blanton, Veroniaca O’ Mara and Patricia Stoop (Turnhout: Brepols, 2013) 23.11~12世纪盛行的流浪布道士非常具有煽动性,他们也特别关注妇女,比如司提反(Stephen of Muret,1052-1124)尤其关注妓女、女演员,注意聆听她们的声音。因此“男性宗教领袖人物可能比基督教历史上任何时期(当代除外)都知晓需要女性,并欢迎她们的出现,对宗教体制施加影响”。*Giles Constable, The Reformation of the Twelfth Century, p. 65.这为妇女在向来由男性主导的修道事业中发表自己的主张创造了条件。
新兴修会的创立以及各种避居隐修方式的复兴吸引越来越多的女性加入其中,为她们打开了窗口,认识到修道方式的多元性。在此背景下,修女们开始对男性主导的修规戒律发出怀疑的声音。圣灵修女院长爱洛伊斯在写给阿伯拉尔的信中质疑道:“今天的男人和女人们仍在入同样的寺院,尊奉同样的教规,较弱的女性所承受的寺规约束同男性教友没什么两样。目前,在拉丁教会中,女人同男人一样尊奉着圣本尼迪克特教规,尽管只有男人——不论是地位低者还是地位高者——才能够完全服从这种教规,因为很显然他是为男人所写的。现在暂时撇开教规的其他各条不考虑:女人们怎么可能去关心教规中所写的有关修士道袍的大兜帽、内裤或肩衣,或者他穿用的短祭袍或羊毛衫呢?”*蒙克利夫英译,岳丽娟中译:《圣殿下的私语: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书信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56页。不管爱洛伊斯是不得已还是自愿地将立论点建基于女性天生比男人软弱,但这是西欧历史上女性修道者第一次理直气壮地提出为何女性要接受男性修规的约束,反映了女性在男性威权笼罩下的修道运动中展现独立思考的勇气和能力。*事实上,在这封信中爱洛伊斯关注的重点固然在于当前修女院的需求,但她同时也通过讨论本笃修规在指导修女生活方面的缺失,延伸思考基督徒生活中律法所扮演的角色,探查男女虔敬生活中需要外在行为的有效性。因此爱洛伊斯并不仅仅是爱情故事的女主角,我们不能忽视她所思所问中表现出的独立人格。爱洛伊斯质疑几乎是一统拉丁基督教世界几百年的本笃修规谈到了男人、老人、小孩,病人等各类人,思虑周全设想了各种情况,为何就是没有讨论到女人:“我在想,当他按照男人的体质和季节的变化作出安排,以使他所制定的规章为每个人毫无怨言地执行时——如果他能为男人制定出如此的教规,他会为女人制定出什么样的规定呢?”*蒙克利夫英译,岳丽娟中译:《圣殿下的私语: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书信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2、56页。
因此,圣克莱尔修规的诞生是妇女修道运动迅速发展的需要,它践行“贫穷”、“爱”、“镜鉴”等核心理念,表达了女性对灵修规则的独到理解及其对自身的期许,打破了罗马晚期以来修女们一贯被动服从男性主导修规的传统。
三、 圣克莱尔修规的现实影响和历史意义
圣克莱尔修规产生的实际影响有限。首先,圣达米阿诺的贫妇及其修规只在一定范围内获得成功。相同建制的修女院在13世纪中叶开始超出翁布里亚地区,扩张到托斯坎纳、马凯等地,之后西班牙、英国、法国、德国都陆续建立“克莱尔贫妇”(the Poor Clares)修女院。但教皇并不愿意放任对克莱尔修女院的控制权,1263年,即克莱尔去世后第10年,教皇乌尔班四世就另行制定了一个修规,强加于除了阿西西修女院和圣阿格尼丝(圣克莱尔的追随者,波希米亚公主)在布拉格的修女院外所有圣方济各修女院,该修规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拥有集体财产,遵守该修规的被称为圣克莱尔修会(O.S.C),继续严守圣克莱尔修规的则被称为克莱尔贫妇(P.C.),前者的数量比后者要多。
其次,克莱尔“贫穷”和“爱”的核心理念虽然令“圈禁”有了新的含义,但性别的偏见并没有就此消失。实际上,从一开始圣达米阿诺的贫妇们就遭遇尴尬。1221年胡戈里诺作为贫妇们的保护者,试图任命方济各修士菲利普(Fra Philip Longo)担任修女院的巡查员,不料方济各大怒,批评菲利普是修会的恶性肿瘤和破坏者,胡戈里诺不得不妥协,转而任命西多会教士看守女院。多数方济各修士并不愿意为女院提供教牧,视之为甩不掉的麻烦,为此抱怨连连。1263年修会会长波纳文图拉收到阿拉贡(Aragon)省会长转过来的一封信件:“毫无疑问你明白,亲爱的兄弟,我们修会因为圣克莱尔修会名下修道院引起的威胁、麻烦和诉讼而多么烦扰。这都是因为她们请求教宗在不利于我们的指控当中宣布并立法规定我们必须为她们提供仪式服务;因此,除非兄弟们首先认识到圣父在公开文献中赐予我们的完全自由,否则不宜与她们有过多的联系。”*Lezile Knox, “Audacious Nuns: Institutionalizing the Franciscan Order of Saint Clare,” Church History 69.1 (Mar., 2000): 41-62.同年在比萨召开的修会大会试图解除男院和女院的关系。尽管由于教皇乌尔班四世和波纳文图拉的坚持,该决议最终没有通过,但双方的纠缠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关于该问题的详细论述可参考Joan Mueller, The Privilege of Poverty: Clare of Assisi, Agnes of Prague, and the Struggle for a Franciscan Rule for Wome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直到1296年教皇将修女们置于圣方济各会保护枢机的管辖(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ardinal Protector of the Franciscan Order)*Jeryldene M.Wood, Women, Art and Spirituality: the Poor Clares of Early Modern Italy, p. 30.之下才得以缓和。
再次,13世纪末14世纪初妇女修道的形势日益严峻。1273年方济各修士图尔奈德吉贝尔(Guibert of Tournai)为第二年在里昂举行的大公会议撰写了一份提案(De scandalis Ecclesiae),说“我们这里有叫做博格因的妇女,她们中的部分人以热衷投机、诡诈闻名。她们解释就是最精通圣经的专家也难以理解的圣经奥义,并翻译成通行俗语。在她们小小的修道院里、在工作间里,甚至在公共场所,一起诵读这些文本,十分大胆,没有应有的尊重。我亲眼看见、读过,并且手里就有一本法语本圣经,这样的本子在堂区书店里任何人都能买到,异端、谬误、可疑、彻头彻尾愚蠢的解释由此可能被复制……摧毁那些本子,约束翻译者,烧死那些确证满嘴谎话的人”。博格因这类以妇女为主导或妇女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半修方式(semi-religious)遭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各地主教不同程度地予以压制或驱逐,而正规修会也开始注意保持其与女院之间的距离。1274年里昂大公会议措辞严厉地重申第四次拉特兰大会决议,并特别指出:“我们永恒绝对禁止所有未经教宗许可,在上文所说大会之后成立所有宗教生活形式和托钵修会,我们抑制它们传播。”*Norman P, Tanner S.J., eds.,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Volume II (London and Washington D.C.,: Sheed& Ward,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1990) 326.禁止成立新的修团,将现有非规范女性修道团体归并到传统修会体制中去,导致女性在修规方面独立发表意见的机会越来越少,她们大多只能在现有修规基础上进行适度修改,圣克莱尔修规也因此成为修女规章史上无从跨越的高峰。
然而该修规的意义远不止于为圣方济各女会提供了一份合适的修女规章,它的历史意义远大于其现实影响。作为西欧历史上第一份出自女性之手的修规,它实现了两个方面的突破:
第一,标志着修道领域性别意识的觉醒。从隐修活动兴起一直到中世纪早期,在这长达七八百年的时间里,基督教修女在关乎自身日常生活方式的修道制度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这固然是与当时西欧修女院数量较少的整体状况相适应;究其根本原因却在于长期流传的修道理念。妇女一旦加入修道院,就脱离了“婚姻的弊病、孩子们的哭闹、讨厌的领居、忙不完的家务”,进入神的领域,同时也丧失了身为女性的性别特征而成了男人。哲罗姆(Jerome)训导说:“既然女人的功能是生儿育女,她的灵魂同身体一样与男人有异。但如果比之沉溺世俗,她更愿意侍奉上帝的话,那么她就不再是女人,而应被称为男人。”教父们赋予男性气质更高的评价,无论多么欣赏女性,他们内心依然将亚当的堕落归因于女人,是爬蛇率先攻陷的对象,女人不但本性脆弱,其本身就是诱惑和邪恶的代名词。因此当他们夸赞坚守宗教生活的女性时更愿意将之比作男人,比如纳西昂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azianzus)称赞他守寡的母亲拥有男性的灵魂,尼萨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Nyssa)认为自己的姐妹玛卡瑞娜(Macrina)超越了其女性的本性。*Jo Ann McNamara, “Sexual Equality and the Cult of Virginity in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Feminist Studies 3.3/4 (Spring-Summer, 1976): 145-158.在教父们教导下,修道女性似乎也怀有同样的认知。在皮鲁西恩(Pelusium)沙漠隐修的爱玛·萨拉(Amma Sara)批评修士们时就自称“我是男人,你们是女人”。*Palladius, The Sayings of the Desert Fathers, trans. Benedicta Ward (London and Oxford: Cistercian Publications, 1975) 229-230.大格里高利(Gregory the Great) 记载有一位寡妇坚持要过节欲的生活,医生警告她说压制欲望产生过多的热度会让她像男人一样长出胡子,这个寡妇为了灵魂的益处很开心地接受了变成畸形的可能性。*Jo Ann McNamara, “Sexual Equality and the Cult of Virginity in Early Christian Thought,” Feminist Studies 3.3/4 (Spring-Summer, 1976): 145-158.妇女在进入修道院之后一定程度上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当作了男人,因此无论在教父还是修女自己看来,与修士一样恪守修士规则难道不是应有之义?他们和她们根本不认为在男性修规之外,还需要根据女性生理和生活特征设立修女修规。圣克莱尔修规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这一固有观念,从女性自身需求出发制定修规。从这一角度而论,圣克莱尔修规的突破性意义不仅在于作者的女性身份,更在于它试图赋予原本无性别,实质只具备唯一性别——男性的神之领域以性别意识,在其中为女性立言。
第二,克莱尔打破了一贯以来宗教男女合作的写作方式。爱洛伊斯在写给阿伯拉尔的信中请求道:“我们这些基督的婢女们,也是你的基督女儿们,有两件事恳请您指导,这两件事于我们自身而言是非常有必要弄清楚的。其一是请你指教我们有关修女会的来龙去脉,以及我们所从事的职业的权威所在;其二是请你为我们制订一种教规,并形成文字,这种教规应当适用于女人,而且也请你详述一下我们该保持的生活方式和习惯”。*蒙克利夫著,岳丽娟译:《圣殿下的私语:阿伯拉尔与爱洛依丝书信集》,第52页。爱洛伊斯熟读经文,精于拉丁,善于思考,觉察到修女们的迫切需求,却没有自己着手整理撰写修规或编写修女历史,而是遵从传统,请求男性导师阿伯拉尔答疑解惑。这是基督教创教以来即形成的一种两性写作模式:由妇女发起并敦促男性撰文。例如,罗马晚期伊塔莉卡(Italica)和柏丽娜(Paulina)请求奥古斯丁为她们写下人类对上帝的认识,而这些书信后来构成其撰写《上帝之城》的素材;富孀玛塞拉(Marcella)请求哲罗姆为其解读希伯来圣经文并各种经义,哲罗姆抱怨说:“你自己不写任何东西,除了折磨我,迫使我读经。”*Kimberley Benedict, M. Empowering Collaborations: Writing Partnerships Between Religious Women and Scribes in the Middle Ag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4) 4.类似的案例还有阿尔昆和查理曼的孙女古德拉达(Gundrada)、达米安(Peter Damian)和阿格尼丝皇后(Empress Agnes)等等。因着妇女们的反复究问诞生了基督教历史上不少经典作品,但无论女性在这些作品的诞生过程及其内容上发挥了多少影响力,她们始终隐身其后,几乎从未走上前台。事实上,达米阿诺的贫妇刚刚成立时,克莱尔也没有撰写修规的打算,直到教会前后制定的两份修规都未能贯彻圣方济各的神贫理念,而作为精神导师的圣方济各又业已去世,克莱尔这才不得不将女性已经让渡出去或者说被剥夺的写作权利收回。它的出现有一定偶然性,却无疑打破了妇女有问题就求诸男性落于笔端这一女性参与基督教写作的传统模式,特别在宗教管理文献上这是第一次。自此,女性在某些事务上可以不再求诸男性,而是自己动手表达主张,比如1344年瑞典的圣·布里吉塔(St.Brigitta)创立布里基廷双修会(order of the Brigittines)并撰写了修规,该修规在1370年获得教皇批准;14世纪西欧各地盛行编辑修女院姊妹书,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她们自己撰写编辑完成的;15世纪圣克莱特(Saint Colette)改革方济各第二会时在圣克莱尔修规基础上多次动手修订等。
但在肯定圣克莱尔修规价值的同时,我们不能高估它在中世纪性别意识方面的贡献。它虽然唤醒了修道领域的性别意识,然其所矢志继承的却是男性导师圣方济各的意志;它标榜全面追随圣方济各,却一开始就放弃了其“赤身追随基督”流浪传教的核心理想,实施严格的“圈禁”政策;在极力强调女会独特镜鉴作用的同时,却又努力维系与圣方济各第一会(即男会)的特殊联系,而这些矛盾现象恰恰体现了中世纪修道妇女复杂的历史处境。修道妇女要在教会中获得身份认同,必须在男性威权的话语框架下寻求适度的自我表达,这个适度既是自愿也是现实约定,难以区分,从而令性别因素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体系中呈现出一幅复杂图像。
[责任编辑陈文彬]
The Development of Rules for Nuns in Medieval Western Europe: The Rule of Saint Clare
WANG Li-hong
(DepartmentofHistory,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Abstract: Nuns wer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medieval monasticism. However, the rules for nuns have been easily ignored by the researchers because they were made or dominated by men. Centered on the rules of Saint Clare that was first initiated by female and recognized by the Curia, this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meaning of some special words, such as “poverty,” “love” and “prison” in the rule, and discusses how women imperceptibly reshaped the image of an ideal monastic female that had been made only by fathers in old times. It takes notes of the changes of the cognitive modes on the ideal convent both by male and female, as well as the subtl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makes analysis of how female had to keep complicated relations with male friars to gain their identity recognition in the background of overwhelming male authority in the medieval movement of monasticism. The rules of Saint Clare had not been adopted by many convents except for P.C., but it did change the role of women in monasticism; that means women would have attended and attributed more than our formal imagination to the movement of monasticism which was dominated by men in that time.
Key words:gender; the rule of Saint Clare; nuns
[作者简介]汪丽红,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