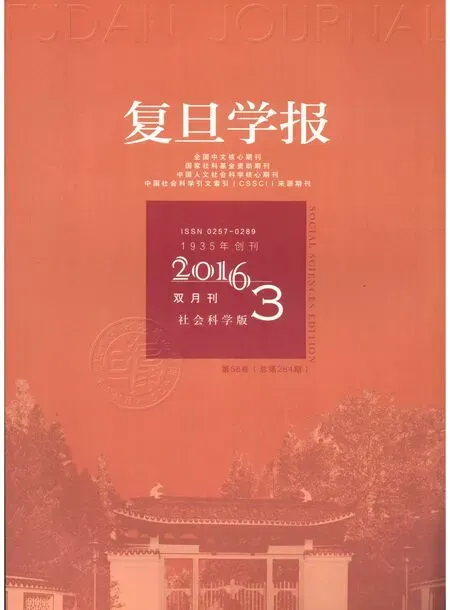古代文艺才器思想论
赵树功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宁波 315211)
古代文艺才器思想论
赵树功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宁波315211)
【摘要】才器思想肇始于汉魏之际,它是在以器为用、成用为德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文才出发讨论德,就必然要涉及这一论题。具体到文艺范畴的才器思想,其于主体素养强调器量、器识,关注文才的涵受居守之道;于创作则以文学艺术美学价值与现实功用的关系协调为归趋。从魏晋六朝至隋唐,相关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六朝时期强调贵器用而兼文采;隋朝李谔代表政府发声,继承《诗大序》所宣扬的儒家文学思想本义,从文艺本位立论,强调崇本(质)抑末(华);唐代裴行俭则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先器识而后文艺”说。后世才器思想的继承大致延续了以下两个维度:器识与文艺离、器识与文艺合。但无论离合,关注主体人格境界、文艺社会价值的立场是一致的。以器识为观照,王国维所批判的羔雁的文学、啜的文学,既是古代文艺创作的弊病,也是当代文艺的镜鉴。先器识后文艺的思想虽然不乏功利主义的偏见,但作为一种警示,也时时提醒文人不能沉醉于风花雪月的梦幻与辞事韵调的经营,要具有济世热肠与现实情怀。
【关键词】才器文才器用器识先器识后文艺
才而论“器”,是才的效益最大化发挥与避免虚浮无实而引申出的必然命题。具体到文艺范畴,所谓“才器思想”主要是指文才发挥与器量、器用、器识的关系。于主体素养而言,它强调器量、器识,关注文才的涵受与居守之道;于创作则以文学艺术美学价值与现实功用的关系协调为归趋。文艺才器论肇发于六朝,深化于唐宋之际。其间具体的思想虽然时有出入,但主体的修养与文艺的现实关怀却获得了历久不易的坚守与认同。
才器思想属于中国古代才德关系理论的重要内容,但当代学术界缺乏系统的关注。本文从才器论的演化生成及主体内容、才器论的继承维度、才器论观照下的文艺病弊入手,在综括古代文艺才器思想的同时,希望能为当代文坛提供借鉴。
一、 器的意蕴拓展与才器论的形成
从训诂学角度看,正如许慎《说文解字》释称:“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段玉裁注云:“饭食之用器也。”含味其意:器就是装盛饭食、物品的用具。用具各有其功用,此为器用,戴侗《六书故》即释云:“器,用也。”*戴侗著,党怀兴、刘斌点校:《六书故》,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23页。初民觅食艰难,四口中间有犬以守,正说明所装载者极为重要;凡器物之用皆主乎容受,自然以容受量大者为优,此为器量。
春秋之际,器的应用从物质领域延伸至精神层次,成为人才评判的标尺,其核心意蕴集中于“成务为用”。如《老子》便不止一次明言“器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人之器而不用。”苏辙疏解:“民各安其分,则小有材者,不求用于世。什佰人之器,则材之什夫佰夫之长者也。”*苏辙:《老子解》,《文渊阁四库全书·道家类》第1055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35页。这里的器用被直接阐释为了才用。《论语·公冶上》:“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瑚琏本是古代宗庙祭祀用的黍稷盛器,故此孔安国解为“汝是器用之人”,朱熹亦云“器者有用之成材”*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93页。,以成用、才用释器。
器的功用并非缘乎他物,而是自成根苗,得之自然,属于主体之德的范围,*“德就是得”的结论,系学者们通过对卜辞中“德”字的考释得出的,意见较为统一。因而春秋之际论器以言功用的同时,也逐步将其用于道德的描述。如《论语·八佾》:“管仲之器小哉。”随后列举管仲不俭、无礼等病累,以此言其德行。于是,成用与德也便呈现出一定的融合迹象。整理先秦文献形成的《礼记》中有专门的《礼器》篇,其核心思想即以器用为德,其中云:“礼器,是故大备。大备,盛德也。”郑玄注:“礼器,言礼使人成器,如耒耜之为用也,‘人情以为田’,‘修礼以耕之’,此是也。”*朱彬:《礼记训纂》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357页。修礼而行乎人情世界,就如整顿耒耜而耕种,如此方有收获,这便是以具礼成用为盛德。而东汉之际“德器”连文,既是以器为德的体现,也是以成用为德思想的发展。*班彪云:“崇简其人,就成德器。”《后汉书》卷40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28页。
器要成就器用,所依托者便是本身材质所具备的“形名度数”。古人论器,“举一器而形名度数皆该其中”,*参阅朱彬:《礼记训纂》卷10郑玄注、王懋竑注,第357页。如此则其用便有了具体的指向。从材质、器用论器,是才、器理论关联确立的内在根据。东汉王充从器用容量出发,明确揭示了才、器的本然关联。《论衡·程材》云:“世名材为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王充以为,儒生博通,即为器量之大者,因而秀出群伦;而才在当时又被称为“名器”,才器一体,故而器大盈物者必然材大用广。*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45页。按,才、材二字古代相通。班固论屈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班固著:《序离骚》,《楚辞章句》附,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48页。也是才、器对言,以才为器。
器的认知深化以及器、才统一性特征获得确认的时代,正是才性理论蔚然兴起的时代。作为才、器认知融会结出的果实,“才器”范畴于汉魏之际开始流行于人物品目。班固论汉代名臣就曾言:“自(王)吉至(王)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称,稍不能及父。”又如《三国志·蜀书》有“才器过人”之目,东晋郭璞注《尔雅》“佌佌琐琐,小也”云:“皆才器细陋。”*参阅《三国志·蜀书》卷39,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4册,第983页;《汉书》卷72,第10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068页;邢昺《尔雅注疏》卷4,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十三经注疏》,第2590页。《世说新语》及其注文中以才器论士更是屡见不鲜。
随着才器范畴及其意蕴、价值取向的扩散,器的内涵深深浸入道德人格考量,才器的内涵由此获得了较为完整的定型。从涵受而不轻易泄露之德论才器,引申而出的就是器识范畴。器识论也出现在两晋之际,如《世说新语·方正》注引《晋诸公赞》言山涛之子“雅有器识,仕至左卫将军”,《世说新语·识鉴》注引《晋书》“(杨)朗有器识才量,善能当世,仕至雍州刺史”等。*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472、295、396页。魏收《魏书》也有“崔逞文学器识,当年之俊”等品鉴。*魏收:《魏书》卷32,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67页。所谓器识,就是器用与识度的综合,呈示于尽务成用之志与明辨是非见机而作的识见,以及不为苟且、能容堪受的胸襟。正如曾国藩所论:
试之以富贵贫贱,而漫焉不加喜戚;临之以大忧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谓也。
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识之谓也。*曾国藩著,王澧华校点:《黄仙峤前辈诗序》,《曾国藩诗文集》文集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35页。
这种解释已然有了出于标立模范目的的理想化设定,但合乎器识诞生之际包纳成用有为及其德性保障的内蕴。无论内敛涵受的器量还是成务为用的器用,皆为德器的体现,是主体之德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才与具其功用、且可纳入德性理解的器相融,“才器”由此诞生。它包括以下涵义:
其一,“才器”的本义就是以器物比附于人才。如戴震所言:二者于材质或质地相比附:“以人物譬之器,才则其器之质也;分于阴阳五行而成性各殊,则才质因之而殊。”二者于精粗成色相比附:“为金为锡,及其金锡之精良与否,性之喻也。”二者于彼此赋分命定相比附:“其分(指为金为锡及精良与否)于五金之中,而器之所以为器即于是乎限,命之喻也。”*戴震著,何文光整理:《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9页。人才相异,就如同器物的区分。由此看来,“才器”范畴的出现,实则就是主体假物以观照自我才性的手段。
其二,《易传·系辞上》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才本虚灵,器有形质,“才器”就是才呈示于器用器识,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
其三,主体所具有的器,可以纳才于其中(或负才于其上),它既可衡量才之大小,又能保持才涵蓄有力而不轻易泄露。正如刘熙载所云:“才非器,则无以忍屈伸、超荣辱、公恩怨。而薄物细故得以动之,始虽或幸有所立,非所以适于久大矣。”有器以涵之,则才可以在该显露之际显露,在应隐忍之际隐忍,如此方可获有才之利而不受多才之害。因而“才各有所能施,器各有所能受”,*刘熙载著,薛正兴校点:《持志塾言》卷下,《刘熙载文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页。器承受的大小,决定了才施为的大小以及个人成就的高下。
从以上所论器对才的影响而言,器可以理解为“居才之道”:“才固难也,居才尤难。士之挟一长而掉头嗔目,侈然谓‘莫己若’者,限于器也。”*施闰章:《书带园集序》,《施愚山集》文集卷6,合肥:黄山书社,1992年,第119页。器代表了修养的程度,由此决定了才施展的空间。
二、 从“贵器用而兼文采”至“先器识而后文艺”
从魏晋至隋唐,才器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
阶段一。器被纳入文艺理论探讨始于《文心雕龙·程器》,由于刘勰论文标榜天才,因而本篇论文与器,其本质就是才与器的关系研讨,核心思想即“贵器用而兼文采”。
首先,刘勰对文人才器的论述是从文采与器用两方面展开的。这在本文开篇就已鲜明揭橥:“《周书》论士,方之梓材,盖贵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朴斫成而丹艧施,垣墉立而雕杇附。”《尚书·周书》有“梓材”一篇,论人才辨析。梓有文饰,故有“文梓”之称。据此吴林伯按:“则梓材犹本书《熔裁》所谓有文采之‘美材’。”以梓材喻人物之美,而其标准就在如梓之文采与备其器用。*吴林伯:《文心雕龙义疏》,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32页。下同。文采、器用兼容论的基础就是儒家提倡的文质彬彬。刘勰尊儒,视此为文人的立身之本。以此为根据,他将汉魏六朝以来的著名文人纳入观照:“近代词人,务华弃实,故魏文以为古今文人之类不护细行。韦诞所评,又历诋群才。后人雷同,混之一贯,吁可悲矣。”曹丕、韦诞讥评文士病累已为人熟知,刘勰是带着很强的感慨论及这一点的:前贤耳提面命,一一摘斥,却毫无效果,后之才子们依然不以为戒,与前代失德者雷同,实在令人悲叹!随后便列举了十六位汉魏著名文人,一一论其“疵”之所在。刘勰此处以“疵”为不护细行的失德,而对这种行为定性之际,他使用的标准就是“务华弃实”。“华实”意同于“文质”。本节文字表面,着意在德,实则是说以上文人不能成其器用故而一味炫耀文华,生成偏弊,刘勰之意正在于摘刺诸公文才文采与器用难以统一。
其次,在文采基础上格外强调器用的意义。由器用论文人之德,在六朝之际可谓通识。刘勰是相关思想的集大成者,《文心雕龙·程器》篇将成用视为文士之本然:“盖士之登庸,以成务为用。鲁之敬姜,妇人之聪明耳,然推其机综,以方治国。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即使居家主内不以究理事务见长的妇人,尚且能够随时引譬、明晓大义以助成功勋,昂昂丈夫岂能仅仅拘乎刀笔而无所作为?成务为用,由此被明确凝聚到“达于政事”。既明乎文又成其政事之用也便成为真正文人的价值所在。《文心雕龙》其他篇章同样贯彻了这个思想,诸如《原道》言人文目的在于“彪炳辞义”以“鼓天下之动”;《议对》认为“辞以治宣,不为文作”;《辨骚》认为《离骚》之所以自铸伟辞,正是因为屈原“壮志烟高”、有着治国美政的规划。皆在文才文采的基础之上孜孜劝以济世经济。*吴林伯:《中国古代文论家论作者修养》,《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
概而言之,《程器》篇才器论的核心便是文艺才华与政事机能、文章之美与用世之智都应兼备,此即“摛文必在纬军国,负重必在任栋梁;穷则独善以垂文,达则奉时以骋绩”,凡此种种,皆属“君子藏器,待时而动”之意,是富有才器的体现。
阶段二。隋际鉴于六朝文艺雕绘满眼的情形,从官方发起了反思。李谔代表政府发声,其《上隋高祖革文华书》便是这种反思的代表。本文在此前泛论文质彬彬艺术形态的基础上,从文艺本位对“华”与“实”两种创作风体及其社会效用作出辨析:“实”即有本有源有益于世,“华”即绮丽浮靡。并以官方立场推广求本求实的写作:“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劝惩,义不徒然。”以劝惩为切入点,正俗调风、褒德序贤、明勋证理皆为诗文器用。求末求华者恰恰相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李谔概括这种创作(主要指向五言诗)的主要特征:体尚轻浮、竞骋文华——驰逐才气以博俗誉,而应有的担当则荡然捐弃。这一切皆可归结于“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的“损本逐末”。“用”与“无用”两个范畴的对比,虽然从学理上讲忽略了文艺的美学特征与美学之用,但作为对六朝贵族文艺骋才风尚的清算,于有为有用的呼唤,也强化了文艺本来就具备的现实功用维度。*魏征:《隋书》卷66,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5册,第1544页。
阶段三。六朝强调文采器用兼具,器用多指向事功;隋际文人开始在文艺本体范围之内论器用,将其从政治事功之作为拓展至文艺功用。两种主流才器思想在唐代实现了融会,裴行俭“士之致远,先器识而后文艺”的论断由此诞生。*欧阳修:《新唐书》卷108,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册,第4088页。这个论断相比此前的思想变化有二:一则原先并言的两个部分,至此被分出了先后,器用器识居先,文才文采居后;一则刘勰所论“器用”被调整为“器识”。
就先后次序而言。先器识而后文艺,与先道德后文艺、德弥厚而文弥高、德本文末等论有相近之处,只不过器识在才德关系维度上是德丰富意蕴的具体化形态之一。所谓先后并非是一个时间概念,意味着先从事于政事,随后才可言乎诗文辞赋。其主旨在于区划文艺与器识的地位轻重,警示文士们把握人生价值取向的大势,强化主体道德人格与经世致用的修养。裴行俭在以“先器识而后文艺”这种思想评判王勃等才子之际,以为正因为才子们“浮躁炫露”,没有器识,所以虽有文艺才华,却依然不可能“享爵禄”——这是刘勰所谓“达于政事”的途径,也是历代文人以为光宗耀祖的首务。这种因果逻辑,显然是将“器识”与兼善天下结合了起来,其中自然包括先务功名,退而游于艺。但更多则表现为:以济世苏世为终身之志,以实现如此襟抱为信念,佩之携之,义无反顾。但凡合乎以上前提,有情怀、有兴会、有闲暇自可怡然命笔。可见“先器识而后文艺”是一种志量的条件,并不存在要不要文艺、何时方可寄情于文艺的规限。
而在“器识”对“器用”的代替中,则有着对文人更高的要求。器识之论中兼容着器用,不过魏晋六朝论器识,在才具器用之外,其识的意义多源自玄学的通明悬览与佛学对识的显扬,集中于明析物理事理。但自汉魏、魏晋更迭至南朝的倏忽易姓,文人各附势家,不守其节,明乎物理事理却不辨义理,其所谓识在儒家思想的大道观照之下,也便显示了其乱世求全的苟且性。即令如此,器识也未成为其时尊奉的圭臬,反而是无为逍遥、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了数百年的风尚。唐代国家一统,文士们鉴于魏晋六朝的乱象与文人的无为无节,将器识尊为大德,并在玄学之识、佛学八识心王之识的基础上将明乎义理纳入识中,因而较之魏晋六朝之际论器识又有了极大的提升。
三、 “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后世承继维度
“先器识而后文艺”的思想随后各代都得到了维护,其承继维度主要包括以下两端:其一,将器识与文艺视为实行与艺术创作的分野,从器识文艺的主次、本末地位来考量,提倡文人应当以器识器用为先务、首务,文艺则为闲暇消遣之末品。这一思想以宋代文人较为突出,如石介云:
天下之所尊莫如德,天下之所贵莫如行。今……不修乎德与行,特屑屑致意于数寸枯竹、半握秃笔间,将以取高乎人,何其浅也!*石介:《答欧阳永叔书》,《石徂徕集》卷上,《丛书集成》初编本。
尚德崇行,而于文辞则深致不屑。这种意见有其偏执之处,也与现实境况的焦虑及反思不无关系。宋景德年间,契丹屯兵澶渊城下,当时大臣素不讲习韬略,故而相顾惊骇,时人嘲笑:“何不赋一诗退虏?”其事其论乃是有所激而为,影射出国家危亡之际时人于器识器用的迫切期待。及其极端,则有刘挚教子孙“先行实后文艺”,置换裴行俭的“器识”为“行实”,并声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脱脱:《宋史》卷34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1册,第10858页。。如果说论文人当备器识尚属于修为上的标准,兼容着人生不同的求索,且如刘勰所云有待时而动之意,那么“先行实后文艺”,则将器识的丰富内蕴坐实并凝定于行实。如此置换不仅明确将文艺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也赋予了施行先后的顺序。即使诗赋文辞不尽废弃,也只关心所谓“言则本乎情性关乎世道”的创作,其“辨篇章之耦奇,较声韵之中否,商骈俪之工拙,审体制之乖合”等于艺术审美的穷探力索,一概纳入“有之固无所益,无之亦无所阙”的范围。*魏了翁:《裴梦得注欧阳公诗集序》,《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54,《四部丛刊》初编本。
对文艺的不满进而引发了宋代文人对人才选拔制度的反思。王禹偁云:“古之君子之为学也,不在乎禄位,而在乎道义而已。用之则从政而惠民,舍之则修身而垂教,死而后已,弗知其他。科举已来,此道甚替,先文学而后政事故也。”*王禹偁:《送谭尧叟序》,《小畜集》卷19,《四部丛刊》初编本。科举考试偏重诗文,其于人才遴选便被解读为先文学而后政事。王安石变法呼应了这种反思潮流,不仅科举考试废止诗赋,即使文人的闲题漫吟也被纳入违禁。改易力度不可谓不大,但其后人亡政息,科举也渐复旧貌,不过经义策士却由此流行起来。至南宋末年,叶适对此依然表示不满,其《宏词》首先通过对南宋流行的四六骈体文章的挞伐,抨击了科举词科之弊:
自词科之兴,其最贵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为陋而无用。士大夫以对偶亲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联之工而遂擅终身之官爵者。……其人未尝知义也,其学未尝知方也,其才未尝中器也。
进而将矛头专门指向南宋以经义策士而终以宏词选官的矛盾:
且又有甚悖戾者。……绍圣崇宁号为追述熙宁,既禁其求仕者不为词赋,而反以美官诱其已仕者使为宏词,是始以经义开迪之而终以文词蔽陷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已为宏词,则其人已自绝于道德性命之本统,而以为天下之所能者尽于区区之曲艺,则其患又不特举朝廷之高爵厚禄以与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于不肖而不可救。*叶适:《水心集》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别集类》第1164册,第933页。
王安石求功用而立实学,罢词赋而试经义,不久便难以维持。南宋之初,虽然号称追溯熙宁,人才选拔再一次摈斥词赋,但经义进身之后如欲得高官厚禄,又必经宏词考试,最终又归于文艺。所以叶适以为行事乖谬,不仅科举词科应当改革,即使宏词也当罢黜。其立论的出发点就在于:如此选拔出的文士“其才未尝中器”。当然,叶适所论才器有着更高的要求:既要中器,即合实用;又要知义知方,即明乎义理。
宋人之后,这种从本末观照器识与文艺的思想时时被祭起,郑燮曾将文采富赡的才子们一笔抹煞:“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郑燮著,吴可点校:《与江滨谷江禹久书》,《郑板桥文集》,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127页。清人反思八股,也从才子文人之虚浮无用痛下针砭,如左宗棠就称:“八股愈作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古人经济学问,都在萧闲寂寞中练习出来,积之既久,一旦事权到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目今人称为才子,为名士,为佳公子,皆谀词,不足信。即令真是才子、名士、佳公子,亦极无足取耳!”*吴庆坻著,张文其、刘德麟点校:《蕉廊脞录》卷8引,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34页。这其中已经包含大厦将倾之时的焦灼。
先器识后文艺、先行实后文艺之论中,器识所强调的经世之用独立于文艺之外,因而以上之论可以称之为器识、文艺相离之论。
其二,从强化文艺的功用出发,要求创作要体现出器识道德,此即器识、文艺相合之说。于创作而论先器识后文艺,历来没有异议。陆游虽然曾说:“唐人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是不得为知文者,天下岂有器识卑陋而文词超然者哉?”仍然是先器识而后文艺论的另一种认定形式。在陆游看来,真正知道文艺为何物的文人,必然是有器识的,否则不可能有作品中的超然之气。明人徐树丕很赞赏这个思想:“此言深得文章大旨。古今来非无文章美赡而人多卑污者,然其文必无超拔之气。”*徐树丕:《识小录》卷1,涵芬楼秘笈本。这实则就是一种器识、文艺的相合之论,也可以视为器识、文艺的因果之论,虽然以器识为根基,但归结点却在于文艺本身。作为唐人之论的折中,这种学说得到众多文人的肯定,袁宗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便是这种观点的代表。
文章首先论述文人当敛才而养德养器识:“夫士戒乎有意耀其才也,有运才之本存焉。有意耀其才,则无论其本拨而神泄于外,而其才亦龊龊趢趢,无纤毫之用于天下。夫惟杜机葆贞,凝定于渊默之中,即自弢其才,卒不得不显。盖其本立,其用自不可秘也。”袁宗道是从如何才能创作出真正佳作这个角度讨论先器识而后文艺的,因此,其所谓“本”更多集中于道德与人格的境界,而于经世济用则语焉不详。为了说明自己立文之本在于道德器识这个基本思想,他随后列举了一批因德不立器识不修而遗恨致祸者:
晚代文士,未窥厥本,呶呶焉日私其土苴而诧于人。单辞偶合,辄气志凌厉;片语会意,辄傲睨千古。谓左屈以外,别无人品;词章以外,别无学问。是故长卿摛藻于《上林》,而聆窃赀之行者汗颊矣;子云苦心于《太玄》,而诵《美新》者靦颜矣;……康乐吐奇于春草,而耳其逆叛之谋者秽谭矣。下逮卢、骆、王、杨,亦皆用以负俗而贾祸,此岂其才之不赡哉?本不立也。本不立者,何也?其器诚狭,其识诚卑也。
器识卑鄙、狭隘或者心思险测,会直接影响到一位杰出文人的创作空间与创作心态,影响到其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当然,严重者也影响到其生存空间。
但是,仅仅有德有器识仍然不够:“譬之麟之仁,凤之德,日为陆离炳焕之文,是为天下瑞。”重视德器并非排斥文才,文才如同麟凤之彩,可使具有仁德的麟凤更加高贵、优雅,因而才被视为国之祥瑞。由此袁宗道得出结论:“信乎器识、文艺,表里相须,而器识儇薄者,即文艺并失之矣。”必器识、文艺兼合,文才始可发挥其最大的创造活力。至于弃其德器炫耀才华者,“何异山鸡而凤毛,犬羊而麟趾”?文才成为其贾衅的祸根,自保尚且不足,“乌睹其文乎”!*袁宗道著,钱伯城标点:《白苏斋类稿》卷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1页。
器识、文艺相合又被称之为“道器相合”。即使从比较凿实的文道论观照,要完成以文载道、明道、贯道的使命,宋儒视文艺为玩物丧志、弃艺能而言道的偏执依然是不可行的。就是说,即使就功利而言功利,也必须实现道、器融合。“道器相合”的“道”接近器识文艺之中的器识,而“道器相合”的“器”则指文艺之术。如章学诚就曾论称:孔子不直接言道,而是将其融入文辞,唯恐世人舍器而求道,其不废文采、反对枯索之意隐乎其中。历代文才的尊尚皆出自文质彬彬的提倡,依循于孔子尚文之意,因而后世文人本不该数典忘祖,对文才抱有偏见。从传道的角度来讲,道必赋形托体而后可以传布,道的言说与普及也不可能离开文艺才技。实际上,孟子也表达过类似思想:“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说明“义理不可空言”,不然难以产生感染力。综合孔孟之论,义理的传播必须要实现其与“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的融合。宋儒所谓工文害道之论,如此而言也便如“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一样滑稽了。*叶瑛:《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39页。
当然,即使主张器识文艺相合,其倡言者也并未降低对文艺功用、品格应有的要求,诸如“不明经则无本,不论史则无用,不能表扬忠孝节义则不足以垂教,不达世故则类迂儒学究而无补于时事,不审进退出处则文与行违”等,清人便视之为“文可不作”的五条律令。*金埴:《不下带编》卷1,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5页。这些律令延续的正是李谔以有用无用论文的理路,意在为“有关系”的创作张目。
四、 器识透视下的文艺之病
“先器识而后文艺”论中器识、文艺相合论在古代文艺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文艺创作从此强化了如下诉求:文学当以有为而作发其端,以雅正与文顾行顾言为境界,以其有本有源有关系为追求,既有益于时,又教化于世。即使遣兴娱情的创作,也要以畅神葆真为本,修辞立诚,为情造文。
对器识、道义、心术、志气、器用的强调,在指明创作之路的同时,又透视出古代文艺创作的弊病,王国维将其概括为“羔雁的文学”与“啜的文学”。
其一,羔雁的文学。“羔雁”本意出自《礼记·曲礼下》:“凡挚,天子鬯,诸侯圭,卿羔,大夫雁。”*朱彬:《礼记训纂》卷9,第75页。二者是古代卿大夫相见时的礼物,引申为人际交游之间以诗文为酬酢,又曰应酬。应酬的创作是日常人生中诸般礼义交往或者风俗仪式等,对文艺创作所产生的需求与推动,如婚丧嫁娶、祝寿贺迁,如文人之间的饯送赠投、雅集文会等等。不必有情兴的鼓动与情感的交流,有需要则濡墨挥毫。此类创作在古代文学中所占分量极大。自唐中叶以后,其风气已难以收拾。明末陈子龙就曾明确批评当时文人以诗为贽:“荐绅比之木瓜,山林托为羔雁。”*陈子龙著,孙启治校点:《李舒章仿佛楼诗稿序》,《安雅堂稿》卷3,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页。清初陆陇其《李先五诗序》云:“阀阅之家,人有应、刘投赠之章,词皆曹、陆。岂当世之才人果若是其盛哉?夫亦征逐以为荣名,抑羔雁以资润泽乎?”*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别集类》第1325册,第144页。也以“羔雁”直陈。
概而言之,羔雁的文学弊病有二:文质难符,为文造情,文不似文。达官贵游彼此投桃报李,贫贱下士以之趋炎附势。李日华论道:“酬以狥俗,有强欢之笑,有不戚之悲。应猝则取办捉刀,填虚则借资祭獭。百丑方丛,一妙何适?此岂复有诗哉?”*李日华著,赵杏根整理:《张振凡河草序》,《恬致堂集》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47页。从“岂复有诗”敷衍,陈子龙道其“无神理”;陆陇其揭其“无心”*陆陇其《李先五诗序》云:“故予谓近人之诗,虽有可观,而求其不没于心如古人者正少也。”;包世臣则斥之为徒具“声色”*包世臣《澹菊轩诗初稿序》云:“至以诗为羔雁,而声色之外,殆于无诗矣。”。
阿谀虚套,假面违心,人不似人。王嗣奭网罗墓志、考满、贺寿、送行等被纳入羔雁之具的冗滥之体逐一批判,首标应人请乞阿谀无行:“必须长篇,必须谀饰,长则捏无实之言,谀则撰违心之语。”文人们出自交接需要或者考虑到切身利害不能不敷衍于诸般礼俗性写作,而虚套、谀饰甚至违心捏造杜撰由此成为常态。无志无节,的确人不似人。
有鉴于此,顾炎武一生杜绝羔雁应酬文字,自道其目的即“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顾炎武:《与人书十八》,《亭林诗文集》文集卷4,《四部丛刊》初编本。。所谓不堕入文人,即不养就文人习气。王国维承前人之论,将以文学为羔雁列入文学衰败的重要原因:
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季、北宋之诗(除一二大家外)无可观者,而词则独为其全盛时代。其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皆诗不如词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除稼轩一人外)。观此足以知文学盛衰之故矣。*王国维:《人间词话未刊稿》,周锡山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69页。
伪饰横出的创作再高产,也无以谈文艺的繁荣!此论洞察到了文艺为功利驰逐的无穷后患。
昔顾恺之夏月登楼,家人罕见其面,风雨晦暝饥寒喜怒皆不操笔。唐有王右丞,杜员外赠歌曰:“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盖前人用此以为销日养神之术,今人反以之为图利劳心之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昔人冠冕正士,宴闲余暇,以此为清幽自适之乐。唐张彦远云:书画之术,非闾阎之子可学也。奈何今之学者往往以画高业,以利为图金,自坠九流之风,不修术士之体,岂不为自轻其术者哉!故不精之由,良以此也。*王伯敏等:《画学集成》(六朝—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619页。
立顾恺之、王维为模范,艺以养心,不可以之图利,人品高则艺品自可绝俗。所谓以创作牟利的现象接近后人所谓的“游”:“或通以款门,或缄以侑椟,则乞糈之惭,歌龟之陋,伟硕者方涕唾之,其为风雅之辱,又曷胜洗也。”*李日华:《张振凡河草序》,《恬致堂集》卷15,第647页。通款曲、投豪门,恬颜向人以求余沥,如此干谒、献纳,可谓斯文扫地。
王夫之一生于此类创作剖击甚多。他认为,前有陶潜“饥来驱我去”,误堕其中,杜甫鼓其余波。随之贫贱文人们一发不可收拾,“啼饥号寒,望门求索”成为诗歌创作的重要动力和内容。所谓诗人由此便“有似乡塾师”、“有似游食客”、有似“衲子”、有似“妇人”。而其识量不出数米量盐、抽丰告贷。
还有一类与此近似的“诗佣”:“诗佣者,衰腐广文,应上官之征索;望门幕客,受主人之雇托也。彼皆不得已而为之。”这类创作当然不会有什么质量,其套路无非是:“移易故实,就其腔壳;千篇一律,代人悲欢;迎头便喝,结煞无余;一起一伏,一虚一实。”在王夫之看来,此类创作皆以糊口为目的,虽其“自诧全体无瑕”,实不知已“透心全死”。*王夫之:《薑斋诗话》卷下,丁福保辑《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第21页。
吾人谓戏曲小说家为专门之诗人,非谓其以文学为职业也。以文学为职业,啜的文学也。职业的文学家,以文学为生活;专门之文学家,为文学而生活。今啜的文学之途,盖已开矣。吾宁闻征夫思妇之声,而不屑使此等文学嚣然污吾耳也。*王国维:《文学小言》,周锡山编:《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29页。
文艺器识既然如此重要,那么器识从何而来呢?核心在于孟子所谓配道与义浩然之气的存养。而存养的真谛又为“功夫在诗外”五字概括无遗。如曾国藩云:“古之善诗古文辞者,其工夫皆在诗古文辞之外。若寻行数墨,求索愈迫,去之愈远。”他以杜甫为例:“杜氏文字之蕴于胸而未发者,殆十倍于世之所传。而器识之深远可敬慕,又十倍于文字也。”将“诗外功夫”与“器识”直接打通。张之洞则将这层意思表达为“须人有余于诗文者始佳,诗文余于人者必不佳”。*王葆心:《古文辞通义》卷16引,王水照辑:《历代文话》,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94 页。人器量识度宏阔,非诗文可以全部鉴照,其创作自然与从诗中学诗、在技巧中寻阶梯者大不相同。不堕文人习气,不沉醉于风花雪月的梦幻,济世热肠与人文情怀所熔铸的才是诗文真正的根基。
[责任编辑罗剑波]
On the Thoughts of Literary “Cai Qi” in Ancient China
ZHAO Shu-gong
(SchoolofLiberalArtsandCommunication,NingboUniversity,Ningbo315211,China)
Abstract:The thought of “Cai qi” was originated in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This topic is inevitably involved in the discussion of virt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talent. The literary thought about “Cai qi” has two dimensions: how to treat or use the talent; and how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reative utility. From the Wei to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his thought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of development: pay the same attention to the literary utility and literary grace; emphasize the utility and restrain the literary grace; ideology and knowledge came before literature. I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this thought, it could be noticed that the two dimensions have been inherited: ideology and knowledge is separated or merged with literature. And for each dimension, personal cultivation and social value were attached with great importance. For the third stage - ideology and knowledge came before literature - a trace of utilitarian bias could be found, but meanwhile it also alerted literati to the literary fantasy or exaggerated literary grace and instead advocated social benefit.
Key words:Cai qi; literary talent; utility; ideology and knowledge; ideology and knowledge come before literature
[作者简介]赵树功,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