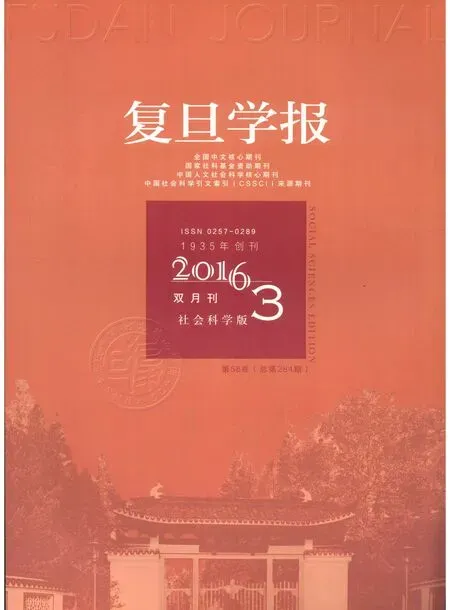游牧、农耕两大生态区整合背景中的清代多民族治理
邹 怡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 200433)
游牧、农耕两大生态区整合背景中的清代多民族治理
邹怡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摘要】清是一个包容众多民族、地跨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的帝国。清代的多民族治理,需要置于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关系演变的大历史背景中加以理解。游牧区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农耕区能提供稳定、丰富的物产。中国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从先秦、秦汉时期的“骚扰式合作”,到东汉末年转向“雇佣互惠合作”。魏晋以降,游牧民族入主农耕区,又开始建立地跨两区的政区,随之发展出实现两大区域在资源和军事上功能互补的二元治理模式,并在两种政治体制的衔接调和中逐步向中央集权制迈进。清自部落发展为帝国,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就经历了漫长游牧—农耕互动史的浓缩版。清政府处理民族事务的对象和技巧,固然与满洲人出身内陆亚洲的地缘关系和政治传统有关,但其多民族治理的目标继承了前代对中央集权国家的追求。新清史研究强调,清帝国成功的多民族治理得益于其统治中枢满洲人所具有的内亚民族特性。国家是民族的工具,民族特质决定国家性格,新清史的这一思路实质上是对西方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经验的一种比拟。而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民族是国家的工具,民族是国家推行管理的一种手段。清政府对满洲认同的强调,是为了维持集权帝国内游牧与农耕民族间的互补关系,而非强调帝国的满洲特质。
【关键词】清朝多民族治理游牧农耕集权制
清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帝制王朝。有清一代,政府进行了广泛的边疆经营。从康熙至乾隆时代,通过与崛起于内陆亚洲的准噶尔帝国的持续作战,清王朝逐步对蒙古草原、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地建立起有效的管理。自雍正朝开始推行的改土归流,令长期处于松散羁縻状态的西南民族地区亦纳入王朝体制的直接管辖。加上广阔的汉族农业区和皇族兴起的东北地区,在清帝国辽阔的疆域内,多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将清王朝放诸世界历史,其所处时代也正是欧洲现代国家取代封建体系、民族主义兴起并向外传播,两者合流,形成民族国家体系,开始用明确疆界划分国家主权的时代。尽管在近代与西方列强的接触中,清朝的领土曾饱受侵扰,但不得不说,正是清王朝在这一世界历史的重大变革之期,维持了对多民族疆土的有效管理,为当代中国广袤版图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近年来,学界对清代多民族治理的关注与“新清史”的兴起密切相关。“新清史”的“新”,乃相对于强调满清汉化的传统清史研究思路而言。后者认为,清政府的统治得以成立,缘于其对汉族中原王朝正统的承袭。*代表性观点可参见Ping-ti H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h’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6.2(Feb., 1967): 189-195. 何炳棣:《捍卫汉化:驳伊芙琳·罗斯基之“再观清代”》(上)(下),张勉励译,《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第3期。而新清史将眼光更多投向清帝国内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尤其是皇族宗室所在的满族,重视满文等民族语文史料的解读,注重从非汉民族视角来解析清的政治格局,由此自然生发出对清代边疆治理、民族政策的热烈讨论。与传统清史的“汉化”观点相对,“新清史”一派认为,清在本质上是内陆亚洲满洲人的帝国,正因为如此,清方能跳出中原王朝华夷之辨的束缚,以开放的心态涵纳多种民族,建立起多民族的帝国。*重要的新清史著作包括:Evelyn Sakakida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hilippe Foret, Mapping Chengde: The Qing Landscape Enterpris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Mark C. Ellio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Ruth W. Dunnell, Mark C. Elliott, Philippe Foret, James A Millward, New Qing Imperial History: The Making of Inner Asian Empire at Qing Chengde (Taylor & Francis, 2004). 较详细的综述,可参见党为:《美国新清史三十年;拒绝汉中心的中国史观的兴起与发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4~200页。换言之,清帝国成功的多民族治理,并不是因为他继承了中原王朝的正统,而是缘于他的内亚特质。若依中原王朝正统的治理理念,清不可能在民族治理上取得这样的成就。
因此,在这一课题上,新、旧清史的观点分歧可大致概括为:“新清史”在意“特性”,而“旧清史”强调“延续”。欲言“特性”抑或“延续”,便不能仅就满清一朝的片段历史而论,故本文拟拉长考察的时段,通过梳理清以前历代王朝的民族治理实践,在史实中观察、判断清代的多民族治理在大历史背景中,究竟是一种“特性”,还是一种“延续”。
一、 游牧、农耕两区关系的演变
清的崛起可上溯至东北的女真部落。与诸多游牧民族的争霸故事类似,努尔哈赤所部建州女真在部落竞争中逐渐强大。对可在较大空间范围内移动的游牧部落而言,强大的标志不是占有广阔的土地,而是获得其他部落的支持,可动用他们的人力及畜力资源。残酷的竞争和松散易变的联盟,令部落在增加友盟、壮大实力时更多基于务实的考虑,而未在意族群的区别。更何况即便同属女真,各部落间也存在着风俗的差异,并因竞争关系而一度成为敌手。*王先谦在《东华录》中回顾努尔哈赤早期创业历史时写道:“时诸国纷乱,满洲国之苏克苏浒河部、浑河部、王甲一作完颜部、董一作栋鄂部、哲陈部,长白山之讷殷部、鸭绿江部,东海之渥一作富集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扈一作呼伦国之乌喇一作拉部、哈达部、叶赫部、辉发部,争为雄长,互相攻战。”(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宣统三年(1911)存古斋排印本,第12页b)董鄂氏、完颜氏,后来均列居满洲核心“八大家”,参见三田村泰助:《明末清初の満洲氏族とその源流》,《東洋史研究》第19卷第2期,1960年。在努尔哈赤成为后金大汗之前,听从其指挥的部落和村庄就已经包括女真、蒙古、朝鲜和汉人。*参见滕绍箴:《满族发展史初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03~225页。努尔哈赤还接受了明廷的封号和明朝辽东将领李成梁的暗中帮助,*《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五,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条:“始命建州夷酋都指挥奴儿哈赤为都督佥事。”(《明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影印本,第11册,第4028页。)李成梁与努尔哈赤的结交,可参见和田正広:《中国官僚制の腐敗構造に関する事例研究:明清交替期の軍閥李成梁をめぐって》,北九州:九州国際大学社会文化研究所,1995年。游牧部落愿为争霸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尔哈赤被推举为后金汗时,创立了超越部落的军民整编组织——八旗,囊括女真、蒙古、朝鲜和汉等民族。*八旗制度创立于努尔哈赤成为后金大汗之前还是之后,学界还有争议,但相差不过一二年,大体而言,八旗制度与努尔哈赤成为大汗基本同步。参见石橋崇雄:《八gūsaと八gūsa色別との成立時期について-清朝八旗制度研究の一環として-》,《中国近代史研究》第3卷,1983年。虽然该组织的整编方式超越了部落,但旗人是旗主的属民,原本旨在超越部落的八旗成为一种新的部落,八旗对努尔哈赤的效忠依然基于一种部落联盟式的关系。*参见周远廉:《后金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论丛》第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4~262页。虽然自努尔哈赤后期至皇太极时期,一直致力提高大汗的权威,但相对康雍乾时期对诸旗贝勒的压制和对皇权的加强,此期的政治结构依然具有极为浓厚的部落联盟制色彩。这类似于公司入股,大汗是老板,加盟部落是股东。老板获得股东的忠诚需仰赖不断的分红,即部落联盟需要持续的经济利益加以维系。部落联盟性质的后金,最初并无占领大片农耕区的战略计划,他将兵锋指向农耕区,是因为联盟扩大,需要获取维持联盟所需的红利。*巴菲尔德著,袁剑译:《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29页。相比游牧区,农耕区能提供更为丰富而又稳定的经济资源。在进军农耕区的过程中,满洲人为免除来自侧翼的威胁,击败漠南蒙古,并与之结成联盟。在占领农耕区后,满洲人很快就遇上了亟待解决的复杂问题:如何在经济、政治等层面协调游牧和农耕两个区域和两种人群间的关系,*后金攻取辽东后,汉人和女真人在经济和生活上的矛盾及努尔哈赤的对策,可参见魏斐德著,陈苏镇、薄小莹等译:《洪业:清朝开国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8~64页。这正是清代多民族治理内在的本质问题。
这一问题由来已久,放长眼光就会发现,游牧和农耕两大区域的历代政权在双方长期的接触中,一直尝试着用各种方法来协调两者关系。
早在两周秦汉时期,农耕政权就与戎、狄和匈奴等游牧民族发生军事冲突。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表明,彼时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文明,业已形成兼杂血缘与地缘的部落联盟游牧集团,*谢剑:《匈奴社会组织的初步研究:氏族、婚姻和家庭的分析》,《民族学论文集》(下),宜兰:佛光人文社会学院,2004年,第858~859页。该文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40本下,1969年,第669~719页。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清人入关前的政权形态。限于游牧区的资源,部落联盟需要以贸易或战争的方式向外获取用于分发成员红利、维持联盟运作的资源。在游牧民族发动一系列骚扰掠夺战之后,农耕民族或以巨大代价远征反击,但更多情况下采用了和亲呈贡这一体面而又相对低成本的方式来应对游牧民族的需索。*狄宇宙著,贺严、高书文译:《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223页。游牧民族的军事力量令农耕民族畏惧,但农耕民族很快觉察到,在满足游牧民族经济要求的同时,可采用雇佣兵的形式,利用其战斗力。汉末魏晋时期汉地割据力量援引游牧骑兵的事例就屡见不鲜。*例如,袁绍对乌丸势力的利用,“会袁绍兼河北,乃抚有三郡乌丸,宠其名王而收其精骑。……袁绍与公孙瓒连战不决,蹋顿遣使诣绍求和亲,助绍击瓒,破之。绍矫制赐蹋顿、(难)峭王、汗鲁王印绶,皆以为单于。”(陈寿:《三国志·魏书》卷30《乌丸鲜卑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831、834页。)更多例证,可参见陈振江:《魏蜀吴三国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发微集》,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47~563页。但农耕区的战乱令游牧民族不便向汉地政权索取稳定的奉馈,进入农牧交错带的游牧民族也受到汉族王朝的压制。*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30、40页。于是,游牧民族尝试进入农耕区自立政权,此即五胡十六国及随后的北朝时期。最初由南匈奴人建立的前赵及其后继后赵,表面上采用了中原王朝的官制,但政权的内在骨架还是以单于与其子弟间血缘纽带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制。最终,皇权在部落诸王的争权中被粉碎。*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2~30、40页。继之而起的鲜卑慕容氏燕政权,大量接纳汉族流民,并根据游牧、农耕的各自所长,摸索出一套州郡、营户二元体制。州郡是中央集权制的典型表现,而控制主力部队的营户制虽然起初有中央直接控制军队的用意,但因为精锐的北族骑兵组织依托于部落制,营户最终为掌握军权的部落贵族分别占有,形成为部落联盟制的形态。*唐长孺:《晋代北境各族“变乱”的性质及五胡政权在中国的统治》,《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外一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8~159页。燕政权最后同样亡于宗室部落的争权。鲜卑拓跋氏的北魏继承了燕的二元制,为加强中央集权,采用“子贵母死”等貌似离奇的方法离散部落联盟。*田余庆:《北魏后宫子贵母死之制的形成和演变》,《拓跋史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59页。同时,因为负责农耕税收的集权制掌握了军队的后勤基础,对部落造成挤压,从而遭到部落贵族的强烈反对,北魏的汉化改革和反复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松岡弘:《北魏漢化政策の一考察—皇太子恂の反乱—》,《駿台史学》第98号,1998年。
隋唐在政治安排上虽然内化了不少北朝二元制积累的政治技巧,但对游牧区的控制基本上恢复到了雇佣兵的模式。突厥、回纥先后成为隋唐皇帝最为倚重的军事力量,他们当然亦据此获得大量作为回报的财富。*林幹:《突厥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4~91页;林幹:《试论回纥史中的若干问题》,《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1919~1981)(下),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605~611页。直至辽人占领幽云十六州,同一政权奄有游牧、农耕两区的情形方才再度出现。辽朝按经济区建立了名之为“南”、“北”枢密院的二元制,但王朝实权掌握在部落联盟制的北院手中,南院基本上只是面向农耕区的税收和民政管理机构。*岛田正郎著,何天明译:《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9~43、150~165、170页;崔瑞德、克劳斯-彼得·蒂兹:《辽》,傅海波、崔瑞德编,史卫民等译:《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6~79页。最终,王朝内部部落贵族的权力争夺、王朝外部其他部落联盟的兴起挑战,内外形成夹击,导致了辽的覆灭。此种灭国方式,在游牧帝国中颇具典型性。继辽而起的金,因横跨游牧、农耕两区而同样采取了分地域二元制。鉴于辽的教训,金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支持弱小部落,抑制强大部落,特别注意防范其他游牧部落联盟的结成。*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33~234页。同时,在军事动员和农耕区管理中,金的政治安排也更多地从部落联盟制转向集权官僚制。*例如,在地方行政区划设置上,金代突破了辽代北枢密院部族系统和南枢密院道路州县两套系统并行的安排,全国统一实行路制,虽然细究起来,游牧区和农耕区的路从发生开始即有本质的区别(详见余蔚:《中国行政区划通史·辽金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97~517页),但区划在形式上的统一体现了金廷对中央集权的追求。另外,金代最富特色的制度猛安谋克制,早期为女真部落兵民组织,随着金政权的强大,金廷对该制度改造的主趋势是排除其中部落贵族的势力,加强中央对猛安谋克的直接控制,即加强中央集权,参见三上次男著,金启孮译:《金代女真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53~256页。但是,在这一步上走得最远的完颜亮,最终被面临失权危险的部落贵族联合杀死。*海陵王完颜亮激进的中央集权制改革,参见陶晋生:《女真史论》,台北:食货出版社,1981年,第44~47页。
金注意防范周边强大部落的成长,但没有压制住成吉思汗的崛起,他没有依靠本部落氏族,也没有通过部落选举获取权力,而是依靠个人追随者和恐怖威权建立了自己的草原帝国。*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237~249页。巴菲尔德认为成吉思汗的这种崛起路径与其他草原政权均不相同。这对元朝的政治体制,尤其是专制集权的强化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在下文还将提及。蒙古人避免直接用集权官僚制冲击部落联盟制,而是刻意提升大汗直属的力量,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作为大汗宿卫军的怯薛。这支军队不同于以往部落联盟合股组建的军队,常设而忠于大汗,从而超越部落制,成为专制集权帝国的军队。*参见姚大力:《论蒙元王朝的皇权》,《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2~166页。成吉思汗崛起时,依赖的主力是追随自己的伴当,在草原征服过程中,其他氏族部落或完整、或零散地被纳入成吉思汗麾下。随着战争的推进,成吉思汗用发端于军事整编的千户百户制对人口进行编组。*成吉思汗的千户百户制,与金的猛安谋克制颇多相似之处,但对于金的制度对蒙古制度的影响,不能作太高的估计,更大程度上是在征战过程中自发形成。参见姚大力:《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第8~10页。虽然黄金家族诸王及驸马,千户百户那颜下还可有私属人口,一部分千户百户的构成还直接依托旧有的氏族部落,但千户百户制度在总体上超越了部落联盟制和封建制,千户百户那颜已非封建领主或参与联盟的部落首领,而是帝国的军事—行政官员。成吉思汗虽然用千户百户制剥夺了旧氏族部落的权力,但出于家产制观念,他将大量土地和人口分给了黄金家族的成员,千户百户那颜也能拥有自己的私属人口。*参见姚大力:《草原蒙古国的千户百户制度》,《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第39~40、56页。并且,这些贵族的后代因名为“大根脚”的门荫关系,能轻易占据高官职务,在官僚制的形式下进行着部落式的权力竞争。*蒙古部落贵族在官僚制外衣下的争权,集中表现在元代异常频繁的皇位更替上,此两者关系的精彩论述,参见萧功秦:《论元代皇位继承问题——对一种旧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蜕变过程的考察》,《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7期,1983年,第22~39页。贵族群体的巨大开销,也被转嫁至其他族群,尤其是农耕区的汉族群体之上。而汉族,尤其是南方汉族,因相对缺乏根脚,并因科举制的萎缩,难以利用官僚制渠道与“部落首领”们相抗衡。*参见姚大力:《元朝科举制度的行废及其社会背景》,《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第219~278页;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8年,第150~154页。元朝在征战中创建的行省制度,盖出于集权指挥的动机,在战事结束后,被沿用为中央管理农耕区的地方行政机构,但因为在官员委任上带有明显的民族差别,行省成为游牧统治集团面向农耕区的财富征集机构。*元代占领南宋旧域后,将行省作为资源征集机构,这突出表现在对分别名为“括勘”和“抄数”的土地和户口调查的重视,参见植松正:《元代江南政治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97年,第68~97页。然而汇集的财富仍未能满足游牧集团豪奢的需索,反倒激起部落贵族间的纷争。所以,在元末南方汉族的义军进攻华北时,元廷自身已因贵族开支巨大而频现财政危机,政权亦因内部争斗而动荡不堪。
植根于农耕区的明朝并无悬念地采用了集权官僚制,行省制度在加以分权改造后被顺利继承,成为实施中央集权的利器,这与行省制度源出军事集权不无关系。但明朝未有兼容并包广大游牧区的计划,维持着与汉朝时近似的游牧—农耕关系,时战时和。*此段历史的梗概,可参见莫里斯·罗萨比:《明朝与亚洲腹地》,崔瑞德、牟复礼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1368~1644年》(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94~215页。在明代保守的边疆政策影响下,嘉峪关成为汉人士大夫心目中华夏与异域分界的象征,参见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36-38.
二、 清代的多民族治理
回溯至此,就自然地衔接起清的崛起。从小微部落到地跨游牧、农耕两大区的大帝国,清的崛起建基于上述游牧区与农耕区之间长久的互动经验之上。游牧生活包含着狩猎技能和机动能力的培养,在生活中伴生出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农耕定居的优势在于资源的集约利用和稳定的产出。前述农耕与游牧两区的关系史貌似纷繁,但从宏观入手,便能梳理出一条较为简明的关系演变脉络。游牧人群劫掠农耕人群,获取资源,可谓“骚扰式合作”。在接触中,农耕人群认识到游牧人群的骚扰目的和军事实力,遂开始了雇佣兵形式的互惠合作。进一步,农耕区政权式微,“骚扰”与“雇佣”两种合作均无力承担时,游牧与农耕两区又尝试合并互补,这一工作在历史上多由军事力量强大的游牧一方完成。但游牧区的部落联盟制和农耕区的集权官僚制难相兼容,成为两区整合中最大的障碍。自魏晋以降,出现不少杂糅的尝试,但均难以长久维持。在实践中,前燕、北魏开创的分领域二元制,被辽、金、元继承后,优化为分区域二元制,被证明是一种相对有效的整合方式。但是,诸朝的实践也展现了二元制中存在的一些内在矛盾:二元制整合的互惠基础是用农耕区的出产换取游牧区的军事保护,若无制衡机制,极易造成需索过度,元朝推行的民族等级政策更是压制了来自农耕区的制衡力量的声音;二元制中的另一个问题是,来源于政治上常占上风的游牧民族本身,横向继承制和部落联盟的权力分享机制,极易引发权力争夺,导致政局动荡。前述采用二元制的王朝无不败亡于上述两个难题的夹击之下。
清从部落至帝国,随着规模的扩大,在因应现实需求的过程中,短时间内经历了浓缩版的游牧—农耕关系演变史。清的多民族治理方式,基于前人丰富的试错教训而创生。在整体上,清选择了经实践证明兼容性最佳的二元制,并吸取前朝教训,尤其针对上文总结的二元制内的两个难题,设计制度,进行破解。本文起首提到的诸多清代民族治理实践,置于该大历史背景中便能很好地加以理解。
清代满洲认同的不断重申和加强,常被作为清王朝谨守内亚王朝内核的证据。但细究这一民族认同主张,可以发现,皇帝反复强调的满洲民族特性,最重要的是骑射尚武传统,这正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进行互惠整合的根本。*皇太极大量任用汉族官员,接纳儒学,但他坚决反对改满洲衣冠为汉人服饰,他作了两个假设,来说明骑射的重要性。“朕试设为比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图鲁劳萨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与尚左手之人何以异耶?朕发此言,实为子孙万世之计也,在朕身岂有变更之理?恐日后子孙忘旧制,废骑射,以效汉俗,故常切此虑耳。”《清实录·太宗文皇帝实录》卷32,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2册,第977页b。皇太极对汉地制度与汉地服饰不同的态度,反映了其满汉互补的政治主张。此外,必须注意的是,雍正、乾隆时期,满洲界定趋严,大量汉军旗人出旗为民,其实有着财政上的背景。王朝承平,八旗人丁滋长,开支随之高企,给清廷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精简旗人有着节省开支的明确目的。*王钟翰明确指出了“国语骑射”政策与八旗财政供养问题之间的关系,参见王钟翰:《国语骑射与满族的发展》,《清史新考》,第64~66页。同参见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 306-313.因此,八旗的重新界定、满洲认同的重申,与其说是强化政权的民族性,不如说是对王朝支柱军事力量的一次精简整编、对游牧—农耕互惠关系的一次协调。被裁撤为民的主体是入关后加入八旗的新汉军,他们并不是八旗中最精锐的核心。事实上,有不少入关前即加入八旗的老汉军和蒙古八旗作为精锐依然留于八旗内。*乾隆在谈到汉军出旗时指出:“朕思汉军,其初本系汉人。有从龙入关者,有定鼎后投诚入旗者,亦有缘罪入旗,与夫三藩户下归入者,内务府王公包衣拨出者,以及召募之炮手,过继之异姓,并随母因亲等类,先后归旗,情节不一。其中惟从龙人员子孙,皆系旧有功勋,历世既久,自无庸另议更张。”(《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卷164,乾隆七年四月上“壬寅”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1册,第10263页a。)经整肃后的满洲认同,“不分满汉,但问旗民”,同时包括这部分汉人和蒙古人。*八旗内汉、蒙族人的满洲认同,均有详细个案支撑。参见细谷良夫:《尚可喜一族的旗籍与婚姻关系》,张永江译;张永江:《升允考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编:《清代满汉关系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91~105、254~265页。精简开支,提升战力,在维持一支有力的王朝军团的前提下,减少对农耕区的索取,防止重蹈元人覆辙,避免激化游牧、农耕两区之间因财富流动而发生的矛盾,这才是清朝中期强化满洲认同的实质。
清王朝吸取其他二元制王朝因过度需索而激化民族矛盾的教训,注重保持各民族固有经济生活的治理思路也表现于处理其他民族问题上。清朝在西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一般认为是中央政府加强对民族地区的控制和开发,这的确是清政府的目的。*参见王钟翰:《雍正西南改土归流始末》,《清史新考》,第178~243页。但还需注意到,与改土归流并行实施的是“封禁”政策。力推改土归流的干将——云贵总督鄂尔泰便禁止茶叶客商进入普洱府的夷民茶山,只允许他们在山外设店交易。*鄂尔泰在《请设普洱镇疏》中提到了有关客商入夷人茶山的规定:“[引者按:思茅六茶山地方],前从贩茶奸商重债剥民、各山垄断,以致夷民情急操戈。查六茶山产茶每年约六七千驼,即于适中之地立总店买卖交易,不许客人上山,永可杜绝衅端。”(黄元直修,刘达式纂:《元江志稿》卷22,艺文志二·文类二,《中国方志丛书》第14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58年影印本,第249页b。)乾隆、嘉庆和道光时期各版本《户部则例》的“番界苗疆禁例”中也禁止客民擅自进入苗地,更不允许客民置办苗人田产。*参见武内房司:《“开发”与“封禁”——道光时期清朝对云贵地区民族政策浅析》,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364~365页。类似的“封禁”政策也能在保护蒙人、满人田土的法规中见到。可见,清政府秉持的理念是,各民族自有其生活环境及经济方式,不应随意改变,尤其禁止对作为生存之本的土地的侵扰。清政府认为,各民族、各经济区之间的交流互惠,可通过行政层面的调拨,如国库税收的征缴和发放、省级财政上的协饷制度而达成。*参见王业键著,高风等译:《清代田赋刍论(1750~19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2~23页。清政府也支持利用商业活动推进各民族间的互惠,*例如,对清代贵州苗族清水江流域的研究表明,清政府在经略苗疆过程中,重视对交通线的控制,改土归流后,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维护一个区域性市场——就清水江而言,为木材市场——的良性运转。参见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47~49、277页。但令清政府始料未及的是,市场经济会给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形态造成深刻冲击,动摇上述清政府所秉持的民族治理理念。于是,不少新的政策围绕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居民利益的保全而追加展开。*民族地区在融入区域市场,对土地、山林等资源进行商业性开发后,引发诸多环境问题。对此,针对性的对策多保留于地方碑刻中,不少环境史研究即围绕碑刻而展开。例如,清水享:《云南南部的生态环境碑刻》,杨伟兵主编:《明清以来云贵高原的环境与社会》,第154~182页。
草原尚武,部落联盟首领由联盟成员推举威武之人担当,联盟成员亦可用脚投票,选择退出联盟,联盟的维持端赖个人魅力,但此种权威在代际传承后,极易发生变动而导致政局动荡。在草原上,联盟重组虽不利于联盟首领维持自己的地位,却有利于各部落通过重新站队,优化自身利益。*Joseph Fletcher, “Turco-Mongolian Monarchic Tradi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 3/4, Part 1. Eucharisterion: Essays presented to Omeljan Pritsak on his Sixtieth Birthday by hi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1979-1980), pp. 238-239.而在农耕区集权体制下,这意味着负责垂直管理和水平协调的行政部门发生痉挛,对政府和民众而言,均非益事。元朝频繁的皇位更替和政策摆荡便与此密切相关。*萧启庆:《元中期政治》,傅海波、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563~566页。因此,通掌游牧和农耕两区的清政府,着意改变游牧民族的权力结构。努尔哈赤创制的八旗制,将同盟部落按军事需求重新编组,对他而言,这无疑是一种集权。但八旗各有兵民,为旗主属民,可与同为旗主的皇帝相抗衡;同时,还有深具部落联盟传统的议政会议制度,令八旗至皇太极时就已成为一种新的部落联盟。*与其他部落联盟首领代际传承时出现的情况类似,皇太极即位后,因无其父努尔哈赤的威望,受到诸旗贝勒的抗衡与牵制。天聪六年(1632)九月,胡贡明在奏言中道:“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引者按:即“正黄旗”]一贝勒也。”(胡贡明:《五进狂瞽奏》,罗振玉编:《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潘喆、孙方明、李鸿彬编:《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标点本,第34页。)针对八旗对皇权的潜在挑战,康熙特意任用各旗旗主不能臣属的亲贵代办各旗旗务,从而架空旗主。*康熙甚至屡次特命皇子代办旗务而不欲假手于本旗王贝勒,参见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93页。雍正的即位,深陷诸旗争权背景,因此,雍正将非皇帝亲为旗主的下五旗行政权,全部收归由皇帝任命的都统。*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第293页。八旗,至此完全成为清帝国的军队,不再具有部落分权的意义,从而大大降低了部落间争权而削弱中央政府权威的可能性。值得对比的是,与清帝国在内陆亚洲草原争霸的准噶尔帝国就一直未能摆脱汗位更替时的部落纷争,清政府的多次远征便利用了准噶尔帝国内各部间的内讧。*宫胁淳子著,晓克译:《最后的游牧帝国——准噶尔部的兴亡》,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7页。
草原部落的自由竞争,还可能令新的威权人物和强势部落脱颖而出,成为潜在的联盟领袖,从而对中央政府造成威胁。清自身的崛起便遵循了这样的路径,辽、金、元的易代也重复着近似的故事。因此,清政府面向蒙古各部,设计了盟旗制度,尽力消弭强势部落的崛起。前文已经提及,游牧民族对土地所有权的观念较为淡薄,部落的强大重在属民的归附和牲畜的增多。盟旗制度反其道行之,针对不同蒙古部落的具体情况,或承认世袭领地,或赏赐指授游牧地,将八旗以外的蒙古各部编为旗,划定领地边界。*一般而言,有世袭领地,且未受外部势力强制迁移的蒙古部落,就地编制成旗;失去领地,前来投奔的,指授游牧地安插。参见岡洋樹:《ハルハ·モンゴルにおける清朝の盟旗制支配の成立遇程-牧地の問題を中心として-》,《史学雑誌》第97卷第2号,1988年;齐光:《アラシャン=ホシュート部の清朝服属と西北情勢》,《満族史研究》第6号,2007年。旗内的行政结构继承了诸部服属前固有的权力组织,但在旗下亦划地而治,并根据人口的增长和移动,析置新的行政辖区。例如,阿拉善和硕特旗下的巴格(扎哈),就由康熙三十六年(1697)初设时的6个,细分为光绪四年(1878)的36个。*齐光:《清朝时期蒙古阿拉善和硕特部的社会行政组织》,《历史地理》第27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2~105页。此种裂土而治的行政建制方式,颇有西汉七国之乱后“众建诸侯而小其力”的意味。恰如部落可用脚投票,选择膺服的联盟领袖,游牧民族个人亦可自由选择愿意归属的部落,这也正是草原势力消长机制的具体运作方式。但是,清代不允许蒙古人随意脱离旧主,投奔新的保护人,将此类行为定性为一种犯罪。*清代在《蒙古律例》基础上编纂,用于处理蒙藏等地事务的《钦定藩部则例》中规定:“内、外扎萨克旗下蒙古及家奴无故逃走,由该管扎萨克立即派员查拿。查拿到案,鞭一百。经他人拿获,由存公项下赏给一牲畜。隐匿者,均罚一九牲畜。”(张荣铮等点校:《钦定藩部则例》卷46,“修改七百二十五”条,光绪三十四年(1908)理藩部排印本,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点校本,第354页。)由此,清政府借鉴农耕定居区的行政经验,依托蒙古诸部旧有的权力结构,划定行政区界线,禁止牧民转换归属,用一种类似“户籍”的做法,增加了游牧区人力和资源流动的粘滞性,从而防止资源在流动中聚合,形成危险的挑战力量。与清朝争霸的准噶尔帝国,虽因部落竞争而多次发生内乱,但在部落力量的流动重组中,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等草原英才亦不断涌现,他们正是中央政府最担心的敌手。虽然清政府对准噶尔帝国的获胜,受益于内乱、疾病等偶然性因素,但新近的一些研究表明,正如忽必烈对海都的获胜,清对准噶尔的胜利亦得益于来自定居农耕区强大的后勤保障。战争期间,屯垦、仓储与商贸的发展,促进了清王朝的国家建设,为前线提供了坚实的后盾。*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58-406.巴菲尔德针对准噶尔帝国的灭亡也评述道,游牧帝国的生存体系已经瓦解,内陆亚洲的竞争将出现在定居力量之间。*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第380页。
清与藏区的接触,很大程度上以蒙古为中介。明万历年间,俺达汗往迎达赖三世锁南嘉措,蒙古开始以格鲁派藏传佛教,即黄教,为统络蒙古各部众的精神纽带。满洲人在与蒙古人结成联盟后,以之为中介,也开始联络西藏政教领袖。*崇德二年(1637),在蒙古人的鼓动下,皇太极首次致信西藏,因未知藏区详情,收信人为吐蕃特汗。西藏地方接信后,达赖、班禅和藏巴汗于崇德五年(1640)遣使盛京,崇德七年(1642)使者抵达。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遣使随西藏使团入藏,同时致信七位呼土克图、藏巴汗和固始汗。其时,固始汗已于崇德七年(1642)春攻杀藏巴汗,其所派使者于崇德八年(1643)九月抵盛京。顺治于元年(1644)正月明确回信固始汗,提及延请上贤,但未指名达赖,直至顺治五年(1648)方指名往迎达赖。顺治三年(1646),固始汗遣使抵北京,庆贺清军入关。在此过程中,蒙古人欲密切与达赖的关系,满洲人欲借助藏传佛教力量稳定蒙古诸部,西藏政教领袖则根据周边势力的消长,欲寻求强大的保护者和供养人,三方各有所需。初时,满洲人以西藏情势未定,谨慎地广泛结交西藏政教各派,待固始汗政权稳定后,方确定结交固始汗、往迎达赖的方针。参见李保文:《关于满藏最早建立互使关系问题》,《西藏研究》2003年第2期。西藏社会的整合中,宗教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历史上,各教派为在竞争中获胜,有向外界寻求世俗力量支持的传统,所以,在黄教相对其他教派取得压倒性优势的表面之下,潜藏着各方外部力量的角力。在“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方针的指引下,清逐步排除了和硕特蒙古、准噶尔蒙古和西藏地方贵族的势力,令清廷成为黄教最重要的直接供养人和保护者。由于清是透过蒙古进入西藏事务,故清对西藏的治理最初试图移植蒙古地区依赖当地王公的札萨克模式。但清廷先后采用的分权式噶伦合议分辖制度和政教分离的藏王—噶厦体制,反倒令西藏内部潜藏的教派纷争和地方豪势力量显在化。为克服以上动乱势力的抬头,加之两次藏廓战争令清廷意识到,“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之外,西藏具有重要的国防战略地位,经过调整,清廷最终采用了政教合一、达赖与驻藏大臣分理僧俗两务的双头政治体制,*有关清代西藏行政制度演变的精彩缕析,可参见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92~227页。达赖喇嘛的实际地位和作用还略高于驻藏大臣,参见同书,第219页。充分利用了长久整合西藏各部的宗教力量,并用以驻藏大臣、驻藏军队为代表的中央集权行政与军事力量加固了这一整合。中央集权力量成为最重要的宗教供养者和保护人,从而达成了西藏的稳定。
乾隆和咸同年间的多次回民事变,也令回民问题成为清代民族治理中重要的一环。清廷最初并未将回民问题作为独立的民族事务来看待,回民与汉民一起被纳入编户齐民系统,并无区别。这一方面与回民散处汉地“大杂居”的分布特点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回民成员来源多样,至晚明以降方以伊斯兰教信仰为认同基点形成族群共同体,然成员关系依然松散、简单有关。*参见姚大力:《“回回祖国”与回族认同的历史变迁》,《北方民族十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2~79页;钟焓:《民族史研究中的“他者”视角——跨语际交流、历史记忆与华夷秩序语境下的回回形象》,《历史研究》2008年第1期。但明末清初以苏菲派为代表的新教的传入推动了门宦制度的发展,原本独立松散的教坊,成为各级教掌统辖教众、等级严密的基层社会组织。伊斯兰教内部新、老两派为争夺教民而发生教争,清廷为平靖地方和打击新兴基层组织力量而介入回民问题。在编户框架内,清廷先后推行了由政府指定教掌,用乡约取代教掌,认可由教掌担任乡约、在教坊下设立保甲等措施,至乾隆末年,最终以承认并依赖回民基层门宦组织为代价,方才将对回民的管理维持于保甲框架之内。在此框架中,清廷禁止回民在教坊间自由流动,以阻止强大集团力量的诞生。*参见路伟东:《清代陕甘人口专题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19~66页。故乾隆以后,咸同间发生的西北、云南回民事变,几与回汉信仰差异无关,*回民事变过程中,能看到双方成员均同时包括回汉两族:弹压官军中不乏回民,大理杜文秀政权中大量擢用汉人,云南回民领袖马德新素有调和儒回两教的志向,西宁地区的回民起义领袖马桂源还出资修缮孔庙。参见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南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0年10月再版,第112~113、175~176、347页;王文定:《同治年间甘肃汉回人民联合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回族史组编:《回族史论集(1949~1979年)》,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58~459页。实为市场竞争和地方产业转型引发的劳动力生计恐慌*参见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32、59~69、75页;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序言——兼论陕西回民运动的性质》,《回族史论集(1949~1979年)》,第444~447页。与政府严防回民抗争的既定方针*穆斯林教争引发的地方动乱,令政府、尤其是汉族官员将回民视为桀骜顽梗之人,故虽然中央主张汉回一视同仁,然法律表达和地方实践却倾向于对回民加重惩罚,从而导致了回民对官府和汉人的抵触。参见王树槐:《咸同云南回民事变》,第47~51页;Jonathan N. Lipman, “‘A Fierce and Brutal People’: On Islam and Muslims in Qing Law,” Pamela Kyle Crossley, Helen Siu, and Donald Sutton ed.,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83-110.交相作用的结果。至于对新疆回部的治理,是清对准噶尔战争胜利的产物,与对内地回民的政策并无实质关联。清以驻扎大臣为中央派出代表,当地贵族担任的伯克实为驻扎大臣任命的地方民政官员,而非部落首领。在诸藩部中,清对回疆实行的是一种与中央集权制最为接近、保留地方自治权最少的行政体制,因此,新疆也成为最早顺利转为行省的藩部。*参见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第228~259页。并且,值得注意的是,新近的研究表明,与此并行,在文化和社会领域,清廷却并未刻意在新疆推行汉化政策。*参见James A. Millward and Laura J. Newby, “The Qing and Islam on the Western Frontier,”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pp. 113-134.
三、 结语
清是一个地跨游牧和农耕两区域的大帝国,本文通过回顾中国历史上游牧和农耕两区关系的演变,将清代的多民族治理置于一个农耕—游牧互动的长时段背景中加以理解。
游牧社会,寓兵事于生活,故发展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因活动空间广阔,便于退避,盛行松散的部落联盟制。与之对应,农耕社会物产丰富,早在战国晚期,便已在封建争霸的战争动员中发展出中央集权。游牧社会凭藉武力,能从农耕社会获取资源补充,农耕社会则利用资源换取游牧社会的军事襄助。早期的“骚扰式合作”,至东汉末年开始转向“雇佣互惠合作”。随后,魏晋时期农耕政权的孱弱又激发游牧民族入主农耕区,建立地跨两区的政权,两种经济模式及相应的政治制度由此面临抉择。在实践中,军事与资源功能互补的二元治理模式脱颖而出。前燕、北魏、辽、金、元一线的二元治理王朝为清帝国的治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清的多民族治理理念系针对前人的得失而设计。
清自部落发展为帝国,随着规模的扩大,短短几十年时间,就经历了漫长游牧—农耕互动史的浓缩版。清承续历史,将两大区域的整合建立于不侵扰各自生活、功能互补的基础之上。因此,清代“但问旗民”的满洲认同的确认,实质上是对帝国军事精锐的一次精简,以达成在对农耕区适度索取的基础上维持一支足够强大游牧军队的目标。清在西南开发中,改土归流与封禁两种政策并举的事实,也反映了清政府在不侵扰民族生活的前提下实现资源互补的治理理念。
部落联盟制下的权力斗争是造成清以前二元制政权内政混乱的主要原因。因此,清对游牧民族部分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改革。满洲八旗的权力收归皇帝任命的官僚,消除了部落争权的物质基础。对八旗以外蒙古诸部的治理,尊重其传统的权力结构,但通过划定各旗界线,实施逃人法,用制度阻滞土地和人口资源在各部间的流动重组,从而维持一种静态的势力平衡,防止新的游牧联盟力量的崛起。
藏区的地方力量,早有由宗教加以整合的传统。清初在“兴黄教以安众蒙古”方针的指引下,以蒙古为中介,作为宗教供养人,进入西藏治理。最初曾试图模仿蒙地札萨克制,扶植地方王公力量来管理当地,结果反而导致曾被宗教弥封的地方纷争显在化,最终清还是依赖宗教,辅以中央派出力量,抑制地方各部力量在竞争中崛起。对回民的治理思路与之相似,以确保地方治安为目标,以认可宗教组织为代价,维持了对回民在保甲框架内的管理,并通过禁止回民在教坊间流动来阻止集团力量的兴起。
在长时段的考察中,可看到两条脉络。一条是不同生态区之间互补方式的调整与磨合。在此意义上,汉以外其他民族并未完全汉化,立足于本民族生活地区生态环境的民族特质,正是各民族和合共美的基础。另一条脉络是不同民族间政治体制的衔接与调和。在此意义上,似乎能看到鲜明的“汉化”足迹。从本文的史实分析可知,此种“汉化”,本质上是对中央集权国家制度——一种比部落制、封建制更有效率的人力动员组织方式——的接纳。由于中原汉人在战国晚期群雄争霸的战争动员中便已发展出中央集权国家制度,加之周边人群在迈向中央集权的道路上总与和汉人的接触——尤其是战争——相关联,所以,政治体制向中央集权迈进,常被视为“汉化”。但笔者认为,这与其理解为“汉化”,不如理解为对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接纳和继承。
“新清史”研究强调清的国家体制为满洲人所建,该思路有着深刻的西方经验背景。近代西方主权国家的兴起,是一个由民族赋权的过程。尤其是自下而上推进建国进程的民族国家先行者——英国和法国,为对抗封建贵族的统治,形成全民性的民族共同体,并以民主方式赋权政府机器,建立民族国家。*参见里亚·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224页。简言之,国家是民族的工具,民族的特质决定了国家的性格。“新清史”强调建国中满洲人的民族特质,显然出于一种发端于西方经验的比拟思路。
而中国历史中,国家与民族的关系有所不同。中央集权国家早在战国末期群雄竞逐的战争中形成,国家机器的合法性并非来自民族共同体的赋权,而是来自天命。大德可为天子,自然、万民合理、合礼地正常运转,被视为皇帝及其官僚集团获得天命正统的标志。*参见池田知久:《中国古代的天人相关论——董仲舒的情况》,沟口雄三、小岛毅编,孙歌等译:《中国的思维世界》,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6~97页。华夷之辨,表面带有民族之分,内里关注的却是政治文化之分,“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愿意接受中央集权国家的政治理念,在施政中达到自然和万民的和谐运动,便是对正统天命的继承。对中央集权国家的诉求,超越了民族的区隔。因此,清朝皇帝愿意遵从不同民族的传统,表达其对天命的继承。*面对满、汉、蒙、藏不同民族,为树立符合不同民族传统的合法性,清朝皇帝担当着可汗、皇帝、转轮圣王和文殊菩萨等角色。参见何伟亚著,邓常春译:《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2~33页;王俊中:《“满洲”与“文殊”的渊源及西藏政教思想中的领袖与佛菩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8期,1997年。与西方经验中国家是民族的工具相对应,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民族是国家的工具。民族认同,成为国家推行管理的一种手段。例如,清政府对满洲认同的强调,就是为了维持集权国家的精锐武装。清末以降,从反满主张到中华民族等概念的兴起,也顺应了不同情境下国家政权建设的需求。*参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创刊号,2002年。而民众将民族认同视为一种从政府谋取利益的“制度套利”工具,根据不同情境,使自己汉化或非汉化,借助政府力量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获取实利。*汉化的情形颇多。例如,元明以来不少西南土著族群,将自己的祖先塑造为源出中原、因从军征伐而来到西南的汉人,他们在生活中也多开始践行汉人的礼仪习俗,或自称汉人。因为攀附汉人认同,融入中原王朝体系,可令他们获得更好、更安全的社会身份。参见谭其骧:《〈播州杨保考〉后记》,《长水集(第二版)》(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0页;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5页。除西南外,王明珂该书还展示了更多中国历史上空间性和社会性华夏边缘人群的此类行为。非汉化的情形亦有。前文提及的八旗内汉、蒙族人的满洲认同即为例证。此外,胡化风气浓厚的北齐,高德政、高隆之等汉人家族追随王室而自认为鲜卑人,亦可为一例。参见陈寅恪:《北齐的鲜卑化及西胡化》,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294~295页。
最后,再回到本文起首提出的问题:清代达成的多民族治理,相对前代,究竟是一种“特性”,还是一种“延续”?笔者认为,清政府处理民族事务的对象和技巧,固然与满洲人出身内陆亚洲的地缘关系和政治传统有关,但其民族治理的目标乃建基于对中央集权国家的追求。若清无意继承中央集权国家体制,那么,民族问题的处理结果很有可能是封建邦国,或是部落联盟。如果说,对中央集权国家体制的追求,体现了清对正统中原王朝的继承,那么,我认为清代达成的多民族治理成就更大程度上缘于对前代历史的“延续”。
[责任编辑陈文彬]
A Review on the Multi-ethnic Governance of the Qing Dynast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Farming and Nomadic Regions
ZOU Yi
(CenterforHistoricalGeographicalStudies,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The Qing Dynasty was an empire including dozens of ethnicities and extending across farming and nomadic regions. The multi-ethnic governance of the Qing Dynasty should be understoo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farming and nomadic regions. Nomadic region has strong military power, while farming region can provide stable and rich resources. Therefore, China has explored and developed a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mode in history, and gradually went toward unitary state by coordinating and integrating the political systems respectively deriving from farming and nomadic regions. From tribe to empire, in dozens of years, Manchurians experienced a condensed version of the integration history of farming and nomadic regions. The objects and skills in ethnic affairs of Qing government deservedly had a relation with the geopolitical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traditions of Manchurians from inner Asia, while his aim of multi-ethnic governance inherited previous dynasties’ pursuit of unitary state. New Qing History emphasizes Qing’s successful multi-ethnic governance benefitted from Manchurians’ inner Asian ethnic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ideal is essentially analogized from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nation states in modern west. In that history, state was a tool of nation and state character was determined by ethnic characteristics. While in Chinese history, nation is a tool of state; in other words, nation is a kind of administrative mean adopted by state. Therefore, the Manchuria identity emphasized by the Qing government is to maintain the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mode between farming and nomadic regions in one empire, but not to emphasize the Manchuria characteristics of empire.
Keywords:Qing Dynasty; multi-ethnic governance; nomad; farming; unitary system
[作者简介]邹怡,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史与人文遗产研究创新团队”研究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14YJC770050)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