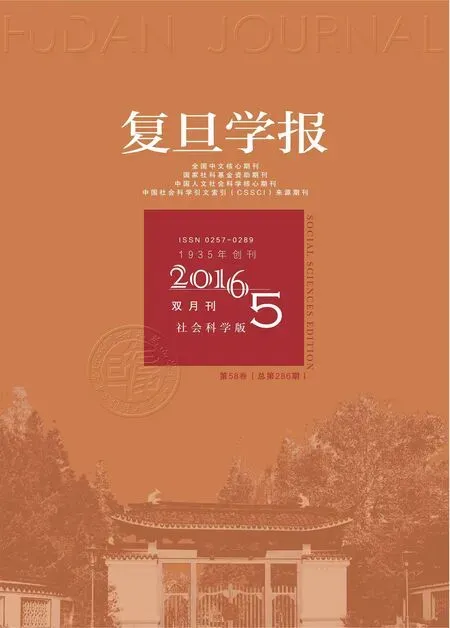公众监督与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立法建制
侯 健
(复旦大学 法学院,上海 200438)
法学研究
公众监督与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立法建制
侯健
(复旦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38)
公众监督引发公民批评权与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冲突。既要保护公民批评权,也要保护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这一冲突可以通过界定隐私权的法律边界来解决。流行的观点建议在立法中引入“公众人物”概念,制定不同的规范,规定他们的隐私权受到更多的限制。这种因人设制的思路违反了权利平等和法律一般性的原则。在立法建制方面,应当确立统一的隐私权规范,这一规范平等地保护和限制所有人的隐私权,它包含界定隐私权边界的三个准则:公共领域、公共利益、自愿公开,其内容是“自然人享有隐私权,未经本人的同意不得公开其隐私或侵入其私人生活。在公共领域或涉及公共利益的活动中,隐私权的行使受到限制”。这一规范表明,任何人的活动如果发生在公共领域中,或者涉及公共利益,其隐私权都可能受到限制,不独国家工作人员如此。这一规范在适用过程中同样可以有效地解决公民批评所引起的隐私权纠纷、合理地界定公民批评权与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边界。实际上“公众人物”是一个司法概念而非立法概念,是统一的立法规范在特定类型的案件中的适用结果。
公众监督批评权隐私权权利平等法律的一般性
一、问 题
在当代中国,公众监督是重要的反腐方式,这种方式是公众通过在媒体和互联网上曝光国家工作人员的某些信息,以形成舆论压力,引起负有监督之责的公权力部门启动监督程序。这种方式是有法律依据的,那就是宪法第41条规定的批评权:“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但是隐私权也是法律所保障的权利,国家工作人员也享有隐私权。这就引发了两种权利的冲突。批评者可能因为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而面临民事诉讼、行政甚至刑事处罚。法学界在隐私权边界问题上有广泛的共识,即改变我国法律没有区分“公众人物”(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在其中)与普通公民、在司法实践中给予他们的隐私权以同等保护的现状,把“公众人物”隐私权与普通公民隐私权区别开来,对前者予以特别规范,相比后者受到更大的限制。很多研究者还建议了制度改进方案。这种方案一般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公众人物”的界定标准;另一部分是有关“公众人物”隐私权的特别限制的规范。*例如以下论述:“自隐私权概念产生时起,人们就已经开始在把握隐私权设立目的的墓础上区分不同主体所享有的隐私权”,参见李新天、郑鸣:《论中国公众人物隐私权的构建》,《中国法学》2005年第5期; “公民在其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的身份,从社会学的角度,根据其受关注程度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普通公民、政府官员和公众人物,参照此划分标准,不同类型的群体,因其受社会关注度的不同,其享有的隐私及隐私权亦有不同”,参见喻军:《论政府官员隐私权及其规制——以绝对隐私、相对隐私为切入点》,《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5期;“在我国的《侵权责任法》中对于官员的隐私权作出统一的界定并提出官员隐私权被侵害的救济手段”,参见沈菡惜、徐荣:《网络反腐中官员隐私权的范围及保护》,《法制与社会》2015年第6(上)期。王利明认为,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人,分为政治公众人物和社会公众人物;公众人物在人格权的保护上有自身的特点,适用不同的规则。参见王利明著:《人格权法研究》(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59页以次。
这是一种因人设制的思路。不同的人享有不同限度的隐私权,适用不同的规范。这种思路运用到立法中,就要求在立法中引入“公众人物”或“公共官员”的概念,以一些事由特别限制公众人物的隐私权。这种思路运用在司法实践中,就导向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在面对隐私权纠纷时,首先判断权利主体的身份是普通公民还是“公众人物”,然后再决定给予同等保护或差别保护。这种思路旨在达到这样一种效果,即让国家工作人员或“公众人物”更多地为公众所了解,满足公众知情的需要,有利于公民批评或公众监督。
这种思路的现实关怀是可赞赏的,但是笔者感觉到其根本的问题在于,它至少在表面上抵触关于权利平等的信念。《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它将权利与身份连接在一起,根据人们的身份来赋予权利。如果说在古代贵族制社会某人因为身份而享有特权是不合理的,那么根据这种思路某人因为身份而丧失权利也不能算是合理的。这种思路还可能会加强国家工作人员对于权利不平等的担心和对于新制度的抵触。这是一个需要回答、实际上却没有得到很好回答的问题:为什么国家工作人员和普通公民不能平等地享有隐私权?为什么批评者曝光普通公民的私密信息可能构成侵权,而曝光国家工作人员的同样信息却不构成侵权呢?
笔者认为,在立法建制方面,应当确立统一的隐私权规范,这一规范以同样的准则平等地保护和限制所有人的隐私权,没有必要引进“公众人物”概念;只要确立的规范合理可行,在制度适用方面同样可以有效地解决公民批评所引起的隐私权纠纷、合理地界定公民批评权与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边界。我们首先论述统一的规范。
二、统一的规范
一个理性的人既不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封闭起来,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一切都曝光于天下。如果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敞开自己,让自己的一些信息进入社会的信息流,人们就可以更多地了解周围的世界,更好地形成对世界的判断,更恰当地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对个人、对社会来说都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一定程度”到底是多大程度呢?这个界限在哪里呢?刑法规定,侵入他人住宅是犯罪行为,这样住宅就是一个界限;还规定通信自由是不可侵犯的,这样私人信件就是一个界限。但是总的说来,我国法律特别是民事法律对于隐私权界限的规定并不清晰。判断隐私权的界限,既需要考虑隐私权的价值,也需要考虑批评权利、公众监督等价值。“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尹文子》。这里尝试提出确定隐私权界限的统一规范。
(一) 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因为哈贝马斯的研究而广有影响。在这里,这个概念的内涵要比哈贝马斯的界定更为宽泛,*按照哈贝马斯的界定,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是指十七至十九世纪在欧洲主要国家形成、存在并发挥某种功能的特定社会结构。在国家与社会逐步分离的背景下,国家是公共权力存在、运作的政治领域。在社会方面,可以区分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指狭义上的市民社会,包括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家庭及其私生活领域。所谓公共领域,就是在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形成的一个公共的领域。这一领域是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公共领域的主体是公众,其形式就是由咖啡馆、沙龙、宴会、报纸、刊物、书籍等机制所构成的公众交往网络,其力量就在于形成公众舆论。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32~60、82~83页。不仅包括社会公共领域,而且包括公共权力领域;不仅包括有形的公共空间或公共场所,也包括无形的公共关系领域。一个人置身于公共领域,他的言行自然置于不特定多数人的关注之下,也就无所“隐私”。在公共领域内,人们的隐私权是受到限制的;一般情况下,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行没有隐私权附于其上。
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拥挤的地球上。人们在公共空间中的活动可能会受到其他人的干扰。在大街上,他人对我们的注视可能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和警惕。但是通常的注视并没有侵犯我们的作为隐私权组成部分的安宁权。正如普罗塞尔所言:“在公共街道或者其他公共场所,原告没有安宁权,别人仅仅只是跟随他,不构成对其隐私的侵入。在这样的场所对其进行拍照也不构成对其隐私的侵害,因为拍照不过是进行了一场记录,这种记录与对某人可能被他人自由地见到的在公共场所的形象没有本质区别。”*William Prosser,Privacy,48 California Law Review 383 (1960).不过对普罗塞尔的话不能作绝对理解。因为在公共空间,如果他人的行为引起我们很大的不安、烦恼或恐惧,足以破坏我们内心的安宁,就有可能侵犯隐私权。比如,如果某人在拍摄街景时摄录了作为街景一部分的我们的形象,他的摄录行为没有侵犯我们的隐私权(但可能侵犯肖像权),但是如果每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都会发现有一台摄像机莫名其妙地跟踪拍摄我们的形象,就会感到不安、疑虑重重,并可能失去内心的安宁。内心的安宁并非是如闲居在私人空间里静如止水的那种状态,而是一种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情的专注状态。当这种专注状态受到根本破坏时,就有可能侵犯隐私权。
那么,什么是公共空间呢?首先,公共空间未必是公有空间,公共空间不是以它的所有权的性质来界定的。因为有些非公有的空间也可以用于公众活动。有一种定义将公共空间界定为根据所有者(或占有者)的意志,用于公众活动的空间。*张新宝著:《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年,第196页。这种界定是从用途的角度着眼的。这是一种较为可取的界定,但是需要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多少人以及人们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可以看作是“公众”?可以认为,作为公众的人数是不特定的,或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特定的。公共空间可以分为几种情况:一种是不特定的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空间(例如露天广场);另一种是不特定的人们都可以在符合一定条件下自由出入的空间(例如影剧院);再一种是虽然进入空间的人是特定的,但是人们之间并没有特定的私密关系(例如会场)。
公共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公共空间。它未必是一个物理空间,比如一块场地、一个会议厅。它还可以指按其性质来说注定会受到公众关注的某种公共关系领域,例如某种职业或社会角色。这些职业或社会角色的本质就是要通过吸引公众注意而获得一定的利益或体现一定的价值,比如演员、运动员和政治活动家。一个演员可能从未在大庭广众中活动,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的职业活动处在公共领域中。
(二) 公共利益
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限制隐私权的范围,甚至排除隐私权的存在。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公共利益准则不同于公共领域准则。私人空间内的行为如果侵犯了公共利益,也是没有隐私权的。比如某人在住宅内从事犯罪活动,这种活动并不因为发生在私人空间里就享有隐私权。有关国家机关可以在法定条件下进行搜查和检查。再如,某人以邮寄的方式从事违法活动,也不能基于隐私权请求法律保护。有关机关可以在法定条件下开拆邮件进行检查。
公共利益的标准是很难把握的。从主体角度看,公共利益是有利于每一个人的利益,与私人利益或特殊利益相对而言。它不是某些个人、集团或阶层的特殊利益,而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的、普遍性的利益。从内容角度看,公共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它不仅是目前的利益,也包括长远的利益;它不限于物质财富,还包括精神财富。
从主体和内容的角度界定公共利益也是目前法学界的通常方式。这样的界定仍然是很含混的。笔者以为,借助经济学里的“公共物品”概念可以使公共利益的内涵变得清晰一些。萨缪尔森等人通过与私有物品相比较来说明公共物品的性质:“与来自纯粹的私有物品的效益不同,来自公共物品的效益牵涉到对一个人以上的不可分割的外部消费效果。相比之下,如果一种物品能够加以分割因而每一部分能够分别按竞争价格卖给不同的个人,而且对其他人没有产生外部效果的话,那么这种物品就是私有物品。公共物品常常要求集体行动,而私有物品则可以通过市场被有效率地提供出来。”*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高鸿业等译:《经济学》(第12版),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第1194页。也就是说,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公共利益实际上就是公共物品,或者是公共物品所包含的利益。它具有非排他性(或开放性)。公共利益不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一些人享用某项公共利益不排除其他人对该项利益的享用。公共利益是开放的、全社会共享的利益。例如,消除空气中的污染是一项能为人们带来好处的服务,它使所有人能够生活在清洁的空气中,要让某些人不能享受到清洁空气的好处是不可能的。它还具有非竞争性。一部分人对某项公共利益的享用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该项利益的享用,一些人从这项利益中受益不会影响其他人从这项利益中受益,受益对象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例如国防保护了所有公民,其费用以及每一公民从中获得的好处不会因为一个人出生或另一个人死亡而发生变化。
(三) 自愿公开
如果隐私权也包括公开隐私的权利,即公开自己的私密信息和私人生活的权利,那么自愿公开就是一个多余的原则。如果隐私权只是隐私的权利,而不包括公开的权利,那么自愿公开就是一个有意义的准则。
一个人出于某种动机自愿公开自己的私密信息,他认为公开隐私要比保守隐私更为有利。一个人同意他人公开自己的私密信息,或者同意他人进入自己的私人生活而不视为干扰,而且也知道他人将会把这些私密信息传播给不特定的第三方。这都是自由的个人决定。在这些情况下,当事人不能主张侵害赔偿。
在现代社会中,有些职业注定要比其他职业更依赖大众传媒或更依赖于众人的关注。没有众人的关注,这些职业就无法成功。众人的关注是一把双刃剑,可能带来荣耀,也可能带来烦恼。这意味着,选择这些职业,就意味着自愿放弃某些个人信息的私密性质。相反,有些人是被动地、不自愿地卷入到公共事件之中。这一事件使他置身于公共领域之中,但是对于他的那些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信息,其他人未经同意,不能加以传播。比如对于发生在公众场所的猥亵事件,公众可以自由地传播猥亵者的信息而不能提到有关被猥亵者的信息,如果提到被猥亵者的信息,就侵犯了其私密权。
公共领域、公共利益和自愿公开这三个准则表明隐私权的界限,也是判断侵犯隐私权行为是否成立的标准。权利人就发生在私人领域内、不关涉公共利益的个人言行和信息享有隐私权;其他人没有经过本人的同意,不可知悉这些私密信息和侵扰其生活安宁。判断隐私权的界限,或者判断隐私权是否受到侵犯,需要综合考虑个人言行是否发生在公共领域、是否关涉公共利益、当事人是否同意公开等因素。
许多研究者认为,“新闻价值”、“合理的公众兴趣”或“公众的知情权”也是判断准则。笔者认为,“新闻价值”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准则。它是一个失衡的准则;它意味着,当事人是否有隐私权取决于对另一方是否有价值;当一个人的私密信息对另一方有新闻价值时,他就不能对这些私密信息主张权利。在个人的隐私权与大众传媒的新闻自由权冲突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经过大众传媒报道的个人信息都具有新闻价值。一个信息是否有新闻价值,是从新闻从业者的角度来定义的。“合理的公众兴趣”或者“公众的知情权”也不是一个适当的准则。如果只要是公众感兴趣的,一个人就不能保有隐私,那么隐私权就失去大半的意义。公众兴趣未必是健康的、合理的。如果要在公众兴趣中区分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两部分,还需要运用其他的准则,例如以公共领域、公共利益来判断。“公众的知情权”很难说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权利,它的主体是谁?如果是不特定人数的公众,那么谁可以代表这个不特定人数的人群主张、行使权利?这个概念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公众的知情权不同于公民的知情权。公民的知情权是公民个人了解政府的某些行动或政府所掌控下的某些信息的权利。当公民行使这项权利时,政府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例如开放它所掌握的某些资料。而且判断“公众知情权”与个人隐私权之间的界限也是需要依据“公共领域、公共利益”等准则来厘定。
三、规范的适用
上述有关隐私权内涵和界限的准则和标准普遍、平等地适用于包括国家工作人员在内的一切自然人。我们可以把它们结合起来,作一个集中的表述:“自然人享有隐私权,未经本人的同意不得公开其隐私或侵入其私人生活。在公共领域或涉及公共利益的活动中,隐私权的行使受到限制。”这一规范表明,任何人的行为如果发生在公共领域中,或者涉及公共利益,其隐私权都可能受到限制,不独国家工作人员如此。我们可以适用这一规范来处理公民批评权与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之间的冲突。
第一,公共权力的运作是一个公共领域。公务行为发生于公共领域,没有隐私权附于其上。如果公务行为可以暂时不公开,也并非基于保护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需要,而是基于保护国家秘密的需要。没有永远不可以公开的公务行为和国家秘密。在公共领域中,国家工作人员不是一个私人,而是一个“公仆”,国家工作人员是为了制定、执行和适用法律而存在的,而现代社会中的法律是民主的和公开的,原则上国家工作人员的制定、执行和适用法律的行为也应当是公开的,为公民所知情。
这里,笔者想到韦伯关于现代政治特征的描述。韦伯认为,现代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理性化的官僚体制。理性化要求清除政治领域中一切私人性的、情感性的、容易造成不稳定预期的因素,要求一切公务行为以公开的、可预知其后果的方式进行。因此,理性化的官僚体制把官员的生活彻底地分成公私两个领域:“现代的机关组织原则上把办公室与私人住所分开。因为,它从根本上把职务工作作为一个分离出来的领域同个人的生活范围分开,把职务上的财物同官员的私人财产分开。”*马克斯·韦伯著,林荣远译:《经济与社会》(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80页。这种分离是一个关键特征;没有这一特征,现代民主政治就不可能产生。
如果批评者传播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开场合的言行,不能被认为是侵犯了隐私权,因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在公开场合的言行(特别是自愿的言行)并没有隐私权。如果批评者曝光了国家工作人员有关职务行为的信息,也不能被认为侵犯隐私权,因为这些行为不等于私人行为,不包含私人利益和隐私权。
第二,在现代民主社会,公共权力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设立的,也是为了公共利益而运作的。但是公共权力要由具体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行使。国家工作人员既可能以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式行使权力,也可能以违背公共利益的方式行使权力。普通公民作为公共权力的委托者,需要了解一些信息,用以判断哪些人来行使公共权力有助于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受委托的人是否以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式来行使权力。一个人的品行直接关系到他能否负责地行使公共权力,关系到公共利益能否得到维护。这样,公民就有必要了解受委托人的品行以判断他们是否适合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只有这样,公民才可能选出履历清白、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把公共权力委托给他;也只有这样,公民才能使受委托的人谨慎行使公共权力、不至于受到不良诱惑和腐蚀。权力本身是一种巨大的腐蚀力量。没有细致的检察,没有防微杜渐的措施,没有强有力的制约,一个优秀的人在掌握权力之后也可能会受到腐蚀而堕落。因此,个人隐私一般应受到保护,但是那些行使公共权力的人的与职务适任性有关的个人信息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个人私事,已经影响到了公共利益,应当受到民主的审查。
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信息是否关涉到公共利益呢?仅就私人财产本身而言,无关乎公共利益。但是财产状况能够透露出占有者的许多信息。在现实社会中,一个人奋斗的结果主要是作为财产体现的,其人生成就也累积成财产数量。如果一个公职候选人的财产数量明显超出正常的水平,而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选民自然有理由怀疑候选人获得财产的手段或方式是否正当合法。财产状况就成为选民了解候选人品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于在任的国家工作人员来说,更是如此。贪污、受贿的直接结果就是非法地增加个人财产,违法行使公共权力往往是为了敛财。财产数量的非正常增长就是这些违法行为的迹象。在我国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本身就构成犯罪。违法行使公共权力,以权谋私,无疑是损害公共利益的。批评者曝光国家工作人员的真实财产信息,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都是有利于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的,也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
第三,如果公权领域可以看作公共领域,那么进入这一领域一般可以看作是自愿的行为。担任公职并不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它是诸多职业中的一种职业。没有人被强迫担任公共职务或被强迫继续担任公共职务。任何人若试图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可以被认为已自动将他的人格置于公民的质疑之下,以便获得对他的适任性的赞同。或者说,他可以被认为为了获得公共职位带来的好处而自动放弃了许多私人权利。这也是自愿公开原则的体现。
国家工作人员的言行和个人信息比普通公民更加受到关注。这是由这一职业的性质决定的。西方谚语有所谓“怕热就不要进厨房”。明知厨房热,还是选择进去,就得要忍受那较高的温度。在选任过程中,公职候选人为了当选可能会主动、或者按照选任规则的要求公布一些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一经公开,就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
运用这一规范来分析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界限,需要注意以下方面:(1)不是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都会受到同样多的限制。一般来说,国家工作人员的私人生活投入公共领域越多,他的隐私权受到的限制就越多;国家工作人员的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他的隐私权受到的限制就越多。(2)无论哪一级国家工作人员都享有一定的隐私权,他们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那一部分隐私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损害他们的这部分隐私并不能促进公共利益,是一件有害而无益的事情。(3)这一规范不仅是隐私权的限制标准,也是保护标准。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施加较多的限制,可能会引起一个问题,即这样做还能不能吸引优秀人才到国家机关任职,从而维持或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公共服务的质量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依靠经验性数据来判断的问题。例如,通过调查不同时期新招聘的公务员学历水平来判断是否可以吸引优秀人才,通过调查人们的满意度来判断公共服务的质量是否下降。如果为了吸引更优秀的人才服务于公职部门而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施加严格的保护,这也是公共利益的要求。*国内法学界在谈到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时候往往引用并赞美据说是西方国家的一句法律格言:“高官无隐私。”其实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也有一句古训:“为尊者讳。”对这两句话都不能不假思索地接受。对于它们的选择适用需要根据社会和时代的变化、根据公共利益的需要来判断。
在这里,我们没有列举“公众人物”的范围和类别,没有通过判断国家工作人员是不是“公众人物”的方式而界定其隐私权的界限,而只是把一般的规范适用到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问题上。适用这一规范的结果就是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作较多的限制,便于公民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了解、批评和监督。这与因人设制、然后适用有关特别规范的结果,表面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适用过程是公平的。因为国家工作人员不过是受到较多限制的一种情况而已。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受到限制,不是因为他们是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因为他们更多地置身于公共领域,其言行更多地关涉到公共利益。当普通公民的行为发生在公共领域中,或者与公共利益发生了关系,其隐私权同样要受到限制。根据这一规范,在适用过程中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施加了较多的限制,但是并没有给他们施加特殊的限制。平等的限制不意味着同等的限制。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较多的限制,是从同样适用于公民隐私权的规范推论而出的。这样也就不存在国家工作人员“牺牲”其隐私利益的问题。这种公平地适用统一的平等规范的方式更可取。
四、对事不对人
有人可能会质疑,在立法建制中排除“公众人物”这个概念以使隐私权规范成为一般的、平等的规范,但是这一概念不正是国外诽谤法中的概念吗?笔者以为,这一概念是司法概念,而不是立法概念,或者换句话说,它是一个特殊事例,是一般性规范的适用结果,而本身并不是一般性规范。我们可以在美国的一些诽谤法判例中找到这一概念,仔细阅读这些判例,发现“公众人物”概念其实是适用先例中“实际恶意”原则的结果。*例如这些判例:Wolston v.Reader’s Digest,443 U.S.157(1979); Hutchinson v.Proxmire,443 U.S.111(1979); Gertz v.Robert Welch Inc.,418 U.S.313(1974)。在民法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中也极少发现“公众人物”的概念。*就笔者的孤陋寡闻,唯一在隐私权条款中提及“公众人物”概念的是中国的《澳门民法典》第74条。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澳门研究中心、澳门政府法律翻译办公室编:《澳门民法典》,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页。一些国际和区域人权公约中也未见这一概念。*例如涉及到隐私权的以下条款:《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第7条、《美洲人权公约》第11条,等等。我国作为一个成文法国家,不同于美国等判例法国家,在立法的时候需要注意把一般性法律规范与司法适用中的特殊事例区别开来:哪些内容可以作为一般性规范写入立法之中,哪些内容可以留给司法解释和推理发展出来。
法律的一般性是法治的基本原理。这一原理要求,法律规范所表述的是一般的、可以普遍适用的原则或规则,尽量避免因人设制、陷于细节。富勒将一般性看作是法律的“内在道德”,看作是一个规则之所以是法律规则的内在标准:“一般性有时被解释成意味着法律必须客观地运作,它的规则必须适用于一般性的阶层并且不能包含专门针对某些人的内容。”*富勒著,郑戈译:《法律的道德性》,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6页。这就需要在立法时超越社会境况的具体细节和作为适用对象的人的身份差别,进行适当的抽象,需要透过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把握其背后的普遍性规定。古代罗马人得以用法律征服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法学家们用抽象概念表述了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原理。我国现行有关隐私问题的法律规定的缺陷并不在于它没有引入“公众人物”这一概念和相关特别规范,而是在于没有充分、清晰地表述有关隐私权的基本原理,以至于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对不同身份的当事人予以同等保护的不合理结果。
法律的一般性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体现人人平等,避免造成专断。在这一方面,哈耶克说得好:“法律若想不成为专断,还需要满足一项条件,即这种‘法律’乃是指平等地适用于人人的一般性规则。这种一般性(generality),很可能是法律所具有的特性(亦即我们称之为的“抽象性”)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方面。……真正与‘身份之治’(a reign of status)构成对照的,乃是一般性的、平等地适用的法律之治,亦即同样适用于人人的规则之治。”*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191页。另一个功能是有助于使人们在立法过程中达成共识,减少法律出台的阻力。这也是一个立法策略:对事不对人的法律更容易获得通过,更容易得到人们的认可。
当然,对哈耶克所质疑的“身份之治”,也不能一概而论。身份可以分为自然身份(例如性别、年龄、父母、子女、夫妻)和社会身份(例如国家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城市居民、农民工)。*近年来媒体上有一种建议,说应专门立法保护农民工的利益。农民工的利益应当加以保护,但是未必要通过专门立法的方式。如何界定“农民工”的身份?为什么适用于农民工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其他具有相同条件的人?实际上农民工的利益得不到保护,正是由于其他一些专门立法未能平等地扩展适用于农民工的缘故。自然身份是无法改变的,基于这种身份赋予权利或施加义务有时是难以避免的;社会身份是可以改变的(在民主社会中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改变的),同时也是很难界定的。所以应尽量避免基于人的社会身份赋予权利或施加义务。“国家工作人员”、“公众人物”是社会身份,而且在立法中并非不能避免那种对这类人物隐私权予以特别规范的做法。只要隐私权规范充分把握住了相关的原理,就不必担心在适用中不能达到合理的结果。在适用中对具有不同社会身份的人的隐私权予以不同的保护和限制,正是统一的、普遍性的规范在多样的、特殊性的境况中的具体体现。立法建制需要处理好一与多、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权利既应受到保护也应受到限制。宪法基于批评国家工作人员是一项民主权利、有利于制约权力和保障公共利益这些考虑而规定保障公民的批评权。隐私权因为权利人的言行涉及公共利益或发生在公域之中而受到限制。保障与限制的原理是相通的。这就是法律规范所需要依据的普遍性原理。当批评权遭遇隐私权时,解决冲突的适当办法是从这些普遍性原理出发来制定规范,并将规范平等地适用有关具体情况,而不是因人设制,在实施时“对号入座”。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批评权与隐私权的适当平衡。
[责任编辑刘慧]
Public Scrutiny and the Legal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Public Official’s Privacy
HOU Jian
(Law School,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8,China)
Public scrutiny on the internet leads to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ights of criticism and privacy,which can be resolved by defining the boundary of privacy.The popular suggestion is that the privacy of “public figure” should be given less protection than that of ordinary person according to two deferent kinds of norms.Public official is a “public figure”.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suggestion is contrary to such principles as equality of rights and generality of law,and it is not necessary to import the concept of “public figure’s privacy” into Chinese law system.What ought to be done is to stipulate general legal norm of privacy.The norm consists of three factors which define the boundary of privacy: public sphere,public interest and voluntary publicity.The norm equally protects and limits everyone’s privacy.It is up to the courts to apply the norm and deduce the concept “public figure” from the application.As the result of the application,public official’s privacy is more limited than ordinary person’s.The norm suggested above accords with the principium of equal rights and legal generality.Above all,“public figure” is a judicial concept,not a legislative one.
public scrutiny; right of criticism; privacy; equality; generality of Law
侯健,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司法部2012年度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一般项目“网络反腐的法治保障与规范”(项目批准号:12SFB2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