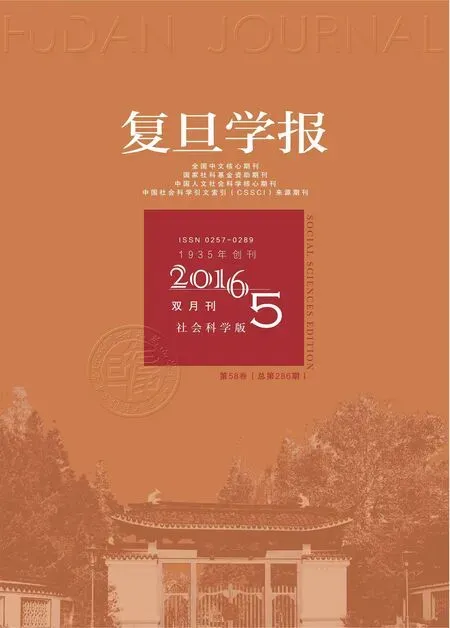边疆结构与“历史中国”认知
袁 剑
(中央民族大学 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边疆结构与“历史中国”认知
袁剑
(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在座的很多都是我的老师,所以这次我主要是来学习的。这里仅就自己关注的一些议题谈一些自己的体会,不当之处,还请各位指正。
我原来做清代边疆史,现在在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工作,主要偏向中国西北和中亚这块。当然,从“边疆”到西北与中亚,这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古代中国的发展史,是边疆与中原关系进一步密切与稳固的历史,同时也是历代王朝治理能力与策略日臻完备的历史。我们看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以发现,曾经有着不同颜色的历代疆域,到了清朝中叶平定准噶尔之后就变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颜色。清朝的大一统可以说实质性地奠定了当代中国版图的基础。与此同时,清廷对其东北、蒙古、新疆和西藏等诸边疆区域,又因其特殊的历史与地缘特征,实行具有差别化的治理方略,而这些治理方略又构成了清朝边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对清代边疆内部多样性特征的认知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清代国家治理的历史脉络,同时也对当代中国的边疆治理提供了历史经验与启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认知又反过来影响着我们对于清之前中国历史的认知,因为这种区块化的边疆地域划分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历史中国边疆的基本划分模式与框架。
“边疆”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地区”,它被灌注进了诸多历史、文化、观念的要素,在历史中国叙述中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我们的印象中,“边疆”作为一种具体实指,往往是条带状的,但实际上这只是现代民族国家体系定型之后才出现的现象,在西方近代民族国家结构之前的中国历史语境中,边疆往往具有移动性,并且其范围也并不局限于紧邻国界的区域。例如,在清代,“新疆”一词就在南方多地出现,直到清朝后期,才成为“西域”之地的专指。因此,边疆在中国史中一直扮演着一个具有伸缩性地域的角色,而且在这种地域中,也伴随着居住在其中的族类与人群的历史迁徙、文化变迁、认同流变等过程。可以说,边疆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历史中国的外围大小,以及历史中国内部民众的数量与构成问题。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他著名的《历史中的边疆》(The Frontier in History)一文中曾指出,边疆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而不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只有在出现边疆观念之后,共同体才会将其与地理形态联系在一起。从属于一个群体的意识,这个群体将某些人囊括其中,同时又将其他人排除在外,比起该群体对在领地内自由生活与迁徙权利的追求,这种意识要强烈得多。如果我们再抽象一点来看的话,边疆实际上是一种内部和外部权力关系的指示器,一方面它成为历史上政治控制的一种实施区域,例如有些官员获罪被流放到边疆地区,所展现的是中央权威的内部权威性。而在另一方面,边疆又成为将内部民众与外部世界隔绝的一种自然与人文屏障。所谓自然的屏障,是指边疆地区与中心地带相比较为贫瘠的生态环境与艰险的天然特征;所谓人文的屏障,是指边疆地区民众与中心地带民众相比较时所呈现出的具有较大差异的社会与人文特征。这两重屏障既限定了历史中国基本的发展空间,同时还确定了内部的“自我”与“他者”、“文明”与“蛮夷”、“化内”与“化外”、“郡县之地”与“羁縻之域”的基本格局,直接引导到历史中国的“大”与“小”问题。我们以长城为例,就可以发现,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抵御外敌入侵、防止北部游牧力量进入中原,更大的意义在于防止中原民众跑到外边去,从而维系中原—边疆关系的稳固,防止双方力量发生根本性逆转。可以说,历史中国中的边疆结构是我们探寻历史中国的“内”与“外”问题的关键之一。
我们注意到,由于边疆本身具有不同于“民族”与一般意义上“区域”的特征,因此,边疆治理也不同于民族事务管理与地方治理,它兼具对“人”与对“地”的政策安排,并具有鲜明的历史与现实维度。在具体的问题层面上,边疆结构以两种主要的外在表象让我们对历史中国的范畴与连续性问题有所反思。
其一是清代边疆遗产如何在历史中国的话语叙述中加以合理归类,并在当代中国进行自洽性解释的问题,这是关于如何处理“地”的问题。以清代边疆为例,随着历史的推移,它已经变成了一种被我们所继承下来的“遗产”。但如果我们细究的话,就可以发现,这种“遗产”实际上隐含着两层意义,即作为制度传承的边疆治理遗产,以及作为具体实物的边疆地域遗产。在具体实践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时刻会面对边疆治理方略的历史继承性问题,这不仅需要对历代中原王朝边疆治理政策进行知识梳理与分类(虽然其中有些知识并非是中原王朝的),进而形成从古至今中国边疆治理方略的整体性逻辑,而且还需要在分析的过程中将对边疆各区域(东北、蒙古、西域、藏地和西南地区)的相关治理政策进行历时性排列,并在排列过程中尽量弥补其中的缺失环节,以确保边疆治理政策的连续性。而在另一方面,又要面对与当代中国边疆地区及清之前历代王朝边疆地区的范围设定与对接问题,而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变迁,各边疆地区的具体范围存在着难以进行历史性接续的问题,进而衍生出“东北”、“蒙古”、“西域”、“藏地”与“西南”又是什么的问题。历史学和人类学近些年关于这些地区的研究实际上正是在回答这一问题。
其二则是跨界民族的议题,这是关于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和当代的边疆地区,如今生活着诸多的跨界民族,例如蒙古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乌孜别克族、朝鲜族等,虽然这一名词是建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话语之上的,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跨界民族当代分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历史中国内部边疆地区的变动所致,其中有些是这些民族群体的主动迁徙(人的移动),有些则是由于民族国家之间边界线的变动(界的移动),如果我们把历史往前推的话,就可以发现,很多现在的跨界民族并没有跨界。因此,如何去看待和解释当代在中国边疆地区的跨界民族历史及其现状,如何在纵向的历史叙述里面解释这些现象并与周边国家的相关历史叙述相协调,同样影响着我们如何看待历史中国的外延与内涵,并考验着历史中国话语叙述在周边邻国历史话语竞争态势下的力度与信度问题。随着中国周边国家内部自我历史认同建构以及国族建设的推进,尤其是原苏联中亚五国独立之后国史、国族建构趋势的日渐明朗,历史中国的边疆叙述话语在一些区域尤其是西北地区正在受到挑战。
总之,对历史中国的叙述和思考不可能脱离对历史上中国边疆的叙述和关注,正是历史上的中国边疆才构成了历史中国“小”与“大”之间的一环,成为我们越出传统中原王朝视角思考中国问题的关键支点所在。因此,如何更好地形成一种具有内在统一性与外在协调性的边疆话语逻辑,如何更好地将边疆“人”与“地”的变迁历程梳理出来,进而更好地界定历史中国框架下中原王朝与边疆区域之间的内在关系,将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和认知历史中国的时空演变提供一种有效的分析框架。笔者正在进行的中国与周边国家各时期“边疆”关键词的梳理与分析研究,正是力图从一些细节性层面出发,形成关于历史中国上的“边疆”以及边疆结构的初步共识,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认知历史中国这一更为宏大的议题。
非常感谢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和葛老师给我提供这个机会,也欢迎大家就这一议题进行后续的交流!
[责任编辑陈文彬]
袁剑,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