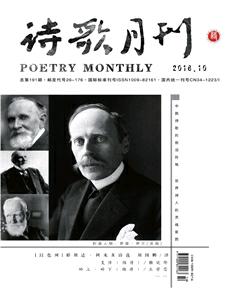岭上·岭下(组诗)
王学芯
山脊上的雨滴
雾从黄昏开始层层
覆盖往事 山峦一步步走远
深夜的雨滴在玻璃板上
在头顶
响彻我的内心
山的黝黑变成天空的皮肤
最细致的轮廓线
不仅消失
灯光也已熄灭
我像挂在山峦上的一滴黑雨
背靠一面临时的墙
狗在汪汪地叫
雨水从山峦的头上滑下
我不知道这个山里的天空
明天早晨有
怎样的忧伤灿烂
岭上
喧响在溶化
这个山岭属于四溢的油菜花
当它的呼吸和一扇门的喉咙
连在一起 一所房屋
被抬高了许多
这个岭上看见的所有山岭
都已成为火苗
腾空升起
躯体上和阴影里的灰尘
都在变成微笑的气息
只有我
隐藏在一座房屋的墙内
被一百瓦的白炽灯光
纸的反射
漂成白色的人
石潭十八寨
山和这里的人在生活下去
最初或最后的年轮就是油菜花开
忘却的日历忘了
用嘴说出多雾的光阴
重复的早晨和晚上
把历史变成一句
我听不懂的谜语
华源河和昌溪河汇入新安江
囤积的一些水潭
放在不觉得害怕的
手边
梦边
用皱纹
编织一座天平桥的流水和雾霭
十八寨居住在各个山头
穿着风景的衣服
在水的倒影中看到自己的照片
以及咯咯笑的牙齿
幽暗落在明亮之上
锅灰吹开了细细的墙缝
衰老的炊烟
等于一个影子在贴近窒息的空间
在我耳朵的小径里走动
在黑与白之间
从昨晚到今晨
我翻转向左 夜浸在
墨池里看不到
我想见到的天空和山的容貌
早晨翻转向右
雾一片迷蒙藏起所有的面孔
天空、山和人
同样消失
向左向右我只看到自己的眼镜
颧骨
鼻子
脑子里是一片黑与白的交替
我不知自己现在何处
不知黑与白
哪个更真实
唯独又一场雨过后
脚前多了一个
水洼
光找到一点点晃动的影子
松果的味道
我在一棵松树下
捡了十九枚松果对这个数字
没有说法 只是
眼睛掠过山坡
有种莫名的味道伴我而来
这些松果坠落在地
作为果实或风雨中的躯体
离开树木
放弃半空的生活
我的手指还是一再地
接近怜悯和土壤
松果坚硬
以自己的鳞瓣保持一种矜持
像黑色的眼睛里
带刺的目光
变得干燥而无常
走进鬼村
我好像看见最后一户人家
坐在最后一间房间里咕哝
穿上迁徙的鞋子
墙裂拐过街角的地方
门窗一扇扇悄悄拆下
墙壁被一个个窟窿击穿
不管是灯光还是太阳
光线的针插不进黑乎乎的阴影
蛛网依稀可见
鞋子离开地面
转过身反应极快的猫
蹭在桌子的脚边
这个村的真正死亡
从这一刻开始墙上斑驳的光影
让呼吸静止
我小心翼翼穿过摸索的小巷
在最后一户人家面前
看到一张鬼脸
北山岭
北山岭这个山脊 雾穿过房屋
和我的呼吸 和上千年的光泽
石头在雾的高处
山脊行走 山岭奔跑 雾已弯腰
房屋的脚比城市化更快
现实控制了风景
这个山脊 这屋里的一切
远离家远离翻山越岭而来的油菜花
借宿的一个枕头
被价格加长
被黑夜默默地延长
让雾
变成山脊上裸露的石头
走在冬季的山路上
山岭沉默。
假如嫩叶和花拓宽每一根树枝
雨滴和鸟鸣在葱绿和光亮之上
同我的心脏一模一样
我走下坡路的时光
嗓音依然
会从体内生长出来
山岭沉默。
一处密集的房子变成了荒村
窗口如同浸黑的长方形朽木
低低的空中
飞栖的鸟
它的羽毛颜色
隐没在比它更暗的树丛深处
岭下
这岭下在身边起伏
山脚被鸟落、鸟飞、鸟鸣的树丛
卷起粗糙的毛边
我躲闪一个个弯道和扑面而来的险峻
在岔口犹豫和心慌
草边的路匝
如同暗示
一步踉跄或稍稍地晕眩
就会有一串抽动的杂技
飞尘翻滚着空气
房屋绕着圈子忽近忽远
空空的田野上
风中的头发触动高山
我在越来越低的
路上继续往下
住在狮子山里面
一片灰暗的天空躲在夜的角落里
更暗的山脊线和山峰
如同一头卧躺的狮子存在
伸出的一只脚前
油菜花变成浅色冷却的气息
浸在瑟瑟的风中
白昼如在身后
黑夜没有一处灯光所有一切
在骤然间停顿
我走到哪里
就把狮子带到我平静的身边
我在呼吸一座狮子山的春天
为自己点亮一点点光
深山漆黑 响彻内心的一缕灯光
如同熄灭的烟蒂
风在树林里每一片叶子
像大地最深处的眼睛
我是一只焦躁的土灶
在三月寻找木柴、菜苔和池塘里的鱼
渴望锅边的香味
心灵
恰如原始的嘴寻找声音的手指
慢慢地适应暗黑 并在
椅子上改变主意
用野外的头灯照见灵魂
在纸上
点亮一点点我热爱的光
源口
源口就像森林
每天的水
汇集起清澈又瞬间消失
源口就像土壤
日复一日
短暂的清澈又很快坠入污浊的溪流
所见的一切就是这样
源口之外好像荒无人烟或在
遥远的天涯
池塘变得越来越浅
村民的手和菜叶、尿盆、洗衣粉
都在水里翻动
因此有更多的光线出现
更多的光晕在
石块上流淌
因此只有反证
水是能过滤干净的源口的水
可以一饮而尽
在黑色的气息中
深夜我在山前的阳台坐着
对面二十米外的墓穴跟我脚趾
隔开一块油菜花地
仰天凝望这极其陌生的夜空
如同一粒黑色的纽扣
扣紧胸口感到
黑色的气息
在我全身弥漫
我点起一根烟对面的墓穴
暗淡了些 油菜花地变成浅色桌布
上面冷冷的风中
放着四枚生了锈的星星
我站立起来发现桌布在突然倾斜
一会儿朝我涌来
一会儿覆盖着墓穴不动
春夜啊我在与不在之间?
寻找白鹇
白色的凤凰。
白鹇是种珍稀的鸟禽
它不告诉任何人它的所在和行踪
它被传说羽毛如同白银做的钥匙
深山里的每棵树间
移动着门心
体态在轻雾间藏匿或消失
树丛的门上到处闪动着羽翎的影子
那红红的嘴
映现成千上万棵聚集的树身
于是它的嗓音挤满了出现的眼睛
手指扣动在枯白的蒲草丛中
而我沉浸或故意显露
一半是为了问好一半是
为了永恒的传说和梦中的深山
蓝雀的出现
咫尺之内的田野 山势
下淌 两棵耸立的银杏树
梢尖上
变幻着大块大块的乌云
背衬的古村落
时光斑驳
鸟声永远不会枯竭。蓝雀的出现
人影愈加稀少
几栋房子的露台被浓荫掩覆
苔藓布满台阶
铁锈爬上栅栏的窗口
蓝雀回到银杏树上
从空房的屋脊飞过空房的屋脊
在筑巢的敏捷中
薄薄的嘴唇
喉咙带了些沙子的声音
门前岩
一块岩石是座山峰
穿着青色的雨衣在远离我的
门前
我的脚没去翻越风光
没用手指
触摸我无法触摸的草叶
我在溪边 在
并不有力的雨中 用一种
纯净的呼吸对应着峡谷的水流
和它的气势
一种湿润的存在 默默想些
绷紧的道路上 一缕青烟
蓝天被山峰的刀刃一块一块割伤
光芒像树叶脱落
感到脚下的山地鞋底
有了些平稳
门前岩穿着青色的雨衣
已在支撑另一面天地
在远离我的
门前
山前塘
足够小的池塘住进一座山
山有了强烈的
生活感觉
足够大的池塘住进一棵树
树枝上的光点
渗出灵魂的嫩芽
池塘里的太阳和月亮
绕着山和树散步汪汪的叫声
新的春天已经开始
我出现在水中
白天的脸黑夜的脸
像上了一层阴郁的清漆
斜躺在万籁俱静的床上
当深山的暮霭飘出远行后的客栈
我在单间小屋把头
枕在平静的手上
床是条干净的河流 我像
吸在堤岸上不动的蜗牛
墙的白色和夜晚
沉入树木之林
窗上的星光给我唯一的明亮
这陌生人家狗在门前狂吠
房屋面对的弯曲小径
伸向山前的坡沟
我斜躺在静听风声的床上
四周万籁俱寂。
4月7日听夏洪林说紫砂
在艺术馆内心
静谧的下午屋内流溢出细语溪泉
天长日久的地质地貌
被手轻捻
情感末梢里的紫砂在掌心
像只眺望的鸟
在阳光的岩石上
平心静气的完美物体
如在悬空的钢丝上移动 六神七窍
化作心中的光华
那一刻风在卷动天地
我知道世上
又多了一个易碎的生命
在独立的山巅
我像在金丝线的光中 生怕
稍一走神
回到人间
隐没在生命的深渊底层
206.3.1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