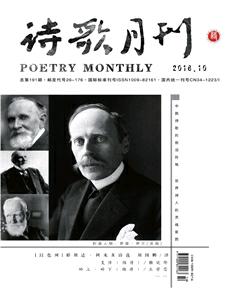写诗是一种精神疗伤
唐成茂
“诗人的品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诗人之诚”
问:你的诗歌论文多次提及“诗人的品质”以及“诗人之诚”,请问作为新时期的诗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诗人之诚”具体指什么?
唐:概而言之,对文字的景仰和对生命的信仰、普世情怀、道德底线等等,都是诗人所应具有的品质。
文本自觉以及文本的独一性既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必须具有的诗人品质。
作为新时期的诗人,我们就是因为要洞明命运的虚无、人性的悲凉而坚持理想。
我们要像对道德倍加景仰一样,景仰和敬畏我们古老的文字。爱不是敬畏,敬畏超越尊重,在对文字既热爱又尊重还深深呼唤深情抚摸推进更新中表现敬畏,文字和灵魂合二为一,化为血肉,如影相随。除了对文字的景仰,对生命的珍重,普世的情怀,诗人必须遵守道德的底线。写作也要遵守道德底线。诗人的道德底线不是约翰-罗尔斯提出的“不奸淫、不偷盗和不杀人”的底线理论学说。道德底线是我们必须捍卫的行为准则,必须坚守的社会精神和意义,必须在创作中做一个严于律己的人,不伤害人,不破坏秩序,等等。
成功的诗人重视对文字的锤炼,对语言有自觉的认识和归属感。成功的诗人都是文体家,自觉修炼出一种非我莫属的创意文体。优秀诗人都还有义无反顾寻找自己表达天空和大地的意识和品质。我们需要对权威大声说“不”,我们需要一意孤行、我行我素,需要挖空心思、苦心经营,需要探索最适合自己的表现方式以及认识社会看透世界的最佳途径和思想力。
但堪称文体家的诗人寥寥无几。所以诗人们整体要走的路还很漫长。可这是诗人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这是诗人必须具有的文字品质,必须的修炼,必须完成的语言“长征”,这是不适合诗人生长而诗人又大行其道的纠结的时代,金钱已不值钱,而诗人比比皆是,每一片树叶落下都会砸到一位诗人。
在诗歌经典化的狭窄道路上,没有文体创造意识和建树的诗人首先就缺少了探索的品质,也许你有汪洋恣肆的情感大潮广阔物理坐标上的思想烧灼但最终挤不上通向未来的那孔独木桥。荷尔德林发出的“诗人何为”的著名叹息,又一遍遍地响起。而希腊诗人、《日落爱琴海》的作者埃利蒂斯在天堂为落日画出了岛屿。他将太阳捧在手上,说:谁也不知道我们的命运,我们会知道太阳的命运……埃利蒂斯在获得诺贝尔奖时,坚持要“为光明和清澈发言”。尽管他深知时代的贫瘠、生命的虚空。
具有文本自觉以及文本的独立无二追求的诗人们,如埃利蒂斯,去除作品悲壮中的冷硬色彩,坚持理想,簇拥大爱,在大地上展示大美。坚持以独此一家、别无二店、唯我独尊的文字,“为光明和清澈发言”、从容不迫地歌颂生命之重、人性之美吧!这是诗人之诚,这是诗人必须具有的文字品质。
诗人要有“精神贵气”和与灵魂交合的异质性风采
问:无病呻吟、无关痛痒的概念与符号写作,无法抵达精警智慧的思想福地,最终导致诗歌精神沉沦、八面受敌、危机四伏。物化的坚冰冻伤了诗意和良心。在如此语境下,诗歌创作是不是比任何时候都更困难?既然诗歌已经边缘化,诗歌创作非常困难,诗人们为什么还要坚守心镜中的“一线天空”和“一米阳光”?在诗歌和灵魂坚守的战斗中,诗人们以世俗目光中的“弱者”和“边缘人”身份力量微弱地开展心灵的“抗战”,在此过程中怎样彰显“精神贵气”?
唐:在当下,诗坛充斥着空心的稻草人,诗歌已经丧失了对现实社会本应具有的回应能力,诗歌缺少了直接关乎生命与血性的词语主张和精神回应,而是倾心于修辞炫技和词语的智力游戏的所谓实验性、探索性,他们追求的文体越来越远离诗歌的生命本源和读者,丧失了应对现实和走向心灵的诗歌自觉和自信,因而正在大面积溃败或者说走向困境并被边缘化。我们遇到了比任何时候都差劲的诗歌生态,我们的写作比任何时候都更困难。现在文学退居时代的次要位置,诗歌完全无法进入经济的轨道,无法像书法、绘画等艺术品一样走向市场,也不可能像小说一样实现“华丽转身”,变成电影和电视剧,卖个好价钱。
我们所面临的世俗,物质主义已经武装到了牙齿,我们的写作是一种灵魂的捍卫,我们要保卫我们灵魂深处的诗歌,我们打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诗歌保卫战”。在这场诗歌艺术的“保卫战”中,也不断有“丢盔弃甲”的战士。诗歌在节节溃败,我们在一次次退守。放弃诗歌的“逃兵”脸色煞白地嘲笑我们的坚定、坚持和坚守。
诗歌是我们对无所不在的束缚和世俗迫害的最有力反抗,并在此过程中彰显我们诗人的尊严和高贵。除了我们已一无所有一无所求,除了精神的尊贵我们已无物可以彰显大量大气大贵,我们坚定信心,纯洁心灵,誓与诗歌共存亡同始终。
我们以世俗目光中的“弱者”和“边缘人”身份力量微弱地开展我们的心灵“抗战”。我们抵抗似乎力量强大的对我们层层围困的敌人,我们反抗有形无形的约束和挤压。这种约束和挤压,过去更多地来至于体制。而现在,是来自时代、媒体、高科技、商业运作以及语言本身的掌控。这就需要我们在“求真求新”意志之下对灵魂和困境的双重揭示,对生命的直击和探幽烛微以及对血脉的特殊导读与照亮,使我们获得自由想象和独立思考的能力,获得观察事物的精确度,精神的张扬和灵魂的交合,以及写作的从容、优雅与庄严……
我们正面临深度沉沦和极限危机,我们的写作步履维艰。但是,我们不会沉沦,不会退缩,更不会在世俗“淫威”之下举起白旗。因为时代需要诗歌和诗人,需要纯净而贵气的文字,需要我们抵达一种刻骨铭心、撕心裂肺的尊严之美,一种舍我其何、责任所在的生命担当和尊荣之光、辉煌之媚;因为我们唯求在现代主义诗歌谱系中,过着普通人的生活,精神生活可能有一些伤痕的诗人,仍旧用日常书写昭显悲壮浪漫主义精神诉求,功勋章一样地抚摸我们的历史和文化,顽强地给本也伤痕累累的时代展示沧桑之美、悲壮之态、痛苦之力,展示我们精神的贵气以及与灵魂交合的异质性风采。
当代诗歌写作者的困难不是知识、智慧、才华的短缺,而是心灵的空虚与困顿与困惑。写作的庸常化、媚俗化、奴性化导致精神文化的矮化、钝化和异化。不少诗歌写作者写作中没有心智,心灵没有质量,人格没有独立,做人没有气场和不够大气,在机械的操作、盲目的跟风、媚俗的撒娇、无力的做派中,让旭日之光落入风尘,让精神之花布满尘埃,让圣洁艺术的柔美花朵黯然枯败……
我们的诗歌写作者需要增加文化纵深拓展的力量和心灵质量的提升、由方块文字彰显的精神气度,以抵达一种精神境地,抵制物质化的东西对诗人的诱惑,纯洁屡屡被污染的诗坛,让诗歌更美丽,让诗人更有底气,让诗坛更加圣神更加充满活力吸引力。应该以“别样的心态”理解“诗人已死”
问:诗人死了、活着的诗人不再“守节”之类似是而非之论曾经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抛出网文,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诗歌尚存吗?诗歌会消亡吗?
唐:我们应该以“别样的心态”理解“诗人已死”,我们应该看到诗歌的复苏,看到大批诗人的坚守。100多年前,维克多·雨果就用反证法驳斥了“诗歌消亡论”。那时的诗坛阴霾密布,人们不相信诗歌,诗人自己也看贱诗歌,写诗的人越来越少,已武装到牙齿的世俗一步步得寸进尺地挤压诗歌和诗人越来越窄小的天空。诗人几乎没有容身之地。这时,维克多·雨果挺身而出,他铿锵有力地驳斥了“诗歌消亡论”者的荒谬论调,认为诗歌不会消失。雨果说,如果诗歌消亡了,那就等于说,再也没有玫瑰花了,再也没有月光了,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也消失了……母亲不再爱孩子,天空越来越暗淡,人心已冷硬、死亡。尽管物欲的坚冰在吞噬着宝贵的诗意,但是诗歌是顽强的,诗歌的顽强,让它仍然成为我们心中的神殿和向往,当人们的生活越来越枯燥的时候,我们仍然会想念诗歌,仍然会追求诗歌,诗人们仍然会回到诗歌中来。
不得不承认,有个阶段,诗人已死,我们已经堕落。比如海子、顾城、骆一禾、戈麦等诗人之死。写诗的人纷纷叛逃,乒乒乓乓地扔下诗句,毅然决然地走向世俗,走向物化的坚冰。或坠入生命的渊薮,作别于“人世”。诗人,这个曾经置身于社会声望之巅峰、引领时代之潮流、尊严而荣光的辉煌之词汇,已被人列入“最近十年就会消失的词汇”之中,其如美人之迟暮之黯淡,只能常常无奈地回忆起那已经逝去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之光芒,以及已经显得久远的才子佳人之浪漫情怀,我们没有见到其华丽转身的动人心魂之时刻,只见到其夕阳底下失去了魅力和光彩的隐隐约约的仓皇、凄凉的背影和太息,诗人的伟岸和傲立于人群中的姿态渐行渐远欲说还休。
于是,诗人死了、活着的诗人不再“守节”之类似是而非之论甚嚣尘上。甚至有人抛出网文,提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还有人写诗吗?诗歌会消亡吗?诗歌会安乐死吗?诗歌“安乐地死去”。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诗歌身体的倒下、肉体的死亡和灵魂的安息。
这里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诗歌写作艺术上的继承问题。诗坛曾经经历过全部欧化和对传统的全盘否定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当时在一些诗人笔下体无完肤、荡然无存;二是诗歌本身和诗人数量的问题。经过“朦胧诗”运动后诗坛一段时间内寂静无声。大工业化冲击下、全民言商大语境下诗人纷纷“变节”、诗歌退出“江湖”。诗歌和诗人于是籍籍无名、微乎其微,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尤其在靠生活阅历加战斗激情创作“史诗”的年代,“浮出水面”的诗人和作品,并无前瞻性和指导性以及创作的心灵实绩。诗人成为世俗中的逐利者,享受安乐,不与寂寞为伍,不厮守孤独,因此“安乐地死去”。
何谓死亡?死亡就是灵魂(psyche)出离肉身(soma)。诗人的死亡是人在江湖,心离诗意。从世俗意义上说,就是虽死犹生,死而复生,活得更好。这其实是诗人返还俗世,归入芸芸众生行列之举。这跟我们追求的哲人之死、高贵地离世,不是一回事。关于死亡,苏格拉底说,因为绝对的正义、美和善存在着,亦即真理存在着,纯粹的心智能够通达纯粹的真理。因此,哲人在生前必须尽可能多地接近知识、少迷恋肉身,使灵魂不受肉身牵累、保持纯净,以迎接神的恩典时刻的到来。在生离死别之际,苏格拉底在雅典人民法庭做了最后一次演说,说,“我毕生努力追求的,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哲人……”苏格拉底用金黄的气节描绘了自己的死,嘲笑了雅典人的生,用死亡的勇气,践行自己的哲学主张,捍卫了精神的尊严。
但真正具有诗歌情怀的人,无论他在哪里,无论他处于何种境遇,都不会放弃诗歌。诗歌在自己心里,如身体的肌能,不可剥裂。因为生活和工作的关系,暂时的停笔,只能是一种写作的“战略转移”,绝对不是放弃,绝对不是诗人在向世俗投诚。在大时代急遽变革的过程中,需要诗歌来指引。如果说文化是国家的灯塔,诗歌就应该是文化的良心和走向。在激情澎湃和青春燃烧的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深圳,诗歌不但没有走向没落和消亡,反而如破土之新芽,蓬蓬勃勃生长。
在创造过唐诗宋词之辉煌的中国,近年来诗歌有回暖迹象。在大工业化冲击语境下,诗人最终没有退出“江湖”,最终能为诗歌“守节”,诗歌“反季节”地“绝地”开放并且无比灿烂。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拾起诗歌的火把,开始或坚持艰苦但快乐的诗歌朝圣旅行。其中诞生了一批“归来派诗人”,他们穿过生活的雨林,热情地“归来”。诗歌写作队伍在壮大,诗歌活动越来越频繁,诗歌已经出现文化化、常态化的趋势。中国诗歌的力量越来越大,不断有诗歌事件冲击诗坛,不断有新的、具备一定影响力的诗人横空出世。盛世出佳作、繁荣出诗歌。在能够创作史诗的当下,诗人在延续着汉语诗歌的辉煌之旅。诗人创造了如此的诗意人生:“世界处处皆诗意,每一位有心人都在诗般的境界中,过着诗意的人生。”
正如广东一位著名评论家说的那样,一个曾经诞生过唐诗宋词的国度,总会有人选择留在诗歌的腹地,继续汉语诗歌的辉煌之旅。写诗是对人生的承诺,这个承诺从年轻时就已经开始,诗歌以及诗歌精神已与自己的生命紧紧相随,是不应该在某一天像丢掉一个廉价的职业一样将其丢掉的。中国已经成为正在扩大的诗歌容器,盛容着各种理论冲撞交流的新诗歌理念和新诗歌作品。在如此大容器下的诗坛,不仅诗人在不断“复活”和“归来”,不仅诗歌文化圈在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大量思想先锋和写作愤青涌入改写诗歌孤独、寂寞又无聊的历史,特别是在社会急遽发展变迁的大时代能够诞生与时代发展同步的大诗歌——宏大叙事、历史反映、生命礼赞……鼓荡着青春和激情,如朝阳之初升,如大地之回春。当代诗人保持着强大的生产力和思想力、意志力,其作品展现了写作的丰富和辽远,他们的经验、思想、才华和创造力,使中国诗歌更加鲜活不断获得新的延伸的生命。将极大的包容性和独立精神相溶于水并归于无形,以新锐、新觉、新思、新话语品质,隐于改革开放的洪大激流,经诗歌的旧工业化改造,以原始能耗的最初级商业阶段的粗放型话语权和话语方式,汲取东西方文化相碰撞形成的思想营养以及大改革大开放大包容文化可作为艺术原料、养分的宏大气场的鼓舞,在隐性“沉没”中激烈发酵膨胀,脱颖而出划破长空的诗歌光芒。诗歌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的生活
问:在一些诗歌调查文章或诗歌评论文章里,经常会见到你流露出来对20世纪80年代中国诗歌情状的眷念和怀念。你对那个已经逝去的、诗歌大行其道、诗人备受追捧的激情燃烧岁月就真的那么值得留恋吗?
唐:是的,我留恋那段美好时光。那个时代诗歌是一盏明灯,照亮了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诗人不缅怀在心灵深处永远闪耀着思想光芒的1980年代。那是诗歌大行其道、诗人备受追捧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在那个时代,“朦胧诗”风起云涌,诗坛红旗飘扬,几乎人人都是诗人,诗人是人民的英雄和舵手,诗歌是我们的全部生活和命运。在那个诗歌当道、人人读书和写诗的年代,我们贫穷落后,我们生命渺小如草芥,心灵的荒原渴望精神的甘霖……我们和诗歌不期而遇,我们从此拿起钢刀般、森林般的笔,写下一行行发光的文字。我们以我们的手写我们的心,我们用心做文字的上帝,我们用文字做生活的导师。我们用诗歌启迪智慧的灵光,用诗歌拯救荒芜情感的大漠,用诗歌做灵丹妙药减轻心灵的疼痛,我们在生命的隘口用诗歌贯通了走向未来的“断头路”……有了诗歌,我们的生活就不再贫穷,我们的心灵就不再有荒漠,我们的前方就不再黑暗无边……没有一个人不怀念或向往那个“文字为大、诗歌为王”的年代,诗人们一门心思淬炼诗歌之剑,个个懂得诗句的排列、框架的构建、情感的表达、意向的铺设……人人都是诗人,个个都是勇敢地奔赴诗歌圣地的“诗歌义勇军”。
在那个诗歌史上彻底捣碎了“旧时代”的特殊时期,诗人们热火朝天、热情洋溢地创作一首首或汪洋恣肆或动人心魂的现代主义诗歌,诗人热衷于参加各种诗歌活动,所以到处都能够看到诗人的影子,诗人时时伸手就能够抓到诗意。那森林般的手臂、潮水般的呼喊,不是为娱乐明星,而是为诗人,为诗歌领袖,为诗神缪斯。在那个诗神高于或大于天神的年代,诗人们没有上帝,没有神灵,缪斯是最受尊敬、追捧的上帝和神灵,缪斯给人温暖,用爱照亮世界。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诗人对社会的贡献无比之大、无限之阔。这是诗人暂时未被世俗所接受,诗人的价值暂时未被世俗的眼睛所发现之处。世俗的眼睛发现不了诗歌对生命经验的深层洞悉,世俗不可能容忍天才的浪漫主义诗人在肮脏的世俗社会对生活的诗意营造。
诗歌是谜,行走如风,
无迹可觅,无法把握
问:诗歌写作有没有章法可循?有没有“诗歌方程式”之说?怎样看待诗歌写作中的个人性与历史性问题?
唐:诗歌是谜,诗歌来无影去无踪,无迹可觅。我们永远找不到清晰的诗歌写作路线图,尽管我们都上过写作课,也许部分人还有厚重的写作理论积淀。诗歌是难解的方程式,谁也不敢说自己就拿到了解题的标准定理、定义和公式。谁也不敢说自己写的就是诗,就是好诗,别人写的就不是诗,就是歪诗。诗歌之谜,永远没法破解。诗歌就是诗歌,诗歌写作就是经营语言的过程,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到语言为止。诗人对语言的追求和追随近乎忘我,近乎苛刻,一往无前,永不回头。写诗就是用语言切入生命的内部,切入灵魂的最深处,在一切已经秩序化的语言化中发出有别于人的声音,捣碎别人也捣碎自己,从而建立一个诗歌化的容易引起人的心灵震颤和共鸣的陌生化的语言世界,获得无限珍贵、令人叫绝、鲜为人知的艺术个体。诗歌无迹可寻,并非说诗歌是空穴来风,没有自己的形体和组合方式。诗歌自由摄入和存在、发展的方式和文字秩序。诗歌有质地,具轻质性或厚重感,精密度很高,不可约束,字面意义不可翻译和解说。诗歌具有精确的归位意识和无限开阔、令人遐思绵延的包容性功能,超越日常情态。诗歌离经叛道,破除一切迷信和僵硬的口号、范式。诗歌体积小、质地轻,行走如风,无法捕捉,无法把握。不可以给诗歌强加上思想教化的职能。诗歌也与生活关心、主义论争等格格不入,也不提倡使命意识。投入火热的生活现场,体验光怪陆离的社会百态,这是小说和纪实散文的任务,与诗歌关系并不是太大。
令人不解的是,现在这些东西竟然成为了责难我们刚刚新鲜出炉、腾腾冒着热气、活泼可爱的诗歌惯常性的理由,成为一首诗歌是好是坏、有否价值、值不值得推荐的致命标准,为没有灵魂、没有语言的质感与立体交错形态的人云亦云的平庸之作争辩护嘴的逻辑前提。有的评论家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的道德评判规则,诗歌的批判功能,要求诗人按图索骥式地照单买菜式地批量“供应”。
诗歌是唯一真正反理论依据的艺术形式,不与金钱挂钩,不与实用主义有任何瓜葛,不接受“新闻采访式的”写作任务。我们的诗歌,无比自由,无拘无束,打破了时间、空间的边界以及所有附加的条件。具有综合处理复杂对象能力、充满大爱尊严、具有质疑精神、对美有终其一生的渴望的诗人,追求和追随诗艺的诗人,能够将非诗的甚至是肮脏的丑恶的东西经过诗歌化的处理各归其位,变成既有准确性又有广阔性,既有个人性又有公共性,既原汁原味地反映心灵之欲又对诗歌之美有所贡献的作品。
我们的诗歌,语言始终顺着风,意境时刻贴着地,观照日常抒写和细腻情绪。表象和意蕴平静、和谐、开阔、大气。仿佛来自岩浆的底部,弥漫着泥土根部的气息,浸淫着柴草味、胭脂味和青翠与温馨的情愫和仪态。个人性其实也具有时代性,个人性高于强加的时代性,个人意识其实也具有历史容量、哲学重量、美学质量、生命力量。
写诗是心灵疗伤的精神救治
问:有心理学家说,让一个心理病人爱上一门艺术,这精神治疗才可以根治人的心理病。从这个角度说,写诗其实就是一个人一生精神疗伤的过程。你对此如何看?
唐:是的,写诗就是在精神疗伤。一个人的童年创伤,可以用写作来治疗。诗人在此过程中,温暖了自己,也激励了读者。诗人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缔造者。我们的作品必须应对现实,深入生活,有哲学之思,能将现实浓缩成可以触摸、可以感知、可以展望的诗意化的文字形象,给人推动之力、憧憬之美。在现代主义诗歌谱系中,有使命感和责任意识的诗人可能精神生活留有文化的伤痕,但是诗人留有文化的伤痕的作品仍然具有美学价值,仍然会在现实的世界、内心的世界进行诗性呼唤,反映文化心态,表现高层次的哲学意识、人性诉求。我们的诗歌写作者需要增加文化纵深拓展的力量和心灵质量的提升、由方块文字彰显的精神气度。
我在一本心理学著作上看到一个观点,让一个心理病人爱上一门艺术,这精神治疗才可以根治人的心理病。海明威也曾经说过,一个人的童年创伤,可以用写作来治疗。写诗其实就是一个人一生精神疗伤的过程。每个人都有童年,有的人童年生活艰苦、悲楚,这种童年生活将影响这个人的一生。有的人自此萎靡不振,对生活失去信心,浑浑噩噩地了此一生。而有的人拿起笔来,记录童年生活的况味和沧桑,点点滴滴都是情。后者就是诗人,写作是诗人心灵疗伤的精神救治方式,诗人越是童年生活艰苦、悲楚,作品越是要写得温情和美好,让人看到就是夹缝中也有新希望。这就是大气和大义,这就是大爱无疆。诗人在此精神疗伤的过程中,温暖了自己,也激励了读者。诗人的内心布满伤痕,但在抚摸功勋章一样的历史伤痛时,展露的是沧桑之美。站在精神的雪域高原,诗人能够忍痛抵制诗歌精神文化的矮化行为,让心灵世界抵达精神崇高的文化彼岸,彰显一种回望之美。在大气而高贵的诗人群里,一切定义与不定义的诗歌文字都为之太轻,只有心灵的痛苦与快乐,能够让读者感受生命之重、体会诗歌之崇高和文字之辉煌。
卡夫卡的内心疼痛是没有天梯、没有通往天堂的道路,卡夫卡的内心都是对天堂的幻想,展示给我们的是诗意的美丽和带有文化神秘元素的远方。金斯伯格那有名的《嚎叫》展示的是发泄之苦与怒吼之美,针扎般给人的心灵以真实的体验。这就是我们居于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之境况之下、寻寻觅觅已久的理想化的文字姿势和写作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