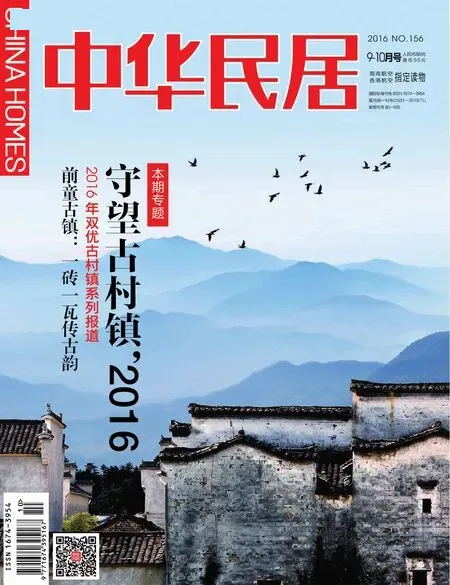爱面食的锡伯族“马架子”,“来兰皮”
爱面食的锡伯族“马架子”,“来兰皮”


马架子是泥土和茅草搭建的纪念碑,镌刻着艰苦创业和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值得人们永远敬仰。
在我国历史上,华北和东北之间往来频繁,但无论是行军作战,还是民间旅行,在明代以前,古人一般都不通过“辽西走廊”这一沿海的狭长平原地带,而是取道建昌、朝阳、义县、北镇这条线。这条路离海岸较远,是丘陵地带,史称“辽西故道”。当年秦始皇东临碣石、曹操北伐班师、隋文帝东征高丽走的正是这一故道。我们要讲的辽宁锦州市义县万佛堂村,便是处于辽西故道上的一处锡伯族聚落。
据史料记载,锡伯族虽然由蒙古八旗编入满洲八旗并调入齐齐哈尔、伯都纳等城驻防,但他们生活的区域并没有太大的变化。随着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锡伯族人口不断增多,势力也逐渐增强。清政府为了加强对锡伯族的控制和统治,采用分而治之的民族政策,将锡伯族迁往盛京及北京等地。勤劳勇敢的锡伯族人民,在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的历史上,建立过不可磨灭的功勋。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平息准噶尔叛乱后,清政府为加强伊犁地区防务,从盛京、辽阳、义州(今义县)等地抽调锡伯族官兵1000余人,连同眷属共4000余人,自沈阳艰苦跋涉一年多,步行一万多里,在新疆屯垦戍边。锡伯族为建设边疆、抵御外侵做出巨大贡献,于是当地将每年农历四月十八定为锡伯族的“西迁节”以示纪念。全国锡伯族总人口大约19万,基本分布在辽宁和新疆伊犁地区。如今现居义县北的锡伯族人便是当年南迁盛京之时,留守于此地的锡伯族士兵的后人。其他各县区的锡伯族人,则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因工作分配或婚姻嫁娶,由各地迁来的。
锡伯族的房子有其鲜明的民族特点,早先有种介于窝棚和正房之间的被称为“马架子”的民居,它和土墙茅草房一样,都是土坯砌墙,草苫顶,也有门窗。房子的形状像一匹趴着的马,它只有南面一面山墙,窗户和门都开在南山墙上,这是昂着的马头;屋脊举架低矮,“马屁股”上耷拉着厚厚的茅草。房子从正面看呈三角形,侧面看呈长方形,由于简单易建,在过去的东北较为常见。当年北大荒垦荒时,垦荒的官兵们却对“马架子”情有独钟。在他们眼里,马架子就像屹立在沙漠中的金字塔,神圣庄严。有位老兵写道:“斯是马架,唯吾德馨。四墙霜如银,房顶草如金。谈笑有三军将士,往来皆农垦尖兵。炕上绘宏图,炉边谈远景。无思乡叹息,无畏难之逃兵。延安土窑洞,罗霄茅草棚。革命者曰,展望前途,无限光明。”马架子是泥土和茅草搭建的纪念碑,镌刻着艰苦创业和乐观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值得人们永远敬仰。

除了“马架子”,锡伯族还有种人字形大屋顶房,宽敞大方,屋檐宽出半米左右,窗户很大,有的一间房子就有四五个窗户,窗户格木形状都很精致,小而多曲,几乎和雕刻的一样,并且门框、窗、屏风上都有精雕细刻的图案。这种房子造法也相对简单,先用木料搭起房屋的骨架,然后用土坯垒起来抹泥、刷灰。房屋前面墙两头,都有一米多宽的“玛图”(挡风的屏墙),房屋的廊檐和“玛图”并齐。老式房屋廊檐很宽,可以遮风避雨,保护门窗不受风吹雨淋。如今,锡伯族人多建被称为“来兰皮”的房屋,其大致造法是:当房屋垒到一定高度后,把比碗口粗的椽子从中间锯成两片(细一些的不锯)在墙上水平放7根、9根或11根(奇数)。剥了皮的苇秆(芦苇秆踩扁后泡在水里数天,使之不易扯断)5根至6根一把,用苇子隔3至4厘米一把扎在横椽底下,在苇子上面抹粗麦叶子泥,等干后,房子里层再抹细泥上光,称之为“来兰皮”,最后再在来兰皮上面垒山墙封顶。随着锡伯族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建筑材料的多样化,现在锡伯族民居多改为瓦顶,还出现了不少砖木结构的新房。值得一提的是,锡伯族以西为贵,故西屋由长辈来住。过去房屋都有“安巴纳罕”(大炕),这种火炕由三面环绕的南炕、西炕和北炕组成。南炕由爷爷奶奶或父母睡眠,北炕由客人睡眠,西炕一般不睡人,有贵客来时请之坐卧。一般客人和家人不能在西炕上坐卧,因为西炕靠山墙立佛龛供佛。
在万佛堂村住上一些日子,你就会发现,锡伯族人日常生活中非常喜欢面食:蒸馍、发面饼子、面条、韭菜盒子、南瓜蒸饺等在他们的餐桌上十分常见。要是来了尊贵的客人,热情的村民还要杀羊款待,做一桌丰盛独特的“全羊席”(锡伯族人称之为“莫尔雪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