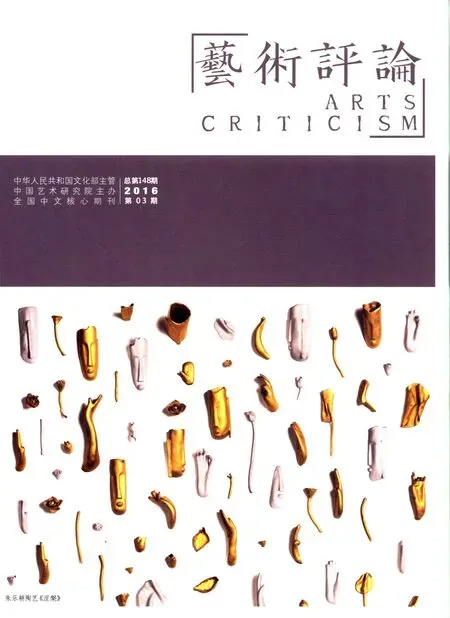我们该如何谈论上海越剧观众
谢雍君
我们该如何谈论上海越剧观众
谢雍君
在上海,聚集着一批最内行的越剧观众,这批观众,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剧目?是古装戏还是现代戏?传统戏还是新创剧目?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喜欢越剧,他们的年龄结构如何?有多长的看戏经历?看戏的频率是多少?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越剧是怎样的?这些问题,我们业界好像知道一些,又好像不很确定。其实,我们对越剧观众的了解,一直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程度。所谓的似是而非,如果往深里说,就是不了解。
我们一直在说观众是上帝,这是保证良好市场的前提和保证。但事实上,我们一直只限于口头表达,而没有将这种表达付诸行动,用实际的调研方式去了解他们。比如,文化部及地方文化部门曾做过多次戏曲调研,包括越剧。但这些调研的重点是剧种、剧团,而不是观众。尽管观众在演出团体看来,对于剧团的创作生产相当重要。但事实上我们的调研都忽略了这个内容。
十年前,是越剧百年华诞暨上海越剧院建院五十周年。时任院长的尤伯鑫向记者介绍说:“上海越剧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本地演出市场比较好。我们剧院每年220场演出,其中将近一半是在上海完成的。”[1]所谓上海越剧演出市场好,言外之意,上海越剧院拥有厚实的观众基础,是其他省份的越剧团体所不可企及的。这个特点,十年后依然鲜明,并没有因为时光的逝去而黯淡。
那么,上海越剧观众到底是怎样的观众?
每个剧种的发展史上,都有一个特殊的群体,推动着它们前行的车轮。昆曲、京剧是这样,越剧也是这样的。
追溯越剧发展史,发现早期绍兴的笃班闯荡上海滩时,班里是清一色的男艺人。以班主的初心,希望能以男班的形式在上海落户。但是,几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到了30年代,他们开始改换思路,以女班形式冲击大都市市场,结果大获成功。这次的成功是以前几次对上海戏曲市场的了解作为基础的。因为班主们发现,这个时期的上海歌舞剧场、戏场出现了一批女观众。早期的笃班不招女生,为了抢占上海市场,班主们打破旧规矩,在上个世纪30年代起开设女班,只招小女孩训练。从这个角度来说,越剧最后能够在上海滩扎根,乃是顺应了上海大都市观众群体中女性占有大比例的变化趋势。这点与文人士大夫推动昆曲发展、宫廷贵族推动京剧发展,是不同的。
当我们谈论昆曲时,一定会提到文人士大夫曾起到的特殊作用。从魏良辅给昆曲定腔定调起,昆曲艺术传播主要依靠文人士夫群体,他们的生活情趣、审美品味如豢养家班、筑造园林等,影响了昆曲艺术的生态及其发展。而当我们谈论京剧时,常会提到另一个群体,那就是宫廷贵族。清代晚期的帝王喜欢京剧是戏曲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特别是慈禧,对京剧的欣赏、推崇提高了京剧的社会地位。在慈禧之前,清宫演戏以昆、弋腔为主,不看重二簧戏,认为它低俗、嘈杂、不雅致。但慈禧不仅挑选伶人进宫演戏,促使京剧表演艺术不断提高,而且亲自参与改编京剧剧本,提升了京剧的文学品味,推动了京剧艺术在贵族阶层的流传。
当我们谈论越剧时,联想到的既不是文人士夫,也不是宫廷贵族,而是上海市民观众,尤其是女性观众。上海女性观众的审美品位影响并催生了越剧艺术的成熟、定型,如果没有上海女性观众,就没有女子越剧的兴盛。越剧表演美学的确立,与上海观众女性眼光和审美评判的反哺密切相关。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戏场里,越剧女班的崭露头角,《梁祝》《古庙冤魂》《宝玉与黛玉》等剧男女主人公催人泪下的悲情故事,拨动着女观众那敏感的心弦,吸引着她们进入戏场。女观众成为女子越剧的拥趸。但是,她们又不是单一的受众群,她们与男性观众不同的审美情趣和欣赏习惯,反过来推动女子越剧的成型和完善。40年代,细腻深沉的尺调、悲愤激越的弦下调的出现和创造,都是上海女观众的欣赏品味在女子越剧艺术上的映射和呈现。女观众对悲情、柔美的推崇与迷恋,加速了女子越剧走出只有四工调、清板音乐形式的形成时期,而进入更加富有表现力的音乐成熟期,加快越剧剧种成长和定型的步伐,助力女子越剧在十里洋场的扎根和壮大。
关于越剧的未来发展,曾有诸多文章提出不同看法,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越剧必须保持女子越剧的特性,以创作古装戏为主。之前,笔者也秉持此种观点,以为越剧若欲使自己具有特性并与其他地方剧种区别开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保持并发扬其两大特性,即女子越剧和古装戏,二者缺一不可。但最近,笔者看到一份资料后,对这种看法,稍稍有所修正。
这份资料是《舞台下的身影——20世纪40、50年代上海越剧观众访谈录》一书里两位越剧戏迷的回答。采访者问:“比较喜欢看古装戏,还是现代戏?”戏迷回答:“这倒不管。”采访者再问:“只要演得好看,您都要看的?”戏迷回答:“我主要是认人的,演什么戏不要紧的。”从中笔者寻获到一个信息:上海戏迷是认角儿、捧角儿的观众。这就为越剧为什么会有流派、甚至流派纷呈的现象,寻获到渊源。昆曲以剧本为重,历史上没有流派之说。而越剧不同,自上个世纪30年代越剧流派的逐渐产生,由此相应地诞生了一批追捧演员的女观众。“他们不仅要欣赏原有一批老艺术家的演出,要听他们喜爱的流派;同时还希望后起之秀能继承老师的流派,要求他们从表演到唱腔越像越好,最好能保持‘原汤原味’。在演出中,一句拖腔像老师,可以博得满堂彩,一步台步像老师,可以赢得众人赞。”[2]这就能理解,上海越剧院为何不必忙于到外地演出,每年在上海的演出场次就可以占有年演出量的一半。因为上海越剧院有不同流派且技艺超群的演员,这些演员又拥有各自的戏迷。不管演什么,是古装戏还是现代戏,是全本戏还是折子戏,只要演员上台演出,上海戏迷就会以热烈的掌声奉送给他们的偶像,用热情的呐喊来表明他们对偶像的热爱和追随。
上海越剧观众的身份并不单一,从传播的角度来说,具有传播受体和主体合二为一的特点。他们既是戏迷,又是行家;既是传播受体,又是传播主体。
越剧源于浙江嵊县,却在上海成型。上海观众见证了越剧发展史上每一个寻常细节和几次重大变化,他们是越剧历史的在场者和亲历者。从这点来说,杭州观众乃至绍兴(嵊县)观众都望尘莫及。越剧有多长的发展历史,上海观众就有多长的观剧史。因着如此深厚的历史因缘,上海越剧观众不是普通的戏迷,而是越剧行家。
越剧观众从戏迷转变为行家,经历了一个从看热闹到看门道的过程。1949年之前,进入戏场的观众大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他们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品位高于普通的市民。1949年之后,观众以工农兵、劳苦大众为主,更多的普通市民进入了越剧戏迷的行列。他们欣赏越剧的水平与越剧艺术的发展进程相平行,是随着越剧艺术的成熟、发展而不断进步、提高的。
1959年,一位爱好越剧上海工人家属、普通市民张佩君说,以前上海里弄里的一般家庭妇女看戏是看人,注重某艺人在戏中换了几件行头,扮相是否漂亮;时间久了以后,就不看重这些了,而关心戏本身,喜欢讨论戏里的主题思想、情节和人物[3]。这位越迷经历了只看重演员外表扮相到留意剧目主题内容的变化过程,她的变化过程正是大多数越迷观众从外行蜕变为内行的必经之路。还有一位越迷,他是一家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但他在迷上越剧之后,就不再搞自己的工程项目研究,而是专注于越剧联谊会事务,并在厂里成立戏曲社[4]。这种将个人的爱好升级为越剧联谊会、戏曲社的集体活动,以及将个人智慧熔铸成集体力量的行为,给越剧观众群体带来的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的,更是从外行抵达内行的质的飞跃。有了戏曲社,越迷们可以自己排戏、演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行家。
所谓行家,指的是他们除了看戏、捧戏,还会评戏、写文章,对当前的越剧现状做出批评。当他们从戏迷上升为行家之时,正是从传播受体演变为主体之时。张利敏,一位越剧老观众,针对上世纪90年代上海越剧界佳作匮乏的现状,曾撰写《上海越剧缘何落后之我见》(《上海戏剧》1994年第3期),指出上海越剧发展的两个问题:一是90年代上海越剧演出题材的选择有失偏颇,二是越剧青年演员的艺术修养有所下降,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半年后,《上海艺术家》《上海戏剧》两家杂志联合组织了一次越剧批评讨论会,特意邀请上海越剧界的编、导、演及专家学者,就90年代上海越剧存在的外在困境和内在不足进行研究、探讨,旨在寻求解决方案。而这场讨论的肇始,乃源于越迷张利敏对当时上海越剧现状的质疑和不满。戏迷观众发文章批评戏曲现状,不是个别的现象,这说明了上海越剧观众有着非同普通戏迷的艺术鉴赏力和判断力,他们的艺术品位已经达到行家的程度。
有着日常的熏陶和历史的积累,上海越迷在判断越剧剧目和演员的艺术价值时,不再流于浅层次的赞赏、喟叹,而是进入到深层次的品味、审视和评判,从日积月累的观演经验中生成一套属于他们特有的审美判断标准。这种标准既有感性体悟,又有理性思索,兼具感性和理性的双重特性。这种审美评判的双重性,成为了上海越剧观众的审美特性。
剧种与观众的关系,如同鱼和水的关系。鱼水相依,不可分离,一个剧种的现实生存、未来发展,也与观众的追随、推赏密不可分。上海越剧观众的三种特点,既有其独特性,也有与其他剧种相同的共同性,它们相互交织,成为上海越剧观众的传播特性。鉴于此种特性,上海越剧创作生产可以遵循以下三种基本原则。
其一,遵循市民趣味的原则。
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越剧观众主要以家庭妇女、工厂女工、女教师、女中学生等组成。但不管哪种类型,都是市民阶层。所谓的市民,即受过一定的文化教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但不是知识分子。市民趣味与文人趣味是有所不同的。如果说文人趣味是讲求高雅精致,讲究品位,崇尚意境的话,那么,市民趣味则具有趋俗、尚奇、求变、好乐特点。相对于文人趣味的纯粹性,市民趣味有着更多内涵,也更为复杂和多变,市民趣味甚至包含有文人的某些趣味。如,到了新时期,越剧观众群因为增加了新生力量,他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学生、白领阶层,那么,越剧的市民趣味则增添了文人趣味。但是,市民趣味依然是市民趣味,他们隶属于市民阶层,而不是纯粹的文人阶层,它与文人趣味有着本质的区别。顾锡东先生曾经总结新时期浙江越剧剧目的特点是“一俗二浅”,所谓的“俗”、“浅”,正是市民趣味最通俗的阐释。小百花越剧在浙江省内外的流行,青春靓丽的舞台呈现,通俗浅显的故事情节,满足了都市市民的审美需求,映证了新时期都市市民对越剧市民趣味的呼唤和渴求,使市民趣味的文化特色得到了再次强化。
其二,遵循捧角的原则。
众多懂行观众的存在,意味着上海越剧为自己培养了大批忠诚者,他们对心目中的越剧有着自己的要求和衡量标准,讲究演员的表演和唱腔是否正宗、正派。观众喜欢捧角,这是好事。但也是面双刃剑,因为越剧创作人员的创作有时会被观众的喜好所束缚。演员唱腔、做派越像前辈,越有渊源,越受欢迎。但上海越剧人不能只满足于此,而应该跳出越迷爱好的篱笆,找到创作新空间和增长点。我们应该注意到,越迷除了追捧,他们还喜欢时尚,喜欢变化。凡是有创意、有意味的新作,都会赢得他们的欢迎。
其三,认可观众身份的双重性,遵循既顺应观众又引导观众的原则。
如何既能顺应观众的欣赏水平,又能发挥剧团创作的特色和潜力,笔者以为袁雪芬先生在40年代的改革策略,对我们依然有借鉴作用。袁先生30年代演出的传统戏,基本上顺应当时上海滩观众的审美趣味。但自40年代创作新剧目开始,从《古庙冤魂》《断肠人》《雨夜惊梦》,到《香妃》《祥林嫂》,她逐渐调整创作策略,不再以单纯满足观众的传统欣赏方式为目的,而是有效地开发他们审美趣味里的多样性和可能性内涵,在新剧中融入新思想,让观众随着她创作理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逐步接纳她的新越剧。这种以引导为主、顺应为辅的创作策略,至今还可视为越剧创作的基本原则之一。
上海越剧观众的行家身份,说明上海越剧作品投放到市场后,所遇到的问题会比其他越剧团更多,得到认同的难度高于其他城市。但是有高度,才有挑战。能够站在一定高度创作出来的作品,成活率也会相对高些。那些能够经受住上海越剧观众检验的剧目,一般来说,离精品就已经不远了。所以,上海越剧界能拥有如此高水平的观众,是件令人庆幸的事。顺应观众,引导观众,让观众的喜好转化为发展的动力,能做到此点,就会成功。
注释:
[1]黄小驹.上海越剧:在“行走”中捕捉发展机遇[N].中国文化报,2006-5-8.
[2]纪乃咸.中国越剧大批评[J].上海艺术家,1995(1).
[3]看戏十年——记本刊编辑部召开的观众座谈会[J].上海戏剧,1959(2).
[4]中国越剧大批评[J].上海艺术家,1995(1).
谢雍君: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杨明刚
——王海城作品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