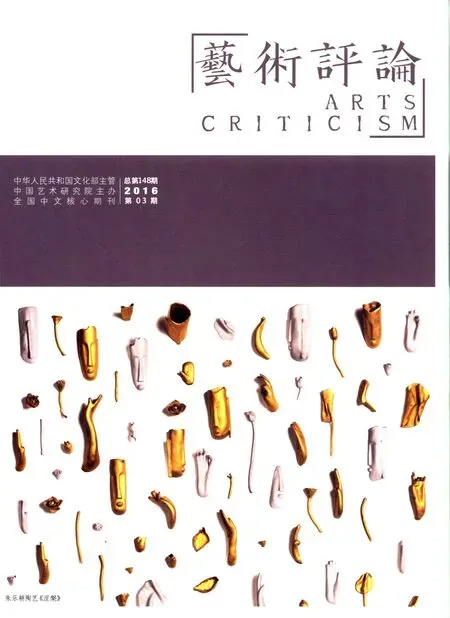纯粹与变异——关于身体的聆听、凝视与言说
肖向荣
二、用作凝视的身体——结构方式的变异与纯粹的凝视
纯粹与变异——关于身体的聆听、凝视与言说
肖向荣
纯粹与变异,是2015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创意舞蹈研讨会的主题,引起了国内外舞蹈专家们的热烈解读。文化的多元交融,亦成为此次舞蹈研讨的重点。来自澳洲、美国、台北、香港、北京的7所大学带来代表自己教学理念的13部作品。地缘和文化的差异,使得这些作品呈现出某种似曾相识但却陌生的形态。熟悉的是,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当代舞的美学正逐渐建立起一套范式,无论受到哪一个地域或是哪一种文化的影响,作为当代舞所应该具备的身体性、技术性以及构成舞蹈动作的方法都是有迹可循的。来自美国的作品大都可见崔莎的放松技术的蛛丝马迹,香港的客席编舞流露着强烈的欧洲新舞蹈的气息,来自台北的两个作品兼具美式风格与东方气韵,来自北京的作品则是浓浓的学院手工作坊的老味道。然而,正如刘建教授在研讨会上提到的“通过纯粹提炼而更加纯粹,在纯粹的变异中达到更高精度的纯粹”,这些作品都基于追寻某种纯粹而自觉不自觉地进行变异,在不断地变异中去找寻更加高级的纯粹。
本雅明曾经在《在世纪交界处的童年柏林》中如此形容:“在城市里要像在森林中一样迷路,则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多年之后,我才学会这门艺术,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从我练习本里绘制的纸上迷宫即可窥知一二。”这就可以解释在当今全球化、互联网时代的当代舞创意者身上为什么有一种我们熟悉的气味,这些生长在城市里的人,无论纽约、洛杉矶、台北,还是珀斯、北京,尽管经纬度不同,文化不同,所受到训练也是形态各异,但却有一种共性正在逐渐加强,或者说在所有“追求更高级的纯粹而不断变异”的过程里,只有一样东西是纯粹的,即:城市属性。这里要讨论的关键词是“城市”,13部作品13个名字各个不同,背后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城里人,再确切地说就是“城市里迷失的人”。虽然本雅明也说过“在一座城市里找不到自己的方向,可一点也不有趣”,但是恰恰是这种迷宫式的游戏极具当代舞创作者的灵感,戴剑《虫子为何忙》显然是城里人朝九晚五的写照,古倩婷《易碎物质》从物理名词导入实际是挑明人与制度的战斗,苏安莉《冬恋》则是无可救药的城里人对一场雪的期待,耿军、马灵芝《事件》虽然在节目阐述中写道“很久以前,村庄里,来了异乡人”、力图脱离城市这个概念,但是身体却出卖了他的掩盖,大量城市生活动作剪接拼贴都说明先前那句话是“此地无银”。作为城市里的人,迷失已然成为某种纯粹的标示,回忆与梦境、迷宫与回廊、恍惚与惊搐,这些都是当代舞中所呈现出来生命状态,在不同文化构成中变异成某种城市间的肉身幻象抑或是一种全球式的精神抽搐。
一、用作聆听的身体——语汇的变异与纯粹的聆听
苏珊·桑塔格对卡内提的宣言有 “倾听者”(hear-er)而非“观者”(see-er)的描述,他发现“盲目是对抗时间与空间的武器。我们存在正是一种巨大的盲目”。对于舞蹈者的身体而言,用可以被倾听来形容是因为这三个作品的作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偶像”这样的主题:《易碎物质》中的制式大衣,《事件》中的贴满彩色符咒的外乡人,《偶像》则干脆就将空心皇帝雕塑放在舞台上。笔者将这些作品归纳于“倾听”并非轻视其可舞性,相反,他们各自的动作语汇均呈现出某种“纯粹的变异”而赋予作品一种“巨大的盲目”,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像以往欣赏舞蹈那样关注舞者的动作流程、风格、技术,尤其是古倩婷为香港演艺学院所做的《易碎物质》,舞风时而暴烈,时而猥琐,时而忘乎所以,时而小心翼翼,这位希腊籍的编舞家游走于欧洲,但是她并没有带来爱琴海的和煦暖风,也没有欧罗巴的优雅从容,舞者的身体体现出各种文化变异,中国功夫、日本空手道、巴西的街头格斗作为用来表达意图的语汇,所呈现出的音乐性(节律)大于程式化的舞蹈动作。笔者在观察古倩婷的课程时发现一个有趣的关系,她的教学方式以及启发舞者的方式极为独特,与其在说教学,不如说是在挑衅学生,师生之间处于一种对抗的状态,凶横,暴烈,所有的动作都出自身体本能的反应,犹如一个格斗学校的现场即视感。如此怪异的舞风却并没有矫揉造作之感,而是迅速将观者带入她营造的盲目的世界。身体不再是舞蹈的工具,动作也不再遵循舞蹈的常规法则。正如她自己所说:“易碎物质”本是物理学名词,指一些挤压而成的物质只要受到来自另一个方向的压力便会分解或是改变形状。借用如此简单的力学改变,舞者的身体要么征服较量克服痛苦,要么选择投降屈服,身体性的视觉刺激被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刺耳的咆哮、机器的噪音,耳朵作为专注的接收器成为唯一的证人,见证在舞台上发生的专制与对抗、屈服与反制等等戏剧性的画面,舞蹈的身体被肢解为支离破碎的残片,让观者凭借自己的想象去完成编导者所绘制的迷宫拼图。来自北京的两位编舞者虽然没有选择如此极致的表达方式,但是在身体的使用方式上,都规避了常规的身体表达,甚至呈现出宁可哑剧也不要动作的某种倾向,可以看出,这个当代舞的美学范式,正在被极大地拓展,舞蹈正在跨越动作的边界,向着更广阔的身体经验发展。视觉经验将不再是评判舞蹈的唯一标准。身体不会撒谎的这句格言被以上三位编舞者改写成了“耳朵是唯一的证人”(苏珊·桑塔格语)。
二、用作凝视的身体——结构方式的变异与纯粹的凝视
作为观看的舞蹈存在了几百年,观众选择用眼睛观看舞蹈早已约定俗成。舞剧不仅仅要剧情的推进,还要高超的技艺展现,于是在大部头的舞剧以及二十分钟以上的舞码中结构方式很难被彻底推翻,戏剧性的隐藏推进以及舞蹈动作直白表达将观众的视觉神经挑逗到极致。在当代舞中也有大量的结构范式,基里安的荷兰舞蹈剧场、以色列的帕切瓦舞蹈团的表演都体现出如此的结构方式,将身体的精致化放入一个极简主义的结构中,看见身体看见技术。然而来自纽约的戴剑与来自台北的林文忠却有不同意见,他们呈现出一种共同的变异方向,就是在结构上抛弃形状形态以及一切看上去是结构的东西。这也许是因为这两位中国血统的编舞者有着共同的身体经验和艺术履历:第一,他们都是在东方文化下进行舞蹈启蒙训练,戴剑在广州,林文忠在台北;第二,他们都在纽约跳舞,戴剑在沈伟舞团创团,而后成为崔莎·布朗最宠爱的东方演员,而林文忠游走于美国各个大小舞团,在比尔·提·琼斯的舞团里踏上他的舞者生涯的高峰;第三,他们都不善言辞。这两位都是闷不作声的人,如果不是他们的朋友或是同道,应该很难听到他们的声音。沉默成为他们的共同的特质。也许正是因为沉默,才使得他们的作品具备“凝视”(staring)的质感。“凝视”是相对与“观看”(looking)而言的。这一点,苏珊·桑塔格在《沉默的美学》中有详尽解释,不多赘述。首先是《虫子为何忙》,犹如笔者开篇提到作为当代舞的共同特质——城市,这部舞作特点是缓而不慢,静止地流动,作为舞者的身体的观看性被缩小,甚至有些地方很容易被忽略,也不再有完整的结构感,笔者跟随排练的全过程,戴剑最沾沾自喜的就是“找到一种以往从未有过的结构方式”(戴剑语)。由于刚刚完成纽约大都会美术馆计划,他兴致勃勃地要研究在公共空间里的身体表达。舞蹈家进入博物馆表演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莎莎、华尔兹、西提拉比、沈伟都有类似经验,然而影响戴剑的身体最深者是崔莎·布朗,在公共空间表演的大家崔莎女士给予戴剑十分富足的经验营养。《虫子为何忙》实际跟虫子无关,作者本身也没有采用全知视角来鸟瞰人类。相反,作者采用孩童般的平视视角,在孩童的注视下,每一个微观都被无限放大,这样的动作细节需要观众将自己的观演模式调整到“凝视”方式。一个钢铁的结构被放在绿草坪上,舞者有意无意地静止、交谈,看似简单的碎片动作,环境音乐,老式留声机的音响效果,像极了我们童年那个沉闷无聊的夏日午后,正是因为这样沉闷、这样无聊,使我们更加为电光石火般的微小变化而感动。偶尔微风,偶尔窃窃私语,偶尔路人甲闯入,戴剑成功地将公共空间移植到剧场内部,连灯光都是如日光一般的运动,一不留神,巨大的钢结构就移动到另一个空间里,再一不留神,全剧就结束在一个小女孩的指尖上。一切莫名其妙,但一切却顺理成章。《虫子为何忙》不是成年人的自问自答,而是曾经的天真、相信、好奇心都随着岁月光阴不可救药地失去,永远地失去。作品的时间轴似地推进,恰恰适用于舞台表演,这一点在林文忠的《长河》中也是异曲同工,在鼠标和遥控器能够随意控制进度的年代里,喜欢与否都不能任性地快进暂停或是关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所有事件的发生。这一点,我们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三、用作言说的身体——文本变异与纯粹身体的言说
日本剧作家山崎正和在他的《世界文明史——舞蹈与神话》这样阐述:相对于“做”的身体指向划一化与集体化,“在”的身体意在异质化与个别化。作用于外界的“做”意味将身体作为意志的工具,而工具的使命就是使统一运动正确反复。与此相反,确认“在”的身体每一次都是探索未知,因此必须与前一次不同。[1]关于“做”与“在”的身体有了两种趋向:可言说与不可言说。回到身体符号学,恰如刘建教授在研讨会上所说,“作为舞蹈者的身体他的存在,应是追究更高级的纯粹”,是否可以这样解释,当身体成为意志的工具时候,他是可言说的,例如《天鹅湖》《红色娘子军》等等;当身体作为存在的价值,就变得不可言说,如这两天晚上的当代舞系列作品。来自世界各地的创作者们并不是想讲一个故事,在他们的创作的原初也许有一个文本。常肖妮隐藏了《皇帝的新装》这寓言,John park 将一个商代流传到非洲的传说解构浅尝辙止,肖向荣为西澳大利亚表演学院创作的《Fowing Stone》也来自于查尔斯,西米克的诗歌只言片语,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王童引入《甄 传》的故事原型。文本一如以往地存在,但是大部分编舞者都选择回避情节,淡化剧情,仅仅留下原作的一丝丝气味。笔者与多位编舞者讨论,认为在文本变异与身体的言说中大都是如此构成,文本仅仅作为作品的意志的一个工具,而用来自我言说的身体却恰恰是文本不可言说的一部分。写到这里,想起本雅明曾经“想写一本完全是引文的书”,编舞家不再像以往创作者那样忠诚于原作,选择文本的意义可能远远不在文本的本身,而是将文本通过身体译制成另一个作品,文本成为一个入口,作为生活在今天这个世界的人来说,这个入口是通往“在”的身体的意义所在。人为什么要存在?人如何存在?以何种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这些问题成为更多创作者的原点。在犹如迷宫般的浩瀚文海中,每一位创作者都像一叶孤舟,在固执地找寻自己的航线,拒绝洋流,彼岸在何方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用身体的探险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本届创意舞蹈研讨会以“纯粹与变异”为主题,旨在将教育与创作放在同一个平台上来比较研究。舞蹈是身体的艺术。身体既是表演的媒介,又是表达的主题。值得关注的是,这一届的编舞家都是各大学舞蹈系的专职教师,他们都有着多年舞者的经验,有些甚至依然坚守在舞台上。创新是国内热议的题目,但是这几年的国际交流很少提及这个词,身体的研究及其可能性却被重新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单纯形式感的标新立异、高科技的技术使用反而成为这些创作者避之不及的“怪兽”。回归身体,回归人性,回归作为创作的原点,独一无二的原点,才是永恒的主题。舞蹈,作为最古老艺术之一,以原始舞蹈的宗教仪轨,到文艺复兴之后的自娱与娱乐性观赏,始终在不断发展着。时至今日,舞蹈的纯粹,又成为趋势,回到本体研究的原点上。作为教育单位中的一员,我们可能无法教授某种创新技能,也无法强迫学生尊崇自己的丛林法则,我们唯一能做就是不断让他们看见世界的现状,看见真相,看见多样性的变异,在不断变异之中,也许有人就能成为“更高级的纯粹”。我想这就是以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舞蹈系为发起人的国际舞蹈院校联盟[2]的共识吧。
注释:
[1]山崎正和.世界文明史——舞蹈与神话[M].方明生、方祖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18.
[2]国际创意舞蹈联盟院校包括:澳大利亚西澳表演艺术学院、美国那佛罗里达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台北艺术大学、中国文化大学、香港演艺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美]苏珊·桑塔格.土星座下[M].廖思逸、姚君伟、陈耀成译,台北:麦田出版,2012.
肖向荣: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舞蹈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杨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