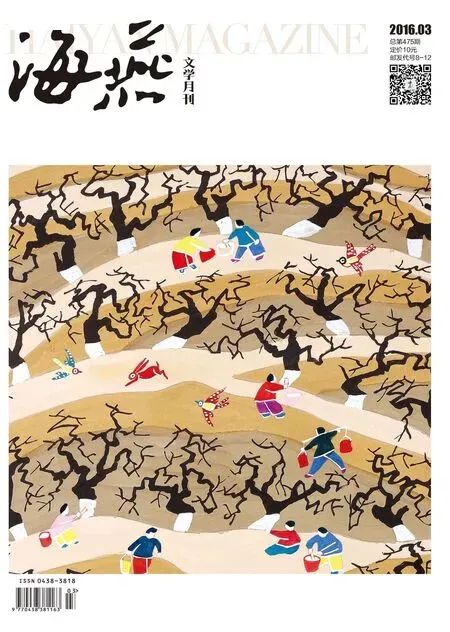多少年才能堆出一座山
□杨角
多少年才能堆出一座山
□杨角
杨角,四川宜宾人,职业警察。诗歌作品散见《诗刊》《星星》等,并入选《中国年度诗选》《中国诗歌排行榜》等多种选集,曾获中国公安2014年度诗人奖,四川省“首届天府文学奖”,《现代青年》2014年度最佳诗人。出版个人诗集6部,散文集、合集2部。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3届高研班学员。
长江零公里:一滴水
明天会流向哪里,无法预知
但对昨天,我绝口不提
投胎为水,一生就是一条下坡路
就是把心气放下来,一点点接近大海
黄昏太安静了,我试着
从心中取出一片峡谷,让所有散步的人
都能听到轰鸣的水声
一首诗写到这里就是一个人活到了这里
往前,一条年轻的江失去了好身板
往后,礁石林立的峡谷不再有一口好牙齿
作为一滴水,走过万里路
到这里都将归零
流水上千年,因早晨而获得重生
一首诗写到这个势头上
只求每天都有一次出发,都有一轮太阳
从江水中升起
在横断山区
我想问问最初堆山的那个人
从有溪水的山脚下
用石头,一层一层往上堆
要多少年才能堆出一座山来
大部分石缝都是整齐的、平行的
可以向着一个方向延伸
为什么有的突然断裂了,变成了斜行
他是不是也懈怠过,或思想走神
是不是石头不够,停歇一段,又改填泥土那些天然的山洞,是不是有意
给居住在山里的神,预留的窗子
我还要问,要怎样的技术
才能把一座山堆进天空里去
要修改哪些参数,才能在半山腰堆出白云
在横断山区,我一路走,一路问
一只鹰从云层穿出来,使我眼前一亮
转瞬,它一抖翅膀,又去了远方
格桑花
花朵是女人投的胎,在这里
它们叫卓玛、拉姆,那些叫不出名字的
应该叫它们次仁
突然来到一群美女中,内心
挂满露珠。不忍亲,不忍碰
她们是我前世的妻妾,今天是百年后的重逢
一声轻唤我就来了,唤一声我就应了
这高原上的土著,星空忘了带回的精灵
上帝只是给了它们一个六月
它们便随时可以开上天空
男人天生不是做花的命,犹豫再四
我决定留下来,与前世相认,一只蝴蝶
老是在花间,遇见一只垂直起降的蜻蜓
在若尔盖写诗
再往北就出四川了
就是甘肃和青海的地盘
满身风尘的胡杨张着永不愈合的伤口
我不愿看见
带刺的沙枣睁着警惕的眼睛
我,也不愿看见
到一条大河为止
我的诗只写到大河以南
北方有高原,我也有,只是略低一点
北方有大漠,我没有,但可去词典里看一看
没有的东西我都不写,我只写草原,写牦牛
写九寨沟——这滴全世界最大的泪水
它已经蓝得无法无天
再往北就是诗人马加和萧萧的题材了
我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写不出大西北的苍凉
我收拾行李,明天,先回成都
在橙岛
远方是圆形的。
没有桥,远方带着波纹,
由一艘木船送往天边。
这个岛子不姓杨。没关系,
只要有木字旁,有花香。
远方的云朵不停地落在一座小岛上。
花果同枝,橙花如云。
一个季节的情绪被春天反复提升。
一场盛大的聚会在暗中进行。
从表面看,那些花朵、绿叶,
只是在风中,轻轻摆动。
我来了,就不走了。
我用祖传的姓氏,在橙林深处
为自己搭一座草棚。
红桥镇
桥还在,但不是红的
一条小河,带着硫磺的浑浊,四季流着
枯水季节,大半边河床
荒废在一汪流水旁边,内心铺满砾石
等待来年的洪水,把它背走
一座镇子被几匹山环绕
右手是云南,左手是贵州
天上飞着高原的云朵,四川的鸟
苗族和汉族都是这里的土著
隔山唱歌,下河捕鱼
一只背篓,把三个省的天空都装下了
镇子以前叫梅花镇,现在叫红桥
南边那座山上,有亭子,有寺庙
九十岁的黄善人牙齿快落完了
他也说不清楚,这座石桥,为什么不是红的
一个疯子对一座城市的规划
所有山丘全部推平,取消公路
平地上修房子,只修一层
一人一间,按姓氏笔画分配
让汽车消失,出行乘坐飞机
住房下安轮胎,水陆两栖,防震防灾
交通都走天上,规划立交,100米一层,避免飞机撞车
几千年了,上帝住在天上,笑看人类拥挤
我们往天空发展,让上帝也拥挤一回
实现这个规划大约需200年
这个时间并不长呀,从湖广填四川开始
我已在此生活了三个多世纪,你只需转三次世,投三次胎
就能住进一座比乡下还要宽敞的城市了
我的大学
这些年,我已在体内
建成一所大学,自任校长
所有课程全天候开放
文科在左心室区域,工科在右心室区域
研究生和博士生,安排在心脏部位
甚至可以高出我的头顶
动物学、植物学、社会科学平衡发展
白天上汉语课,入夜上外语课
一旦发现谁被暴力和猪油蒙蔽了心脏
加修一学期《圣经》
善良是校训,专业不细分。遇崇洋媚外者
多学《孔子》与《孟子》;对好吃懒做、脂肪过剩的人,集中上体育课,参加义务劳动
苦了那些学子们,摊上一个写诗的校长
搬寝室,课程搞混,是常有的事
女生住进了唐朝或民国,男生搬往隋朝和宋朝
动物学在人群中上课,美术课改在了森林中
本校长尊崇人性,倡导个性
凡打铁超过嵇康,挥锹不弱刘伶,大肚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者
皆可毕业
对心怀杂念、自以为是,在校区内装神弄鬼之辈
一律留校察看,迁往体外的B区
由蚂蚁和瓢虫上课,教他们从最小处学起
心电图
被一只麻雀衔枚致谢的
应当有:树木、干草、稻麦
和一条在沙粒中
把身子断为两截的蚯蚓
还应当包括猎人突然压低一厘米的枪管
绷紧又松开的弹弓,故乡棬树上
那只伸向鸟巢最终收回的手
这些年我像一只麻雀
口衔木棍
对那些危难中给予帮助
愤怒时放下石子的人
一直心存感激
只是至今我还没说出一句
完整的感谢
水中捞月或难分胜负
用一只竹篮打水,能收获十万颗金星
结识水底捞月的先贤,看见一群自得其乐的人
谁说竹篮无用,谁又说一场空。提刀杀水
水有断裂的痛感。呻吟是卷曲的。
抽去声音,它就是一种花,从水面一直开到天涯
在岸边坐久了,内心的江会跑出来
会有手无寸铁的人驾着战船向江中撒网
日复一日捕捞浪花。结网之人已不在岸上
他们重新回到水中。这个世上,捕捞者与被捕捞者
走到一起,是迟早的事。他们间的胜负
必须要一场决斗,才能重新分出
与黄昏抗衡
突然发现一种游戏,可以玩一辈子。
尽管,我最终将是那个认输的人。
但今天我还没输,我还有很多绝技没有用上:
降魔掌、阴阳剑、夺魂枪,我正在
秘密修炼撒米成兵的本领。功成之后,我可以
体内体外闪转腾挪,人与自然相互置换,
古今中外自由穿越。
有好几次我动用意念和咒语,用自我安慰
和障眼法,使黄昏推迟了一秒。
晚钟响起,灯光晚亮半步。星星姗姗来迟,
我被自己镇住。
有一种固执叫明知不可为而为,叫死无畏。
当夕阳
又一次掉进长江,转世为一堆气球,
我是那个背着气球沿街叫卖的人,双脚离地
就要飞翔的人。这么多年我一直
在为一堆气球,安装方向盘,和引擎。
花生米定律
二弟生前曾说:吃花生米
总是先拈大颗的,再拈小颗的
最后连小颗的也拈完
这些年我改变了一个习惯:吃花生米
先拈挨我最近的,然后稍远的,由近及远,不分大小
一路拈下去……
我一直试图打破二弟发现的这个定律
其实人和花生米是一样的
年长者是大颗的,年幼者就是小颗的
只是我至今还没找到,那个挥动筷子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