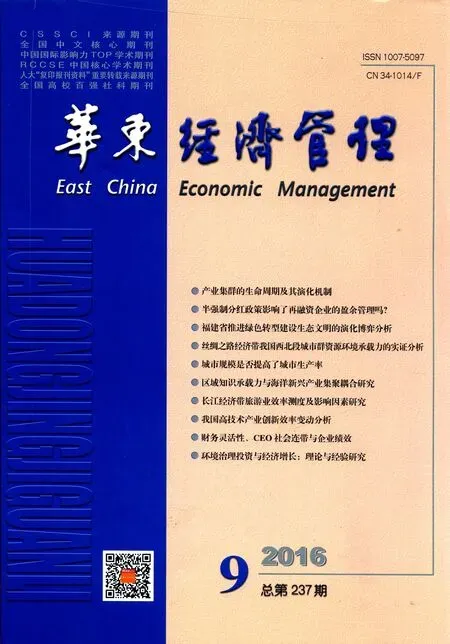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及其演化机制
——基于开放条件下长三角重点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吴福象,杨 婧
(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985”高校经济学人计划
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及其演化机制
——基于开放条件下长三角重点制造业的实证分析
吴福象,杨 婧
(南京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93)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企业以代工的形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众多企业扎堆在此形成了中小企业集群。然而,近年该地区产业集群的去集群化现象开始逐渐显露出来。文章选取长三角22个制造业的数据对其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进行了实证研究,探寻产业集群在生命周期各阶段的演化规律,在此基础上提出促使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再发展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2005年以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程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而在长三角制造业集群演化中,伴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集聚效益上升开始越来越快,不过在区位熵超过某个临界范围时,集聚效益上升开始变得缓慢,而资本深化程度和开放程度均具有正向效应。可见,当前长三角制造业集群可能已经处于生命周期的成熟与调整阶段,增长动力不足,发展变缓。因此,从集群产业链的角度来讲,需要适时进行战略调整和再定位。
产业集群;生命周期;产业演化;集聚程度;集聚效益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就确立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并以加工贸易作为战略突破口。具体表现在通过关税减免、出口退税、设立出口加工区等一系列举措,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此种战略导向下,诸多跨国公司的区域内积聚提高了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同时,通过国际外包等形式的生产合作来引领本土企业进入产品内分工环节,并借助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销售网络,让中国经济尤其是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当中。
与此同时,以老板进城和外资牵引为主体特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加速了中国非均衡发展战略在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实施,尤其是制造业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长三角地区也凭借其特有的区位、劳动力、技术等优势,成为中国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
的主要承载地,并逐步发展成为我国工业化程度和层次最高的地区之一。
不过,自从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也面临着许多难题:一是整体投资回报水平下降,发展模式面临转型的压力;二是产业技术创新动力不足;三是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逐渐趋于饱和,部分制造业有向中西部迁移的趋势。比如,2014年上海、江苏和浙江制造业工业销售产值分别为3.10万亿元、13.56万亿元和5.99万亿元,相比前一年,除上海市销售产值份额有所增长外,其余均有所下降。
从“微笑曲线”来看,长三角地区承担国际分工的环节仅仅处于中间附加价值最低端位置。目前,中国的生产成本优势逐渐流失,尤其是来自东南亚、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长三角利润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微笑曲线”的谷底日益加深,同时使得长三角劳动力与发达国家技术交换时越来越处于不利境地,产量的扩大并不能带来实际利润的增加。从这一层面讲,该地区有落入“丰收贫困”陷阱的风险。此外,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新常态双重背景下,受资源约束和国际市场的影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开始出现产业向外转移的迹象,转移方向除了我国中西部之外,还向东南亚进一步转移。例如,优衣库的一些国内代工厂业绩萧条,温州数以千计的小鞋厂因接不到订单而关门歇业,电子电器行业三星、仁宝、富士康也纷纷在东南亚和印度设厂。与之相对比,墨西哥制造、东盟制造由于开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效应开始显现,使得这些国家成为接纳发达国家和地区产业转移的新阵地。
关键的问题是,长三角作为我国制造业水平最高的产业群落,是否因为过度集聚带来新的无效率,应当促进集聚还是限制过度集聚?从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来看,该地区目前处于哪一阶段,其演化机制如何?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的发展历程,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又有怎样的影响和示范作用?本文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展开研究。本文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述评,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及假说推演,第四部分是数据说明、指标选定与统计分析,第五部分是模型构建与计量检验,最后是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许多学者研究了我国制造业的变动趋势,指出东部制造业的集聚曾经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比如,范剑勇(2004)[1]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布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绝大部分行业转移进入东部沿海地区,但国内市场一体化水平总体上仍较低。罗勇和曹丽莉(2005)[2]利用EG指数对中国20个制造业行业的集聚度进行测算,发现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程度依次上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与工业增长表现出较强的正相关性。雷鹏(2011)[3]则指出产业集聚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表现出其积极的正面效应,同时也存在扩大地区差距的负面影响。
近年来,国外学者开始关注集聚的负面效应[4],我国学者也逐渐关注到集聚效应的动态性问题。比如,杨扬等(2010)[5]的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速度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我国城市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的临界值的实际人均GDP水平在28 283元左右。徐盈之等(2011)[6]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经济圈已经出现了过度集聚,并且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吴三忙(2010)[7]通过集聚程度对时间的回归发现,近年来促进产业扩散的离心力作用开始显现,部分制造业呈现由东部地区向其他地区转移的态势。孙浦阳(2011)[8]的研究表明,伴随着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集聚的好处将被削弱。陶永亮(2014)[9]研究发现,空间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当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集聚促进增长,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减弱。
纵观现有研究,发现存在以下两个不足:一是过多地关注制造业的集聚趋势,而对扩散趋势关注较少。产业集聚曾经促进了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年来随着土地、劳动力、能源等成本的上升,长三角制造业正面临产业结构调整的问题,是否出现了促进产业扩散转移的离心力值得关注。二是对细分的制造业行业关注较少。过去的研究将整个制造业看作是一个整体,对分省分行业两位编码制造业数据分析不够,现有的研究细分制造业也主要是对集聚程度与时间进行回归,没有关注到细分制造业的集聚效益问题。
三、理论分析及假说推演
下文主要是以长三角制造业为研究对象,基于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的关系和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两个视角,分析长三角制造业集群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关于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交互关系的理论
产业集聚理论的源头,最早可以追溯到Alfred Marshall(1890)的《经济学原理》[10],他从劳动联合、要素共享和知识溢出三方面论述了外部性原理。随后,Alfred Weber(1909)又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进行了更深入的论述,从费用角度来分析企业经营者的区位决策,认为经营者一般在所有费用支出总额
最小的空间进行布局,其理论主要从燃料和原料费用、劳动力费用以及集聚效益三个因子出发,认为企业是否相互靠近主要取决于集聚效益与集聚成本的对比,如果某一点上集聚效益引起的生产成本的降低超过了运费和劳动费的增加之和,更多的企业将会选择向该地点集中。
不过,产业集聚这一理论却是由Michael Porter于1990年正式提出来的。而产业集群是特定的产业集聚现象,Porter(1998)认为产业集群是指在一定区域,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结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根据空间经济学理论,产业空间布局实际上是两种作用力达到平衡时的结果。其中,导致产生集聚形成的向心力,是本地市场效应与价格指数效应共同作用所形成的集聚力;而导致扩散的离心力,则是市场竞争效应带来的分散力。
理论上讲,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劳动力或企业向某一区域集中,扩大了该区域市场规模和供给能力,以收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的企业将选择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作为生产区位,这是本地市场效应。反之,某一区域集中了很多企业,在本地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加,从外地输入的将减少,意味着该区域市场上产品价格相对较低,在相同的名义工资水平下,该区域的实际工资水平较高,使得该区域更具有吸引力,这是价格指数效应。市场竞争效应是企业由于过度集中导致彼此不利,因此不完全竞争性企业倾向于选择竞争者较少的区位。从作用力角度看,产业表现为集聚或扩散,主要是由这三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集聚效益主要是由于企业间的分工协作、共同使用公共设施、共同享受通讯信息以及更便于集中管理等方面而获得的效益[11]。目前,产业集群的指标主要是用来衡量在实际生活中的集聚程度和集聚效果。Williamson(1965)[12]的倒“U”型假说认为,集聚效益与集聚成熟间呈倒“U”关系,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与集聚发展阶段有关。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在承接国际制造业外包过程中,主要以加工业为主,并且许多工序相互联系,这些企业共同布局在同一地区,形成了地域上的产业集群。从产业结构看,长三角制造业是由一批进行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联系的中小企业共同形成的互补互动、竞争力较强的产业群落[13]。由于企业和地区限制,集聚程度不可能无限高,在该地区刚刚出现产业集聚时,各企业的发展不受限制,而且会随着其他企业的加入,产生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之后产业集群会由于竞争的抑制效应,而降低发展速度,甚至出现衰退。
制造业的发展同时受到集聚力和分散力的影响,集聚效益与集聚程度接近饱和水平相关,因此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的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也就是说任何集聚都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在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日益提高的今天,集聚程度更引起人们的重视,以防止过分集聚引发过多的环境问题。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空间集聚对长三角制造业发展具有非线性效应,在发展早期,集聚对集聚效益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当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集聚对于效益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弱,甚至会造成效益的下降。
(二)集群的生命周期与去集群化的动态演变
与生物群落一样,产业集群作为一个有机的产业群落,它的出现、增长和发展也是一个动态演变的过程。类似于自然界中生物种群增长表现出来的逻辑斯蒂曲线,产业集群的演化过程中,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的关系可能也呈“S”型。
Michael Porter(1998)在《集群与新竞争学》以及《竞争论》中,对产业集群的生长和演化做了简要分析,将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孕育、进化和衰退三个阶段,同时对产业集群的良性循环及其解体进行了阐述。Porter将产业集群衰亡的原因归结为两种因素:一是内生因素,如集群资源优势的丧失、集体思考模式以及内部创新机制的僵化等;二是外来因素,如技术上的间断性和消费者需求的转变等。
Ahokangas、Hyry and Rasanen(1999)提出了一个演化模型,认为一个典型的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应有三个阶段,即起源和出现阶段、增长和趋同阶段、成熟和调整阶段。在一个地区,最初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建立了一批快速增长的新企业,这些企业相互集聚,吸引其他企业不断进入该地区。而大量新企业的进驻,使得该区域吸引力不断增强,集聚作用加剧,逐步向集群发展,既包括生产同一产品企业的集聚,也包括纵向联系的企业以及相关机构的集聚。随着完善的基于价值链的集群分工网络的形成,产业集群进入了成熟期,企业间既竞争又合作,同时,产业集群内企业开始实施全球战略,在更多的国家销售产品,并获取原材料,集群开始加入全球价值链。但是,迅速增加的资源竞争将导致成本增加,以低成本作为企业竞争力越来越难以维持,出现集聚不经济,集群规模出现负增长,甚至导致集群的衰败。为了使集群持续下去,就需要适时的战略调整和再定位,比如调整结构、促进产业升级、鼓励并强化创新、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完善市场组织网络、对造假行为制裁等,促使集群进入快速增长的轨道,
并保持较强的竞争力和创新力。然而,并非任何一个产业集群都是可持续发展的,只有那些能够成功地进行战略调整的集群,才能始终保持较高活力。
从动力机制的角度[14]来看,最初,长三角制造业集群的形成,主要是得益于我国的对外开放和本地区位条件,包括生产要素价格、运输成本以及市场条件等因素,这些诱发因素随着制造业集群的成长而不断变化,具有不确定性和孤立性,相互作用关系不稳定。此后,在市场条件下,更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被吸引到长三角地区,与专业化相对应的规模经济和与多样化相对应的范围经济共同作用,形成一种复合经济效益,驱动力因素包括交易成本节约、规模报酬递增以及设施服务共享等。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由于地区内部和功能环境决定企业必须开展研发活动,企业间的人际接触和信息交换促进了本地区的创新行为,知识外溢、集体学习与内部竞争压力在本地区形成了创新网络,维持着长三角制造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推动产业集群持续发展。但是,由于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地价、劳动力成本上升,污染严重、人口拥挤等,集聚效益被削弱。由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长三角制造业群落出现了过度集聚现象,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来看,目前某些集群可能已经进入了成熟与调整阶段,增长动力不足,发展变缓。
四、数据说明、指标选定与统计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2002-2014年长三角两省一市分行业制造业数据,考察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时空变化特征。各产业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上海市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和《浙江省统计年鉴》。
按照最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11),制造业门类属于C类,包括13-43大类。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02)相比,修订之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被拆分成汽车制造业(C36)以及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C37)两个行业,为了统一口径,2012年之后将这两个行业进行了合并;同时橡胶制品业和塑料制品业被合并成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29),将2012年之前的数据进行加总。本文选择长三角两省一市具有代表性的22个产业作为研究样本,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因素,文中用到的工业总产值均用GDP平减指数进行了处理。
借鉴OECD制造业技术分类标准,本文的22个产业分为四类:
(1)资源依赖型产业:C13农副食品加工业、C22造纸和纸制品业、C28化学纤维制造业、C30非金属矿物制品业、C3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C3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低技术产业:C14食品制造业、C15饮料制造业、C16烟草制品业、C17纺织业、C18纺织服装和服饰业。
(3)中技术产业:C25石油加工及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C26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C29橡胶和塑料制品业、C33金属制品业、C34通用设备制造业、C35专用设备制造业、C36-C37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高技术产业:C27医药制造业、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C39计算机及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40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二)指标选定
1.集聚程度的测度指标
(1)赫芬达尔指数(HHI)是一种测量产业绝对集中度的综合指数[15],它是指一个行业中各市场竞争主体所占行业规模的平方和,用来计量行业的离散度。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Xij代表i地区j产业的规模,用X1j、X2j和X3j分别代表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j产业的从业人数以表示各自的产业规模;Xj代表整体的市场规模,用两省一市行业全部从业人数表示,即Xj=X1j+X2j+X3j,HHI越大,产业越集中。
(2)区位熵用来衡量某一产业的相对集中度,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集群识别方法[16],用一个区域特定产业的产值(或从业人员数)占该区域工业总产值(或从业人员数)的比重与全国该产业产值(或从业人员数)占工业总产值(或从业人员数)的比重之间的比值,区位熵大于1,则为专业化部门,区位熵越大,专业化水平越高。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j为长三角地区j产业从业人员数;N为长三角地区所有产业从业人员总数;Aj为全国j产业从业人员数;A为全国所有产业从业人员总数。
2.集聚效益的测度指标
(1)成本费用利润率是一个衡量集聚效益的指标,能够体现经营耗费所带来的经营成果[17],企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越高,其经济效益也越好,它是企业一定期间的利润总额与成本、费用总额的比率,表明每付出一元成本费用可获得多少利润,计算公式为:

成本费用一般指主营业务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三项期间费用(营业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
费用)。由于成本费用利润率反映企业正常营业活动的获利能力,因此这里的利润是指营业利润而非利润总额。但是直到2009年,才有关于各行业三项期间费用的完整统计,数据缺失严重。
(2)人均产值可以用来衡量经济效益,本文借鉴范剑勇(2006)[1]、孙浦阳(2013)[8]等人的处理方法,用各行业工业总产值除以从业人数,单位为万元/人。
(三)集聚程度分析
市场化改革以来,东部地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成为制造业的主要集聚区域,2004年该地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共96 410家,全国37.5%的制造业企业集中在该区域。自2005年开始,我国部分制造业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程度开始下降,截至2014年,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数占全国比重下降为26.20%,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此外,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也以2004年为拐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特征。
从行业构成来看,在制造业内部两省一市有较为明显的同构化特征,2014年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前10大制造业中有7个共同行业,但各行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还是有所区别,有比较优势、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不完全相同。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前10大制造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76.44%、70.43%和60.03%,制造业专业化程度依次下降,此外,资源密集型产业、低技术产业、中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比例分别为:6∶4∶60∶30、16∶7∶44∶33和13∶15∶50∶22,上海和江苏的计算机及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等现代产业比重较大,技术型产业优势明显,而传统的纺织业在浙江仍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关于2005年以前的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化,现有研究已经很多。表1是对长三角地区2005年和2014年22个行业集聚程度的测算,分别从从业人数占比、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熵三个方面共同刻画。
从表1可以看出,产业布局自2005年以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低技术产业从业人数占比从4.67%下降至3.57%,纺织业人数大幅下降,资源依赖型产业和中技术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各提高了20%左右,而高技术产业占比从3.51%上升至5.60%,提高了59.7%。2014年,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两大产业从业人数均超过长三角地区从业人员总数的2%,从事高技术产业的人员迅速增加。
2005-2014年9年间,在22个制造业中,只有烟草制品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两个产业赫芬达尔指数略微下降,其余产业的赫芬达尔指数上升,其中14个产业增幅超过10%,说明在长三角内部,产业布局呈现出更加集中的态势。2014年,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计算机及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等10个行业赫芬达尔指数超过0.45,从高度集聚行业的属性来看,一类是高技术产业,另一类是资源依赖型行业。
在22个制造业产业中有19个产业2005年的区位熵高于2014年,区位熵下降最严重的是饮料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纺织服装和服饰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这些行业属于低技术和中技术产业,而增幅较大的行业是仪器仪表制造业和化学纤维制造业,增幅各为22.12%和15.54%,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产业集聚程度出现下降趋势。2014年,有5个产业区位熵超过2.5,从高到低依次是:化学纤维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纺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表1 长三角地区20个制造业行业集聚程度
(四)集聚效益分析
2014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为6.45%,而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分别为7.34%、6.85%、5.75%。表2给出了分行业全国及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成本费用利润率的情况。
从表2中可以看出,四类产业中,成本费用利润率最高的产业集中在高技术产业和低技术产业,资源依赖型产业的成本费用利润率最低。在22个行业中,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成本费用利润率超过全国水平的行业数分别有8个、16个和8个,而比全国水平高出1个百分点的则各有4个、6个和3个;造纸及纸制品业、橡胶及塑料制品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这3个行业,两省一市的效益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上海市的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2014年严重亏损。这表明两省一市的部分制造业行业效益下滑严重,亟需进行产业升级改造。

表2 全国和长三角地区20个制造业行业成本费用利润率
五、模型构建与计量检验
(一)模型构建
为了进一步检验、分析制造业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的关系,需要构建计量模型。本文计量模型设定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解决内生性问题[18]:首先,可能遗漏了必要解释变量,导致解释变量与残差项相关;其次,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相互影响作用。系统GMM方法是一种能够自主引入工具变量而有效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因此很适合作为我们的解决方案[19]。在设定模型时,本文借鉴孙浦阳(2013)[8]在研究产业集聚与劳动生产率关系时构造的模型:

其中,Pdt和Pd,t-1表示t时期和t-1时期d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Ddt表示t时期d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Xdt为控制变量的列向量。
通过前面的分析认为,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的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倒“U”型关系,因此选择了人均产值的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考虑到影响产业地理分布的力量既存在集聚力又存在分散力,因此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之间可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的,因此本文构建了两个动态模型,进行对比研究:

其中,PGdt表示t年d产业的人均产值的增长率,PGd,t-1表示滞后一期的人均产值的增长率;LQdt表示t年d产业的区位熵;Xdt表示一系列其他影响被解释变量的控制变量;KP、FDI和PT分别反映人均固定资本、外商直接投资和基础设施三个控制变量;ε表示不可观察的产业固定效应;ϕ表示特定时间效应;ν表示随机误差项。具体变量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参照生物群落增长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逻辑斯蒂曲线,本文认为在“产业群落”的演化过程中,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的关系可能也呈“S”型,因此,本文探索集聚效益的增长与集聚的关系。本文用人均产值的增长率(PG)来表示集聚效益。
(2)滞后项。用以检验上期经济增长对本期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20]。经济增长存在惯性,若滞后项系数为正,则上期的高速增长会促进本期增长,经济可能处于扩张阶段;若滞后项为负,则经济可能已经发展成熟。
(3)关键解释变量。考虑到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以及转型升级,本文选择了区位熵(LQ)作为集聚程度的衡量指标,具体计算见公式(2)。此外,本文引入区位熵的平方项(LQ2)来检验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4)控制变量。①人均固定资本(KP):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人均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取决于人均资本,分析比较认为,固定资产投资能够改善产业生产环境,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为了探讨资本深化程度,本文采用人均固定资本代表资本投入水平,计算方法是固定资产净值/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再对其取对数。②外商直接投资(FDI):外商直接投资可以代表开放程度,它可以提高相关产业产值,同时通过技术溢出效应有利于深化产业分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效益,本文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比重来
衡量这一指标,处理过程中美元按照历年人民币汇率进行换算。③基础设施(PT):各省的信息化程度可以表示基础设施水平,它是用邮电业务总量/GDP计算得到,基础设施不仅能直接作为要素投入进入生产函数,还可以通过溢出效应间接促进经济效益增长。
(二)计量检验
本文所用数据为长三角地区2003-2014年的动态面板数据,散点图显示大多数产业的增长均可以用逻辑斯蒂曲线进行很好的拟合。为了解决模型估计面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系统GMM方法对长三角22个制造业集聚程度和集聚效益进行回归分析,这里所用的软件为stata12,可以得到表3的回归结果。

表3 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关系的系统GMM回归结果
由表3可知,Wald检验表明模型总体效果显著,AR(2)>0.05可知模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性,而Saragan检验显示了工具变量的选择也很恰当。模型(1)给出了运用系统GMM方法对制造业集聚程度与效益之间关系的计量结果,是线性模型,而在模型(2)中,本文引入了集聚程度的平方项,是非线性模型。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中,制造业集聚程度的影响系数为负,表明当前集聚程度对集聚效益的促进作用为负。分析认为,从区位熵来看,长三角制造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大部分产业目前已经实现了专业化生产,因此可能由于集聚程度过高,使得拥挤效应变得不容忽视。模型(2)中,区位熵及其二次项的影响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长三角制造业集聚程度与效益增长之间是“倒U”形关系,与假说1相吻合,最初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集聚效益增加越来越快,而当区位熵超过某个临界时,集聚效益增加越来越慢。这一结果证实了我们的猜想,即区位熵可能实际上直接影响的不是劳动生产率,而是其上升的快慢。长三角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近年来一直上升,而且仍有上升趋势,只是未来增长的空间变小了。
对于一阶滞后项的分析发现,滞后项的系数为负,而且在两个模型中均显著,说明上一期的集聚效益的增长不利于本期集聚效益的增长。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存在着惯性,在市场没有很大波动的情况下,上一期的高速发展一般会使得企业对本期也有很好的预期,从而加大投入,本期也会实现高速发展。但是这里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况,这是由于目前长三角制造业可能已经进入成熟期,因此集聚的作用几乎已经完全发挥出来了,集聚效益持续增长下去的动力不足,与本文的假设2相符。
最后,对于控制变量的参数估计,在两个模型中,人均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系数均为正,并且非线性模型中的系数大于线性模型,但是基础设施的系数却为负。人均资本对集聚效益的参数估计显著为正,说明长三角地区固定资产投资改善了产业生产环境,人均资本越高,越有利于集聚效益的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集聚效益的参数估计也是显著为正,外商投资越多,该地区制造业厂商能够便捷地获得所需资本补给和先进技术,提高相关产业产值,其经济效益必然更好。而对于基础设施,它的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期相反,但是,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集聚效益的增长,因此系数为负并不意味着长三角制造业集聚不再提高效益,而只是对效益的促进作用变弱了,也可以解释为由于信息化水平上升,长三角制造业企业与集群外企业的交往变得更加便利,可能会使集聚效益不再显著。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产业区位理论,通过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发现,在长三角制造业集群中,集聚程度与集聚效益增速之间呈现倒“U”型趋势。从本文的实证结果中,可以得出三个结论:第一,自2005年以来,我国部分制造业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转移,长三角地区产业区位熵有所下降,但内部产业布局更加集中,高技术产业尤其是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从业人员占比大幅增加;第二,长三角地区部分行业效益下滑严重,橡胶及塑料制品业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已经失去比较优势,集群可能已经处于生命周期的成熟与调整阶段,增长动力不足,发展变缓;第三,在长三角制造业集群演化中,最初随着集聚程度的提高,集聚效益增长越来越快,而当区位熵超过某个临界时,集聚效益增长变慢,而资本深化程度和开放程度均具
有正向效应。
以上研究结果证实了本文前面提出的猜想,也就是说,目前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结构并非最优,从集群产业链的思维角度来看,需要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和再定位。长三角产业集群可能已经进入了生命周期的成熟期,过度集聚、争夺原材料和市场等开始显现拥挤效应。从集聚效益动态演变的规律看,可以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以下两点建议:
(1)适当进行产业转移,协调东中西部发展。政府应当发挥其在集群经济圈演进中的积极作用,将新行业放在核心区,传统行业放在外围,核心区与外围协同合作,引导部分产业集群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期待在中西部地区形成新集群。产业基础雄厚、与国际市场更为接近的东部沿海地区,以产业高端化、现代化为目标,中西部地区继续发挥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比较优势。对于长三角地区的一些低技术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例如食品和饮料制造业、烟草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以及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近年来专业化一直在下降,经济效益也逐渐降低,说明这些产业已经失去活力,通过对外投资及园区合作等产能合作手段转移至其他地区可能更具优势。
(2)明确长三角的发展定位,促进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一方面,要牢牢抓住未来具有发展前景且同时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新技术、新产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战略性投资和布局,提升产业结构,主动“腾笼换鸟”;另一方面,要提高经济的效益和质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着力实施科技、产品、管理、商业模式的创新,实现扩大规模与提高效率的统一。积极推动长三角地区与外国的合作,引进、消化、吸收全球最近技术,加快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及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以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等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以高技术产业为核心的集群,做强做优先进制造业。
[1]范剑勇.市场一体化、地区专业化与产业集聚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2004(6):77-84.
[2]罗勇,曹丽莉.中国制造业集聚程度变动趋势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05(8):106-115.
[3]雷鹏.制造业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11(1):35-45.
[4]Antonio Ciccone.Agglomeration Effects in Europe and the USA[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2,46(2):213-227.
[5]杨扬,余壮雄,舒元.经济集聚与城市经济增长[J].当代经济科学,2010(5):113-118.
[6]徐盈之,彭欢欢,刘修岩.威廉姆森假说: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4):95-102.
[7]吴三忙,李善同.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时空演变特征分析:1980-2008[J].财经研究,2010(10):4-14.
[8]孙浦阳,韩帅,许启钦.产业集聚对劳动生产率的动态影响[J].世界经济,2013(3):33-53.
[9]陶永亮,李旭超,赵雪娇.中国经济发展进程、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J].经济问题探索,2014(7):1-7.
[10]Henderson V J.Marshall's Scale Economies[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3,53(1):1-28.
[11]Stuart S Rosenthal,William C.Strange.The Determinants of Agglomeration[J].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2001,50(2):191-229.
[12]Jeffrey G Williamson.Regional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National Development:A DescriPTion of the Patterns[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5,13(4):1-84.
[13]吴福象,刘志彪.城市化群落驱动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来自长三角16城市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J].2008(11):126-136.
[14]刘力,程华强.产业集群生命周期演化的动力机制研究[J].上海经济研究,2006(6):63-68.
[15]Cindy Fan C,Allen J Scott.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and Development:A Survey of Spatial Economic Issue in East Asia and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hinese Regions[J].Economic Geography,2003,79(3):295-319.
[16]徐谷波,董克,汪涛.创意产业集聚、技术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J].华东经济管理,2016(1):83-86.
[17]吴福象,沈浩平.成本费用利用率与地区产业结构升级[J].南京审计学院学报,2013(2):6-13.
[18]韩庆潇,查华超,杨晨.中国制造业集聚对创新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J].财经论丛,2015(4):3-10.
[19]Marius Brülhart,Nicole A Mathys.Sectoral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a panel of European regions[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2008,38(4):348-362.
[20]刘修岩,邵军,薛玉立.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中国地级城市数据的再检验[J].南开经济研究,2012(3):52-64.
[责任编辑:周业柱]
Life Cycle and Evolutionary Mechanism of Industrial Cluster—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Key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YRD under Opening Condition
WU Fu-xiang,YANG Jing
(School of Economic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93,China)
Under opening condition,enterprise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YRD)integrated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 the form of 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many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panies gathered together and gradually formed the industrial cluster.However,a new disintegration phenomenon occurred in recent years.This paper carries ou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cluster degree and cluster benefits of 22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the YRD,explores its stage in industrial cluster life cycle,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on the further development.This study shows the cluster degree of the YRD has been decreased since 2005.In the evolution of the YRD manufacturing cluster,the agglomeration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luster benefits at the beginning,but then the role of agglomeration decreased,at the same time,both capital deepening and openness have a positive effect.The manufacturing cluster in the YRD had been to the stage of maturity and reorientation,and its rapid growth may be running out of steam.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cal chain,proper strategic adjustment and reorientation are needed.
industrial cluster;life cycle;industrial evolution;cluster degree;cluster benefits
F263
A
1007-5097(2016)09-0001-08
2016-03-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A0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子课题“区域经济协调与城乡发展一体化”(2015gjxt)
吴福象(1966-),男,安徽安庆人,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区域和产业经济;杨婧(1993-),女,安徽蒙城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经济研究。
10.3969/j.issn.1007-5097.2016.09.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