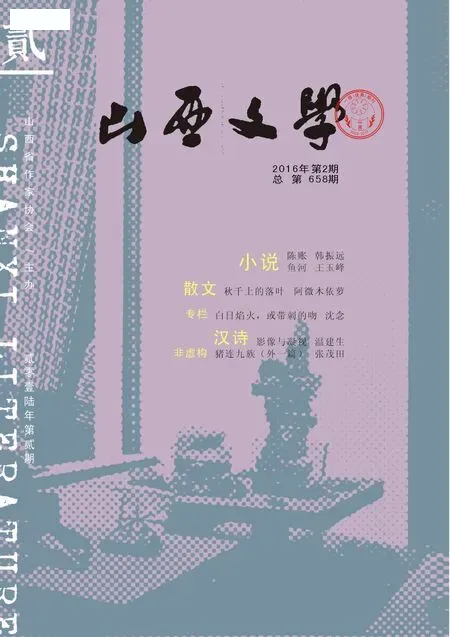闲 人
山 榭
闲 人
山 榭
林家富,这是一个很俗的名字,可见是平常人;可是,他却有不平常的一面,在出版大院,人们都叫他“林局长”;然而,他虽然有局长的面相、身段、派头,却没有经过组织部门任命。一言以蔽之,像个局长却不是局长。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话长了。
林家富的父亲是南下干部,是本省出版局的第一任局长。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局长。不过呢,说是出版局的局长,也不见得会出版。他父亲参加过淮海战役,被打断了腿,走路一瘸一瘸的。解放后,他的战友都被安排到党政机关或国营大中型企业等重要岗位,挑重担,扛大梁,因为考虑到他的腿伤,组织上为他找了一份相对轻松的工作,那就是搞出版。当年,他的老首长是这么对他说的:
“去管管白面书生,这是让你吃软工啊!”
初时,他是不想去的。他对领导说,他是一个革命者,革命者轻伤不下火线,把他弄去舞文弄墨,这是轻视他;况且,他闹革命前,也就是一个庄稼汉,胸无点墨,斗大的字不识一筐,叫他搞出版,那不是赶鸭子上架吗?不干不干,干不了!
但是,组织上没有理睬他,一纸任命,他不干也得干了。
林局长走马上任。不多久,经组织介绍、撮合,认识了一个南下服务团的女编辑,生了一个白胖儿子。这就是林家富。林局长倒也实诚,他说,我家祖祖辈辈是穷人,不图别的,就指望家里能富起来。
林家富在出版大院长大,打小受到方方面面的宠爱,自不在话下。不说林家富是恶少,至少是捣蛋鬼,用王朔的话表达,就叫“顽主”。读小学时,他潜进出版社,“偷”出长镜头,当望远镜玩。可是,当年这可是很值钱的家伙啊,出版社报了案,警察来侦察一番。小顽主吓出一身冷汗,把长镜头藏在食堂的大灶里。那时,还是柴灶,好在炊事员点火时发现了,否则,好端端的宝贝将付之一炬。他母亲气得中风,年纪不大就坐在轮椅上了。更不幸的是,他父亲在“文革”中自杀了。就是说,局长家道中衰。
林家富没有像他母亲一样有较高的学养,倒是遗传了他父亲的基因,大大咧咧,不会读书,也可以说是斗大的字只识八九筐。后任的出版局领导,是他父亲的老部下,他是革命后代,所以就把他安排到海浪出版社当校对。后来,弄了一张文凭,就改当编辑了。出版人生的孩子,干起出版,比非出版系统的人生的孩子,当然要有更多的优势。
可是,干出版,确实非林家富所爱。年轻时,他的理想是当歌舞厅的老板。但是,没有本钱,他只能委屈在这家出版社,为学生编编作文之类。每当他的编辑室主任把作文书稿给他,他总是这么嘀咕一句:“叫我编这破书,不厚道,黑社会。”
“不厚道,黑社会”,是他的口头禅,也不知道他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
毕竟革命家庭出身,好歹是局长的公子,大户人家的架势还是在的。林家富与“反潮流英雄”张铁生、黄帅等是同龄人,但他绝对不是“反潮流”一派,而是“赶潮流”的人,什么东西流行了,他准是在第一时间用这东西武装自己。这话说得抽象?且听我娓娓道来。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街头流行BP机。
就像早年人们拥有一辆自行车或时下人们拥有一辆小轿车便代表流行和时尚一样,那阵子,谁要有了BP机,显然,谁就是有钱人,是领导了时代潮流的人。这有一个证明,那时年轻人结婚,小伙子送姑娘金项链,姑娘往往送小伙子BP机,小伙子别在皮带上,这就像当年八路军首长腰间插着一支手枪一样神气。
这天已经过了八点半,编辑室各位开始伏案看稿,屋里静悄悄的。林家富姗姗来迟。平日,他也经常迟到,迟到自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所以,往往蹑手蹑脚地悄悄进来。
今天,他却不是这样。
他穿了一套灰色的西装,扎了红色领带,白衬衫外面有一件绿色毛衣。通常,毛衣没有塞进皮带里面,大家都知道,那样穿着太老土,是乡镇企业家的打扮。可今天,林家富也把毛衣塞进了皮带。在办公室门口,他两手插在牛仔裤口袋里,西装一扣不扣,还把衣服的两摆甩到双手的后面。他先“呃哼呃哼”两声,很神气地在门口站了五六秒钟,就像社长来查岗一样。可是,没人抬头看他一眼,大家正忙着哩。他只好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拿着茶杯到水壶那儿倒水,一边倒水,一边又“呃哼呃哼”几声,可着嗓门说:“水开啦?”年轻的女编辑程竑头也不抬地说:“你不是正在倒水吗?”那口气里的意思是,水要没开,你能有水喝吗?真是奇了怪了。林家富自己也觉得好笑,一边倒水,一边问水开了没有。他只能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编辑室又归于平静。
坐在位置上,林家富依然静不下心。他又把西装的右摆往后甩,低着头,手在BP机上摆弄,玩赏。哈,我有了宝贝了!他窃喜。哎,这上面怎么有个斑点呢?他立即解了皮带,连套带机,很隆重地将BP机脱下,是有一个小斑点,他用食指在舌头上沾了一点口水,然后使劲搓,还好,一搓就干净了。他把BP机再套进皮带,站起来,扎好皮带,把裤子往上提了提。坐下,喝了一口茶,又“呃哼呃哼”几声,除了他的“呃哼”外,编辑室还是一样死静。
他坐不住,站起来,西装两摆再往后甩,双手又插进口袋,他走到程竑桌前,肚子还稍有点前凸,笑道:“改稿呀?”程竑抬头看了他一眼,也笑着说:“是呀,发稿时间到了,来不及了。”又埋下头继续干活。他又以一样的身姿走到老编辑郑慧泉面前,亲切友好地说:“老郑,正忙哩。”老郑也礼貌地抬了抬头:“是啊,忙。”又接着工作了。他犹疑了一会儿,还是走到老大姐旷苗青前面:“大姐,在看什么稿呀?”大姐倒是站了起来,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用手拍拍右肩,扭了几下腰,不无发现地说:“哎呀,西装革履,像新郎一样,你今天要回娘家呀?”边说边去倒水。不过,这也没有引起大家更多的关注。
林家富多少有点失落,他扯了一段卫生纸,上厕所去了。在厕所里,他边玩赏BP机,边思考着什么,那神情,仿佛在考虑一个重大选题。
他回到编辑室门口时,眼前突然一亮,他看到电话机!那时候,一个编辑室还只有一台电话机,话机放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上。他情不自禁地拿起话筒,拨了一个号码,俄顷,他肚皮上的BP机怪叫起来。他扔下电话,西装两摆往后甩,双手插着裤袋,摆着方步进来了。
不约而同,BP机的声音让埋头干活的人们一律抬起了头,编辑们先是东张西望,接着看到林家富摆进来,大家都站起来了,你一言我一语:
“哇噻,家富有BP机了!”程竑的声调透着羡慕,折着腰看他皮带上的玩意儿,“来看看来看看。”
“嗨,这劳什子,有什么看头的。”林家富拿捏着漫不经心、满不在意的语调,仿佛在说她少见多怪。
“不得了,不得了,”郑慧泉和林家富保持一米左右的距离,“年轻人是能干,在外面发了财了?”
旷大姐也许比较节制,她多少是见过世面的:“BP机好是好,可是,你又不做生意,用得着吗?”
林家富觉得旷大姐的话有点酸:“怎么用不着,这不是有人呼我了吗?”说着,就把BP机取下,仔细瞅着,“什么事呀,还急着呼我。我要回电话了。”边说边朝电话机走去。
还是程竑泼辣,年轻人对新鲜玩意儿也特别感兴趣,她一把抢过BP机,左看右瞅,仔细研究。林家富“啧啧”道:“这破玩意儿,看什么看呀……”听得出来,声调中掩饰不住得意。
突然,程竑尖叫道:“咦,3630004,这不是我们办公室的电话吗?!”这下,郑老先生也不再矜持,他细长的身子上长着细长的脖子,像要吃草的鹅一样探出头:“我看看,我看看。”看罢,证实道,“3630004,对呀,还真是。你怎么自己呼自己呢?”旷大姐先是不作声地眯着眼怪笑,扯了一下林家富的耳朵,又用食指点了一下他的额头:“你这臭小子!”接着,大家哈哈大笑。
林家富用手拍拍自己的后脑勺,“嘿嘿”地傻笑着。
日新月异,高歌猛进,生活在日日进步着。不多久,“大哥大”诞生了。据说,“大哥大”也是有身份人的徽章。虽然与BP机时代一样,林家富不做生意,但还是在第一时间购得“大哥大”。
上下班时间,人们经常看他一手提着皮包一手抓着“大哥大”。人们永远搞不懂,他的皮包为什么就装不进他的“大哥大”?林家富在马路上一边走,一边提着“大哥大”叽里呱啦乱叫,神气活现,好像在指挥千军万马。
有一回,全局开大会(那时,局长还没有“大哥大”),会议召开前三五分钟,林家富提着他宝贝“大哥大”大喊大叫着什么,吸引了许许多多人的眼球。他那个神气啊,满脸通红,呈猪肝色,几近醉酒状态。正在兴头上,突然,他的“大哥大”响了起来。哇噻,这下是真有电话打进来了。换一句话说,此前,他是拿着“大哥大”表演啊!他自己似乎也吓了一跳,拿下“大哥大”,愣愣地,或是有点不解地看着它,仿佛看着怪物。乖乖,如何早不响晚不响,偏偏这时候响,够不配合的,很不给面子啊!足有五六秒钟,才醒悟过来,接了电话:“喂喂,谁呀!”
与当年的BP机一样,自然是一阵哄笑,传为佳话。
后来,苹果手机成为身份的象征时,他虽然根本不懂电脑,甚至不会打字,也第一时间显摆了,还是打着满不在乎的腔调说:“一个哥们送的。唉,这什么破玩意儿啊!”仿佛就要把苹果给扔了。
BP机之类,是表象的,只证明与“局长”的身份相吻合。实际上,出版大院对林家富人人以“局长”相称,还因为他真有局长的派头。初时,每一任新局长到岗,不是他父亲的战友,就是他父亲的部下,他总是座上宾。后来的,有的新局长与他并不相识,他呢,因为他父亲曾经是局长,凡局长自然都是他爹的门生,都是他的“铁哥”。仿佛亲朋故友一样,他上前勾肩搭背,拍着人家的肩膀叫“兄弟”,新局长张着漠然的眼睛,想发作,不明就里,又不便发作。然后,林家富来一句“你这人哈,不厚道,黑社会”。怎么“不厚道”?如何“黑社会”?新局长被搞得云里雾中。林家富敢和自己如此,想必是有来历、有来头的吧?很快,知道了他是老局长的儿子,新局长先是哑笑,仿佛自己被配合着演了一场滑稽戏。接着一想,好歹是老局长的儿子,而且这老局长还不是一般的老局长,是扛过枪、负过伤的革命前辈,这可不能怠慢。新局长也不晓得水有多深,于是,也就认了这个老革命的后代为“兄弟”。不过,为表调侃,也不知道从哪一任局长开始,敬称他为“林局长”,如此,他彻头彻尾地继承了他父亲的称谓,“林局长”这个桂冠也就永远地戴在头上了。
可能是遗传基因起了作用吧,“林局长”比局长还像局长。出版社开选题会,吃饭时,一般有一个主桌,出版局的局长或副局长来了,林家富是不请自来,都是端坐在主桌上的。有时候,主桌上的客人来得多,位置不够,副社长都得移位,他却全然不理不睬,比局长还更像局长。
主桌的酒一般会稍好一些,五粮液也是喝过的。他好酒,尤其好白酒。有一点是他的长处,他爱倒酒,自己斟了,也替别人满上。不过,有一个小秘密,一般人是不容易看出来的,一瓶白酒倒一半或一半不到时,他就把半瓶酒放在脚边,叫嚷着让服务员再开酒;再倒一半,又放脚边。如此,一场宴会下来,他会拎三四瓶剩下一半的白酒,弄回宿舍,后面怎么消受,就不得而知了。
桌面上如果有烟,他是先弄一包塞进口袋,另拿一包,逐个分烟,剩下的也放自己面前消受。
久而久之,海浪出版社的人都知道林家富的雕虫小技,有看他不顺眼的人,每每从另一桌到他脚边悄无声息地“偷”走那半瓶酒。一场夜宴下来,他全无所得,郁闷至极。
每天下班,他总是最后走,用立体袋(大信封,寄书稿用的,一个大约七八毛钱)装一袋仿佛书稿之类的东西,看上去,他每天带书稿回家加班哩。其实呢,是他到各办公室“偷”来的旧报纸、清样和样书。日积月累,靠这些,不是也可以卖些钱吗?
有一回,林家富所在的编辑室一部书稿丢了,翻箱倒柜,挖地三尺也找不到,那是一部不能用但要退还作者的书稿,找不到了,只好赔钱。
出版社的员工都住在职工宿舍,林家富的对门是校对科长。
一天,林家富的儿子忘了关水龙头就去上学,结果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万不得已,他把家里珍藏的旧报、清样全都清理到过道上,散了一地。校对科长下班回来,一眼就看到那部让出版社赔钱、到处没地方找的书稿。他苦笑,直摇头。心想,一个局长的儿子,一个看上去那么赶潮流的那么潇洒的人,“林局长”,你何至于如此,真是何至于如此!
这也不怪他,他爹早早死了,没有留下余荫;他母亲虽也是老革命,但瘫痪了,坐在轮椅上。他要维持体面,要当好“林局长”,容易吗?
虽然爹妈没有传给他官位,他母亲还真是帮了他不少忙。母亲瘫痪,但一个月一两万块钱的工资,全落入他袋中。因为是1949年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她母亲享受高干医保,而这成了他的摇钱树。
每周,林家富总会开溜半天,理由很堂皇,说是陪他母亲去看病,实际呢,他拿母亲的医保卡去开药。
初时,医生还会提醒他,乱开药是违规的呀,不好太张扬。渐渐地,医生与他形成了“神圣同盟”。可以说,他要开什么药,就开什么药,要开多少,就开多少。药开多了,医生或有提成?再后来,据林家富说,医生就是他的兄弟了。开药时,医生对他说:“开一单核磁共振?”他娘在家,连看病都没来,如何共振?他知道医生的意思,很是慷慨道:“开吧开吧,不就是核磁共振嘛!”医生开了,送给医生的一个亲友去共振了,钱呢,却算在林家富他老娘的革命账上。
从医院出来,他提着一大袋的药,这时,有几个熟人就跟上来了。一个六七十岁的糖尿病患者急巴巴道:“兄弟,今天有开糖尿病的药吗?”
“有,有。”林家富的语气中透着可以布施于人的优越感。
“几折给我啊?”老者问。通常,林家富以市面价格的五到七折,把这些药倒卖给他的老顾客。
“七折。”他牛逼哄哄道。
“兄弟,兄弟,老汉我一个月才一千多元的退休金,这你知道的,五折,如何?五折哈……”
“你真是麻烦,讲了多少遍了,一千多元,关我屁事!五折就五折!”很快,林家富与老者完成了交易,白花花的银子进了袋中。
他的药包里,还有消炎眼药水、肠道营养粉(美素)、片仔癀茵胆平肝、筋骨贴、皮炎平软膏之类的药。
在办公室,谁对他比较好了,或是他看谁比较顺眼了,他就会送一瓶消炎眼药水给人家,说:“嗨,你成天在电脑前工作,眼睛会难受的,滴一滴这眼药水,可以保护眼睛哈。”
或者,送膏药,说:“兄弟,这是我们的职业病,脖子难受了吧?要担心颈椎出问题啊,这膏药挺好,来贴贴,贴贴哈。”
至于肠道营养粉,那是要送给与他关系更好的人。比如,某人帮助他女儿辅导作业了,作为酬谢,他就送了营养粉。人家说:“我肠道没问题啊!”他说:“都能吃,都能吃,有益无害,有益无害哈。”无奈,只得收下。
他大多的药是寄回老家,给他在老家没有参加革命也无医保的七大姑八大姨。他寄药,通常是通过发行部,用公家的邮费。发行部主任有时不耐烦,怫然不悦,骂他老占公家的便宜,搞什么搞。他乖觉伶俐,讨好地媚笑道:“兄弟,兄弟,帮帮忙哈。”接着,掏出两盒茵胆平肝:“你应酬多,吃点茵胆平肝,保保肝,保保肝哈。”让人哭笑不得。
有几回,也不知道他是犯愁呢还是夸耀,说他老婆又和他老娘吵架了,没办法,就送他老娘去住院了:“反正单人病房,反正有保姆跟着,住就住呗,我还省心。”他嘀咕着。
这么多年,就这么下来了,他的开药盛举已经不是新闻了,大家都见怪不怪。他呢,也不以为有什么不妥。不是吗,前些日子,他还大大咧咧地炫耀说:“哈,今年才三个月,我已经开了三十几万了!”为了他的特权,他的脸上满是油腻的得瑟。
林家富是怎么当编辑的呢,书稿让他编,他不编则罢了,要编了,凡是他改过的地方都要严格审看,把对改成错是小意思了,比如,自己的“己”,他经常改成“已经”的“已”;可改可不改的,他是经常改的,比如“太阳从东边升起”,他要改成“东边升起了太阳”;最有趣的是,他经常会生造一些字,问他这是什么字呢,他也会说出什么字,但事实上并没有这个字,所以,他是海浪出版社唯一能造字的编辑,作用或正与仓颉同。
说起来,他还在出版史上留下痕迹哩。当年,他到上海组稿,因为他爹的人脉,竟组到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余秋雨的文章在《收获》上连载过。当然了,那时余秋雨还没有暴得大名。余秋雨的书稿,林家富看来看去,这不过是一部旅游图书嘛,于是拿起编辑的刀斧,大砍大删,砍成余秋雨说的,“在任何旅游景点都能兜售的旅游小册子”。当时,余秋雨在国外讲学,委托别人看清样。这一看不得了,立即叫停。如果这书任由著名编辑家林家富删削,这世上还有家喻户晓的余秋雨吗?还有《文化苦旅》这部畅销书吗?
他既是编辑,又上了中级职称,总得有点工作任务吧。时势造人,这可能是出版社管理史上的一大发明,他按照出版社的外编费规定,自己用钱请离退休的同志帮他编稿。就是说,他一边赚着体制内的种种好处,用体制内收入的一小部分,请了帮工。如果说,他爹当年是雇农,受雇于地主,参加了革命,林家富现在是大有长进了,他成了雇别人的人,而且雇的不是他爹那样的农民,而是高级知识分子。
实在无法让他当编辑,他只能吃空饷了,是个大闲人,天天坐在电脑前玩游戏。玩累了,就到相关编辑室串串门,看见谁的烟放在桌子上,讨一支抽了,还另取一支两支夹在耳朵上。如果这编辑室没人,他干脆把一包烟全揩油去了。如此,有人一见他来,惯性动作是把烟收起来。仿佛别人都是他的特供,他说:“烟呢,怎么都没烟?烟也不让抽,你这人不厚道,黑社会。”没有人应他一句,他叽咕着:“不厚道,黑社会……”悻悻走了。
新社长方向明来了以后,把闲人和捣乱的人做了调整,有的人出走了,有的人有了可以有所发挥的岗位,总之,各司其职,大家都相对忙了。可是呢,林家富局长还真是享受了局长待遇,反正他的活自己请外编给干了,似乎也不惹事,也有编辑室要他,方向明也没把他怎么样。当他上了五十岁时,外语、计算机享受免考待遇,中级职称也给聘了,工资加了几百元。好人谁不会做呢?方向明在“林局长”面前,也只能是一个老好人。
可是,人人都在忙,就他和另外一二人闲着。他似乎感到了环境的压力。到老同志那里闲聊?因为他有“小偷小摸”的恶习,大家都不怎么搭理他。于是,他经常到新来乍到的年轻人那里嘀咕:“唉,干吗搞得这么忙啊,海浪社这么点钱,有什么干头啊!”他还会准确无误地告诉年轻人,时代出版社年终奖金是十几二十万元云云。总之,海浪社不是人待的地方。他还说,“我是体制内的,要不然,早下海了!我要下海,哼,早就大款了!海浪社这么点钱,还不够我塞牙缝,还不够我下班后到酒馆里浪一浪,有什么干头啊!”说到“浪一浪”时,他语调特别加重,手做着起伏的动作,平时抠抠搜搜的,这会儿却做出够浪的样子。他对年轻人也格外关心,叫这个年轻人去考公务员,叫那个年轻人去考公务员:“海浪社有什么干头啊,赶快去考公务员,赶快去赶快去!”委实像个疼人的兄长。
方向明呢,全都看在眼里,但也很无奈。他心想,这样的人,如果撂到未庄,不就是阿Q先生吗?现在有幸没有成为阿Q,还真是新社会之功。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林家富成为编辑,成为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生动的体现。他这么煽阴风,点鬼火,实际上是他内心空虚甚至无助的表现,因为大家都在干活了,他不是被突出了吗?于是,最好多几个不干活的人,最好多几个捣乱的人,如此,会让他觉得不那么孤单,会有安全感,也是对林家富本人的一种保护。想到这,方向明感到释然,人人都要把日子进行下去,哪怕阿Q,哪怕林家富,也有生存权哈,宽容一点哈,不要太计较,哪个单位不养几个闲人?
方向明迎面走来,林家富堆起媚笑,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方社长,嘿嘿……”方向明正眼也不看他,仿佛没有看到这个人一样,面无表情地走了。林家富还是笑着嘀咕:“黑社会哈,方社长你不厚道,黑社会……”
山榭,原名房向东,1960年生,福建福州人。鲁迅研究专家,现任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社长。出版有《钓雪集》《鲁迅生前身后事》《鲁迅与胡适——立人与立宪》等。
责任编辑/陈克海 chenkehai1982@126.com
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