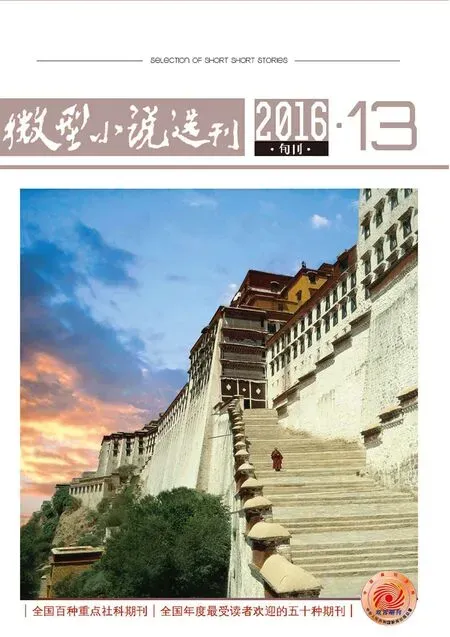春天的木鱼
□陈东亮
春天的木鱼
□陈东亮
那年春天,程子读高三时,妈妈跟人私奔了。
妈妈会唱歌,获过省歌咏比赛通俗唱法的银奖。多年来,风裹着妈妈的歌声,填满了这座小城的旮旮旯旯,这是程子的荣耀。妈妈走之前,在程子面前哭过,但程子当时以为,是风眯了妈妈的眼。程子没什么感觉,妈妈就走了。
爸爸砸烂了那个男人的家,开始灌醉自己,叽叽歪歪说着胡话。程子没去上学,头伸到裤裆里,努力低下,再低下。他倚在门口发呆。藏着寒气的春风,吹到程子心里。他抖着冰冷的脸,哆嗦着瘦削的身体。荣耀正被讥笑撕碎,四周的窃窃私语和指指点点,让他有种莫名的恐惧。蚀骨的疼,火一般在他胸中燃烧。程子把他牙齿咬得嘎嘣响,眼神正变得坚硬。他的眼睛里,似乎藏着把刀子。早春的太阳是冷的,和月亮没什么区别。程子搞来把匕首,对着空气捅来捅去。他的嘴巴也不闲着,嗯嗯啊啊的,发出些奇怪的声响。程子感觉,心里时而被什么东西塞得满满当当,时而又空空荡荡的。
爸爸把程子送到乡下老家,扔下部破手机,离开了。爸爸做着点小生意,总有忙不完的事儿。爷爷皱纹里融着笑,白发在春风中飞舞。他摸了摸程子的头,搓热了手,捂了捂程子的脸,又慢慢在程子身上拍了拍。接着,爷爷搓着手,在屋里转了几圈,又攥紧程子的手,摇了摇头,却什么都没说。
那几天,程子不出门,和院里的榆树、石榴树较上了劲儿。他扬起匕首,准确地扎在树上。一下,又一下。匕首耀着日光和月光,刺得眼痛。程子的心,却一直暗着。树上新疤摞着旧疤,春天的汁液从树上冒出来,像傻子或婴儿流着口水的嘴巴。那块旧磨刀石,在石榴树下埋着半个。夜晚,程子刺啦刺啦磨着匕首,耀眼的火星包围了他。漫天星光泻下来,和火星融在一起。爷爷什么也没说,只是过去摸了摸程子的头,给他递过去一条热毛巾。
毛巾温着程子冰冷的脸。这种热似乎链接了程子内心的热。他突然开始流泪了,仰着脖子对着月亮哭。接着,他弯腰闭眼,让泪水流淌下来。泪滴砸在地上,成了一个个黑乎乎的小泥坑。爷爷又递过来一条热毛巾。程子待在那儿,爷爷屋内屋外地跑,循环洗着毛巾递给他,仍然啥都没说。
后来,爸爸偶尔来个电话!程子觉得爸爸真可怜,只知道赚钱。但这么多年过去了,爸爸也没赚到什么钱。偶尔,他也给爸爸打个电话。可是,有天傍晚,刚吃完饭,爷爷忽然说:“给你妈打个电话吧。程子的心剧烈翻腾了下,接着冲到院子里。“妈妈”这个词儿,似乎已不能在他面前提起。他壁虎般抱着树,号啕大哭。他的脸贴在龟裂的树皮上,肩膀一抽一抽的。树上有什么东西,刺破了他的手。他把手指放到嘴里,咸咸的。
那天晚上,程子忽然听到咔咔的声响。
是记忆中的木鱼声。程子见过那个祖传木鱼—中间空,外面雕刻着好看的花纹。爷爷坐在屋门口,正慢慢敲着木鱼,咔,咔。木鱼声和程子的哭声,糅在一起,似乎像两个人,在小院里一起慢慢踱着步子。不知过了多久,四周都静下来。木鱼声停了,程子也停止了哭泣,走到爷爷跟前。爷爷脸上有明晃晃的泪光。
“爷爷,你怎么了?”程子问。
爷爷顿了下,说:“小子,我娘—你老奶奶瘫痪那些年,天天要听木鱼响。我就天天敲半夜。每天膀子酸得疼,又木又麻。我敲了好几年呀!那是爷爷的亲娘呐!”爷爷说得很慢,似乎在一字一顿地说。爷爷似乎还想说什么,但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月亮的清辉,洒在他们身上,程子忽然感觉心很疼。
接下来的日子里,爷爷天天敲木鱼,反复敲。他就反复听。
世界上最简单的声音,往往会救赎最复杂的心灵。
几年后,大学毕业后的程子,考上了公务员。多年后的今天,他已官至副县长。
而爷爷,在村西的坟地里睡着。
每年春天,程子总要抽时间,回老家看看爷爷。爷爷的土坟,是田野里的一株植物。春天的草香,在坟地四周弥漫着。总有喇叭花,或不知名的小花儿,爬上坟头,像极了爷爷的眼睛。程子点燃了火纸,接着在爷爷坟前跪下。
那一刻,木鱼声总会在空中响起。
(原载《飞天》2016年第5期甘肃赵剑云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