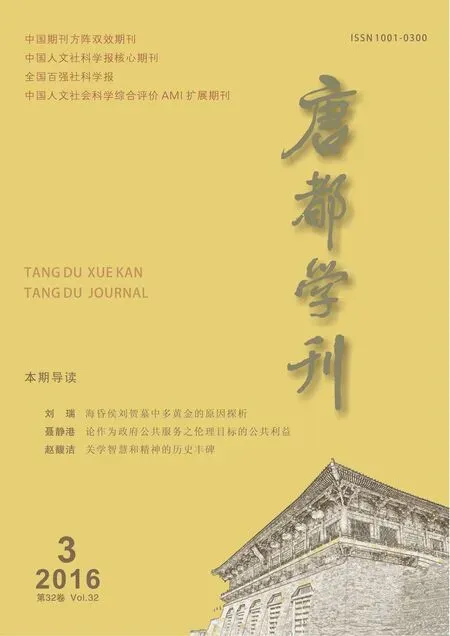大明宫研究的力作
——评杜文玉教授《大明宫研究》
黄寿成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大明宫研究的力作
——评杜文玉教授《大明宫研究》
黄寿成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西安 710119)
大明宫始建于贞观八年(634),最初名为永安宫,次年改名大明宫,龙朔二年(662)又改名为蓬莱宫,咸亨元年(670)更名曰含元宫,长安元年(701)又恢复为大明宫。大明宫与太极宫、兴庆宫又合称为唐代长安城的“三大内”,是李唐王朝最高统治者居住生活的场所,更被视为李唐王朝政治中心之所在,也是有唐一代皇帝行使权力并且居住时间最长的一组建筑群。虽然以往有些学者对大明宫中某些建筑有所研究,特别是主要从事考古工作的学者,对大明宫的考古发掘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可是学术界一直缺少一部对于大明宫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而杜文玉教授的《大明宫研究》这部三十八万多字的著述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
一

此书还详细论述了含元、宣政、紫宸三大殿,杜教授利用考古发掘报告《唐大明宫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资料,指出:“含元殿殿址东西长75.9米,南北宽49.3米,殿面阔11间,进深3间(59.2米×16米)翔鸾阁的台基东西约长24.5米,南北宽13米,栖凤阁大体相同。殿前与两阁之间,有平行的三条踏道,长达120米,中间的一条宽约25.5米,两边两条各宽4.5米”。书中说到其他两殿由于地层扰乱的缘由只能确定其位置,其中宣政殿遗址的其他情况不详。紫宸殿“殿基的西部早已破坏无存,仅东部还残存一部分。”“殿基南北宽近50米。”此书对大明宫三大殿研究的最出彩之处,就是对其功能的研究,不仅指出了它们分别是唐朝外朝、中朝、内朝朝会的举行之处,更重要的是对三朝朝会的内容以及相关礼仪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对三朝朝会的历史渊源的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有关麟德殿的研究学术界已有一些成果问世,但是都不如此书的论述全面详尽。此书不仅考述了麟德殿的台基、中殿、前殿、后殿的具体情况,指出“早期朝堂的建筑比较简单,只有一座大型庑殿和一道东西向的墙垣”。而“晚期的朝堂基址,是在早期的基址上重建的,但向东移了16米,并向北展宽4米。又在西端北侧向北新建了一排厩庑,南北长43米多(北端被路沟破坏了一部分),东西宽10.4米。”对于其功能的研究突破了娱乐性建筑的旧有认知,指出其除了娱乐、宴饮外,还具有外事、宗教、招见地方大员以及学士等方面的功能。
此书还利用正史、政书、类书等传世文献研究了延英殿、金銮殿、三清殿等重要宫殿的方位与功能,其中有不少方面都涉及唐朝的重要制度,如延英召对制度、学士院制度等。对设在大明宫内的中书省、集贤院、门下省、弘文馆、史馆等机构的方位与职能,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研究结论。在研究中不仅仅重视正史、政书等典籍,甚至还充分地利用了笔记小说,如使用《剧谈录》的资料,考知望仙门距离左神策军驻地不远。利用《教坊记》的记载,指出:“(教坊)显然是指教习之所,且不限于伎乐一端,后始专教伎乐,此制实起于隋代”。
杜教授还绘制了大明宫图,编制了《大明宫丹凤门举行大赦典礼表》《麟德殿召见外来使者表》,以方便读者阅读,是一部是研究唐代大明宫相当完备的著述,而论述详备则是此书的一个显著特点。
二
这部论著的另一个特点就是纠正讹误。杜教授对于宋敏求、胡三省、徐松等宋代以来学者所撰写《长安志》《资治通鉴注》《唐两京城坊考》等著述中脱漏的一些宫内建筑的地理方位和功能进行了考证,根据欧阳修《新五代史》、马端临《文献通考》、叶梦得《石林燕语》、骆天骧《类编长安志》,指出:“胡三省注曰:‘唐东内以含元殿为正牙,西内以太极殿为正牙。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牙,与衙同’。其实是不对的,在唐代含元殿是正殿,而正衙则是指宣政殿,也称前殿”。“大明宫中所谓正衙是指宣政殿,而不是含元殿。”又运用《旧唐书》《新唐书》等正史的记载,指出:“胡三省注云:‘金吾左、右仗,在宣政殿前’。胡三省的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对,皇帝在宣政殿坐朝时,金吾仗排列在宣政殿前,这是没有问题的,但这里显然不是指朝会时的仗卫,而是指左、右金吾仗舍(院),因为这里才是临时关押罪犯的场所。左、右金吾仗舍位于含元殿前,左、右朝堂之南,文宗时发生的所谓‘甘露之变’,所说的夜降甘露的石榴树就在其仗舍院内。”还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及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等文献资料,指出清人徐松所绘制的《大明宫图》东内苑的范围有明显错误,并究其缘由,认为程大昌的《雍录》说:“其(大明宫)广袤亦及五里。五里之东,尚有余地,可以为苑。故大明东面有东内苑。……此之内东苑者,包大明宫之东面,而向南直出,与大明宫城之丹凤门相齐。……此苑之北亦抵禁苑也”的记载比较可靠。还认为徐松“待诏院在史馆西”的说法,与其书所附的《西京大明宫图》不相合,是徐书的讹误之所在。
书中还对于传世文献中涉及大明宫的记载不太准确之处加以考辩,如“关于金銮殿在大明宫中的功能,宋人沈括有所论述,他说:‘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应供奉之人,自学士已下,工伎群官司隶籍其间者,皆称翰林,如今之翰林医官、翰林待诏之类是也’。对于沈括的这种说法,程大昌批评说:‘沈氏又曰: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玉堂、承明、金銮殿皆在其间。此又失也,承明、玉堂皆汉殿耳,唐无此名也’。程大昌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唐大明宫中确无此二殿。沈括说唐翰林院乃皇帝燕居之所,实际上是说翰林院是供皇帝消遣娱乐的场所,这种说法指唐前期的情况是不错的,如果指唐后期的情况则失之偏颇了。”又如关于待制院的用途,书中利用《新唐书·百官志》《册府元龟·帝王部》《唐会要·待制官》等文献资料,指出徐松所说的“唐初,仿汉立待诏。后以武后讳,改诏为制,每御正衙日,令诸司长官二人奏本司事,谓之待制。贞元间,又令未为长官而预常参者亦每日引见,谓之巡对,亦谓之次对”。也是不全面的,他指出“其实皇帝在延英殿召见待制官并不限于正衙朝会后,其在延英召对日,与宰相议政结束后,亦召见待制官”。这一切均体现了杜教授考证精细之治学特点。
另外,书中还指出今人杨鸿勋《大明宫》一书附有《唐长安大明宫复原平面图》,将殿中省绘在御史台之西,把御史台绘在中书省西面,与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大明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一《大明宫》的记载全然不符。
在纠正前人及今人讹误的同时,对于今人的研究成果也广泛利用,如利用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大明宫西夹城与翰林学士院诸问题》一文,“以右银台门内北边10余米处的房屋遗址作为翰林院和学术院还是差相仿佛的,但仍略嫌偏南,距麟德殿稍远,而此‘所谓翰林院遗址的北边200余米’残存的南北向夯土墙则更接近于文献记载中翰林院和学术院的位置”,认为“此说甚是”。纠正了马得志认为学士院遗址在西夹城内的错误观点,认为西夹城内应是右藏库之所在。在这部著作中杜教授既指出前人以及今人著述中的不足,又能充分利用古今学者的一些研究的正确结论,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也是难能可贵的。
三
这部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即博采众家之长。有关延英殿位于大明宫的什么位置,文献记载不一致,宋人宋敏求《长安志》认为在紫宸殿的东面;唐人《唐六典·工部尚书》、宋人程大昌《雍录·延英殿》、清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均认为在紫宸殿的西面。书中指出:“傅熹年所绘的大明宫平面图,将延英殿绘在紫宸殿的西面,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绘有两幅《唐大明宫图》(考古、文献各一幅),均将延英殿绘在宣政殿之西,紫宸殿西偏南的位置。傅、史两位当代学者所绘虽稍有不同,但基本方向都是不错的。”又进一步指出,“有学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这两次发掘的结果,判断延英殿的具体位置应在紫宸殿西南约50米处。可供一说。”另外,在指出徐松《唐两京城坊考》所附《唐大明宫图》所绘的东内苑范围有明显错误的同时,又利用此图确定了太和门的位置,指出此图“亦绘有太和门的位置,却与日营门东西相齐,明显偏于东内苑之南。程大昌说其位置在‘苑之南’,而太和门在吕大防图上的位置却在东内苑中部,故徐松之图的标绘更为准确一些”。
此书考述谨严,如右银台门考古实测仅有一个门道,但是据文献记载,应有三个门道,杜教授则采取谨慎的治学态度,说“既如此,为何考古简报却说只有一道门,是史籍记载不实,还是因为右银台门遗址破坏严重,仅残留下来了一个门道,目前尚无法判断”。可称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绝不盲目猜测。
总的来说,杜文玉教授《大明宫研究》一书,搜集资料广泛,可谓一览无遗,既有传世文献,又有考古资料,论证详细,考辨严谨,逻辑性强,博采众家之长。不过书中也有一点小小的不足,即全书缺少一幅唐代长安城的全图。这可能是杜教授认为在这部研究大明宫著述中那幅图可有可无,不过作为读者特别是一些非唐史专业的学者在阅读这部三十多万字的大作之时,如果能够看到唐代长安城的全图,就可以对于大明宫在长安城中的具体位置有了清晰的了解,这样就更有利于读者阅读,进而理解大明宫在唐代长安城中的重要地位。
[责任编辑 朱伟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