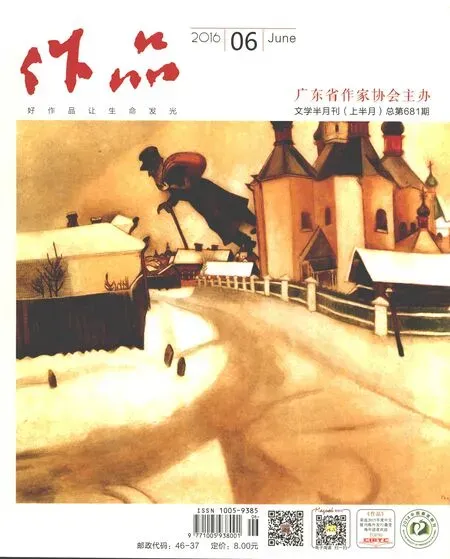王闷闷作品互动短评
王闷闷作品互动短评
〉〉向茗(1993年11月生于江苏宿迁,现就读于江西井冈山大学艺术学院。诗歌散见《四川文学》《诗歌月刊》《飞天》《江南诗》《星星》《中国诗歌》《作品》《青春》等文学期刊。参加2015年第八届“星星诗歌”夏令营,2015年中国诗歌“新发现”夏令营。)
本篇小说讲的是张二光看病就医的一个漫长过程,剧情跌宕起伏,表现复杂的矛盾冲突,叙述故事的发生、发展、高潮和结局,在情节的发展中展现人物性格的变化,反转有序的将一个农村乡土的生活现象呈现给大众,作者对人物的外貌、对话、行动和心理等描写深入人心,通过典型的人物形象、典型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完整的故事情节的具体描写,反映出中国农村变革后的现实生活!
〉〉宋林峰(青年作者,山西高平人。小说及评论见《山东文学》《延河·绿色文学》《西湖》《作品》《辽河》《咸阳日报》等。现居咸阳。)
看的什么病?实际上到最后他的病都没有确诊。可是在这看病的途中,人世冷暖、社会丑恶尽收眼底,张二光如同一个摄像头,不断切换角度带领读者看“病”,瘤,这个现实社会的“瘤”还少吗?引人深思。
〉〉焦琦策(生于1990年。小说见《都市》《牡丹》《朔风》《渠江文艺》。)
一个头疼病从村里的赤脚医生看到县医院,再看到市医院,最后到省医院,这个病还是没看上,在病情恶化残余的生命中,在激烈的爆竹声中,听到的却是恶霸张常五上任村长的“喜事”。小说以主人翁张二光的看病历程为线索,简洁而直白地勾勒出一副乡村琐事动态图。在图中,人物丰满鲜活,看似在写别人,却是在写每一个人。它截取一个横断面,一个时间段,却映射出整个中国乡村变革给人们带来的巨大震动。小说是乡土的,是完整的,更是现实的。
〉〉邓可君(1993年生于四川简阳,主要写诗,兼及小说、评论,作品散见于《星星》、《山东诗人》、《中国2014年度诗歌精选》、《世界华文媒体》等。)
《张二光看病》 是一篇具有颗粒感的人物故事。
在经历过大众教育的青年人眼中,鲁迅、沈从文、高晓声的作品或多或少的代表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标准,也无时无刻不传递着一些经典的审美意识和写作自觉。正如我在张二光身上所见到的。
人生往往比牌局来得认真,在去城里看病的旅途中,你看到了张二光的觉醒,也看到了不可逆转的悲哀。最后你发现,那些来路和去路上的人实在不断提醒你,应该勇敢的治好眼睛,哪怕资源紧缺。
〉〉孟甲龙(1993年出生,甘肃会宁人,就读于兰州财经大学,2015年度中国·大别山“十佳诗人”,诗歌多刊于 《读者》《散文中国》 《当代作家》《诗意人生》《海外诗人》等,出版诗集《秦淮河女人》。)
于私,我很喜欢乡土作品,于公来说,故事浓烈悲悯,通过看病这一线索揭示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社会现象。作者细腻的描写对人物性格刻画非常到位,好似身临其境。张二光看病无果,以小见大,反映了社会存在的真实现状,即便主人公后来有了觉醒,可回天乏力,疼痛悲哀。
〉〉顾彼曦(青年作者,作品见于《诗刊》《星星》《美文》《延河》《诗选刊》《诗歌月刊》等刊物。)
乡土小说最难的莫过于形象塑造和乡土语言。作者对细节描写有一定的功底,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立场与对农村事物独到的见解。那些农村人的难言之情和无奈之举。作者可能也深处这样的环境,并为之长期悲痛不已,所以才选择通过小说这种题材来反映讽刺。使得小说有了故事,更有了担当与思想。
〉〉蔡其新(1995年7月生,广东廉江人,现就读于广东警官学院。2011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兼习文学批评。)
作者使用乡土味道浓重的语言描写,契合农村事物的气质,具有笨拙的气质,也较注重细节描写。张二光作为中国农村底层传统农民的代表,具有十分可笑的生存处境,堪忧的健康问题,没有生存的保障,城市对医疗资源的垄断、国家和政府无法调控这种天然的城乡差距,这也是矛盾所在,作者从矛盾的根源出发去探寻人的存在意义。作者作为旁观者,通过“张二光看病”这一事件对中国农村社会现状进行观察和透视,笔触紧紧地跟随老人就医的心路历程,将存在的普遍性现象——农民无法得到公平公正的医疗待遇,通常会因为疾病陷入死亡的绝路诸如此类的悲剧以“小事件见大社会”的方式进行揭示,小说同时揭示底层社会的某种黑暗但没有提出调和矛盾的方案,直至主人公悲剧的结局,主人公最后的觉醒——选择安然面对死亡的态度。
〉〉牛冲(1991年生,河南周口人,毕业于郑州大学。有小说诗歌见于《中国诗歌》《延河》《飞天》《牡丹》《海峡诗人》等,系2014年《中国诗歌》夏令营学员,曾获第四届周口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创办有元诗歌基金会。)
文章朴实,真诚,用比较平缓的叙述方式描述一个农村老头的看病历程,用旁观性的事件暗示张二光老人的心理过程,纠结,无奈,担心,怀疑,看病的每一个过程都是生活中的再现场景,让人触手可及。农村赤脚医生的朴实,县城医生的状态再到省城医院的现状都是这个国家的真实缩影,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细节描写非常到位,让整篇文章看起来十分饱满。
〉〉王磊(1990年生,陕西府谷人。诗歌散见于《延河》《诗歌月刊》《中国诗歌》《扬子江诗刊》《海峡诗人》《星星·散文诗》等百余家刊物。有作品入选《中国当代短诗选》《陕西青年诗歌选》《2013年中国诗歌排行榜》《2014年陕西文学年选》等多种选本。已出版诗集《鸟日子与诗生活》《多余的悲伤》,主编《陕西90后诗歌选之十二生肖》合集。)
这是一篇语言朴实,构思巧妙的乡土题材小说。整篇小说从老农民二光感觉自己得了坏毛病为轴展开叙述,情节的推进也似乎在我们预料之中,甚至我觉着一些人物对话太过琐碎,还有在旅馆“偶遇”张连喜婆姨的那段和火车再“偶遇”铁栓都是刻意为之,但是当我读到最后二光眼睛一点点黑下去时才觉着前者安排得如此巧妙。作者正是用琐碎的对话,心里起伏变化,看似刻意的安排等等在为我们构建一场无药可治的“大病”,以窥一斑见全豹的方式放大着一些尖锐的社会矛盾,虽然不一定鲜血淋漓,却足以像一块大石压在胸口让我们喘不上气,很沉重!
〉〉胡游(90后,湖南省作协会员,毛泽东文学院十四期作家班学员,湖南第一师范学生。获2015年《西北军事文学》优秀作品奖,2015年凤凰诗社子云诗歌奖等,在《诗刊》《中国诗歌》《作品》《参花》《山东诗人》《创作》等发表诗歌和小说。有散文和诗歌入选本。)
作者凭着对真理和正义的热情来写作,对小说人物绝不偏见的热情,无论是美或丑,是喜剧,是悲剧。作者在小说里是隐藏起来的,进而把“张二光”摆了出来,成就“第二个自我”。作者没有以传统小说抛头露面的方式,简单创作。而是小心翼翼介入精巧、复杂和隐蔽。通过“张二光”,诱导读者产生当下农村巨大变革的临近感。同时,小说受到先锋文学的影响,还剔除了不道德的叙述有力的花言巧语,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零度写作”。从某种方面来说,《张二光看病》是每个农村人,都在进行的一种历史活动,这种活动,像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遇到熟人,遇到不公。然后,作者写主人公会有的一些意识,一些心理活动,填补时空背景。不知不觉,作者的影子就浮上来了,跟读者有了进一步的交流,把世俗的人情冷暖倾倒一番,最后不动声色地迅速撤离,只留下“活”和“不活”。
〉〉丁林(90后,一只走路看书的生物狗。)
90后的作者把一个60后的倔强直率的小老头写得惟妙惟肖。文章从张二光的角度写,却一点也不显得突兀,看不到这个形象不该有的''影子'',让人在推敲时不禁认同:嗯,这是这样的人可能会做的事。刚开始读的时候觉得张连喜婆姨的片段颇有些多余,尔后才发觉是丰满人物形象的同时透露出一点村里男人无能的状况,为下文村子里的故事做铺垫。张二光看病一路看到省城无果回村,一定程度上影射了张铁栓和村子的未来:村子得了张常五这个“瘤子”,跑到省城去也没法解决,甚至张铁栓回不来了。而张二光不治病,就跟村里人不抗争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怎么活呀”。作者从一个小老头的故事影射到一个村子,再用一个村子的故事讲述了一个社会现状。不过有两个地方,个人认为或许能稍作改进:第一个是,张二光怕床压坏是透露出他的节俭甚至可能是抠门,而且从''拍土''的片段也看得出是一个性格耿直的人。那么这样一个人,在被告知打车要20元实际上却花了40元时会不会真的忍气吞声呢?第二个是,村子的问题是中途插入的,虽然没有什么突兀之处,但文章前面做些铺垫和暗示或许能有更多提升,比如孩子叫张二光去盖章的部分,就是一个展示村子状况和二光性格的机会。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