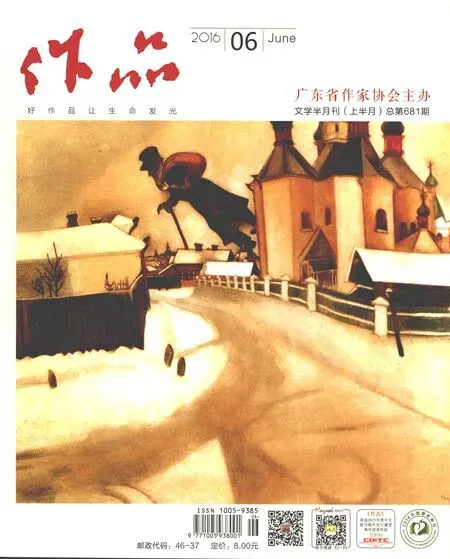张二光看病
文/王闷闷
张二光看病
文/王闷闷
王闷闷男,真名王震,1993年出生于陕西子洲县,陕西省作协会员,中短篇小说散见于《延河》、 《延安文学》、《伊犁河》等刊物,出版长篇小说《咸的人》、 《米粒》,即将有新长篇出版,现居西安。
其实刚开始拿到投稿的二十多篇作品的时候,我并没有多看好《张二光看病》。首先是因为不太喜欢这个题目,其次是不喜欢泛滥的乡土题材。但是当我真正走入这个文本的时候,我发现它带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一些读城市小说、青春小说根本不会产生的感觉。仿佛就是要告诉我,这才是祖祖辈辈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先人们。不过我也在怀疑我的这种感受,出自于我与作者地域上的联系,但是愈发深入的阅读,却又让我挖掘出了不少的震撼。作者用一个琐碎的看病故事,并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看病难”这样的现实问题,而是让一种宏大的生存问题投射在现实当中。在大时代中,每一个平凡的人,“活”还是“不活”,到底“怎么活”,才是这篇小说让我们真正值得思考的内核。但愿每一个看完这篇小说的读者,都能跟我一样,给自己的心“看了一次病”。但愿我们的心“看病”,不会万分艰难,不会无药可救。
——祁十木
1
张二光在村里受了大半辈子苦,临了临了,不争气的身体还是出了问题。每顿吃少半碗饭,就这,还得老伴劝说念叨半天,和乖哄小娃一样,他忍受不住,才强扎挣吃的。常说头疼,娃们让他去医院看,他只是到村里的赤脚医生处瞧,赤脚医生猜测说是感冒或着凉了,卖他几包感冒药或头痛药,走时,他要求再拿几粒止疼片。
以往的止疼片是用不上,最近却把原先积攒下来没吃的都快吃完了,就这,非但不顶事还越发疼得厉害了。他想,咦,这他娘的是咋了,不是得什么不治之症了吧。想到死,死,他也不怕,都五十五六的人了,娃娃们一个个都是好的,没什么撂不下。本来连赤脚医生那也不想去,估计就是那老问题,可前几天儿子回来走了一趟,他觉得不行,得活着。就算是不怕死,那也并不代表想死啊,能活还是活着好么。
2
儿子回来,是一张表上需盖个村上的章,说是单位上要弄个证明,他在路上就给家里打电话,老伴接的:“喂,儿啊,回来了?”对面说:“喂,妈,还没回来,在路上了,你让我爸接下电话。”老伴放下电话,喊院子里正坐着吃烟的他:“老汉子,快回来,娃娃要你接电话了。”他不想回去,就是站起这一下他都难受,脑袋里有许多的无头苍蝇在乱窜,最终定会乱成一团,成为天旋地转的睁眼瞎。
家里的老伴见外面没动静,很是生气和焦急地走出来:“老汉子,你聋了还是断气了,娃娃等着呢,快回来接电话。”他没办法,只好站起身,做好忍受晕阙及黑暗的准备,唉,却没有,白准备了,边往回走嘴里边嘟囔:“有个什么事了,还非要我接。”
他接起电话:“喂,成娃,咋了?”对面说:“爸,你先到村长那里,看章子在不。”他说:“好,老子不死,就伺候你孙子。”把电话扔给老伴,出去了。一会,老伴也到院里来了,对着桩子上坐着的他说:“娃娃让你接个电话,看你那样子,害得娃娃最后还担心地问我,你怎么了,是不是不想去。”他愈发的干脆利落,说:“那有个什么,我说能行,还要再说什么,婆婆妈妈是你们婆姨女子家的作风。”今年这个夏天热得怪异,挣上命的热,成天晴得蓝瓦瓦,旱云疙瘩漫天飘浮着,就夜里能凉快点,让人和庄稼歇缓歇缓。
老伴说:“娃娃就用你这么个,就把你能的。娃娃现在有你这么个老子了,没有的肯定不叫。”他不耐烦地说:“那你也能去了,你又不是没长手没长腿。”老伴几近愤怒,要破口大骂:“我和你能一样?怎么说你也是男人了,是这个家的主事者,是娃娃们的依靠,你不是没见过那没老子的娃娃,走到哪都感觉抬不起头,走不到人前。”就是这话把他触动了,下了决心:不能死,要活着。不说为自己,也得为娃娃活着。第二天一大早,他就睡不住了,种地那会早上是想多睡会,自地被整走,按理说这下好了,想睡到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可现在那些想多睡会的渴望都张了翅膀,飞了。早早醒来,眼睁得老大,盯着窑顶,外面有了动静,不看都晓得,是从地里传来的。不睡了,起,到赤脚医生那里。
3
赤脚医生是外面来的,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老医生,准确说,是中西结合的产物,非要较真,那还是中医比较擅长。租赁了公路边上的一孔窑洞,成了村里的医院。别说,平时的些小病痛,老医生可谓是手到病除,简单几粒药或打几针,再不行打几瓶点滴,保准欢蹦乱跳。中药能治疗些时间较长的顽疾。他六点走出家门,先在公路边上溜达,平展展的川地被挖掘得丑陋不堪,看着就心疼。经营多年的几亩地,几万块钱就给买断了。不在钱多少,主要是靠这谋生吃饭过日子了。如今几万块钱能做个什么,两三年就花完了,然后呢?好多人说这里将建一个工厂,没具体说什么工厂。只说等修建起来,在周边随便做个什么,都比种地强。种地能挣几个钱,现在谁还靠种地过日子。
他手背抄着,边慢悠悠地走着边想,地里尽是大机器,有挖掘机、推土机、铲土机、大卡车、压路机……挖掘起的土,湿润得很,摔在一边,等待新一天的暴晒。他看到的,被挖掘的不是地,是祖坟,于是,恨得牙齿咬得咯嘣嘣价响,却没有丝毫办法。多看一眼就多一分悲伤。他倒想眼不见心不烦,他毕竟不是瞎子。再一个办法就是离开这里,可又能去哪里?根在这里了,全是他娘的胡扯淡。
八点左右,诊所门开了。他进去还没说话,老医生就说:“又头疼了?我看你还是到大医院瞧瞧,看到底是怎么了。”他如实说:“我最近的疼和原来的不一样,疼得很厉害,有时眼睛都麻麻糊糊。”老医生吃惊地看他,让他坐下,给仔细瞧瞧。拿手电照眼睛,拿镊子在口腔里敲打,拿听诊器听心脏,号脉……使出了浑身解数,最后得出结论:“二光啊,为了保险起见,我看你还是去大医院,最好做个头部的CT,我这条件有限,吃不准你是什么病。按我的推断,估计你脑袋里面长了东西,眼睛麻糊,是那东西在触动妨碍到你视网膜弄的。”这话把他说的太痛了,看来真的是严重了。不晓得是不是人们常说的瘤子,他站起来,强作欢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那你说是不是瘤子?”老医生担忧且紧张地说:“不好说,得去医院检查了再说。”他问这个,是想确定严重与否,瘤子的话,有良性和恶性之分,良性的,做了手术,一般可以活多则几十年少则十几年;恶性的,即使做了手术,也是霜打的茄子,秋后的蚂蚱,活三两年就到头了。他拿上药,从诊所走出来,阳光那个刺眼,真不是肉眼能触及的。低头的一瞬间他想到了什么,折回去又和老医生说了几句。
到大医院,去不去?他纠结,去的话肯定会惊动家里人,会一发不可收拾。纵然撒谎,去医院,那肯定是有病了,自然就会引发一连串的疑问,什么病,检查得怎么样,严重不严重等等之类的问题。公路上是黄尘漫天,一辆辆大卡车拉着从地里挖出的土,到公路上有一个大转弯,车身一横,抖落下许多溢出的土,被过来过去的车一碾压,有的被粘在轮胎上带走,周边百米的公路尽是土。呛得他,咔咔咔直咳嗽,好在土味是美妙的,他喜欢闻,闻不够。不时会在公路边站住,让疯狂忙碌的汽车过去,他再继续走,手依旧背操着,像是乡村里的一位哲人,正在沉思生与死、天地宇宙万物间重大深奥且艰涩难懂的哲理性问题。
4
一辈子没大的爱好,特别钟情于打麻将。一有空就上阵,来几把。村里什么都缺,就不缺人。老的年轻的都有。原先还偶尔会出现人少的情况,包括凑一桌麻将都费劲。自打听说要在村里修建工厂,人就迅猛地密集起来,成了质量上乘的布料。整天聚在村里,用打牌、喝酒、闲聊来打发时间。还没整地就这等死的样子,整完地后,就更是化为灰烬了。来场麻将,招呼几个人不就几秒的事情,容易得和吃面条一样。在窑里,四个人围坐着桌子,麻将咣当咣当咣当摔打在桌子上。随着一声“胡了”,他高兴地把牌推倒,见大家是大眼瞪小眼,他补充说:“胡七万。”大家的表情依然不明朗,他随即看一眼推倒的麻将,胡的那张牌怎么不是七万,而是三万了,怎么可能,是看错了?不应该,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他红了脸膛,大家都胡乱的把牌推倒,说没事,就当这把和了,没输没赢。接下来又发生了几次这样的事情,他的头开始痛裂,不能再玩了。没到五点,就散了场,通常能玩到七点多,散场回家也是恋恋不舍。
他一路上都晕晕乎乎的,特别想躺在炕上睡上一觉,恨不得一步踏进家门。忍着疼痛,快步地走着。
回去二话没说就倒在炕上,老伴说:“今上回来这么早?一般到七八点都死得不回来,今上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他沉默着,没力气说话。院子里拣菜的人,看炕上的人半天没有动静,悄悄的,怪不习惯,这人是怎么了,一回来就躺在炕上。她说:“老汉子,你是不是又头疼了?”他胡乱应付一句:“没事,大概是被窑里死烟味熏的。”她说:“让你少去那些地方,就是不听,尽是吃烟人,能把人呛死。”
他盘算着,不行,真的得去医院看看。但不能让家里任何人晓得,用什么样的理由来遮掩呢,得想周全,不然会生出无数麻烦。试想,他们若是都晓得了,肯定不会让他一个人去,会组织起庞大的队伍。娃们忙,顾不上,要是再请假,划不来。他长手长脚,老大人,不是三岁小娃。一个人去,仔细想能找到的借口。躺会感觉舒服多了,起来,拿个小凳凳到院里坐下,说:“老婆子,我年轻当兵时的几个战友来信说想聚聚,我明天起身,去河南,和几个老兄弟一起聚聚。估计这也是最后一次,都老了,活一天少一天。”她停下手里的活,说:“这么远,你一个路上能行?”他笑着说:“看你憨的,想什么呢,我一个还不能行?这么大个人了,还能丢了?他们会提前到火车站接我,放心。”她无心再做手里的活,心不在焉,自己言语:“哦,路上可要注意安全,现在乱得很,坏人多,把东西拿好……”还没走,就开始安顿上了,他看了一眼她,唉,都老了,白头发在逐渐变多,黑头发的空间将会越少。
收拾好用的东西,装了一大包。
5
去火车站,他改变了方向,去县城。他提着行李,公交车上人满满的,县里今天遇集,一车受苦人,说着家长里短。县里人很多,刚下过雨,泥糊子水在公路上肆意的流淌,等太阳出来,一晒,黄尘满天飞。他到了县医院,听说先要挂号,问个人先找到挂号的地方。
“娃,我想问下在哪里挂号?”他问一个女护士。
“大爷,就在那个窗口。”护士给他指了指不远处的一个窗口。
跟前就他,再没其他人,号直接就挂上了。诊断的和老医生说的一样,他又问了个人,跟着去了放射室拍片。快到了,那引路娃娃说到了,自己过去。他走到门口,看到一个连白大褂都不穿的人,趴在桌子上睡觉。他很郁闷,这才十点多,哪里来的瞌睡。他轻声的敲了下门,睡觉的人没反应,又敲了几下,逐渐加了力量。睡觉的人才不情愿地爬起来,舒展着身子,用惺忪的睡眼看着他,问:“老汉,你要做什么?”他说:“我拍个片子,你看看单子。”那人把他手里的单子接过去,看了一眼就扔在桌子上,指着一个机器台子说:“去那里躺着。”他放下手里的行李包,准备躺下,那人白了他一眼,说:“哎,你先到外面把身上的土拍净,尽是些黄尘。”他在外面拍打身上的土,听见里面的人还说:“都要和你这样的人,背一身土来,那机器用不了几天就得大修。”他听到这,心里不舒服得厉害,使劲地拍打身上的土,本就不该出来,后悔出来了。
进去后他直接躺上去,那人敷衍了事地给他做完。好了后,出门时他补了一句:“我这样的人怎么了,我看你爹娘也是这样的了,把你一下就养成个城里人了?”那人立马反驳道:“你这老汉怎么这么说话。”他停下脚步,站住,说:“我怎么说话了,那你说我应该怎么说。我出门前也穿得都净净价,是路上的黄尘飞起来才粘上的。你说脏,你要我怎么说,也说我自己脏?还是说不该来这拍片子?”那人气得嘴唇直哆嗦,说:“你,你,你,你这人,怎么这么,这么胡搅蛮缠呢。”
拿着片子来到二楼一个办公室门前,让医生看看这片子。他敲了敲门,里面的人说:“进来。”一个头发油光发亮的男人,对面坐着个漂亮的女人,头发披肩,身穿白大褂,两个人在闲聊,不管进来的他。两个说笑着,他等了几分钟,说:“医生,我来让你看看片子。”那四十多岁,肥头大耳的男人说:“等等,没看见我这正谈论工作吗?”工作?他的耳朵没出问题吧!分明听见他们是在说晚上到什么地方吃饭,这难道就是工作?他提起行李包,准备走,老子不看了。男人看他这架势,说:“你把片子给我。”男人对着窗户看了几眼,居高临下地说:“老汉,从这片子看,你脑袋里像有个东西了,你还是尽快去市医院,那里条件好,能检查得更清楚。”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出来了,和村里老医生说的差不多,也等于他娘的没说。
医院出来,他的脚步很沉重,看什么都觉得虚无缥缈,软绵绵的没了骨头,车是孩子手里的棉花糖,天上飘的云很是轻浮,世界是灰暗的。去哪里?这里也说是脑袋里长了东西,也许就是肿瘤,怎么活?走到广场,到处都是喜庆欢快的音乐,老年人闹秧歌,年轻人跳舞,好不快活。他本想直走过去,还是停站住,看下,好像所有的东西都在呲嘴咧牙的笑他。他愤怒,胸中的怒火冲天,为什么县城里的人活得这么好,晚上吃过饭可以这样享受的锻炼,锻炼是什么?他说就是吃了不得饿,受苦人这会正刚从地里回来,忙得做那口吃的,许是吃早上剩下的饭,许是烩一锅,许是熬点米汤。他梗着脖子,不再停留,径直地走过去,终于安静了。
6
马上坐车去市里,到了市里是十二点多,这么晚能去哪里?可以去一个角落或天桥底下凑合到天亮,但他不想,他不是流浪汉。他虽是一个受苦人,但最起码可以堂堂正正的去住旅馆,不住贵的就行了。出了车站,附近就有好多小旅馆,一夜三十,去了一家。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也就是凑合住。能遮雨挡雨就好,别下雨了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天还不算太热,夜深了,房里有一个破电风扇,调大调小都一个速度,慢悠悠,老态龙钟的样子,更像是将死之人,出着一口可有可无的悠悠气。门关上,躺在逼仄的床上,白色的灯光,照着乌黑的墙壁,地上黑漆漆湿黏黏的,能把人恶心死。热得喝点水都喝不成,没热水壶,好在包里还装着半瓶矿泉水。三点多,他没有睡着,眼睁着,胡七八糟的想一些事情,像是诗人,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咚咚咚咚的敲门声,很轻很妖娆。他问是哪个,没人回应。问了几次都是一逑样的安静,他气汹汹的站起来,去开门,门一开,一个四十多的中年女人如决堤的洪水一样涌进来。他好惊讶,这是什么意思。
他说:“你这是做什么?半夜三更的。”
涌进来的女人已经坐在了床上,低着头,妩媚的说:“大哥,当然是伺候你的么。来吧,坐这里来。”她拍着自己的旁边。
他算看出来了,这是个小姐。可他怎能做这样的事情,传出去还活不活人,就催促地说:“你快走,我这里不需要你伺候,该上哪里上哪里。”女人站起来,直往他身上贴,他死活拉扯不开,女人成了没骨头的妖精,怎么摔都摔不开。拉扯中两个人的眼睛对上了,这不是那谁吗?女人也看出来了,在哪里见过,肯定认识。
他想起来了:“你是张连喜家婆姨?”女人不好意思地说:“是了,二光哥,你这是去哪里了?怎么住在这里?”他说:“我是到市里找个人,你这是?”他没有直接说出,想给她多少留点面子。记得每年快过年,张连喜就带着婆姨回来,穿得簇新,村里人都说他们在外面挣下了。张连喜给个厂子看大门,婆姨给做几个人的饭,两个人一月下来差不多能挣八九千。谁成想是这样,做着这么些营生,和听到的纯粹是天壤之别,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她倒究是闯出来的人,尴尬了一下就恢复了嬉笑,说:“我这,你晓得,不这样没办法,你连喜兄弟懒得什么也不做,整天还要吃要喝,我就出来做这个。他也不管,一天吃上喝上就行。这个时间正在租赁的家里呼呼大睡呢。”她重新把身体粘黏上来,说:“二光哥,你就来么,你可以不给钱,我就是想和你睡一觉。”
大半夜,跟前有一个女人这样诱惑,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受不住,勾得他心烦意乱。他转过来一想,来就来一下,那有个啥,完了给撇几十块钱。人活逑的也没什么意思,说不来什么时候就死了,或许睡一觉就有可能醒不过来,或许走路被车撞,或许颠倒一下就命赴黄泉了。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就他这样,脑袋里长了东西,不晓得能活多久,不弄白不弄。
他说:“能行,来。”两个人缠在了一起,倒在破旧松散的床上,床吱呀吱呀的直叫唤,他在快活过程中,生怕床散架了,那可就不是几十块钱的事了,而是几百都不晓得能解决得了不。紧张中又不乏刺激,仿佛回到了年轻的时候。
他醒来时,女人不在了。他想到了什么,去摸衣裳的口袋和行李包,钱和行李都在,一点没少。长舒一口气,却又害怕起来,她怎么不要钱,许是他没醒来,她等不住他醒,又不好意思推他醒来,就走了。不会是要讹诈他吧,应该不会,都一个村的。他没想多少,潦草穿好衣裳,提上行李包向医院进发。他没坐车,打问到说医院离这并不远,就试着走,歪打正着,端端的,没绕弯路。才七点多,医院还没上班,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他问了一个护士,说明自己的情况,护士说先挂个号,拿上县上拍好的片子给医生看,看医生怎么说,然后您再做打算。
挂号的人很多,要排队,不和县医院那么方便,就他一个人。两个多小时后,终于到了医生跟前,他把片子给医生,医生没和县里医生一样,举起对着亮光看,而是别在一个明晃晃的玻璃墙壁上。他想,这就是区别,大医院和小医院的区别,多么专业。医生说,按这个片子来看,脑袋里是长了东西,再做个磁核共振,这样做出来能看得更清晰。他只能说可以。他跑遍了医院,为做这个磁核共振还是核磁共振,跑了很多路,等了老半天才做上。做出的片子要等明天才能取,那他在市里还得住一晚。今晚,去哪里住都行,只要不去昨晚那里。
他在医院跟前找了个小旅馆,比较隐蔽,七拐八绕的小胡同里隐藏着一个逼仄不堪的院子。老了,不得不服,这么一天下来,累得实在是不行了。挨着枕头就睡着了。
第二天取到片子,医生看过后,说脑袋里就是长了东西,而且还不小。眼睛有时候会模糊,是因为长出那多余的东西在不断变大蔓延,侵占视网膜的空间。和到这里来之前老医生给他说的一样,再要是觉得不甘心,那就去省城的大医院,那里最权威。
7
下午买了去省城的火车票,结果(大概)——脑袋里长了瘤子,并且很大。他还是想去省城的医院看看,倘若实在没办法,天不让活了,那就坦然的接受现实。火车出发了,咣当咣当的变轨,甩掉一个地方又一个地方,他注视着窗外,却没看外面,看不看都是陌生的地方,没有记忆与印象,更没什么意思。
到省城是第二天早上五点多。车上无聊时,他看到离自己不远的座位上坐着一个病恹恹的老汉,和他年龄差不多,周围坐的肯定是老汉的儿女们。他听到老汉身边的女人说:“爸,你不要担心,我们就快到医院了,大医院和小医院不一样,什么都能治好。现在医疗这么发达,我们都在了,放心。”老汉头靠在椅背上,说:“我晓得自己得的是什么病了,要是真的是那恶性的,你们就不要花那钱了,我也不想开一刀,让我完完整整的走。”身边的男人说:“没事的,爸,不管恶性的还是良性的,现在都能治。再说,市上检查的那也不一定,等我们到了再做个检查。”老汉不再说话,静默地坐着。五六个小时过去了,他口干得很,急需水分的滋润。站起身,去接水的地方接杯开水。在过道里小心翼翼的移动着,过道里也站着不少人。在接水处接到水后,想吃根烟,就先吃根再回去。不经意的一瞥,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村里的英雄张铁栓。比他小四五岁,也是快五十的人了。一直做事都比较武断,按村里人的话说是二百五着了,火药桶子,一点就着。英雄称号是货真价实,拿伤痛换来的。铁栓也看到了他,说:“二光哥啊,你这是要去哪里了?”他说:“去省城里看个同学,”吃了一口烟说:“铁栓,你这是去哪里?腿上的伤还没好利索。”铁栓斩钉截铁地说:“我的事你也晓得,我要去告村长及其他那些当官负责的,还有村霸无赖张常五。”他点点头,没有发表什么评论。
铁栓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在村里只要有没道理的事,他都会去管。今年开春,村里几年前都吃上了自来水,原来一道街共同吃水的井子就荒废了。张常五在离井子不远处修了五顶五的二层楼。请来工匠,准备把井子封住,往里扔个水泵,修个水塔,直接引到他家。开工了,谁也没说什么,有说的也都尽是在背地里议论。这井子本就是大公的,是一道街上所有人的,如今张常五想独占,大家都晓得这不对,张常五在侵占公共的财产,却没一个人愿意吭声阻拦。铁栓看不过去,就去阻拦,自然和张常五起了冲突,张常五是村里一霸,仗着这个动了手,拿铁锨砍伤了铁栓的腿,伤口很深,看着都发怵。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出了院,人家张常五啥都不管,说这是铁栓活该,谁让他多管闲事了。铁栓告到县上,县上有张常五的关系,村里领导都被买通了,不仅送了东西还请吃了饭,都作证说是铁栓先找的事,无理取闹。后来好多村民实在看不过眼,给铁栓作证,但县上法院依旧判决说是铁栓的过责。最让人不能接受容忍的是,铁栓出院回来,医院花了许多钱不说,没几天,又被张常五找县上的混混打了一顿,撂下话:“要是再不老实,敢胡乱告状,见一次打一次,甚至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铁栓被惹怒了,不顾生死,也撂下话:“只要我活着,就告,有本事把老子给弄死。”这不,现在在火车通风口处的过道里铺张报纸坐着,和他遇见了。
铁栓叹了口气,说:“现在的人,都怕事,明知张常五是错的,都不敢去惹。就是看,好像事不关己,尽看热闹。再说,你看看今年村长的候选人,竟然有张常五,还有,看看村委那几个当官的,哪个不是村里名誉臭得不能闻的人,都是霸道之人。我就想不通,怎么成了这样,正儿八经的理却硬不过权势,那些人没理也是有理,我是有理也没理。”他也同情铁栓,可爱莫能助啊,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只能安慰说:“总有能说理的地方,不过,你要注意安全,张常五的心坏着呢,什么恶事都能做得出来。”铁栓坐着,疲倦地说:“没事,有种他小子把我给杀了。”
第二天车快到站,他又去接水,没再看到铁栓,他不由自主地胡想起来。
车站出来,到处都是车和人,招揽生意的喊叫声,到底怎么走,这次真是到大城市了。站在一个地方好久,才反应过来,得去省军区医院。寻了半天才把目标锁定,一个穿着朴素的老头,看着像是退休老干部,像城里人。老头很客气,说这里到省军区医院可以坐哪几趟公交车,打车的话得二十块钱。他也没有记住坐哪个公交车,问题是直接坐不到,还得倒车,这就难为他了。他人生地不熟,看哪哪都一样,迷路是最应该的。看衣裳上灰土一层,就能晓得他是从偏远地方来的,别再上当受骗了。打个车,不就二十块钱么,方便不算还能直接到。下车时,人家开车的说四十五块钱,他说怎么那么贵,司机说看表,那里的确显示着四十四,他也没好意思为一块钱再说什么,忍着给了。不管怎么说,总算是到地方了。
没有其他的不同,就是人多楼高车多,到处都是一样。在医院门口,他吃了一惊,老天啊,这哪是医院,医院里有公路,公路上有红绿灯。他把周围大体看了下,比家乡的县城大概都大,只是一个医院啊。也是,周边几个省来说,这都是最好的医院。几个省的人来这里看病,人不多就不正常。进了门,大厅里人头涌动,他不晓得往哪里走。看到好几绺长长的队,排在各个窗口前。他猜想,这里也应该是先挂号。可去哪里挂号,还是得问下人。
“护士,你说我看病,是不是得先挂号了?”他说。
“叔叔,你说什么?”护士一脸的迷惑。
他又说了一遍,护士依旧说:“叔叔,你说什么?”
他就郁闷了,这么年轻的娃按说耳朵好着了么,怎么就听不下他说什么,第三遍的时候,护士说:“叔叔,你说普通话,方言我听不懂。”他尽最大努力说普通话,可大部分还是方言,只有个别字是按普通话的套路,护士最后按着听到的只言片语,给他做了解答。
“叔叔,是的,先挂号,到那里。”按指着的方向,他看到了无尽头的长队,护士说:“可以挂专家号和普通号,尽量挂专家号。不过专家号每天有限。这会您肯定挂不上了,要挂只能在明天一早四五点就来排队。还有网上可以挂,您是第一次来,肯定不行,只有等办了医院一卡通才可以。”他听得一头雾水,天呀,挂个号都这么难,还看个逑。泄了气。电梯上的人是满满的,他好奇,楼上是什么地方?楼上的楼上又是什么地方?他不晓得。太多了,不光这一栋楼,还有好多。
8
他在椅子上坐了会,想,先到医院里转转。每走一步,到一个地方,他都停下好一会,看标志性的东西来记住,为一会返回去做准备。这样谨慎,最后还是迷路了。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转出来,一身汗,太热了。肚子咕咕叫了,去吃个饭。不敢走远,就在附近,饭贵不算还不好吃。要了一碗面,十块钱,卖相还不错,但没煮熟,饿了,半生不熟的也吃了好多,剩下一点点。
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路上,人来人往的。看到马路对面有一个卖饼的,想去买一个吃。看着车辆穿梭不止的公路,他不晓得怎么过去。唉,明显的感到一种压迫,一种格格不入,一种难受,一种厌恶……找个住的地方,这病到底还看不看了,挂个号都这么难,边走边想着。看不看病,今晚也都得住在这里,回不去的。
正儿八经体会到了恶劣环境,一个简易小房子,四十块钱一晚上。就一张床,一个小破柜子,一个脏了吧唧的暖壶。床单不光黑而且油腻腻,看着都恶心,怎么睡在上面。他坐着,空气里充溢着一股子霉湿味,呛人,闷热得难以流通。他浑身淌水,衣裳都湿了。
他不晓得怎么躺在床上睡着的,估计是瞌睡得实在撑不住,就顾不得脏不脏了。
既然来了,那就看看,不然白跑一趟了。半夜三点多热醒来了,坐到四点多,提上行李去了医院。医院和白天没什么区别,只是人少了很多,不过他相信用不了多久又会密密麻麻起来。排队,他前面已经有了三四个了。八点多,快要上班了,他突然肚子疼,想去厕所,怎么办?实在是急,不然会拉在裤子里。行李没人照看,只能拿着。一秒也等不的,没办法,去了厕所。等回来前面排的几个人已经办完了,他给别人解释说他刚在这里,谁都不信,不让他插进队伍,让到后面去排。别说,这些人是真的没看到他排队,就算有的看到了也会说没看到。他看了一眼长长的队伍,还排个逑,肯定还没到他就没号了。
算逑了,他一个人生闷气:老子不看了,大不了一死,还能怎么样。回家,死也得死在家里。想到了村子里的老医生,心里高兴起来。娘的,这里有什么好,不就是专家多机器先进么。回去,回去了让老医生看,吃中药。
9
回去后老中医给他开了十几服的中药,先让他吃着。他晓得,这是死马当活马医了,即便是这样,那也比城里的医院好,最起码自在和舒畅。
他在一天天地丧失白天,黑夜不断地增多,终有一天他的世界将全部变黑。黑成一个土窑子,在地里生根发芽,努出地面,长成一个无言静寂淹没于山间的小土堆。
在有一道缝隙的白天的时候,他听说铁栓失踪了,找了很久,怎么也找不到。一道缝隙的白天一闪变成了火车上拖着疲倦身体的铁栓,再一闪就全部黑了,成了无尽的黑夜。
村里响起了鞭炮的声音,他沉浸在黑夜中,问老伴:“村里谁家办事了?这会放炮放得这么激烈。”老伴哀叹了一声:“唉,常五当上村长了,村里人以后可怎么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