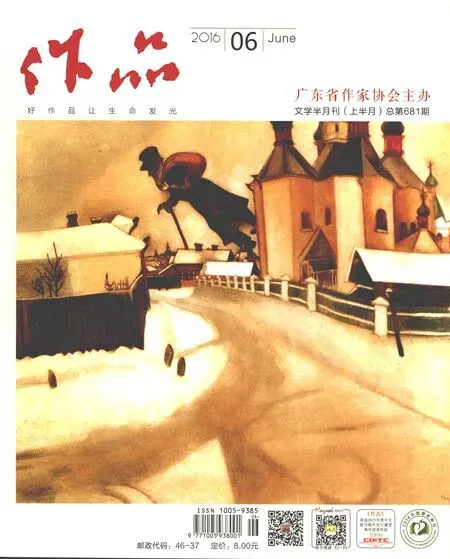祭 日
文/江 冬
祭 日
文/江 冬
江 冬湖南隆回人,1985年生,在《作品》、 《文学界》、 《湖南文学》、 《创作与评论》等刊发表过中短篇小说。
武伟又搓了搓凉飕飕的手臂。他没料到老家的清晨会这么冷。五月下旬,城里的人几乎一律穿上了短袖。他和妻子就都是穿着短袖回来的。昨天母亲就说了他,后来他又被母亲给他们安排的那床厚被子吓了一跳。但母亲是对的,昨晚他们一点都不觉得被子盖得太热。用母亲的话说,这里可是山里面。这本不需要提醒,他就是在这地方长大的。然而这么多年来,他很少待在老家,对于这里的气候,多少有些疏忽了。
母亲没有叫他穿一件父亲留下来的衣服,他也没有提。她倒是把自己的一件外套递给了妻子。妻子昨晚没穿,今天却还没起床,也不知会不会穿上。
因为有淡雾,天色一片混沌。远处的天空有点灰暗,头顶上的那一块则显得透亮。应该不会下雨。空气里有一股清香,是四周那些草木散发出来的。一抬眼就能看到山。这是一个山洼,一条四五米宽的小河穿过,河两岸分布着几十户人家。这时还听不到什么人语,只有鸟儿的啼鸣从四面八方传来,仿佛只有它们,才是这一带真正的居民。
那条狗一直在他的视线里。毛不是纯黄,夹着白色,腹部则一片雪白。鼻子和眼睛漆黑。耳朵又小又薄,呈三角状,向上竖起。脸也是三角状的。它和他在电视上见过的狼的样子差不多,可见和狼是近亲,正宗的土狗。但它看上去一点都不可怕,虽说有半米来长,那双眼睛却毫无神采。大多时候,它都鼻子贴着地面,围着那个给它喂食的黄色搪瓷碗兜圈子。他估计它大概是饿了。
昨天他们一走近门口,这条狗就从趴着的树底下立起来,朝着他们吼叫。妻子吓得躲到他身后,而他一看到它那空洞的眼神,心立刻镇定下来,并逐渐感到它那眼睛里流露出的更多是胆怯,好像是它受了惊吓。母亲跑了出来,朝着它猛挥了下手臂,并大声呵斥:“叫死嘞叫!”那狗立刻安静了,谄媚似的摇了下尾巴后,就又趴在了原地。母亲告诉他,狗是一个熟人送的。他随口说,那狗还蛮听她的话,母亲似乎想了想,才说好歹已经喂了它几个月了。
和公路只隔着一丘稻田,武伟能清楚看到那边的来人。公路上冷冷清清,好一阵子只路过了一对母女。女儿十来岁,走得明显比母亲快,但又一直在母亲身边,因为她几乎不走直线。她穿着蓝色紧身长裤,显出腿的细瘦、修长,仿佛两根结实有力的弹簧。相比之下,那位母亲的腿则显得短胖而臃肿,尽管她还依然年轻,但已让人感觉到她不可挽回的衰老。
表弟竟然不是从公路那边过来的。他走了河边的小路,斜插过来。那条路太窄,而且有长坡,并不大适合骑摩托。不过确实要近很多。
“哥,今天要上山?”
“是啊。”
表弟比印象中的更黑更壮了些,和武伟说话时的那种沉稳,也使他感到陌生。
“你和二姑都没早和我说,不然今天我也陪着你们去。”
“不用呢,这次家里人都没喊。你现在事情好多吧,累不累?”
“活都干不完,累当然有一点,日晒雨淋的。二姑在屋里吧?”
“在呢。”
“那我去看看。”
看着表弟往门口走去,武伟略一犹豫,还是叫住了他。
“猛子——哦,要不还是……”
表弟愣在那里,突然露出一个憨厚的微笑,并挠了挠后脑勺。这是他记忆里的那个表弟。他不禁拍了拍他的手臂。
“就是那条狗?”
武伟点了点头。
表弟环顾了一下四周后说:
“哥你找根绳子来吧,要结实一点的。还要一个袋子,我去找。”
表弟往楼梯那边走去。武伟想哪里能找到绳子。想了会后,他决定去他们睡觉的那个房间看看。
家里还是个木房子。这样的房子,即使在这个山洼里,也是不多见了。父亲还在的时候,一直叨唠着要拆掉房子建砖房。他一门心思地指望着武伟。但武伟在城里买了房,要还贷款,后来又有了孩子,要攒够几十万,似乎遥遥无期。现在只剩下母亲一个人了,她便说住在这老房子里还更舒服。武伟则说房子还是迟早要建的。但这么说的时候,他心里再清楚不过,这是一件多么飘渺的事情。
一进大门是堂屋,堂屋后面是厨房。起床后,他就一直听到母亲在那里面忙活。现在已满屋都是饭菜的香味。堂屋靠右侧的一张小方桌上摆满了今天要用的东西:一篮子金箔纸元宝,一叠打了金钱印的烧纸,一包未开封的细香,一壶盐水瓶装的烧酒,一卷鞭炮,几个苹果,一把香蕉。父亲的遗像摆在正对大门的神龛上。武伟尽可能地不去看他。但每次一进堂屋,父亲的形象便会猛地在他脑海闪现:脸颊消瘦、狭长,眼神斜向一旁,薄薄的嘴唇紧抿,仿佛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最后那几年,他和父亲已无话可说。但父亲的话,还是通过一些亲戚,拐弯抹角地传进了他的耳朵——说他没出息,说他娶的老婆不好,说他这辈子还有得亏吃……
堂屋右侧是看电视的房间,他和妻子就睡在那里面。妻子还缩在被子里,听到他进去,便睁开了眼睛。
“你还睡啊?”
“睡不着。”
“那你还不起来?”
“好冷啊。”
武伟用眼睛四处搜索,觉得有可能的地方,还走过去翻一翻。
“是不是你弟过来了?”
“是啊。”
“你在找什么?”
“绳子。”
没有找到绳子。武伟叉腰站着,又开始想还有哪里可能会有。
“你跟妈说过了没有?”妻子压低声音问。
武伟朝门口扫了一眼,才小声地说:“说过了。”
“妈说什么没有?”
“没有。”
“妈是不是不高兴了?”
武伟没有回答。
“怎么连根绳子都没有!”
他控制不了自己的恼怒。
“要不我们给妈买只猫吧?”
他的视线回到妻子身上。
“要不今天就去买?你们这镇上应该有猫买吧?”
妻子的急切袒露了她的心虚。母亲不能和他们住在一起,都是因为她的缘故。尽管母亲曾给他们带过一段时间的孩子,但妻子和她隔三差五便会争吵。她们有太多习惯、观念上的分歧。妻子跟他摊牌:孩子只能由她自己的母亲来带。于是岳母一退休,便理所当然地取代了母亲。而这一次,他原本打算把儿子也带回来,妻子却坚决反对。她的理由是,这是他第一次开车回去,他技术本来就不熟练,何况又有那么多的盘山路,万一出了状况怎么办?儿子可不能冒这个险!他虽知妻子的话不无道理,却还是赌着气,妻子又毫不妥协,以致几乎无法成行。临走之前,他才给母亲打电话,说孩子突然有点发烧,虽没什么大碍,但最好还是留在家里观察。母亲好一阵担心。
“下午我们就去镇上看看吧。”他对妻子说,却知道,这也是为了他自己。
“你用这个不可以吗?”妻子指着搁在床柜上的一个坏插线板说。
武伟抓起它,把线扯开,有一米多长。电线连着插板的地方已经裂开一个大口。他用力一扯,那线就断开了。
武伟拿着电线往外走,穿过堂屋时,忍不住又往厨房那边瞟了一眼。母亲坐在灶膛前烧火,弓着腰,头发蓬乱,仿佛一只蹲窝的母鸡。武伟昨天劝过母亲理一理头发,母亲则说又不是在城里,哪有那么多讲究。恍惚间,他觉得母亲的眼睛晶亮。也许是烟熏或火光映照的缘故,他不敢细瞧。
表弟还在楼上,听得到他踏在楼板上的嘭嘭声。也不知道小声一点,武伟在心里说,并不由地想象自己在楼上会是什么情景:踮着脚,压抑着呼吸,碰触任何一样东西都小心翼翼。努力甩掉这些念头,他希望表弟能快点下来。二楼堆满了稻草、柴火、木材以及别的杂物,找个袋子应该不难。
表弟下来的时候,手里不仅拿着一个白色的大饲料袋,还拿着两根方木条。
武伟把手上的电线朝他扬了扬,问可不可以。他点了点头。
表弟朝狗走去。那狗显然认得他,并没有躲避,而是仰起头,在他的裤腿上嗅着。表弟俯身摸了摸它的头,它便从他胯下钻过去,绕了一圈回来,又继续嗅他的裤腿。表弟把电线从它脖子下穿过,然后开始打结。那狗扭动着身子,像是在抗拒,但又并不坚决。当表弟抓着电线将它提了起来,它才猛地甩头想要挣脱。表弟又往上提了提,它便只能用后腿踮着地面,再也使不出力气来。
“哥,袋子。”
武伟忙将袋子朝狗的头上套下去。表弟手一松,那狗便有半截身子进了袋中。表弟立刻又一手将狗按住,一手帮着拉扯袋口。眨眼间,那狗就只剩一条尾巴还在袋外。表弟又猛地将袋子往上一提,扑通一声,狗掉了下去,同时响起一阵“呜呜”声。那声音既凌乱,又沉闷,仿佛那狗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来。
表弟扭紧了袋口,又用拖在外面的一截电线紧紧缠了几圈。狗在袋子里激烈地动着,却连“呜呜”声也没有了。
表弟递给武伟一根木条,自己也拿一根。武伟以为是要他朝狗击打,却见表弟将袋子提起,朝楼梯那边走去。拐了个弯后,表弟猛地将袋子朝那边的一口石缸扔去。那石缸是一整块石头凿出来的,放在那儿已不知多少年了,一直积着雨水,似乎从来不曾使用过。
落水的刹那,袋里响起一声仿佛哭泣般的尖叫。武伟的心随着猛地一跳。表弟已将木条往袋子压去,并招呼武伟过去。武伟也将木条插了进去。木条迅速下沉,剧烈的颤抖传到他的手心。
湿漉漉的尼龙袋摊在那里,袋身几乎成了绿色,像是刚刚从染缸里提出来的一般。
表弟朝他说了句什么,武伟只感到他的声音在耳边回荡,却不明白是什么含义。待反应过来时,表弟已不在身边。
袋子四周的水迹在扩散。随着那些水的流动,武伟觉得那个袋子也还是会动弹,但无论怎么盯着,都只见到一个硬邦邦的形状。
他突然感到内心空空荡荡,而他又那么迫近地希望找到一种感受来面对眼前的景况。他扫视四周,什么人都没有。此时没有一点风,附近那些杉树、梨树、泡桐、毛竹,全都一动不动。但他分明感到它们的每片树叶上都长着一双眼睛,而这些眼睛全都在注视着他,看他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这就好像一年前,在给父亲治丧的日子里,他在空荡荡的内心里努力地搜寻悲伤。但大多时候,他都一无所获,以致茫然不知所措。几天下来,他都如木偶一般,别人要他做什么,他才做什么。所有人都以为他只是受了父亲去世的打击,一时缓不过神来。但他明白,自己其实再清醒不过。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没有悲伤,只有疲惫。如果可以,他恨不得马上躲起来,但他清楚地知道不能这样做,因而更感疲惫。
他又想起昨天的那些情景。在二爷爷家的堂屋里,和二爷爷、二奶奶聊了会家常,他估摸着可以走了的时候,二奶奶突然提到了母亲喂养的那条狗。
“好远巴远地弄过来,还真是费了心思呢。”
“不是别人送的么?”
“哪个会送?两岁多的狗,自己留着吃肉多划算!”
“我妈有条狗陪着她也好。”
“那是的。你娘对那条狗还真是好,听到说你娘吃么个,它就吃么个。”
武伟没有接话。二奶奶又接着说:
“还是有点怪,养么子狗啰——”
“有么子怪?学人七嘴八舌的。”二爷爷打断二奶奶,还瞪了她一眼。
“我又没说么子!”二奶奶含糊过去,没有再说什么,武伟也便顺势告了别。
在回家的路上,妻子问武伟他们是不是说到那条狗了——她听不懂他们的方言。武伟什么也不想说,便说只是随便说了几句。
到了晚上,他们虽早早躺下,却迟迟无法入睡。外面说不上是安静还是吵闹——屋子前面是竹林,后面是一口大池塘,右侧是稻田与公路,左侧是一片菜地,再往前则是一栋已被弃置的木屋。随着入夜渐深,屋外的寂静也仿佛越来越凝重,因而一些细微的声音也变得喧哗起来——他能清楚地听到附近草丛里虫儿的欢唱,听到风滑过附近山坡上的树林,仿佛什么人在远处不停地呼叫。后来,外面又响起一声接一声的狗吠,一时在这里,一时在那里。那狗像是围着房屋在绕圈子。仔细一听,它的吠叫急切而低沉,既像是在呼唤,又像是在哀求。
武伟正想着那狗是怎么回事,他疑心已经睡着了的妻子却冷不丁地在黑暗中问他:
“你说那是一条公狗还是母狗?”
妻子走了过来,没穿母亲的那件外套。
“你弟走了?”
“走了。”
“也不留他吃个饭?”
“他说吃过了。”
“那个你没要他带走?”
妻子指了下好像一块奇特化石的尼龙袋。
“给他带走,他会带回去吃掉。”
他知道妻子从不吃狗肉,也不喜欢别人吃。
“那怎么办?”
“我会扔掉的。”
武伟本来的计划,是要表弟把狗带回去的,一来算是酬劳,二来也省得自己麻烦。但就在不久前,他突然觉得应该给它安排一个更好的归宿——这是他唯一能做的事情了。
他鼓足了勇气,才伸手去提它。一种湿黏的感觉,蛇一般钻进他的心底。他立刻想到了放弃。然而在妻子的目光下,他突然又生出一股怒火。他猛地往上一提,然后梗着脖子往前走。他以这样的方式,似乎是想告诉妻子:我做这些,都是因为你。
“你早点回来,妈等下……”
妻子没把话说完,但他已明白,她是害怕单独和母亲待在一起。
“我很快就回来。”虽这么说,他却想着妻子也应该受点教训。
沿着稻田往公路上走。手上的重量似乎越来越沉。他想到可以拖着走,但又觉得这样违背了他要善待狗的初衷,便又坚持着。
他把车开离了公路,来到一条长满了野草、露出两条车辙印的土路上。一路都是上坡。路的右侧是山壁,左侧可以看到连绵的稻田以及房屋。镇上的街道,也在那一边。除了少数几块秧田,稻田多是灰白色,都耕犁过了,积了水等待插秧。
开阔的感觉很快就过去了,越往上,越是往山林里面钻。逐渐地,两侧都只能看到树木。武伟突然怀疑起自己的记忆来,又疑心是这条路改了道,毕竟他已近二十年没有走过这条路了。但没办法掉头,他只能继续向前。
路没有错,他开上了水库的堤坝。堤坝有好几米宽,中间依然有两道白色的车辙。车子一上来,视野立刻又变得开阔起来,右侧是一大片水域,左侧又呈现出了刚才被山丘遮盖了的稻田与房屋。此外,这里的天空再没有任何遮拦,仿佛一顶乳白色的大帽,结结实实地压在他的车顶上。
他把车开过百来米,到了堤坝的中间才下来。走在堤坝上,他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记忆中那个平平无奇的水库——少年时候,他常和伙伴们来这儿钓鱼,虽然没哪次真的钓上了什么——水库两侧的树林密实而庄严,风吹动着薄雾在水面上飘荡。远处的水面是亮白色,仿佛水波在不停地翻涌,近处的水面碧绿,却也并不平静,无数的涟漪在扩散、消逝,然后又有新的乍现。是一些叫水黾的虫子在水面上滑动(他已忘记它们的本地叫法)。堤坝上长满没膝的野草(他也忘记了它们的名字),草上开满指甲大小的野花——中间黄色,外面一圈白瓣。几只白色粉蝶在附近的草丛起落,一群蜻蜓直直地飞过他的头顶,似乎完全无视他的存在。
视野里一个人都没有。一只鸟儿的啼鸣从水边的树林里传来,每次都啼叫两声,隔一小会儿又重复。但完全看不到它的身影,甚至连它到底在哪个方位都说不大清楚。
风一直吹着,满耳簌簌的风声。他觉得身上更冷,却也感到更为清爽。他几乎忘记了来此的目的,而一想到,便觉得自己确实是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他把装着尼龙袋的白色塑料箱从车上搬下来——塑料箱他不打算要了。他抓着箱子,缓缓地下坡,来到了水边。他又一次握住了绑着电线的袋口,依然有点湿黏。然而这一次,一种奇怪的感觉立刻涌遍了全身。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呆在了那里。就要把它扔下去了——心里一闪过这样的念头,两股热泪便涌出了眼眶。
这感觉其实并不陌生——就在昨天晚上,他们在前坪里给父亲烧纸钱。他拿着一根小棍,边烧边搅动。黄色的纸钱被火苗舔舐,迅速变为黑灰。火光忽明忽暗,像一只躲闪的眼睛在打量这个世界。缕缕白烟升腾,携带片片黑灰。他不时往火堆里添新的纸钱,不禁又有了那种不知身在何方的感觉,仿佛自己只是一个木偶,在做着另一个人必须要做的事情。然而骤然响起了母亲的哭号。原本站着的母亲瘫坐在了地上,边哭边拍打膝盖,身子也随之俯仰。她抬起身子时,火光映亮了她湿漉漉的面庞。妻子在旁边拉扯劝慰,母亲却似乎已忘记了周遭的一切,将一声紧跟一声的哭号送进了冷清的黑夜。那时候,他就感到有什么东西在体内涌动,可还来不及体会,它便又沉寂了下去。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