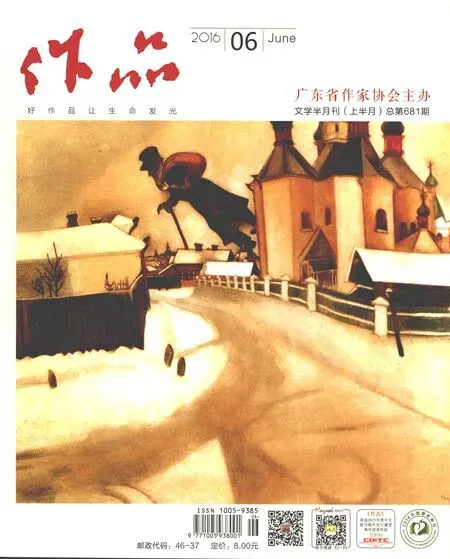老虎·食物·红纱巾
文/贺小晴
老虎·食物·红纱巾
文/贺小晴
贺小晴四川绵阳人。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13届高研班、第28届高研(深造)班学员。作品载于《当代》、 《北京文学》、 《中国作家》、 《天涯》、 《花城》、 《作家》等刊,部分作品被转载或进入年度排行榜;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等你把梦做完》、 《脆响》,长篇小说《花瓣糖果流浪年》,报告文学《艰难重生路——汶川大地震丧子家庭再生育纪实》等。获第五届徐迟报告文学奖提名奖,第八届四川文学奖,世界华文文学学会、花城出版社联合征文特等奖等。
1
那天晚上,二姐和幺姐来我们家,带来了一筐脐橙。那些脐橙椭圆形,金灿灿红彤彤的,每只都长有一个受惊样的圆眼睛。装脐橙的是一只方竹篮,那个年代每户人家都有一只。农民用它装鸡蛋或者水果出售,城里人用它买米买菜。我妈从厨房拿出一只一模一样的竹篮,将脐橙从二姐和幺姐的篮里,捡去我们家篮里。
我爸那时候正坐在客厅的那对单人沙发上。沙发铺着布巾,布巾上是一只正在扑食的老虎,体大神威,占满了整个沙发。因为老虎,或者因为别的原因,那对单人沙发成了我爸我妈的私人宝座,即使他们不在,我也从不会去坐,只偶尔侧过脸去,看老虎几眼,觉得我爸走后,它就是他的替代物:威严,沉默,不苛言笑。
想起来我爸那时候比老虎还威猛。他不在时,我看着老虎,并不觉得它会吃人。我爸回来,一屁股坐上去,老虎不见了,我却像真伴着老虎一样紧张和难受,老想着他走,一心盼着能有个事来,让他马上离开。
那时候,大人们都说小孩子盼过年,我不盼。我只盼我爸出门。最好是出远门,好久好久不回来。
尽管如此,我爸在家时,我也并不觉得度日如年。毕竟他是我爸。再怎么讨厌我也换不了人。久而久之,也就习惯成自然,有了从容麻木的心态。
那天晚上,看着我妈把方竹篮拿出来,把脐橙一个个往篮里捡,我爸这才有了反应。之前二姐和幺姐进门,说了一大堆客气话,我爸只是坐着,一言不发,仿佛菩萨接受着信徒膜拜。在我爸心里,或许他觉得他是有资格享此待遇的。二姐和幺姐不是我的姐姐,也不是我们家的亲戚。幺姐是我的初中同学,因为比我大,也因为她住的那条街都叫她幺姐,我也就跟着叫了。幺姐身体不好休了学,留级来到我们班,成为我们班最大的女生。而我偏偏年龄最小,又有着一副与她截然不同的打闹性格,她便主动包揽,把我当成了小妹妹。
二姐则是幺姐的二姐,自然也就是我的二姐。
我爸大概是看着自己的女儿有诸多的不如意,又或者从我的身上觉出了我对他的抵抗和排斥,他像要寻找替身似的,对幺姐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喜爱。有时候,我简直有种感觉,如果睡梦中梦见女儿,他梦见的肯定是幺姐而不是我;如果不是血缘的绳索把我们死栓在一起,最想要挣脱的,肯定是他而不是我。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幺姐的身体极度虚弱。常常,夜深人静时,我躺在里屋佯装睡着,其实在偷听爸妈谈话。那时候是他们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茶几上的茉莉花茶冒着烟,茶杯端起放下的声音不断响起。我闭着眼,能看见他们一人坐一张沙发,把两只老虎实实压住,心满意足地喝茶,喘气,说话。
但他们说的不是什么知心话,也不是谈情说爱,仍然是一堆鸡毛蒜皮。有时候说我,有时候说些不相干的人,有时候说幺姐。说我时多半是数落我的不是:哪天哪天回家晚了,哪天哪天吃饭时发呆,走神,哪天哪天又折腾出一个新发型……说幺姐时,爸妈二人口径一致,态度高度统一,夸幺姐性情好,懂规矩,那条黑辫子又粗又长,人家就从来没在头发上费过心思。
我妈称我黄毛丫头。我妈说我的头发先天不足,像我爸。我爸对此不拿意见,也不看我,只对我头发上别的东西感兴趣。我爸说是学生就要认真读书,别把心思用去别的地方。我爸没明说别的地方是哪,但我知道他说的是我的头发——我头发上红的黄的蓝的发夹和蝴蝶结。我头发少,不漂亮,我只能用这些复杂的颜色混淆人的视线,掩盖我的沮丧。
有时候,人家夸我,说我长得白,脸型小,眼睛又黑又大,像我爸。我爸也不拿意见,沉着脸,对人家的夸奖和我的五官视而不见。稍后,人家走了,我爸也不抬头,也不改色,只用沉闷的声音说,别去听那些人的,小孩子家,要把心思用在学习上。
有一次,我们班一个男生,摸黑来到我家巷子,紧贴在我家门上。但他什么也没做,只那样贴着。恰好我爸开门出来,男生见了光,兔子一般跑掉了。我爸看见了一条黑影,折转身来审讯我,认定我和他串通好了,想图谋不轨。我不言,死憋着我的泪水。那阵子,我有种感觉,我爸我妈生下我,就为了拿我当敌人待。他们的人生事事圆满,只缺少一个敌人。
这事后来平息,多亏了幺姐。那天,幺姐来到我们家,趁我转身,我爸就问幺姐,那个男生是谁?幺姐说,她真不知道。但她可以保证,我没跟男生串通好。这样的证明远不足说服我爸。幺姐只好说出,我们班的某某男生给我写信,用一只装乒乓球的圆盒装着,塞在我的课桌下,我看见后,硬要还给他,还是幺姐陪着我一起去的。我爸听了,不表态,鼻孔里哼出一声,表示怀疑。幺姐只好又说,那个男生,是我们班打乒乓打得最好的,还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
我爸这才缓了脸色。他大概在想,既是乒乓球干将,又是团支书,那一定是班上最优秀的男生,这样的男生我都没出啥事,大概也算是个交代。但他并未就此罢休,只道,还给他,还给他干啥?不去交给老师?
这正是我瞧不上我爸的地方。他们太相信组织或者老师了。他们从生下来起,就坚定地相信,自己不该是自己的,是父母的、组织的……他们像定位器中的目标一般被锁定,被监控,被主宰,不觉屈辱,反倒以为受了重用,得了恩惠,一旦失去监控,脱离了统治,顿时便感觉乱了方寸,迷失了方向。
以我爸这样的人生观,我现在的归宿,要么是父母的,要么就该是老师的。
2
这事之后,我和我爸互相隔膜着,厌烦着,却也相安无事。那天晚上,我躺在里屋,听见我爸我妈说了一通废话后,忽听我爸说,你注意到没有,最近春月(幺姐的名字)瘦得厉害,不会又有啥病吧?
我妈就像被点醒了似的,一个劲附和。还说某个太阳天,她在街上碰到幺姐,老远见她,瘦得像一张皮,骨头在皮下,被太阳照着,数都数得清。
我妈又说,平常她跟妹儿(我的小名)一起来,进进出出,看惯了,也不觉得有啥不同。那天隔得远,又有太阳,真像是变了一个人。
瘦得都不像人了。我妈又说。
我爸后来始终没有说话。
几天之后,就有消息传来,幺姐真的病了。是严重贫血。血色素低至4g/L.,而低于3g/L.,就会有生命危险。
也就是说,幺姐的命已经垂危,已经接近临界点。
我的心在那一刻狂跳不已。那时的我还不明白什么叫生命,什么又叫死亡,只是被一种本能的、骨子里漫出的紧张和恐惧所控制。我想象不出平常亲如姐妹,就像影子一样跟着我的幺姐,怎么突然就变成了人人谈而色变的另一个人。
更揪心的是,我不知道接下来,幺姐究竟该怎么才能摆脱这个危险,重新成为曾经的幺姐。
我爸由此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我爸那段时间,骑着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车圈擦得锃亮,车的后架上,随时载着幺姐。我仿佛知道他在带着幺姐寻医问药。有一种药叫“肝膏针”,据说是那个年代治疗贫血的特效药。因为特效,既使贵,也奇货难求。我爸使出他的所有功夫,不但找到了这种药,还白白送给她打,不要钱。
我爸知道,幺姐家的兄弟姐妹蒜瓣一样多,父母又是老实巴交的竹器厂工人,要他们明白血色素4g/L.意味着什么,实在不易,要他们支付这笔钱,更是困难。
毫无疑问,幺姐的病后来好转了,血色素直线上升,回到了7g/L.,接近正常人的数据。我爸因此成为功臣,成为幺姐全家人的救星。
此事已过去多时,我们差不多都忘了。幺姐继续是我的同学,我们继续同上同下。我爸心里得意,嘴上早已不提。那天晚上,幺姐跟着二姐来到我们家时,我突然有种异样的感觉:幺姐已不是我的同学幺姐,也不是白天的幺姐,幺姐是二姐家的幺姐,来自另一个星球。那天的幺姐腼腆,谨慎,仿佛第一次来我们家,脸上挂着陌生的微笑。后来我才懂,那是求人者脸上特有的微笑,那也是受恩者面对恩人时常露的微笑。那微笑小心,吃力,生怕有丝毫不妥,因此显得紧张而卑微,刻板而生硬。我的心有些疼痛,却不愿做任何努力,也不想与眼前的幺姐同流合污,只坐在角落,将一只脐橙拿起,放下,再放下,再拿起。
好在头顶的灯光昏暗。灯光之下,所有人的表情,都是被抹涂过的,又被模糊掉了。
3
我爸对二姐和幺姐的客气话和感激之情无动于衷,却不可能对篮里的脐橙置之不理。对脐橙或者柑桔或者别的任何水果,我爸都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们这地方自古以来都种柑桔,由柑桔又派生出若干品种,如血橙、脐橙、广柑、碰柑等等,除此之外,一些特别的乡镇,还有成片的梨子园、苹果园、米枣大枣等等,由此我们县成为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我爸也成为保存水果的个人典范。
原来我爸对水果的兴趣不在吃,也不在品尝水果的味道,而在于保存。我爸对水果的这种偏好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尽管我们县水果丰富,但整个社会都缺钱。有水果需要有钱买。我们家不缺钱但我爸仍受着钱的威胁,生怕有朝一日,自己家也沦入吃了上顿没下顿之列。出于高瞻远瞩居安思危的天性,我爸生出了理想:如果能在别人家没米吃时自己家有米,别人家没水果吃时自己家还有水果……唯一的办法,就是备足存好。我爸由此迷上了食物的保存之道,并将它当成事业做,当做学问来研讨。比如说我们家买米,家里明明只有三个人,一人一斤一天也就三斤量,可我们家的米柜子能藏下两个大人,柜里的米永远都是满的。我们的家乡盛产挂面,家乡的那条凯江河,沿岸的人家都会做一种细如银丝的手工挂面,随时随地都可以买到新鲜面。而挂面的制作人人皆知,需要放大量的盐,盐份重了不利保存,时间稍久就可能霉变。可我爸每次去买挂面,随便的一个理由,都可能买回一大堆。保存挂面就成了我爸的学术课题。他先将挂面用篮装好,放在家中的一只角落里,以为那地方阴凉干躁有利挂面存留,可没几天,面把的一头原本像脸蛋一样洁白细嫩的表面,长出了一层绿色霉斑。我爸一把一把细细看着,仿佛看着自己心爱的女人脸上长出的色斑,脸上的表情与其说是心痛,倒不如说是疑惑。眼下而言,挂面的事故并不能影响我爸的生活,即使挂面全部霉烂,我们家也还暂不致断粮。但我爸意识到问题严重。世事难料。命运无常。满世界的人都在为口粮奔波算计。眼下的自足不等于永远平顺。我爸有必要居安思危,高瞻远瞩。
我爸通过独自思考、与人探讨和向人请教等办法,正式折腾起挂面来。他先是用塑料布将挂面一层层包好,放在盛米的柜子上面。效果仍然不佳时,他瞄准了我们家的衣柜,把柜里的大部分衣物请出来,把挂面裹进厚厚的棉被里,再用绳子系牢。问题再度出现时,他打起了我妈的那口大皮箱的主意。我妈出身望族,家道中落,嫁给我爸时,她已经两手空空,只带来这口大皮箱。大皮箱终年上锁,放在爸妈住的里屋,用一道花布帘专门挡着,里面塞满了各样“宝贝”。闲暇之余,我妈最好的消遣,就是把皮箱打开,把里面的东西翻出来,叠一叠,摸一摸,再原封不动放回去。
我不是个长心眼的人。从小到大,我妈都骂我,有一半心思被狗吃了,成天拖三拉四,魂像尾巴一样拖在背后,而不是装在心里。但对我妈的皮箱,我还真动过心思,想看看里面到底锁着些什么。六月的一个上午,太阳如火,我妈抬出她那口大皮箱,爆晒在阳光下。我看着我妈一件件拿出里面所有的东西,再将箱子倒了个底朝天,用两张圆凳撑着,晒起箱底来。我终于有了机会一件不漏地看清我妈箱子里的宝贝时,这才有了顿悟:我妈那只永远锁着的箱子里,其实没什么宝贝,只有几件我爸妈稍好的毛料衣物和一张羊皮被褥,另有几样零星的、连我也看不上眼的东西,比如说,几粒铜钮扣,几朵大概是我妈姑娘时期用过的绢花,一只老掉牙的铜烟斗,一个长满霉斑的铜酒壶,如果有什么钿软,只能算那只最后现身的戒子,可那只戒子既没装盒子,也没套布袋,就那样赤裸裸躺在箱底的角落里,黄不黄黑不黑的,质地是什么看不清,能看清的是上面的一层明显的污垢。
原来我们家真正的“宝贝”,不是别的,就是我妈的那只大皮箱。我妈用布帘遮挡的,也不是别的,也是那口大皮箱。皮箱之所以成天上“锁”,不为别的,仅代表它的身份和它高贵的来历。是皮箱就得上锁,正如是好马就得配好鞍。至于皮箱里锁着些什么,实在已经不重要了。
那把挂在皮箱上的黄色铜锁,既代表皮箱的威严,也是我们家底气的象征。
既然皮箱里没什么紧要宝贝,那么锁衣服还是装挂面,已经无足轻重。我爸让我妈打开皮箱,以身作责,先把自己的衣服拿出来,再把我妈的衣服拿出来,那张羊皮褥子,我以为他也会搬出来,他搬了,却是铺开它,把已裹好塑料布的挂面一把把放上去,再将褥子裹严,放进箱,上锁。做这些时,我爸像裹着一个初生婴儿,脸上是少有的温存与柔情。我爸边做边解释:这是要防潮。羊皮褥防潮,皮箱也防潮。一层层潮防下去,我们家的中心就不再是那口大皮箱,而是皮箱里那些挂面宝贝。
结果还真奇了,用这种方式保存挂面,少则能存三个月,多则能存半年甚至一年时间。
4
我爸从保存挂面上受到鼓励,开始折腾所有食品的保存之道。最典型的是水果,而水果中,最具探索意义的,自然是柑桔类水果。
柑桔类水果成熟在冬天。而四川的冬天阴冷潮湿,心自然跟着寒冷。寒冷的心遇上水果,既使再馋再饿,也还是心存畏惧。勉强剖开一只橙或者桔,咬着牙塞嘴里,牙率先打颤,再到喉咙,胃,一路冷下,在心里结成冰。于是就有了梦想:这些美味的柑桔若能生在夏天该有多好!
我爸是一个生冷的梦想者。他的梦从来不缺,可他的心从来都如冬天的柑桔,即使再甜,也给人寒意。这一次,他几乎放弃了对于柑桔的个人态度,一门心思实施着这个梦想。他不再以消费者的味觉享受柑桔,而是像一个枝术专家那样,着力于柑桔的品相和口味。买时他一丝不苛,尝遍所有可供选择的品种。买定了,背回家,他对柑桔的口味再无兴趣,只在保存之道上下功夫。其实也没什么功夫可下。我爸没有保鲜剂也不放心将那些汤汤水水的化学物涂在柑桔上让我们吃,他能施展的空间很有限,只能依据保存挂面的经验,土法上马。而挂面干净利索,可以裹在皮褥里,橙或者桔肯定不行。再说皮箱里终年藏着挂面,柑桔类水果只能另辟蹊径。于是我们家衣柜的大部分空间,就成了柑桔的家。几床备用的棉絮,就成了柑桔永远的“床”。
定期,我爸会打开衣柜,将那些重如巨石的棉絮一床床抱出来,就像抱着自己怀孕的女人,小心地把它放去桌上,再打开棉絮,一只只检查那些水果。那些水果在棉絮里裹着,果真如胎儿置身母亲的子宫,一天天起着变化。只是胎儿的变化是奔向新生,越发的长大成形,柑桔的变化则是趋向死亡,越发的陈旧腐朽。每一次检查,我爸都会选出一些已在霉烂的水果,它们的表皮生着大小不等钢蹦样的绿斑,绿斑上再生一层白霉。我爸用手指轻按那些霉块,心疼和惋惜之意难以言表,让我有种清晰的错觉,即使我坏了烂了要死了,我爸也不会如此痛心。
我爸用一只筲箕装着那些正在变坏的水果,我和我妈就知道了,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得全力以赴吃掉这堆东西。于是在我们家,尽管我爸买回来的都是上等佳品,可我和我妈吃进嘴的,从没有一只好水果。而且我们对付水果的态度,从来都不是享用,而是在用杀手的狠劲干掉那些水果。
如此想来,我爸对水果的热爱,不在吃,而在于保存,不无道理。
如此想来,那天二姐和幺姐带来的那些水果,落入我爸手里后,就不可能有别的命运。那天我妈将脐橙从一只篮捡往另一只篮时,刚捡了几只,我爸就站起身,我妈便如接到某种指令似的,住了手,望着他,又挪开身子,主动让贤。我爸当仁不让,靠近前去,接替了我妈的活。
之后我妈和我都明白过来,我爸站起身,是不同意我妈的做法,单在腾挪水果时,他就要进入保存程序。他一只只查看着那些水果,眼神专注锐利,又不乏期待和柔软,仿佛在辨认失散多年的亲兄弟。偶有一只可疑的,便举了手,拿去灯光下映照,再放去一旁的筲箕里。我便歪着头想,那些筲箕里的水果,又该是我和我妈的任务了。
时间没完没了地沉默。我已经差不多厌烦至极。我已经看过幺姐无数次了,想示意她,跟我走,去我的房间,我们自己玩。幺姐已明了我的意思,但她只是笑,不回应,或者干脆不看我,只看着我爸。我了解此时幺姐的心思,她是绝不会跟我走,拂了大家的意,尤其是拂了我爸的意。她的懂事和忍耐让我恼火,可奇怪的是,我却从不曾因此烦过她,怨过她,相反总觉得她活得太费力,太委屈,反对她生出一种怜惜般的依恋来。
我厌烦的是我爸。我已经不明白为什么家里的人如此乏味,为什么家里的日子如此无趣,而我又无从选择,只能无趣地跟着他们活下去。
就在我在一只独凳上百无聊赖,就要崩溃时,事情有了转机,我爸的手里握着的,不再是一只脐橙,而是一只牛皮信封。
那时候的牛皮信封不装钱。整个社会还没有多余的钱塞进信封。那时候我爸妈的工资,也就是几张十元的票子。十元的票子又小又窄,多数的人家,那票子还在工资册上就已派完了用场。那时候更没有送红包一说,因此我爸在看见牛皮信封时,即使他再看重钱财,也不可能去想是二姐和幺姐给他送钱来了。
这就让我爸困惑不已。
我爸手捏牛皮信封,眉头紧蹙,一改先前的从容自得,仿佛遇到了一件不明飞行物正落到手上。我妈和我都坐不住了,又深知我爸的德性,越是关键的时刻,我们的好心越容易被他当成驴肝肺。我妈靠上去,手如一把上膛的枪紧缩在袖管里,随时准备着出击。我则干脆站起来,少有地靠近前去,伸长了脖子。
我爸不看我妈,瞪一眼我,那意思是,走远点,这儿没你的事。
我一阵恼火,几乎就要扭过身,坐回我的位置,或者干脆扔下幺姐,冲回房间去。
这时二姐说话了。二姐说,这是大姐夫从上海回来,带回来一条红纱巾,送给妹儿的。
红纱巾?我想。
但我想不出所以然来。只隐约记起,确实听幺姐说起过,在她的上面,有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她们个个都已成人,像断线的珍珠散落各地,并不时常见面。二姐是例外,就嫁在同一条街上,隔着几间铺子。日子也如出嫁前一样,窘迫而辛苦。今天,她是代表幺姐的家长来我们家送礼。而她的大姐,听幺姐说,大得足以做她的阿姨,嫁去了上海,于是她们的大姐夫,成为大上海的代名词,他们家所有物质的荣光和精神的优越,都源于大姐夫。只是大上海太远,远水难解近渴,他们家的日子仍然艰辛。
然而大上海突然飘到眼前,还带来了红纱巾,还是送给我的,仅这一条,就足以让我晕头转向。
那时节,我们被浸泡在一堆灰黑里几近窒息。也曾有过例外,那就是红色:红旗、红领巾、红袖章……但在我懵懂的意识里,那些红色是算不得颜色的,甚至因为背负的内容太重,比灰黑更生冷,更让我生畏。
可我依稀知道大上海。甚至也知道这世界还有着纱巾之类虚无飘渺的物件。那都是从偶尔所得的糖果纸,小人书,或者从几部零星的电影里看来的。这些事物美得虚幻,美得心疼,明明知道是好东西,却因为隔得太远,够不着,不愿意把它当真,于是它真成了梦,在心的某一个荒岛上飘着,几近于无。
此时这梦中之物突然到了眼前。我惊得不轻。慌乱得仿佛周身着了火。但我仍然记住了,二姐说的,是特意送给我的。
我的手心脏一般在我的另一只手上跳着。我按住它。用它们互相按住。我得管住我的手。我得冷静。我不能惹恼了我爸。这时候,最好让他平静地,像接受这些脐橙那样,接受了这件礼物,再转手给我。
我甚至暗暗希望,我爸并不明白这是什么好东西。这种既不能遮风,又不能挡雨,更不能当饭吃的玩艺,比起他那些挂面脐橙来,根本就一钱不值。
我看见我爸,几根惨白的手指进了信封,几根惨白的手指又出来了,那手指真白,就如剥了皮的葱蒜,又比葱蒜更硬更直,就像一把竹筷,竹筷的后面,一缕红霞般的云朵,跟了出来。
5
那纱巾后来究竟是什么样,我已经记不真切。我只记得我爸将它拉出信封时,我的心停止了跳动。我的手,我的手见了那片红云,突然生出了翅膀,以飞蛾扑火般的疯狂扑上去,却被挡在了途中。
后来我总是想,可不能小看了这些大人。尤其是我爸这种不动声色的男人。他们看上去呆板,沉闷,对世界无动于衷,可他们就像如来佛的手掌一般法力无边,啥事也逃不脱他们的法眼。我原以为我爸对纱巾之类的物件既无认知,也不屑于上心,谁知那纱巾刚出信封,我,他,还有我妈,我们都被怔住了。我们的生活看似平稳,周全,还略有富余,几乎看不出任何缺失,可这条纱巾的突然闯入,让我们同时意识到另一种存在,另一种不遮风不挡雨也不能当饭吃,却能将人击中,让人顿时飘上天堂或坠入深渊的另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可有可无。长久以来,已被作为负担减掉,被作为病毒删除掉了。如今它卷土重来,重新登上了台面,我们顿时无所适从,哑口无言。
我毕竟年幼无知,本能比大脑反应更快。我的手先于我的大脑伸出去,被我爸铁棍般的手臂挡住了。我爸收回手臂,用他那竹筷般的手指拈起那道红云,抖开来,散成一片。我的眼前腾起一个世界:我看见自己系着那条红纱巾,揣着满满的心事,在轻纱,在薄雾间,在潺潺的流水和高高的白云之间,像身边的杨柳那样垂着头,扭着腰,缓缓地走……
那纱巾无风自动地飞向我。我接住它,感觉自己也变成了风。同时接住它的还有我妈和二姐幺姐——当那片轻纱般的世界确凿出现时,作为女人,我们谁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我爸什么时候松了手我已全然无知。我们围拢在一起,四十根手指汇成海洋,要吞没那片云朵,那些风。我们轻轻怯怯地搓揉,抚摸,仿佛它是婴儿,鲜嫩新奇如刚刚来世,每一寸肌肤都是新的生命。我们轮番着抚遍了它的每一只角,每一道孔,手指间留存着既如沙粒,又如凝脂般粗糙滑腻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纱巾是谁发明的。源于什么样的灵感触动这世界有了纱巾?那些繁复细微的孔,那一缕缕几近无形的纱,那些织它出来的金梭和银针……据说当时的纱巾,用料并不讲究,多是些化纤或尼龙质地,然而一种梦想,一种对世界的虚无的认知和对美的认同,催生出这样的尤物,于是沙砾变成了凝脂,实物织成了梦幻,一览无余的世界,被蒙上了一层薄纱。
我对它的感觉已不可能再用“喜欢”一词去表达。它就是摄魂之物。它就是我的魂。瞬间已将我脱胎换骨。同时我还发现,不光我,就是这纱巾的原主人,二姐和幺姐,她们也未必不是同样的感觉。很显然,在家时,她们也未必看过它,即使看过,在那个一心一意挣取食物、对付生存的环境里,这种物质的出现,多半会一晃而过,留不下任何印迹。
而此时,同样的一方纱巾,在四个女人目光的注视下,还了它本来面目:它不仅仅是礼物,它是被长久遗忘了的另一个世界。它就是美的化身。
而美是女人的命门。
就连我妈,尽管她已被岁月淘洗得温和从容,无惊无喜,此时她站在那方纱巾前,伸出手指抚摸着纱巾,那手指也是轻微的,仿佛受了惊吓,指间微微有些颤抖。
我妈用颤抖着的手指扯过纱巾,那片红云再度飘飞。我妈接住它,对折成三角形,再细细地折成长条,向我的脖子靠来。我闭上眼,再睁开,那些云霞和雾霭已绕在了我的脖子上,再在我的胸中系成了一只蝴蝶结。
我腾云驾雾去到里屋,站在衣柜的穿衣镜前。
我从里屋回到客厅时,我妈的目光接住了我。我看见她的眼里还有波光闪动,看上去很像泪花。我妈她一定认为我美。女儿的美就是我妈的从前,也是我妈的骄傲。在美的面前,我们互为彼此,也达成了从未有过的理解和默契。
我去看幺姐。此时的我多么爱她。我接住了她软软柔柔的目光,目光里没有艳羡,只有欣慰和宁静。我想扑过去,紧紧拥抱着她,对她说,我喜欢死你了。
就在我向幺姐靠去想和她抱成一团时,我爸说话了。我被我爸逮回现实。好长时间了,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我已经以为这世界没有他,只有我妈、幺姐和纱巾,只有这轻的柔的色彩斑斓的世界。
我爸说,好了,行了。
似乎仍觉不够。又说,够了。
我停住。梦醒一般看着他。
我爸见我恍惚,加重了语气:
戴一下就够了,取下来。
我像机器人接到指令那样取下我的红纱巾。
还没等它彻底从我的脖子上绕下来,我爸已伸出那只大手,一把扯过去。那一刻,我发现,我爸的手奇大无比,像一把钢钯,把整个世界顿时钯光。我看着我爸将那方大如天幕的红纱巾叠起来,叠起来,直到叠成了一只火柴盒;再看着世界黯淡,熄灭,沉寂。风没了。云没了。水花和浪涛都没了。世界重新死去。只留下那堆脐橙,像只只撑饱的肚皮,在我家的桌上打盹。
6
后来,后来就不用说了。我爸将那条红纱巾,收拾好,重新塞进了牛皮信封。我爸边塞边说,这东西,好是好,可它不适合现在的妹儿用。她现在的心思,要放在学习上,这些东西戴了,会分散她的心思。
我爸一点不在乎他这样做,二姐和幺姐会作何感想。在活着的问题上,他向来经纬分明,对积攒食物和清除精神烦扰有着同样的热情,甚至不惜以此热情,对抗整个世界。
他就是真理,就是整个世界。我们没有谁敢与他对抗。
我爸之后宣布了他对红纱巾做出的最后决定:
把它收起来,待有一天妹儿长大了,再拿出来,给她用。
我爸伸出手,向我妈要来钥匙——那只大皮箱的钥匙,那只存放过我祖外婆、外婆的钿软,存放过我妈的戒子和我爸的衣物,如今正存着大堆挂面的皮箱的钥匙,然后他站起身,进了里屋。
我听见布帘子低泣般的呻吟,我听见铜锁怕冷似的颤抖,我听见皮箱盖撕裂般的疼痛,我听见红纱巾沉入深渊前,无声的呼救……
奇怪的是,那天晚上,我并没有伤心到失眠的份上。我甚至没感到伤心,只觉疲惫,身体像抽掉了筋骨一般绵软发皱。幺姐和二姐走后,我拖着步子进屋,倒头就睡。
第二日,日子重新复原。
初二下学期时,我以考高中为名,读了住校,离开了我爸和他的老虎。初三时,却发生了一件我自己也感到诧异的事:同样以考高中为名,我剪掉了自己的长发,留起了不分男女的刺猬头。这种发型后来已成为我的符号,我在人群中的标志,伴随我战题海,背单词,上考场;伴随我在日复一日的阳光、阴雨、冷风、霜冻中蹉跎,直到成人。
我已主动将自己调成了静音,褪成了黑白照。
我再也没有向我爸或者我妈提起过那条红纱巾。我爸和我妈大体也忘记了此事。但我没有忘记。仍会在日子的某些缝隙里,想起它。想起它时,我仿佛看见一只火狐,一个美丽的肥皂泡,耀眼而虚空,既使你用手握着,仍明白它是幻影。
毫无疑问,我成为我爸所愿的好学生,考上了高中大学,一路平坦,顺利抵达至成家立业结婚生子的成人世界。
直到我爸去世。我们家的老屋要连根拔了。我妈那时已头发白尽。她佝偻着身子,钻进那道布帘,打开了那口大皮箱。我木然地坐在客厅,我爸的那只老虎上。我爸已去,老虎也上了年纪,我已经无所惧怕,只隐约觉察着自己正在衰老。
老半天,我妈出来,树皮样的手里,握着那枚钥匙。我妈说,这钥匙给你,这只皮箱,你把它搬去你那里。
我眼皮不抬地嗯着,接过钥匙。我妈伸出了另一只手,给,拿去。我妈说。
我再接,仍然没抬眼皮。手指伸进牛皮信封,触到了一种粗糙的,滑腻的,如沙粒又如凝脂般的物质。
恍惚算,已经三十年过去。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