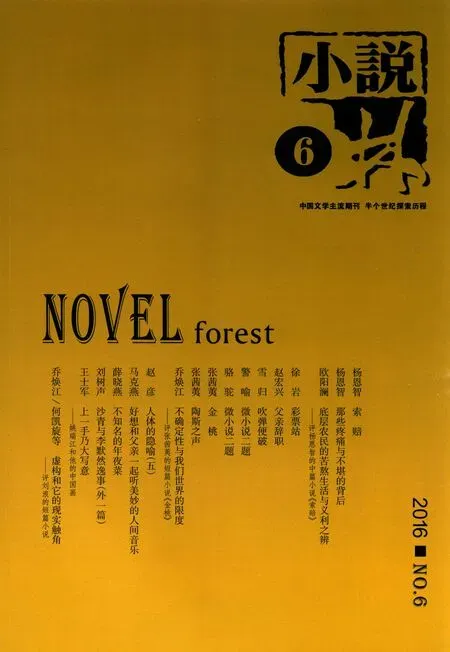人体的隐喻(五)
◎赵彦
人体的隐喻(五)
◎赵彦
肠
1
肠是一个过程。
它的线性造型注定要成为一段里程。如果说胃是个站台,肠就是铁轨,路,和一切在路上的事物。是肠让食物有了一段费时的光阴,在肚子那样小的一个空间里,肠硬是牺牲自己制造出一段崎岖的长征来,它折叠起自己,把自己变弯,变成曲线,在人体里盘成一段长于人体身高5-6倍的长度,以便能够更久地留住食物好好消化它们。可以说,是肠给我们制造了曲折,制造了慢,制造了回味。
我们会大大方方地提起胃、肝、心脏,却很少会提起肠,因为肠里面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该称呼,是食物还是粪便?如果是后者,我们在某些场合提及这个词便会有失礼节。肠不像其他的器官,例如肛门,会让人直接想到污秽和淫秽,肠有轻微的污秽,人们较少地提起它,而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器官,中性,缄默,有用,也很少用肠去修辞其他的事物。肠,通过这一点保持了它词语的纯洁性。
胃在消化这件事上过度高调,它让我们觉得似乎消化这个功能都由它来承担,实际上它只是一架研磨机器,一个中间环节,只能消化一些蛋白质,肠才是人体最终的消化和吸收器官。肠通过豢养数以亿计的细菌家丁(400多个种群)来对由胃消化不了的食物进行再次消化,如脂肪、淀粉之类的。肠子借助它的胰脂肪酶来消化脂肪,将其变成脂肪酸和甘油吸收入血;淀粉由其胰淀粉酶来转化成单糖,包括葡萄糖和果糖等,最后被吸收入血。也就是说,血液有一大半成分是从肠子里输送过去的。但肠的确是我们身体里最为污浊的车间,它乱糟糟的,还产生屁,所以我们的身体尽可能地让它位于下部,它深藏起肠,不让它发出声音,也不让我们闻到它的气味,在身体外面,我们摸不到它。
2
肠是生物体内最为基础的器官。腔肠动物就是这样一个极端的例案:为了让身体轻便和简约,它们舍弃了其他器官唯独保留了肠子,甚至不惜将自己变成肠子的模样,如蛔虫,它的身体只有一个开口和一个出口,看上去就像是从高等动物身上截取的一段肠子。从环节动物开始,肠管才开始有了肌层,肠管各部分的形态和功能开始不断地分化,直至到了脊椎动物,消化器官终于有了如下几种形式而不仅仅是肠:口腔、咽、食管、嗉囊、砂囊、胃、肠和直肠。也就是说,食管、咽喉、胃、肝、肾、肛门都是肠进化的产物。如今,人类的进化已经可以将肠视作次要的器官了,一个失去肠子的人,若其他器官功能健全的话,还能活上五六年。
古人认为人体内最重要的内脏是心和肠,心用来思考,肠用来消化,所以有“懒心无肠”这个成语。心和肠是人体最重要的内存,要是没有它们,人就是一具空皮囊。一个头脑简单、不会关心别人、做什么都不上心的人就是一个“懒心无肠”的人。而“肠子悔青了”是指一个人在极度后悔时,肠子会发黑变质。古人又认为肠还能思考。
3
中国古代一种叫做“挂肠”的酷刑。其刑罚极其残忍:施刑者在一根横木上绑上一根绳子,并将横木高挂在一个木架子上。这个木架子木杆的一端置有一个铁钩,另一端挂着一个大石块,就如一杆巨大的秤。行刑时,施刑者将铁钩放下来塞入犯人的肛门,将犯人大肠头拉出来挂在铁钩上,然后往下拉另一端的石块,这样,当铁钩的一端升起,犯人的肠子就被抽出来,并高悬挂成一条直线。如此,犯人不一会儿就气绝身亡。
脾
脾是永远的配角。我们把脾视作一个次要的器官,并在很多时候忽略它,同时我们还以为脾是“脾气”的“脾”,它有可能都没有实体,至多是一个情绪发射器,就像房间里用来控制湿度喷雾的那架小机械。它谦卑,幽闭,淡泊,低调,高度自治。仿佛只是来人体里占一个空间,并不发挥作用。它也不像胃那样一天三次地犯“作”,更不像肺那样无时无刻不让你操劳——为了肺,你得让嘴巴和鼻子同时工作,至少得让其中一个呆在岗位上。
我们对脾的无知得自于它与死亡的关系的疏离,它很少会患上让你致命的疾病。脾的主要功能是参与人体的免疫反应,吞噬和清除人体里衰老的红细胞、细菌和异物,同时产生淋巴细胞及单核细胞,并将其贮存在血液中。脾脏在人类胚胎期就是一个重要的造血器官,出生后则可以为我们制造淋巴细胞和单核细胞。不过,这一系列作用和功能似乎仍无法让我们明白,因为我们的肉眼无法看到淋巴、单核细胞和细菌。对于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就像站在山巅的观光客,只能看到人体的海面,看不到人体中具体的波涛,看不到软弱的海藻,看不到慵懒的海星,看不到巨大的鲸,看不到海下面的杀戮和海床的挣扎。正因为这样的原因,脾在人体里就像一个朴实的网管,一个闷头闷脑的IT男。与脾相比,胃、肺和心脏几乎是搬砖的体力劳力者,它们的工作具体而辛苦,而脾,则只是几十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它盯着远处,沉默地运算着那些最为微观的程序。
脾,更像一个隐居者。
肺
肺的存在,使我们的身体变得对空气上瘾。要是五分钟内不吸入新鲜空气,我们的身体就会全线罢工。肺首先对空气予以确认,肺使我们知道,在看得见的世界之外,另有一个比可见世界更大的宇宙,那些似乎融化在光线中,没有方向,没有质量,也没有气味的东西,是一种更为重要的存在。这种存在以一种似乎是静止的形式将我们松松地包裹着,我们在它里面感觉不到,只有离开了它,我们才知道危险来临。这种存在,也即空气,就是这样随随便便地制造出了光线,制造出了雨,制造了我们,也制造出了死亡。而肺是唯一能够指认出它的人体器官。肺通过嘴巴、鼻子、气管把它纳入自己的叶片中,把空气中最重要的物质——氧留下,将二氧化碳送出去。这个过程,每分钟发生六七十次。
肺可以说是我们体内最为忙碌的器官,它和心脏一样,无时无刻不在工作,它使我们身体里那些大大小小的空隙布满空气,同时又不至于多到暴胀,因此它每次都做一组相反的动作,吸进和呼出,从不出差错,也从不过度。它的呼和吸衔接如此紧凑,就像歌声和它的回音那样,在肺这两块小小的肉上发生。在这两个运动之后,我们的血液里充满了氧分子,这些氧分子与血管里的葡萄糖结合(氧化)后,为身体提供了大量我们必需的生物能和热能。要是没有肺,我们不知道空气竟是一种成分复杂的重要的合成物。我们看上去的世界是那样的透明,透明到我们以为只有固体才是重要的存在,液体也可以通过它能被弄皱,被蒸发,被消失而让我们感知到,但是气体没有影子,没有触感,却处处存在,它的存在比任何固体和液体都强大——空间,整个使银河系膨胀和变大的东西,其实就是气体。这一切都是肺让我们知道的。所以肺不止是我们用以认识事物的工具,它自身就是需要我们认知的知识。肺柔软,硕大,扁平,两张朝左右张开的肺叶上布满了像海绵一样的小气孔,肺位于人体内脏的最上端,就像一把遮阳伞,将下面的器官牢牢遮住(因此古人称它为“华盖”)。肺可以说是我们长在身体里的叶子,就像叶子作为植物的呼吸器官一样,肺在身体里给我们提供与外界的最为重要的接触和交换。
也可以这样说,肺是我们身体中最为信赖外界的器官,它敏感,紧张,安静,知性,它以触角朝内的方式去感知外界,它与外界的联系建立在每分钟六七十次的痉挛之中,每一次痉挛,都是一次重要的化学过程——它凝视并分离了那些氧气、氮气、氩气、氦气、氖气、氙气、氡气、二氧化碳,而这些关于分子的知识我们需要进化上千万年才能掌握。肺的敏感就在于此,它对事物的把握是鞭辟入里的,它不把空气视作一个整体,而是一些成分,成员,组成,结构。通过这种方式来得到事物,使我们受益更多。
所以在身体中,肺是最为文艺的器官,它如此需要外面的世界,却又羞怯地藏匿自己,它深知自己吸到的每一口空气都是旧的——这些被我们称作新鲜空气的空气不知有多少次在别人的嘴巴和肺中循环过,也在自己的肺里轮回过,它带着他人的气息,带着口臭,带着被言语污染过的体重,一次次地进入我们的身体,进入肺的表面,而我们浑然不觉。我们总是觉得这一口与下一口不同,我们觉得时间会洗去空气旧的表面,当它进入我们的身体时,会唤起我们新的活力。那些不过是改头换面的氧分子进入我们的血液后,让我们的血重新在血管里奔跑起来。事实上,与肺有关的疾病,例如肺结核,也是最文艺的,因为它最青睐作家和艺术家。那些患上肺病的人通常都脸膛彤红,热情洋溢,非常适合将创作需要的灵感唤起,在他们亢奋的视觉中,世界的每一部分都是缪斯洁白的肢体,他们拥抱它就像情人们沉沦在对方的怀抱之中。肺病是一种热情病和灵魂病,拜伦、济慈、福楼拜、契诃夫、普鲁斯特、卡夫卡、劳伦斯,鲁迅、萧红、郁达夫,巴金、丁玲、林徽因,这些大作家都曾得过肺病或死于肺病。他们的作品是身体废墟上开出的妖娆之花,肺病作为其中的肥料,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痛苦和激情,而痛苦与激情正是附着在作品这颗种子上的两片对立的果肉。一方面病人的肉体正在变成灰烬,另一方面,在他们的心中,滚烫的火苗舔着语词的轮廓,舔着句子,并将它们送出体外。肺病成了丰产和亢奋的隐喻。
注意啊,这不完美在我们体内
如此热辣,所以欢乐,在这苦痛里
栖身于有缺陷的词,和坚决的声音
(叶芝《一部戏里的两首歌》)
乳房
1
乳房,主要指女性乳房,它在功能性上令人尴尬:既是婴儿的厨房,又是男人倾慕的性器官。这种双重功能性,使得圣洁与淫逸就像一朵并蒂莲开放在它粉色的塔状肉体上。
乳房形象乏味,就像我们胸部突起的两个肿块,肿块的顶端各有一个小小的深色的蒂结,好像愈合的伤口,亦如包子上的收口,告知人们下面有着无穷无尽的美味;这个人体配件要是到了男人身上,就变成了两块不给予、不诱惑的浮雕,它们扁平,小巧,乳蒂与乳晕之间的紧凑使其具有微弱的美学上的价值,但在功能上却完全是暗哑的,是一段没有人有兴趣去阅读的盲文。
乳房得到那么多赞美与它的造型没有任何关系,只因赞美它的人的身份的特殊性:对母爱耿耿于怀的孩子和耽于女色向来拥有最大话语权的男人。前者出于饥饿,后者出于性欲。乳房对两者都笑纳了。当人们不方便直接称赞下半身的性器官时,乳房往往成为一个缓冲器。几乎所有被赞美的乳房都知道,之所以被人们欣赏,是因为人们在表达欲望时有着一种声东击西的习性。
在性这件事上,男人基本上是一个顾客。女人提供场地,提供服务,最后还提供果实。男人则是个纯粹的消费者。男人的身体几乎没有什么婉约的可供欣赏的部件,除了乳房——那段阅读起来显得有点乏味的盲文和单调的浮雕。男人的乳房作为一个服务对象缺少变化,没有乳汁可以奉献,在身体的风景中,它仅仅是个平乏的路标,指示着人们从提供思考的大脑到提供快感的性器之间只有这么一截短路径,这段短途不能让男人们充分犹疑,所以常犯错——栽在男女关系上的男性不计其数。女性的乳房高耸、骄傲、有着富有营养的内存,它向上生长的立体状本身就具有一种生命的体积感、延伸感和崇高感,它还模拟人类的成长过程:年幼时,它是两枚小小蕴积的核;发育后,它显得饱满、挺拔,并且提供奉献;年老时,它懂得真正的重心所在,不再张扬跋扈,它低到尘土里,只为在脚下寻觅那生命真正的意义。
2
在人类各种器官和部件中,乳房并非一个深刻的成员,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器官:它只有在青壮年时才派上用场,大部分时间只是一件被闲置的装饰物。人们轻视某些身体行为是因为它们具有重复性,例如吃和性交,乳房恰恰是两者的供应商。大脑所提供的思考具有最高的地位最被人们珍视,因为思考每一次都不一样,每一次都会抚过不同的词汇,抚过不同的元音、辅音,抚过感叹句、叙述句、疑问句,抚过语法,抚过句号和问号,每次都可以为身体形成一个新的行为和产生新的运动。但是吃和性交却只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它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直至死亡。乳房的次要性和非深刻性还在于:它有两只,一对,可以互相取代。人的身体器官有很多是单数的、唯一的,但也有很多是双数的:眼睛、耳朵、眉毛、鼻孔、肾、睾丸、手、脚。在其他许多器官苛求精减原则,却在眼睛和乳房等上面造成重复和浪费有身体自己的寓意:人们不仅需要自己,需要单个独立的自我;也需要相反的自己,需要对照物,需要补充,需要反面。
3
作为性器官系统里的一员,乳房的形象最为贞洁:第一,它位于上半身,离大脑位置较近,较靠近精神;第二,它与哺育和孩子有关,也就是说与未来相关。第三,它没有淫冶的内部可以让人窥视。乳房也因为它的“贞洁”而在中国传统的性文化里几无立锥之地。中国古代文献中很少有描写它的。在最为人赞颂的古典名著《红楼梦》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描绘女性乳房的句子,甚至在《金瓶梅》《肉蒲团》《玉房秘诀》这样一些声名狼藉的情色小说中乳房的描绘也几乎是空白的。《绣榻野史》漫不经心地提到过,但只有“两个奶头,又光又滑”之类的乏味句子。到了清代,人们似乎意识到了乳房之美,开始在诗歌中半遮半掩地赞美它。与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样,在现实的性活动中中国男性也更倾慕于女性其他部位甚过乳房。如腰和脚,尤其是脚。在男人们看来,女性的三寸金莲不仅是她们性器官的外化形象,裹过小脚的女性还因为行走困难常刺激阴道附近的肌肉,阴道更为紧窄,性交时可让他们得到更多的快感。于是,把玩女性的小脚,而不是乳房,成了中国特色的性文化(花样竟多达四十八种)。而女性的乳房更事关食物,它们远离性器官,又常被厚实的衣物所蒙蔽,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崇尚多子多福,女人的乳房几乎大半生都被新生儿叼着,男人几乎没有机会拨开他们去欣赏它们。
在巴西,乳房也攸关社会地位而非性快感。在巴西上层阶级家庭里,女孩一过十五岁就会被家人送去做割乳手术,因为这个手术可将她们与大奶头的下层妇女区分开来。在欧美国家,乳房则是社会生活的一切隐喻。据玛丽莲·亚隆(Marilyn Yalon)1997年出版的《乳房的历史》,乳房不仅事关性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也具有不同的地位和意义: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与诗人为乳房涂上情色意象,乳房在那个时候是艺术:18世纪欧洲思想家将乳房打造成公民权利的来源,乳房在那个时候是政治;到了近现代,乳房被经济社会绑架,这个时候它是商业。从古至今天,男人与社会都在乳房上大做文章,不断地将女性的乳房据为己有。而所有关于乳房的隐喻都是经过男性眼光折射之后的想法。
可以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女人都从未占有过自己的乳房。女性乳房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只为孩子和男人服务,它以厨房和卧室交集的方式存在在女人身体上,最后却只用疾病来折磨它身后的主人——平均每八个女性就有一个死于乳腺癌。乳腺癌,用患过乳腺癌的桑塔格的比喻来说,本质上就是一种增殖病——癌细胞的自我复制和出生,这对于增殖过人类、哺乳过自己后代的乳房来说是不啻为一个恶意的报复。如今,乳房又为社会增殖财富添砖加瓦,乳罩的发明、乳房的整形手术、乳房疾病的治疗,使得它哺育了一个又一个繁荣新兴的产业。
但乳房从未哺育过女性自己。
在女性乳房高耸的山峦上,跳跃着交媾、生殖、财富和文明的火苗,在山峦之下,却是一片无尽的投向自己的阴影。
赵彦,1974年3月出生,发表中短篇小说及随笔若干,现居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