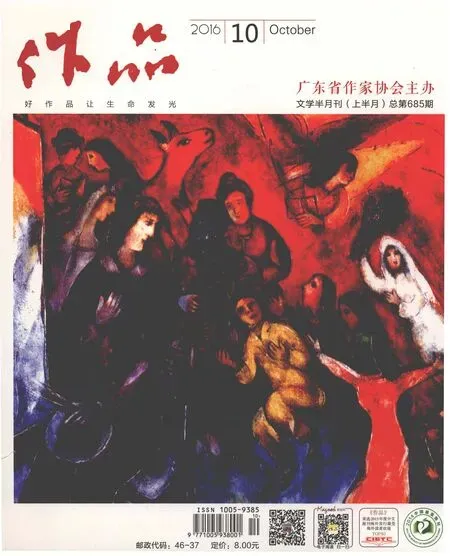铸 鼎
文/林为攀
铸 鼎
文/林为攀
林为攀林为攀,生于1990年,福建龙岩人,青年作家,编剧,作品曾发表于《作品》《 山东文学》《 大家》《 文艺风赏》 台湾《时报》人间副刊《 青年文学》《 萌芽》等;中短篇集《当一朵云撞见一张纸》将于近期面世;长篇小说《追随他的记忆》将于11月面世。
在一个名为“小说家”的微信群里,活跃着大概30位90小说家。他们平时聊八卦、聊小说、聊生活,不亦乐乎。通常,聊着聊着,就有人突然“失联”,而隔半天或一夜后,那个“失联”的人则会冷不丁晒出一篇小说来——据说是此前聊天的某个点,激发了其创作灵感。在那些“失联”事件中,林为攀次数排榜首。在其带动下,有一段时间,群里一度掀起了以大家笔名命名的小说创作热潮,而《鬼鱼》也有幸荣登风云榜,颇受好评。赘述诸多,我试图表达的是,有趣的小说往往是在不经意间玩出来的,《铸鼎》便是如此。该文是难得的不以人物为主角的小说,通过一只鼎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到精神属性的经纬推演,折射出了马斯洛需求理论的人类普遍性。读此文,有人看到历史,有人看到民族,有人看到战争,有人看到权力,还有人看到欲望,然而,我想陈述的是:陈希我先生曾将小说分为四个层次,为生活,为艺术,为思想,为精神,而他同乡林为攀的《铸鼎》,恰恰就是难得的见精神的小说。
——鬼鱼
我在地下睡了很长时间。
一般只有死人才会长眠地下。我不是死人,却和死人睡在地下的时间一样长,可以说,我跟死人没什么两样。但死人一般有活人追忆祭奠,而我却早已被世人遗忘,从这点来说,我不及死人。可话又说回来了,死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和花草树木一样,不会思考,更不会说话,而我不仅能思考,还能记起自己的故乡,所以我又比死人强。
在我睡着的这段时间,我经常做梦。我突然发现纠缠我的梦境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个世界。我一般都在白天合眼,晚上睁眼。很多人认为地下是不分白天黑夜的。但在我看来,地下是昼夜最为分明的地方,只要在地下听到鸡啼,我就能知道太阳出来了,而月亮升起的预兆一般是犬吠。所以,这么多年来,我凭借着鸡啼犬吠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白天黑夜。
不过,这个情况不久之后就出现了变化。那天,我听见了两阵鸡啼,即在同一天里出现了两个白昼,而本该到来的黑夜却无故消失了,这两阵鸡啼的间隔时间刚好跨越了一个白天。正当我准备睁开眼时,发现天又亮了,我刚睡醒又要继续入睡,就像我出土后经常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倒时差一样。我感到很奇怪,以为自己听错了。这不是没有可能,我呆在地下的时间太长了,耳朵难免不出毛病,即使没有问题,也难保没有层积的淤泥、动物骸骨和一些矿物质堵塞我的耳朵。
层积的淤泥在我出土后,我发现它们竟能驱动运载我的那个庞然大物。这个怪物长有四个不停滚动的圆圈,驾驶它的人在我看来和地下那些动物骸骨的轮廓几近相似,而由那些矿物质打磨的装饰品也挂在他的脖子上,戴在他的无名指上,比夕阳的余晖还灿烂。
我掏了掏耳朵,发现自己没听错。确实又是一阵鸡啼。过了很久,我发现出毛病的不是我的耳朵,而是地上的世界。地上的人嫌白昼太短了,人为制造了很多会发光的物体,当这些发光物在黑夜到来之后集体发射出恍如白昼的光芒时,让那些本该进巢做梦的鸡不禁以为天又亮了,只好强打起精神,对着并未泛出鱼肚白的东方引颈高歌。
这倒让我想起了以前遇到过的一些怪事。还是在地下——是不是在同一个地下我就不得而知了,我总觉得地下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漂移,我现在说不定距离当初入土的地方隔了十万八千里也说不定——我突然感觉头上被类似于房屋倒塌的巨响砸了一下。我好像包在茧中的虫子一样,遭遇了来自外界的重击,好在这层茧足够坚实,并未让我受到丝毫伤害。我被吓得不轻,以为自己又被人举过顶然后重重地砸在了地上,把地面砸出了一个凹坑,还崴了自己的脚,经过很多锻铜匠的精心修补,才得以恢复原貌。
我从一口突然移到身旁的井里往上看,发现很多马车在运载着修建宫殿所需的大理石,而这些大理石都来自高山,或者连鸟兽都很难征服的悬崖。这些民夫就靠一双长满老茧的双手和那个充满韧劲的肩膀,将这些大理石肩扛手提,运到山脚下停着的马车上。这些马车浩浩荡荡地把大理石运到王朝的都城,建造起一座座巍峨的宫殿。但一般不要多久,这些宫殿又会毁于下一次战乱中,新的统治者又会征万民,运巨石,重建毁于战火的宫殿。
有一个年迈的民夫经过井口旁时,体力不支,不小心将巨石砸在了井边,就是这声突兀的巨响让我此后经常做梦。他试了好几次,欲重新背起这块足足有百斤重的石头,却无奈地发现自己再也扛不动了。他和巨石一样也砸在了井边。在他断气之前,他把头凑到了井口,让我得以窥见他那张饱经磨难的脸。这张脸除了那双还会转动的眼球,其余的部位都僵化了,就如罗盘一样,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皱纹。他想喝一口水,但井底离他太远了。他够不着。他最后永远地倒在了地上,我看到他挂在井边的那张脸,很快被虫蚁蛀空,不久显现出镂空的骷髅,他身上的衣服也随着四季的更迭,变得比风还碎,比水还稀。
可以说,这样奇怪的事我经历得不少。有时候我会想,要是我会说话就好了,那我就可以让这些人类,让这些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少干点愚蠢的事,多做一些明智的事。至于何谓愚蠢之事,何谓明智之事,倘有和我活得一样长的人应该能分清楚。但人类的寿命一般始于混沌之时,终于明事之前,即是说,人类的寿命长度不足以让他们明晰事理。我觉得只有周而复始的太阳和月亮有这个本事,但它们每天都悬挂于天际,从来不愿意屈尊降到人间,把这些道理告诉世人。
看到这个可怜的民夫,让我想起了我诞生的那天。我由来自首山的铜制作而成,首山在今天的河南境内,因为八百里伏牛之首,故得名首山,我最后成型也是在同为河南境内的荆山之下。当时采铜的民夫可不比这些运巨石的民夫少多少,至于冶炼锻造我的人更是不计其数,换言之,我的诞生其实比建造宫殿所耗费的人力还多。想到这,我的心里涌现出一股难以名状的羞愧之情。我刚开始的作用是拿来炼丹,但凡对历史有过了解的人都知道,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帝王都有过长生的夙愿,打造我的黄帝有之,嬴政有之,就连号称千古一帝的李世民亦有之,更不用说后世那些不安帝王本分,只懂享乐的糊涂君王了。
当我重见天日被运载到那个有四个圆圈的怪物身上之后,很多人都对我紧实的皮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不相信几千年前即有如此铸鼎工艺。他们按照残缺的典籍上的记载,企图一比一还原另一个我,但美观及坚固程度都不及我分毫。我知道,从那时起,只有我自己才能知道我,只有我能说清我是由哪些材料构成,又是由何样火候淬炼而成。
要打造一个和我差不多的鼎,首先是铸模透气,这样才可以防止青铜冷热变化时收缩开裂,同时有助于空气排出,让器物表面更平整光滑。其次是刻字——说实话,我出土后已经认不到所见的那些字了。我被放在一个四面透明的玻璃柜里,外面贴的说明书,虽然看似和我所处时代的笔迹一样,但仔细看,还是有所差别的,甚至有的意思完全弄反了,这些不说也罢——在泥范上可直接刻字,铸成后文字笔锋清晰,甚至能铸出现代工艺也无法铸造的字画、镂空画、高浮雕等效果。然后是合模,必须保证上下两部分严丝合缝,半毫米的误差都会让鼎身上的字和花纹错位。然后是用上千度以上的高温对模范进行陶化处理,最后再往模范上浇铸铜水便大功告成了。
黄帝第一次见到成型的我时,先是感到很吃惊,然后又是一脸难色。后来我才稍微摸清他的脾性,一般当他开心时,他脸上就会同时出现吃惊和为难的神情,这点,是让很多以面目表情丰富著称的戏伶都望尘莫及的。在他之前艰难战胜蚩尤时,他脸上也出现了这种表情,在他之后从我身上成功炼出仙丹,顺利实现“上骑龙垂胡髯”的长生梦时,我在地上看到逐渐升腾至云端成仙的他脸上又出现了这种神情。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他那让我捉摸不透的表情。
此后,他的表情经常在我面前出现。后来,禹令施黯铸其他八鼎,加上我,总共九鼎,搬至夏邑,象征着九州。再后来,秦国崛起,在搬运九鼎的过程中,不慎遗失的一鼎,就是我。这怪不得搬运的那些人,是我自己要跑的。我没想到,我的出现非但没有消弭战争,反而让很多人误以为只要拥有了鼎就能成为君王。更可笑的是,很多人借我之名是假,满足自己贪欲是真。在我消失之前,我曾砸死了那位大力士秦武王。每次想到这,我的眼前都会重现这位明明全身筋骨已断,却还装成没事人似的大力士,看到他满脸大汗强行在臣下面前抖威风我就会忍不住乐出声。这是我单调的地下生涯仅有的乐趣。
或许这也是我此生唯一做过的好事了吧。
看着没走几步就重重摔倒在地的秦武王,我不禁抬起了头,似乎在朦胧的云里又看见了那张似笑非笑,似气非气的脸,我浑身一觳觫,再抬眼看时,云里分明什么都没有,只有卫士护驾的喊声久久地回荡在耳畔。
我有一点需要补充,其实我最开始的作用很可能只是拿来蒸煮食物而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性质就变了。或许从黄帝日渐苍老的那刻开始,又或者从人类以为成功战胜大自然的那天开始,反正,我后来就没再用来蒸羊羔……蒸鹿尾儿……卤煮寒鸦儿了。我被用来炼仙丹了。我不知道黄帝真是吃了从我身上炼的丹药成了仙还是用了障眼法欺骗了世人。但即使黄帝升天果真是一出谎言,人们还是愿意相信并设法让后人也深信不疑的。即便没有,也会虚构出另外一个替天行道、在炼丹炉里练就火眼金睛的神话人物。有时候,世人需要这样的精神鸦片麻痹自己。但说来好玩的是,这样的精神图腾最后往往会变味:最开始替他们声张正义的是这类人,最后剥削统治他们的同样是这类人。
炼丹,分为炼制内丹和外丹,前者本指在丹炉中烧炼矿物质以制造仙丹,其后有人以人体拟作炉鼎,用以修炼精气神;后者指通过各种秘法烧炼丹药,用来服食,或直接服食某些芝草,以点化自身阴质,使之化为阳气。后人经过数个世纪的炼丹,意外从丹炉里发现了一种“发火的药”,即火药。但可惜的是,华夏后裔通常用火药制作烟火爆竹,装点操办黑白喜事时的门面。这种死要面子的做法后来在洋人的坚船利炮面前可没少吃苦头。这些事在我长眠地下时可是一点都不知道,还是辗转于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通过别的出土文物或是那些巧舌如簧的导游口中得知的。
它们或他们的话让我想起了地下那些不见天日的岁月。我的记忆始于黄帝锻造我那天,终于秦武王之死这刻。黄帝之前的事我一概不知,秦武王之后的事我也不清楚。虽然我在地下生活了好几千年,但我的记忆只有这短暂的数百年。还是后来在博物馆的日子里,我才续上了其余时间里所发生的事,这才稍稍让自己看上去真的如活了几千年一样的老怪物那般厚重、沧桑。
在它们的讲述中,让我知道了那些运载大理石的民夫是怎么回事,更让我知道了后来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那段漫长的历史,却丝毫没有损失,因为历史看上去好像是在变化,是在进步,但实则一直在原地踏步,变化和进步的只是一些器物。而人,掌管器物的人类却始终没变。只不过不同的是,他们打架的方式有所变化而已,最开始是用削尖的木头,然后是钝了的刀,最后是枪炮。
随着打架方式的改变,人们的道德观也相继提高。这体现在强者每次战胜弱者所摆出的姿态上,而弱者只能被迫接受强者所施加的道德。强者才有道德,弱者只有屈从。此外,审美观念也有所变化,只要看看现在的人是如何崇尚纤瘦的,就能大概知道古人是怎么向往肥胖的。这在字画、建筑等一些艺术品上也有所体现。
在他们的讲述中,我才知道我生活的那段历史居然和他们的讲述有如此大的出入。这本该属于我的记忆,却在他们故弄玄虚、添油加醋中变了味。他们说:“我的出现是用来洗澡的。”只不过没有控制好火候,将洗澡变成了蒸煮,并提到了一些大无畏敢为天下先的勇士。他们说:“我还能用来防雷。”依据是在我生活的时代,雷电经常劈死人,为此发明了鼎,人只要躲在鼎下,就能有效避雷。“这比美国的富兰克林用风筝引雷领先了数千年”。一字之差,避雷变成了引雷,同样是一字之别,坏事变成了好事。我后来才发现,本该用来反思的历史,却多了一股莫名的优越感,充斥于印刷品上的各种对比性的表述更是让我看了直摇头。
从那以后,我就不喜欢听他们说话了。我本来在地下生活得好好的,非要把我挖起来。我知道他们不是真的爱我,而是我能提升他们虚假的荣誉感。他们把我挖出来后,连我的身世都还没搞清楚就急急让我在世界各地展览。在他们的印象里,鼎的作用已经被研究得很透彻了,不就是象征权力嘛。还真不是,象征权力是后人的附会,我只是一个用来蒸煮食物的器皿而已,就跟你们现在做饭所需的锅一样。把锅当成权力的象征,岂不让人笑掉大牙。但人类做出贻笑大方的事说实话可真不少,不仅用锅象征权力,最后甚至还发明出在石头上刻字,以此宣示皇权。
每当遇到让我困惑的事时,我都会想起黄帝。这位把我制造出来最后又抛弃我的人,如果有机会见到他,我倒要问问他为什么要制造一口锅来蒙蔽愚蠢的世人?在我还深埋地下时,睡梦中他的表情都是喜怒参半的,当我见到几千年后的阳光时,他的表情就只剩下嘲讽了。我在地下睡得很安稳,但很奇怪,有时候安稳的日子能保持三百年左右,有时候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后来我才知道,地下的安稳来源于地上的和平,地下的动乱来自地上的战争。如果能提前知晓这个规律,或许我会有效利用那些安稳的岁月,这样我就不会在动乱的年月里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了。每当睡安稳觉时,我总喜欢鼎口往上,鼎脚向下,就像我早年生活在地上时那样,因为这样可以让我能听到太阳升起的声音,还能偶尔聆听到风中的鸟鸣声。当我鼎口下罩,鼎脚上翘时,就是我失眠的预兆。
每当这时,我就会把自己包裹起来,抵御来自地上那些刀枪剑戟碰撞发出的刺耳声。这些都还好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地下也打起了雷,爆发了山洪,我是说地上的刀枪剑戟变成了枪炮坦克。这些一会儿像放鞭炮,一会儿又像刮头骨的声音惹得我火大。当那个白天响起两阵鸡啼时,我就知道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没过几天,我发现我的眼前突然多出一把锄头。就是这把锄地的锄头意外发现了我的踪影。这把锄头的主人喜极而泣,广而告之,终于告别了持续数代的农民身份,用上面褒奖的奖金进城做起了生意,不久后顺利成为了城里人。而我则被一台庞大的起重机提了起来,那天是我埋在土里几千年以来第一次看到阳光。我哭了,我的热泪一个劲地顺着鼎身往下流,我看到很多人把我围住了,他们的装饰可奇怪了,这要换在我生活的那个时代,统统都会被押出去砍头。我还没看清楚千年后的阳光长什么样子,就有人用一层锡纸把我包住了,据说为了保护我,不让我在地上被氧化。几十年前,有人挖了一个皇帝陵墓,那些陪葬品甫一出土就在阳光下化成了灰烬。从那以后,人们就停止了公开的挖墓行为,只有一些非法盗墓分子还活跃在一些不为人知的角落。
很多人都说,技术不过关时就不要挖掘文物,留待后人发掘。这话的意思是留点老祖宗的遗物给后人摆谱。从这点来说,挖与不挖都是没有区别的,挖了会损坏,不挖又见不到,损坏和见不到某种程度都是再见的意思。当然,那些没挖掘出的文物还是能安慰人们的心理的,就像暂时被冻结的银行帐号,假以时日,户头里的钱还是能用的,就是不知道是自己用呢,还是被别人用。
好在我很争气,出土后外貌没有多少变化,还是这么英俊,光滑细腻。但是求你们别老是盯着我的脸看好不好,也要关注关注我的内心呀。他们用放大镜把我全身照了一遍后就匆匆下了结论:鼎;作用:威慑天下。得知这个结果,我真是百口莫辨,没办法,只好让他们把我运进博物馆,让更多人来参观我英俊的外表,曲解我的初心。
我从出土那天就很快适应了阳光,我后来才知道有四个滚动的圆圈的怪物原来叫车。我从土里被搬到了车上,透过薄薄的锡纸,发现这个地方和我当年逃跑的地方不太一样,我当年也是在车上,在马车上,和其余八鼎,我趁着押运我的士兵不注意,偷偷从车上滚了下来,最后落到了一条河里。由于体重的原因,我没有被河水冲走,而是嵌在了淤泥里,久而久之,我渐渐听不到流水声了。我越陷越深,最后完全被埋在了地下。后来听说那些始终没发现少了一鼎的士兵由于算数不好集体被秦王咔嚓了。我在一条河里把自己深埋,最后却在一块地里回到地面,可见,这些年来,地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以至于我有种刚诞生于世的恍惚感。就像婴儿第一次见到这个世界,一切都是新奇的。
在去往博物馆的那天,我还是坐在车里。这种车密不透风,只有透过车窗才能看到外面的景物。就是我想跳车也办不到了。我听到车发出巨大的喇叭声响,就像我在地下有时听到的那样,我看到车外围了很多人,就和战场上的士兵一样多。我不知道这是要把我运到哪,刚开始,我以为真是又发生战争了,战争时,一般都有鼓声提振士气,难道在这个我感到陌生的年代,提振士气改成敲鼎了?最后我才发现不是,他们把我搬进了一座看上去透明实则围得密不透风的房子,即是他们口中提到的博物馆。在博物馆里,我被罩在一块玻璃内,参观我的人站在玻璃外对我指手画脚,窃窃私语。
我的身边有一张说明书,上面写有我的名字,籍贯以及用处。“别信,都是假的,我就是一个用来做饭的锅。”我很着急,冲着他们跺脚。每天进馆参观我的人很多,为此有些小伙伴不乐意了。它们在我到来之前,一直都是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受到的关注也最多。它们以为我和它们一样虚荣,喜欢像猴子露出红屁股那样吸引别人的目光,我才不屑,我生活在地下数千年,什么时候在乎过别人的目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我一直生活在与世无争的地下,但地面上关于我的传说却从未断过。
“你们成吗?”我说。
“你这傻大个,别这么嚣张,迟早把你给劈了。”说这话的是一把斧子。据说历史可追溯至上古时期。不过看它的样子,别说劈我了,就连劈毛都不行。
“大哥,消消气。”一把古扇支开了扇翼,给那把破斧煽风点火。
“再废话凿你一个大窟窿。”一个锤子也插上了嘴。
我没敢再吱声,一把斧子还好,要是加个锤子,可就难说了。要知道,斧子锤子加起来威力就大了,堪比古代的尚方宝剑。
突然间,我有点寂寞,我怀念在地下的岁月。这时,进来一个小孩,他指着我对身边那个女人说:“妈妈,这就是金庸在《鹿鼎记》里写的鼎吗?”
“鼎和鹿就是一个隐喻,象征天下。”她笑着说。
“妈妈,以后我也要逐鹿铸鼎。”小孩说。
“哈哈。”她乐了。
在我面前,有个可滚动播放纪录片的视频播放器。在这个播放器里,我知晓了很多事先并不知道的历史,也无意间得知我接下来会被送至世界各地,参加“谁是历史最长的出土文物?”的竞选比赛,看样子,人们对我最终能角逐冠军有十足的把握。其他参赛文物有刻在石头上的汉谟拉比法典、乌纳斯法老金字塔铭文,加上我,总共三件有望最终争夺冠军的文物,不仅要比三件文物的历史,还要比上面镌刻的文字含义。历史长,文字隽永的才会最终胜出。
但我对自己却没多大把握,因为其他两件文物的文字已经考据得差不多了,只有我身上的那行字还没有任何头绪。不过这又让研究我的那些考古学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因为只有深刻的文字,悠久的历史,才会考据得如此艰难。这么说来,或许我会成为优胜者。
去往国外参赛那天,同个博物馆里的其他文物都对我表示了祝贺,只有锤子斧头依旧冲我摆了一张臭脸。我没管它们。我很期待将要乘坐的飞机。在我那个年代,天上只有飞鸟,没有人能在天上飞,想都别想。墨子曾经发明过能载人的木鸢,那也只能飞几分钟而已,哪能像飞机似的,在天上飞这么长时间。在飞机上,我看到了大地原来不是方的,而是像有弧度的弓,地上的景物都变得很小,就是最明察秋毫的人,也无法分清哪个是人,哪个是蚂蚁。我从地下一下子来到天上,经历不可谓不波折,但我却生出一股苍凉之感,我知道古往今来,很多独上高楼的人最后都由于舍不得下来,导致跌得很惨。
飞机发出巨大的轰鸣声,我沉睡地下的后期,也曾听过类似的轰鸣声,与之相伴的是不间断的爆竹声。那些爆竹声在我头顶,在埋葬着我的地面上炸响。经常把我从睡梦中吓醒。如今我又亲耳听到了轰鸣声,只是等了很久,却没等来爆竹声,只有机舱内机师的说话声。一个在说:“这鸡巴破鼎比一机的乘客还重。”另一个说:“起码坠机了只有你我会丧命。”
“鸡巴,把这破鼎搞丢了,我们的命都不够赔的。”第一个机师说。
我仔细看着窗外,希图能在天上看到黄帝的身影。我以为他会来接我的。当初他之所以弃我独自升天,就在于我太重了,会拖累他。而现在,我终于也能飞起来了,可是他却没来。难道他还是怕我会拖累他,将他从天上拉回到人间吗?
两个机师还在不停地说我坏话。我很生气,用第三只足重重砸了下机身。机身擦亮了流云,发出四射的火花。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机师才将机身恢复平稳。他们不敢说话了,都闭上嘴认真地看着前方。我要让他们知道,开飞机也要保持好方向的,别以为天很大,就可以到处乱撞。万一撞到了鸟啊,云啊,雨啊,雷啊,损失谁来赔?
不知过了多久,飞机降落了。有一辆车从红地毯的那一头开到靠近机身的这头。有几个大力士模样的男人把我抬出机舱,然后拾级而下,小心地将我抬到车厢。这几个大力士,说实话,力气太小了,力气加起来还不及当年秦武王的一半。当年要不是看他不爽,我也不会砸死他了,现在这几个小力气我没心思砸他们,任由他们满脸自豪地在我身上证明他们的雄壮有力。
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我第一次看到五大洲,比所谓的九州大多了。如果当年我知道世界这么大,或许我会跳下一片海,借助强劲的季风周游世界。而不会像现在这样,被人用困在飞机上的这种方式窥探世界的全貌。
更不会像现在这样,被锁在黑白黄三种人的眼光里,动弹不得。他们挨个上前抚摸我,打量我,敲打我,每个人脸上都很激动。或许我的出现,会让他们改写人类的文明史。为什么人们总是把目光放到过去,决定人类命运走向的难道不是未来吗?可能过去才能让人类重拾信心吧。不可捉摸的未来只有天知道。
评选结果出来的那天,我做了一个梦。一个深沉又甜蜜的梦。我不知道其他两位选手,汉谟拉比法典和乌纳斯法老金字塔铭文那天有没有做梦。我见到他们的第一眼起,就觉得它们很眼熟。我想起来了,在很久很久以前,我诞生的时候,就见过它们。它们的样子和当年的变化很大,也许是在土里呆了太长时间,导致身上的肌肤发生了变化。我还记得当年我们玩得很要好,没想到数千年之后的今天,我们需要通过这种所谓的比赛来决出高低。
本来人类都是从一个地方来的,由于气候等原因,最终散落至世界各地,他们最开始带去了相同的语言,但随着岁月的嬗变,他们的发音方式和文字相差越来越大,以至于现在的人类已经认不出来了。我知道他们不可能考据出我们仨刻在身上的文字其实是一个意思,他们身后所属的国家,人民,以及所谓的历史都不会让他们这样做。
我不敢确定我现在说的话它们还能否听懂。我想了很久,最终没有开口说话。它们也没有说话。我滑入了梦境。在梦的尽头,我发现自己回到了首山。我还是掩埋在土里的黄铜,我的身子分布在首山的各个角落,在漆黑的地下通过身上橙黄的铜光互相打招呼。直到有一天,有人把这些黄铜挖了出来,把它们浇铸成一个鼎的样子。虽然此后结合在了一起,但我们却从此没再开口说一句话。变成鼎后不久,我又像黄铜时被埋在了地下。在漫长的掩埋生涯里,我遇到过很多发光的矿石,试图从这些如星辰般微弱的光芒中找寻自己的家人,但都一无所获。从那以后,我就只能靠做梦,回到我那个在首山的家。
我还记得黄帝在我身上刻的那句话:“民以食为天。”翻译成现代汉语是:“粮食即权力。”